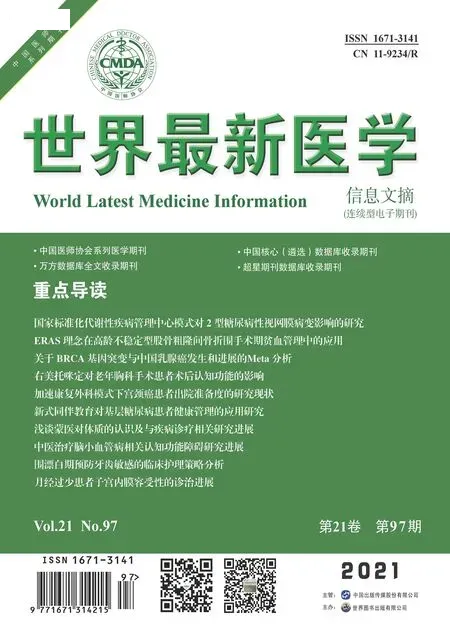于白莉教授辨治汗证经验
罗茂林,于白莉
(1.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0;2.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 成都 610000)
0 引言
汗证依据其出汗的时间、性质,一般要辨自汗、盗汗、绝汗、黄汗、战汗,在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提到了出汗的病因,《灵枢·五癃津液别》曰:“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素问·经脉别论》曰:“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说明气候变化、情绪波动以及饮食活动均会引发汗出异常。在《素问·阴阳别论》中提出:“阳加于阴谓之汗。”明代医家张景岳对其有注“阳言脉体,阴言脉位,汗液属阴而阳加于阴,阴气泄矣,故阳者多汗。”《内经讲义》解释为“阳脉之象倍受盛于阴脉之象,当有汗出”。则是对汗出机理的概括[2]。汗液的生成与阴阳二者密切相关,阳气维系着人体正常津液的贮存及其生理功能,阳守则阴藏,阳气动而加于津液,津液受气取汁变化而出,此为生理性的汗出,是人体阴平阳秘的标志之一,但是当阴阳之间的动态平衡遭到破坏时,阳气失守,阴津不藏,白昼人身阳气自升,阳脉倍盛,稍动则溱溱汗出,动辄益盛;夜寐表阳入于里,卫阳内扰营阴,故见汗液浸浸自出,此二者即自汗、盗汗均为病理性汗出,是阴阳失和的产物。后世医家在《内经》基础上对汗证治法有所发挥,姚洁琼等总结隋唐以来10 位著名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孙思邈、张景岳、王清任、叶天士、张元素、吴鞠通)治疗汗证的辩证、选方用药后认为这些著名医家治疗汗证主要治法为益气固表、滋阴清热;同时朱震亨认为“诸病多因痰而生”,认为汗证亦不例外,故喜用化痰利湿法治疗汗证,王清任则认为“不知血瘀亦能令人自汗、盗汗”,创造性地发展了通过活血化瘀治疗汗证的方法。
1 选方精当
1.1 柴胡桂枝汤
此方为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合方,《伤寒论·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发汗多,亡阳谵语者,不可下,与柴胡桂枝汤,和其营卫,以通津液,后自愈。”《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其原书主治太阳少阳并病,症见:汗出,发热恶寒,肢节痛,乏力,呕吐等临床表现。其汗出是因为太阳表证未愈,邪气与正气交争于半表半里之间,营卫不和,卫气不能固于表,营气不能守于里,固而汗出。桂枝汤是《伤寒论》的代表方之一,历代医家赞誉此方为张仲景“群方之冠”,桂枝汤本主“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曰中风”,其病机为“荣弱卫强”。卫行脉外,司固外开阖之权,营行脉中,濡养五脏六腑,两者密切配合,即营卫调和,若卫气失其固密之责,营不内守,疏泄于外,而发为汗证。其卫气失固、营不内守实为阳气失用,营阴外越。卫阳虽行脉外,却是从内所发,若卫气由内向外而发过于太阳经本位,则可成为郁表之风邪,风为阳邪,其性轻扬开泄,故见汗出,汗出多必泄脉内之阳,故郁表之阳愈盛,脉外风邪愈盛,则脉内之阳愈泄,汗出则愈不止,柴胡桂枝汤方中用桂枝助阳化气,合白芍一散一收,解肌发表而透邪外出,使表邪得解,里气安和,白芍、大枣收涩脉外之阳。同时利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疏利肝胆、调理气机的功效,两方合用,既可以和营卫,调阴阳,又能疏肝胆,利枢机。营卫和,气机畅,阴阳协调,则汗自止。有报道高建忠运用柴胡桂枝汤加龙骨、牡蛎治疗营卫不和所致出汗,疗效较好[3]。于教授多将本方用于治疗感冒迁延不愈,病程日久,外感余邪留恋所致的异常出汗,亦获良效。
1.2 藿朴夏苓汤
藿朴夏苓汤出自《医原》,原书记载:“邪在气分当分湿多,热多。湿多者……治法总以轻开肺气为主,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自化,即有兼邪,亦与之俱化。湿气弥漫,本无形质,宜用体轻而味辛淡者治之。”藿朴夏苓汤组成如下:藿香、厚朴、半夏、赤苓、杏仁、生苡仁、白蔻仁、通草、猪苓、淡豆豉、泽泻,该方所治汗症是因于湿热内停、蒸腾津液外出所致。严鸿志在《感证辑要》卷四中引作:“藿朴夏苓汤,以淡豆豉代丝通草,为具有理气化湿,疏表和中功效的湿存气分方。”藿朴夏苓汤融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3 种祛湿法为一方,同时配入了健脾醒胃、理气行滞之品,后世医家在原方的基础上加减化裁,集宣肺、运脾、利小便为一体,多治以湿邪为患,无论外感、内伤,兼寒、热、虚证,与肺、脾、肾、三焦相关的多种疾病亦广泛应用。《感证辑要》中此方以辛温芳香的藿香、淡豆豉与苦杏仁相配,开通上焦肺气,宣化湿浊,使邪气从表而解;半夏与白豆蔻有辛温开郁燥湿的作用,而白豆蔻还能芳香醒胃,厚朴苦温燥湿,行气降浊,半夏、白豆蔻、厚朴三药配伍,辛开苦降,燥湿降浊,宣畅中焦气机;茯苓、薏苡仁、猪苓、泽泻淡渗利湿,其中茯苓、薏苡仁还有健脾作用。此方辛宣芳化、辛开苦降、淡渗利湿3种祛湿法并用,同时配入了健脾醒胃、理气行滞之品,组方十分全面。于教授指出,湿邪为病,缠绵难愈,郁久化热,若以病因论,则湿为本,热为标,临床治疗该型汗证不能一味固涩收敛、滋阴清热,而应以利湿为主,湿去方可清热。藿朴夏苓汤集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三法于一方,是清热祛湿法的代表方剂之一,正如石芾南所言:“湿去气通,布津于外,自然汗解。”临床运用该方治疗汗证时尤重舌诊,舌体胖大或有齿痕舌,舌苔表现为白厚腻或微黄而腻等均是湿浊内阻确切证据。在治湿的同时,不能忽视健脾,脾为“仓禀之官”,主运化水湿,临床治疗湿热汗证当配党参、白术等健脾运脾之品。徐凯、朱尔春等在治疗湿热汗证时,亦多运用此法,往往效如桴鼓[4]。
1.3 青蒿鳖甲汤
本方主治温病后期、阴液已伤,而余邪深伏阴分,症见夜热早凉、热退无汗,舌红苔少,脉细数。青蒿鳖甲汤所治汗证为盗汗,盗汗多由温病后期,余热未尽,邪热深伏阴分,迫津外泄所致[5]。人体卫气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卫气夜入阴分鼓动阳邪,则两阳相搏,迫津外泄作汗,晨起卫气出阴分而行于阳,因“阳邪陷入阴中”,表无阳热之邪,故昼静身凉。吴鞠通谓“青蒿不能直入阴分,有鳖甲领之入,鳖甲不能独出阳分,有青蒿领之出。”此外,细生地清阴络之热,丹皮泻血中之伏火,知母佐鳖甲和青蒿清热养阴,全方共奏养阴清热,透邪外出之功。
1.4 当归六黄汤
当归六黄汤乃滋阴泻火之良方,被誉为治“盗汗之圣方也”,主治阴虚火旺所致的盗汗证,症见发热盗汗,面赤口干,心烦唇燥,大便干结,小便黄赤,舌红苔黄,脉数。朱丹溪认为“盗汗属血虚、阴虚”,主推当归六黄汤,给我们指出了本方所治汗证的病因病机。戴思恭《论治要诀》认为:“自汗多而血涸津脱者。”亦可用本方。《景岳全书》云:“阳证自汗或盗汗者,但察其脉证有火,或夜热烦渴,或便热喜冷之类,皆阳盛阴虚也,宜当归六黄汤为第一。” 指出阳盛火热所致自汗、盗汗亦可用本方。唐容川于《血证论》中指出:“阴阳两虚自汗盗汗可用当归六黄汤加附子。”可见无论自汗、盗汗均可使用本方。而青蒿鳖甲汤以夜热早凉,热退无汗为辨证要点,两者以此相区别,但王耀光治疗发热盗汗,症见午后低热、盗汗,多梦,口干,体倦乏力,手足心热,舌红少苔,脉细数,将两方合用,亦获良效[6]。当归六黄汤方中,当归、二地滋肾养血;芩、连、柏泄三焦之火,又能苦寒坚阴,黄芪益气固表实卫,俾阴复热退卫强则汗止。
2 重视脾胃
“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说明汗来源于水谷之精气,脾主运化水谷,胃主受纳水谷,脾胃为汗液的化生提供了基础。若先天禀赋不足,脾胃孱弱;久病年迈脾胃之气不足;饮食劳倦损伤脾胃,脾胃虚损失于运化,日久伤阳,阳虚则不能固摄津液,津液外泄而为汗。或脾虚不能运化水谷,以致停食生湿,郁而化热,湿热蒸腾津液外出而为汗。由此可见,脾胃功能失司与出汗亦有所关联。并且四川地区气候多湿,其民嗜辣,外湿与内湿阻碍气机,多损伤脾胃,使气化不利,气不布津外泄肌表而致汗出[7]。故于教授在运用前面所述四方治疗汗证的基础上,常合用益气健脾、除湿止泻之参苓白术散。参苓白术散是在四君子汤基础上加山药、莲子、白扁豆、薏苡仁、砂仁、桔梗而成,继承了四君子汤益气健脾的功效,同时加用补脾益气之山药、莲子,健脾除湿之扁豆、薏苡仁;醒脾行气之砂仁,使脾胃受纳运化的功能得以逐渐恢复;土为金之母,补脾土之气亦能起到补肺气的作用,方中用桔梗开宣肺气,通利水道,载诸药上行而成培土生金之功[8],肺与皮毛相表里,司汗孔开合,肺气充实,宣发功能正常,则汗的排泄适度。
3 验案举隅
蔡×,男,31 岁,于2019 年8 月24 日初诊,患者1 月前不明原因出现汗出偏多,疲倦乏力,未予治疗,刻下症见:多汗,以头面为甚,疲倦乏力,头晕,耳鸣,口干不欲饮,无恶寒发热,纳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微黄腻,脉滑。中医诊断:汗证;证属湿热内阻。方以藿朴夏苓汤加减:广藿香15g 姜厚朴15g法半夏15g 茯苓15g 豆蔻15g 炒白扁豆15g 建曲15g 麸炒白术15g 陈皮15g 荷叶15g 芦根30g 紫苏叶15g 浮小麦30g 山萸肉30g 酒黄芩15g 醋北柴胡10g 生黄芪30g 桑叶30g,水煎服,1 日3 次,每次100mL。
1 周后复诊,患者述汗出明显减少,疲乏、头晕、耳鸣减轻,在原方基础上加鸡血藤30g,继服4 剂,症状好转,基本恢复正常。
按:本案因患者舌苔微黄腻,且有口干不欲饮等湿热内阻的症状,故诊断为湿热汗证,湿邪内阻,郁久化热,湿热蒸腾津液外出则为汗;脾主四肢,湿邪困脾,则脾不能将水谷精微输布营养周身,故见疲倦乏力;湿热内阻,津液不能上承于口,则见口干不欲饮;湿热上扰清窍则见头晕、耳鸣。于教授运用藿朴夏苓汤加减,方中藿香、豆蔻、厚朴、紫苏芳香化湿,使湿从表解,半夏、陈皮、茯苓燥湿化痰,黄芪、白扁豆、白术益气健脾化湿,柴胡、黄芩、荷叶、芦根清热养阴,浮小麦、山萸肉、桑叶收涩止汗以治标。全方重在利湿,兼清热养阴止汗,切中病机,标本兼顾,故收效甚好。
4 小结
于教授治疗汗证先别虚实阴阳,认为历代医家对汗证虽有不同的认识,但临证之时若能从阴阳虚实的层次上进行分辨、把握,对汗证进行正确的辨证,抓住主要病机,辨证施治,仍可以驾轻就熟,达到较好的疗效。辨证之法虽多,但仍应谨守整体观念谨熟阴阳,审机立法,方能提纲挈领,执简驭繁,切不可见实泻实、见虚补虚,无犯虚虚实实之戒。气虚不固者,予柴胡桂枝汤既可驱邪又能扶正,使邪去而不伤正。阴虚盗汗者,予青蒿鳖甲汤、当归六黄汤滋阴清热。湿热内阻,湿重于热者,予藿朴夏苓汤利湿清热。于教授指出,上述四方在临床治疗汗证时效果确切,应用广泛;但汗证的选方用药远不止这四种,故临床治疗汗证既要考虑辩证运用上述四方,但又不可拘泥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