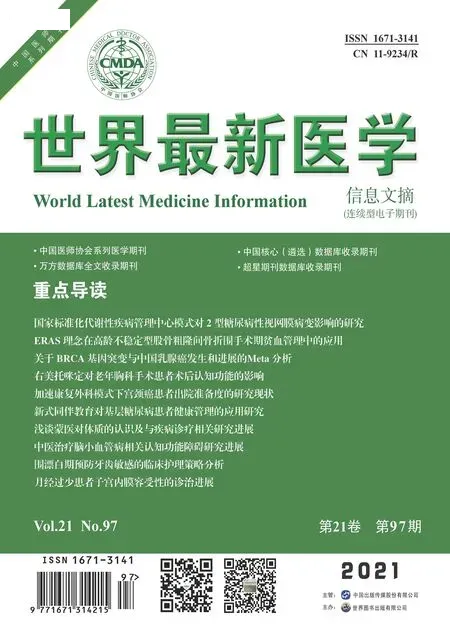卒中后抑郁脑网络重塑和症状学的研究进展
向丽红,袁建新*,王卓
(1.华北理工大学心理与精神卫生学院,河北 唐山 063210;2.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磁共振室,河北 唐山 063000)
0 引言
PSD 是指卒中事件发生后,持续两周及其以上的以抑郁症状群为主的情感障碍性疾病,约1/3 的卒中患者并发有PSD[1]。一项临床荟萃结果显示PSD 和全因死亡率(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的风险比为 1.59,但迄今为止的研究不足以确定PSD 与卒中复发之间的关联[2]。PSD 常以抑郁症的核心三联征为主,情绪低落、兴趣丧失和意志减退,可伴有睡眠障碍、过度焦虑、记忆力减退等症状[1]。PSD 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卒中部位、神经递质、免疫等方面,随着机计算机科学和功能影像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脑科学的提出,PSD 作为脑部疾病之一,脑网络学说逐渐兴起并快速发展[1]。人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多个神经元及其集群或者多个脑区相互连接成庞杂的结构网络,并通过相互作用完成脑的各种功能,我们称之为功能网络,结构网络和功能网络统称为脑网络,两者密不可分。目前关于PSD 的脑网络研究主要集中在默认网络(default mood network,DMN)、突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SN)、认知控制网络(cognitive control network,CCN)、情感网络(affective network,AN)等[3,4]。本文将着重对上述特定脑网络、多网络和全脑网络在PSD 中的重塑及其症状学变化进行综述。
1 局部脑网络的重塑
1.1 默认网络(DMN)
DMN 在静息状态下功能比较活跃,而在任务状态下功能受到抑制,它与内外环境的监测、情绪的处理、内省、思维认知的维持、思维记忆的提取等密切相关,研究表明,DMN 是抑郁症的重要神经病理机制[1,5]。该网络主要包括内侧前额叶皮层、后扣带皮层、楔前叶、双侧顶叶(包括角回)、双侧颞叶和海马等脑区[6]。Wang S 等[6]研究指出后扣带回皮层、颞顶叶交界处和内侧前额叶皮层是DMN 网络功能的关键脑区,并对这些脑区与特定的认知和健康状况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后扣带回皮层、颞顶叶交界处和内侧前额叶皮层激活与认知和健康相关的特定主题(如:决策和吸烟)相关,且三者共同支持多种认知功能,例如决策、记忆和意识。目前对抑郁症的脑成像研究表明,皮层下白质损伤会破坏与情绪相关的某些神经回路,从而导致对抑郁症的易感性,抑郁症脑功能的改变主要发生在前额叶皮层、前扣带回、杏仁核、腹侧纹状体、海马、岛叶、丘脑和基底神经节,前额叶皮层被认为在认知和情绪活动中起关键作用,这些大脑区域的功能异常可能会出现情感和认知障碍[5]。Hordacre B 等[7]分析卒中患者的卒中部位证实额叶、颞叶和顶叶区域与PSD 发生相关。Zhang XF等[8]利用功能磁共振对PSD 患者进行脑功能连接分析,发现左侧杏仁核与双侧楔前叶和右侧眶额叶的功能连接增加,且右侧杏仁核与右侧颞极、右侧直回、左侧眶额叶的功能连接也增加。Liang Y 等[9]应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PSD,结果显示PSD 患者的前额叶皮质和背外侧前额皮质、右侧眶额皮质、颞叶中部及下部皮质和下顶叶皮质之间的脑功能连接增加,其中左侧腹内侧前额皮质、双侧背内侧前额皮质最为明显。由此可以看出,上述研究中涉及到的脑区都是DMN 的重要脑区,这提示PSD 的发生发展与DMN 功能连接的改变密切相关。Vicentini J E 等[10]利用静息状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DMN 在卒中患者情绪处理的作用,研究表明:卒中后伴有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患者左侧顶下回和左侧基底核的功能连接增加,且贝克抑郁量表、贝克焦虑量表评分与DMN 功能连接之间的特定相关性表明,抑郁症状与左侧顶下回的功能连接增加相关,而焦虑症状与小脑、脑干和右侧额中回的功能连接增加相关,可见DMN 网络重构与PSD 患者过度焦虑、消极思维等抑郁症状相关。
1.2 突显网络(SN)
SN 主要由前扣带、腹侧前岛叶皮质、杏仁核、下丘脑、腹侧纹状体、丘脑和一些脑干核团等脑区组成,该网络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同条件的刺激,各脑区能被共同激活,这提示这些部位密切连接并形成一个特定的网络,共同参与一些脑功能的加工活动[11]。SN 参与人脑的高级认知加工功能,与个体的认知、情感和思维密切相关[12,13]。Shi Y 等[14]使用基于体素的形态测量学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PSD 患者,结果表明:PSD 患者前额叶皮层、边缘系统和运动皮层灰质体积减少,进一步对前扣带皮层进行种子分析,发现前额叶皮层、扣带回皮层和运动皮层的功能连接性大大降低,但与海马回、海马旁回、岛叶和杏仁核的功能连接性增加。这表明卒中事件降低了同侧大脑区域的兴奋性,PSD 可能通过额叶-边缘回路的大脑网络影响情绪。Zhang X F 等[8]利用功能磁共振研究PSD 患者SN,发现其网络中的杏仁核与脑岛皮层的功能连接增强,且这种网络重构与PSD 患者过度焦虑、负性思维等抑郁症状相关,Xu X 等[15]研究也证实SN 脑网络连接效率的改变与抑郁严重程度相关[15]。Balaev V 等[16]研究证实PSD 患者额中回和左侧角回的白质连接明显增强,且该连接的改变与抑郁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这也证明了Xu 等[15]研究的猜测,PSD 的严重程度与潜在白质的破坏程度呈正相关。Vansimaeys C 等[17]利用精神病理学中的网络模型对卒中后急性期抑郁症状进行网络分析,描述症状之间存在的动态联系,结果显示了两个独立的症状网络:(1)第一个网络涉及快感缺乏、疲劳、对自己的消极想法和悲伤,这表明快感缺乏预示后期疲劳和后期消极想法的激活;(2)第二个网络为悲观和集中注意力能力减弱,结果表明悲观预测后期悲观和后期集中能力减弱,一方面,快感缺乏在其网络其他症状的初始和渐进激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认知症状(消极思想和悲观主义)导致情绪恶化和注意力缺陷密切相关。由此可见,PSD 患者情绪和认知的调节与SN 功能密切相关。
1.3 认知控制网络(CCN)
CCN 主要由额叶和顶叶皮质脑区组成,具有处理各种任务中实施认知控制的功能,与执行功能密切相关[3,18]。Jaywant A 等[3]综合了PSD 和卒中后执行功能障碍的神经影像改变发现两者额顶叶功能连接减少。Sotelo MR 等[19]通过间接结构连接识别卒中后脑网络的变化,反向论证卒中后患者脑网络的重构,这也为我们提供一种新思路,利用功能磁共振,分析各个脑区域之间的连接性,建立预测模型,为PSD的诊断提供临床指导。Kaiser EE 等[20]研究通过功能磁共振参数预测缺血性卒中猪模型中的功能缺损情况,对临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应用上述研究方法,Jaywant A 等[3]研究证实卒中后额叶和顶叶、同侧皮层下区域和双侧小脑的间接连通性显著降低,加入回归分析时,间接连通性降低的脑白质体积使图像参数与上肢运动障碍之间的关联性增强,这表明这些变化与上肢运动的执行功能障碍相关。Hordacre B[21]等研究也证实卒中患者的预后与同侧额顶网络的功能连接正相关。Egorova N 等[18]研究证实PSD 患者左侧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和右侧缘上回的功能连接度明显降低。DLPFC 和右侧缘上回是CCN 在额叶及顶叶的关键脑区,同时研究提示CCN 联系下降程度与PSD 患者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呈正相关。Haleem[22]等研究也证实了抑郁和DLPFC 变化之间的正相关关系。Auwal BH 等[23]通过整理卒中后并发疼痛和抑郁的患者病例报告发现,DLPFC的重复经颅直流电刺激可以改善个体卒中后疼痛和抑郁症状。CCN 与其他大脑网络的高度连接,与很多心理疾病密切相关。它能以目标导向的方式调节临床症状,形成一种反馈机制,作为一种神经生物学媒介调节与情绪相关的症状[24,25]。Tozzi L 等[25]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通过Go-NoGo 任务研究抑郁患者,证实CCN 与情绪症状调节相关。Auwal BH 等[23]通过整理卒中后并发疼痛和抑郁的患者病例报告发现,疼痛、抑郁、睡眠障碍、肢体无力、虚弱等抑郁性症状群也可以通过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改善脑网络功能得到积极反馈。
1.4 情感网络(AN)
AN 由杏仁核、前扣带皮层、海马、下丘脑、脑岛、眶额皮质和伏隔核等结构组成,参与情绪处理和介导动机行为[4,26]。Zuberer A 等[27]研究证明情绪识别与加工与双侧颞上回、颞中回、杏仁核、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楔前叶以及右后丘脑等脑区相关,情绪识别与加工有障碍的患者右侧颞上回、颞中回和右侧后丘脑相邻的皮层中低激活。Gulyaeva NV 等[28]研究证实腹侧海马病变与PSD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ShishkinaGT 等[29]研究通过基因组学证实海马参与人脑认知和情绪调节等高级神经活动。KaiserRH 等[30]使用功能磁共振来评估额叶-脑岛网络功能与青少年情绪健康的关系,结果表明脑岛和额顶网络的外侧前额叶区域之间的低连通性与预期的情绪健康有关。Xu X 等[15]用扩散张量成像构建结构脑网络并进行图论分析,计算并比较了PSD 和非PSD 患者的网络测量值及功能评估和网络测量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PSD 患者的整体和局部效率提高,局部连接中断的区域主要位于认知和边缘系统区域,包括额上回、额中回、扣带后回、颞中回和杏仁核,这些部位都与情绪障碍和高级认知功能有关。在该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PSD 患者的全球和区域网络测量值与PSD 的严重程度相关,抑郁水平与颞上回、楔前叶、海马、杏仁核、岛叶和丘脑等区域的区域网络测量值之间存在正相关,这可能与杏仁核、海马体、岛叶和丘脑构成了边缘-皮质-纹状体-苍白球-丘脑回路密切相关,这个特殊的回路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回路中的微观结构变化可能导致PSD患者的区域相互作用不断增强[15,31,32]。因此,上述功能和结构连接分析的研究表明额叶-边缘系统的异常区域连接,这背后的神经解剖学基础可能包括广泛的联系中断和皮质-纹状体-苍白球-丘脑回路的损伤,这些特定脑区正是AN 的关键脑区,最终导致AN 重塑,且抑郁症状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与AN 的重塑密切相关。
2 多网络和全脑网络重塑
在对PSD 患者脑网络的研究中发现:PSD 脑网络的改变不仅仅存在于单个特定局部脑网络,而且可在多个脑网络同时发生重塑[17]。这些特定脑网络常常在解剖结构上相互重叠,如海马、顶叶既是DMN 的脑区也是CCN 的脑区,也是AN 的重要组成区域,或通过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功能连接而相互发生影响。Balaev V 等[16]应用功能磁共振研究PSD 患者脑功能连接后发现:PSD 患者DMN 和SN 均发生改变,其中DMN和SN 间的功能连接增强,且这种连接的强度与抑郁严重程度呈正相关。EgorovaN 等[18]综合分析了多个研究后得出结论,PSD 特定脑网络发生协同改变,并呈现以下特征:DMN 的功能连接下降、AN 的功能连接增加、CCN 的功能连接减弱。Jaywant A 等[3]综合了PSD 和卒中后执行功能障碍的神经影像学发现,CCN、SN 和DMN 的结构和功能改变与卒中后抑郁和执行功能障碍有关,并指出这三个脑网络相关性如下:(1)静息状态网络内内在功能连接的变化;(2)DMN、SN 与CCN之间的功能过度连接;(3)额顶叶功能连接的减少。此外,颅内的梗死病灶不仅可导致局部特定脑网络的改变,而且会引发整个脑网络发生重构。研究表明,人脑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small-world network)特征,确保信息在脑功能区域间以低能量成本和较短连接代价实现高效的传输与整合[33,34]。Xu X 等[15]应用功能磁共振研究PSD 患者脑网络也发现PSD 的脑网络连接整体和局部效率均发生变化,呈现为局部网络连接高度集群化、全脑网络连接冗余化,且这种整体和局部连接效率的改变与抑郁严重程度相关。本地效率表示本地集群的数量,反映功能隔离,网络隔离的增加与抑郁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尽管大多数研究表明更高的网络隔离保证了高网络容错性,但结果可以间接证明增加的网络隔离并不总是积极的,从经济角度来看,大脑连接的构建和运行成本很高,因此过高的网络隔离可能会增加大脑的整体布线成本[15]。Sun C 等[35]基于图论分析PSD 患者的脑电图数据,结果显示:PSD 患者的半球间连接显著减弱,顶枕叶和额叶之间的联系减弱,聚类系数较低,且与PSD 严重程度正相关。Hong W 等[36]也对PSD患者大脑结构变化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PSD 患者左侧额中回的灰质体积减少,前额叶与边缘系统连接减少,此外61%左侧额下回和39%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变化与PSD 的躯体与情感症状有关,这可能与脑损伤后额边缘网络受损有关。
3 小结与展望
卒中局部病变导致脑功能损害,为代偿局部脑功能的减退,局部脑网络发生重构,而局部脑网络的重构进一步引发了全脑脑网络拓扑结构的重塑,最终导致脑功能异常,出现临床抑郁症状,即发生了PSD[34]。在现有的多模态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由于扫描设备、参数设置、影像图像处理过程以及影像特征的筛选和提取不尽相同,从而影响其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成像标准。“影像组学”这一术语由Lambin 等[37]于2012 年首次提出,是指分析影像学数据,以提高疾病的诊断、预测和预测精度的技术集合,主要包括:图像获取、病灶分割、特征提取和筛选、模型构建和临床信息解析等[37,38]。影像组学的发展通过对图像数据特征的深层次挖掘,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重要参考指标。未来在PSD脑网络影像组学研究的基础上力求与PSD 临床症状、相关生物学标志物及基因表型等相结合,探究PSD 脑网络影像组学与PSD 临床症状及转归之间的关系,实现对PSD 的精准诊疗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