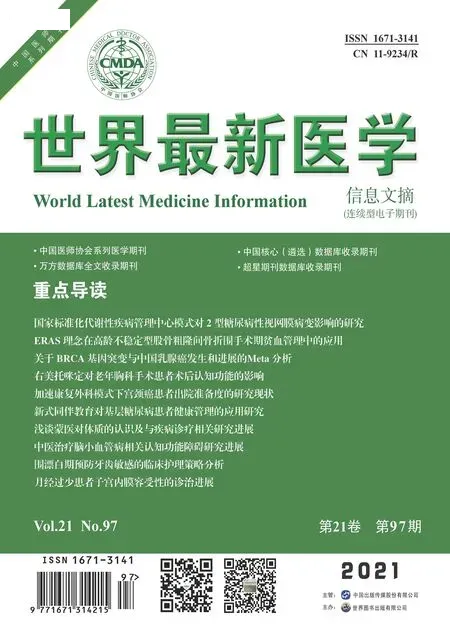中医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研究进展
张陆昕,唐学贵
(1.川北医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7;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肛肠科,四川 南充 637000)
0 引言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又称非特异性UC,是指一种病因暂不明确的、病位主要局限于大肠黏膜及黏膜下层的非特异性炎症,现代医家多将其归因于饮食不洁、情志因素等,临床上以腹痛、腹泻、里急后重、黏液脓血便为主要表现,伴随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甚至有研究表明,溃疡性结肠炎按照“炎症-不典型增生-癌症”的规律演进,癌变概率约为5%~10%。由于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我国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本文研究将从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中医内治法、中医外治法四个方面将近年来中医药治疗UC 的进展综述如下。
1 病因病机
祖国医学中没有UC 所对应的特定名称,中医内科学根据其临床表现多将UC 归于“久痢”“休息痢”“肠澼”。将慢性持续性的UC 对应为“久痢”,发作期和缓解期交替出现的UC对应为“休息痢”,《素问·太阴阳明篇》:“饮食不节,起居不时,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满闭塞,下为飨泻,久为肠澼。”中医认为本病主要由外感邪气、饮食不当、情志损伤、素体脾虚等因素引起,病位属于大肠,但与肝、脾、肺、肾密切相关。目前,大多数现代医家都认为脾虚是UC 发病的根本,在此研究基础上,王新月[1]认为,情志失调为UC患者发病的主要因素,情志的剧变会影响肝脾肺三脏的生理系统功能,肝失疏泄、肺失宣肃、脾失健运,大肠传导失司,湿热蕴结于肠,发为溃疡;国医大师徐景藩[2]认为本病大便有血,痛位固定,故病及血,血色由鲜红转为暗红,血热、血瘀为两大重要病理因素。李京津[3]等认为李东垣的“阴火理论”与UC 病机有相通之处,脾胃元气亏虚为基础,逐渐发展为气机升降失常,阴火内生,最后浊瘀酿毒,损伤肠道。
2 辨证论治
解赢[4]通过检索统计近二十年中医药治疗UC 的文献,得出UC 中医证型前六位分别为大肠湿热(25.1%)、湿热内蕴(15.4%)、脾虚湿蕴(14.6%)、脾胃虚弱(10.5%)、肝郁脾虚(9.7%)、脾虚湿热(7.1%)。刘明峰[5]将138 名UC 患者的主要症状与肠镜检查工作报告进行数据分析,按频次分为大肠湿热证〉脾胃气虚证〉脾肾阳虚证〉血瘀肠络证〉肝郁脾虚证〉阴血亏虚证。任炎等[6]总结其他专家经验后,运用病症结合分型模式,将UC 分为湿热蕴结证、脾气虚弱证、脾虚湿热证三个主要证型,阳虚、阴虚、血瘀为兼证。
3 中医内治
国医大师徐景藩[7]认为本病活动期患者大便有血,血色由鲜红转为暗红,故病及血热、血瘀,在治法中必须坚持凉血行瘀之方药,如侧柏叶、地榆、丹皮、槐花,另外根据临床经验发现,常规使用凉血药效果欠佳者,加入紫草后常能明显改善症状;徐景藩教授还认为下利病久食少,多属于疏泄太过导致肝脾不和,而非疏泄不及,应敛柔治之,如乌梅、木瓜与白芍、甘草,酸甘相伍;而腹鸣、腹痛、下利有血,为肠中有“风”,加用蝉蜕、僵蚕、防风,可以祛风、抗过敏。
梅笑玲教授[8]提出“重疏导 慎涩敛”的治疗原则,认为本病多为虚实夹杂,缓解期以正虚为主,仍有湿热瘀血等实邪内伏,故只用敛涩之方药则会使邪气滞留,蕴结为毒。梅笑玲教授认为应当重用疏导之法,以化湿、清热、祛瘀、解毒为主要疗法,或大量疏导中加入少量敛涩之品,使得邪去而不伤正。在长期的临床用药中,梅笑玲教授总结出了对症方药--复方菊花散,其基本药物组成:菊花12g,黄芩12g,蒲黄9g,白及12g,白术12g,马齿苋9g,临床疗效甚好。
王长洪教授[9]认为UC 缓解期以脾肾阳虚为基础,湿热毒疲等邪气内伏,故病程缠绵、日久,正虚邪恋、正邪相争贯穿疾病始终,提出了针对UC 缓解期的“健脾温肾、清化湿毒、涩肠敛疮”的治疗大法,并自创愈溃方(淡附片、青黛、肉桂、苦参、白术、苍术、仙鹤草、地榆、甘草),随兼证加减。既往应用温阳、清热等治法临床效果不佳或者UC 病灶较高者加用莪术、红花、川芎,临床疗效显著,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盛益华等[10]以“肺与大肠相表里”为基础,认为UC 日久耗气,损伤肺的生理功能,水道失调,痰饮内停,认为治疗时应佐以补肺之品,以提高治愈率,降低复发率。
罗云坚教授[11]首创“伏毒致病”理论,认为邪毒内伏于手阳明大肠经及足厥阴肝经,伏而不发,待正气衰弱之时,由外感邪气触发,则久伏之毒由里外泄,损伤肠道;治疗上提出祛除伏毒应贯穿病程始终。对于活动期大肠湿热毒邪内结的患者,常以基础方:白头翁15g,牡丹皮15g,黄连9g,薏苡仁30g,白花蛇舌草30g,木香(后下)12g,乌药12g,黄芪20g,临床疗效比较理想。
4 中医外治
4.1 中药灌肠、中药结肠滴注、中药栓剂纳肛
由直肠直接给药,避免了胃肠道消化液及酶类对药效破坏,以及药物刺激产生的胃肠道反应保证了药物浓度,获得了更好的疗效。戴高中等[12]提出了白头翁汤加减(白头翁15g,秦皮10g,白及10g,煅石膏10g,地榆10g,黄柏10g,黄连3g,红藤10g,乳香10g,没药10g,三七粉3g,槐花5g,儿茶10g,五倍子10g,枯矾10g,生黄芪20g,人中白10g)灌肠能有效抑制大肠湿热型左半结肠型UC 的NF-KB mRNA 的合成,从而达到抑制UC 患者的炎症反应的目的。董雪莲等[13]提出不同时辰中药灌肠对UC 的治疗效果不同。卯时、申时、亥时分别对应大肠经、小肠经、三焦经经气旺盛之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得出卯时中药灌肠相较于申时中药灌肠、亥时中药灌肠,不仅在治疗有效率上有显著差异(卯时92.5%、申时80.0%、亥时77.5%),而且在降低影响UC 的细胞因子(Hs-CRP、IL-6、TNF-α)水平上卯时中药灌肠也有显著优势。隋楠等[14]通过比较气药灌肠法与传统灌肠法治疗UC 的疗效得出,气药灌肠可以利用不同的气压推进灌肠药液,使灌肠药液能够达到近端结肠病灶,治疗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灌肠法。中药结肠滴注与中药灌肠相比,具有药物保留时间长、容易被患者接受的优势,而中药栓剂较前两者而言操作更加简单,常用的有野菊花栓等。
4.2 针刺
针刺是在经络学说的指导下,通过辨证论治选取特定的腧穴作为治疗靶向,不同的针刺手法作为具体操作技巧,辅以现代科学仪器,达到治疗研究目的。王宝琛等[15]选取足三里、天枢、上巨虚为治疗UC 的主穴,再随证配穴加减,3 个疗程后结果显示52 例UC 患者中痊愈22 例(42.3%),显效23例(44.2%),好转4 例(7.7%),无效3 例(5.8%),总有效率为94.2%。阚成国等[16]采用电火针的操作方法,选定天枢、关元、中脘、内关、足三里作为主穴,在根据不同的辨证分型辅以配穴,治疗UC54 例,结果显示近期治愈37 例,有效ll 例,无效6 例,总有效率88.9%。郭保君等[17]通过临床研究发现,采用腧募配穴法,背腧穴取肾腧、脾腧、胃腧、大肠腧,募穴取天枢(大肠经募穴)、中脘(胃经募穴)、关元(小肠募穴),配合隔姜灸,其肠镜检查和病理检查结果均优于单纯西药组,为脾肾阳虚型UC 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
4.3 艾灸
艾灸集合了中药与针刺的优点,通过选取不同的艾灸穴位、操作方法以及药物组成,使之具有不良反应小、复发率低及远期疗效好的优势。常玉洁,吴艳红等[18]选取神阙八阵穴(以神阙穴至关元穴长度为半径作圆周,以巴登分分圆周而形成八个特殊部位),以关元穴为起始点顺时针艾灸,结果表示明显降低了血清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王晓梅[19]提出艾灸可能是通过下调TLR4 和TNF-α 表达介导的级联反应达到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目的。李国娜等[20]通过分析研究近十年艾灸治疗腹泻的规律总结得出,艾灸常用来治疗慢性腹泻,多采用温和灸、隔物灸,穴位主要选取天枢、神阙、关元、足三里,常用天枢配合关元来治疗,临床疗效较好。
5 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具有重要的代谢、肠道保护及塑造黏膜免疫系统的功能,此外,还能通过产生抗菌因子和定殖抗性、拮抗营养物质和受体,来阻止潜在致病菌的产生。研究表明[21],遗传易感人群对肠道菌群的黏膜免疫反应失调导致肠道炎症可能是 UC 难治愈原因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着手于中医药调节肠道菌群以治疗UC 的研究。
就中药单体而言,小檗碱(BBR)是一种从黄连、黄柏中提取出的生物碱,研究表明[22],BBR 可以缓解UC 并调节Treg/Th17 平衡,还可以干扰 Bacteroides(拟杆菌属),Eubacterium (真菌属) 和Desulfovibrio (脱硫弧菌属) 的相对丰度。丹酚酸 A(SAA)是从丹参中提取的一种活性酚酸,WANG 等[23]研究发现丹酚酸A 对于提高DSS 诱导的UC 大鼠模型肠道Verrucomicrobia(疣微菌门)、Akkermansia(艾克曼菌)、Bacillus(芽孢杆菌)、Blautia(布劳特氏菌属)、Firmicute(厚壁菌门)、Lactobacillus(乳酸杆菌) 及Lachnoclostridium 的相关丰度,而减少Ruminiclostridium、Roseburia(罗氏菌属) 及Bacteroidete(拟杆菌属) 的相关丰度有着很好的效果。氧化苦参碱(OMT)是一种从苦参中提取的天然的喹喔啉生物碱,氧化苦参碱可增加DSS 诱导的UC 小鼠模型中 Bacteroidetes(拟杆菌属) 和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减少Coprobacillus(粪芽孢菌属)、Clostridium(梭菌属)、Firmicutes(厚壁菌 门)、Paraprevotella、Parabacte-roides、Dehalobacterium、Ruminococcus(瘤胃球菌属) 及Staphylococcus(葡萄球菌属)的相对丰度。此外,OMT 还可改善肠屏障功能及抑制 TLR4-MyD88-NF-KBTL 信号通路[24]。
就中药方剂而言,许多临床研究表明大黄牡丹汤、黄连解毒汤等可以改善 UC 患者肠道菌群紊乱。大黄牡丹汤主要由大黄、牡丹皮、桃仁、芒硝、冬瓜仁构成,具有泻热除瘀,消痈散结之功。Luo 等[25]研究发现大黄牡丹汤可增加 DSS 诱导的 UC 小鼠肠道Acti-nobacteria(放线菌门)及Firmicutes(厚壁菌门) 的相对丰度,而减少Bacteroidetes(拟杆菌门) 及Proteobacteria(变形菌门) 的相对丰度。此外,大黄牡丹汤还可增加短链脂肪酸(SCFA) 的含量及Treg/Th17 的比例。黄连解毒汤的成分为黄连、黄柏、栀子及黄芩,研究发现黄连解毒汤可提高DSS 诱导的UC 小鼠肠道Oscillibacter(颤杆菌克属)、Desulfovibrio(脱硫弧菌属)、Lactoba-cillus(乳酸杆菌)、Clostridium(梭菌属) 及Roseburia(罗氏菌属) 的相对丰度,降低Escherichia(埃希氏菌属)、Odoribact-er、Anaeroplasma(厌氧支原体属)、Helicobacter (螺杆菌属)、Acinetobacter(不动杆菌属)、Alloprevotella、Eubacterium(真杆菌属)等的相对丰度[26]。
6 思考与展望
UC 是中西医公认的消化系统疑难病种,西医治疗UC 方法比较单一,一般采用抗感染、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等治疗,疗效尚且不能满意,且存在缓解期反复复发、糖皮质激素依赖或抵抗等问题。中医以整体理论为指导,采用内服与外治相结合,具有不良反应小、复发率较低等优势,但目前来说中医药治疗仍然缺乏完善的临床实验研究体系以及系统的治疗方案,希望在不断的探索与研究中,我们能早日攻破溃疡性结肠炎这一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