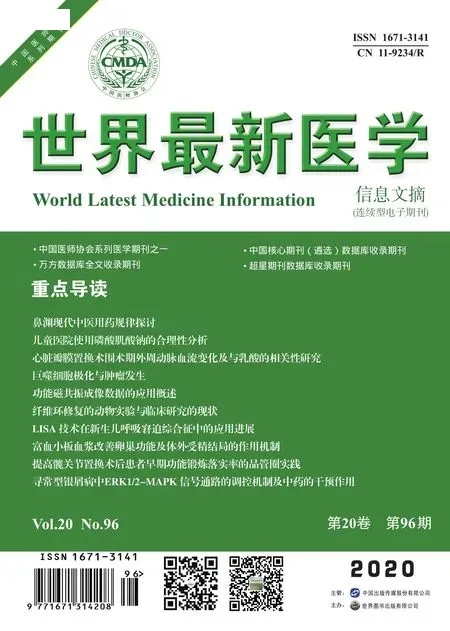巨噬细胞极化与肿瘤发生
张法达,高喜丹,庄庆春,何棣,苏衍萍,赵上*
(1.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院,山东 济南;2.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医学科学院)组胚教研室,山东 泰安)
0 引言
巨噬细胞形态多样,分布广泛,是人体免疫系统中重要的细胞群体,既参与固有免疫又参与特异性免疫,具有杀菌,吞噬,抗原呈递,分泌细胞因子等多种免疫功能。多样性和可塑性是单核巨噬细胞谱系细胞的标志。巨噬细胞的可塑性通过获得由特定组织(例如,肺泡巨噬细胞)和免疫微环境定向的独特形态和功能特性来证明。巨噬细胞受到IFNs,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影响与或IL-4/IL-13信号传导,巨噬细胞经历M1(经典)或M2(替代)激活,这代表了激活状态范围内连续的极端情况[1,2]。在机体内单核吞噬细胞的功能性偏斜发生在生理条件下(例如,个体形成和妊娠)或者在病理条件下(过敏性和慢性炎症,组织修复,感染和癌症)时发生。但是,在某些临床前和临床条件下,已观察到处于不同激活状态的巨噬细胞独特型或混合表型的共存,反应了巨噬细胞的动态变化和复杂的组织衍生信号[4]。本文就巨噬细胞极化和表型,巨噬细胞极化的分子机制,肿瘤相关巨噬细胞进行综述,为以巨噬细胞为中心的诊断和治疗策略提供基础[7]。
1 巨噬细胞的极化与表型
巨噬细胞良好的可塑性保证了其可以在不同的病理生理微环境中,受不同的细胞因子和微生物产物诱导下向不同的方向进行极化,巨噬细胞的极化是一个连续的状态,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是这一极化状态的两端[1,2]。且可以在不同的极化状态下进行转换。遗传学认为,不同极化方向的巨噬细胞在转录作用上也有不同,并且发现了Fizz 和YM-1两个极化相关基因[2]。
前期研究发现,在γ干扰素,脂多糖和TNF-α等细胞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巨噬细胞可以极化为具有宿主防御功能的经典活化型(Classically activated macrophages,M1)巨噬细胞。M1细胞具有IL-12hiIL-23hiIL-10lo表型;产生效应分子(活性氧和氮中间体)和炎性细胞因子(IL-1β,TNF,IL-6);作为诱导细胞和效应细胞参与Th1极化反应;并介导抗细胞内寄生虫和抗肿瘤反应。组织基质中的信号分子IL-10,IL-4,IL-13,TGF-β,糖皮质激素,凋亡细胞释放的分子和免疫复合物等也对单核巨噬细胞的极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这些信号诱导功能性表型与M2细胞具有分选特性的功能(例如,高甘露糖和清道夫受体表达)相似,但在趋化因子库方面与它们不同,我们称之为M2样细胞[5]。M2型巨噬细胞由Stein等人于1992年首次描述,则被认为参与抑制寄生虫和促进组织重塑和肿瘤进展。各种形式的M2巨噬细胞具有IL-12loIL-10hiIL-1decoyRhiIL-1RAhi表型[1,4],M2型巨噬细胞的这些变化是通过精氨酸酶途径实现的。M1-M2巨噬细胞的趋化因子表达谱也不同。M2细胞通常具有高水平的清道夫,甘露糖,半乳糖型受体和精氨酸代谢,即通过精氨酸酶转变为鸟氨酸和多胺的能力。分泌IL-4,TGF-β和M-CSF等细胞因子。通常,M2细胞参与极化的Th2反应。促进杀死和包裹寄生虫;分布在肿瘤组织, 促进肿瘤的发展,组织修复和重塑;并具有免疫调节功能。未成熟的骨髓抑制细胞具有与M2细胞相关的功能特性和转录谱。
极化的M1-M2巨噬细胞的表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体内和体外逆转[4,5]。此外,疾病的病理学变化通常与巨噬细胞激活的动态变化有关。尚不清楚这些开关的机制是否涉及循环前体的募集或原位细胞的再教育。但是,现在很明显极化的T细胞(Th1,Th2,Treg)是巨噬细胞极化激活的关键协调器[2]。
2 巨噬细胞极化的分子机制
巨噬细胞极化的分子机制详见图1所示,信号分子,转录因子,表观遗传机制和转录后调节因子组成的网络是巨噬细胞激活为不同形式的基础。规范的IRF / STAT1信号通路被IFNs和TLR信号激活,使巨噬细胞功能偏向M1表型,或者被IL-4,IL-13/STAT6激活M2表型[6]。M1巨噬细胞上调IRF5,这对于诱导引发Th1和Th17反应的细胞因子(IL-12,IL-23,TNF)至关重要[7]。IL-4 I型和 II型受体[8]激活Stat6,这反过来又激活了M2极化的典型基因的转录,例如甘露糖受体(Mrc1),抵抗素样α( Retnla, Fizz1)和几丁质酶3-3( Chi3l3, Ym1)[9]。IL-10激活 STAT3介导的与 M2样表型相关的基因( Il10, Tgfb1, Mrc1)的表达[10]。STAT介导的巨噬细胞激活受细胞因子信号抑制物(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SOCS)家族成员的调节。IL-4和 IFN-γ(后者与TLR刺激协同作用)分别上调SOCS1和SOCS3,从而SOCS1和SOCS3分别抑制STAT1和STAT3的作用[11]。在IRF/STAT/SOCS途径的下游或与之并行,一组转录因子协调极化的巨噬细胞活化。核受体PPARγ和PPARδ[12]控制与M2巨噬细胞活化和氧化代谢相关的基因的不同子集。有趣的是,STAT6与两个PPARγ协调并协同作用[13]和Krüppel样因子4(KLF4)可促进巨噬细胞功能[14]。KLF4与Stat6协同作用,通过螯合NF-κB激活所需的共激活因子来诱导M2基因 (Arg-1,Mrc1,Fizz1,PPARγ)并抑制 M1基因 (TNFa,Cox-2,CCL5,iNOS)。Krueppel样转录因子 2(Krueppel-likefactor2,KLF2)通过抑制NF-κB/HIF-1α的活性来调节巨噬细胞的活化[15]。IL-4还可以诱导人巨噬细胞的c-Myc活性,其控制M2激活的基因(SCARB1,ALOX15和Mrc1)以及STAT6和PPARγ激活[16]。
TLR参与导致NF-κB活化并产生与M1巨噬细胞相关的炎性介质[17]。但是,NF-κB的激活也激活了消除炎症所必需的基因程序[18]以及与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TAM)的M2极化[19]。此外,诱导p50NF-κB同二聚体对于体内外M2极化至关重要[20]。缺氧诱导因子HIF-1α和HIF-2α在M1和M2极化的巨噬细胞中差异表达[21]并分别调节诱导型NOS2(M1)和精氨酸酶ARG1(M2)。表观遗传的变化和非编码RNA也参与了巨噬细胞极化的方向[22]。IL-4诱导小鼠巨噬细胞中组蛋白脱甲基酶JMJD3的上调,从而改变染色质修饰以促进M2基因表达并抑制M1基因。miR-155最近被确定为靶向IL-13Rα1亚基,从而减少了人类巨噬细胞中的一组M2基因[23]。低氧诱导因子-1(低氧诱导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
3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与肿瘤发生
与癌症相关的炎症的特征是单核巨噬细胞谱系的细胞募集到肿瘤组织中[24],这也是条件转移前的利己,有利于癌症的继发定位。经典激活的M1极化巨噬细胞具有显示抗肿瘤活性并引发肿瘤组织破坏的潜力。至少在小鼠的某些致癌模型中肿瘤进展与从M1到M2的表型转换有关[25]。M2型巨噬细胞具有显著的促进肿瘤生长作用,一般被认为是促肿瘤细胞。肿瘤细胞可以分泌IL-10,IL-6 和IL-17等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可以促使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后又分泌IL-4,TGF-β和M-CSF等细胞因子,进而又促进肿瘤细胞的浸润,生长和增殖,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M2型巨噬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IL-10可以抑制T细胞的激活,影响其他免疫细胞对肿瘤的杀伤作用。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减少了了NO的合成和释放,降低了巨噬细胞对肿瘤的杀伤作用。

图1 巨噬细胞极化的主要途径及M1-M2巨噬细胞极化途径之间的串扰
在小鼠和人类发展的后期阶段,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通常具有类似M2的表型,具有低IL-12表达,高IL-10表达,低杀肿瘤活性并促进组织重塑和血管生成。如霍奇金病,神经胶质瘤,胆管癌和乳腺癌所示,TAM浸润通常与预后不良有关[26]。但是,具有各种功能状态的TAM可以共存于同一肿瘤中[27]。各种途径可调节骨髓单核细胞的肿瘤功能,包括肿瘤来源和宿主来源的信号。淋巴细胞是TAM功能的关键协调器,但是在起源于不同器官的肿瘤中的途径不同。例如,发现巨噬细胞功能的倾斜是由皮肤中产生IL-4的Th2细胞介导的[28]和通过产生抗体的B细胞在乳癌中的发生[29]。B1细胞可以促进皮肤癌的发展,而成纤维细胞也可能有助于驱动巨噬细胞极化和促进肿瘤的回路[30]。
肿瘤细胞产物,包括细胞外基质成分,IL-10,CSF-1和趋化因子(CCL2,CCL18,CCL17和CXCL4),将巨噬细胞置于M2样促进癌症的模式中[24]。TAM还可以通过激活STAT3和声波刺猬通路来产生乳脂球-表皮生长因子VIII(milk-fat globule-epidermal growth factor-VIII ,MFG-E8) ,从而与癌症干细胞(CSCs)相互作用并促进其致癌性[31]。需要鉴定参与不同人类癌症中炎症的各种细胞和分子途径,以将我们对癌症相关炎症的理解转化为有意义的治疗进展。
4 展望
巨噬细胞极化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可以极化为M1型巨噬细胞攻击肿瘤起到抗肿瘤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极化为M2型巨噬细胞起到促肿瘤作用。人工诱导巨噬细胞极化为M1型巨噬细胞,可以在肿瘤的临床治疗中起到显著作用,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