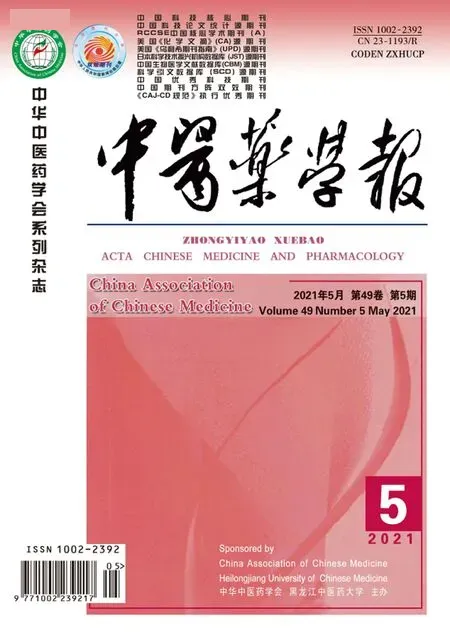“郁痹共病”对类风湿关节炎治疗的启示初探
许萍,左坚,李丹凤,胡英豪,钟树志*
(1.皖南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安徽 芜湖 241001)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高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病理特征,中医将此归入痹证范畴。一般认为皆因外邪侵袭,人体气血、经络闭阻所致,证见筋骨、关节疼痛麻木,活动异常,末肢关节畸形残疾等。现代医学所指抑郁症属于传统郁证范畴,以抑郁烦闷、不安烦躁、胸胁胀痛满闷等为主要临床表现。根据目前共识,上述两者分属免疫及神经系统疾病,病理特征及治疗方案均存在极大的差异。但研究表明,抑郁症与RA关系密切,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共病性特征[1]。立足于中医经典理论,本文在“因痹致郁”或“因郁成痹”因果关系辨证的基础上[2],以祖国医学和现代研究相关进展为基础,侧重于讨论精神类疾病和RA之间的共性病理特征,以治则治法的互通性,在目前创新性RA治疗药物难于取得突破的背景下,为新型抗风湿临床方案的开发奠定理论基础。
1 支持痹证与郁证联系的中医学观点
1.1 情志不畅是痹证诱因
汉代华佗所著《中藏经》曰:“气痹者,愁忧思喜怒过多……注于下,则腰脚重而不能行”,明确提出“气痹”的概念,并指出其成因皆为情志太过。这一观点得到后世继承。如宋代许叔微所著《普济本事方》载: “悲哀烦恼伤肝气,至两胁疼痛,筋脉紧急,腰脚重滞,两股筋急,两胁牵痛,四肢不能举。”清代罗美对上述理论进一步发展,在其所撰《内经博议》中云 : “凡七情过用,则亦能伤脏气而为痹。不必三气入舍于其合也……盖七情过用,而淫气能聚而为痹,以躁则消阴故也”。他认为,情志过用亦可是痹证发生之主因,而非仅协同于六淫之外感。痹证时则痛甚,疼痛因而是其主要兼症及重要的继发性病理因素。《内经》最早提出情志与痹证在内的诸痛证的关系。《素问·痹论》曰:“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心躁则痛甚,心寂则痛微”。上述论述指出痛证的疼痛程度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明代龚信所撰《古今医鉴》言: “郁火邪气……是故外邪得以乘虚而凑袭……诸般气痛,朝辍暮作而为胶固之疾……为周身刺痛……诸般气痛”;而《临证指南医案》亦云:“此劳怒动肝,令阳气不交于阴,阳维阳跷二脉无血营养,内风烁筋,跗臁痹痛,暮夜为甚者,厥阴旺时也”。以上论断巩固并发扬了情志过用致脉络失养、筋脉拘急,乃至为痛的痹证辨证学术观点。
1.2 疏肝解郁有利于痹证治疗
基于上述病机判断,解郁治法理论上可有效治疗痹证。《证治百问·痹》(清代刘默)记载,特定痹证分型只因抑郁而成,与外感内伤皆不相关,主要治则为疏肝解郁,临床收效良好。当代中医蒋小敏[3]认为,郁证与痹证密切联系:郁证多因肝气郁滞,失于疏泄;痹证患者大多数为中老年妇女,女子孕、胎、产之后营血亏虚,冲任不足,肝血亏虚,更易情志抑郁而发病;同时,该病活动期若曾伤于情志,会闭阻气机,郁而化热,因热生毒,进而加重病情。因此,蒋小敏擅以解郁之法治疗痹证,遣药组方长于使用陈皮、柴胡、玫瑰花等疏肝理气之物。另一当世名家冯兴华[4]主张在祛风湿的基础上,痹证治疗应兼顾疏肝理气,调理情志,以应对情志失调与肝郁气滞所致血行瘀滞,其临床擅用加味逍遥散治疗痹证。上述主张得到了当代中医学界的广泛接受:中医名家马武开[5]亦擅用柴胡、郁金等疏肝解郁药治疗RA;周乃玉[6]重视从肝论治痹证,临床常采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柴胡桂枝汤、小柴胡汤等以疏肝理气为要的经方;袁征等人的研究表明,疏肝解郁法指导下配伍组成的舒肝方(由柴胡、牡蛎、郁金、石菖蒲等组成)治疗RA疗效显著[7]。
2 精神性因素与RA相互联系
RA病程长、病情缠绵反复,患者关节长期疼痛,逐渐进入畸形及功能丧失的病理过程。慢性病痛及肢体残障必然诱发抑郁为主的心理性问题,而后者又将加重RA的疼痛及炎症表现。研究表明RA患者存在抑郁倾向的比例高达41.90%[8]。抑郁作为RA患者最为常见的精神性伴发疾病,其危害不仅表现为治疗依从性差导致的预后不良[9],排除干扰因素以外的实际疾病活动度也显著高于无抑郁倾向的患者[10]。
与之相似,其他负面精神因素对RA也存在深远的影响。心理压力被认为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尤其RA的发展和恶化中发挥重要作用[11]。Merdler-Rabinowicz R等发现RA患者群体在心理应激源和既往创伤事件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12]。危地马拉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RA患者的既往心理创伤事件发生率更高[13]。一项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也证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与更为严重的RA临床症状和压痛呈现正性相关性[14]。此外,退伍军人的创伤暴露和PTSD会增加RA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风险[15]。
3 心理因素与RA交互作用的基本机制
关于心理因素如何介入RA的发生、发展,导致炎症及疼痛的持续恶化,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定论。但有部分线索为探明这一关联提供了初步方向性指引。众所周知,中枢神经对外周分泌具有主导作用,因此相应的情绪状态会经由这一机制对机体施加广泛影响。现已证明,心理应激源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和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具有调控作用;上述系统的紊乱必然导致免疫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失调,最终推动自身免疫疾病的发展[16]。同时有研究分析了具体的心理压力源,包括性虐待和PTSD等对免疫系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压力源的激增导致固有免疫系统的平衡崩溃,进而影响了整体适应性免疫的功能状态[17]。
相对而言,RA对精神状态的影响相对清晰。如上所述,RA伴有严重的慢性疼痛和持续性关节结构或功能损伤,而持续的疼痛和失能是抑郁的主要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慢性疼痛和抑郁共病的概率为30%~60%,且前者是后者的重要诱发因素[18]。机制层面上,RA慢性疼痛与抑郁共同的神经通路已经被发现:从中缝背核经杏仁核到外侧松果体的一个特定的血清素能通路被认为是控制慢性疼痛与抑郁症状的共性关键神经回路[19]。
4 基于神经系统干预治疗RA探索
4.1 迷走神经刺激治疗RA
基于上述联系,情绪及药物因素通过相应的神经刺激理论上也能影响RA的预后。其中,迷走神经干预的临床意义已得到初步探索。迷走神经刺激已被广泛接受为抑郁症的辅助治疗,最近的研究表明,刺激迷走神经亦可减轻RA的慢性疼痛与炎症表现[20]。现有研究表明,胆碱能抗炎通路(Cholinergic Anti-Inflammatory Pathway, CAP)作为连接神经和免疫系统的重要中枢,是迷走神经激动缓解RA症状的关键机制途径[21]。RA或抑郁等状态下,CAP功能不足,导致机体中枢性炎症应对障碍;相反地,迷走神经的激动则通过干预免疫系统中巨噬细胞等操纵的免疫功能及炎症反应,实现抑郁和RA的同步缓解[22]。与此同时,RA伴发的认知功能障碍主要由胆碱能神经元的退化导致,迷走神经的有效激动及相应的下游CAP状态的上调将有力缓解递质不足及神经元过度凋亡导致的精神疾病[23]。上述理论得到了广泛临床及基础研究结果的支持[24-25]。Koopman FA等的临床研究表明,迷走神经激动可抑制肿瘤坏死因子分泌,显著减轻RA患者病情[26]。
4.2 精神类药品在RA治疗中的应用
抗抑郁药物在RA治疗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一方面,抗抑郁药物可用于疼痛管理,以提高疼痛阈值;另一方面,该类药物可缓解RA伴发的的焦虑和抑郁,改善睡眠[27]。上述因素共同改善RA患者生存的质量。更为重要的是,抗抑郁药物可有效缓解并控制RA的关节炎症状,降低了疾病活动度指数[28]。有意思的是,RA患者在接受有效的抗风湿治疗后,其对抗抑郁药治疗依赖也随之降低[29]。这一现象既体现出抗风湿与抗抑郁药物之间的疗效协同,也间接反映RA对抑郁这一病理状态的促进作用。
与此相似,抗癫痫药也表现出对RA及其他类型关节炎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因其突出的神经病理性疼痛缓解疗效,普瑞巴林在膝骨性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的治疗中广泛应用。利多卡因联合治疗可有效缓解OA患者疼痛感,减轻关节炎临床症状,降低血清中促炎细胞因子IL-1、IL-6、IL-8等的水平[30]。在佐剂性关节炎模型大鼠中,普瑞巴林表现出类似的活性。经该药物治疗后的模型大鼠体内的各项免疫、炎症及关节炎指标均明显好转,且其对疼痛的阈值大幅提高[31-32]。
5 纤维肌痛综合征的启示
纤维肌痛综合征(Fibromyalgia Syndiome,FMS)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肌肉骨骼疼痛综合征[33]。其典型病理特征包括广泛的肌肉骨骼疼痛、疲劳、睡眠障碍,且常伴有抑郁、焦虑、认知功能障碍症状。该病与RA同属于风湿免疫病,且两者均有较高的心理创伤经历和抑郁水平,并且多达13%~25%的RA患者伴有FMS[34]。诸多的相似之处及密切联系决定了两者的治疗具有高度的可借鉴性。
目前广泛认为,FMS伴发的肢体及精神功能障碍与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和岛叶皮质共济失调有关。虽然该病的病因病机尚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该患者群体普遍存在DMN与脑岛连通性增强;而美国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显示FMS与抑郁等精神障碍有很强的相关性[35]。与上述结论对应,哥伦比亚的一组调查中发现,最常用于治疗FMS的药物是抗抑郁药和止痛药[36]。上述证据表明,作为一种经典的免疫性疾病,神经性因素在其发生、发展与治疗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FMS相似,Neil Basu等人提供的神经影像学证据表明部分RA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驱动的疾病[37]。另一证据是,RA疼痛并非完全由外周炎症导致,而是由神经系统参与的典型混合性疼痛。在RA症状得到了充分的控制的情况下,大量患者仍存在显著程度的疼痛[38]。先进的成像技术正在揭示RA患者的神经生物学变化[39]。上述线索提示,中枢神经系统异常可能也是RA的重要原发因素,而对应的治疗也可能取得与FMS上类似的良好效果。
6 小结
RA的确切病因和病机仍不明确,从而导致目前无法实现其根本治愈[40]。许多RA患者对现有药物的反应并不充分,导致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上述背景下,抑郁等精神类疾病与RA往往交织发展。但深入研究表明,精神因素不仅仅单纯是RA的副产物;而两者的伴发亦不是纯粹的概率事件。大量证据提示,两者存在共同的机制基础。即中枢神经系统的异常干预机体基于神经调控实现的免疫稳态;相似地,RA伴发的精神疾病也是在免疫内环境恶化条件下产生的中枢神经病变的临床表现。可以预见,从神经系统入手将为RA的治疗推开一扇窗,有助于治则治法创新,及临床收效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