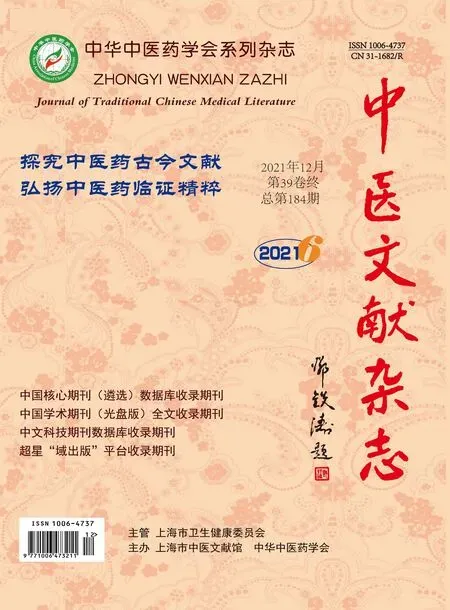房中术在晋唐道教观念中的演变*
陕西中医药大学(咸阳,712046)
在中医养生学体系中,其应用实践部分有许多富有特色、内涵深远的内容,如房中、服食和导引等。其中,房中术出现颇早,但因其特异的性学色彩而受到后世主流社会在伦理上的排斥,并且在道教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出现神秘化的倾向。
早期房中术与道教的产生
先秦至汉代的中医学,具有相当浓厚的“方技”色彩,或者可以作为方技的组成部分之一,甚至在职业群体划分上,医者、方士两种身份之间的界限亦不是十分明确。《汉书·艺文志》将方技分为四家,分别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东汉医家张机《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云“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是医学与方术之渊源的例证。
马王堆出土竹简书中的房中文献有《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三篇,主要阐述房中术及探讨房中养生。包括“五动”“五音”“五征”等女子性反应描述、“八道”“十动不泄”等有关男子房中术的内容,以及关于房中补益与禁忌的“七损八益”。《汉书·艺文志》另载有“房中八家”,今已失传。此外,还有两部重要的房中养生专著《玄女经》与《素女经》,内容大抵与马王堆的房中文献相近[1]。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房中术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其在理论上视性别为一组对立统一的范畴,将其纳入“阴阳”的概念,进而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性行为哲学层面的意义,认为“阴阳交合”是一种自然规律,两性关系实质是宇宙模式的一种高度概括的具象表现[2]。与《黄帝内经》相同,这类著作大多托名黄老、天师、容成、彭祖、玄素等先贤或仙人,在一定程度上有圣王教化之色彩。
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其滥觞于方仙道与黄老道。纵观其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亦将房中术作为一种重要炼养方法。如东汉《列仙传》记载:“涓子者,齐人也。好饵术,接食其精……受伯阳九仙法。”其中所论方法,指的就是“接阴之道而食其精”的意思[3]。
方仙道和黄老道继承了马王堆文献医疗养生房中术的内容,结合神仙方术、典籍和宗法思想,推出了新的成仙房中术和广嗣之法,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王堆文献中的阴阳大道和合气之术。房中术将性别纳入“阴阳”的认识,并随着房中术本身一道被道教所吸收,并基于阴阳学说的哲学内容,与“成仙得道”的目标进一步相结合。
房中养生与道教理念分化的历史原因
时至晋唐,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房中术和道教各自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北朝寇谦之、南朝陆修静改革天师道,山林之中有葛洪炼服丹药、陶弘景融汇诸宗,实开一代道门新风。同时,中医学也在晋唐时期蓬勃发展,尤其是临床诊疗水平有较大提升,这也丰富了房中术中有关生殖保健、性疾病与治疗等具体的医疗内容。故在此两种趋势下,晋唐时期房中术逐渐褪去神秘色彩,其在道教中的地位也在变化。
1.天师道改革与佛教传入
东汉末年,张鲁降曹后,曹魏政权多次北迁汉中住民,在客观上促进了天师道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和向上层社会的推广。至西晋北方战乱,天师道一道随着士族南迁,逐步成为江南道教的主流。但是当时的天师道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组织松散腐败、理论混乱不一等,限制了道教的推广。在这一情况下,寇谦之、陆修静分别于南北两地展开道教改革,其中寇谦之的改革对道教房中术影响较大。
寇谦之的改革,即“清肃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涤除了长期存在于道教内部的低级蒙昧,使其在更为清洁和精神化的层面上获得新生[4]。而这一过程中是将男女合气术视为需要整顿的重要内容的,虽然说合气术在理论上超过了房中养生的界限,并不完全等同于房中术,不过在广义上来讲,这种改革的确也阻碍了房中术在主流道教中的公开流传。
此外,西晋时期戒律严格、主张寡欲的佛教传入中国,在南朝至隋唐快速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与道教思想相互交融,也影响了道教对房中术的态度。
2.内丹术的发展
内丹术是道教另一个重要的炼养方法。一般认为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是丹法祖书,晋唐时的葛洪、苏元朗、司马承祯、陈抟等更进一步发展了内丹术,使其理论和操作都趋于全面[5]。
内丹术在形成阶段,也吸纳了许多房中术的内容。如“贵精”的理念就可见于“上药三品,神与气精”(《高上玉皇心印妙经》)。但是对于这一点,内丹家还有相对独特的认识,即“炼精者,炼元精,非淫佚所成精”(《金丹四百字序》),特别强调与性行为无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练神返虚的三步周天,成为内丹术成熟的标志[6]。
相比之前其他的炼养法,内丹术更强调对心性的静定训练。如《吕祖百字碑》所言“真常须应物,应物要不迷。不迷性自住,性住气自回”,因此清净寡欲就成了一种基本要求。虽然同样使用“阴阳”“精气”等哲学基础,但是内丹术强调修炼者基于“天人合一”的个体独立性,将阴阳解读为人本体之阴阳,而非男女之阴阳,即所谓“气回丹自结,壶中配坎离。阴阳生返复,普化一声雷”。
随着内丹术兴盛,房中术在道教炼养功法中的重要性也产生变化,其地位也逐步被取代。
3.上层社会对于房中术的兴趣
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汉代望族的基础上以及九品中正官制的导向下,形成了一批规模庞大、势力雄厚的门阀,即世家。虽然这些贵族作为当时的上流阶层,拥有优越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但当时政治生态却极其恶劣,斗争残酷。在危机四伏、如履薄冰的氛围中,世家子弟多寄情老庄、信奉宗教、崇尚玄谈,表现得纵情放荡、不拘礼法,成为风气[7]。与此同时,社会中的性观念也较为开放,并未形成严密的礼教之防。故此也给予了房中术逐步世俗化的条件。
大部分道教典籍中,对这类引房中术而行欲乐的行为是不赞同的,并称这类不得正确法式的修炼者为“秽仙浊真”。如《洞真太上智慧消魔经·真药玄英高灵品》云:“虽获仙名,而上清不以比德,虽均致化,而太上不以为贵……且崄巇履冰,多见倒车之败,纵有全者,臭乱之地仙耳。”其针对违背常规伦理、超越婚姻家庭道德范围性行为的不赞同,可以视为是对六朝性开放社会环境的一种抨击。
房中术的内涵与意义
基于多种原因,房中术的内涵与意义也在转变。从本质而言,房中术是养生学观念与道教成仙理想的分立。这些变化中,施行房中术的主要目的也发生了转变。以此为出发点,房中术的两性关系也产生了侧重偏移,在具体实施上,是对待施泄与快感享用的态度出现了分化。
1.房中术的目的改变
在道教整体发展过程中,围绕教旨与养生学,一直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施行房中术的目的究竟是延年益寿还是成仙。
在早期的合气术与房中术相关论述中,明确强调成仙的目的。《上清黄书过度仪》中记载的八生、解结食、九宫、蹑纪、思三气和思一宫等,就是确指合气交接。虽然这种“过度”与房中术不尽相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标志化的宗教仪式存在,建立在宗教神性之上,但依然是以性行为当作媒介。而就具体的房中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房中补益第八》中有言:“昔黄帝御女一千二百而登仙。”更早的类似记载出现于《庄子》《神仙传》《列仙传》中,都是肯定房中术和成仙之间的关系的。
葛洪大力反对行房中术成仙的说法。其在《抱朴子·内篇》中提出:“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他严格区分能够成仙的金丹术和房中养生术[7],认为房中术虽能除病长生,“但不得仙尔”。自此,道教成仙理想与房中养生在道教观念中开始分立,即虽然认同房中术具有祛病延年的养生功效,但其不是能够达到成仙目标的修行方式。
2.两性关系中的侧重偏移
社会因素影响两性关系在房中术的发展方向。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男权不断被强化,具体表现在房中术施行中特指以男性为主导,也更强调男性通过房中术获益。这一过程导致了女性观的转变,进而使得房中关系有了明显的侧重偏移。
在《列仙传·女丸传》中有如下记载:“女丸者,陈市上酤酒妇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过其家饮酒,以素书五卷为质。丸开视其书,乃养性交接之术。丸私写其文要,更设房室,纳诸年少饮美酒,与止宿,行文书之法。如此三十年,颜色更如二十时。仙人数岁复来过,笑谓丸曰:‘盗道无私, 有翅不飞。’遂弃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这个故事包含着“采阳补阴”的方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早期方士男女平等的思想。而在《上清黄书过度仪》中有“男女共奉行道德”“男女更相过度”等记载,也体现了男女相对平等的事实[8]。
之后类似的内容就逐渐减少,虽然存在描述凡男与神女结合的隐书之道,看似女性地位较高,但实质上主要站在男性角度叙述。作为一种内景术,对于女性修炼者而言并没有修习的价值。至后来世俗房中术中,则多有挑选妇人、更换御女等描述,侧面说明了男性居于主导地位。
3.对待施泄与快感享用的态度
房中术以性行为为载体,但性行为本身存在的“精”的施泄与快感享用,和神圣化的宗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9]。
一直以来的房中文献,都对施泄进行过讨论。如《素女经》有云:“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年三十者八日一泄……年六十者即闭精勿复更泄也。”说明早期房中术是可以主张施泄行为的,只不过需要适度“保精”,并根据身体情况安排。但是由于道教炼养中对“精气”重视程度的提高,对施泄带来的精气流失就更为担忧,因此对于施泄的态度,逐步从“少施”到“接而不施”,最终转变为禁欲。
宗教内容是清净神圣的,必然是将快感享受分隔开的。并且在“清净寡欲”的倡导下,房中术,尤其是主张快感享用更明显的黄赤之术,自然就成了宗教家批判的对象。陶弘景在《真诰》中以“似骋冰车而涉于炎州,泛火舟以浪于溺津矣,此非真正,亦失于万万”,表达了对于施行房中修行可能带来风险的焦虑。
基于这种矛盾,如果将房中术单纯作为养生术来看待,只是立足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单纯讨论保持健康、减少疾病,该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所以房中养生理念和道教思想分治,在此层面上是必然趋势。
房事保健与房事疾病的预防诊治
自房中术成为养生术开始,大量医家也在此基础上对于房事保健与疾病预防与诊治进行了诸多探讨。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房中专著《冲和子玉房秘诀》《徐太山房中秘要》等,葛洪《抱朴子》、张湛《养生要集》、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也多重视房中养生,《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医心方》等综合医著对此多有提及。
对于房事保健而言,最核心的是把握“顺应自然”和“节欲保精”这一对辩证关系的平衡[10]。如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御女损益篇第六》中有言:“房中之事,能生人能煞人,譬如水火,知用者可以养生,不能用之者立可死矣。”
顺应自然即指男女之欲不可压抑。即“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婚姻养育者,人伦之本,王化之基,圣人设教,备论厥旨”(《千金要方·妇人方上·求子第一》)。强抑性欲反而有悖生理需要,不但无益于养生,反而容易损害健康,致生疾病。
在顺应自然的同时,也不可过分放纵,须节欲保精。如孙思邈《千金要方·房中补益第八》所说:“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无节制的纵欲会损耗人体元精,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御女损益篇第六》言:“凡精少则病,精尽则死,不可不忍,不可不慎。”
房事养生保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房事禁忌。如“交接尤禁醉饱,大忌,损人百倍”“御女之法,交会者当避丙丁日,及弦望晦朔……”,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11]。
除养生保健的内容外,对有关房事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的部分也有相关论述。如“人有所怒,血气未定,因以交合,令发痈疽”(《千金要方·房中补益第八》)、“欲小便忍之以交接,令人得淋病,或小便难,茎中痛,小腹强”(《养性延命录·御女损益篇第六》)。对治疗房事疾病的方剂也有记载。如对于妇女交合出血,有《外台秘要》引《千金要方》交接辄血出痛方“桂心二分、伏龙肝二分,上二味捣末,以酒服方寸匕,瘥止”,此外还存崔氏疗合阴阳辄痛不可忍方等。
结 语
房中术产生伊始,就是一种具有养生色彩的方术。而方术是道教前身方仙道的重要基础,道教思想与房中术,不论是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形成,还是具体的应用文献记载,均能体现两者之间不只是简单的彼此引证,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交叠,相互之间亦多次渗透。
道教炼养和中医养生在各自的发展史上追根溯源,都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上。这作为一种特殊的医学文化现象,值得加以研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下的关键转变,有助于追溯中医养生学的整体历史轨迹,深化对中医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