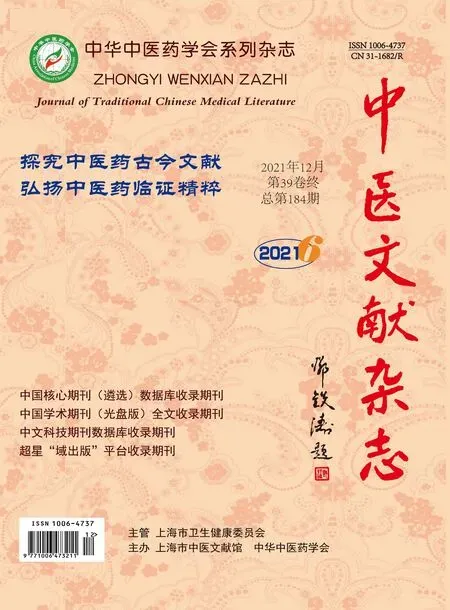中医防治疫病中的隔离思想与实践*
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30053)
隔离思想自古有之,如先民“有巢氏”的记载,即反映了远古人类避险的求生本能。自《黄帝内经》后,隔离成为防护疫病的医疗手段。历代对于隔离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医学本身,而是包括理论、方法、措施在内的一整套体系。中医学隔离思想的发展,可以说对防治疾病尤其是重大疫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防护措施,古已有之
远古时期人类饱受自然界风霜雨露和蛇鼠虫兽的摧残,为了避寒避暑、防御野兽和敌人侵害,发明了衣物、房屋、门户以及城墙等隔离和防护措施。
1.服装防护
服装的起源有很多观点,如遮羞说、御寒防晒说、保护说、美观说等[1]。汉代刘熙在《释名》中提道:“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这一说法囊括了御寒防晒说和遮羞说。原始服装具有御寒防晒、防护荆棘及工具等尖锐物剐蹭刺伤等作用,是古人自我防护意识的体现。
2.房屋藏身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便懂得藏身于天然的洞穴来躲避野兽的袭击,正如《易经·系辞》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到了中期,人们开始走出洞穴,动手建造巢穴,《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2]到了新石器时代,在南方较潮湿地区,已有了初期的干栏式建筑,具有躲避野兽虫害、通风防潮、避寒避暑的优点。从穴居、巢居,到干栏式建筑,再到西周时期的砖瓦房[3],人类抵御外界风寒暑湿邪气和蛇虫蚁兽的能力逐渐增强。
3.门户遮挡
最初的房屋是没有门户的。门的出现增强了安全感,不仅可以遮风挡雨,也能抵挡野兽袭击。于是逐渐产生了门户的崇拜,门神也随之诞生。据记载,周代便出现了“祀门”,《礼记·祭法》有关于“祀门”的详细记载。用于雕刻门神的木板往往采用桃木,人们认为桃木能够辟邪,门神能够驱邪挡煞,两者相配,相得益彰[4]。与门神相类似的厕神、灶神等对神明的崇拜,体现了人们对于隔绝邪气的迫切愿望,以及精神庇护的强烈需求[5]。
4.城墙防御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逐渐出现了部落城乡等地域划分。旧时农耕民族为应对战争,建起了城墙。《汉书·食货志》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汉书·郊祀志》云:“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神农、黄帝时代大约相当于我国新石器时代之中晚期。又如《吴越春秋》提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可见当时的城建已颇具规模。城墙作为城市、城池和城堡的抵御外侵防御性建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城墙具有较强的防御作用,不仅能阻挡敌人的进攻以及山林猛兽的袭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将疫疠邪气隔绝于外。在疫病流行期间控制人员的出入,对于控制疫病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服装、房屋、门户和城墙体现了人类保护自身和同类的迫切需求,展现了我国先民的智慧,也为后世医学隔离思想和措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隔离思想,重在避免
中医学历来重视疾病的预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为后世奠定了中医预防理论基础。当时医家将“治未病”与“治未乱”类比,认为“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穿井”“铸锥”均是金属时代的标志,揭示了文明时代重视防护思想的事实。
1.日常防护
《素问·上古天真论》言“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九宫八风》谓“圣人避风,如避矢石焉”,体现了古人对邪气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又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提出“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告诫人们要顺应四时以避寒避热。后世医籍描述更为详细,如《理虚元鉴·知防》云:“春防风,又防寒;夏防暑热,又防因暑取凉,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又防风。”[6]
2.医疗防疫
疫气是一类具有强烈传染性的外邪,又有“疠气”“疫毒”“戾气”“异气”“毒气”“乖戾之气”等称谓,其所引起的疾病称为疫病,包括瘟疫、痢疾、疟疾、鼠疫、麻风、天花等。历代都有大疫流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记录。根据《中国灾荒史记》中的不完全记录,从周代到清代,我国发生过308次疫灾,其中以明清两代大疫发生的次数为多,明代64次,清代达139次[7]。对疫病的防治,《素问遗篇·刺法论》明确指出了疫病传染的普遍性和症状的相似性,其特点是“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同时还指出疫病常常通过“天牝”(即鼻)来传播,即现代医学所说的呼吸道传播;“避其毒气”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医隔离思想的确立,说明当时的医家已了解到口鼻部位的隔离防护对于防止疫病的传播至关重要[8]。
3.人痘接种
人痘接种术的产生是世界免疫学发展史上的创举,到了明清时期,种痘术已趋成熟。《医宗金鉴》卷五十六至卷五十九为《幼科种痘心法要旨》,可以说是种痘教科书,详细记载了种痘的方法、禁忌、注意事项和意义等,并列举了痘衣法、水苗法、旱苗法等种痘法[9]。人痘接种术对于防治天花等传染病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正如张琰的《种痘新书》所说:“遍历诸邦,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记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若行于天时,安有如是之吉乎。”其原理是通过人为的感染,大幅度提升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与《黄帝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念相合,可以认为是隔离思想在防治方面的体现。
随着后世医家对于疫疠之气的认识逐渐深刻,各种隔离措施也更加丰富和完善,在疫病的防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疫病防治,隔而治之
古人为了防止或减缓疫病的传播,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隔离措施,包括自我隔离、病患隔离、尸体隔离、虫害隔离、海关检疫等。
1.自我隔离
古时医家早就认识到病邪会从皮毛口鼻进入人体,如《灵枢·百病始生》有言:“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皮毛入。”又如吴又可在《温疫论·原病》中提到“此气之来……邪从口鼻而入”,已充分重视自身口鼻和皮毛的防护。典型的隔离方法有涂抹法、塞鼻法、粉身法[10]等,大多是用雄黄、菖蒲、藁本等祛邪避疫的药物接触鼻腔或皮肤,达到将病邪隔离在外的目的。有躲避隔离法,如清代康熙帝为了“避痘”专门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顺治帝也将“南苑”和“养心殿”设为专门的避痘所,此外,还有“已出痘和未出过痘的皇室宗亲不得共聚一处”的规定[11]。
2.病患隔离
关于我国隔离患者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论语·雍也第六》中记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12],孔子并未入内探望,因为伯牛的病具有传染性,需要隔离。到了秦汉已有隔离所的设置,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秦墓书简《封诊式》上有载:“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所谓疠迁所,就是用来隔离麻风病人的处所。《汉书人物全传》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疫病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13]此后,历代遇到疫病流行时,便会效仿此法,在宋代有“养济院”“安乐坊”等政府指定隔离场所。在民间也有自发的隔离措施,如对于天花、麻疹患者,往往将其隔离在家中,并在门上插红布条用于警示他人[9]。明清时期,若有人患麻风病,家属便会主动将其远放于海上进行隔离[14]。除了隔离患者外,人们已意识到病患的密切接触者也需要隔离。如《晋书·卷七十六·列传第四十六·王彪之传》中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此规定不仅圈定了隔离人群的范围,还限制了隔离的天数。可以说,隔离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是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病流行的有力措施。
3.尸体隔离
人们发现患者的排泄物、呕吐物、接触过的物品以及尸体都会传播疾病。清代熊立品的《治疫全书》提到“四毋”,即“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告诫人们不靠近病人床榻,不触碰病人的尸体和物品,不食用病人的食物,其中蕴含的思想与现代医学接触隔离、呼吸道隔离和消化道隔离的理念相合[15]。为了防止这些污物散播疫病,清代官府曾宣发告示:“如有染患时疫,凡病人寓房之内,无论共人之或愈或亡,所有吐泻沾染住家,须封糊紧密,用硫磺草药之物熏烧。至中厕秽浊之地,更以生石灰铺垫,不时打扫,务使清洁。”[16]疫病流行之时,历代统治者都会下令收尸,或填埋或焚烧。如清末曾鼠疫大流行,晚清政府将三厂卡哨作为埋葬尸体的场所,并在其周围挖壕沟,以作隔离[17]。将患者的排泄物接触物及尸体处理妥当并隔离,防止病毒和细菌借此大量繁殖,避免其污染空气、水资源等,可以有效防止二次传播。
4.虫害隔离
许多疫病的流行与虫兽之害有关,如鼠疫、疟疾等。早在汉代已有使用蚊帐的记载,如《后汉书·黄昌传》有言“黄昌因夏多蚊,而贫无畴,佣债为作畴”,《岁时广记》提到“都人端午作罩子,以木为骨,用色纱糊之以罩食”。此外,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发明防蝇食罩[18]。这些手段在最初发明时与防治疫病无直接关联,但在很大程度上能减少以虫兽为传播媒介或传染源的疫病流行。到了清代,防疫与隔离虫害的记载已颇为详尽。刘奎在《松峰说疫·卷之二·除秽》中提到“凡温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识观入温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并针对苍蝇这一传播媒介提出“逐蝇祛疫法”。林庆铨的《时疫辨》中指出老鼠是鼠疫发生的源头,并告诫人们不要靠近死鼠,“今之鼠疫将作,鼠必先死,鼠死目突而赤,顷刻有蛆臭秽莫近,触其气者立毙”[19]。隔离或消灭这些携带疫毒的虫兽,可以很大程度上切断传播途径,减缓疫病流行。
5.海关检疫
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加,海路贸易日益繁荣,为了避免海外病源传入国内,海关检疫制度因此而生。市舶司是我国最早的海关检疫机构,始于唐朝,盛于宋朝。到了清朝,政府设立海关,并建立了海关检疫制度。岑玄珍在《中西合璧内科新编》中记载:“对于舟车往来之商港,应设检疫处,严重取缔所有运来货物。所有运来货物,皆须消毒,方准起上。”1894年,广州疫情蔓延时,海关规定往来船只必须接受检疫,须先在船上进行隔离诊视,确保无虞者才能上岸,检疫合格者派发“免疫通行证”[17]。海关检疫制度是传统隔离防疫措施的延伸,这一举措减少了国际间疫病的传播。
上述传统的中医隔离措施,有力地体现了中医防疫有效性和科学性,并且在当时的疫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避免更多人群受到疫病的侵袭。
上医医国,医治之道
应对重大的疫情,单靠民间自发的防疫行为和普通医者的力量显然不够,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当疫情波及范围广、牵连人数多时,只有政府发挥积极联动机制,才能保证民众采取正确的防疫措施,政府统筹提供防疫物资和人手,民众才有能力和资源防范疫情。《国语·晋语八》曾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所谓“上医医国”,就是需要将治未病的思想融会贯通于政治决策中,从国家层面来杜绝或减少疾病根源。
隔离患者这一举措十分依赖国家强制力,只有公办的隔离场所和强硬的隔离政令,才能保证隔离到位。但仅仅隔离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看政府发起隔离的目的以及背后有无正确的医学知识支撑。秦汉时期的“疠迁所”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最早的隔离场所,但当时并无治疗麻风的方法,政府隔离政令的初衷也并非救治患者。《秦律》规定可将麻风病人直接处死,或发配至疠迁所后“定杀”,或任其在疠迁所自生自灭[20]。可以说,只有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隔离才切实成为切断传播途径、保护健康人群、方便医者观察病情、找出治疗方法及措施的有效手段。
历史证明,大疫发生的次数及其严重程度除了与当时的医疗水平密切相关外,还与社会稳定度、政治清明度有关。疫情的控制有赖于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得力的治疗机构,以及政府及时协调和落实防疫工作的实施。社会动荡的年代,往往疫情发生的次数较多。如东汉末年,不仅大疫次数多,且牵连时间长、波及范围广。而唐初及贞观以后,社会安定,政府仁德,大疫次数明显减少。面对疫情,政府采取隔离患者、施医赐药、保障卫生、放粮减赋等防疫措施,可使疫情得以及时有效地控制。
可见,国家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上级政府及时发号施令,下级官员贯彻落实防疫措施,广大人民积极配合,才能战胜疫情。正如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上下联动,全民一心,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古为今用,共击疫情
疫病的传播和流行离不开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环节。因此,防治疫病的关键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各种隔离措施的制定,体现了古人对这三个关键点的认识。
传染源,即患传染病或携带病原体的人和动物。“疠迁所”“安乐坊”等政府指定隔离场所的设立,以及《晋书》中“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百日不得入宫”的规定,说明古人认识到患病者及其密切接触者都有传播疾病的可能。对蚊蝇鼠兽的隔离措施,体现了古人对动物传染源的重视。
现代医学把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分为水平传播和垂直传播,水平传播包括呼吸道传播、消化道传播、接触传播、虫媒传播及血、体液传播等,垂直传播即母婴传播或围生期传播。古人在数千年抗击疫病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对传播途径的认识。对于呼吸道传播疾病,指出“此气之来……邪从口鼻而入”,并发明了塞鼻法等隔离方法;对于消化道传播及接触传播疾病,强调“毋食病家时菜”和“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对于虫媒传播疾病,制定了多种多样杀灭和隔离虫兽的措施。古人亦认识到保护易感人群的重要性,例如清朝统治者采用“避痘法”来保护未被天花感染的人群。
古人对疫病的认识以及采取的各类隔离措施对于现代医学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中医传统的隔离防疫手段,如香薰包、喷涂剂、滴鼻剂在当今抗击疫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隔离思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来源于先民长期的生活实践,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历代医家将其应用于日常防护和疫病防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隔离思想在防疫中的应用更凸显了国家和政府 “上医医国”的理念。中医隔离思想流传至今,融合了西方医学理念,提升了科学性,变得更加成熟,在临床中还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