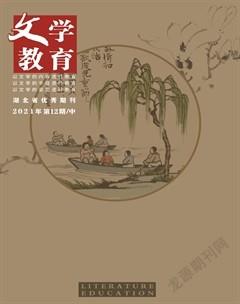二语学习者汉字正字法意识研究评述
林慧 张北镇
内容摘要: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二语学习者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心理学研究已有了长足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二语学习者正字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正字法意识的发展由浅入深,母语背景和汉语水平的影响较大。本文将对二语学习者正字法意识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评述,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正字法意识 部件意识 部件位置意识 部件组合规则意识
正字法是文字的书写规则(李虹,2006;冯丽萍,2006;张积家等,2014等)。任何语言都有正字法,但不同语言之间并非一致(李娟等,2000;鹿士义,2002)。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采用拼音文字系统,其正字法主要表现在字母的组合及单词的拼写等方面。与之不同的是,汉字为二维结构,其基本书写单位为笔画。笔画构成部件,部件再构成整字。那么,汉字的正字法就涉及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层面(Ding, Peng, & Taft, 2004; Taft & Zhu, 1997)。其中,部件在汉字构成中的作用突出,部件使用规则是汉字正字法的核心。另外,汉字书写单位与发音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较弱,正字法深度较高,这是汉字的另一显著特征(张积家、王惠萍,1996;鹿士义,2002;Schmalz et al, 2015)。汉字正字法系统的独特性使其成为汉字二语习得的焦点问题,在汉语国际化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学习者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发展问题值得关注(如张娟娟,2016;郝美铃、周思浓,2019;刘志敬等,2020等)。
正字法意识则是指人们的正字法知识以及该知识的使用情况(如鹿士义,2006;刘婷雁,2013;张娟娟,2016等)。汉字的正字法意识以部件层面为主,既包括不同部件的组字功能与分布规律知识(冯丽萍,2006),还包括部件组合规律和部件位置信息等知识(如江新,2001;郝美铃,2007;张金桥,2008等)。现有研究一般将汉字的正字法意识分为部件意识、部件位置意识和部件组合规则意识三个方面(如彭聃龄等,2006;陈琳等,2015;张娟娟,2016等)。部件意识是对部件的认识,表现为真假部件的识别与判定。部件位置意识是对部件在整字中位置的识别,表现为不同部件在整字中出现位置规律的知识。部件组合规则意识是对汉字结构类型的认识,表现为部件组合规律知识。
一.研究方法
汉字正字法意识的考察大都通过对不同类别汉字与临时构造假字及非字的对比进行。假字与非字的区别在于是否符合正字法规则。前者符合正字法规则,但在现实中没有使用,如“侻”;后者则根本不符合正字法规则,如“兑”。两者均无大脑表征,人们对其读音和意义的推断只能基于正字法规则进行。正是如此,两者也成为正字法意识考察的有效工具。对于假字,人们倾向于借助正字法意识将其识别为整字,从而在真假字判断时出现错误。相反,非字的判断则不太可能出现该类错误(张娟娟,2016)。另外,相关研究还可通过对假字的识别任务来对语言学习者的相关正字法意识进行测量(郝美玲,2007)。如刘婷雁(2013)就采用了线条图代替正确部件的方式构造非字,以此对部件意识进行考察。张娟娟(2017)分别构造了部件熟悉、部件位置正确的假字和部件不熟悉、部件位置正确的假字以及部件错误、部件位置正确的非字和部件熟悉、部件位置错误的非字,通过对这四类临时构造词的对比分别实现对部件意识和部件位置意识的考察。
实验任务方面,近期的研究大都采用在线的真假字判断任务进行(如张金桥,2008;郝美鈴、周思浓,2019;刘志敬等,2020等)。与纸笔测试等离线任务相比,在线任务对每个实验项目的反应时间均有要求,且实验项目随机呈现,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显性策略的影响,更加有效地揭示知识的自动化使用情况。如张金桥(2008)采用该任务对印尼华裔留学生的汉字正字法意识进行了考察,发现低年级的印尼华裔留学生已形成汉字正字法意识,主要表现为具有左右结构的汉字正字法意识。于此同时,眼动技术、ERP技术等技术也得以使用(张积家等,2014)(顾介鑫等,2007;毛媛等,2017)。研究者通过对生理指标的观察获取更加准确的数据,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
二.现有研究综述
文献综述发现,汉语正字法意识研究突出对母语儿童的考察。相关研究丰富,结论相对成熟。研究发现,母语儿童在学前阶段就开始发展部件位置意识,小学低年级开始萌发部件意识和部件组合规则意识,五年级时正字法意识基本成熟。相比之下,学界对二语学习者的考察数量不足,结论也不够完善。仅有的少量研究表明,母语为拼音文字的外国留学生至少需要两年的课堂学习才能形成相对成熟的汉字正字法意识。另外,学习者部件位置意识发展较早,随后出现部件意识,部件组合规则意识则在最后(如鹿士义,2002;冯丽萍,2006;张金桥,2006等)。于此同时,研究者还对可能影响正字法意识的因素进行了探讨,母语背景首当其中(如鹿士义,2002;李利等,2014;张娟娟,2017等)。
母语与二语的类型差异是影响二语发展的重要因素,该影响在汉语正字法意识中也有发现(如李利等,2014;张娟娟,2017;刘志敬等,2020等)。其中,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之间的差异明显,研究发现汉字文化圈学习者的正字法意识萌芽更早、发展更快(刘婷雁,2013)。该差异在汉字认读和汉字书写上均有体现(吴门吉等,2006)。另有研究发现,同属汉字文化圈内的不同母语学习者之间也有差异。如日语大量使用汉字,其正字法与汉语更加接近,日本来华留学生的正字法意识优于韩国留学生(郭琦,2012)。
汉语水平对学习者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影响也得到关注(如李利等,2014;王建勤,2005;张娟娟,2017等)。研究发现,汉字正字法意识与汉语水平共同发展,关系紧密。高水平汉语学习者的正字法意识也相对更高(鹿士义,2002)。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不仅体现在汉字识别任务中,在书写任务中也是如此(李利等,2004)。另外,冯丽萍(2006)还对汉语水平和母语背景的交互作用进行了考察,发现汉语水平对不同背景学习者的影响不尽一致。无论是日韩留学生还是欧美留学生,汉语水平均与正字法意识正向相关。然而,与日韩学生不同的是,欧美学生对上下结构汉字中部件位置的合法性还不能准确做出判断,对这种结构汉字的正字法意识仍处于发展之中。也就是说,汉语水平对欧美学生正字法意识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而且表现在质的方面。
三.将来研究展望
现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奠定了该领域研究的基础。今后的研究需对现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同时也需不断扩大研究的视野范围。对此,我们可在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母语背景对二语者汉字正字法意识发展的影响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母语影响已在不少研究中得到重视,相关研究重点讨论了文化圈不同的学习者群体之间的差异(如吴门吉等,2006;刘婷雁,2013;张娟娟,2017等)。于此同时,我们还需关注文字本体差异,从类型学的视角深入探讨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细微差异,从微观层面探讨二语正字法意识的发展特点。在研究设计方面,我们也可将汉语母语者纳入受试范围,将其作为参照基线,通过与其的对比发现二语者的特点。
第二,二语正字法意识发展研究尚待完善。正字法意识的发展研究是该领域的另一重要议题,不少研究通过不同水平被试的对比进行。同时,对相同被试的跨时跟踪测量更加体现了相关研究的新趋势(如Cheng & Huang, 1995; 李娟等,2000;Chan,Loh,& Hung, 2021等)。但对二语者的跨时研究当前较少,尚待丰富,以更加全面展现二语者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路径及发展特点。
第三,正字法意识对二语者汉语能力发展研究有待探讨。对汉语儿童的研究发现,正字法意识的发展对识字量、阅读理解能力等语言使用能力均有较强预测力(如李娟等,2000;李虹等,2006;史冰洁,2011等)。有的二语研究也对识字量与正字法意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数量较少(鹿士义,2002;王建勉,2005;冯丽萍,2006)。正字法意识对阅读理解等综合语言能力发展的复制性研究尚未发现,更不用说其与听力理解、写作等其他语言能力的扩展性研究了。然而,对字母语言使用者的研究早已发现,正字法意识在不同语言能力的发展中均有影响,那么汉语的状况如何则需更多关注。
第四,不同类型汉字的分类探讨也是将来研究的新课题。汉字类型丰富,正字法意识的探讨也应尽量广泛,全面关注。如有的研究发现不同结构汉字使用涉及的正字法知识就有差异,其习得可能发生于语言学习的不同阶段。那么,今后研究就有必要对不同类型汉字进行分别探讨,形成对二语者汉字正字法使用能力的全面了解。
第五,汉语教学中正字法意识发展的干预研究值得关注。毋庸置疑,恰当的教学干预能够促进元语言意识的发展。在留学生汉字教学中,也有研究对相关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陈琳等,2015)。今后的研究也应在该方面进行更多探索尝试,发现汉字教学的有效途径,提升二语者汉字正字法意识发展效率。
当前研究对汉字正字法意识发展问题进行了开创性地探索,奠定了该领域发展的基础。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的范围,同时更加注重微观问题的深入探索。一方面,正字法意识对二语者汉语能力发展研究有待探讨;另一方面,汉字教学的有效途径有待探索;同时,我们需关注文字本体差异,从类型学的视角深入探讨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细微差异;最后,华裔学生的汉语习得问题也值得关注。一方面,华裔学生是承载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华裔学生的自身形象也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华裔学生的漢语习得,对增进华裔学生对传统中华文化的认同、提升中国软实力具有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Chan, T. S. P., Loh, E. K. Y., & Hung, C. O. Y. (2021).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indergarteners’ orthographic awarenes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ir lexical learning performance. Current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1 -01797-2
[2]Cheng, C. K. , & Huang, H. M. (1995) . The acquisition of general lexical knowled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school children. In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Chinese and other Asian languages.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陈琳,叶仕骞,吴门吉.语文分进和并进两种教学模式下非汉字圈初级汉语学习者的正字法意识[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02):19-25.
[4]Ding, G. S. , Peng, D. L. , & Taft, M. (2004) . The nature of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radicals in Chinese: A priming stud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0 (2) , 530-539.
[5]冯丽萍.外国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及其发展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1):12-17.
[6]顾介鑫,赵仑,刘涛,杨亦鸣.应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研究词汇识别中汉字正字法的作用[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07(26):5097-5101.郭琦. 日、韩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对比实验研究[D].中山大学,2012.
[7]郭琦. 日、韩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对比实验研究[D].中山大学,2012.
[8]郝美玲.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萌芽与发展[J].世界汉语教学,2007(01):29-39+2-3.
[9]郝美玲,周思浓.汉语初学者汉字阅读准确性与流畅性影响因素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9,33(04):548-562.
[10]江新. 初学汉语的美国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实验研究[A].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对外汉语研究的跨学科探索——汉语学习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2001:12.
[11]李虹,彭虹,舒华.汉语儿童正字法意识的萌芽与发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01):35-38.
[12]李娟,傅小蘭,林仲贤.学龄儿童汉语正字法意识发展的研究[J].心理学报,2000(02):121-126.
[13]李利,李璇,奥烈霞.汉语水平与母语背景对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影响[J].心理研究,2014,7(06):37-42.
[14]刘婷雁.汉语学习者汉字构形意识的发展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3,11(06):35-42.
[15]刘志敬,郝美玲,汪凤娇.正字法意识和语音意识在留学生汉字学习初期的相对重要性[J].华文教学与研究,2020(03):55-60.
[16]鹿士义.母语为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汉字正字法意识发展的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03):53-57.
[17]毛媛,董静,王权红.汉字正字法家族效应的ERP研究[J].心理科学,2017,40(03):534-539.
[18]Qian, Y. , Song, Y. W. , Zhao, J. , &Bi, H. Y. (2015).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of orthographic awareness in Chinese preschoolers. Reading and Writing, 28(4), 571-586.
[19]史冰洁,李虹,张玉平,舒华.部件特征和正字法意识在儿童汉字书写发展中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7(03):297-303.
[20]Taft, M. , & Zhu, X. P. (1997). Submorphemic processing in reading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3(3), 761-775.
[21]吴门吉,高定国,肖晓云,章睿健.欧美韩日学生汉字认读与书写习得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06):64-71.
[22]Xenia Schmalz; Eva Marinus; Max Coltheart & Anne Castles. 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orthographic depth[J].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015, 22(6) : 1614-1629.
[23]张积家,王娟,印丛.声符和义符在形声字语音、语义提取中的作用——来自部件知觉眼动研究的证据[J].心理学报,2014,46(07):885-900.
[24]张积家,王惠萍.汉字词的正字法深度与阅读时间的研究[J].心理学报,1996(04):337-344.
[25]张金桥.印尼华裔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J].语言文字应用,2008(02):116-122.
[26]张娟娟.东南亚国家华裔、非华裔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对比研究[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6(03):17-26.
[27]张娟娟.东南亚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情况[J].海外华文教育,2017(01):82-91.
科研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汉语形声字的二语加工研究”(18YJC740138);江苏省社科项目“作为二语的汉字认读加工机制研究”(19YYB002).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