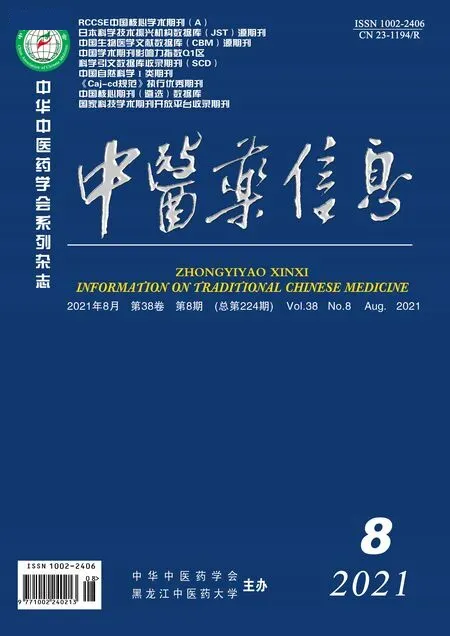王肯堂《医学穷源集》运气学诊疗体系初探
刘明洋,韩海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王肯堂为明代中后期著名医家,临床经验丰富且著述等身,辑《证治准绳》、刊《医统正脉全书》,为融通金元诸家思想以及传承中医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王氏晚年所作《医学穷源集》中,其医疗风格忽然改变,以运气学贯穿理、法、方、药的全新体系,冲破了以往诊治疾病“平脉辨证”的固有局面,认为运气学为“审证之捷法,疗病之秘钥”[1]2。且从书名“医学穷源”来看,显然王氏以为运气学为中医学之源,郑重之意可见一斑。然而此书迄今为止研究者极少,故对其运气学诊疗体系进行探析、推介,是十分必要的。
1 《医学穷源集》理论发源脉络
《黄帝内经·素问》的七篇大论奠定了中医运气学的基础,唐代启玄子《素问六气玄珠密语》进一步对五运六气的理论进行阐释,强调了运气理论产生的天文学背景,并详细论述了六十年中运气加临的各种格局[2]。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天干方”十首、“地支方”六首,为运气学的方剂应用提供了范式[3]。宋代官方刊布的《圣济总录》详细地收集了六十甲子每一岁的天、泉间气中运主客等运气背景,以及所应的气候、物候、民病、药食所宜等,推动了运气学说的普及。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定数”式的推算,容易造成医家在临床的机械应用。如《伤寒钤法》结合命理思想,根据患者出生以及生病时间,机械地建立一套推病定治法,几乎抛弃了中医学“因人、因时、因地”的辨证思想,因而产生了不少弊端。
金元四家则撇开繁复的运气加临推演不谈,另辟蹊径,从医理、治法、药性等方面对运气学进行了发挥。如刘完素便是运用运气学“亢害承制”的思想对《素问》“病机十九条”进行了发挥,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学病机学的内容[4]。后世诸家在著述中虽然对运气学多有阐述,但是至今运气学在临床上的应用还多停留在根据干支对发病时间的简单推算、与运气理论的初步结合,以及对已有运气方(主要是“三因方”)的发挥运用。然而王氏的《医学穷源集》不仅辨证地继承和发展了运气学的理论,更以运气学之理融通贯穿了中医学生理、病机、药理、方剂等方面,并且因机应变地施用于临床。
2 一以贯之的病理、生理、药理体系
2.1 人体与天地气化密不可分
运气学难以在临床上施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运气学体系和当今中医学体系的脱节。一般来讲,五运六气所探究的对象为天地气化以及对气象、物象、人体的作用,当今中医学体系虽然主张对疾病认识的“三因制宜”,但实际上,在临床施用时,仍然以“因人”为主,所谓的“辨证论治”未超出此范畴。《素问》云:“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人生养于天地之中,如鱼生于水而养于水,故人体的常与病、与天地之气息息相关。王氏所构建的运气学体系,始终把人放在天地气化之中考虑。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气化不平,人体自身的脏腑虚实、气血盛衰、七情饮食,以及自然界六淫邪气的侵袭均可使人体气化不平而为病。然而人体气机及自然气候的变化、六淫邪气的转移,均暗自随天地气化而变迁,故五运六气等运气因素所构成的天地气化背景,可以说是人与万物共同的生、化环境,它们是密不可分的。
2.2 运气学与病理联络
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论,认为阴阳二气的相摩相荡和五行之气的生成克制,是事物生、变的原因。王氏在《医学穷源集》中言:“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而后有是形”。无形的气不可见,然而通过对阴阳、五行之理的把握,由其所生之物、所显之象,便可从有形的“象”知悉其背后无形的阴阳、五行之气,此为“司外揣内”的方法,即《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言:“天地阴阳者……以象之谓也”。
阴阳在气化的精微层面可分为三阴三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天、地、人三者本源相同亘古不变,且同受三阴三阳之气的制约。“经”,有常而不变之意,也有经纬制约之意,故三阴三阳亦称“六经”。关于六经应象,《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载:“厥阴所至为风生……少阴所至为热生……太阴所至为湿生……少阳所至为火生……阳明所至为燥生……太阳所至为寒生”。寒、燥、火、湿、风、热六气即三阴三阳在自然界呈现出来的气象。异常的六气可变为六淫之邪,成为致病因素,三阴三阳之气也就间接地成为病因学的因素。并且通过人体六经与经络脏腑的联络,天地之气的异常也可以直接加于人体的脏腑经络而为病:“厥阴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致为稸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瞀昧、暴病;阳明所至为鼽,尻阴股膝髀䯒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此为三阴三阳系统对病因的统摄。
2.3 运气学与生理的联络
王氏通过对人体脏腑的六经分属、六经之间相比相配的深入分析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状态。如人体太阳一经包括膀胱足太阳之脉、小肠手太阳之脉的经脉,以及膀胱、小肠的脏腑,还有“膀胱者……毫毛其应”的毛窍。脏腑、经脉、毛窍三者在太阳一经的统摄之下,完成太阳的气化功能——“太阳寒水”的代谢。王氏在书中太阳的功能及水液布散的渠道总结为:“太阳之气本于水府(膀胱的气化功能),外行通体之皮毛(化为汗液),从胸膈而入于中土(精者洒陈于脏腑,浊者化为尿液出于前阴)。”太阳一经蒸化水液、循环周身的作用,王氏有形象的比喻:“太阳起于极阴(最下、最寒)之地,故海水极深之处,而日出焉”。
太阳一经须同时与他经相协才能完成自己的生理功能。太阳与少阴为表里之经,太阳为少阴之使、少阴为太阳之守,气本相同,故王氏认为“太阳之气,必藉肾经真水以养之”,太阳才能温煦气化。太阳外合皮毛,而肺主皮毛,太阳化汗外出的作用必有肺脏功能的参与才能实现,故“手太阴(肺),实与太阳之气相合,此金水相涵之义也”。太阳主三阳之开、太阴主三阴之开,“太阳与太阴,则身中乾坤也……身中统摄手足六经之脉,全在于此”,地气上腾、天气下降之机在于二经。故王氏从相配的角度分析,认为只有太阴的气化作用与太阳相配,太阳才能正常的气化而不病。
2.4 运气学与药理的联络
中医对本草的运用,多遵照本草学著作中药物的主治功效,主治与病证相合,气味与病情相投便可使用。《医学穷源集》中王氏用药却与此大相径庭,认为“读本草有法,勿看其主治”[5]。因为所谓的药物,是天地五行、六气自然合化的产物,他们不是为了治病而生的。所以学习本草,应该“验其味,察其气,观其色,考其何时苗,以何时花,以何时实,以何时萎”,因“象”而知“气”。知悉药物禀赋之气的偏颇,便可以以偏救偏,纠正人体气机的不平而使病证消除。主治功效只不过是先贤对药物作用结果的部分总结,为末;对药物由象测气的分析以知药理,为本;如果仅执功效治病,是为本末倒置,必然“举一而废百”,不能把握药物功用的全体。
如“惟夏枯草近时专用为肝经药”,但是其味辛性寒,辛为金所化之味,寒为太阳所化之气,故“禀金水之气”,加之夏至阴生而枯萎,故能以阴化阳,使阳气流通无滞,所以王氏扩充其功用为:“而内消坚积,上清火热,又能使水气上行环转”。再如阳明之气为“介化”,故锋芒坚硬之象的药物皆禀阳明燥金之气。所以药物“兼锋刃之形者,助金气也”。如苍耳子既可去湿,又能制约肝气过亢的原因,就在于“其形之多刺”。“前方用蟹壳,而此方用象皮、猬皮,皆有戟刺之形,阳明之象也。”由此可见,王氏之所以能对药物灵活运用于临床,就在于他能把药理、病理、生理放在天地气化的统一整体中考虑和把握。这样,纷繁的病因、病情、药效就纲目井然,药物的运用便可因机应变,而不仅仅局限于药物的主治功效。
3 王氏运气学临床应用范式
通过对《医学穷源集》112个医案的梳理,可以发现王氏在临床诊治疾病有其大致的范式。首先根据疾病发生时间的运气节点,推算该时间节点的运气背景——大运、司天、在泉、主客气、主客运等因素,并梳理诸运气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运气因素的改变和改变之后的运气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次,将运气背景与患者病状参合分析,以确定患者病情与运气诸因素的生克、顺逆情况,进而掌握患者的病机。最后,综合病机与运气因素,确立治法,选择药物。如《医学穷源集》木运年第一个医案:“郑姓,廿七,感冒风邪,燥热无汗。脉象浮数无力,两尺沉细(注:两尺不应岁气也)。此壬子年立秋后五日方也”[1]70。
首先分析该患者看诊时间的运气背景为:大运-太角、客运-太宫、主运-少宫;司天-少阴、在泉-阳明、客气-太阴、主气-太阴(运气背景推算法在运气学著作中皆有论述,兹处从略)。其次,分析患者的病机与运气背景情况:患者触冒风邪之后,见燥热而汗不出,当为风邪阻滞、毛窍闭阻、邪热内郁之证,脉象之浮数与证相合,可知风在皮毛为邪实。但脉之无力显出虚象,燥则津液受伤,单纯从患者的角度分析,当为肺虚津伤,不能化汗外出,故使邪结于外不散,再加上两尺脉沉细,还有阴血或者下焦肝肾不足的深层因素。治疗的方法,应该益气养阴清热,兼以发散风邪(此为“辨人”)。但如果考虑到运气因素,主客气均为太阴湿土,主运少宫、客运太宫,都与湿土有关,所以其关键矛盾应该是人体的太阴系统(手太阴肺、足太阴脾,肺主皮毛、脾主布散水谷精微上合于肺),不能与自然界当令的太阴之气相合而布散。脾不能化精于肺,导致太阴脾肺阴津不足而邪湿不化。再根据北政之岁(中运属金、水之年为北政)阳明所在不应脉的特点,可以推知两尺脉因运气因素的抑制而呈现出与病情不和,并非营血或者肝肾不足(此为“辨天”)。最后,综合“辨人”与“辨天”的分析,确定其治疗方法应该清润太阴,助脾化湿,升散风邪,故以麦冬、生地黄清肺滋脾,木香、茯苓化湿邪而助太阴运化,前胡、柴胡散风邪而升阳气,秦艽、甘草交合天地之气,使流通无滞。
王氏这种“辨人”“辨天”(实际上还有“辨地”——地理高卑、风俗淳散等)的综合分析法,是中医学“天人相应”以及“三因制宜”思想的完美体现。从多维角度分析病情,有利于更全面、深入地把握病机,提高疗效。
《医学穷源集》经王氏弟子殷宅心整理出版后一直未能流传开,殷氏一脉却“什袭藏之,珍逾拱璧,私为家学,不轻以予人”。然而该书为王氏一生对中医理论及临床研究的精华之作,也是升华之作,改变了运气学重推演、重理论而与临床难以贴合的局面,十分值得大家深入研究,故为抛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