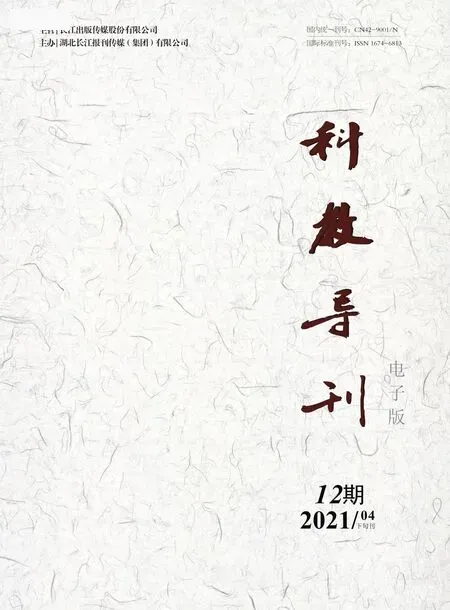高等教育的“两个规律”与“适应论”论战
冯子然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1 高等教育“两个规律”提出的背景及内涵
潘懋元先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提出要建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并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首次探索。20年后,他再度倡导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在他的建议下,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成立。1980年11月8日至20日,潘先生应一机部教育局之邀,到湖南大学为一机部所属院校领导干部教育科学研究班作了题为“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的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该学说为《高等教育学》的编写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四年后,由潘懋元先生主导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该著作的出版成为了高等教育学科建立的标志。
从全书的内容看,书中的许多理论和观点正是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和高等教育特点论的指导下形成的。高等教育的“两个规律”是高等教育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外部规律,也称教育同社会关系的规律,指的是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系统的其他子系统——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这条规律被表述为:“社会主义教育必须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服务。”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依据是教育的本质,它是教育的本质的体现。在《高等教育学讲座》中,外部规律得到了更加全面系统的阐述,外部规律的含义和表述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和丰富。教育的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这条规律的主要含义就是“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
而内部规律,或叫教育自身的规律,指的是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它内部各个因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规律。它被表述为:“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或者“社会主义教育必须通过德育、智育、体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内部规律就是教育方针所包含的教育目的的内容。
“内外部关系规律”学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立教育主体地位。把教育作为一种主体,就是要重视教育群体的内在声音。同时,两条基本教育规律也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教育的外部规律制约着教育的内部规律,教育的外部规律必须通过教育的内部规律来实现。教育的外部规律和教育的内部规律是相互起作用的,缺一不可,也不可分割。
2 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分歧与论战
2.1 高等教育适应性与“两个规律”的关系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高等教育的特征来看,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分为九点,“适应性”就是其中一点。“适应性”原本为生物学概念,它指的是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一种特性,这是一个有机体能够存在的前提,否则该有机体就面临灭亡或绝种的危险。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有机体的适应性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在教育学界,人们普遍接受“适应性”这一基本观点,人们也把教育看成一个有机系统,处于与周围环境或其他社会系统不断地适应过程中,人们一般相信教育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系统,因此必须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的、信息的和能量的交换,这样才能维持教育作为一个有机系统的运转。这正是系统论给人们阐述的基本原理。
高等教育的“适应性”,即潘懋元先生所提出的外部规律:“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里的适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教育主要受到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三个因素影响。同时,潘懋元先生在总结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过程中,也提出教育受要三方面的制约,并为三方面服务。一是教育受政治制约并为政治服务。二是教育受经济发展制约并为经济服务。三是教育受科学文化发展制约并为科学文化服务。可以说,“适应论”是由教育的外部规律所引申出来的,即现代高等教育要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适应世界高新科技发展的需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适应社会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这不仅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而适应于各国的高等教育。
2.2 关于“适应论”的论战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两位教授展立新和陈学飞的长篇文章《理性的视角:走出髙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否定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两个规律”的理论,否定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求的“适应论”,作者认为,“高等教育适应论是一种无奈的历史选择”,导致两大失误:一是“颠倒了认知理性与各种实践理性的关系,使国内高等教育难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二是“不惜压制其他实践理性的发展,以至于在髙等教育的各种目标之间、不同的目标之间与手段之间,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突破与超越适应论,是现阶段我国髙等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该文章在竭力否定和贬低高等教育“两个规律”理论和“适应论”的同时,鼎力推崇和提倡所谓的“认知理性”,认为高等教育要摆脱“适应论”的思想束缚必须“回归认知理性,建设完善的学术市场”,认为“髙等教育本质上是发展认知理性的事业”、“高等教育追求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认知理性的发展”。
而杨德广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的“适应论”是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必然,是高等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潘懋元提出的“两个规律论”即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是“适应论”的理论基础,是符合实际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推动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对此,他撰写了文章《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历史的误区吗?——与展立新、陈学飞教授商榷》,刊登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3期上,对展陈的观点进行一个反驳。杨认为,该文用哲学上的一个普通概念“认知理性”来否定和取代高等教育“适应论”和“两个规律”论,甚至将其提高到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不适当的。观点中片面地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性的视角”,是脱离现实、不顾现实社会的需求,是思想的倒退,历史的倒退,是一种退缩到“象牙塔”里的企图。对此,本文指出,潘愗元的“两个规律”论是符合教育实践和客观现实的,并非由展、陈提出的“认知理性”所取代。
不久后,展立新、陈学飞又发表了新作《哲学的视角: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四重误读和误构——兼答杨德广商榷文》,点名与杨德广教授商榷“适应论”。该文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引用了从马、恩、列到涂尔干、舒尔茨等人的观点,进一步否定高等教育“适应论”,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实质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建设健全学术共同体精神,是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长盛不衰的根本保障。展、陈在文章中鲜明地提出:高等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基本关系并不是“适应”与“被适应”的关系,而是批判反思主体和批判反思对象的关系。因此,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不是迎合政治权力和“当权者”的需要,而是要自觉把政策、权力、当权者等,都当作批判反思的对象。
对此,杨德广教授认为其中的有些评判过于断章取义,有些观点甚至是错误和片面的。他认为,“学术共同体”仅适用于一些研究性大学而不适用于应用型、专业型大学,展、陈只片面的考虑大学的学术研究功能,而忽略了大学生的实践性、现实性和技能性。其次,展、陈强调了大学的“批判性”问题,而大学生不能只为了“批判”而“批判”,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大学的批判性是建立在维护国家利益的、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因此并不存在对立。另外,关于大学与社会“适应”与“被适应”的问题,杨教授指出几个例子,中世纪的大学为教会服务,美国现代大学为社会服务,威斯康星大学提出社会服务职能,说明大学的“适应性”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存在大学必须为当权者和政治服务的关系。综上所述,潘懋元提出的高等教育适应论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客观现实的,大学如果一味地强调学术功能,不接地气,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所发展,那么很容易被社会淘汰。杨德广教授还结合学界上其他学者提出的“适应论是受特定年代计划经济和传统理论模式的产物的”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发展,更要主动去适应。由于教育的滞后性,高校要发展更是需要去“超越”,如果把“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误以为不要适应,注定是走不通的。
3 结语
总体而言,高等教育“适应论”能够较好地处理好知识与个人及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因为它首先把社会发展需求放在第一位,其意义就是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的存在,高等教育仅仅是社会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不能封闭起来推行自我中心主义。同时高等教育必须尊重人的发展要求,因为人不仅是社会的基本构成,也是社会价值的归宿,换言之,没有人就没有一切。这正是教育内外部规律的内涵。但两个规律学说对知识独立价值论述偏少,常常给人一种忽视知识、忽视髙等教育本体的印象。这也正是“理性视角”批判的重点。
世界各国的大学从一个功能发展到两个功能,再发展到三个功能,这就是主动适应社会的必然结果。因此,并非像展、陈所说,“高等教育‘适应论’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社会需求角度阐述和论证高等教育问题的理论”。事实上,“适应论”适合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高等学校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应建立教育产业、发展教育市场。这是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