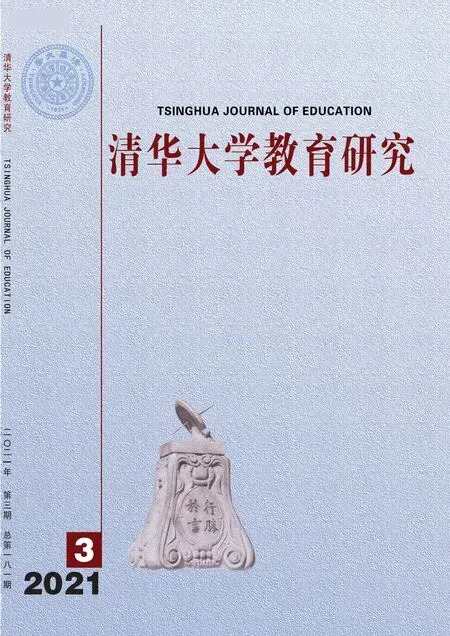突破再生产:布迪厄理论的另一面
朱 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教育研究院,美国)
自20世界70年代末传入中国以来,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对中国的教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启发了大量诘问教育公平的重要研究。杜亮、牛丽莉和张莉莉对中国21世纪以来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布迪厄的理论是学者们用以解释教育不平等的核心框架。(1)杜亮等.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进展述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5):40-48.在如今的中国教育学术界,布迪厄已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然而,许多运用布迪厄理论的实证研究却也面临着一个关键的瓶颈,似乎很难突破对“再生产”理论的验证,难以对布迪厄的理论内涵有所深化或延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布迪厄的理论产生了“审美疲劳”。甚至,布迪厄的名字在很多教育研究眼中已经成为了悲观决定论的代名词——珍视个人能动性的教育研究者往往对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弃如敝屣,转向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等的文化生产理论寻求启迪。从欣然接受到质疑,国内研究者对布迪厄的理解和运用正在深化。在经历了初步介绍阶段和广泛探讨阶段之后,中国教育研究对布迪厄理论的运用正在进入深入的反思探讨阶段。(2)李春影,石中英.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回顾与评论.比较教育研究,2018,(8):38-47.
总体而言,当下教育研究对布迪厄理论的运用一面昂扬着批判制度、改造现实的激情,另一面又因为看不到打破教育再生产的希望而透露着绝望、苦闷的颓势。本文指出,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布迪厄理论的碎片化、片面化吸收所造成的。具体而言,布迪厄之所以被广泛看作结构决定论的代表,是因为当前教育研究对布迪厄作品、理论的吸收和运用还碎片化地、片面地集中在对他早期《再生产》《继承人》等作品的讨论,很少对布迪厄后期提炼出的实践理论进行深入的了解。李春影和石中英梳理了中国教育研究中对布迪厄理论的运用,发现“文化资本”“场域”和“惯习”是中国教育研究应用布迪厄理论时使用最为广泛的三个核心概念,“实践逻辑”近年来开始受到了一些关注但相关讨论还是非常有限的。(3)李春影,石中英.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回顾与评论.比较教育研究,2018,(8):38-47.杜亮、牛丽莉和张莉莉也同样发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概念在近十几年的研究中被运用得非常广泛。(4)杜亮等.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进展述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5):40-48.然而,布迪厄非常强调他的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性,指出只有将他的两个或几个概念放在一起进行关系性分析时才能显出某个概念的全部意涵。(5)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因此,不得不警惕的是,“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所受到的倾斜性偏爱,同时也隐含着忽略“文化资本”与其他概念的关系性、忽略布迪厄理论全貌的风险。这种碎片化、片面化吸收的趋势,不仅存在于中国教育研究对布迪厄理论的运用中,在英语学术界也同样如此。布迪厄本人在英美国家进行学术讲座时都不得不多次进行澄清,甚至抱怨英语学术界对此理念的碎片化吸收。(6)Ibid.学术界对布迪厄理论碎片化、零碎化的吸收,与布迪厄建立一种综合性的、整体性理论的愿景是背道而驰的。终其一生,布迪厄始终致力于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超越主观与客观、结构与个体、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二元对立。
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寻
布迪厄在社会学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要超越结构性与能动性、客观与主观、宏观与微观之间二元对立的当代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命题,并且创新性地用实践理论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解答。置身于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学术传统中,布迪厄清楚地看到两者各自的优势和局限。在布迪厄就读于巴黎高师的20世纪50年代,自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以来的结构主义学术脉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布迪厄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便明显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同时,现象学的思潮也正处于其发展的高峰时期,布迪厄曾明确表示自己深受现象学尤其是梅洛·庞蒂和胡塞尔的影响。(7)Derek Robbins,Bourdieu and Culture(New York: Sage, 1999).
布迪厄既深深地受到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从中汲取营养,又始终在试图建立一种突破两者的研究方法论——一种避免客观主义而又不落入主观主义的方法论。(8)Loïc Wacquant,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Sociological Theory(1989): 26-63.在布迪厄眼中,客观主义的不足在于忽视了行动者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而主观主义的不足则在于只关注个体的意识、忽视了个体的无意识。布迪厄批判道,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将社会科学简化为对行动者所给出的“汇报”的再汇报(9)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39-40.,但是,行动者自身对社会生活的“汇报”并不能捕捉实践逻辑中无意识的部分。通过后期对实践理论的反思和提炼,布迪厄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超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目标。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布迪厄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想要超越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结构性与能动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但目标的达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早期,布迪厄的作品还带有更多的结构主义、客观主义色彩。直到后期,他才在研究与反思的基础上找到了自己用来超越对立的路径、建立了更具整合性和整体性的实践理论。
在早期的60年代和70年代,布迪厄还把作为他老师之一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当作重要的学术参考。(10)David Swartz, “Bridging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Religion: Pierre Bourdieu’s Political Economy of Symbolic Power,”Sociology of Religion 57,no.1(1996): 71-85.在布迪厄写于这个阶段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许多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子:无论是在《再生产》中对学校教育制度的分析还是在《On The State》中对国家机制的分析,布迪厄的论述都与阿尔都赛在《论再生产》一书中对学校意识形态机器、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分析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11)Julien Pallotta, “Bourdieu’s Engagement with Althusserian Marxism: The Question of the State,” Actuel Marx 2(2015): 130-143.然而,到了后期的作品如《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布迪厄则经常在字里行间要将自己与阿尔都塞区分开来——多次明确地强调自己“非常反对(阿尔都塞所提的)‘意识形态机器’这种概念”,批评阿尔都赛为“悲观主义的结构功能主义”。(12)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02.
布迪厄对教育场域进行分析的作品——《再生产》《继承人》等,都正产生于在他尚且更具结构主义、客观主义色彩的阶段。这便导致了教育研究者所关注的布迪厄似乎总是带有一种结构决定论的悲观主义色彩。甚至,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种将布迪厄与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进行比较的趋势:认为布迪厄是否定个体主体性的、悲观的结构决定论者,而威利斯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则是歌颂主体能动性的乐观主义者。(13)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然而,这样的论断,不仅忽视了布迪厄理论的复杂性,也忽视了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内部的复杂性。实际上,布迪厄与伯明翰研究中心的成员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如同布迪厄一样,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也始终在寻求主观与客观、结构性与能动性之间的平衡点。更巧合的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深受结构主义的阿尔都塞的影响,而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是出人意料的。之所以出人意料,是因为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创始人们都秉持着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然而他们在继承马克思理论的时候却转向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非卢卡奇等人所提出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将阿尔都塞的理论确立为伯明翰研究中心的理论核心,导致了包括霍格尔特、汤普森在内的老一代领军人物纷纷离开了该中心。但是,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及其年轻追随者的热情之下,阿尔都塞理论的崇高地位在该中心仍然保持了长达十年之久。(14)Kuan-Hsing Chen and David Morley,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David Morley and Chen Kuan-Hsing(Milton Park: Routledge, 2006).可见,无论对布迪厄而言还是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而言,如何处理客观与主观,结构与个体,宏观和微观等之间的二元对立都是一个棘手的、需不断探索的问题。
无论是布迪厄的阶级分析视角还是对“资本”概念的运用,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但是布迪厄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布迪厄一直试图超越的。尽管布迪厄在教育领域往往被看作是冲突论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者们却又往往倾向于将布迪厄看作是涂尔干的追随者(15)Brubaker Rogers, “Rethinking Classical Theory,”Theory and Society 14,no.6(1985): 745-775.——因为对象征符号和象征分类的研究在布迪厄的理论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还有学者指出韦伯才是对布迪厄影响最深的理论家,认为布迪厄理论核心在于分析象征符号控制是如何展开、如何建立合法性的——而这正是韦伯所给予他的理论基础。(16)David Swartz, “Bridging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Religion: Pierre Bourdieu’s Political Economy of Symbolic Power,”Sociology of Religion 57,no.1(1996): 71-85.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可以断定的是,布迪厄绝非是一个简单的冲突论者、一个绝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阶级问题的分析中,布迪厄的理论还糅合了涂尔干的功能主义以及对象征符号的关注,也糅合了韦伯对合法性建立机制的分析。站在众多社会学理论巨匠的肩膀上,布迪厄想做的并非是某一门派的继承者,而是综合各家所长、补各家所短的,超越客观与主观、宏观与微观、结构性与能动性之间二元对立的融汇贯通者。
二、实践的无意识性
正是通过后期对实践理论的提炼和反思,布迪厄找到了超越结构与个体、主观与客观、身体与心灵、宏观与微观、物质与符号等之间二元对立的路径。(17)谢立中.布迪厄实践理论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46-158.布迪厄对实践的重视与马克思一致,而且他自己也明确声明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18)Richard Jenkins, Pierre Bourdieu(Milton Park: Routledge, 2014).但是,布迪厄研究实践的方式又是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只要对经济基础进行充分的研究,便可以揭示人类社会的行动实践了。但是,布迪厄所关注的,并非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和分配,而是作为文化层面的各种象征符号,例如语言、艺术、时尚、学历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继承者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关注与布迪厄类似。但法兰克福学派和布迪厄分析文化的路径又有很大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是大众文化消费背后的阶级意识,归根结底是更宏观的政治分析视角,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除了宏观的结构分析之外,还从认知的层面对个体微观的实践逻辑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一独特的认知分析的视角,使得布迪厄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学家们区分开来。
布迪厄指出,实践在很多时候都是无意识的、前反思性的。在大部分的生活实践中,行动者的惯习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支配着行动者的决策和策略选择。惯习是一系列持久的、稳定的性情倾向,是行动者从过去的经历中所习得的观念、行动方式、思考方式的总和。(19)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惯习往往是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不自知的流露,是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不经意识思考和抉择的自动反应。布迪厄经常用运动员的记忆反应来类比惯习:惯习就如同运动员反复训练所得的自动反应一样,它印刻在个体的心灵和身体之中,分秒之间自动迸发,完全不需要运动员进行思索和判断。通过惯习这样一个概念,布迪厄想揭示的是个体不自知的意图、没有认知参与的对世界的认识、前反思的潜意识的对社会的了解。(20)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9.
布迪厄对无意识的强调,是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挑战,可以追溯到尼采、梅洛·庞蒂的理论当中。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中,心灵是自由意志的主体和认识活动的基础,而身体则被当作是遵循接卸法则的被动延申。而在布迪厄的理论中,行动者的实践在很多时候是受到无意识的、前反思的惯习所支配的。对无意识和身体化的知识的强调,最早可以追溯到尼采对笛卡尔的主体主义的意识哲学和理智主义传统的反对之中。在尼采看来,身体具有比有意识的心灵更加基础的无意识特征,而意识不过是一个派生的现象,是身体的无意识所建构的表层,所谓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不过是人刻意为自身的各种状态所虚构出来的一个统一的解释机制。(21)郑震.身体: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新视角.社会学研究,2009,(6):187-205.在尼采之后不久,梅洛·庞蒂也发展出了身体现象学、提出了对笛卡尔理论中身心二元对立的不满,强调前意识的身体知觉是有意识的心灵的基础。(22)同上.布迪厄本人多次表示,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便体现在布迪厄对身体与心灵、有意识与无意识之二元对立的坚决反对上。(23)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从根本上来讲,否定身体与心灵、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二元对立,也便是否定将行动者作为理性主体的理论预设。然而,现有很多运用布迪厄理论的实证研究,都心照不宣地将个体看作是竭尽所能地、在计算和运筹中换取更多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本以获得或彰显更高社会地位的经济人。这是与布迪厄理论基本立场相悖的。布迪厄本人多次明确地表示,他的理论除了在形式上与经济学理论相似——借用了“资本”等概念——之外,与经济学理论的理性行动者预设没有任何关系。(24)Loïc Wacquant,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Sociological Theory(1989): 26-63.理性行动者的预设深受笛卡尔的意识哲学和理智主义的影响,而布迪厄从出发点上就不认同笛卡尔所提出的意识和心灵作为思维和实践基础的论断。在布迪厄看来,支配个体实践的并非是意识和理性计算的利益,而是行动者的无意识的、前反思性的惯习。(25)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在讨论实践无意识这一理论预设的革命性意义之前,让我们先简要分析一下布迪厄的总体理论框架。布迪厄指出,惯习和资本、场域一起共同决定了个体在具体行动中的实践:(惯习)(资本)+场域=实践。(26)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资本”的概念是布迪厄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借用的,表示可以用于生产或交换以获得更多利益的资源;布迪厄将资本的形式进行了扩展,将其分为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四类。(27)Pierre Bourdieu and John G. Richardson,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ed. Mark Granovetter(Milton Park: Taylor & Francis, 1986), 241-258.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就是由不同的“场域”构成的,场域指的是充满竞争的、关系性的社会空间。(28)Loïc Wacquant,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Sociological Theory(1989): 26-63.布迪厄经常用“游戏”来解释场域,解释他的场域和资本这两个概念如何紧密相连。在纸牌游戏中,每种不同的游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决定了不同纸牌在该游戏中的价值高低;纸牌的价值并非是恒定的,同一张牌在不同游戏中可能就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而每一个场域就像是一个“游戏”,都有着自己特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决定了什么样的文化或符号在这个场域可以作为有效的“资本”流通,也决定了不同的文化或符号之间的价值序列和转化汇率;场域的规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权力便是制定规则、定义价值序列的象征符号权力,阶级斗争便是针对为了争夺象征符号权力、使自己所占据的文化或符号成为有效资本的过程。因此,不同于物理的“空间”“区域”等概念,场域更像是一个战场,是动态的、关系性的、充满了时刻进行着的斗争的。(29)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若是不考虑惯习的无意识性和非理性而是按照理性经济人的理论预设,那么个体在场域中的实践则无非是,争夺象征权力来使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更有价值,或者遵循场域中既定的规则行事以获取更多的货币作为资本;总而言之,行动者的实践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然而,这种理论经济人的理论预设却在以下两方面与布迪厄的理论相冲突。
首先,布迪厄理论强调,个体并非是受利益支配的理性行动者。个体参与“游戏”的前提是,个体认同场域的规则并认为场域所允诺的最终奖励是值得追求的。然而,惯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一个人的观念里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很有可能,个体感兴趣的并不一定是社会主流所认同的追求——例如金钱、地位等。(30)Ibid.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家伙们”便是如此。“家伙们”对学校教育所能允诺的脑力劳动并不感兴趣,认为脑力劳动是女性化的,对学校的纪律言听计从则更是不可忍受的“娘娘腔”做派。“家伙们”所感兴趣的,是彰显自己的男性气概,是父辈所从事的体力劳动。由于对学校制度的胜利品并不感兴趣,“家伙们”也就并不会选择遵循这个场域的规则,而是经常与学校正式制度作对,并且嘲笑那些遵循这套制度的循规生们。(31)保罗·威利斯.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3.可见,经济利益并非是支配个体行动的唯一要素,个体也并非是完全的理性经济人。
其次,布迪厄强调,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眼中的社会规则来参与游戏,但个体对场域规则的了解程度参差不齐。尽管“场域”和“游戏”在很多方面是高度相似的,但是两者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场域的规则并非总是像游戏的规则一样一目了然并且能诉诸语言而口耳相传的。(32)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因此,对于熟悉这样场域的人来说,场域的规则往往是不言自明的;而对于不熟悉特定场域的人来说,个体通常是意识不到其规则是什么的。威利斯的研究揭示,在规则清晰的场域中,受惯习支配的行动者都不一定会认可、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而是倾向于按照自己对男性气概等的既定观念(惯习)来行事。可想而知,在规则更为隐秘的场域中,个体惯习所能发挥的支配作用自然就会更大了。看不清规则何在,个体便只能靠自己的惯习生活了——若是自身惯习与场域期待一致,个体便像水中的鱼一样怡然自得;而若是个体的惯习与场域规则所奖励的不一致,个体便很可能生活在自己的规则里,浑然不知自己的行动居然与场域所奖励的行为相反。
三、超越“主体能动性-社会结构性”二元对立
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文化再生产并非是对个体主体性的否认,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结构之间亦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个体的主体性恰恰是文化得以再生产的重要一环。“主体性”往往与“能动性”合二为一,称为“主体能动性”。根据《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大辞典》和《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人的能动性”表示主体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作用,预设人可以在社会实践中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33)金炳华.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廖盖隆等.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卷.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然而,与马克思不同,布迪厄并不认为人的实践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也不认同人总是可以通过主观意识来认清世界的规律。因而,在布迪厄的理论中,主体性也并非是与结构对立的、要改造世界的主观意愿。相反,由于无意识的作用和惯习的支配,很多时候个体的主观意愿实际上是顺应、维护社会结构的。
在运用“文化资本”和“惯习”的概念时,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它们看作是主体能动性的绊脚石。这样的取向对应的是这样一种预设:即将主体能动性看作是个体想要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以融入新场域、进而实现阶级流动的主观意愿和努力。因此,文化资本的匮乏和难以改变的惯习便无疑是阻碍个体改变自身的结构力量。在这种视角下,主体能动性是苦苦挣扎却求而不得、无法逃离的绝望与无助。
然而,这种将主体能动性与结构对立起来的视角,完全不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本意。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中,主体能动性并非只是指个体有意识地想要逃离原有阶层、突破结构限制的愿望和努力,也是个体无意识地守着自己原有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执着和坚定。例如,威利斯笔下充满叛逆性的“家伙们”,虽极致地彰显了他们不受学校体系控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但他们的反学校文化却又是深深地扎根于看重男性气概、偏好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文化,是他们惯习的反映。“家伙们”的文化生产一面代表着对学校文化、对既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反叛,一面也体现着工人阶级文化代际传承的结构性。正是由于惯习的存在、日常实践的无意识性,行动者的主体性和结构性从一开始便交织在一起了,“剪不断理还乱”。“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是创造性的体现,却也是结构性的注定。那些将布迪厄看作是结构决定论、看作是悲观主义的诠释,正是忽略了主体性与结构性之间相依相存的这种复杂关系。
主体性和结构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表明,个体的惯习之所以难以改变,不仅是因为新的行为方式会使得个体感到不适应、不舒服、不自然,同时也是因为个体的观念和思考方式在无意识地拒斥新的行为方式、新的观念和态度。新旧价值观、新旧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会使得个体陷入矛盾之中。面临这种矛盾,个体可能会舍旧从新、积极地拥抱新场域的文化规范,也可能会对新场域的文化规范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甚至加以贬低、嘲讽。
因此,个体要学习新的文化、行动方式或规范,首要的便是要反思自己无意识之中的漠不关心或者或拒绝与排斥。然而,由于实践往往是无意识的、前反思性的,个体的自反性也是有限;所以,要促进个体对新文化观念或规范的学习,就需要向个体解释新场域中或明或暗的规则,并且向引导个体认识其在进入新场域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和场域。正如理查德·吉恩柯斯(Richard Jenkins)所言,关于场域规则的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34)Richard Jenkins,Pierre Bourdieu(Milton Park: Routledge, 2014).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也指出,关于场域规则的知识本身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种文化资本,很有必要向大学中的工人阶级学生解释高等教育机构等场域规则。(35)Annette Lareau,“Cultural Knowledge and Social Inequali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no.1(2015): 1-27.
四、总结
本文指出,强调实践逻辑中的无意识,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关键核心。然而,实践的无意识是被许多教育研究者所忽略的,这使得很多运用布迪厄理论的教育研究呈现出一种结构决定论的色彩。现有研究往往将布迪厄理论中的行动者看作是理性的、计算的、目标导向的经济人。但事实上,布迪厄理论中的行动者并非完全是理性的,相反,行动者的实践往往是无意识的、前反思性的、非理性的。正是因为忽略布迪厄实践理论中所强调的无意识,不少运用布迪厄理论的教育研究经常将结构性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冲突的二元对立,进而呈现出一种结构决定论的悲观主义。只有考虑到行动者的非理性、实践的无意识性,“惯习”在布迪厄理论中调节结构与个体的意涵才能被充分理解,布迪厄的方法论区别于客观主义-结构主义与主观主义-主体主义的创新之处才能被揭示,运用布迪厄理论的教育研究也才能避免千篇一律地重复“再生产”论调,才能更深入地揭示如何提供激发个体能动性的教育性支持。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不只是对教育体制中再生产机制的揭露,也是对文化学习过程的揭示。正如廖青和黄绮妮所指出的,当下学术界在运用“惯习”概念时往往错误地将其看作是不可更改的固定秉性、往往忽略了惯习的开放性。(36)廖青,黄绮妮.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的惯习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2):76-82.本文强调,对实践感的研究,能更深入地解释惯习为何难以改变,进而揭示惯习何以可能改变以及支持惯习的改变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性支持。唯有将对实践逻辑的分析纳入研究范畴,教育研究才能更深入地继承并反思布迪厄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化脉络的实践逻辑进行研究,是中国教育研究者对布迪厄的理论进行本土化发展,与布迪厄理论进行进一步对话并对其进行反思甚至批判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