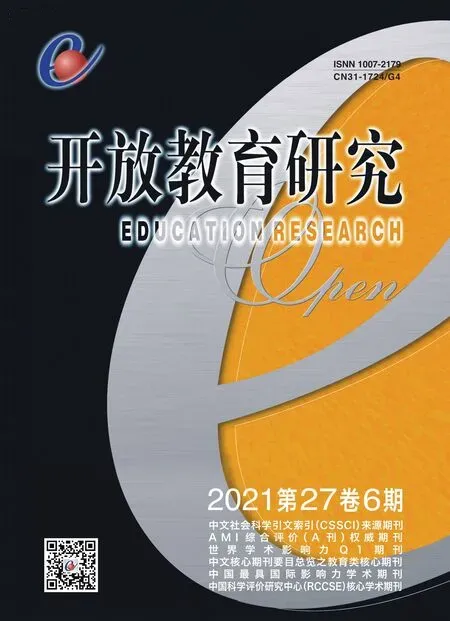人工智能教育中“人—技术”关系博弈与建构
——从反向驯化到技术调解
孙田琳子
(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Ellul,1983)曾说过,现代技术已发展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技术应用的不良后果与有益影响是不可分离的,一切技术进步都是有代价的。在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冲击下,人的主体性地位开始受到威胁,人机界限变得模糊。“赛博人”“数字劳工”等新概念不断萌生表明,技术不再是人的附庸和延伸,而成为人类主体的一部分,人机合一的“技术人”假说正演变为现实。这一境遇迫使人们思考到底是人改变了技术,还是技术改变了人?教育中的人与技术如何达成和解?随着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在教育领域的迅速普及,教育发展的效益性与技术运用的负效应之间长期博弈与共存,技术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变革了教育中的人技关系,警惕教育过度技术化等批判呼声催促人们重新审视教育主体与教学技术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智能时代,教育主体与新兴技术如何建构新型的“人-技术”关系是当下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
一、现代技术裹挟下的教育伦理审思
科技革命虽已成为驱动教育发展的新引擎,但“技术的逻辑”有时会背离人们的初衷,偏离预设的轨道,挣脱人们的控制,甚至导致公开或隐蔽的反主体性效应(孙伟平,2020)。教育实践长期依附智能技术的宰制,将会引发教育主体的行为异化和认知退化。
(一)技术反向驯化促逼主体行为异化
“驯化”是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其词源演变于“家居化(domestication)”,意思是媒介技术经过消费过程进入人们的私人空间——即家居,成为日常生活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驯化动物”与“驯化技术”的演化过程进行类比:被驯化的动物习惯得到人类的照料,逐渐成为家庭成员之一;同理,电视、电脑等媒介技术由于满足受众需求在家居空间中得到一席之地,媒介技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必须接受驯化过程(罗杰·西尔弗斯通,2004)。而技术的“反向驯化”是指人与技术从属关系的颠倒,技术在介入人们生活的过程中渐渐支配与控制人的社会生活,人们的行动决策不自觉地受到技术的约束和影响,造成去主体化和行为异化等失调现象。技术和人类是一对互相依存的矛盾关系,人类创造了技术,而技术在被不断驯化并纳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也在以自身的技术意向结构“规训”着社会主体,媒介技术从帮助人探索和描述世界转为“促逼”人类在技术限定的关系中生存(刘千才等,2018)。从古希腊柏拉图《斐德罗篇》里的塔姆斯法老认为文字的出现会让人们依赖外在符号而使记忆退化,再到现如今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饭前拍照”的用餐行为、导航软件成为司机的不可或缺,都证明了这一点。吴国盛(2016:67)指出钟表等时间工具的发明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像吃饭、睡觉这些事情往往不是由于你的生理反应,而是因为“时间到了”。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技术正是因为代替了人类部分的行为功能,导致面对问题时人们不愿再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反而更愿意选择技术的方式,结果是机器越来越“聪明”,人却越来越“笨”。可见,智能产品的惯性使用致使人们不愿主动思考,人类在改进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在反向驯化人类,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行为和思维。
(二)智能技术惯性使用构筑知识茧房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由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提出,指人们在信息领域习惯性地被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认知禁锢于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信息茧房意味着人们的选择性注意自动筛选相近资源信息、过滤其他干扰刺激;从行为科学来看,行为偏好促使人们借助自己的偏好做出具有倾向性的选择与决策。随着大数据算法的日益演化,用户画像愈发精准,长此以往,学习者的关注喜好不断被个性化推送充斥,失去接触多元化知识的机会,从而困顿于信息窄化的“知识茧房”。在新技术的不断渗透下,人们抛弃了纸质书籍而对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爱不释手,思维习惯从线性的文字阅读转变为发散的图像阅读,碎片化知识带来的虚假获得感使人误将“知道”视作“理解”。若学生长期接受智能技术的精准推送,不仅剥夺了他们主动选择的权利,还将破坏其对新事物的原始感知,干扰深度学习和独立思考,形成固步自封的认知囚笼。假使教师过于依赖教学技术,原本生机勃勃的课堂将会在电子监视设备的裹挟下演变成福柯(Foucault)笔下冰冷透明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技术垄断了教育管理的权力,学生沦为被规训的监视对象,形成信息不对等的倾斜关系。传播学中“容器人”的概念也体现了现代人与媒介技术之间顺从或反抗的挣扎过程,大众媒介的长期麻痹致使人们变成自我封闭的容器。技术的革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性,技术越智能化,留给人们的自主空间就越少,难免会搁置人们的部分思想和体验。频繁寻求技术的帮助对于新生代学习者来说更像是饮鸩止渴,在获得片刻的效益满足后慢慢侵蚀他们的独立人格。人们不得不站在长远立场,警觉智能技术引发的学生认知发展固化和主体地位式微等问题,严防教育主体沦为技术产物的“附庸”。
二、教育主体与教学技术的三种博弈形态
追溯技术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技术从人们谋生的工具手段逐渐演化成具有“思想”和行为能力的似人又非人的某种存在,其“拟主体性”愈发显现,特别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更呈现出人际拟态的特征。教育主体和教学技术作为利益相关方,为寻求自身发展,在不断相互作用中产生冲突失衡、又渐趋于平衡的博弈关系。
(一)对立与失衡:“人-技术”关系嬗变下的教育场域
从石器时代到蒸汽时代,机器生产已然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发明推动社会走向工业文明。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技术被普遍认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手段,此时的技术是作为被利用、被控制、没有主观能动性的人造物,实用和效率是工具理性的价值尺度。利益驱动人们强调技术的目的性和实用性,漠视人的情感需求和精神价值,难免引发人的异化和物化。然而,现代技术从被动的客体存在逐渐进化为自主行动的拟主体存在。在机器经历了从“个体形态”到“主体形态”的演化中,人与技术之间的从松散耦合关系发展为主客体倒置,技术物表现出更多的自动性、主体性和智能性(成素梅,2020)。直到机器拟人化、人类机器化等极端现象的出现,“人-技术”关系又重新被检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工业发展对人性的反作用,人的劳动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变成了奴役人的异己力量,从而造成人的片面发展。海德格尔(Heidegger)认为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并将现代技术本质归结为促逼人的“座架”(enframing),人的本质在技术异化下消失殆尽(马丁·海德格尔,2005)。芒福德(Mumford,1963)从人类学视角批判了以“巨机器”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对人类的控制,认为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技术,技术的本质是人性精神力量的外化。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将人类社会演变分为“工具使用”“技术统治”“技术垄断”三个阶段,技术突飞猛进使人们无所适从,呼吁警觉技术对一切意义和价值的垄断(尼尔·波兹曼,2019)。依此来看,当人们一味关注自身主体性时,征服自然和控制外界事物的欲望愈发膨胀,就会陷入技术工具论的窠臼;当技术具备与人类相比拟的主体性时,人性就会被非人性、技术性的力量所压迫。长此以往,人与技术之间彼此割裂与对立,不可避免地陷入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状态。
这种技术悖论也存在于教育场域,教育主体与教学技术之间常常会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教学技术既影响教育主体追求的目的,反过来也影响教学生活和使用技术的人,产生违背技术目的的后果(付强,2020)。在技术工具论的视野中,教学媒体是一种没有生命的、传递知识的工具或手段,以“效果与效率”为核心的传统技术功效背后隐喻了只重视知识传递效率的“预成性”教学观(张刚要等,2017)。工具主义教育观桎梏于“知识本位”的传统思维,将教育目标与价值生生剥离,把学生视为生产流水线上“输入—产出”的物品,忽视培育过程的情感投入与人文关怀。在此价值取向下,教育难免培养出千篇一律、像机器一样的人,背离了育人初衷。当人工智能介入教育领域,高效便捷的技术温床使教育主体慢慢丧失能动性和判断力,滋生惰性思维,顺应数据算法所提供的便利,却被智能技术的反作用侵噬。依此来看,计算主义盛行下的教育实践应谨防被技术反向驯化的危机,从技术至上回归以人为本,避免受物化思想干扰培养单向度的人。
(二)适应与平衡:经验转向下的“人-技术”关系建构
伴随20世纪80年代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跨越了传统技术哲学悲观主义的藩篱,开始关注技术对人的积极作用,试图寻找人与技术之间的某种平衡。唐·伊徳(Don Ihde)吸纳了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技术具身思想,论证了知觉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性,从现象学视角将人与技术的关系分为具身关系、解释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技术成为人与世界居间调节的中介。斯蒂格勒(Stiegler)提出“代具”理论,即技术弥补了人在世界中生存的先天缺陷,形成了“人-技术”的人性结构,这意味着人与技术需结为一体才能感知到世界的全貌。拉图尔(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关系思维引入哲学分析,每个行动者为主体,人与技术处于相互认同、相互影响的对等关系,要在二者相互作用的场域中寻求稳定点。伯格曼(Borgmann)用“装置范式”思想揭示现代技术的本质,技术凝结了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人们可借此控制社会发展进程,超越海德格尔的悲观技术立场(孙田琳子,2020)。德雷福斯(Dreyfus)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局限应归结于意识生成问题以及无法摆脱对表征的依赖,这表明人类智慧也有智能技术无法超越之处(孙田琳子,2019)。莱文森(Levinson)认为新媒介是对旧媒介的补偿,强调技术发展的人性化趋势(保罗·来文森,2011)。在此境遇下,人与技术经过不断的调适与演化逐渐发展成一种互为关照、互相补充的关系,人类创造并改进了技术,技术延伸了人的生活世界,作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形成了趋于平衡的“人-技术-世界”结构。
教学媒体不断从单一机械化向智能多元化升级换代,教育场域中师生主体与教学技术之间也逐渐形成了互相依存的适应状态。随着现代技术的革新,教学技术不断“代具”了师生自身的不足。譬如,智能测评技术弥补了教师分身乏术的有限精力,虚拟现实技术拓展了学生的感官体验,智能导学系统强化了学生的教学存在感。人工智能在学习过程中发挥着延伸作用,并通过构建融合共生的人机关系,形成“人-技术”的存在结构(安涛,2020)。同时,教学技术的具身功能催生了人与技术行动一致的教学活动。当学生或教师非常熟练地使用智能技术,以至于感觉不到教学活动中技术的存在,这时技术发挥着隐形、透明的具身功能,也将技术促进教学的真正效益发挥到最大化。为达成共同的教育目标,教育主体与教学技术之间的对抗逐渐消解,磨合形成内在一致的关系结构,技术在融入教育的过程中愈发彰显出人性化趋势。追求工具在教育中的上手状态而非霸权统治才是技术恪守职责的表现(李芒等,2020)。
(三)融合与共生:技术调解下的“人-技术”关系重构
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数据系统每天都在自我更新与演进,自动完成认知、决策和执行等常规任务,因而,智能技术展现出更多自主性和主体性,“人-技术”关系开始呈现出一种主体间性,甚至技术有时可以影响使用者的行动轨迹。技术工具论认为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其伦理属性由人的使用方式决定;而技术实体论认为技术可以作为独立的道德能动者,故此技术人工物具备了伦理意蕴。荷兰技术哲学家彼得·保罗·维贝克(Peter - Paul Verbeek) 的技术道德化思想肇始于伊德的人技关系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伯格曼的装置范式理论,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发展了技术调解论,试图构建新型“人-技术”关系。他认为道德决策是人类和技术人工物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以物化的形式发挥着道德“在场性”的规范作用。有学者将这种技术的意向结构所规定的价值取向称为“技术的逻辑”(吴国盛,2016:9)。例如,刀这种工具的意向结构指向了它的切割功能。严格地说,意向性始终是一种人与非人意图的混合事物,即一种复合意向性,在“人-技术-世界”关系中,意向性分布于人与非人之中。因此,技术引导功能的实现路径是:道德→技术→人工物→引导→人的德性(贠兆恒等,2019)。基于后现象学视野,维贝克的技术调节论将人与技术视作相互连接的共生体,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与技术之间的二元界限,技术从行动层面改变了人的行为,也从知觉层面转换了人对世界的认知(李洋,2020)。在道德物化的视角下,教学技术与教育主体实则是道德共同体的共生关系,一旦拥有一致的行动目标,双方利益都有所扩充,将会构成双方共赢的“正和博弈”局面。
鉴于维贝克的道德物化理论,在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中人们可以充分发挥技术的调解作用,将某些价值理念嵌入教学技术引导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形成双向促进、协同发展的“人-技术”关系。如此一来,一方面提升教学技术中教师角色的价值存在,即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与主导者,不仅可以决定课堂中技术何时、以何种方式“入场”,还能通过设计技术的使用脚本引导学生学习。在技术调解下,教师的思想、观念、方法依托教学技术的使用过程而展现,通过技术产品的设计、开发与应用等环节规划学生的学习路径;另一方面,促进生成融合共生的“人-技术”关系。规避技术负效应的有效解决办法不是放弃使用技术,而是将人与技术形成协调一致的统一体,二者不再是对立或压抑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显现离不开人的使用,人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效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应取长补短,构成行动共同体,使教育效益最大化,形成平衡的、伦理自洽的教育活动(孙田琳子,2021)。
三、技术调解视域中人工智能教育的实践向度
一直以来,人与技术互构的平稳进程因为技术功能的急剧膨胀而失衡(张务农,2019),技术的反作用时常引发背离教育初衷的两难困境。在此,本文试图从技术调解视角探索如何化解人与技术的矛盾关系,并从“人-技术”关系维、技术维、主体维等层面建构人工智能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关系维:基于复合意向性的人机协同体建构
科幻作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1982年首次提出“技术奇点”说。雷·库兹韦尔(2011)进一步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技术都是以指数级增长的形式发展,机器智能将在未来某一时间节点超越人类智能。若此,人与技术之间的抗衡将变得岌岌可危,不论智能时代是否来临,寻求平衡和谐的人机关系是规避社会风险的可能出口。技术调解论作为当代技术伦理学的新思潮,强调现代人与技术之间交互关系的有效建构,弥补了技术哲学发展中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的不足,成为注重技术物质性与道德性的第三次转向。其中,维贝克的复合意向性探讨了技术意向性对于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建构作用,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建构中不只是中立的工具或手段,还调节人的知觉、理解与行动(李日容等,2018)。后现象学视域下的技术意向性呈现一种建构性技术伦理立场,这种人机交互的意向性通过互相建构的方式缩小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彼得·保罗·维贝克,2016)。至此,人与技术争夺主体性的长久博弈在复合意向性的指引下最终达成和解。
不论是传统的黑板教具还是现代的智能导学,教育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唯有教育主体与教学技术化解对立、融为一体,才能调和技术给教育带来的负作用。为防止再次陷入技术凌驾人的窠臼,教育场域中的人与技术需构成相互规约与牵制的交互关系,充分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技术的引导作用,建立双向平等的主体间性,形成目标与行动一致的人机协同体。现阶段的人机交互仍以“机器→学生”的单向反馈为主,“学生→机器”的反馈渠道和信息匮乏,可见,形成人机双向的反馈机制,构建主体间性的新型人机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董艳等,2021)。除了增强双向反馈外,构建人机协同体需把握机器智能性与学生自主性二者间的设计尺度,既能保障信息技术对学习者的学习支持,又要避免学生对技术的过度依赖。这要求改进智能技术的算法模式,保留学习者的自主权,根据任务情境嵌入需要他们主动思考的内容;其次,要唤起学习者的主体意识,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价值判断能力,打破信息茧房的枷锁。人工智能能为教育者分担重复机械的知识传授工作、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但人们更应坚守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注重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提升教育主体的主导性,以防主客体关系变迁下技术对人的反向驯化。
(二)技术维:嵌入智能技术脚本的教学活动设计
透明性(transparency)、可解释性(interpretability)和可说明性(explainability)是AI复杂算法的重要原则。人工智能的使用算法分为“黑箱”和“白箱”,白箱模型对于人类专家来说是可以理解和解释的,但对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黑箱模型却难以解释,对其盲目使用不仅危险且有悖伦理。这也佐证了技术本身就蕴含伦理价值。倘若人们在算法的“黑匣子”中调控技术的伦理成分,从根源上引导技术向善发展,也许是走向人机和睦共处的突破口。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主体间的交往离不开潜在的秩序,即理性和价值的引导。道德物化思想强调技术人工物的内嵌价值,而其理论思想的落地在于“前思式”设计,即在初始环节通过技术结构和功能的设计,限制、引导以保障最终结果的正当性,将技术的内嵌道德理念外显出来。拉图尔提出脚本的概念揭示技术物对人及其行为的引导作用,即利用技术产品自身的功能或局限预设使用者的行为路径。换言之,技术其实早就规定了使用者该如何行动。比如,马路减速带的脚本是“靠近时请减速”的安全提示,一次性塑料杯的脚本是“用完请丢弃”的使用说明。技术产品的设计者需关注与提升前置性伦理敏感度,让设计者将道德物化思想以及价值敏感设计的框架引入创新活动的起始环节(贾璐萌,2021)。
鉴于此,智能技术介入教学活动,应充分发挥现代科技的主动性与调解性,将技术脚本与教学情境结合起来,使教育主体在使用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完成预期、合乎教育规律的活动轨迹,通过技术脚本的前端设置规范后续的技术实践活动。例如,当学生自主完成某一学习内容时,智能分析技术将根据他的学习数据推送结构匹配的后续知识单元,并随着机器学习的不断增强形成“量身定做”的教学路线;中学生搜索网络资源时,可通过人脸识别设置“青少年模式”以筛选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当学生跟不上课堂节奏时,可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时识别教师话语中的关键词,快速提取并生成听课笔记;当其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时,可通过自发式预警功能提醒其适度休息、劳逸结合;当操作行为触及到他人权益时,可运用预警技术设置提醒、追踪、问责等机制规范学习者行为。教学技术的脚本线索相当于教学活动的教案逻辑,是教学设计者所持有教育理念的本质隐喻。因此,教学者可通过技术脚本的前置设定引导并调节学习者的行为,将教育理念、目标、方法、评价、情感等内容有机融入智能技术或产品的研发脚本,形成教育与技术双重价值逻辑下的教学活动设计。
(三)主体维:立足技术伦理的科技伦理素养培养
技术调解理论指出技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调节作用,但并不是站在技术决定论立场视技术为决定性力量,而是将技术视为调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方式,其落脚点在于关切人的感知与行为。此外,技术使用者的真实使用情况就好比技术物使用语境中的黑箱,易诱发反弹效应,如节能灯的发明没有节能反而造成人类的过分使用与资源浪费(史晨,2020)。因此,除关注设计者的伦理责任、技术物的道德能动性外,还需从技术使用者入手,培养其正确的技术观念,规范技术使用行为,提升使用者的科技伦理素养。科技伦理素养指通过自我认知和外部教育共同作用下对科技道德规范的认同以及自觉履行的能力(姜春林,2007)。科技伦理素养培养需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逻辑,是将科学之求真、道德之求善统一起来,从而达到“真善美”的至高境界。
近年来,人工智能课程已逐渐融入基础教育体系,成为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计划之一。然而,伴随着智能技术的低龄化使用,中小学生滥用技术的新闻事件时有发生。例如,疫情期间恶意差评“钉钉”软件迫使其下架、恶搞以假乱真的“换脸”视频侵犯他人肖像权等。这些社会乱象让教育工作者不禁反思,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教育到底是要培养精通智能技术的“专才”,还是适应智能时代的“人才”?事实上,此类问题早已初见端倪。因此,随着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的普及应用,开展高校工程伦理教育,应转向关注中小学阶段的人工智能伦理教育,青少年不仅是新一代的技术使用者,更是未来可能的技术开发者。青少年正处于道德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启蒙教育不仅要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与编程思维,更要培养他们的科技伦理和社会责任意识,在技术实现与伦理反思的同步教育中正确认识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新一代负责任的数字公民。这要求教育者要加强技术伦理的有机融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分阶段培养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扭转“重技轻德”“重理轻文”的价值倾向,在科技教育中融入道德教育,从道德认知和情感体验等方面提升学生的技术责任感。其次,教育者需从技术的选择、应用、管理等环节着手,合理引导学生的使用行为,通过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将技术伦理观转化为自身稳定的行为方式。
总之,现代技术对人类主体的反向驯化到正向调解表明,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从人机界线转向寻求融合共生的演变进程,需重新深思教学技术与教育主体的关系流变,探索技术调解下的应然教育实践。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不能走上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应将技术应用的理性反思融入教育发展之中,前瞻性地厘清教育主体与教学技术之间的关系,警惕技术自主性日益膨胀对人们主体性的反向压制。教育者应加强学生技术责任与科技伦理的培养,谨防技术依赖下的本末倒置,建构融合共生、平衡协同的应然人机关系,促进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可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