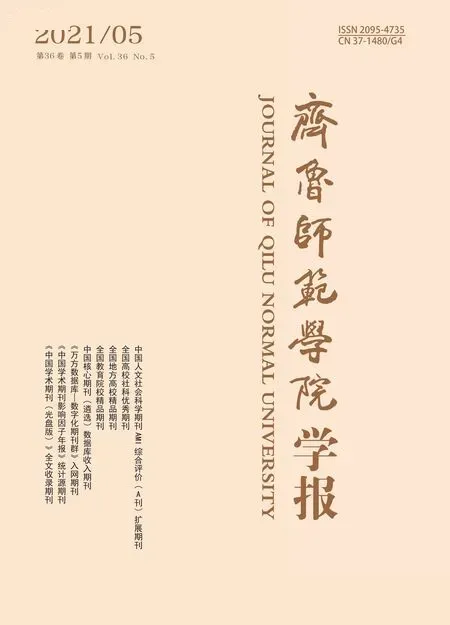《经义述闻·春秋左传》校勘商榷六则
刘泽琳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经义述闻》是清代学者王引之撰写的一部学术札记,该书“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法发现典籍讹误。其“治古书”的成就在乾嘉时期达到了高超的地步,并在校勘中形成了独特的校勘方法,将经典中的字句致误之由总结为“衍文”“形讹”“上下相因而误”“上文因下而省”“增字解经”“后人改注疏释文”等六个方面,又提出了“三勇改”和“三不改”原则。以上观点虽不具有成型系统的理论体系,但仍可视为王引之对校勘理论的探索。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笔者在研读《经义述闻·春秋左传》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一些词条的校勘还有可商榷之处,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试做补正,以就正于方家,亦可对《左传》文义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隐公五年 “鸟兽之肉不登于俎”
本《传》曰:
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1]1727
《经义述闻》:
释文“鸟兽之肉,一本作其肉。”引之谨案:一本是也。此以“鸟兽”二字绝句,“其”字下属为义。言鸟兽固畋猎时所射,若其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此鸟兽也,文义甚明。[2]967
王引之引《经典释文》异文,证“鸟兽之肉”作“鸟兽其肉”,又言“鸟兽”之下当断句,“其”字下属为义。则“其肉”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并列表假设,后句“公不射”为结果,皆是合乎古制及国君行为规范的体现。然此校勘成果对后世影响较小,王氏之说尚未见后世学人引用,如善引王说的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此处传文时均未提异文之辞。
若依王氏所言,则可议之处首先在于“其”字与“之”字可否通用。就此句文义与语法而言,原文“之”字应训为“其”字,二者皆有指代之意,文义互通。同为高邮王氏四种之一,《经传释词》就对“其”与“之”的用法作出了定义,认为二者皆为“指事之词”,又引《尚书·康诰》等六例[3]109,得证:
“其”与“之”同义,故“其”可训为“之”,“之”亦可训为“其”。①
故为何王氏知晓“其”与“之”同义,却在本条目中强加校勘?正如王叔岷所言:
“之”字不必作“其”,“之”字亦下属为义,“之”犹“其”也。王氏《经传释词》九例证甚多,惜忽于此耳。[4]6
且“之”字训为“其”字,在其他虚词专书当中亦有同类说法。如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中载有:
“之”,“其”也,见《吕氏春秋·音初篇》注。[5]721
说明先秦时期就有“之”字作“其”义之解。裴氏认为“鸟兽之肉”中“之”字作“其”字乃后人据文义而改,并举多例证明《左传》中多以“之”字为“其”,而作“之”字者为古本。①杨树达《词诠》中亦举多例证明“之”字用与“其”字同,是探下文而指。①正如《尚书·西伯戡黎》中“殷之即丧”可释为“殷其即丧”[6]117。故由上可知,王氏作“其”字无据。原文作“之肉”,亦训为“其肉”,与王说无异,无需改字。
至于王氏所言“鸟兽”之下当断句,亦有问题。王力先生在其《古代汉语》中说:
在上古汉语里,“其”字不能用作主语。在许多地方“其”字很像主语,其实不是的;这是因为“其”字所代替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名词,而是名词加“之”字。[7]355-356
可知在本文中,“其”字相当于“鸟兽的”的用法,作宾语。若王氏作“鸟兽,其肉不登于俎”,则“其”字之义与上文“鸟兽”二字相重,又导致下文“皮革”“齿牙”诸类缺少定语,破坏了上下文的平衡结构。李学勤即将此句点校为“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8]1672。此句法亦同《战国策·赵策》中言“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
最后,从旁证来说,王氏仅凭《经典释文》中所提异文为根据,缺乏可信度。一方面,王引之在校勘异文时,往往会采用唐代开成石经范本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的引文作为旁证,而“鸟兽其肉”一语不见于以上诸材料中,可证后世传本并不以“鸟兽其肉”为确本;另一方面,多数《左传》注本并未引此异文,或因《经典释文》而仅言“一本作其肉”,亦无旁证。
故在无直接证据表明“鸟兽之肉”原作“鸟兽其肉”的情况下,“之”字无需改为“其”字。
二、僖公四年 “汉水以为池”
本《传》曰: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1]1793
《经义述闻》:
《经义杂记》曰:“《释文》作‘汉以为池’,云:‘本或作汉水以为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成山在南阳叶县南。汉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则‘方城’者,山名;‘汉’者,水名。《传》文‘汉’不言水,犹‘方城’不言山也。”家大人曰:臧说是也。他书所引,多作“汉水以为池”,盖后人依已衍之《传》文加之也。《商颂·殷武》正义引服《注》云:“方城,山也。汉,水名。”若《传》文本作“汉水”,则服《注》为赘语矣。自《唐石经》依或本加“水”字,而各本皆沿其误。[2]987
王引之引臧琳《经义杂记》之说,据《经典释文》异文作“汉以为池”,故“水”字为衍字。又依杜预释“方城”为山名,“汉水”为水名,认为“汉”后不当言“水”,正如“方城”不言山。王念孙依《诗经·殷武》正义中引服虔所注“方城,山也。汉,水名”,认为若原文为“汉水”,则服注“水名”为赘语。以此三说,故言此衍文自《唐石经》有之,他书所传“汉水以为池”皆是后人依据已衍之文所讹。
首先,《经典释文》异文本是一说,未有确证。若如臧说,则王氏改字略有牵强。杜预所言是建立在将“方城”释为“方城山”的基础上的。然就“方城”的释义来说,除上文杜预释为“方城山”外,还有“城塞说”“城邑说”“长城说”等观点④。若“方城”之名即是城塞、城邑之义,本不用言山,又何谈“汉”后不当言“水”?换言之,“方城”言“城”,则“汉水”为何不当言“水”?对于臧氏所言,后世学者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如杨伯峻言:
王念孙据臧琳说,以‘水’字为衍文,其实不确。[9]293
故此处仅据杜预注以反驳传文,确有可议之处。而凭服虔释“汉”为“水名”,亦不可推断出原文本无“水”字。在汉代注解家中,注“某水”为水名并不是个例,如《史记·大宛列传》索隐引服虔注释“盐水”为“水名”[10]3175,另有高诱注《吕氏春秋·离俗览》释“募水”为“募,水名也”[11]511。由此可证,王说无凭。
其次,就修辞而言,“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指用方城作为城,用汉水作护城河,是外交辞令上的骈行对仗。竹添光鸿引松崎之言,认为:
“方城”复名,“汉”单名,故《传》加水字以取整,乃古人措辞之常。[12]401
可看出“方城”与“汉水”并列,均是楚国的防御措施,利用简洁的文字体现出楚国境土之远、城池之险,正如前文齐侯所言:“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故此处的“汉水”并非是因“水”而衍,而是为求工整而作。《文心雕龙·史传》赞颂“辞宗丘明”,《史通·申左篇》盛赞左氏的语言“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皆指《左传》语言整齐而富有节奏。
最后,依据王氏父子所言,后世所载“汉水以为池”皆是“盖后人依已衍之《传》文加之也”,则将后世类书,如《文选》《太平御览》等书中“汉水以为池”的记载纯粹归纳于“因袭谬误”,似乎太过绝对。因此,“汉水以为池”不应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校勘问题,“汉水”对“方城”,是《左传》为对仗工整、行文有致而特意骈行偶句,此种说法是比较有合理性的。
故依据以上观点,王氏之说未必可信。本条与上条“鸟兽之肉不登于俎”异文均是来源于《经典释文》。而此书本在校勘时,本是选择一个底本,然后引各本异文而校。由此可见,文献异文既可以启发学者辨讹误,也可能会误导学者,出现校勘错误。
三、僖公二十八年 “以相及也”
本《传》曰:
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1]1826
《经义述闻》:
杜注曰:“以恶相及。”引之谨案:“及”字之义不明,故杜增成其义曰“以恶相及”。然《传》文但言:“相及”,不言“以恶”也。今案:“及”当为“反”,字之误也。“相反”谓相远。韦注《周语》曰:“反,远也。”上文曰“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从”与“远”义正相对。上文曰“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相从则协,相反则不协矣。僖五年《传》曰“陈辕宣仲怨郑申侯之反己于召陵”,宣十五年《传》“楚子使谓解扬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赵策》曰“赵使姚贾约韩魏,汉魏反之”,《淮南·诠言篇》“约束誓盟,则约定而反无日”高注曰“反,背叛也”,义并与此同。[2]1008
在王引之看来,“增字解经”是经典训释之弊,并言:
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于文句之闲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2]1965
王引之据此驳斥杜预“以恶相及”之解,认为“相及”应作“相反”,为相远之义,与前文“相从”相对,又与“不协”相通。然而,王氏仅凭主观判断认为杜预所言不确,无实际证据。又凭《左传》言“相及”不言“以恶”来判定杜注有误,校为“反”字,缺乏逻辑关系。关于“及”字之义,林尧叟、刘绩等注解家,皆作“以恶(祸)相及”⑤。“及”字在古籍中也多作“牵涉”之解,不单指祸事等负面现象。如僖二十四年《左传》:
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1]1817
杜预将其释为“先亲以及疏,推恩以行义”,又如隐六年《左传》:
长恶不悛,徒自及也。[1]1731
即言“长恶不止,因以害自及也”,此处“自及”与“相及”用法相同,将此“及”字之义放置“以相及也”之中,文义亦通。故如杨伯峻所言:
“及”本有及于祸害之义……王说改字无据。[9]469
竹添光鸿亦言:
凡《传》言“及”者,皆谓死亡,其自致死亡者单言及,此谓同盟相俱死亡之,故云“相及”也。[12]616
从此义来看,“相及”是祸及之义,强调违背宛濮之盟的后果。安井衡亦认为:
《传》言‘及’者,皆谓死亡,其自致死亡者,单言及,此谓同盟相俱死亡之,故云相及也。王引之以‘及’为‘反’字之误,大谬。[13]61
其次,就文义论之,杜注“相及”是说明“有渝此盟”之后果,而王引之校“相及”为“相反”,虽贴合前文“相从”“不协”,却是改变文义。又就王氏所列举的四个例子而言,“反”字皆是背叛之义,放置于此种语境之下,于理不合。
因此,杜注言“以恶”补足文义,并无疏漏,原义应为“若渝此盟,因以恶相及”。王说改字无据,并无意义。
四、文公元年 “杀女而立职”
本《传》曰:
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太子商臣。商臣闻之而未察,告其师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从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1]1837
《经义述闻》:
陈氏芳林《考正》曰:“《韩非子》作‘废女’,上云‘黜商臣’,似作‘废’字为允,然江芈怒,故甚其辞,读者正不必泥也。”又曰“唐刘知几《史通·言语篇》引作‘废女’。”引之谨案:《韩子》及《史通》并作“废”,是也。上言“黜商臣”,下言“能事诸乎”,则此文本作“废女而立职”明矣。若商臣被杀,又谁事王子职乎?《列女传·节义传》载此事曰“大子知王之欲废之也,遂与师围王宫”,亦其一证也。“废”字不须训释,故杜氏无注。若是“杀”字,则与上下文不合,杜必当有注矣。自《唐石经》始从误本作“杀”,而《史记·楚世家》亦作“杀”,则后人依《左传》改之耳。若谓江芈怒而甚其词,则曲为说也。古字多以“发”为“废”,《传》文盖本作“发”,“发”“杀”形相近,因误写为“杀”矣。[2]1017-1018
文记楚成王欲废黜太子商臣而立公子职,商臣欲了解此事真假,遂听从潘崇之计,设宴招待江芈而故意表示不尊敬。果然江芈发怒,说出“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之语。而后商臣确定此事为真,随即弑杀君父楚成王,坐上国君之位。陈芳林与王引之皆认为“杀女而立职”中“杀”字当作“废”字,首先是因为《韩非子·内储说下》《史通·言语》与《列女传·节义传》皆有“废”商臣的说法,为异文提供旁证。其次,因前文已述“黜太子商臣”,下文又有“能事诸乎”,则可证楚王原意为“废黜”商臣,未必会杀之。再次,若作“杀女”,则与前文文义不同,杜预必作训释。而若作“废女”,就与原义相通,故杜注无释。最后,从致误原因上来说,因“发”字古体“發”与杀字古体“殺”相近,故“废”字多讹作“发”字。
综观以上所言,王引之的说法似乎有诸多佐证,又能探求讹字之由,但究其根本,王氏并未解除其中症结。就引文来说,亦有相当多的文献作“杀女”,并不能直接推断出原文应作“废女”。杨伯峻就提出:
《楚世家》及《年表》俱作“杀”,则司马迁所据本本作“杀”,未必为误字。[9]514
王叔岷亦认为:
《左传》之“杀女”,《韩非子》《史通》并作“废女”,盖以废说杀,非杀为废之误也。《楚世家》作杀,乃存《左传》之旧,亦非后人依误本《左传》改之也。[4]78
就推理来说,王氏更无根据,若太子已黜,则亦可被杀,而“能事诸乎”更是潘崇与商臣的主观猜测,与将被杀的客观事实无关。就注文来说,若是“杀”字,亦能与下文相称,而为何杜氏要作注解?从字形上看,王引之认为古文多以“发”为“废”,而“发”与“杀”古字相似。王氏仅言字形相近辄言讹误,缺乏合理论据。
因此,王氏所言虽多,然并没有切实可靠的依据。“杀”与“废”究竟孰是,还未能确定。但从语境上来看,此语是太子商臣“勿敬”的试探后,江芈怒气之言,有夸张成分。本无事实根据,不然商臣与潘崇密谋之事时如何传出?大致是为商臣弑君所作铺垫的“说体”故事而已,正如王氏所言“读者正不必泥也”。因此,既是“说体”文本,若作“废”,则无法凸显商臣造反之决心,
故仍作“杀”字,是与语境相合。如此能与“享江芈而勿敬也”相配,又可引出下文“以宫甲围成王”。
五、昭公二十四年 “莫”
本《传》曰:
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阳不克莫,将积聚也。[1]2106
《经义述闻》:
杜注曰:“阳气莫然不动,乃将积聚。”释文曰:“‘阳不克莫’绝句。”引之谨案:“阳不克莫”,甚为不辞。“莫然不动”之解,亦为皮傅。今案:“阳不克”绝句,“莫”当作“其”,下属为句。言阳气不克,其将积聚而为旱也。“其”“莫”字形相似,故“其”讹作“莫”。而《汉书·五行志》引《传》文已作“莫”,苏林注亦曰“莫,莫而不胜,为积聚也。”则此字之讹,其来久矣。[2]1132
王引之反驳杜预“阳不克莫”绝句一说,认为此句作“阳不克,莫将积聚也”。又将“莫”字校作“其”字,连接下句,表揣测,是言“阳气没有战胜(阴气),大概是在积攒聚集”。王氏之所以作如此判断,是因为“莫”与“其”字形相近,进而认定“其”讹作“莫”起于《汉书》之前,由来已久。
王氏根据字形轻言讹误,并不贴切。首先,王氏无直接证据,仅凭断句其义,辄言“莫”字自《汉书》已讹,似本末倒置。竹添光鸿否定王氏之说。:
或曰莫字属下句,语辞也。言阳犹不克,必至于郁畜,故曰:“得无将积聚乎?”颇与后世将无同“莫须有”语气相类,此说不是。[12]2006
其次,就“莫”字的释义来说,王氏将“莫”校作“其”以表揣测,本身就是在篡改文义。《说文解字》将“莫”释为“日且冥也”。竹添光鸿言:
古日暮字止作莫,《诗》“东方未明,不夙则莫”。[12]2006
杨伯峻亦言:
阳不克莫,莫,暮本字。已过其时为暮。[9]1451
这说明先秦时期,就有“莫”作“暮”,表日暮之时或已过其时之义。说明其本义。根据此义,杜注言“阳不克莫”为“阳气莫然不动”,则是引申之义。沈钦韩即言;
《皇矣》诗传:“貊,静也。”《正义》云:“《左传》《乐记》《韩诗》“貊”皆作“莫”。《释诂》:‘貊、莫,定也。’”[14]346
则如杜释“莫然不动”之义,文通义顺。王引之所举《汉书·五行志》苏林注也有“莫,莫而不胜,为积聚也”的表述,可作补充。实质上,在两汉时期的文献中,莫作“暮”已很常见,如《自悼赋》亦言“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晻莫”即指日暮昏暗貌。
因此,从文义来看,前文已提“旱也”,是因为“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故此时“阳不克莫,将积聚也”,是补充说明‘克必甚’之故。若按王氏之说作“其将积聚”,则无法说明“阳不克”时间或程度,与上下文比较,文义残缺。故此处依旧依杜注所言,原文作“阳不克莫,将积聚也。”此处“莫”释为“暮”。就此观点,王氏不加阐释,岂非避重就轻?
六、哀公十三年 “先王”
本《传》曰:
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毕。何世有职焉,自襄以来,未之改也。若不会,祝宗将曰:“吴实然。”且谓鲁不共,而执其贱者七人,何焉损?[1]2172
《经义述闻》:
陈氏芳林《考正》曰:“案《正义》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时’,则‘先王’似当作‘先公’,惜石经残阙,《家语》载此事亦作‘先王’。”家大人曰:作“先公”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者,后人依《家语》改之耳。《桓五年》正义引此正作“先公”。[2]1153
王引之在此条目中,认为“先王”应当作“先公”。此说对于《左传》的校勘影响很大,后世学者也多采纳王说。王说之所以颇得后人信服,来源于诸多依据。首先,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首提“‘先王’似当作‘先公’”,又言唐石经残缺,故唐以前《左传》原文已不可考,令人不能无疑。其次,王念孙认为今本作“先王”,是后人依据王肃《孔子家语》而改。故王氏认为原文讹作“上帝先王”,当源于《孔子家语》。再次,桓五年《左传》正义言:“有事于上帝先公。”[1]1749此处为孔颖达引《哀公十三年》之文,言“先公”而不言“先王”,可作本校之用。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与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均言“王”是疑字,“先王”似当作“先公”。[8]1925
但是在征引方面,王氏尚有疏漏。首先,陈氏言唐石经残缺,但无明证可得此处“先王”必须改为“先公”。且据王叔岷考证,开成石经仍作“有事于上帝先王”[15]2156。就“先王”与“先公”之别,襄公十一年《左传》杜注言:
先王,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郑祖厉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1]1950
而鲁公之先公为周公旦之子伯禽,与周之先王有本质区别,不可简单混为一谈。
其次,哀十三年《左传》正义言:
景伯称十月,当谓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时,且祭礼终朝而毕,无上辛尽于季辛之事。景伯以吴信鬼,皆虚言以恐吴耳。[1]2172
则孔氏之意有三:其一,景伯所言十月,是指周历十月,《礼记·杂记下》言:
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1]1567
可见周之十月并非祭祀上帝先公之时。其二,祭礼终朝而毕,即“自旦及食时”,并非如景伯所言始于上辛日而终于季辛日,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其三,无论从祭祀之时、持续时间来说,此说辞盖景伯恐吓吴人之语,并非真实存在。故孔颖达认为,“有事于上帝先王”是景伯虚构之事。杨伯峻亦认同此观点:
鲁固无祭先王之礼,然景伯纯作谎言,云祭“先王”,则吴之祖亦受祭,可以恐吴。孔疏俱作“先公”,盖以当时典礼绳之。知其为虚言,而又校以当时典礼,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9]1678
故若祭祀“先公”,则对吴国无警示作用,若祭祀“先王”,则亦包括吴国之祖,在情理上可成立。
再次,《桓公五年》正义引语为“上帝先公”,又言:“彼虽恐吴之辞。”孔氏既已认定此语虽为恐吓吴人之用,然未必为虚言。又桓公五年之言,盖孔氏自行更改,且撰写时间在《左传》成文之后,若为抄写之误或故意更改也未可知。
故在此处,应依原文,仍作“先王”。
上述《经义述闻·春秋左传》校勘商榷六则,是笔者研读王氏著作期间的一点思考。王引之在考据的过程中,大量引用文献作证据,但对于所引内容缺乏贯通,粗看之下,略显繁琐。而就《经义述闻》全书来讲,其中绝大多数的成果都是可供我们借鉴,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倡的。
注:
① 王氏言:“其,犹‘之’也。《书·盘庚》曰:‘不其或稽,自怒曷廖?’《康诰》曰:‘朕其弟,小子封。’《诗·鱼丽》曰:‘物其多矣,维其嘉矣。’《大戴礼·保傅》曰:‘凡是其属,太师之任也。’桓六年《左传》曰:‘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成十五年《公羊传》曰:‘为人后者为之子。’又曰:‘为人后者为其子。’《贾子·大政篇》曰:‘故欲以刑罚慈民,辟其犹以鞭狎狗也,虽久弗亲矣。欲以简泄得士,辟其犹以弧怵鸟也,虽久弗得矣。’”(见王引之,《经传释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9页。)
② 裴氏言:“释文‘之’一作‘其’,《经义述闻》谓作‘其’者是,其说未允,此当以作‘之’者为古本,作‘其’者乃后人据文义而改。《左传》中多以‘之’为‘其’。如‘枕之股而哭之’,‘夺之杖以敲之’,‘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郑人醢之三人也’‘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之属皆是,故知作‘之’者为古本。”(见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721页。)
③ 杨氏举《尚书·尧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等4例,证“之”字用与“其”字同,用于主位。又举《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20例,证“之”字用与领位,亦与“其”字同。(见杨树达,《杨树达文集之三词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1页。)
④ (1)关于“城塞说”:楚有方城,后人注释,或称之为山,或称之为塞。张维华考证,方城山为一地之锁钥重镇,以山言之,则成方城山,以关守之,则为方城塞。且前人称“方城”者众多,言楚方城者,自以叶南之方城为主。(见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1979年,第30-32页。)(2)关于“城邑说”:有人推测方城山和方城塞的交通要道上还有一个叫做方城的城邑存在。(见王振中,《方城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3)关于“长城说”:言楚方城是最早的长城,楚长城在历史上被称为“方城”。《太平御览》引《郡国志》曰:“莱县有长城,曰‘方城’。(见李昉等,《太平御览》居处部二十一,四部丛刊三遍景宋本。)
⑤ 林氏言:“苟有渝变此盟誓,以恶相及。司盟之明神与卫国之先君,纠正其罪而诛殛其人。”(见林尧叟,《左传句解》,收入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左传杜林合注》卷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氏言:“变盟以祸相及。”(见刘绩,《春秋左传类解》卷十六,明嘉靖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