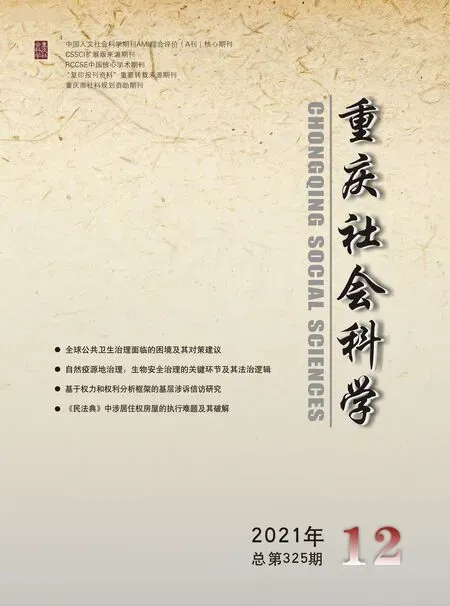《民法典》中涉居住权房屋的执行难题及其破解
廖磊 何雨泽
摘 要:《民法典》在立法层面对于居住权的确认使得房屋上的权利种类更为多樣化,内容更为具体化,但与此同时同房屋相关的执行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居住权的物权属性赋予了其天然的对世对抗性,其设立的登记要件虽然能够就房屋本身的权利冲突提供解决思路,但非以房屋为诉讼标的物的执行情形却缺乏参考标准。而居住权对抗性与传统理论中人役性对居住权转让的限制将导致房屋附上无法去除的权利瑕疵,致使执行程序陷入僵化的困局。欲图完善与优化涉居住权的执行程序,应当从对居住权自身人役性的破除出发,以开放式的立法激活居住权的流通性为基础,以居住权人处分自身权利的自由为起点,实现执行程序中居住权处置路径的灵活化。
关键词:民法典;居住权;民事执行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民法典实施中电子合同生效规则的实证考察与完善”(21SKJD063)。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12-0069-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1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生效标志着我国在法律体系上正式迈入了民法典时代,我国的民法体系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与更新。在诸多崭新之处中,居住权的正式入典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亮点之一。其一方面反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到民法典期间我国社会现实的变迁以及相应的法制供给的调整,反映了我国立法工作的现实导向;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种于我国法律体系而言为全新的制度的引入,如何应对这一新制度可能激发的“排斥反应”,使其得以在我国法律体系之中发挥整体性的制度效能,也成为当下研究之着力点所在。除民事实体法其内部体系自洽性的问题之外,居住权制度对民事程序领域的外部性同样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问题。截至2021年12月15日,裁判文书网上已经上网的与“居住权”相关的执行案件文书已有3 005份之多①,而在居住权现已被正式立法所承认的环境下,可以预见的是居住权将会更多地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而与之相关的民事执行问题也将愈发凸显。打通居住权的实体制度与程序规定之间的连接,是对 “执行难”问题进行攻坚克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抽象的法律规定得以阐释和展开的必要保障。
一、涉居住权房屋的执行难题初探
居住权滥觞于罗马法,最初是作为人役权的一种形式而出现的。设立该制度的初衷在于, 随着“无夫权婚姻和奴隶的解放日多,每遇家长亡故, 那些没有继承权又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因此,丈夫和家主就把一部分家产的使用权、收益权等遗赠给妻或被解放的奴隶, 使他们生有所靠, 老有所养”[1]。其意指居住权人对他人所有房屋的全部或者部分及其附属设施所享有的占有、使用之权利,而本质在于将房屋所有权的内容在居住权人和所有人间进行分配,从而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2]。同租赁权相似,居住权也是一项对房屋使用权人与所有权人作出分离的制度设计。然而作为一项用益物权,其权利效力与稳定性自然均强于作为债权的租赁权。居住权的设立是对于我国现行只承认“租赁”与“所有”的房屋利用二元机制的改革,其在促进房屋利用灵活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权利稳定性的保障,在租赁权与所有权之间取得了平衡。居住权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为我国现行的房屋利用权利体系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为民事执行程序引入了全新的参数。居住权将进一步复杂化民事执行的法律关系,形成“申请执行人(债权人、买受人)—被执行人—居住权人”的三角对抗关系。而如何实现此种三角对抗关系之间的利益平衡,对于居住权这一实体制度同民事执行的程序性规范之间又以何能实现顺利的衔接?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所作出的思考与设想方为民法典时代未雨绸缪的应有之举。
而目前这一问题还未引起当下理论及实务界的关注,目前唯有实务领域的法官对此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其主张先从程序角度判断执行过程中是否需要对居住权的效力作出判断,在居住权确实存在的情况下,以居住权设立方式区分其性质,并以各类居住权不同的设立标准为节点同法院对于房屋作出查封行为的时间作为相对比的锚点。即若居权设立生效的时间先于法院对房屋进行查封的时间,则居住权人可以依据有效的居住权排除执行,反之则不能对抗法院执行[3]。以上观点虽然对于涉居住权问题提供了开创性的思维方式和解决路径,但是其以权利设立时间为标准的单一化模式在这一问题所可预见的复杂性面前依然略显粗糙和淡薄,值得进一步商榷。
(一)居住权并不能必然排除执行
根据民法典中对于居住权的规定,其于我国的物权体系中应当属于用益物权。而用益物权的特殊效用便在于解决物质资料的所有与需求之间的不适应性和不平衡性,所有权应与其权能相分离,从而适应商品经济要求扩展财产使用价值、扩大所有权的需求[4]。而民事执行其本质便是司法机关通过国家强制力所进行的所有权变动,原则上并不涉及执行标的上的用益物权,其依然是房屋所有权的转让与继受,因此用益物权人一般情况下并不能主张对于执行的排除。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故不难看出,包括居住权在内的用益物权不仅不具有对于执行的必然排除效力,法院甚至有权在其阻碍执行利益实现时将其去除。
当然此种不干涉性并非绝对,自2007年《民事诉讼法》确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制度后便为案外人在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情况下向法院提出排除执行诉讼提供了机会。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用益物权可以成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一种类型,但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即案外人用益物权之行使将因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受到妨害[5]。而回观居住权,其作用在于为权利人在他人所有的房屋中居住提供物权上的合法性,其权利意义之一在于防御包括房屋所有人在内的其他人对其居住权利的侵犯。对于所有权人,其有自愿负担、必须容忍居住权人长久占有使用的义务:居住权人对标的房屋享有物权效力,属于没有房产证的房主,可长时间乃至终生居住;同理,所有权人在居住权享有时间内无权赶走居住人。新的所有权人即便事后获得不动产所有权证,也无法改变“居住权”已存的现实,无权赶走居住权人[6]。由此可见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自然不会必然致使居住权人之权利行使受到妨害,自然居住权并不具有必然对于执行行为的排除效力。
实务界对于涉居住权标的的权利定位思路在于将不同形式成立的居住权进行成立时间点上的区分,以此作为判断是否能够排除执行的标准。然正如前文所述,从居住权本质展开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其实际上并不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单纯以时间为标准的解决方案同居住权背后的法律原理相悖,也难以实现权利关系中的利益均衡。
(二)涉居住权房屋的具体执行难题
执行标的物与判决标的物为同一物时,便属于俗称的“判房执行房”的情形。此种情况下,给付之诉的诉求多为要求法院依法直接对涉案房屋作出包括移转所有权在内的处理。而房屋之所以能够成为执行标的的前置法律原因不外乎房屋买卖、不动产抵押等担保物权的设立。然由于房屋作为不动产,具有耐久性、稀缺性、不可隐匿性和不可移动性等特点[7],法律必须对与不动产相关的权利变动作出登记的特殊规定。
如前文所述,不动产交付以及在其之上的他物权设立同样必须以登记为公示要件。而根据当下民法典的规定,居住权的设立与否同样以登记与否为判断标准,因此适用物权体系内部的顺位规则便具有可行性,按照限制物权设定的前后顺序决定其实现顺序[8]。故在此种情况下,登记成立在先的权利人具有对世的权利宣告,自然同时也实现了对于后来权利人的权利告知。因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居住权人同申请执行人(即本诉的债权人)的利益冲突时,可通过调查何者权利登记在先以判断权利的优先性。而同涉及担保物权的情形相似,由于不动产的交付同样以过户登记为标准,即其同样能够以登记形式完成自身权利的公示,从而实现对交易相对人的权利信息披露。无论是所有权抑或抵押权,其成立均以登记为要件,如此其登记时间的先后便能够自然形成以时间先后为标准的权利优先级。概言之,在信息公示化的情形下,执行过程中所涉及的权力冲突可以通过现有的物权公示模式加以调节。
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除前述就以房屋本身的标的而启动的执行程序外,还存在由于债务人未能偿还到期债务,债务人要求通过变卖或者直接过户不动产的形式以实现债权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执行标的物同案件标的物并不具有一致性,此种非一致性造就了更为复杂的执行法律关系。当房屋成为当事人无法清偿债务时的替代性履行方式,法律无法要求债权人对于房屋的权利状态具有充分的认识,房屋居住权的有无债权人在申请强制执行前无从知晓;同时也难以苛求居住权人对于房屋所有人的债务状况具有足够的认知,并对于其偿还能力进行评估以认识到自身可能面对的权利风险。因此前述权利的顺位规则在此种情况下便不再具有可适用性。就现有规则来看,我国执行拍賣程序中对于标的物上所附着的他物权的处理以“承受主义”为原则,即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作为例外,如果上述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的财产上,对在先设定的担保物权或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9]。而当下司法实践中以上原则的应用多在于执行标的之上涉及租赁权的情形,且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配合下其运作模式已相对较为成熟,但就用益物权的情形而言以上规则的适用并不多见,也缺乏更为详细的应用规则。居住权作为一项用益物权,其在为居住权人提供更为稳定的权利保障的同时,也为标的物施加了更为沉重的权利负担,使得房屋的预期价值缺乏明朗性,从而必将导致房屋在实际的执行拍卖过程中面对更为严重的价值贬损。
二、居住权执行过程中的矛盾成因探析
如前文所述,居住权于民事执行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本质上是居住权人作为用益物权的居住权与执行拍卖过程中拍定买受人的所有权权能完整性之间的冲突,即是物权体系中同一标的物上不同种类物权之间的优先性抉择。然而用益物权同所有权人权能完整性之间的矛盾并非民法典或居住权制度所带来的新问题,若欲揭示这一问题之本质所在,便必然需从我国居住权性质之特殊性予以切入。
(一)居住权的权利公示性
作为一项为他人提供使用权能的权利,租赁权同居住权存在一程度的相似性。租赁权是相对于承租人来说的,指承租人对他人所有之物,进行排他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10]。除权利内容外,在权利的设定形式上二者也均可通过意定的形式进行设定。然而租赁权本身的债权性质决定了其与作为物权的居住权存在无法忽视的差异,决定了“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适用无法复制。
作为用益物权的居住权是绝对权,必须要通过登记而设立,这样就可以对抗房屋所有权人之外的任何第三人,能基于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11]。然而,作为债权的租赁权是相对权,其设立不需要采取登记的方式,除了在“买卖不破租赁”的场合具有对抗效力,其他情形仅能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不具有对世性,承租人只能对出租人享有租赁权,不能对第三人主张租赁权[12]。租赁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超债权的保护,但是其物权化并不完整。而承租人所获得的物权对抗效力来自对房屋的实际占有,只有在租赁物交付以后,承租人才得以对租赁物进行使用并享有收益,从而处于一种类似于用益物权人的地位,此际才有通过强化租赁权的效力来保障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使用收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租赁物交付与承租人后,即为承租人占有,使租赁权具有公示性,可使第三人免遭不测损害,以保障交易安全[13]。租赁权得以物权化,从而获得对抗效力的来源在于实际占有下的类用益物权效果,而并非租赁权这一具有相对性的债权本身。而居住权作为一种“正统”的物权,其对世对抗性来自立法阶段所确定的天然性质,而非来司法过程中的二次赋权。
(二)居住权的权利期限缺乏可预见性
在我国民法典的现行规定之中,居住权设立的目的在于为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住房制度的要求①。其立法的一大重要目的便在于强化对于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利的保护,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抚养以及老年人晚年居住安定性的婚姻家事领域。然而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七十条的规定,居住权的消灭条件为“居住权期限届满”或“居住权人死亡”。可预见的是,当居住权的权利人为老年人或者年幼的儿童时,其所享有的居住权时限将会不具有可预测性,或往往以一种长期的形式存在。居住权权利期限的不确定性将难以避免地引发买受人对于“所有权被用益权侵蚀和抽空为虚空所有权”[14]的担忧。而租赁权则往往在合同上约定明晰的承租时长,且短期租赁在市场上占据着主流地位②。由此可见一方面租赁权在房屋之上附着的时间相对明晰,且以短期存续的情况为主,强制执行后拍卖的买受人可以就权利的负担情况作出较为明确的预期;而居住权的存续时间相对具有模糊性,权利存续时长同居住权人的具体状况存有较为紧密的相关性。另一方面,租赁权可以通过转移租金支付对象的方式弥补买受人的权能让渡;然而居住权并未为房屋执行后的买受人提供涤除权利的选项。由此可见租赁权和居住权之间虽然具有相似的权利内容和权利外观,但是二者权利本质及权利稳定性之间的差异致使租赁权的规范模式并不能在居住权的环境下予以适用。
(三)居住权人役性所导致的流动限制
正如前文所言,事前化、物权化是居住权制度出台后对于被执行人权利保护所带来的直接变化。而我国的居住权立法模式具有强烈的传统欧陆民法特色,尤其是其人役性和保障功能尤为突出。从居住权之源流来看,罗马法创设居住权之目的,即在于保障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弱势家庭成员住有所居、老有所养,这一传统为欧陆各国所承袭,故居住权具有极强的人身性,其一般通过遗嘱或遗赠方式设定;与特定的身份相关联,不得转让和继承[15]。谈及这种禁止的理由时,德国学者指出,正因为所有权人在其用益权利和占有权利上被剥夺,故而所有权人的“伙伴”,应只能是所有权人准许的用益权人,而不是该用益权人的权利继受人[16]。而这种对权利主体及权利的内容都进行了严格限制的人役权也就成为比较法上的“限制人役权”。罗马法对于居住权所赋予的人役性色彩在影响后世欧陆国家的近现代民法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居住权设定思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加之我国当下对于住房保障以及住房市场进行调控的现实需要,居住权制度“理所当然”地成为配合我国住房保障政策实施的辅助性手段。
由此可见,我国的居住权制度在内容实质上已然属于传统大陆法系中人役权的范畴。而与地役权相比,人役权最大的特点便在于其具有专属性,即系专为特定人而存在,其不能与权利人分离,进而具有期限性和不可转让的特性[17]。检视我国居住权制度,其忠诚地还原了其人役权性质,维护了所有权人与居住权人之间的限定性关系。但这也导致居住权成为致使民事执行程序进一步复杂化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限制了居住权自身在现代社会中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居住权制度原生于数千年前的罗马帝国,其时代背景于今日已然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居住权制度是否也应当结合目下的社会现实,作出应有调整?
三、德国民法中居住权制度及启示
德国法针对这一问题同样并未采取单一化的视角,而是以变革居住权制度在实体上的内容为进路,通过与执行程序规范相联动的模式打破了居住权在执行过程中的僵局。德国民法典中对于居住权的规定经历了由保守到革新的一个过程,其于第1093条对居住权作出了规定,其中对于居住权的主体与内容细化规定及限制较大程度上保留了罗马法中居住权的救济性导向。在德国民法的他物权体系中,根据权利所依附的对象不同将其区分为了以“物”为核心的地役权以及以“人”为核心的人役权,居住权由于其设定对象及权利内容的限制,则是属于“限制人役权”。
但在社会发展及相应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此种过于保守与僵化的制度模式很快暴露出其弊端。过多的限制性导致居住权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缺乏适用环境,制度价值因自我限制而架空,而其中对于居住权制度的开放性存在的最大桎梏便是其作为人役权而具有的不可转让性,其依据的则是人役权的不可移转原则(derGrundsatz der Nichtübertragbarkeit)。德国民法典则针对这一点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首先在德国民法典内部已经出现了对于人役权不得转让的例外情形规定。其在第1092条第(1)款中规定了“在获得许可时,得将该项役权的行使交给他人”,此规定实际上已经为包括居住权在内的限制人役权行使主体的转移打开了缺口。并且在后续的第(2)及第(3)款中引致了第1059条中对于用益权的规定,其中特别规定“法人或有权利能力的合伙享有限制的人役权,而限制的人役权使权利人有权为输送电、煤气、远程热能、水、废水、油或原料的设施(包括所有直接为运送服务的相关设施),为电信设施,为一个或不止一个私人或公共企业的经营场所之间的产品运输措施,或为有轨电车或铁路设施而使用土地的,该项役权是可以转让的”[18]。这一特殊规定已经打破了人役权不可转让原则的绝对性,从而激活了人役权的流通性。继而在保留现有的居住权规定的前提下,额外创设了“长期居住权”及“分时居住权”,以弥补传统居住权在流通性上的缺陷。在德国的《住宅所有权与长期居住权法》中对长期居住权作出了规定,而其与传统意义居住权的最大区别便在于其可转让及继承,但此种转让受到房屋所有人授意的限制①,同时长期居住权中的具体用途等内容可以依当事人合意作出约定②。而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以设立变种居住权的形式赋予居住权可转让性,正式打破了传统人役权理论对于居住权在流通性上的限制。而对于当事人约定居住权内容的许可进一步丰富了居住权的内涵,从而使得其制度价值更为丰满。
在肯定长期居住权可转让性的基础上,《住宅所有权与长期居住权法》第39条进一步对于其在涉及拍卖过程中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其允许居住权的双方当事人对居住权在拍卖过程中的留存问题进行约定:如果债权人对土地执行因优先于长久居住权或同时存在的资金抵押、地产抵押、按揭债务或者实物负担而进行强制拍卖时,那么长久居住权在土地强制拍卖的情况下,可以与《强制拍卖和破产管理法》第44条相违背而继续保留③。而《强制拍卖和破产管理法》第44条的立法目的在于对拍卖过程中的最低出价进行限定,其规定“在拍卖的情况下,仅允许进行这样的投标,即债权人主张的债权以及从拍卖所得中扣除的程序费用能够足够覆盖(最低投标价)”④。由此可见,依照《强制拍卖和破产管理法》中最低出价条款的规定,在拍卖过程中进行出价时,所出价格应当将被拍卖标的物上所承担的所有债权纳入竞标价格的计算之中,将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转化为终局性的、具体的可分配财产,同时使得标的物回到无权利负担的“纯净”状态,从而在保证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标的物的顺利流转。易言之,基于长期居住权的可转让性及意定性,其作为一项附着于拍卖标的物之上的权利,应当以在拍卖过程中被定价涤除,从而保障标的物的流转价值为原則,以《住宅所有权与长期居住权法》第39条所允许的权利人同意基础上的保留为例外。
由此可见,德国的居住权制度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对于居住权人役性予以破除的过程,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居住权的不可转让性。德国民法典中对于居住权的架构多来自对罗马法制度的继承,其制度价值仍在于传统的对于特定弱势主体的生存居住保障。但随着环境的演变,社会对于居住权价值效用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古罗马时代,其国家职能尚欠发达,罗马家庭在相当程度上担当了今日社会保障之职责,故而由家庭担当有保障之功能的居住权的实现主体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在罗马家庭模式早已转为亲情联络的现代家庭模式,国家接纳了绝大多数家庭承担的保障功能的福利国家时代,则由国家继承了那过去由家庭对家庭成员承担的职责[19]。在生存保障职能由趋于分散的家庭向统一的国家转移的现代社会,居住权其单纯的生存保障性效用已然在一定程度产生了减损,作为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其略显“大材小用”。同时,由生存保障取向所一同继承的还有其作为人役权的不可转让性,对于这样一种权利严格不得移转性(不可转让、不得继承),被德国学者认为是一项不当的缺陷。特别是,对于德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作为建筑造价补助之对待给付而设立的居住权时,这种不可转让性和不得使用出租性,被认为是阻碍了人们进行投资的热情[20]。居住权制度并非昙花一现,其功能也不仅限于弱者保障,这种弱者保障功能的局限不是居住权制度自身的局限或是其自身特点所致,而是一种人为的限制,德国法关于居住权制度的立法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居住权制度这种人为限制的消解过程[21]。在此基础之上,长期居住权与《强制拍卖和破产管理法》中关于执行拍卖的规定之间的衔接便显得水到渠成。长期居住权的可转让性造就了其与其他用益物权同等的定位,使得其在执行过程中的变价涤除成为可能,从而促使居住权的制度价值在执行过程中也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实现。由此可见,德国对于居住权制度的改革始于其传统价值的减损与新兴价值的勃发,是在社会环境演变下保证居住权能够切实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必然选择。
然在对居住权进行改革的过程之中,德国民法典所采取的另设“长期居住权”及“分时居住权”的模式更多地来自德国立法思维的保守。此种二元化居住权格局一方面来自居住权制度在长期运作过程中社会对其所形成的信赖利益,直接针对居住权的改动将会引起既存权利可转让性的变动,从而导致在先权利人权利预期的落空。另一方面,德国民法体现出浓厚的物权法定原则的气息[22],同时加之其追求精细化与严谨化的立法模式,致使其先以转让性为标准分立传统居住权与长期居住权,继而以具体应用场景再设了分时居住权。此种立法路径在体现德国立法模式严谨细致的同时也显露出了二元化居住权架构的细琐与繁杂,其虽然实现了对居住权绝对人役性的破除与其制度价值的激活,但此种二元化的格局造成了居住权制度的体系分裂,而且增加了当事人的选择成本[23]。德国民法对于居住权人役性破除的经验值得我国在未来的修法过程中予以借鉴,但就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而言,德国的经验并非我国当下所能参照的最佳选择。
四、民法典实施中居住权改革的理论构造
居住权不可转让性破除的必要性已在对德国经验的审视中得以充分的说明,居住权转让性的激活当成为下一阶段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论题之一。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德国的经验虽为我国指明了居住权发展的方向,但其方式仍存需优化之处,而欲图寻得真正适合我国的改革模式,则必须从我国的法律体系予以分析,以理论构造为起点展开路径探索。
(一)实体与程序层面的体系适用性
首先在实体层面,我国民法中的他物权体系与忠实继承罗马法体系的德国体系存在明显的不同,而在用益物权之上此种差异的表现更为明显。我国民法体系中不存在地役权与人役权之间的划分,甚至并不存在“役权”这一上位概念,且就我国现行民法来看,目下符合人役权定义的也唯有居住权一项耳。罗马法是顺着用益权的轨迹、权能不断分解形成居住权,居住权的功能不过是锦上添花、简化交易; 而中国法反过来,基于最迫切的实践需求制定了居住权,没有用益权基础,所以它的作用是填空补白、雪中送炭[24]。因此德国法中师承罗马法的人役权的不可转让原则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并不具有足够充分的体系化支撑,也无单独为居住权制度引入、适用这一原则的必要;且德国自身的改革经验也证明了对于人役权不可转让原则的坚守并不符合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现实需求,采取更加温和、灵活的居住权制度构建模式是必然之选择。
从我国现行的物权体系的角度出发,承认居住权的流通性也具有法理上的合理性。在我国民法典的编排之中,居住权同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地役权等权利以平行关系隶属于用益物权的上位概念之下。然而观察“用益物权”之中的各项权利,虽然规制程度有所不同,但均未出现禁止转让的明文规定,唯有居住权一项被明确禁止转让。就当下我国民法典中所规定的用益物权而言,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虽被归为用益物权,但由于我国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及集体垄断性,其所有权性质应当属于有别于私主体所有的“公物权”[25]。而即便是属于“公物权”的土地,在其基础上设立的“用益物权”方未被施以转让性的绝对限制;而作为私主体可自由所有的房屋,基于其所设立的“用益物权”转让性却受到了法律明文的禁止,这一制度设计同所有权受限严格程度的逻辑存有矛盾之处。而回归用益物权制度的价值机能视角来看,不难发现其存在的核心价值不外乎两点:一是有需求之人可在无需取得所有权的情况下得支付代价以利用他人之物,从而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价值,即拥有其物者自不使用,而使他人利用之以收其利益;二是使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巩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得以对抗第三人[26]。而用益物权的可转让性正是保障物的價值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必要保障,对用益物权的可转让性的否认无疑是用益物权价值的“作茧自缚”。而由前文所述 “公物权”而生的“非所有人对于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的土地以使用、收益为目的之物权”并非民法上作为私权利的用益物权[27]。因此我国法律上真正的用益物权只有土地经营权、居住权和地役权三种,居住权的引入,为解决用益物权类型不足提供了良好的契机[28]。承认居住权的可转让性,保证居住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价值得以完全发挥,是充实我国物权体系内容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回归用益物权价值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如前文所言,居住权在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及性质虽与租赁权相似,但在目前立法语境下的人役性导致其在参考适用租赁权相关执行规范时不具有法理前提。而对于居住权可转让性的承认无疑是为执行过程中的权利处理提供了必要前提,只有在实体法层面赋予了其可转让性,居住权在程序法层面才可具备变价的合理性,从而使房屋价值得到解放。唯有买受人具有完整的权利预期的情况下,房屋的变价处理才具有正常进行的可能性,从而为债权的实现提供基本条件。然而防止居住权限制房屋价值实现,致使买受人及债权人利益受到不合理损失固然重要,但居住权保障弱者生存的基础性价值依然不可偏废。若在执行过程中将居住权予以统一清算、涤除,其将必然导致弱者沦为公权强制力之下的牺牲品,也会因此滋生对于居住权权利安定性的不信任,从利益天平的另一侧引起居住权制度的空壳化。
(二)采取开放式的前置立法
从实体法的维度出发,诚然德国法所创设的二元化立法模式对于合理编排居住权的制度构造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但其“两步走”的立法模式并非可供我国选择的最优之举。德国立法中居住权的二元化成因在于居住权立法时间较早,立法者对于后续的社会发展缺乏预见性,从而采取了较为封闭、保守的立法模式。而面对现实的社会需求,为保证现行法律的稳定性利益,其不得不采取“另起炉灶”的方式,从前置立法的角度构造二元化的居住权制度。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并无如同德国法中由于传统居住权制度长期运行所产生的法律稳定性利益,同时也没有人役权制度对权利内容的限制,因而我国并没有从前置立法的角度构造区别于传统生存性居住权的必要性。我国的居住权制度正处伊始之时,尚未有积重难返之困境,及时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对居住权的设立条件、对象以及流通性等事项由封闭的法定性转变为开放的意定性,从而以内化改革的形式实现居住权制度的完善,避免造成物权体系的冗杂。开放式居住权立法的初衷在于充分满足社会的现实需求,这不仅是以私人自治为核心的多元化价值基础之实现途径,而且在德国居住权制度的百余年发展中得到了印证[23]。因而在前置立法中对于居住权的设立采取开放的态度,允许当事人对居住权的内容自行合意是符合当下社会需求的更优选项。
从执行的程序维度加以审视,同样能够得出应当采取开放式前置立法的结论。若在设立居住权的程序中要求当事人事先对意图设定的居住权类型加以明确,其很可能导致当事人在基于对后续法律后果预测之上而选择特定性质的居住权。如债务人可能在基于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债权或抵押权,在房屋之上选择性地设立生存性居住权,利用生存性居住权的人役性及价值取向上的人伦属性,使得变价、拍卖等执行程序进入两难境地,从而延缓甚至阻止执行程序的正常进行。在立法前置区分的语境下,对于生存性居住权的事前审核则成为免当事人滥用居住权制度的必须程序,而此举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当事人对房屋价值进行利用的成本,有悖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的私法价值;同时也为物权登记的管理机关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负担。因此,在前置立法之中,对于居住权应当减少相应的限制,在居住权设立的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基于当事人合意的意定空间。在立法语言上淡去对居住权制度目的的特定化表述,同时去除对于居住权的盈利性、流通性的限制,从而在更为开放、自由的居住权制度下展开更为合理、完善的执行规则建设。
五、以去权程序实现涉居住权的民事执行难题破解
居住权转让性的激活既是其制度本身的价值追求,也是欲图实现其在法律体系中得以和谐运作的必然要求。在理论构建论述虽已对于居住权可转让性的方向予以明确,然居住权转让的具体规则还亟须细化。结合居住权本身性质与其在执行程序中的定位,可在实体法限制解除的前提下,以权利人的处分自由为展开,构造合理、具体的去权程序,从而化解民事执行中的桎梏。
(一)去除实体立法层面上对居住权转让的限制
欲图实现涉居住权房屋在执行过程中难题的破解,则须以实体层面对居住权立法的修改为切入点。现行民法典中对于居住权转让限制在于第三百六十九条,其明确地对居住权的转让和继承予以禁止。在后续的修法过程中,则应当将现行法典中“强限制性”的居住权修订为前述开放式居住权。现行法行文中“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任意性规定并不及于句号之前针对居住权转让和继承的限制,使得本条前半段的内容形成了对居住权转让的绝对性限制。因此有学者提出以扩大任意性规定涵盖范围的模式破除居住权不可转让的绝对性,将法条修改为:“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从而为当事人约定设立可转让的居住权提供可能的进路。但此种模式并非最佳的改革方案,制度创设作为重大的立法固定成本投入,理应尽可能发挥效益,而可流转性则是现代居住权与传统居住权存有明显区分的特点之一[29]。此种改动虽然赋予了居住权转让的合法性进路,但此种任意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法定规范的“豁免性”条款,而其立法的默认取向依然是对居住权转让的否定,居住权的流通性并未因此得到有效的解放。在此模式下,居住权的可转让性来自居住权人与设权人之间的约定,甚言之来源于设权人的意定。一方面,在设立居住权的过程中,当事人往往难以对往后可能发生的权利纠纷与经济用途产生预见性,不会特意就转让性问题进行约定;另一方面,设权人甚至可能故意以阻断居住权转让性的方式阻挠房屋在执行过程中的处理。
而若采用默认许可转让,当事人约定禁止例外的模式,居住权的流动性方可得到更为充分的解放。一方面,无需当事人对此进行专门约定,居住权则默认具有可转让性,其通过降低当事人的选择成本来激活居住权的流动性;反言之,设权人限制其转让性的成本则因此升高,设权人故意限制转让从而影响执行的难度也将因此增加。另一方面,若居住权设立的目的确实仅为保障特定主体的生存需求,方可以特殊约定的方式对转让进行限制。因此,在后续的修法中,宜将第三百六十九条修订为“居住权可以轉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可以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30]。
(二)以居住权人的意志为基准构建去权程序
在前述制度架构的基础上,居住权在可转让性被激活的情况下成为一项完整的用益物权。物权是对物的排他性支配权,是典型的财产权。物权作为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即权利人可自主处分其物权,此乃物权的应有之意[31]。标的物的买受人通过与居住权人达成协议的形式,通过付出双方合意达成的对价,则可以实现对标的物上所附着的居住权的“涤除”,从而获得完整的所有权;同时居住权人也可结合自身具体需求更为灵活地处分自身权利,如其所有的居住权所涵盖房屋面积超出其实际生活需求时,可通过对居住权的转让或置换处理将溢出的权利覆盖面积转化为相应的对价,如此不仅能保证居住权人的权益在原有范围内得以保全,甚至为其提供了提升权利效能的可能路径。
从程序法的视角来看,赋予居住权人保留权利与否的自由是对我国强制执行拍卖程序中“承受主义”模式的补足。作为用益物权的居住权在“承受主义”的执行立法体例之下,只有拍定人现实承受拍卖物上的担保物权或优先受偿权等负担时,才可拍卖[32],其意味着买受人必将继续承担拍卖物上所负担的居住权。而在买受人取得拍卖房屋的所有权后,其在居住权的对抗效力下自然成为房屋的“虚空所有权人”。如此一来,基于前述的开放式居住权立法,在居住权可转让性的前提下,买受人满足自身天然所具有的恢复所有权完整性的意愿便有了实现的可能。买受人可通过与居住权人达成协议、支付对价的形式将房屋上所附着的居住权兑现去除,从而使买受人在恢复所有权完整性的同时实现对居住权人权益的保障。
(三)以多层次标准实现对权利价值的确认
其一,以居住权设立时原所有权人(设权人)与居住权人达成的协议价为首要参考标准。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无论基础法律关系是居住权合同还是遗嘱这一单方死因行为,物权编的居住权在性质上都属于意思自治范畴内的意定居住权,而非法定居住权[33]。在居住权意定的基础之上,开放式的居住权在实质上将“社会性”及“投资性”的居住权予以整合,将居住权的实际用途交由当事人自行约定。在此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基于能使房屋所有权与财产利用权的配置达到最优化,实现最大效益,以满足人们居住和投资的双重需求的投资性居住权[34]及部分以有偿形式设立的社会性居住权。而在居住权基于有偿设立,且有相应的合同将双方当事人合意内容及有效性予以固定的情况下,强制拍卖的起拍价则可以房屋在无瑕疵状态下的评估价加上合同中所约定居住权的剩余时限为比例所计算出相应金额而确定。
其二,除合同约定价之外,还应当以实时市场价值为综合考量。以居住权合同价为标准的定价模式虽然明了、准确,但其并非具有绝对通用性的标准。在有偿设立的居住权情形下,居住权权利的价值并非处于绝对的稳定区间,其市场价值可能随着房屋自身的市场价值而变动,若以合同定价为绝对标准,房屋市场价值所导致的居住权价值变动定将影响对居住权人权益的还原。尤其是在房屋市场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居住权人的权利价值随之上涨的部分应当是其合理合法的利益,较低的合同价标准实质上是对居住权人现有利益的损害。在此情形下,宜将对定价标准的选择交由居住权人,由其基于对自身利益的最佳考量而选择依照合同定价抑或根据市场价确定居住权去除的价格。除此之外,居住权的设立并非绝对的有偿,居住权保有的人役性决定了其具伦理性、保障性的色彩,居住权人对权利的取得也因而具有无偿性,无须支付任何对价[35]。在此种无偿设立的情形下,自然不存在可供参考的定价标准,因而基于目前市场价格所作出的评估是确定其权利价格的唯一渠道。
而针对市场价格的确定则应当以同等条件下的租赁价格为底线进行。一方面,租赁同居住权一样为权利人提供了对房屋的使用权,允许权利人在约定的权限范围及时间范围内使用房屋,其为原权利人所带来的效用同居住权基本一致。然而另一方面,居住权作为一项物权,其具有比作为债权的租赁权更强的稳定性。这般便意味着居住权的设权人将在更大程度上容忍他人对自身所有权的空虚化,而居住权人的权利也因具有对世性而更加稳定,因此居住权的权利价值应当高于同等条件下的租赁权。
(四)补全替代性的居住权去除形式
前文虽主张强调居住权的物权属性,主张设立开放式、可自由轉让的居住权,然而居住权同样将在传统的生存保障领域发挥其制度价值。易言之,在执行过程中,房屋上所设立的居住权乃为弱势群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的情况同样存在。在此情况下,即使金钱对价量合理,虽然在价值实现的层面审视中居住权人并未遭受损失,但经济成本并非居住权人所必须考虑的唯一生存成本。单一化的金钱对价将会导致原居住权人虽然具有了另寻住处的经济实力,却额外负担了另寻住处的成本与潜在风险,如此一来其将重新陷入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之中,此举无疑在事实上造成了原居住权人的利益减损。为填补居住权人在此过程中的非经济性成本,应当允许居住权人要求买受人通过提供替代性居住保障的模式实现对居住权的去除。此处同样可以参考对于唯一住房进行执行过程中通过提供替代性住房保障相关人基本住房权利的解决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申请执行人按照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提供居住房屋,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至八年租金的。”然而《规定》的替代性住房标准是以抽象性的人权保护为标准,以保障债务人(及其家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为目的而制定的,而居住权本身便内含有相应权利期限、居住权所覆盖的房屋面积等问题有着相应的约定,如若直接套用《规定》中的条文显然将导致居住权人利益面对受到不合理贬损的风险。一般而言,用于替代的房屋条件应当在结合其使用期限、房屋面积、所处位置等因素后作出综合的评判,其综合价值应当同原房屋处于相同或相近的水准,其方可保证居住权人权益不因替换而受损。
六、结语
居住权作为一项全新的用益物权,虽然在功能外观上与租赁权等有所相似,但是其权利性质决定了居住权问题不能简单套用原有的执行模式,也并非一个单纯的程序法问题,而应当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视角出发,方可以期寻得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从居住权多年的运作经验来看,无论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居住权制度的构想或改革预期,还是域外的司法及立法实践经验,都无不凸显着对居住权人役性的破除及其流通性激活的趋势。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居住权制度既是充分发挥居住权制度价值的必然需求,也是破解居住权为房屋执行所带来困境的有效手段。开放式的居住权立法以赋予居住权人处置自身权利的自由为途径,以意思自由保护居住权人权益的同时为灵活地促成多方利益实现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案。居住权原有的保障性与稳定性价值能够得以保留,同时其也能够在具体的处置过程中更为灵活地完成权利价值的实现,从而在满足社会真实需求的同时完善其实体性权利与具体程序之间的衔接与联动,实现我国法律体系内部和谐性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陈信勇,蓝邓骏.居住权的源流及其立法的理性思考[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3):68-75.
[2] 申卫星.从“居住有其屋”到“住有所居”——我国民法典分则创设居住权制度的立法构想[J].现代法学,2018(2):105-118.
[3] 李亚彬.试论居住权排除执行的裁判规则[N].人民法院报,2020-07-09(008).
[4] 杨立新,尹艳.我国他物权制度的重新构造[J].中国社会科学,1995(3):78-93.
[5] 汤维建,陈爱飞.“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的类型化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54-63+191-192.
[6] 陈小君.《民法典》物权编用益物权制度立法得失之我见[J].当代法学,2021(2):3-13.
[7] 熊玉梅.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变迁研究(1949—2014)[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4:10.
[8] 常鹏翱.物权法上的权利冲突规则——中国法律经验的总结和评析[J].政治与法律,2007(5):105-110.
[9] 赵晋山.《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05(2):26-31.
[10] 史尚宽.债法各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48.
[11] 王利明.论民法典物权编中居住权的若干问题[J].学术月刊,2019(7):91-100+148.
[12] 吴启宾.租赁法论[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27.
[13] 张华.我国租赁权对抗力制度的不足与完善[J].法学评论,2007(2):46-51.
[14] 马克斯·卡泽尔,罗尔夫·克努特尔.罗马私法[M].田士永,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300.
[15] 刘阅春.居住权的源流及立法借鉴意义[J].现代法学,2004(6):154-160.
[16] 李永军.论我国民法典上用益物权的内涵与外延[J].清华法學,2020,14(3):78-92.
[17] 陈华彬.人役权制度的构建——兼议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的居住权规定[J].比较法研究,2019(2):48-59.
[18] 陈卫佐.德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448-449.
[19] 张力.论居住权的物权法保护——微观与宏观之维[J].兰州学刊,2010(3):142-147.
[20] 申卫星.视野拓展与功能转换:我国设立居住权必要性的多重视角[J].中国法学,2005(5):77-92.
[21] 陶钟太朗,杨环.论居住权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以西欧主流民法国家为考察对象[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45-50.
[22] 陶钟太朗,杨环.论居住权从身份性权利到契约性权利的变化——从罗马法到法、德民法[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9(2):21-24.
[23] 申卫星,杨旭.中国民法典应如何规定居住权?[J].比较法研究,2019(6):65-83.
[24] 肖俊.居住权的定义与性质研究——从罗马法到《民法典》的考察[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2):79-89.
[25] 席志国.民法典编纂中集体土地权利体系新路径[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1):109-113+151.
[26] 薛生全.用益物权的价值取向及立法指引[J].法学杂志,2018(12):47-55.
[27] 席志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土地权利体系再构造——“三权分置”理论的逻辑展开[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43-52.
[28] 席志国.居住权的法教义学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20(9):89-97.
[29] 鲁晓明.“居住权”之定位与规则设计[J].中国法学,2019(3):223-239.
[30] 曾大鹏.居住权的司法困境、功能嬗变与立法重构[J].法学,2019(12):51-65.
[31] 温世扬.从《物权法》到“物权编”——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完善[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36(6):155-163.
[32] 徐明.强制执行中的租赁权[J].人民司法,2008(1):99-103.
[33] 汪洋.民法典意定居住权与居住权合同解释论[J].比较法研究,2020(6):105-119.
[34] 崔建远.民法分则物权编立法研究[J].中国法学,2017(2):48-66.
[35] 鲁晓明.论我国居住权立法之必要性及以物权性为主的立法模式——兼及完善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居住权制度规范的建议[J].政治与法律,2019(3):13-22.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Enforcement of Houses Related to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in the Civil Code
Liao Lei He Yuze
(School Of Cyber Security and Information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Abstract: The confirmation of right of habitation in the civil code makes the types of rights related to houses more diversified and the contents more specific,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enforcementissues related to houses become more complex. The real right attribute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endows it with natural antagonism to the world. Although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can provide solutions to the conflict of rights of the houses itself, there is a lack of reference standard for the enforcement not related to the houses directly. The antagonism and the restriction of human servitude on the transfer of right of right of habit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will lead to the defects of the right that can not be removed, resulting in the rigid dilemma of enforcement procedure. In order to perfect the enforcement procedure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we should start from breaking the servitude of itself, based on the open legislation to activate the circulation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and from the freedom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to dispose of their own rights, so as to achieve the flexibility of the disposal path of the right of habitation in the enforcement procedure.
Key Words: Civil code;Right of habitation; Civil enforcement
(责任编辑:易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