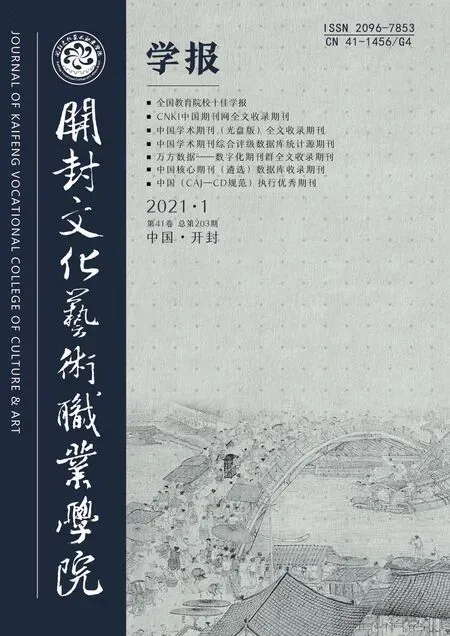论新感觉派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
高 珊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广西 桂林 541199)
诞生于20 世纪20 年代末、崛起于上海的文学流派——新感觉派,包括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主要作家。李欧梵认为,刘呐鸥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建立“现代尤物”意象的作家。“现代尤物”可以理解为都市新女性(或者说摩登女郎),“而更富天才的穆时英则将之变得活色生香”[1]。除了大量的都市新女性,新感觉派的小说中也塑造了一些底层女性形象。但无论是都市新女性还是底层女性,“常常首先与身体联系在一起,而男性则通常与精神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女性的价值和意义都是经由身体得到彰显或隐匿”[2]。笔者希望通过细读文本,探究这些承载着欲望却往往走向痛苦、迷惘或者虚无的女性身体的困境。
一、商品化的身体:都市新女性之一
新感觉派笔下的新女性多为外形充满诱惑力的时髦女郎,以上海为生活空间,身体打上了种种都市烙印。这些都市新女性一方面是审美主体,根据自己的审美偏好选择妆饰,建构身体语言,带有浓厚的西洋风情;另一方面,她们是毫无疑问的审美客体,游走在马路、百货商店、舞厅饭店、电影院等公共空间,身体就像橱窗里的模特儿,展示着化妆品、衣饰等种种舶来商品,沉醉于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公共审美物。正如刘呐鸥《风景》中的叙述者燃青所言:“我觉得美丽的东西是应该得到人们的欣赏才不失它的存在的目的的。”[3]10这句话点出了新感觉派小说中绝大部分女性美的呈现视角——被看,即男性的凝视。在叙述者看来,凝视是一种“发现”及其目光的“锁定”,其中隐含的心理内涵是男性对于美的价值判断。例如,刘呐鸥小说中女性的肖像描写:
“这个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这一个圆形的嘴型和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这不是近代的产物是什么?”——《游戏》[3]3
“看了那男孩式的断发和那欧化的痕迹显明的短裾的衣衫,谁也知道她是近代都会的所产。”——《风景》[3]10
刘呐鸥在不同的作品中都会借叙述者的视角总结女郎是“近代都会的产物”,穆时英在《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里则进一步将这些都市女性的魅力归结为“危险的”:
“‘可真是危险的动物哪!’她有着一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站在轻风上似的,飘荡着袍角。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双跳舞的脚,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红缎的高跟儿鞋上。把腰支当作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贵品哪!”——《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4]197
这段肖像叙述,将身体分解成动物与植物,再加上带某种意味的脚(以诱惑的商品高跟鞋包裹)、腰等身体部分,女性的身体在男性眼中支离破碎,成为美丽的堆砌物。叙述者一边玩赏着这些美好的对象,一边反复描述着其欺骗性与危险性,这种主观判断来自叙述者对这类女性的极度不信任,掺杂着自卑和不自信,是对于自己即将被诱惑的隐忧。叙述者终究成了蓉子众多爱情玩物中的一个,而运用商品装饰和凸显身体之美也成为她吸引异性的驾轻就熟的本领:
“紫色的毛织物的单旗袍,——在装饰上她是进步的专家。在人家只知道穿丝织品,使男子们觉得像鳗鱼的时候,她却能从衣服的质料上给你一种温柔的感觉。”——《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4]215
对身体外在价值的强调,使女性的心灵成为可有可无的空白,当然,新感觉派作家们很多时候也无心去塑造一个有着饱满性格的人物,这些女性只不过是传递都市迷惘、虚无情绪的符号。她们经常抽着烟,眼神寂寞,对于现状并不满意,但是努力挣脱传统价值规训的她们,又未能像汲取新文化的知识女性那样,有着较为强大的内心和一定的精神追求,所以,短暂的感官刺激之后,在下一次的刺激来临之前,她们是十分消极的。
像穆时英《CRAVEN“A”》里的余慧娴,是一个“有一张巴黎风的小方脸的,每次都带了一个新的男子”[4]127的交际花。当律师袁野邨与余慧娴调情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衰老的灵魂:
“淡淡的烟雾飘到夜空里边,两个幻像飘到我的眼前。
一个是半老的,疲倦的,寂寞的妇人,看不见人似地,不经意地,看着我;
一个是年青的,孩气的姑娘向我嘻嘻地笑着。”
“可是我爱着她呢,因为她有一颗老了的心,一个年青的身子。”——《CRAVEN “A”》[4]131
袁野邨并不是真心怜惜余慧娴,虽然余慧娴对于生活的厌倦与迷惘,也引起了这个在都市中沉浮的浪子高度的共鸣,但他真正迷恋的还是其年轻的肉体,这是余慧娴的悲哀,她的命名CRAVEN“A”就是烟的品牌,这个隐喻再明显不过了,其形象、地位、命运、本质就像是这用完即弃的一次性消费品。
在交际花余慧娴那里,我们发现了都市女郎的一种常见生活状态——利用自己的身体收获利益(金钱)或者换取某种价值(更有品质的生活)的时候,她自己的身体也商品化了,成为别人可以拥有或者消费的物品。
刘呐鸥的《礼仪与卫生》里,曾在北京法国使馆任职的外交官普吕业向律师启明赤裸裸地表达了他愿出高价交换其妻子可琼几年的意愿:“你肯的话。我就把K 路角我那家古董店里所有一切的东西拿来借得几年的艳福也是愿意的。……我现在是商人,所以讲点生意话。”[3]62女性在男性眼中相当于物的存在,哪怕是价值极高,他可以不考虑可琼的想法,将她视为丈夫启明——另一个男性的所有物进行买卖。启明一开始颇为恼怒,随即领悟了:“或许这便是流行在现社会底下的新仪式。”[3]63小说的结局让人瞠目结舌:可琼留书出走了,且出于“卫生”考虑,让自己的亲妹妹白然陪伴启明,帮他解决某种需要。启明、可琼夫妻二人不再像传统的家庭那样以礼义廉耻等观念将家庭稳定地建立起来,这两个人完全没有遵循传统道德,各有情人。可琼更是在自我物化为普吕业的玩物后,将妹妹作为保持丈夫“卫生”的玩具奉上,女性被简化成带商品性质的符号。
施蛰存《花梦》里的主人公祯韦是都市里孤独的漫游者,他缺乏社交,经常在街头穿行,从形形色色的都市物象中获取感官刺激,进而跟踪女性,以各式各样的遐想填补精神的空虚和时间的空洞。一天,他跟踪了一个身材苗条的美女至电影院,还大胆邀请美女去喝饮料,在一次次的试探当中,他十分忐忑,因为他将自己的感觉视为神圣的爱情,而对方则是美丽纯洁的女神。事实上,这个美女是一个纵情而不恋爱的情场老手,第一次约会就直接“明示”自己需要首饰,虽然醒悟过来,看透了这个虚荣贪婪的都市女郎的实质,但祯韦并未愤怒离去,也遵循着商业规则,将美女视为娱乐消费品:
“我该当买一些东西给她,不错,因为她也在做工,这个东西便是一种酬报,犹之看电影、赛狗也要花钱买门票的。那么,这样说来,看客们花了钱,电影和赛狗便有精神,使看客感受到分外的娱乐,她也正是这样,卖弄着这样的姿态,是在献弄她的技艺呀!”——《花梦》[5]422
最后,当祯韦从饭店的床上醒来之后,发现连70 余元的钱包都失去了,他只能安慰自己“买了一个高价的经验”[5]425。回顾一下小说题目《花梦》,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短时间的一次恋爱沦为一次交易,追求美之理想终究是一场幻梦,且连幻灭都有着都市的速度感。
以自己的身体为商品,换取金钱的行为看似是商业都市女性身体的解放,但这种有损自尊的获利行为,与部分都市女性缺乏职业能力或懒于劳动有关,并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现代化”生活。当曾红极一时、只是略有岁月痕迹的黄黛茜在听到别人一句“今年是二十岁还是三十岁?”的问话时都失控至当众痛哭[4]237,女性身体的皮相之美之短暂、脆弱清晰可见。而都市新女性通过自我物化获得的金钱,无非又会投入新一轮对身体的投资上,周而复始,最终耗尽其身体的价值,成为金钱的奴仆。
二、情欲化的身体:都市新女性之二
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很多都市新女性一反过去的男性将女性作为猎物来追逐的认知,反“客”为“主”,掌握了主动权,男性往往在两性关系中居于被动地位,甚至沦为女性的玩物,或者说“消遣品”。这也让小说的男性叙述者(新感觉派小说的叙述者一般设置为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产生了一种既恐惧又刺激的复杂的心理感受。
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是一个关于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故事,男子H 在赛马场偶遇一都市女郎,女郎主动邀他游玩,在路上又遇见了早与女子有约的男子T,面对不满的T,女郎波澜不惊地邀请他“三人行”。当女郎在舞场与T、H 轮流跳舞时,H 向女郎询问T 是何人,女郎回答说是跟他一样的人,这一段对话之大胆,令人咋舌:
“——我说,可不可不留他在这儿,我们走了?
——你没有权利说这话呵。我和他是先约。我应许你的时间早已过了呢?
——那么,你说我的眼睛好有什么用?
——啊,真是小孩。谁叫你这样手足鲁钝。什么吃冰淇淋啦散步啦,一大堆啰唆。你知道love-making 是应该在汽车上风里干的吗?郊外是有绿荫的呵。我还未曾跟一个gentleman 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以上呢。这是破例呵。”——《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3]46
当男性还处在感情的初级积累阶段之时,女郎已用精确到以“钟头”的时间长度来测量感情,嫌弃“三个钟头”实在太长,将“谈情说爱”(包括跳舞在内)的浪漫步骤直接斥为“啰嗦”,她埋怨H的时间感太差,实际上是讽刺他把时间都浪费了,应该直入主题,女郎这一番对自己的欲望丝毫不加掩饰的语言,一般情况下本该作为人物的内心独白,毕竟内容太过“震撼”和“直露”,但作家直接借其口讲出,可见这些都市女郎性意识之大胆,对于男性之轻蔑,倒颇有“花花公主”的姿态。于是,这些都市新女性的身体不再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的身体做主,对人性来说,这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李今也指出,现代都市里的这种以“暂时和方便”为特征的情欲关系,最大的弊端在于“把主体性的人降低为从属性的功能或者说是工具,以功能的价值取代了个性的价值”[6],这样看来,所谓女性对身体的“自主”就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而且,这种欲望的追求没有终点,在一次邂逅当中收获的快感,转瞬就会消失,留下余慧娴式的疲惫空虚、黄黛茜年老色衰时的哀怨。这也是新感觉派小说中摩登女郎的命运走向,当肉体中的活力流失、美色衰竭的时候,她们也就无法享受快乐。欲望终究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快乐的主体和对象,又是无法控制的痛苦的化身”[7]。
三、伤痕累累的身体:都市下层女性
除都市新女性外,新感觉派小说中还有一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女性,与前面提到的那些时髦女郎相比,所谓解放身体、释放欲望的享乐生活距离她们太过遥远,她们的身体牢牢地受控于夫权和父权或男性社会的严酷规则。
都市别开生面的生活方式、浸润着西式文化的翩翩少年对一部分下层女性来说具有很强的诱惑力,穆时英的《南北极》《黑旋风》中的小玉儿(两篇不同作品的女性有着一样的名字,可见作者对这名字情有独钟),都背叛了原先的恋人(她们的恋人或是农民,或是下层劳动者),通过嫁给城里人进入现代都市,为此,她们的身体也经历了“城市化”改造。《南北极》里的莽汉小狮子是小玉儿抛弃的恋人(下层劳动者汪国勋)的好兄弟,他发现了小玉儿形象的改变:“脸白多了,走道儿装小姐了!越长越俏啦!……说话儿又文气又慢。那神儿,句儿,声儿,还有字眼儿全和咱们说的不同。”[4]30经过现代文明“教化”过的小玉儿,从皮肤、仪表、谈吐各方面都远离了原先的质朴,或者说,经过“身体改造”,粗糙的特质被“打磨”成了光滑精致,才能更好地融入都市。
更多的下层女性则挣扎求存,或承担起供养家人的生活重任,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她们也只能当女工甚至舞女、暗娼等在社会底层都属低贱的职业,柔弱的身体在冰冷的机器或者男性的蹂躏之下经历着工伤、疾病的折磨,也遭受着精神的凌辱。
穆时英《手指》里的丝厂女工翠姐儿,双手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下长满了水泡,也只能继续干活,“水泡儿破了,淌水,烂了,肉一块块的往滚水里边掉”[4]59,“她的血,皮肉在滚水里爆,十只手指像油条在油里煎,才抽出发光的丝来!”[4]60时髦女郎身上闪闪发光的美丽服装,却是由下层女性的血肉织就,即便同是女性的身体,也有等级的区分,惊心动魄的身体折磨与发亮的丝相对比,让人充满了寒意。最后,翠姐儿更因被监工毒打而死,让人唏嘘不已。再回看小说题目,“手指”——对于人而言,最重要的身体部分之一,先是在工业社会被工具化,进而被摧残,失去其生命机体的活力,象征着下层女性的类似处境。
娼妓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在20 世纪的上海,“妓界繁荣的局面到了20-30 年代发展至登峰造极的地步”[8]。穆时英《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里的舞女林八妹得罪了本地恶棍“象牙筷”,还被他打得遍体鳞伤,舞厅老板为了维护客人,跟巡警诬告,结果被欺辱的林八妹反进了警察局,她面对来访者发出“只想早一点死了算了!我受够了!”[4]474的绝望呐喊,这个在男性社会受着深重压迫的弱女子不仅是对自身生命进行否定,更是对社会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