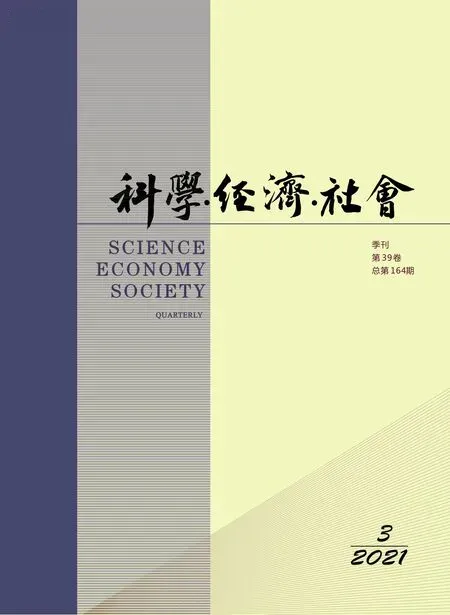新冠与身体环境:生态技术的探究
阿斯特丽德·施瓦茨
朱颖妤 译
在媒体报道中,SARS-CoV-2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是圆形的、通常是红色的、被一个总体来说是突出的辐射状花冠包裹着。在体系上它属于RNA 病毒,是冠状病毒家族的一份子。在2002/2003的时候,就是SARS-CoV-1引发了SARS疫情。病毒学研究在SARS-CoV 溯源中证实这种病毒能跨物种地存在于动物身上,并且可以将不同冠状病毒的基因组进行重组。病毒首先从鼻子和咽喉进入,侵入身体细胞,改写它们的组建程序,打开细胞膜并把整个宿主身体占据为自己的环境,将其变成自我复制的场所。在宿主身体之外,该病毒相当脆弱,一旦作为气溶胶释出,它在各种物体表面上经过室温数小时后便不再存活,在酒精或醛类溶剂、加热或紫外辐射的作用下它的存活时间又会大大缩短。
新冠病毒也需要一个相当复杂的生存环境(Umwelt),就是那些可以给病毒提供有利的生存条件的哺乳动物的身体,田鼠、水貂、猫鼬、狗獾、家猫,特别是世上最常见的哺乳动物——人类——都是这样的身体环境,病毒可以在其中找到适合它的条件。为了不断繁殖,它还必须前往其他的身体,因此病毒就可以反映出它的宿主的行动和接触轨迹,以及与其他哺乳动物之间的关系结构。看不见的病毒会通过宿主的行为模式以及关系结构(Beziehungsgefüge)而变得清晰可见。
因此,这种病毒可以被看作不同物种之间和物种内部关系追踪的放大器或中继器。它使关系的远近形势暴露出来,揭示了人与家畜、野生动物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共生模式,同样也揭示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哪些职业人群出于什么原因会被认为是系统相关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新冠时期与以往的不同,执政者与被管理的居民的角色理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关于文明社会的措辞也变了,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规定带来了全新的日常体验和生活模式。我们熟悉的问候和告别的肢体表达,主要是无意的、亲切的、好奇摸索的或者回绝的肢体接触,已经让位给各式各样被集体接受了的回避策略。它们使身体与身体保持距离,行动踪迹变得不同了。
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内外空间的文化编码(Codierung),由于不可见而又感觉上无处不在的气溶胶,室内空间成了有潜在危险的地方,在剧场内富有表现力的言语与歌唱成了危险有毒的空气来源。社会的文化活动要在城市的露天空间、空旷地区或者线上进行。在那不勒斯,年幼孩子们在路上上课;在巴塞尔,一个学生合唱团邀请大家参加线上盛装音乐会;在萨尔茨堡,一部《新冠歌剧:第47天》于2020年5月1日通过网络直播进行了线上首演。
因而,社会技术结构(Sozio-technischen Gefüge)的重构(Rekonfigurierung)中也有新冠病毒的踪影。在这件事上,并不是所有“新冠结构”的关系、事件、转变和可能性对整个社会或对个人都是消极、有害的。疫情的应对毫无疑问带来了新的教育、艺术和交流的形式,或是将原有的形式加以改进增强。例如,在科研工作和商业活动中,会议差旅被视频会议取代,在家办公呈繁荣发展之势,带来的结果则是通勤压力的降低以及有害尾气排放的减少。
不过在当下技术圈(Technosphäre),在矛盾心理中的容忍态度之外,不利的情况还是占了上风。新的卫生规则和日常技术、访问与边境管制一次又一次折磨我们,决定我们共同生活、到场和接触可能性的方式。最显眼的当属无处不在的口罩,还有在封闭空间入口处设立的消毒台以及地板上贴的间隔规定胶带,手机上的接触追踪应用记录、追踪个人的行动和接触情况。对流动的欧盟居民来说,更难以理解的是边境通道的电子版证件,或是餐馆、旅店及机场的问卷。所有这些技术手段不仅仅嵌入着流行病学逻辑,最首要的还有一层政治逻辑:“社交距离”:在例如奥地利、德国和瑞士都有着不同的距离标准;哪个地缘政治区域对谁来说是风险地区,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种问题,也是外交谈判的对象;在欧洲新冠应用程序的网络中,瑞士都不属于欧洲……国际与国内的监管框架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框架在技术与社会方面规定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交流,并且延伸到国家对于劳动关系、调动和接触方式的规定。身体、人、动物和其他物品之间的接触会在社会政治可以触及的范围内被管控,这些边界区域并不一定与病毒覆盖的范围一致。病毒冲破了自然/文化的分界,并要求我们既不能将大流行看作一个自然事件——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他们的文章里中对此做出了驳斥——又不能将其当作一个单纯的社会技术现象来看待和处理。相反,疫情中的病毒必须也被看作是一个行动者,它永久地打破了自然与文化之间松散的界限。因此,重要的是要关注病毒引发的关系类型,以及它如何通过这些关系将身体作为生存环境并在其中扎根下来,同时改变着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共振(Resonanz)。
所以,新冠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新的社会和技术环境在生成,而病毒作为行动者参与其中。此外,所谓的日常技术圈也从根本上被重置。技术圈这一概念被提出的目的在于突出技术的无处不在,就像19 世纪引入生物圈(Biosphäre)这一概念是为了体现生命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自然力量。全球材料循环的概念与生物圈有关,而在定义技术圈时,我们把技术当作一台拥有准自治动力的全球化机器(“设备”),人口仅仅是它驱动装置的一部分。像在技术—人—机器(Technik-Mensch-Maschine Relationen)的关系中常有的前提那样,人类在技术关系中不再拥有支配力量,转而受到技术结构的驱策。引入技术圈的概念是在呼吁告别看似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概念,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没有被设想过但会发生的结果上,放在技术物(die technische Dinge)的自主独立性(Verselbständigung)上。在我们讨论新冠时期的日常技术圈时,不仅要谈论共同生活的条件的变化带来的不适,同时也要批判性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以人与人的生存环境作为代价的这种不平衡不对称的技术关系结构中,还存有怎样的回旋余地。为了深入探索那些在韧性和响应率都很出色的结构关系、过程和事件,生态技术关系结构的重点会再一次转移并反映出其不对称性,从而揭示结构中的一种共振,而这种共振则代表着一种成功的技术、环境和社会关系。
在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研究(STS)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概念,用来理念上加强上述涵义中的生态技术关系结构,为的是确认对称关系和参与性关系,并将其多样性纳入考量。其中包括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973)提出的联盟技术(Allianztechnik),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2017)的认知集合(kognitive Assemblage),简·本尼特(Jane Bennett,2010)的物的政治生态学(die politische Ökologie der Dinge),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2012)的代理的实在论(der agentielle Realismus),本萨德-文森特、罗威、诺德曼和施瓦茨(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Sacha Lowe,Alfred Nordmann,Astrid Schwarz,2017)提出的技术科学的对象(die technowissenschaftlichen Objekte),以及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2003)的《多重身体》。串起这些概念的是对新道路的探索,它们旨在通过把握对象(Objekt)将知识论和本体论的领域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它们作为有关联的探究活动,能更好地被放在同一主题下讨论。
在对动脉硬化的多重特性进行调查时,安妮玛丽·莫尔提出,多重性不该从一个对象、病体的不同角度来把握,而是反过来研究,对对象和现象不同的处理方式如何导致一个对象的不同类型模式。她的调查表明,关于疾病的知识、医学技术和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都与疾病被宣称的特性有关。在由新冠病毒引发的Covid-19疾病中,也出现了这种对象——即“病体”——的多重结构。相应地,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战胜这个疾病,不应只把重点聚焦在病毒在身体环境中展现出的特性,而且还要考虑到以下两者之间的联系:一个是对待身体的方式,另一个是从中的生产出的有关身体的知识。病人、家属、机器、药品、护工和医生都涉及其中。因此,为了调查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身体环境和身体自身的构建,为了使它们彼此之间更加紧密联系,我们不仅要有病毒学家的意见,还需要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的意见。
这可能还有助于提升行动者之间的响应率,从而形成一种加强社会韧性的Covid-19应对方式,这个韧性依赖于多样性和理性,而不是依赖于一场危情游戏。连争取使社会恢复健康这样理所当然的事可能也会失去它的主导地位,甚至会作为论点被质疑。在“社会”这个实验室中,健康/疾病的关系不应被认为对于使社会恢复健康具有流行病学必要性。不过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情形下,新冠和它的身体环境不仅要被不断重新解释和讨论,还可以将其视作测试对称性和参与性关系形式——例如身体本身和身体环境的关系形式——的机会和可能性。
生活在新冠时期意味着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社会过程中,其中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在生成。根据培根条约的逻辑,科学与社会的协调已不再可能。而在一个知识社会中,科学实践在创新的社会领域蔓延,社会变成了研究场所和开放实验室,像一个“真实实验室”(Reallabor),实验方法和假设的考量与社会接受度相关。实验实践的重大变化在于理想的实验室实验场景(Laborideal)向理想的田野实验场景(Feldideal)的转变。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学而制度化的理性原则不论怎样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转达给社会,为了拓宽和证实知识,理性原则作为认知的引擎将错误合理化了(Schwarz&Krohn,2014)。反过来,科学又会通过社会面临新的责任形式,因为在社会转变的开放空间中进行研究隐藏着附加的风险。
就像目前在媒体中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转变绝不是毫无问题的。一方面,新冠的自然科学专家对那些要他们同时具备知识广泛性和准确度的要求感到恼火;另一方面,通过公共观看(public viewing)实验室操作,许多公民对其暴露出来的愚昧无知感到愤怒。而积极的方面是,牵涉新冠事件的公民更多地了解了有关病毒和它所需身体环境方面的知识在实验室中是如何产生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如何被谈判协商的,尤其是有关它内在临时性的知识。毋庸置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也是一种负担。同样毫无疑问的还有,新冠疫情极其包罗万象,所有的参与者同时既是实验者也是实验对象。举个例子来说,他们是测试口罩有效性的实验对象,同时他们也是实验者,在现有规则下评估何时何地哪种口罩在社会和文化上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实验的力量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如果对象或过程的测试,以及知识的产生在遵守特定规则的情况下可信,我们就能够从新冠时期学到很多,并且将会直接体验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拥有自我负责的实验能力的社会。将“生存环境”作为研究主题,在一个社会和知识的开放关系中有了新的知识指导的作用,这一作用要从生态技术关系结构的角度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