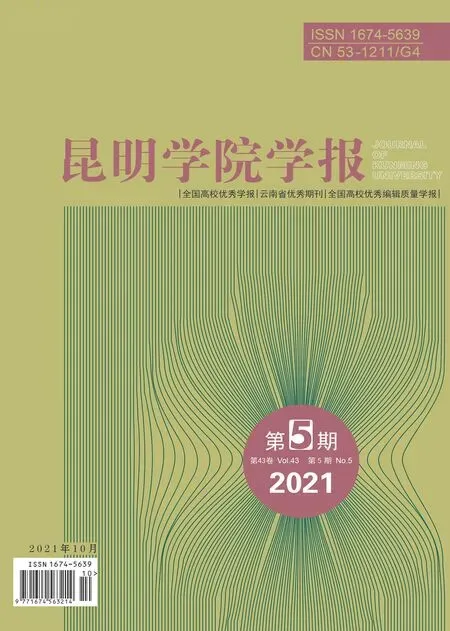开拓与尝试: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转换中的《祈颂姑》
李 飞,罗 意
(新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1956年,奥德丽·伊莎贝尔·理查兹(后文简称理查兹)的《祈颂姑:赞比亚本巴女孩的一次成人礼》(后文简称《祈颂姑》)一书首次出版。此书在出版后的很长时间都未能引起学界重视,其光芒被英国人类学黄金十年中一批对社会结构研究的鸿作所遮蔽。长期以来,学界熟知理查兹多是因其在饮食人类学中的贡献,以及她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会长的身份。事实上,理查兹还是一位仪式研究专家,但其对本巴女孩成人礼的研究被视为范热内普“通过礼仪”之例证。
20世纪60年代后,维克多·特纳、克利福德·格尔茨等人在仪式研究中建构出“过程理论”与“象征理论”,并通过分析仪式的联结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为仪式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由于涂尔干的研究以及功能主义内部争论的热度逐渐降低,在此背景下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英译本在1960年出版后逐渐开始在欧美的仪式研究领域产生影响。1982年《祈颂姑》再版,作为“通过礼仪”的经典再次被确证,其功能主义分析的风格让人回想起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里夫·布朗等人。书中隐约流淌出的对仪式过程、仪式参与者能动性、仪式中各种象征符号与意义的内容,以及对仪式进行中调查者“存在感”的反思,让我们意识到该书应被视为仪式研究范式转换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作品。简·拉封丹在《祈颂姑》第二版前言中强调:“当下,宗教又重新成为人类学的一个焦点问题,而仪式阐释则是理论争议的中心。读者会清楚地看到,有关研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发源于具有开拓意义的本书。”[1]10
对中国人类学研究而言,理查兹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之前都是陌生的。1992年,理查兹的《东非酋长》在国内出版,这是一本关于东非部落社会政治发展历程的著作。之后,渐有学者介绍理查兹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关系和其在饮食人类学中的贡献,以及关于她对东非本巴人的研究。正如有学者认为,“多数人认为人类学家较大量而有系统的营养研究,应该从1932年奥德丽·理查兹(Audrey Richards)分析非洲罗德西亚北部本巴人(Bemba)的饮食营养与其他文化制度间的关系开始算起。她指出食物消费首先是从家户到亲属群体,强调共享和分配,并最终延伸到范围更广的氏族或部落的食物生产系统。”[2]虽然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在其论著《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中提到了马林诺夫斯基最为重要的三个学生,其中理查兹居其一,并提到作为强调抽象结构之上的、实践的、首要性的批评者,理查兹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中尤为突出。[3]然而学界对于理查兹的仪式研究在人类学术史中的重要性仍旧缺乏足够的关注。
2017年,张举文先生所译的《祈颂姑》在国内出版。有学者对该书进行了关注,“奥德丽·理查兹的《祈颂姑》以民族志书写了赞比亚本巴女孩成人仪式祈颂姑的社会背景、仪式过程,并通过仪式象征分析及社会结构分析等理论视角对此仪式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4]尽管该书被纳入了“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序列中,但并未能像丛书中其他著作一样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揭示简·拉封丹所宣称的“开拓意义”,我们拟将理查兹的《祈颂姑》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转换过程中予以审视,通过梳理理查兹对本巴女孩成人礼的描述,以及著作中闪现的观点与写作手法,分析该书对同时期和后世人类学仪式研究的影响,并阐明该书在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转换中的意义。
一、奥德丽·理查兹与本巴人
理查兹1899年出生于英国,1922年进入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主修文化与生物学。正是这种生物学的背景,让理查兹在1928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成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后仍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人类的饮食与营养方面。1930年,理查兹以《一个原始部落的饥饿与劳动》一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此后,理查兹围绕饮食和营养的主题继续在非洲开展她的人类学研究,而且由于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理查兹对非洲氏族部落的研究总是围绕“食物的共享对促进社群团结的功能”[5]这样的主题展开。这也奠定了理查兹在饮食人类学方面开创性的贡献,以及她在西方人类学界的地位。
1931年,理查兹进入非洲赞比亚地区对本巴人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将自己的学术人生与本巴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本巴人,亦被称巴本巴人,生活于非洲中南部,属于尼格罗人种班图类型,使用本巴语。除赞比亚之外,马拉维、坦桑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等与赞比亚相邻的国家及地区也有众多的本巴语使用者。[6]据理查兹的说法,她在本巴社会做田野调查时,本巴人口约有15万,而且 “他们居住在非常广袤的草原,彼此相距甚远。”[1]29本巴人是一个从事游耕的农业民族,他们通过将树林中的树枝收集起来,烧成灰烬后种植“子”。“本巴女人主要负责粮食的生产,要想开垦一片地,男人要先砍伐树木,女人把树枝堆到地中间,这样可以烧成灰,耪成垄,然后播种 。”[1]29因农作物单一和环境恶劣以及耕种方式粗犷等原因,本巴人时常面临食物短缺。
在英国人类学史上,对20世纪30—40年代非洲社会的研究无疑是划时代的,培养出了包括埃文斯·普理查德、M·福蒂斯等在内的一批影响深远的人类学学者。在前往非洲进行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中,理查兹是先行者。与其他人类学家相比,她更早在非洲社会中从事实地调查。以《祈颂姑》为例,其田野资料源于理查兹在“1931年所观察到的”[1]1,与埃文斯·普理查德对阿赞德人与努尔人的调查在同一时期,但因“繁忙的教学工作和世界大战使我二十年没能将本书的记录手稿整理成书。”[1]1当1956年《祈颂姑》面世在那个星光璀璨的时代时,理查兹的光芒被遮蔽了。
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类学中涌动着一股对传统功能主义理论反思的“运动”。该运动与法国对结构主义的反思、美国对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反思一起,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研究反思的大潮,并为20世纪60年代及之后的反思人类学奠定了基础。例如,爱德蒙·利奇在上缅甸克钦人的研究中发现了“钟摆模式”;格拉克曼及其弟子维克多·特纳发现了冲突在社会结构平衡中的价值;弗雷德里克·巴斯则在社会结构平衡假设中引入了能动性、情境与决策模式等重要概念。除此之外,艾伦·巴纳德指出有人尝试“摆脱以往形式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特别是结构—功能主义。而倾向于更加个体和行动中心的研究范式。”[7]同期,美国人类学研究范式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谢丽·奥特纳指出:“一种协裹着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语义学、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融合了美学理论的杂汇,逐渐取代了传统意义的人文科学体系。”[8]在这个西方人类学界研究范式转换的关键节点,理查兹抛出了《祈颂姑》这本仪式研究著作,以纪念导师马林诺夫斯基。
在此书中,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里夫·布朗的思想如影随形般地影响着理查兹,但理查兹又在多处突破了老师们的观点,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类学的各种新理论。简·拉封丹认为,“本书包含的不只是对一个不再表演的仪式的经典描述,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而且也提出大量想法,刺激我们去思考仪式与社会生活的关系。”[1]26接下来,本文将从理查兹关于本巴女孩一次成人仪式的描述开始,去领略《祈颂姑》这本被忽略的民族志之魅力。
二、祈颂姑:本巴女孩的成人礼及其功能
“祈颂姑”是本巴人为女孩所举行的成人礼仪式的称呼。理查兹关于仪式的分析就从这样一场成人礼出发,展现了处于母系社会的本巴人举行祈颂姑仪式的过程与特征。
据理查兹讲,要真正考察清楚女孩成人礼在中非地区的分布是不可能的,而且想要了解祈颂姑仪式的具体分布同样存在困难。因为“在北罗得西亚(赞比亚)、尼亚萨兰(马拉维)、刚果以及安哥拉的许多部落,都为女孩举行成熟期礼仪,并且都用本巴语来命名这个礼仪——祈颂姑(Chisungu)”[1]157,但在这些使用“祈颂姑”这一名称的不同部落中,仪式过程与内容也具有普遍的差异。理查兹在《祈颂姑》的附录甲中通过分类的方式列出了中非地区举行“祈颂姑”仪式的部落,以及这些部落在举行祈颂姑仪式时与本巴部落之间的差异。
在本巴社会,祈颂姑仪式既可能由某个想要为自己的女孩举行祈颂姑仪式的父母发起,也可能由几家人为了他们具有共同年龄特征的女孩共同发起。为女孩举行祈颂姑仪式的是一位专门从事该职业的司仪——“纳齐布萨”,司仪需要受礼女孩的父母去邀请。过去,还要准备树皮衣作为司仪的报酬。“纳齐布萨组织各个礼仪,领头跳舞和唱歌,安排做必要的陶器。她被认为有着很重要的劳务责任。”[1]56仪式之后,纳齐布萨还会与受礼的女孩一生都保持拥有某种特殊的关系。祈颂姑仪式的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长,过去可能会长达6个月或者1年,但随着欧洲殖民政府的影响和社会的变迁,仪式过程已经简短了很多。理查兹所参加并描述的两个女孩的祈颂姑仪式持续时间仅为一个月,然而这仍然比当地所流行的仪式程序要繁复。[1]60在1956年《祈颂姑》首次出版时,理查兹提到:“我现在可以肯定,祈颂姑仪式一定没有我在时那样频繁地举行,甚至可能已经绝迹了。”[1]1
理查兹根据祈颂姑仪式举行的时间顺序,以每一天为单位,分别对一个月中重要的二十天进行了细致描述。她强调,整个仪式都是在一种跳舞和唱歌的状态中进行的,而仪式也可能随时结束。在整个仪式中,第一天、第七天和最后一天最为重要,另外第十七天的“进入丛林”环节也很重要。在理查兹的描述中,祈颂姑仪式似乎给人一种很随意的感觉,但她指出,祈颂姑仪式很明显的有着强烈的仪式禁忌。例如在某些仪式过程中,举行仪式的女人们会严厉呵斥捣乱的小孩;当仪式进行到某个部分时,总能看到路边“那些低着头不敢看的男人们”;两位受礼女孩用衣服遮住乳房却遭到司仪强烈且愤怒的谴责;一个女人因做陶器迟到而被罚上交一个手镯,却丝毫没有获得大家的同情……
仪式对于本巴女孩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就如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所说:“每一个体总是共时性或历时性地被置于其社会之多个群体。为从一群体过渡到另一群体以便与其他个体结合,该个体必须从生至死,始终参与各种仪式。”[9]仪式是女孩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将从可以“干活偷懒”的女孩转变成必须认真干活的女人。不仅如此,到达受礼年龄的女孩会因受过礼仪而得到大家的赞扬,反之则会成为大家所恐惧的对象。从《祈颂姑》中描述的一段情景可见一斑:受礼女孩因仪式要求必须要跳过一个并不是很大的火堆,但她始终没能跳过,最终在母亲恐惧的眼神和强烈的斥责之下成功完成。
理查兹通过对本巴人的祈颂姑仪式进行分析,指出了该仪式的三个主要功能。
一是传达成长与适婚的信息。不同的仪式动作具有不同的表达意义:女孩被裹上毯子送进成人礼房,用毯子包裹女孩在仪式中暗指“隐藏”,旨在通过某些日常生活行为向女孩传达进入社会后的禁忌;女孩全身会被抹上白灰,这是仪式性指责;模仿与生殖相关的一系列行为。这些仪式中的行为表达了女孩已成年,并达到适婚年龄。
二是对女孩进入成年后的教导。在仪式中的很多舞蹈行为是为了教导女孩,使她们学会生活中的技能和如何做好一个“女人”。例如:“纳齐布萨”纳高西埃在泥炕上教女孩分娩的动作和教女孩在月经期如何在河里洗澡等。虽然理查兹指出,在整个祈颂姑仪式中,似乎始终找不到这些为女孩跳仪式舞蹈的女人是如何教导受礼女孩的,因为在很多被称为教导性的指示性动作中,受礼女孩由于被毯子盖住,因此她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动作,但这并不妨碍仪式所体现的教导功能。
三是确认“女孩”向“女人”身份的转变。通过理查兹对仪式的描述可见:仪式前,本巴女孩被认为是“一个小女孩”;仪式中,女孩不断地被教导、嘲弄并向她们的“丈夫”表达敬意;仪式后,她就可以做那些诸如“做饭、做农活”等女人们所做的事情了。在谈到祈颂姑的目的的时候,本巴人认为这个礼仪对他们而言很有必要,因为“谁也不想娶一个没有被跳过祈颂姑的女孩;因为那样的女人不知道她的其他女人同伴所知道的;她也不会被邀请参加别的祈颂姑宴席。她只会是一个废物(cipele),没开垦过的野草(cangwe),没烧过的泥罐(citongo),一个傻子(cipumbu),或干脆‘不是一个女人’。”[1]116而且本巴人认为,只有经历过祈颂姑仪式的女孩,今后才能生很多孩子。本巴女孩通过仪式由“女孩”转变为“女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得以转换。
除了上述三个重要功能外,理查兹还指出,祈颂姑仪式还有集体性娱乐、表达血缘关系、增加仪式主人和受礼女孩社会地位的功能。仪式最突出的特征是大量的舞蹈和歌唱,每一环节都包含了各种类型的舞蹈和歌词。通过这些舞蹈与歌唱,受礼女孩及其亲属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从以上理查兹对祈颂姑仪式意义层面的解释来看,其仪式分析仍旧是功能主义的。她明确指出:“人们举行宗教礼仪是因为这些礼仪对于个体、对于整个社会,或是对于有关群体具有某种功能作用,简言之,因为它们满足某种需要。”[1]115
三、反思与创新:“开拓意义”之所指
在《祈颂姑》成书的年代,英国人类学正处于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向过程研究范式的转换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通常都表现出了较强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是对功能主义的传承,另一方面是对功能主义的反思与突破,但尚未发展出像功能主义一样具有统治力的理论体系。过渡性特征在《祈颂姑》一书中体现得尤为充分,表现在她对仪式中过程、能动性、冲突、矛盾、象征等现象的关注,以及对“自我”在研究中的“角色”的反思上。
理查兹在理论上首要的突破是其在分析中表现出了对“过程”的强调,是对仪式过程与世系情感或认同强化过程的强调。理查兹并未以“本巴人的仪式研究”为标题,而是选择了一场“本巴女孩的成人礼”为研究对象。这意味着,她将仪式视为一场连续的、由不同“小”仪式所构成的仪式系统。在每一场“小”仪式的分析中,理查兹都关注了祈颂姑仪式的具体过程,与范热内普对“过渡礼仪”的处理相似。她避免将仪式“静态化”处理,而是分析行动中的“仪式”。在以往的仪式研究中,群体“内聚力”是一个重要关注点,这正是涂尔干强调图腾作为“集体意识”的原因所在。理查兹则把本巴人关于对自我、部落认同建构分配到女孩不同阶段的成人礼中,并分析仪式展演对调动仪式参与者和观察者的情感在本土知识与群体认同中的重要意义。理查兹从“特别表象”“信条”“祈颂姑中的表现”“其他礼仪中的表现”四个方面将本巴人的仪式行为置身于一种生活行动中,指出在本巴社会“除了有关个体的巫术礼仪之外,没有一个方面不是依靠祈颂姑仪式作为源头,或是现在所施行的成熟期礼仪的某种简化形式。”[1]135她将仪式置于本巴社会行动与控制的体系中,认为仪式作为一种群体之间联结的纽带,具有稳定社会的作用。
理查兹在理论上的第二个突破是对仪式过程中矛盾与冲突的强调,以及仪式在消解社会内部张力中的功能。理查兹在结论部分对祈颂姑仪式进行系统阐释与解读时,专门设定了一个章节来分析仪式中的“无意识的紧张与冲突”。在这里,她展现了本巴人在仪式中的那种性别之间的张力与仪式身份和普通身份之间的反差,虽然本巴人在性别上并没有强烈的敌意,但在性别之间的张力下,“本巴女孩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长大的,被教导的是向男人跪下,将男人置于首位。”[1]146本巴女人渴望拥有孩子,而这需要男人,因此她们意识里会产生从丈夫那里夺走孩子的负罪感。即使这样,“女人们当然强调她们对有关生孩子的事的完全控制权。在这方面,女孩的母亲、姑姑和婆婆是联合在一起的;这样的性别群体将基于宗族世系的群体切割开来。”[1]146本巴女人通过祈颂姑仪式从男人手里争夺对孩子的最大权利,这是母系与父系之间张力的体现。在仪式身份与普通身份之间,面对婚姻,“无论本巴人的恐惧感有多么强烈,从中逃避出来的方法很容易。只要正确遵循仪式规则和依靠年长的人……就可以了。”[1]144理查兹意识到本巴社会中潜在的性别冲突,她指出:“作为完全是探索性的看法,我也提出,在这个特定的母系社会中,缺少两性敌意与感到剥夺男人的父亲权力的负罪感之间也存在互动关系。”[1]149因此,理查兹认为祈颂姑仪式是协调本巴社会性别之间的张力和社会关系的有效行动。
理查兹在理论上的第三个突破是对象征符号的关注。传统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仪式如何满足了人群的需求,如何维系了社会结构的平衡。然而一旦人类学家关注仪式过程、过程中人的行为以及仪式场景中的情感表达时,象征符号便跃然而出。“人类学家奥德丽·理查兹(Audrey Richards)是较早强调象征具有多重意义的学者之一。她认为,一个象征会因为不同语境具有不同意义。这是她在对成人仪式的观察研究中发现并加以运用的观点。”[10]对理查兹来讲具有一定困难的是,如何在仪式分析中去处理好社会结构与象征符号之间的关系,从整部著作可以看出,她在很多时候显得比较犹豫,她既想将仪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解释清楚,又想对祈颂姑仪式过程中的诸多象征符号的文化意义有所阐释,虽然理查兹只是将对象征符号及其文化意义的分析置于附录部分,但这并未妨碍她在这一方面的重要发现。理查兹对祈颂姑仪式的象征性分析集中在为了仪式而准备的必要陶器上,以及仪式中所歌唱的歌词、模仿行为和图案等。她指出:“所有的象征物都可能将多重意义与固定的形式结合起来,有些是标准的,有些是极具个性的。像祈颂姑这类又长又复杂的仪式代表了一系列的观点看法,有些被理解了,有些被半理解了,有些只是被感觉到了。”[1]153因此,我们看到那些陶器制作完成后,在祈颂姑仪式中或许只是被简单地使用过一次,或者根本都没有发现某些陶器在具体的仪式中发挥过哪些重要的作用。但从整个祈颂姑仪式来看,这些必要的陶器对于仪式本身而言无疑是重要的。维克多·特纳曾指出:“一个简单的象征符号既表现强制性的东西,也表现人们所欲求的东西。”[11]理查兹通过对仪式中的象征意义分析,强调这对本巴女孩成人礼的重要作用。她认为陶器被做成不同的模型,象征着本巴文化中的深层含义。例如:鳄鱼作为本巴王族的象征,这种陶器模型可能教给女孩“敬重酋长”。还有象征着喂奶的母亲和怀孕的女人的陶器等等。但不同于维克多·特纳的是,她在分析中没有跳出马林诺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假设,而维克多·特纳则从结构主义层面出发完成了自己的象征分析。
此书的第四个突破是对仪式的细微阐释和主位反思,这是理查兹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体现在她对人类学家究竟能不能理解研究对象之“仪式”的反思。很长一段时期,民族志更像是一种“冷冰冰”的、“实验式”的社会解析记录,人类学家的身影和声音被巧妙地隐藏。而《祈颂姑》的独特之处在于,理查兹从头到尾都呈现出自己的思考,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民族志方法上来讲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例如,“有些关于女人模型上的肚脐的猥亵笑话使我想到是否这后面还暗含兄妹乱伦的意思。但本巴人一般把肚脐看作身体上逗乐和猥亵的部位。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1]81;她甚至相信,“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场,这次为那个女孩和邻村的一个同伴举行的祈颂姑仪式,很可能会是在另外一个时间,规模也会小些,也可能仪式地点会换在一个较偏远的村子。”[1]59-60这一点从《祈颂姑》的章节设定就可以发现。这部民族志被设定为三个章节,第一章描述非洲本巴社会的文化背景,第二章描述祈颂姑仪式的过程,第三章是作者对仪式的“阐释”。在分析中,她明确将仪式参与者、文化拥有者和仪式观察者进行了区分,在对仪式阐释过程中不断强调自己作为一位人类学调查者所存在的缺憾,以及对仪式理解可能存在的不足甚至是“误读”。理查兹始终在思考自己对祈颂姑仪式究竟有多少了解,始终在强调观察到的“细节”和自我的“感受”。
四、结语
理查兹通过对祈颂姑仪式的描述与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非洲母系社会如何使女孩转变成为女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仪式通过一系列歌唱与舞蹈完成对女孩的教导,从而解除因女孩长大和婚姻带来的各种潜在危险,消解本巴社会内部性别之间的张力。以至于理查兹在结尾时为祈颂姑仪式的意义做了一个经典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式的结论:“仪式中的象征运用保证了不同感情的和解,从而满足了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个体,并支撑着该社会的主要机制体系。”[1]156
同时,《祈颂姑》在理论和方法上是不连贯、不够成熟的,但其却又有诸多突破,这些突破在理查兹同期和之后人类学仪式研究中不断发展、成熟,形成了新的仪式研究理论。例如,理查兹对本巴女孩成人仪式中矛盾、冲突的关照,以及对范热内普“通过礼仪”理论的运用,在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分析中得以最终成型。又如,理查兹对祈颂姑仪式中各种象征符号的分析颇有象征人类学的意味,而这一理论在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中得以成型。再如,理查兹对人类学家在仪式研究中(准确地说是“田野调查”中)对自我身份的疑惑,启发了人类学者是否能够真正理解研究对象等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反思人类学的核心关照。《祈颂姑》不仅是一本关于本巴人“女孩”成人仪式的民族志,而且因其对女性以及社会中“女人间的等级结构”[1]62的关注,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