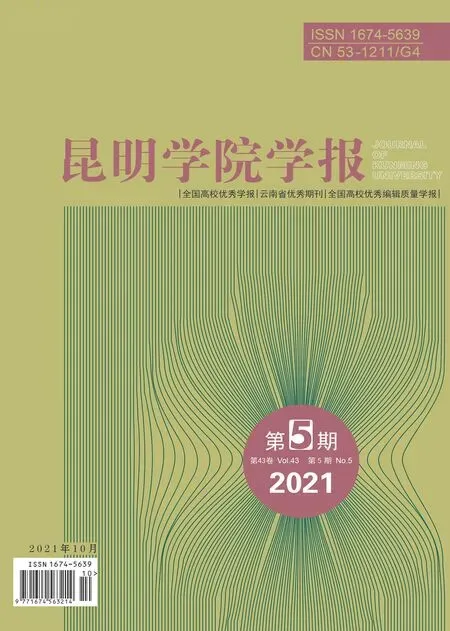女巫形象在儿童文学中的嬗变
腾 旋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女巫”(witch)一词源自欧洲,意指拥有巫术的女人。“女巫”这一形象最早是以神话中的女神形象模糊出现的。神话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形态之一,同时神话也被视为人类的“经典童话”。神话中的女神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女巫的原型。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的返乡途中,在阿依厄岛上遇到了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女儿喀耳刻,喀耳刻邀请船员到岛上大餐一顿,然后在食物中放入魔药,以变形术将船员们变成猪。美狄亚也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女巫,她是女神的后裔,精通巫术和魔法,以赫克忒女祭司的身份出现。美狄亚帮助伊阿宋得到了金羊毛,但当伊阿宋移情别恋时,美狄亚不仅用下了毒的衣服杀死了伊阿宋的新欢,而且还杀死了自己亲生的稚子。[1]无论是喀耳刻还是美狄亚,在神话中她们都是罪恶和灾难的化身,以神力给人类带来了苦难。显然,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并没有明确的女巫形象,她们的形象通常在女神、女祭司和女巫形象之间变化。
而在古典童话中,女巫的形象往往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她们是又老又丑、长着鹰钩鼻的老巫婆;她们穿着黑色的斗篷,骑着扫帚飞行;她们有丑陋的外表和邪恶的巫术,甚至可以合成奇怪的药物来毒害他人……这样的女巫形象在格林童话中屡见不鲜,她们常常站在弱小主角的对立面去作恶,这些形象确立了女巫“邪恶化身”这一形象特质。美国心理学家谢尔登·卡什丹在他的著作《女巫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塑造性格》中提出,在《格林童话》中不同的女巫象征着不同的人性之罪,也即他所说的“儿童七宗罪”:虚荣、贪吃、嫉妒、欺骗、色欲、贪婪、懒惰。[2]然而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女巫这一形象的特质发生了变化,让人们对女巫形象有了颠覆性的认知。这些儿童文学中的女巫不再是邪恶的代表,而是融入尘寰,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她们的神奇之处。进入后现代社会,女巫形象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她们在后现代语境中寻找新的生活模式,承载着人类对自身价值探索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涉及女巫形象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探寻女巫形象演变所反映出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价值和意义变化的深层原因。
一、童话中的传统女巫像——“邪恶女巫”
传统的童话故事源于民间口述传说,它们的情节架构往往具有韵律性和重复性,常是邪不压正或是以弱胜强的“快乐结局”。且在其叙事特质中通常是由主角的行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故事中往往包含着个性鲜明的主角和刻板印象的女巫。在传统的童话故事中,女巫是不啻妖魔的存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格林童话《亨塞尔和格莱特》中的女巫。“谁想呢,老太太只是装出一副和善的样子,其实却是个专引诱孩子们上当的恶妖婆。她造那幢面包小屋,纯粹为的这个目的。一旦哪个孩子落在她手中,她就杀死他,把他煮来吃掉,而这天便是她的节日。”[3]66她把亨舍尔关进马房,并指使格莱特干活以喂饱、喂肥亨舍尔,从而达到吃人的目的。俄罗斯民间童话的老巫婆芭芭雅嘎(Baba Yaga)也以爱吃人而著名,她住在一间会吃人的小茅草屋里,屋子底下长着两只鸡脚并靠此来移动,她屋子外的篱笆则是用一长排人骨插着骷髅头做成的。这种女巫最为邪恶,她们以吃人为直接目的,暴虐、贪婪以及嗜血是她们最本质的特征。
除了吃人的邪恶女巫外还存在着另一类邪恶女巫,她们以毁灭美好、奴隶他人或其他恶毒行为而臭名昭著。在《白雪公主》中,女巫化身为白雪公主的继母,因为嫉妒公主的美貌而屡下杀手。“她痛恨她,忌妒和骄傲像一把野草在她心里越长越高,使她日夜不得安宁。”[4]她吩咐猎人将白雪公主带去森林杀死,留取白雪公主的肺和肝作为证据。拿到猎人替换过的肺和肝(女巫误以为是白雪公主的),她甚至将其烹而食之。知道白雪公主未死后,她又伪装成各种模样并制作各类毒药去毒害白雪公主。在弗兰克·鲍姆的《绿野仙踪》中,东方恶女巫“把孟奇金人控制在手中,让他们日日夜夜为她卖力”[5],而西方恶女巫则统治着温基人。西方恶女巫不仅将女主人公多萝西囚禁起来,还企图抢走她的魔法银鞋。在安徒生童话中《打火匣》里的巫婆则欺骗士兵去树洞里获取宝物;《海的女儿》里住在可怕漩涡中的巫婆明知道小人鱼悲惨的结局,却“可憎地大笑了一通”,并割取了小人鱼的舌头、夺走她最美丽的声音;[6]《野天鹅》里国王娶了一个恶毒的皇后,庆典之后“他们却没有能吃到那些多余的点心和烤苹果”[6]21,恶毒的皇后“只给他们一茶杯沙子,而且对他们说,可以把这当作好吃的东西。”[6]288她把艾丽莎送到乡下寄养,并在国王面前说年轻王子的坏话,而后她使用巫术将王子们变成野天鹅。十五年后,艾丽莎从乡下回家,王后看到她是那样的美丽,心里充满了恼怒和仇恨,她拿出三只癞蛤蟆,每只都亲吻一下,她对第一只说:“当艾丽莎走进浴池的时候,你就坐在她的头上,好使她变得像你一样呆笨。”她对第二只说:“请你坐在她的前额上,好使她变得像你一样丑恶,叫她的父亲不再认识她。”她对第三只说:“请你躺在她的心上,好使她有一颗罪恶的心,叫她因此而感到痛苦。”[6]289这种种邪恶的行为暴露出了邪恶女巫的恐怖之处,也揭示出了女巫内心深处的贪婪、虚荣与渴望满足的欲望。无论存在着怎样的理由,邪恶女巫的本质就是毁灭,她们站在人类的对立面,成为人类的敌人。
邪恶女巫在童话中形象单一,外貌描写极少,不过在众多作品中也能窥之一二。在格林童话《约林德和约林格》中,女巫是“脸又黄又干瘪,两只红通通的大眼睛,一条尖端直伸到下巴的弯弓鼻子”,并且还会喷吐毒液和胆汁。[3]278在《亨塞尔和格莱特》中邪恶女巫“都生着红红的眼睛,看不远,但嗅觉却灵得跟野兽一样,老远就能发觉有人来了。”[3]66芭芭雅嘎则被描写成“样貌很丑,牙齿是铁做的,食量很大但骨瘦如柴”,所以也被称为“瘦腿如骨芭芭雅嘎”(Baba yaga Boney Legs)。丑陋恐怖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女巫的邪恶本质,丑恶与美善对立,这是传统思维模式中形成的直觉反应。
在当代艺术童话中,罗尔德·达尔的《女巫》延续了这一类型的女巫形象,但是他丰富了女巫的形象描写,也使情节变得更加惊险刺激。在达尔的笔下,女巫像猫那样长着薄薄的弯爪子,头上一根头发也不长,鼻孔大且呈粉红色,弯曲如贝壳边,因此嗅觉能力极强,能够嗅出小孩子的气味,眼睛中央有火和冰在跳动,没有脚趾……其中女巫大王的面目更是恐怖,“它是那样扭曲、枯萎,又皱缩又干瘪,看去像在醋里腌过”“正在发臭、化脓、腐烂。它的边缘可以说是全都烂掉了,在脸的中部,环绕着嘴和脸颊”“皮肤都溃烂和蛀蚀了,好像长了蛆”[7]。除了更加丑陋的外表之外,女巫的行为也更加邪恶,她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立了“女巫联盟”,其目的是杀死全世界的小孩。她们不再使用吃人的方式,或是直接使用魔法将小孩子变形,而是借助于药物(86号配方慢性变鼠药)把小孩子变成老鼠,并借人类自身消灭小孩子变成的老鼠。
但无论童话故事中的女巫如何邪恶、强大,最终都难逃一死。《亨塞尔和格莱特》中的巫婆被格莱特推进炉子里烧成灰烬;《白雪公主》中恶毒的皇后被迫穿着烧红的铁鞋跳舞,直到死去;《绿野仙踪》中西方恶女巫被多萝西泼水后熔化而死;《女巫》中全英国的女巫喝了被变成老鼠的“我”放了变鼠药的汤,全都变成了老鼠而被消灭。
邪恶贪婪的本性、丑陋恐怖的外貌、难逃一死的结局构成最初“邪恶女巫”的原型。然而“邪恶女巫”形象的诞生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不无关系。基督教在欧洲的传入导致了社会的根本变化,带来了新的社会精神秩序。进入16—17世纪的欧洲,人们受到政治动乱和宗教改革的影响,面对各种危机人们急于找出当时社会混乱的原因,“女巫”与“魔鬼”联盟的传说以及她们不可揣测的神秘力量使之成为最好的替罪羊。从15世纪起,欧洲就开始了一段“猎巫狂潮”的黑暗运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5世纪出版的《女巫之槌》(TheMalleusMaleficarum)。《女巫之槌》是一本猎“巫”指南,从列述“女巫”的存在及其邪恶的本质,到阐释如何识别“女巫”、审判“女巫”。随着《女巫之槌》的出版,残酷的“女巫审判”开始了,人们通过各种毫无理由的方法认定无辜的女性具有“女巫”血统或参加过“巫魔会”,判定“女巫”与“魔鬼”有交易,让她们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在猎杀“女巫”的过程中,大多数被认定为“女巫”的女性往往会被处以各种刑罚:用针刺遍全身、严刑拷打后被绞死、被大量灌水、吊刑、火刑或剥夺睡眠等等。“欧洲猎巫狂潮的出现,源于宗教冲突、经济变迁、国家权力运作、阶级偏见与支配,以及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与厌女主义等。”[8]伴随着这场浩劫,邪恶而刻板的“女巫”形象被口口相传。这些形象不仅成为辨认“女巫”的标准,也成为文学创作题材。显然,童话中邪恶女巫的出现受到了15—17世纪猎杀“女巫”热潮的影响,这种热潮使得民间口述童话中的女巫形象增多,且童话中对女巫的惩罚也效仿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她们大多被残忍处死。
二、现代新风尚中的女巫像——“玛丽阿姨”
由于每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所差异,因而文学创作中的女巫形象也不尽相同。进入现代社会后,女巫的形象在儿童文学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不再是邪恶与恐怖的化身,而是趋向人性化,其形象和性格都趋向于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现代文学中女巫形象的人性特征逐渐突出。
在《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中,作者特拉芙斯利用日常巫术、魔法通过玛丽阿姨让我们直接进入幻想世界,小说虽然没有提及玛丽阿姨是否是一个女巫,但是从她身上发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仿佛都透露出一个讯息——玛丽阿姨拥有魔法!特拉芙斯将玛丽阿姨塑造成一个神秘、性情古怪、严肃刻板,对孩子经常爱理不理、缺少耐心的样子,以鼻子哼哼代替回答的保姆。她带着一把伞、一个手提包乘风而来,在日常生活中施展着魔法,例如在楼梯上从下往上滑;从空空如也的手提袋里掏出许多物件;“睡前一茶匙”的瓶子里能变出不同口味的液体;用指南针带着孩子们环游世界;将孩子们吃剩的姜饼上的星星用糨糊刷到天上;在生日的月圆之夜和动物园的动物们庆祝,而眼镜蛇竟是她的表哥!玛丽阿姨是多么的神奇!
传统童话中的大多数女巫形象都是年迈的、邪恶的,通常被称为“老巫婆”,尽管有些女巫还未到被称为婆婆的年纪,但她们仍被塑造成童话中主人公的上一代。如《白雪公主》中皇后的继母形象,她既是继母也是女巫。这样的人物设定在民间口述童话中屡见不鲜。女巫的年岁使得女巫和儿童之间产生距离感,这对儿童去想象女巫邪恶的本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特拉芙斯创造出了一个特别的女巫形象:女巫不再是年迈的老巫婆,而是年轻、时尚的小姐。玛丽·波平斯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女巫,拥有一份职业,就像生活中的每一个成人,随处可见。她并不十全十美,还略微有些古怪神秘,但是她不再像传统童话中所描述的那样可怕、邪恶。她拥有魔法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为了给孩子们带去欢乐,而不是作为伤害人类的工具。
此外,传统的女巫的出现都是作为某种困境的诱发因素来使童话中的主人公陷入险境,是童话中的配角,她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完成主人公的个人历险与成长,完成一个叙事功能。而在现代儿童文学作品中,女巫逐渐成为故事的主角,形象也日益丰满复杂起来。在《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中,玛丽阿姨这一女巫形象成了作品的中心人物,故事情节也围绕着她来展开,而其他的人物似乎被弱化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与先前的童话叙事特征有了很大的区别。特拉芙斯继承了英国19世纪童话女作家内斯比特的“日常魔法”的传统,通过塑造玛丽阿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女巫形象,将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地点瞬间变成魔法之地,把魔法变成儿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同时特拉芙斯本人也在作品中进行了解构,玛丽阿姨真的有魔法吗?在“月圆之夜”这一章的描述中,孩子们询问夜晚的动物园会发生什么时,被玛丽阿姨训了几句就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他们在半梦半醒间听见一种神秘的声音召唤着他们,并带领他们来到了动物园。在动物园里孩子们看到了种种颠倒、神奇的景象:一只黑熊负责看门,笼子里关的不是动物而是人类,动物则在园子里到处游荡。最后,所有的动物都到广场为玛丽阿姨举行生日狂欢活动,第二天早上,孩子们对这一切到底是梦还是真实的存在产生了怀疑,于是孩子们询问玛丽阿姨昨夜是否在动物园:
玛丽阿姨张大了嘴。“在动物园?我在动物园……夜里?我?一个规规矩矩安安静静的人……”
“可你在动物园?”简坚持着问。
“当然不在……亏你想得出!”玛丽阿姨说,“谢谢你们,把粥吃下去,别胡说八道了。”[9]133
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状态模糊了梦与现实、幻想与魔法的界限,给玛丽阿姨更添了些许神秘感。在作品中,玛丽阿姨除了拥有魔法外,更重要的本职工作是班克斯家的保姆。作为一个保姆,照顾和陪伴班克斯家的孩子们成了玛丽阿姨的基本职责,她和孩子们形影不离,为了方便照顾双胞胎婴儿,她把床架在约翰和巴巴拉的小床之间,在睡觉之前给孩子们讲故事,带孩子们去广场探望鸟太太。除此之外,她还用魔法给孩子们带来了无数的欢乐和意外的惊喜:她带着孩子们去拜访自己的叔叔贾透法先生,让他们体验在天花板上吃茶点的奇趣;她用神奇的指南针带着孩子们环游世界,说出不同的方位就到达不同的地方;她还带着孩子们去吃姜饼,让孩子们见识到了科里太太掰下指头变成的麦芽糖。但玛丽阿姨并非没有缺点,她时常表现出一副严厉冷酷的样子,忙碌时容易发脾气。此外,玛丽阿姨还特别在意自己的着装,每次路过橱窗时总要照上大半天,特别是在她穿上时髦漂亮的衣服时,她甚至会觉得“从未见过有人这么漂亮的”[9]136,以至于孩子们都不敢在橱窗前催促她。
玛丽阿姨这种新的女巫形象不论是外表还是心理都与人类更加相似,作者打破了女巫固有的刻板印象,打破了邪恶与善良的二元对立固有标准,表现出更多的平民性格和人性化趋势,人物形象刻画不再简单、平面。这种人性化趋势的出现与猎巫狂潮的消退、启蒙主义的兴起有关。随着17—18世纪启蒙时期人们推崇理性思潮的兴起,以理性驱散宗教愚昧和封建专制等思想的普及,女巫与巫术逐渐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隐入民间故事、童话等文学世界之中。19世纪以来,欧洲学界对女巫历史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在1862年出版的《女巫》一书中认为:“女巫的历史就是一部女性在性别、道德欺凌下的血泪史。”[10]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女巫迫害史,并对传统邪恶女巫的本质进行了解构与阐释。“女巫”,这个承载着偏见与黑暗的角色,在科学理性的时代得到了新的解放。
三、反传统中的颠覆性女巫像——“修行魔女”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倡导“打破一切,进行价值重估”[11],多元性、反元叙事、不确定性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儿童文学中的传统女巫形象也面临解构,这种解构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在后现代语境中,女巫形象表现出更多的内涵。她们不同于传统的邪恶女巫,也不同于现代新风尚中严厉古怪的玛丽阿姨,她们被注入年轻的血液,加入少女“纯真”的元素从而表现出活力、乐观、乐于助人的性格特征,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女巫形象中表现出人类的“自我”意识。
在《小巫婆真美丽》中,作者汤素兰塑造了一个天真可爱、调皮捣蛋的女巫形象。小巫婆真美丽是一个100岁的女巫,但是在女巫的世界里仍很年轻,因此她的行为、脾气和孩童非常相似。她生活在QQ镇的好玩街、农场、乡下。她跟普通的孩子一样通过学习掌握(魔法)知识;她会和好朋友向日葵因为矛盾大吵大闹;她在樱桃镇机智地战胜了拳王野兽;她天真善良地用巫术帮助想飞的小朋友们等等。[12]小巫婆真美丽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简单角色,她在修行中成长,从初到彩虹谷修行时自私地占有孔雀湖,到不由分说吃掉邻居丁黄瓜的鸭子,再到照顾残疾的小动物们以及帮助失忆的老巫师找回记忆……[13]真美丽在生活中从有点小任性小自私变得有了责任感,展现出了如普通人般在单纯本性之外的更加丰富化、复杂化性格。
如果说汤素兰的《小巫婆真美丽》塑造的是一个天真顽皮、乐于助人的小巫婆形象,表现的是女巫与日常生活的神奇碰撞,那么角野荣子的《魔女宅急便》则更多地将目光“向内转”,在关注日常的同时探寻女巫的内心世界。作家打破了传统魔女“丑、老、恶”的形象,保留了传统女巫形象中的基本元素,如黑裙子、黑猫、飞天扫帚等。故事讲述的是,身为魔女的琪琪必须在十三岁的月圆之夜离开家去寻找一个没有魔女的镇子独立生活,延续魔女一族的使命——告诉世人这世上仍存在着魔女,仍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与其说《魔女宅急便》是一部书写女巫的故事,不如说它是一部关于“寻找”的故事——寻找“什么是自我”、寻找“什么是魔女”。琪琪自诩为“新时代的魔女”,认为魔法失传不是因为世道变了的缘故,而是因为魔女自身变得规矩、谨慎了。“我可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4]12妈妈要求琪琪穿魔女的黑衣服,“我们是秉承古老传统的魔女,必须珍惜以前的东西。”[14]21而琪琪也是不情不愿的。在选择居住的镇子时,琪琪没有按照妈妈的建议选择小镇子,而是选择了自己心仪的、靠着大海的大城镇。即使是这样有主见的琪琪,在到达柯里柯镇时也十分无措。柯里柯镇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欢迎她,这让琪琪十分难过。她依靠会飞的能力帮人送东西,以此来留在柯里柯镇生活。为了满足客人各种稀奇古怪的要求,琪琪每天都在天上飞着,在拥有成就感的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大家以为魔女什么都能办到,而事实并非如此,魔法并没有让琪琪变得更加自信,而是让她产生了除了会飞之外没有别的长处的怀疑。在快递失重的河马时,医生说找到了重心就找到了自我,琪琪不禁在想,她的生命之灯究竟是什么?在快递黑色信件一章中,琪琪被误解为邪恶女巫,是带去诅咒的人。“以后说不定真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去诅咒之类的东西,而没送出美好的心意。”[14]66她开始怀疑开魔女宅急便的意义,甚至怀疑像这样当魔女究竟好不好。“是因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吗?……这种担忧让琪琪内心的寂寞感更强了。行了,魔女,你也别再飞了。”[15]126在和吉吉拌嘴时,吉吉说:“琪琪最近是怎么了?牢骚满腹,早晚变成一个普通女孩,不再是魔女了。”[15]132这种对魔女身份的迷茫无疑是对琪琪最大的打击,在自我怀疑的过程中,琪琪失去了飞行的能力。而后,在魔女修行中琪琪开始明白,原来魔女的力量不仅仅是魔女的血统,更是源于内心的力量。琪琪对魔法力量来源和意义的探索,是角野荣子对传统女巫形象大胆的解构,不同于传统女巫与生俱来的魔法,角野荣子作品中魔女的魔法有着捉摸不透的“性格”。魔法源于内心的力量,偶尔也会逃走,“利用魔法的威力来伤害别人或大自然,当行为过于粗暴时,魔法就会逃走。”[16]这就在本质上限制了魔女的性格特质——只能是善良、乐于助人的。
后现代儿童文学中的女巫开始了她们的全新生活,她们也像普通人一样有疑惑有激情,在寻找自我认同的同时也面临着情感的成长。在《魔女宅急便》中琪琪就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样,和蜻蜓恋爱、结婚、生子。在这一过程中,琪琪也逐渐认识到内心女性意识的萌发与成熟。在为咪咪匿名送一支钢笔给心上人艾君时,琪琪对情感有了朦胧的认识;在帮异地情侣密兹纳和纳西娜送礼物时,琪琪意识到“也许那时……某个人献给某个人的……某种特殊的感情吧”[15]134;在看到一起演木偶戏的演员妮妮和雅恩之后,琪琪产生了羡慕的想法:“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真好。”[17]108在琪琪懵懂的情感成长中,最直接的触发因素是另一位魔女克克的出现,克克自称拥有魔法,她积极进取,有野心,不循规蹈矩,因此在小镇大受欢迎,抢走了琪琪的风头。克克的出现带给了琪琪更大的危机,琪琪面对这种同性竞争的压力,陷入了沮丧和不安之中,她开始变得心浮气躁。为了能漂亮地出席演唱会,她不惜暂停魔女宅急便,花光自己的积蓄置办衣服和鞋子,甚至为了做头发而第一次开口向客人索取报酬,“几乎丧失了魔女的尊严和原则”[17]186。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琪琪才明白柯里柯镇对自己的意义,最终看清了自己对蜻蜓的心意。
不同于《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的第三人称视角和侧面描写,《魔女宅急便》中更多的是运用心理描写来表现小魔女内心修行的过程,更趋近于现实,展现出“人”的丰富内涵与价值:自我认同、性别意识、寻找理想与生活的意义等等,这些有关人类尊严与价值的议题都被角野荣子放置在了魔女琪琪的成长里。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女巫形象的塑造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人们对人类的存在与价值的肯定、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对人类生存意识的探索。这无疑是女巫形象在后现代主义时期表现的最突出的内涵。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创作倾向,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就是从“自我”立场出发,追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描写自我的迷失和价值的消解。在这种具有“叛逆”性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之中,儿童文学中的女巫形象也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她们从恶的一面转向善的一面,解构了传统的邪恶、黑暗的女巫世界,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构了一个善良、可爱、乐于助人的女巫形象。同时,这一生动的女巫形象也代表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
四、结语
“女巫”是儿童文学世界中最奇特的文学形象之一。从邪恶女巫到表现出“人”的特质的中性女巫再到注重内心修行、展现自我意识的修行女巫,女巫形象一直在发生变化,其所代表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所有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反映,但是无论身处在哪个创作时期,对女巫形象的塑造始终离不开人类的原型。不论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女巫形象,都或多或少具有某些人性特征。在女巫形象的嬗变过程中女巫形象的人性特征越来越突出,从简单的性格人化叙述到更深层次的精神肌理的探讨。在传统的童话故事中,作为反派出现的女巫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她们传达出某种人类自身的恶的一面,主人公通过杀死女巫从而达到克服恶的目的,其存在的价值是阐释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真理。进入现代社会,女巫形象善与恶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女巫形象开始出现人性特征,改变了妖魔化、丑恶化的可怖面目。随着现代社会中后现代因素的出现,人们更多地关注“自我”及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同时,随着反传统和反权威思想的出现,儿童文学中的女巫形象面临着颠覆和解构。创作者打破原有的固定模式,塑造出了新时代的善良、可爱的女巫形象,这些女巫形象以新的方式生活着,被感动、被理解和被爱着。与此同时女巫也面临着现代人的困惑与烦恼,她们通过人生的修行获得了心灵的成长,在不断怀疑中找寻到了“自我”,确认了自我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意义,这反映出人类不断扩大的“自我”意识以及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在女巫形象的嬗变中,人们对女性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妖魔化、丑恶化的老巫婆到融入现代时尚的玛丽阿姨再到少女化、年轻化的纯真魔女,女性从樊笼中解放出来,拥有了自我意识。她们不再是边缘化的角色,在某些作品中,女巫形象甚至开始担任主角。她们也被赋予了自主选择的权力,从被世俗“囚禁”在黑暗森林里的恶魔到拥有可以选择自己职业的玛丽阿姨(玛丽阿姨随风而来,风向改变之时又离开了),再到思考是否要成为魔女的琪琪,女巫们拥有了掌握自我命运的能力。这些现象的出现都反映了人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旧的价值观念不断被解构直至丧失,逐渐被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