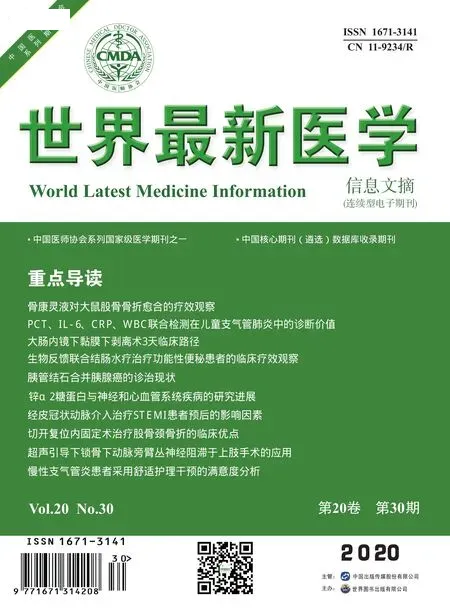药物性肝损伤的研究现状
刘佳,聂伟杰,孟存英
(延安大学,陕西 延安)
0 引言
药物诱发的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是指由各类处方或非处方的化学药物、生物制剂、传统中药(TCM)、天然药(NM)、保健品(HP)、膳食补充剂(DS) 及其代谢产物乃至辅料等所诱发的肝损伤[1]。根据发病机制,与药物有关的肝损伤通常分为两种:固有型(InDILI)和特异质型(IDILI)。InDILI 具有可预测性,与药物剂量密切相关,潜伏期短,个体差异不显著,目前较少见。IDILI 具有不可预测性,现临床上较为常见,个体差异显著,与药物剂量常无相关性,动物实验难以复制,临床表现多样化。InDILI 的主要可疑药物是对乙酰氨基酚(APAP)。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健康的志愿者中,谷丙转氨酶(ALT)的升高经常伴随重复的高治疗剂量而发生。DILI 的严重程度因患者而异,并取决于药物类型和患者自身因素。诊断需要详细的临床病史,以及肝功能,影像学检查和必要的肝活检。根据肝脏损伤的方式分为肝细胞损伤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一般而言,大多数患者可以完全康复,少部分患者会发展为ALF,可能需要进行肝移植,以及发展为慢性DILI。尽管全球研究提供了有关DILI流行病学的新数据,并对其发病机理有了更深入的解释,但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在DILI 预测,诊断和治疗领域。本文从DILI 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预后和管理等方面进行综述,从而对DILI 疾病有更深入的认识。
1 流行病学
在发达国家,DILI 发病率估计在1/100000-20/100000或更低[1]。我国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DILI 年发病率估计在23.8/100000,2012-2014 年DILI 的年发生率估计分别为21.37/100000、23.86/100000、26/100000,DILI 的年发病率从2012 年到2014 年逐渐增加。主要可疑药物为传统中药,草药和膳食补充剂以及抗结核药物[2]。
2 发病机制
肝脏是药物代谢和转运的主要器官,它主要在循环系统中清除药物(尤其是亲脂性药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药物被吸收到肝细胞,其代谢和清除受蛋白质大家族的控制,蛋白质的个体表达和功能受遗传和环境因素控制。药物相互作用和伴随疾病共同影响药物及其代谢产物的积累,并导致药物在肝脏中的压力促进作用。药物被动吸收或通过位于基底外侧质膜的一系列转运蛋白吸收到肝细胞中,这些转运蛋白包括溶质载体(SLC)家族,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OATP)超家族,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OAT)家族和有机阳离子转运蛋白(OCT)家族的成员[3]。肝细胞摄取后,药物通过I 期和II 期酶促反应代谢。在I 期反应后,代谢物通常与母体药物只有很小的结构差异,但药理作用却大不相同。II 期代谢涉及药物或代谢物与内源性分子(例如葡糖醛酸,硫酸盐或谷胱甘肽)的结合,产生极性更大的化合物,通常不具有药理活性。药物和代谢物从肝细胞流出到胆汁中或重新回到血液中,以供随后的肾脏排泄,这主要是由ATP 结合(ABC)转运蛋白介导的,例如多药抗性蛋白1(MDR1),也称为P-糖蛋白,由ABCB1 和阴离子交换机制编码[4]。
人肝细胞表达转运蛋白OATP1B1(由SLCO1B1 编码),OATP1B3(由SLCO1B3 编 码)和OATP2B1(由SLCO2B1编码)。他汀类药物是潜在的肝毒性底物,血浆他汀类药物水平在OATP1B1 抑制剂(如环孢素A 或吉非贝齐)存在下会增加。DILI 的一种可能机制是在I 和II 期反应过程中形成反应性代谢产物。实际上,反应性代谢物与细胞蛋白的共价结合可导致靶蛋白功能或位置的改变,或导致免疫原性半抗原的形成,从而触发免疫反应。DILI 的另一种可能机制是抑制胆汁盐输出泵(BSEP,由ABCB11 编码),这导致胆汁盐的细胞内浓度升高,从而可能破坏线粒体,导致细胞毒性和肝损伤。
DILI 中的肝细胞毒性被认为是细胞死亡、致死性坏死和凋亡的主要调控方式的结果。最终途径是通过增加内膜和外膜的渗透性而导致线粒体完全塌陷。DILI 发病机理中的另一个潜在因素是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其可能通过对DILI的敏感性或对先天免疫系统的影响来影响药物代谢产物的肝肠循环或药物代谢状态。
3 临床诊断
DILI 的临床表现是异质的。DILI 可以和各种病因的急性和慢性肝病相似,症状包括发烧,恶心,呕吐,黄疸,尿黄,瘙痒和右上腹痛。某些药物具有特征性的损伤类型(例如对乙酰氨基酚,胺碘酮,双氯芬酸和异烟肼导致肝细胞损伤型,卡托普利和红霉素导致胆汁淤积型),而其他药物(例如阿托伐他汀,阿洛普里诺醇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具有多种不同的损伤类型。此外,单一药物的不良反应在不同个体中的严重程度可能不同,从无症状的肝生化检查异常到急性和亚急性肝衰竭。
大多数DILI 发作均未显示免疫学特征。免疫介导的或超敏性药物反应的临床特征并不普遍存在,但可以在少部分患者中观察到,包括以下特征:发烧,皮疹,眼眶水肿,淋巴结肿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淋巴细胞增多或反应性淋巴细胞的存在和关节痛。
当前,DILI 的诊断仍属排他性诊断。首先要确认存在肝损伤,其次排除其他肝病,再通过因果关系评估来确定肝损伤与可疑药物的相关程度[5]。诊断DILI 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高度怀疑,因此医生应仔细查询有关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如对乙酰氨基酚)的接触情况,记录开始和结束日期以及发生DILI 的情况。草药和膳食补充剂通常被忽视,需要与潜伏期,药物治疗终止后的反应过程相结合以及解决时间有关的信息,以与可疑的病原体建立相容的时间关系。DILI 的发作时间差异很大,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相关的DILI),症状可能会在停药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但大多数患者在治疗前3 个月会经历DILI。
详细询问病史以排除酗酒,败血症和充血性心力衰竭,评估合并症及评估可能涉及肝脏的相关传染病。根据受损靶细胞的类型可为所需的其他调查提供指导。怀疑患有DILI的患者必须对个体进行病毒性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及戊型肝炎等肝脏相关传染病检测。肝细胞损伤型患者也应进行AIH 评估,包括评估抗核自身抗体和抗平滑肌自身抗体以及血清IgG 水平。然而,AIH 的典型实验室特征是包括呋喃妥因,米诺环素,抗TNF 和他汀类药物在内的几种药物的特征性特征,这使得DILI 的这种特殊表型与经典AIH的鉴别诊断成为一个挑战。当存在自身免疫特征时,肝活检(通常对于评估可疑DILI 的患者并不需要进行活检)是合理的,因为它可以提供重要的诊断线索。
肝活检可以用于评估可疑DILI 患者。活检结果也可具有预后价值。在前瞻性观察队列中对249 名DILI 患者进行的肝活检的系统评价中,发现较高的坏死程度,纤维化分期,微囊性脂肪变性和导管反应表明预后较差,而嗜酸性粒细胞和肉芽肿则更常见于DILI 较轻者。同样,对主要表现为胆汁淤积型的DILI 患者的病理评估表明,胆管丢失可预示消失的胆管综合症的发展,从而导致进行性胆汁淤积并导致肝衰竭,需要移植或死亡。连续进行氨基转移酶检测直至完全正常对于DILI 中的诊断保证也至关重要。氨基转移酶水平的持续下降为诊断提供了支持。
4 治疗
许多DILI 患者可以在不需要积极治疗的情况下自行改善。DILI 管理的关键步骤是及时识别和撤回可疑药物,及时将具有药物诱发性ALF 的患者转至医院进行治疗。延迟发现及立即停止异烟肼和其他抗结核药物是导致肝移植或死亡等不良结局的危险因素之一。有经验表明,轻-中度肝细胞损伤型和混合型DILI,炎症较重者可试用双环醇和甘草酸制剂[6];炎症较轻者可试用水飞蓟素[7]。胆汁淤积型DILI 可选用熊去氧胆酸(UDCA)[8]。上述药物的确切疗效有待严格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加以证实。胆甾醇胺(胆汁酸树脂)可用于由来氟米特(一种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和牛皮癣性关节炎的免疫调节剂)引起的急性肝损伤患者,以加速这种药物的清除。N- 乙酰半胱氨酸(NAC),一种对乙酰氨基酚毒性的解毒剂。胆汁淤积型DILI 严重瘙痒的患者可能会受益于抗组胺药(如苯海拉明或羟嗪)或胆汁酸树脂(如胆甾胺)的治疗。临床医生在胆汁淤积型DILI 严重的个体中尝试熊去氧胆酸是很常见的。DILI 患者进行肝移植没有严格标准,如果出现ALF、精神状态改变或肾功能不全就需要肝移植。对于患有肝细胞性DILI 的患者,黄疸的进行性恶化也应促使临床医生考虑肝移植。
5 预后
DILI 患者的预后与许多不同因素有关。以已故的海曼·齐默尔曼(Hyman Zimmerman)的名字命名的所谓的“Hy法则”仍广泛用于预测DILI 患者的结局[9]。Hy 的定律基于以下观察结果:异烟肼诱发的肝细胞性黄疸患者中,因肝衰竭或需要肝移植而导致的死亡率≥10%,许多其他药物的致死率达到10%,现在被FDA 用来预测药物的肝毒性风险。如果在临床试验中有多个患者符合Hy 定律标准,则涉及的药物不太可能上市,因为它可能会出现上市后的肝毒性问题。Hy 定律的有效性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证实。
其他生化、组织学和临床特征也可影响DILI 患者的预后。DILI 患者外周血和肝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的增多与双硫仑诱导的肝损伤患者及许多其他肝毒性药物所致肝损伤的良好预后有关[10,11]。大多数DILI 患者可以完全康复,只有少数患者会经历慢性DILI。老年,血脂异常和急性发作的严重程度是慢性DILI 的危险因素[12]。在经历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后,许多患者对药物产生恐惧和焦虑,包括对复发,再次接触药物,对其生育能力的影响或对其他药物产生药物不良反应的担忧。因此,在DILI 发作的急性期期间和之后,对每位患者进行生活质量检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