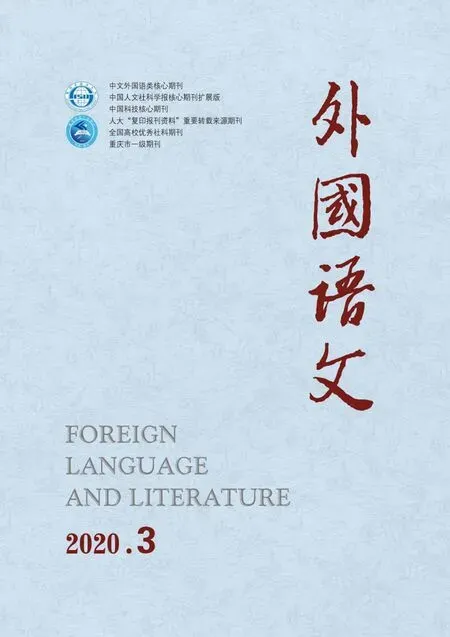关于死亡的寓言世界
——爱伦·坡小说世界探究
刘立辉 向瑶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0 引言
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因大胆鲜明的写作风格和独树一帜的美学思想而饱受攻讦,其中最具争议的便是死亡、灭亡主题的重复。据统计,单是直接提及“死亡”一词的,其诗歌中就有20余处,短篇故事中则“数以百计”,甚至其用词也是借助音响效果传递死亡气息(曹曼,2005:109)。为何他如此热衷于书写死亡,尤其是美人之死呢?在“创作的哲学”中,坡解释称:“美妇人之死无疑是最富有诗意的主题,而这主题如由丧失所爱的恋人道出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Poe,1998:1576)。莫内认为坡小说中的死亡主题是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反映(Monnet,2010:120)。琼斯则从酷儿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异性繁殖下的压力是恐怖氛围的根源(Jones,2018:166)。谭春丽尤为关注坡的“病态文学”,认为其中离群索居或疾病缠身的角色揭露了人类历来压抑的内在邪恶,反映了超离理性藩篱的破碎心态(Tan,2014:3-4)。从叙事层面来讲,坡实现恐怖效果的手段纷繁复杂。唐伟胜立足于“物叙事”,认为在《厄舍府的倒塌》中,“人”与“物”的关系被颠覆,恐怖效果也由此实现(2017:11)。付景川和苏加宁指出坡的侦探小说以空间为框架对社会矛盾加以隐喻,再现了工业社会下的身份焦虑(2016:32)。彭荻则认为小说效果得益于坡匠心独运的时间安排(2009:85),其观点又与刘易斯所说的偶然事件相呼应。以《黑猫》为例,刘易斯认为偶然事件是读者、叙述者和作者相遇、合作的产物,也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Lewis:2012:108)。
学界对坡小说的死亡主题及叙事手法的探讨对揭示审美化的死亡世界无疑具有重要价值。但是,为什么坡笔下的人物虽然身份各异,最终却都走向同一个终点——死亡?“死亡”外衣之下是否掩盖着坡更深层次的世界观?本文试图从寓言式批评的角度探讨爱伦·坡小说世界的宏观建构。剥掉表层话语和叙事外衣,可以看出坡小说的主人公扮演着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的角色,妄图理解、记录、预测甚至重建生死规则和自然秩序,但他们无一例外都走向灭亡。由此,本文认为坡小说中的死亡因素构成了一个精心营造的19世纪死亡寓言。这也是坡在面对如火如荼的废奴运动和来势汹汹的民主制度时发出的喟叹,是面对南方蓄奴制社会土崩瓦解时展露的绝望情绪。
1 寓言解读之合理性
寓言式批评由来已久。从古罗马时期斐洛的寓意解经,到本雅明的寓言式分析,以寓言的方式解读文本可谓源远流长。斐洛坚信,“对于经上所说的话,我们不可不经思考就轻率地接受它的字面意思……我们要仔细考察它从比喻意义上所传达的意思,字面后面的深刻含义,这样才能获得某种知识”(2017:76)。除了《圣经》,这一解读方法是否也适用于其他文本?答案因人而异。但不容否认的是,寓言式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弗莱曾指出,所有的评论都是寓言解释(Frye,1973:89)。同样的,华莱士也表示,“现如今将寓言式写作与其他诗学篇章相区分越发困难”(Wallace,1969:265)。而法兰克福学派代表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则更是为之正名。在《德国悲剧的诞生》中,本雅明系统阐释了自己的寓言概念。他认为,在悲悼剧(Trauerspiel)中,“自然—历史的寓言式面相以废墟的形式得以呈现,而在这种面具下,历史表现出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衰落”(Benjamin,1998:177-178)。面对残破的现实废墟,本雅明考察了巴洛克悲悼剧,认为寓于其中的死亡、尸体等是剧作家们对悲惨尘世的揭示。他指出,过去的比喻失去了令人震惊的可能,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于是过去的比喻对象本身无法再有任何意义,但这些对象的意义能够通过寓言家获得”(184),但寓言家赋予对象意义的行为只能通过忧郁的精神氛围得以实现。由此来看,忧郁氛围是本雅明寓言的核心,并能为已丧失意义的对象重新赋予意义。
那么,寓言式批评可否为解读坡的小说文本打开一道窗口呢?就坡本人而言,虽然他对寓言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但最终还是认可了这一写作方式。在寓言方面,法国作家富凯的《水中女妖温蒂妮》(Undine)对他影响颇深。坡不止一次评论这部小说,称它“毫无疑问是(以寓言解释真实意义的)最佳样品”(Pollin,1975:69)。他还曾指出:“最好的情况是,寓言必须与艺术家力图达到的统一效果交织存在……”(Poe,1984:583)。由此看来,虽然整体效果是坡写作的指导原则,但对他来说,寓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写作手段。盛宁曾评论“坡的小说……是一个读者无法直接认同的世界,若要认同,读者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跳出现实生活的世界,上升到隐喻或象征的层次上去认同”(1992:78)。同样,文斯利特也提到,坡“借助隐喻和神话将自己想传达的真实表达出来”(Vincelette,2008:40)。以忧郁心态赋予对象意义,从而揭示一个时代的寓言是本雅明寓言阐释的重要原则。从这个角度出发,坡的小说无不笼罩在一种“忧郁心态”之下,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反复出现的死亡/灭亡主题。在这种“忧郁”氛围中,坡构建了一个走向绝望的时代寓言。在坡的寓言体系中,一个个走向死亡的主人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试图从不同的立场、角度理解、记录、预测或重建自然和生死秩序,但到最后无一不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尝试都是无用功。
2 哲学尝试的失败
自诞生之际,人类认识世界的脚步就不曾停歇。哲学家们试图穷尽宇宙的真理,探究人类的本源。爱伦·坡的小说中不乏哲学家或哲学信徒。他们是坡借以探究世界、探索生死、认识生命本质的勇士。遗憾的是,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诸多此类短篇小说中,《莫蕾拉》当属代表之一。
历年来,学者们对这个故事的来源多有探讨。早在1937年,尼尔就已经指出,坡的故事与亨利·格拉斯福德·贝尔的故事《亡女》一脉相承。他在文章末尾比较了两个故事的异同,指出坡的故事更胜一筹。他也谈到了莫蕾拉这个角色具有的哲学意义,但并未深究(Neale,1937:238)。如前文所述,坡的故事需要寓言式解读。由此,我们不妨跳出诡异故事的框架,试着探究莫蕾拉这个角色本身所具有的寓言含义。
许多读者认为这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但在小说开头叙述者就已经表明,他对莫蕾拉的感情“与爱无关”(33)(1)本节所引《莫蕾拉》译文均出自鹤泉所译《爱伦·坡暗黑故事全集》,下文引用该篇时,皆以括号注明页码。。二人的结合只是命运使然,并非想象中的爱情,或许这并非一个爱情故事。从叙述者对莫蕾拉的描述来看,这位美丽女子太过神秘:她有“冰冷的手”“美妙的声音”“恐怖的语调”(33),“忧郁的眼神”(34)还“非常具有想象力”(34)。此外,叙述者还称他们是偶然相识,似乎莫蕾拉本人并无出处可循。这些特征足以令人怀疑这个女子存在的“真实性”,使她更像是一种象征而非具体的个人。
那么,莫蕾拉究竟象征着什么呢?我们不妨再探究一下她具有的特质。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神秘感之外,叙述者反复强调这位女郎聪慧过人并有卓绝的想象力。她指引着叙述者进行学术研究,在“我”迷失时,她会从“哲学的灰烬中随意捡出几个古怪的文字,激起我强烈的印象”(33)。除此以外,莫蕾拉还对包括毕达哥拉斯、费希特、谢林以及洛克等在内的众多哲学家颇感兴趣且哲学造诣颇深。至此,莫蕾拉本身业已成为坡笔下哲学的化身,而“我”则是在哲学道路上不断求索的信徒。此外,在谈到“我”对莫蕾拉的感情时,叙述者表示,从第一次见面,他心中就燃起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熊熊火焰”,但他“自己也说不清这火焰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办法控制这火焰的热度”(33)。从寓言角度来看,这种“火焰”不正是一个哲学信徒对真理和自然规律的执着与沉迷吗?如是,这种冲动也就更像是“我”沉迷哲学研究的情感体验。
“我”在莫蕾拉——也就是哲学思想——的陪伴下度过了一段奇妙的时光。但最终“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看着孱弱的莫蕾拉,“我”像是“俯视着深不见底的峡谷”,甚至“极其渴望莫蕾拉死掉”(34)。为什么叙述者如此急切地想摆脱哲学的掌控?或许莫蕾拉临终的话能提供一些暗示。千百年来,哲学亘古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永恒,哲学家们探讨着理智和生死。而在莫蕾拉消亡的那个夜晚,她说:“活下去,或者死掉。今天是大地之子与生命之子的日子,或者说是天堂之女与死亡之女的日子!”“我应该活下去,可我知道我就要死了。”(34)很明显,她意识到生死皆不由人,只由自然掌控,她有着求生的欲望,却无法改变自己终将死亡的结果。《莫蕾拉》中,叙述者实际上是借将死的莫蕾拉之口,道出自己探索的结果——死亡不可避免,一切最终都只能走向灭亡。正是因为窥见了这一真谛,“我”才感到无可奈何,才感到凝视着“莫蕾拉”就仿佛俯视着深渊。莫蕾拉死后,她的魂灵转化为叙述者的女儿继续存在,但在叙述者唤出“莫蕾拉”三字时,她便香消玉殒。其实这进一步深化了小说内涵,即:重生的莫蕾拉实际上意味着叙述者借助哲学探索世界的第二次尝试,而这次尝试的最终结果指向的还是已故的“莫蕾拉”,与第一次并无二致。当“我”喊出莫蕾拉的名字之时,也就是“我”清楚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刻,这时“我的大脑停止了一切活动”(35),四周只有无尽的痛苦和绝望。显然,在两次力图理解世界的哲学探索最终失败之后,“我”还是走向了灭亡。
3 科学实验的失败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曾在二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中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陆扬、王毅指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文化追根溯源,认为“启蒙哲学和科学的目标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祛魅化和去神话化,是用科学知识来代替偶然的心灵洞见”(陆扬 等, 2006:89)。启蒙哲学和科学带来的弊端究竟是否像二位所言此处暂且不表,但毋庸置疑的是,早在启蒙运动时期,理性和科学已经成为学者们的箴言。人们尝试用科学记录和解释一切现象,探索自然和生命。坡处于一个科学实验和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的时代,他本人也对科学有所涉猎,《瓶中手稿》反映了他对科学的兴趣。
1833年,这篇小说首次发布于《周六访客》,是坡为数不多的短篇海洋小说之一。它讲述了叙述者乘船遭遇风暴,莫名其妙来到一艘诡异古船,最后沉入无尽漩涡的惊险故事。梅勒加德和贝尔彻认为,坡海洋小说(包括《瓶中手稿》)的主人公纷纷走上疯癫和死亡之途,而彼时白人英雄主义和民族探险神话正大行其道,坡如此设定,正是反其道而行之,解构了单一的英雄探险模式(Møllegaard et al., 2013:414-415)。梅勒加德和贝尔彻显然也认识到了《瓶中手稿》主人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但正如本文提到的,对这些神秘怪诞小说的认识要跳出常理,求助于寓言解读。伊恩·瓦特曾在《小说的崛起》中指出,一个恰当、可信的名字是特定身份的语言表达,个人身份与恰当的角色命名有着紧密联系 (Watt,1957:14)。可以猜测,适当的角色名字有助于读者对故事情节和角色的理解与信任,增强故事真实性。但在《瓶中手稿》中,通篇没有任何一个被命名的角色。全文以第一人称叙述,其间并没有别的声音,即便是在叙述者做慷慨激昂的自我介绍时,也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其身份的确切信息。相反,其行文更像是在讲述一个童话故事,一个以“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固定句式开始的虚构故事。这就使得整个故事披上了“寓言”的外衣。那么,《瓶中手稿》的叙述者是否有另一个身份?这个故事又是一个什么寓言呢?
小说开头,无名的叙述者“我”就向读者作了自我介绍。“我”有着非比寻常的教育背景和“爱好思索的心灵”(5)(2)本节所引《瓶中手稿》译文皆出自孙法理译《爱伦·坡短篇小说选》,下文引用该篇时,皆以括号注明页码。,我“比谁都难以被迷信的幻觉所欺骗,也绝不会轻易偏离严格的真理领域”(5)。这些正是一位科学研究者的重要特质。另外,这位叙述者从扬帆出海开始,就展露出了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和强大的分析能力。他留意到“月亮的暗红形象”(6)、船尾“烛火没有一丝摇曳”(6)、比平时更加透亮的海水等普通人不易看到的细节;还预见热带风暴的到来……。此外,风暴之后这位叙述者对事态发展的准确记录更是展现了他所具有的“实验者”或“观察者”特质。即便是在绝境中,他也能细致地观察到太阳“带着病态的黄云从海面略升起几度,却发不出清晰的光……”(8)。类似的细节俯拾皆是。在措辞中,“我”更是使用了大量准确的数字以及表示方向的词汇,比如“十五英寻深”(6)“二十步远”(8)“四千吨”(9)“正南方”(12)“五英尺八英寸”(12)等等。数字和方向是最为客观真实的,它们使叙述者的记录有了科学报告的准确性。这种在困境中清晰认知周围环境的心理素质和能力更是说明这位叙述者并非常人。
离开受损的船只,误打误撞来到一艘神秘的古船上后,“我”的行为举止进一步表明了“我”的“实验者”身份。在船上观察了数日之后,叙述者曾明确表示,“一种无法描述也不容分析的感觉擭住了我的灵魂”;“我”还决定将自己的记录“不断写下去……一定要尽力设法(把它送回人间)”(10)。面对未知的境遇,他的第一反应并非恐惧,而是激动,是要将这新体验记录并传给世人。这一表现也与科学试验者沉迷探索的心态不谋而合。除此之外,这个故事还处处暗示着主人公“探索与发现”的使命。文章篇幅不长,但“observe”“observation”“apprehend”“meditation”等词汇则反复出现,“observe”更是出现了四次之多,而那艘古船的船身上也赫然雕刻着“DISCOVERY”一词(Poe,2008:179-189)。由此,我们不妨将《瓶中手稿》看作坡的一个科学实验——一个尝试记录自然和命运的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的结果如何?在坡的故事中,叙述者早已经陷入命运之轮,受其掌控而不自知。这一点在充斥全文的“莫名其妙”的情节发展中得到了证明。例如,在谈到自己出海的缘由时,叙述者坦诚:“引诱我的除了魔鬼般地纠缠我、令我难以安静的神经质的躁动之外,没有其他原因。”(6)另一方面,在遭遇海难之后,作为两个幸存者之一,叙述者说:“我说不清是什么奇迹使我逃脱了毁灭。”(7)同样“说不清、道不明”的状况比比皆是:他是如何落在神秘大船上;这艘幽灵一样的船又为何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风暴中化险为夷……他对上述现象的回答都模棱两可,一言以蔽之就是“不知为何”。仿佛一切在冥冥之中早已有了安排,事态发展远不受自己掌控,在尚未开始实验探究时,他就已经陷入了自己研究对象的陷阱。而在这个“科学实验”的最后,这位勇敢的探索者已经无暇顾及自己的命运,只能随着不停旋转的古船扎进漩涡的魔掌,渐渐下沉直至灭亡。从他这份“莫名其妙”的手稿中,我们也能窥见不可探测的命运安排和不可避免的灭亡。
4 艺术重建的失败
除了小说和诗歌外,坡的文学评论和美学理念引起的探讨也经久不衰。评论家普遍认为他有着强烈的唯美主义倾向,其暗黑故事中隐藏着他对真、善、美以及诗的见解。与康德、艾默生、科勒律治等将真善美视作三位一体的观念不同,坡认为诗(或者艺术创作)只与(美学)品味有关,与真理以及责任感(或道德)并无过多联系 (Poe,1984:78)。换言之,在坡眼中,真正的艺术创作是超越道德观念和常理的。也许这就是为何他的许多小说中都充斥着诸如乱伦、恋尸、恋物等情节的原因。这些主人公更像是超越世俗道德和现实世界的艺术创造者,在艺术世界中创建自己的秩序和理念。这些小说中,《红死病假面舞会》当属翘楚。
坡将这个故事的背景进行了架空,这就使它具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正如范德比尔特所言,《红死病假面舞会》是一个艺术家试图以想象力超越自然控制,借助非道德的艺术手段战胜死神的寓言(Vanderbilt,1968:382)。范德比尔特此言不假,但《红死病假面舞会》意图表达的似乎远不止于此。城中红死病肆虐,但作为一城之主的国王却没有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他对病情并不关心,“仍然欢天喜地,毫不畏惧”(277)(3)本节所引《红死病假面舞会》译文均出自孙法理译《爱伦·坡短篇小说选》,下文引用该篇时,皆以括号注明页码。,等到子民死了一半,他索性挑一千人一同隐居到一座大寺院中去。寺院内,国王安排了一切享乐所需的东西,人们安享太平,而高高的院墙外却是红死病猖獗。
这位国王的“口味很别致,眼睛对颜色和效果又特别敏感”“他的设想火热而大胆,他的计划总闪耀着野蛮的光辉”(279)。这种艺术家般的创造力在他行宫的独特设计上显得尤为明显。国王别出心裁,建造的行宫共有七个房间,其颜色由东到西分别为蓝、紫红、绿、橙黄、白、紫罗兰、黑。屋内没有灯光,只有房间外的走廊里透过彩色玻璃照着室内的火光。且屋子造得极不整齐,每隔二三十步就有一个拐角,无法一眼望到尽头。这样看来,比起他一城之主的身份,这位国王似乎在艺术鉴赏力和设计上更有造诣。他无视道德桎梏,转而投身于这样一个新秩序的创建。关于这七个房间的寓意,已经有不止一位评论家指出无论是从颜色还是从它们由东到西的设置方式,都象征着自然的轮回和人生命的有恒,七个房间也与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所说的人生的七个阶段有异曲同工之妙。(4)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指出,迄今已有不少评论家将此处不同颜色的七个房间与莎士比亚所说的人生由懵懂婴儿到耄耋之年的七个不同阶段对应。但正如他所言,坡在此处所展露的艺术追求却似乎没能引起注意。而这位国王设立行宫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他以艺术家身份创建艺术世界的尝试。
除七个房间以外,这场化装舞会也值得探讨。斐洛曾在《论〈创世记〉》中表示,上帝之所以朝人的脸上吹气,其原因在于:“脸部是感官的主要位置;‘脸’代表理智,理智作为神的代表对器官和感觉进行激励”(2015:74)。化装舞会上的男男女女都遮住了自己的脸,也就丧失了理智,失去了感官。在这样一种无理智的状态下,他们只受这座行宫的掌控,受国王安排下的音乐的支配。从国王关上高高的院门开始,他就已开始营造自己的梦幻世界,这些戴上面具、丧失理智与身份的舞伴与其说是他请来消遣的玩伴,不如说是他精心编制的梦。这位艺术家抛弃了传统道德的捆绑,避开“红死魔”,试图改变致命的自然因素,重新建构自然秩序和自己梦中的“伊甸园”。
那么他又是否得偿所愿呢?实际上,即便将红死魔挡在围墙之外,围墙之内也不是没有死亡的影子。小说对第七个房间里沉重巨大的乌木钟有细致描写。每当这个乌木时钟的长针在钟面走满一圈,大钟就会发出沉闷的巨响,穿透七个房间。每过一小时这个钟便会敲响一次,而听到钟声的众人则停下舞步和音乐,免不了一阵慌乱,甚至面如死灰。在国王创建的这个梦幻世界中,仍然有时间的流逝,规律的钟声提醒人们死亡的到来。这样看来,他的再创造注定是要走向失败的。在小说结尾,面目可憎的红死魔不急不慢地出现在行宫中。国王的门客们显然已经意识到来客是何方神圣,只有“天真”的国王还浑然不知死亡的到来。他大喊着:“是什么人胆敢搞这种亵渎神灵的打扮来侮辱我们?抓起来,撕掉他的面具,让我们看看天亮时要在雉堞上绞死的家伙是谁!”(281)刚刚还沉迷享乐的宾客此时已经清醒,他们四散开来,徒留国王一人惶然面对死亡。这位国王追逐着红死魔,从东边的蓝色房间一路到了西边的黑色房间,最后隐入无尽的黑暗和灭亡之中。突然出现的红死魔由东到西从蓝色房间走向黑色房间,实际上也就是死亡对生命每一个阶段的征服。即便国王高筑院墙,试图以艺术家的身份逃避致命的自然因素、重建生死秩序,但他还是追随着死亡的脚步走向了无尽的深渊。
5 结语
本雅明从寓言的角度考察巴洛克式的悲悼剧,指出不同于古典悲剧的英雄故事,这些悲悼剧意在展示世俗大众的悲惨境遇。剧作家借助废墟、死亡、尸体等灾难性意象暗示尘世的一切都是悲惨、破碎和绝望的。纵观坡的小说,类似的消极性意象俯拾皆是。它们共同构建了坡的寓言世界——一个最终只能走向死亡和绝境的世界。无论是哲学家认识世界的尝试,还是科学试验者记录、预测命运的探索,抑或是艺术家以非道德的手法试图重建自然秩序的野心都必将失败,在坡的世界里,等待他们的都只是无尽的灭亡深渊。随着南方蓄奴制度的土崩瓦解,民主制度的茁壮发展,素来拥护南方传统的爱伦·坡深受震撼。这些鲜血淋漓、绝望诡异的故事与其说是他奇绝想象力的体现,毋宁说是他精心营造的关于这个时代的死亡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