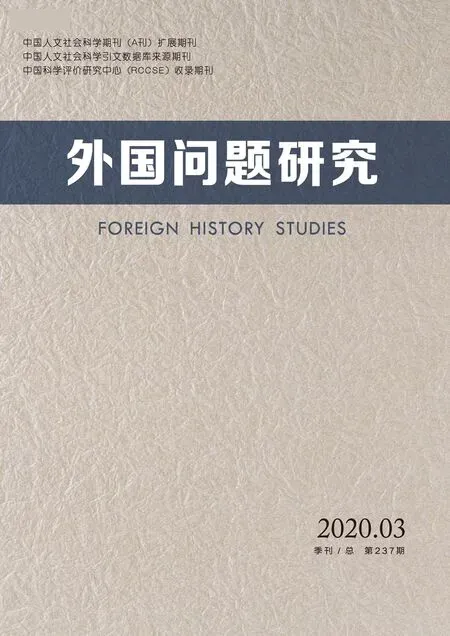他微笑着走向远方
——怀念朱寰先生
韩东育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8月8日凌晨1时许,朱寰先生悄然地离开了我们。凌晨,人一般已进入深度睡眠,可不知为什么,就在这个时间段,我竟然睁开了眼睛,在黑暗中环视不已,仿佛想寻找什么。当我习惯性地摸起静音状态的手机时,却突然被朱先生女儿从大洋彼岸发来的一条消息惊呆了:“东育兄,我爸爸刚刚在家里过世了……。”我脑子里轰的一下,人也整个儿地僵在那里,几乎不能动弹。等缓过神来后,才一跃而起,披了件单衣便径直朝先生家里奔去……。朱先生静静地安卧在床榻上,样子仿佛熟睡。我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双手合什,在戚戚然为老人家祈祷冥福的同时,也真实地见证了什么叫宁静和安详。
最初和先生相识,是当年他做系主任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双肩挑太过繁忙,七九级本科生的中世纪史课程,居然没能赶上朱老师的课堂。没上过朱老师的课却知道他讲课好,在我的记忆中,当缘于一次他对学校教务检查部门毫不留情的训诫:“课堂授课是一个老师德才素质的综合体现。一堂好的授课,是一件不可切割的艺术品。如果按照你们所设计的规定动作去分镜头打分,恐怕我们都不会讲课了。你们强调的教学法训练,很多是对中学的,可在东北师大历史系,除了极个别人外,你听说过我们的老师有不会讲课的吗?!”对这段仿佛是“为师之道”的宣言,恐怕直到今天,也并非所有的教务行政人员都能听得懂。
对大学教师而言,如果说教学是立身之本,那么科研就一定是强身之基。朱先生从来不相信一个没有经过良好学术训练且无力发表优异研究成果的人会讲出深入浅出的好课程。国内念过历史系的所有学生,几乎无人没读过他当年主编的《世界通史》(中古分册)和《世界史·古代编》(下卷)这两部书。它们与其说是大学教材,不如说是对朱先生经年研究成果的体系性展示。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历史研究近乎空白。正是因应新时代的新要求,朱寰先生率先与国内学界同仁一道,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欧洲中世纪史这一新学科和新领域。这些教科书直到今天还能被广泛使用,泰半归功于朱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为全球的华语文化圈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史学专业,并为它提供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不同的汉语史学语汇和思维框架。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教科书曾对我国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和教学有过一些束缚,这一点,史有定评,毋庸讳言。但是,一个不容低估更不可掩去的学术贡献在于,朱寰和其他中国第一代欧洲中世纪史研究和教学泰斗们(周一良、吴于廑、郭守田、马克垚等)的研究,不但为中国,还为全球史学界提供了一个审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和这一文明向现代化演变过程中不可取代的参照体。正是在与西方中世纪封建文化的比较中,我们才对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反思。这意味着,当前国内中世纪学界对欧洲封建化和封建社会多样性的讨论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评估和认识等学术发展态势,也正是包括朱寰教授在内的老一辈专家们最乐于见到的(参见刘文溪《朱寰全集》序言)。当回首朱先生七十多年的中西比较史研究历程时,人们无法不关注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其“显隐必该,洪纤靡失”的学术态度和钻研精神,外不输西方学界,内直追往圣先贤,且早已凝结成堪为后来者楷法的“为学之道”。
不跟朱先生接触,恐怕还很难体会到什么叫忠厚长者。学界同仁和受业师生,一提起朱寰教授,几乎没有不敛衽赞述的。那副正直的头脑,那张慈祥的面庞,那腔真诚的关爱,那双温厚的大手,以及讲话时那高亢洪亮的嗓音和爽朗天真的笑声,都时刻散发出让你难以抵御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光辉。早已置身于学术崇峻之巅且早已“一览众山小”的大学者,他反而极其尊重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他对谁气指颐使,只听到他不光对老前辈言必称先进,即使对晚生后学,也每每尊人为先生,交流称请益。半个多世纪的文明史比较研究,使朱先生最了解世界史学科特别是区域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盲点。当意识到不解决那些盲点问题便不足以奢谈真正的世界史时,他还善于以鼓励的眼光去发现人。他了解我的中国史出身背景,也了解我在东京大学研究过的一个中日比较课题。一天,朱先生很郑重地找我谈话,说以前搞日本史、朝韩史乃至越南史的中国学者,多数都在就一国史看一国史。可是,从历史的流脉讲,不懂中国的历史,其实是搞不了周边国历史的,至少是研究不透的。你能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向,以后去专门研究世界史中的区域国别史吗?如实讲,先生的话与我多年的心思一下子就产生了共鸣,而这一意义巨大的学术点拨,几乎还构成了我归国后二十余年乐此不疲的学术目标甚至成为东亚研究事业得以在国内起步和发展的第一触媒。不宁唯是,作为信仰笃实、站位高远且言行有法、语默中矩的大贤者,朱先生还时时处处去成就人。让学生们心生敬意的雅量和气度,常常体现在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也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威地位去排斥和否定那些尚未成熟的新学人和新尝试上。恰恰相反,他总是鼓励自己的研究生和学院的年轻教师不仅要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尝新,而且要走出去留学或游学,将海外的学术实情带回国内来。尤为重要的是,在历史系的发展过程中,朱先生身上的这些高贵品质,还体现在对学科建设这一被称作“学术共同体”或曰“学术大生命”的无比关心和全力以赴行动中。学者一般分两种:一种是自给自足或只完成自身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即告成功者;另一种则是在自身卓越的同时复能超越自我,去关心整个学科的发展建设事业。朱先生无疑属于后一种。在先生的带动下,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一直以强劲的态势领先国内学界——2000年,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世界史在原有的基础上被再度确认为国家重点学科;2003年,历史系被确定为国家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同年,国家人事部还在历史系设置了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1年,国家学科调整,世界史中国史再度获批为一级学科博士点;2015年,教育部政策教育立法研究机构国际教育法制研究中心在我校落成;2017年,我校东亚研究院被教育部遴选为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同年,世界史被教育部评选为三个国家一流学科之一;2019年,东亚研究院入选高等学校学科创新“111”引智基地;2017—2019年,学校世界史学科连续三年被上海软科评选为全国第一……。我不否认上述成绩的取得,有新生代教师的共同努力,但凝聚于朱先生“为人之道”人格下的团结向上精神和学术共同体氛围,显然曾发挥过更大和更根本的作用。在学科的繁荣具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力的意义上,朱寰教授已不单是东北师大历史系的先生,他同时还是全体从事历史研究者们的共同先生,以至于后学者纵然不能成为先生的亲炙弟子,也都希望能成为他的私淑弟子,比方像我;而朱先生在我个人的成长道路上曾给予过怎样的知遇和提携,恐怕也只有我自己才最为清楚。
今年2月27日,朱先生的夫人、著名明清史专家赵德贵老师仙逝。疫情流行期间,我和学校、学院相关部门的同志无法到医院送别,遂来到他们家中——南园4栋1门802室。去的路上,我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突然失去与自己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老伴,已95岁高龄的朱先生,该是如何悲痛,所承受的打击又是何等沉重!可当我含泪敲开房门时,却不由为眼前的场景惊愕了——只见朱先生笑容满面地伸出双手,用爽朗高亢的声音对我们说:“谢谢东育,谢谢学校的关怀!”言语间,只随口说一句“赵老师老了”,仿佛家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事……。直到朱先生也溘然长逝,我才仿佛明白了他老人家半年前的淡定和笑容里的深意:这一对儿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无私奉献给历史研究和教育事业的老先生,已真正做到了上不愧天、下不怍地和中不负人,惟此也才能真正地步入来去怡然、无碍无挂的神圣境界。我和朱先生住在一个小区。这些天,我总能想起每天早晨老两口相互搀扶、蹒跚而甜蜜地散步时的情景。如今,他们应该又挎起胳膊,如影随形般地依偎前行……。儿女们来信说:“我父母同年出生,同年过世”,而“今天,爸爸和妈妈又可以在一起了……”。朱先生几乎没有钱财留给子女。他的唯一遗产,是全国第一的世界史学科,还有临行前托付给我和学院的几柜藏书。他一生简单而高贵,平易而辉煌。我想,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离去的,他只是在平静地告别过往,在微笑着走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