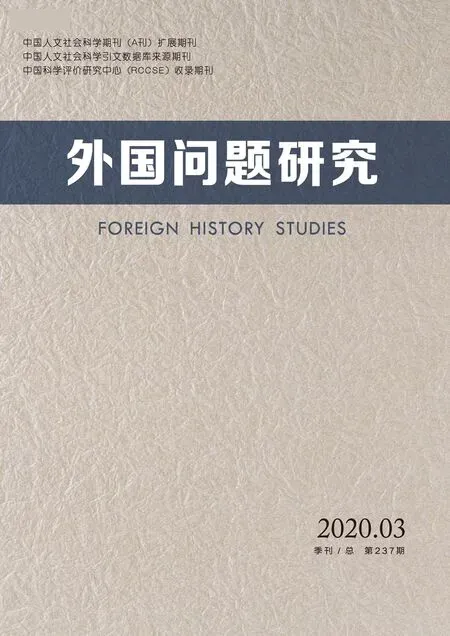中国台湾学界东亚史研究述评
吴红蕾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近年来,随着东亚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进展,中国台湾学界涌现出了一批关于东亚问题的新成果。这些成果的出现,反映出学者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理论认识不断深化,研究视野不断扩大。本文聚焦当前中国台湾学界知名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对相关领域的新成果和新观点加以介绍,以期对东亚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补益。
东亚视域下的传统学问与近代文明是中国台湾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以徐兴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历史人物为线索,对近代背景下的中日思想交流展开了深入研究。徐兴庆教授认为,至19世纪为止,中日韩三国都存在着传统的儒家文化要素,对东亚文明的发展也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西洋文明进入东亚世界之后,中日韩的传统文化都面临不得不转型的命运。外来思想涌入东亚之际,日本及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坚守自国传统学问的优越性,抑或是汲取西洋文明实学的两难之中。(1)徐兴庆:《东亚知识人对近代性的思考》,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在守旧及纳新的矛盾间,“自他认识”也随之形成。换言之,外来势力的压迫,促使中日知识人认识他者,并在与他者对峙的同时增进自我认知。同时,由于各国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地理条件及社会发展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中国、日本与朝鲜知识分子的“自他认识”亦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从近代中日知识分子思想交流的“自他认识”中,探讨中国对于他者(日本、西洋)以及日本对于他者(中国、西洋)相互认识的异同,论述日本、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思想、主张及其思想变迁,比较、分析传统儒教与近代西洋文明的冲突中这些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东亚史学界应关注的问题。(2)徐兴庆:《东亚文化交流与经典诠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
中国台湾学界着力研究的另一项课题是阳明学在日本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张崑将教授围绕该课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认为,阳明学之所以能够吸引日本武士,首先是由于德川政权并非独尊朱子学,又无科举制度,阳明学有发展空间。其次,幕府武家政权的特质是“以武立国”,阳明的军事成就及其个人魅力吸引了武士阶层。再次,武士有重实践而轻理论的思维倾向,喜欢阳明学的“简易直截”工夫,且良知学中蕴含着“事上磨练”的禅学精神,日本武士的“武士道”修养特别需要生死的体悟,良知学的基本态度恰与武士的精神需求相吻合。(3)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关键的是,日本阳明学并不仅仅是中国阳明学的翻版,日本儒者在接受阳明学时就对其进行了“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处理。所谓“去脉络化”是指维新前,阳明学被简化成一种“孝”思想,发生了宗教化、神道化的转向,成为革命的精神动力。“再脉络化”则是指维新后,良知学被井上哲次郎等学者转化为一种“国民道德论”,通过阳明学的宣扬来鼓励日本民众做“天皇的顺民”。阳明学原是发源于中国的哲学,但在日本则成为完全被过滤、被日本化而完成风土化的哲学。(4)张崑将:《阳明学在东亚:诠释、交流与行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阳明学在日本的转化,反映出日本超越普遍主义的“普遍主义”思维模式,日本在长期接受和沉淀中国和西洋思想之后,实际保存下来的还是日本特殊主义的思想。
关键历史人物对东亚地缘政治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郑成功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关于郑成功的研究以中国台湾学者张溪南的成果为代表,张溪南在其著作中对郑成功的生平及其后世评价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郑成功在世仅38年,却在东亚舞台上承担着多重角色。明朝灭亡后,郑成功坚持奉明正朔,延续南明王朝38年国祚,被清初士大夫视为虽“亡国”但不“亡天下”的“仁义之师”,成为“汉贼不两立”和“移孝作忠”的典型代表,并在近代中国充当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精神象征。在17世纪世界各国在东亚的海权争霸中,郑成功接收父亲郑芝龙势力,控制中国东南沿海海权,并通过与荷兰的战争转进台湾地区,张煌言、黄宗羲等人对此各有毁誉。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则强调郑成功母亲田川氏是日本人,日本平户是郑成功的出生地,将郑成功看作扬威海外,到中国帮助明朝抗清的日本民族英雄。日本占领台湾之后,试图转移台湾民众对郑成功的情感,将台湾的郑成功庙改为神社,将“中华心”转移为“大和魂”。张溪南的研究展示了郑成功形象在不同时代及不同语境下的变迁,其研究成果提示今天的学者,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评价历史人物,避免被后人的附会和歪曲所左右。(5)张溪南:《郑成功与荷兰在台湾台南的战争始末与评析》,《外国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
在总结20世纪东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台湾学界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出了新展望。以黄俊杰为代表的学者提出,21世纪必须重访东亚社会文化与思想。这是因为20 世纪亚洲各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之下,丧失对东亚文化的信心,20 世纪亚洲学者常采取“以西摄中”进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分析东亚文化之特色。研究者过度忽略文化或思想交流中的接受者实有其主体性,必经接受者主体性之筛选,外来文化才能被接受并融入。同时,20世纪东亚研究,在民族主义框架之下,成为“国族研究”。为了解决以上问题,21世纪必须展开新的东亚研究,以经典及其价值理念为研究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聚焦“脉络性转换”,开展跨文化的、跨界的、多音的、多元的东亚研究。21世纪东亚研究的具体策略一是要将焦点由结果转向过程;二是要兼顾东亚各地的“共性”与“殊性”,中日韩越各国儒学各有其建构与发展之过程,中国是东亚儒学的起源地,在21世纪必须经由跨域的视野,而重访“东亚儒学”并提炼新的“学术典范”。不能以东亚各地文化之“同”掩盖其“异”,要关注18 世纪以后日本、朝鲜、越南“主体性”之觉醒所造成的东亚各国文化与思想交流中的紧张性;(6)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三是从关键词切入分析思想交流中诠释典范之转移,可以就“东亚儒家传统”或“东亚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找出关键词,请学者撰写对关键词之研究论文,或择定东亚研究重大主题,邀请学者撰写论文,编为供研究者参考之资料书或工具书。总之,21世纪的东亚研究应着重“从东亚出发思考”,从“东亚经验”中提炼新理论,注意与“西方经验”之“不可共量性”,比较“东亚”与“西方”经验,尊重各自的内在价值。(7)黄俊杰:《思想史视野中的东亚》,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中国台湾学界的东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具体问题的分析和研究理论的探索方面都较之前有所发展。学者们普遍认为,今后的东亚研究应以“东亚”为视野,从“东亚”出发思考,以“经典”或“价值理念”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只有这样,才能开创东亚研究的新局面,进而对理解当下的国际局势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