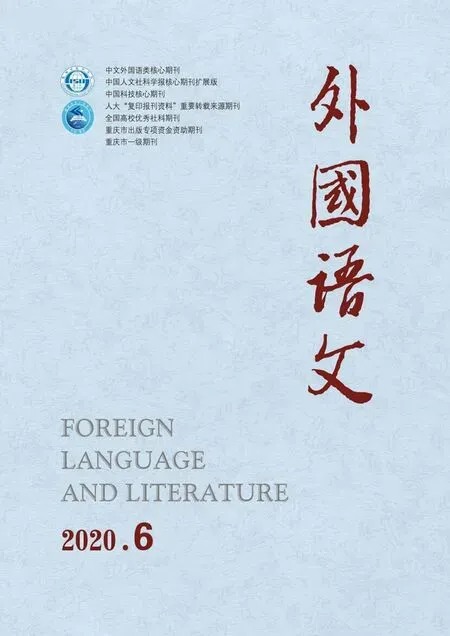嗅觉景观:托马斯·沃尔夫南方身份书写研究
张鲁宁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0 引言
托马斯·沃尔夫1900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山区小镇阿什维尔。他的父亲经营墓碑雕刻,母亲租售房屋维持生计,这成为沃尔夫多部小说的人物原型,沃尔夫因此被誉为“自传小说大师”。与福克纳、韦尔蒂不同,沃尔夫青年时代主要定居北方大都市。和南方疏离的经历让作家可以换一种角度看待他的南方地域身份,也让他对离开故地的南方人的失序感和疏离感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其创作灵感。此外,沃尔夫和斯坦贝克一样数次前往欧洲,旅行经历丰富。创作时间短暂的沃尔夫是南方文艺复兴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杰克·凯鲁亚克、菲利·普罗斯在创作中对于身份的追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沃尔夫的影响。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南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南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快速转型,南方文化传统在部分史学家看来已被美国主流文化所吞噬,南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化”(Egerton, 1974: xxi),但是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南方学者却认为20世纪上半期的“南方精神”依然是过去的延续,南方人民“共同的历史经历”塑造了南方的独特之处(Woodward, 1991:16)。在路易斯·鲁宾等南方学者看来,南方的独特之处不仅指的是一个地域空间,还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Newby, 1978: 3)。因此,南方社会特有的地域文化承载了整个南方社会群体意识,是南方社会传承数百年的民族烙印和精神家园。被独特地域文化滋养的南方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地区认同或地方意识。正如肖明翰所言,任何人“都是这一地区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产物。传统就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他思想的深层结构中, 决定着他的思维方式和对待生活、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 无时无刻不在对他起作用, 影响他的思想和言行”(1998:49)。
沃尔夫离开南方又回归的经历使其对南方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因此南方身份追寻与认同是贯穿他多部作品的重要母题。此外,作为现代主义代表作家,沃尔夫不但在创作手法上借鉴意识流等现代派小说技巧,在创作主题上也着眼南方社会转型期新旧冲突的现代性体验,在小说中表现南方性和现代性的复杂交织。沃尔夫深受艾略特、乔伊斯影响,在开启现代主体身份追寻的同时,塑造的南方人常常表现出离开南方故地的失序感和疏离感。和同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家相比,沃尔夫的跨国经历让他的创作更具国际视野,他对美国社会问题和文化变迁持更客观的态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使处于边缘的感官文化研究得以兴起。21世纪初伯格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与感官相关的研究专著,包括《听觉文化读本》(1993)、《触觉之书》(2005)、《味觉文化读本》(2005)、《嗅觉文化读本》(2006)、《视觉感官:文化读本》(2008)等。《嗅觉文化读本》收录了36篇与嗅觉文化相关的论文,展示了气味对于揭示性别、阶层、文化等身份认同的影响(Drobnick, 2006:1-2)。在论文《嗅觉景观》中,道格拉斯·波尔图首次提出“嗅觉景观”(smellscape)概念,并将其与声景、音景,水景等概念共同纳入“景观”研究,虽然气味常常稍纵即逝,但也“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和限制”(Porteous, 2006: 91),因此将嗅觉景观作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维度,可唤起情感、记忆与意义。
21世纪以来物质文化研究持续升温,文学作品中的嗅觉景观成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在《解读十八世纪小说中的气味》(ReadingSmellinEighteen-centuryLiterature)中,艾米莉·弗莱德曼(Friedman,2016: 3)重点关注了斯威夫特、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塞缪尔·理查德逊等18世纪英国小说家的气味书写,包括作品中的烟草、硫磺、闻瓶等嗅觉景观,为读者把握18世纪英国小说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嗅觉景观书写的政治文化内涵近年来被不断挖掘,评论界认为麦尔维尔、惠特曼、福克纳、托妮·莫里森等作家作品中的嗅觉书写和种族、性别、身份认同乃至创伤都有复杂的审美关联,正如芭贝特·巴波·蒂西莱德在研究伊迪丝·华顿作品时发现,嗅觉景观书写对于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现代主体身份有着重要意义(Tischleder, 2014: 119-121)。近10年来,受“情动转向”影响,有研究者倾向从物的色泽、味道等物理特征透视物如何产生情动力量,进而帮助塑造主体身份。德国文艺批评家丹妮拉·巴比伦(Babilon,2017:19)特别强调,物的味道对主体身份施加的力量可以被称为“情动力”。总之,无论是从嗅觉景观对文化的折射,还是嗅觉景观对主体身份的塑造,都表明嗅觉景观是考察作家作品体验世界的一个重要文化维度。
沃尔夫在作品中塑造了多位寻找现代个体身份的主人公,其独特的嗅觉书写几乎可以和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气味书写相媲美(1)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因患有哮喘而对气味尤为敏感。普鲁斯特对于气味的敏感成为20世纪初心理学研究对象,部分学者甚至以普鲁斯特为名构建了一些心理学概念,如“普鲁斯特时刻”(Proustian moment)和“普鲁斯特效应”(Proustian effect)。。嗅觉景观书写是理解整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支点,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本文从南方小镇的嗅觉景观、都市嗅觉景观、欧洲嗅觉景观三个层面入手,研究《网与石》中的嗅觉景观书写如何为小说绘制当时的物质文化图景;通过主人公在不同时期对于气味的回应及联想,透视作家对于当时历史语境中的南方身份的多重展示。
1 南方小镇的嗅觉景观与南方地域身份
沃尔夫创作了以尤金·甘特为主人公的系列自传小说。小说《网与石》的主人公命名为乔治·韦伯,但其传记色彩依然浓厚。小说中利比亚山的原型是沃尔夫生活的小镇。《天使望故乡》中甘特的父母和《网与石》中韦伯的父母的个性、习惯、甚至职业都和沃尔夫的父母高度相似。在《网与石》中,韦伯的父母婚姻破裂,韦伯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去世后,未成年的韦伯只能和舅舅姨妈们住一起。直到16岁那年,韦伯怀揣父亲的遗产开始大学生活。《网与石》第一部分描绘了韦伯12岁至上大学前一段故乡生活,和嗅觉景观相关的物质文化书写既揭示了韦伯孤独痛苦的青少年岁月,也反映了故乡对其心理、文化身份的建构。
父母的不幸婚姻和舅舅家的寄养生活让韦伯缺乏安全感。沃尔夫通过嗅觉景观书写呈现了青春期的韦伯在南方故乡寄人篱下的孤独与恐惧。舅舅家弥漫着冬天松枝燃烧后留下的“樟脑和松脂的味道”,韦伯并未感到温暖,相反,“曳动”的火光在他“斑驳的记忆中慢慢涌起一丝阴沉的恐惧,这种恐惧难以言表”(7)。舅舅家的气味让韦伯反感沮丧。不但“厨房里的蒸汽味道”“单调乏味”,而且整个房子周围都“弥漫着令人沮丧、毫无生气的绿色蔬菜的潮湿气息”,就连食物也令人郁闷乏味:“剩下的白菜、温热的饭菜、残羹冷炙”(22)。与对舅舅家气味的排斥相比,韦伯“喜欢记住父亲房间里所有物品的气味”,包括“壁炉架上方的苹果嚼烟块发出潮湿、清爽、刺鼻的气味,一端伸入其中,上方插着一面鲜红的旗子;还有陈旧壁炉架的气味,木钟、几本陈旧书籍的牛皮封面发出的气味;摇椅、小地毯、胡桃木梳妆台的气味和壁橱里的衣物的淡淡气味”(23)。虽然父亲的恶习常招致韦伯母亲及其家族的贬损,他不但积极为其辩护,心里还一直珍藏着关于父亲的美好记忆。
由此可见,《网与石》第一部分的嗅觉景观书写精选了具有生活气息的食物、建筑、家具等,揭示了韦伯南方故乡的家庭物质文化,通过两种不同嗅觉景观对比书写展现一副和父亲乃至原生家庭相关的充满亲情的画面。正如莫言所言,故乡绝不仅仅对应着地图上一个小小的版块和一个固定称谓,那里“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埋葬着你的祖先”,是你的“血地”(2004:366)。对韦伯而言,对父亲家庭的嗅觉记忆表明他和父亲血浓于水的亲情,赋予他安全感。因此,与父亲相关的嗅觉书写也可理解为韦伯潜意识中对生命主体意识的一种呼唤。
在《网与石》第一部分,沃尔夫通过混杂的嗅觉景观书写了小镇的物质文化和韦伯灵魂深处的南方体验。南方的一草一物都有着南方特有的气味,无论是街车及其发动机的气味,还是“木具、藤条椅、磨旧的铜器、闪亮的钢制轮缘的气味”,甚至包括较为隐蔽的药店附近林中空地的气味,“柠檬、酸橙、橘子等刺鼻的气味,还有某些不知名的药物发出的刺鼻气味”( 24),各种气味书写和日常生活书写夹杂在一起。韦伯“喜欢房门紧闭的旧屋子的气味,喜欢古旧的货物箱、沥青和房子旁边阴凉处的葡萄藤的气味”(24)。在沃尔夫笔下,人的参与赋予无生命的物情感意义。舅舅五金店的物在亲情衬托下不再冰冷无情,韦伯可闻见“钉子、榔头、锯子、切割工具、丁字尺,以及各种器具凉爽、干净的气味”;在马鞍店里“可以闻见皮革的气味”;父亲院子里砖木结构的气味更让他流连忘返,“那里我们可以闻见油灰、玻璃和干净的美国五针松的气味,还有骡队和木棚的气味”(24)。沃尔夫通过不同视角呈现小镇的物质文化和主人公的嗅觉体验,全方位地表现了南方的物对于韦伯南方地域身份的塑造。
沃尔夫用嗅觉景观书写最具特色的南方物质文化,传递韦伯对故乡味道的记忆与体验,塑造南方地域身份。首先是南方食物的味道。除晚上“从各家各户飘来的”晚饭的“清香”,更多时候是南方人因偏爱油炸、重口味而产生的食物味道,如“食物的气味浓重而特别,很符合冬季和那种诱人、令人饿意顿生的寒冷空气”;空气中飘来油炸牛排、鱼、油炸猪排的香味,还有肝脏、油炸鸡块的香味,最刺鼻最诱人的则是粗制汉堡和炸洋葱浓重的气味”(160)。其次是与典型的南方体育运动棒球赛相关的嗅觉书写。看台上的“气味、廉价的木制旧座位的气味、赛场绿草坪的气味、马皮制成的棒球气味、棒球手套的气味、清爽的灰色棒球棒的气味,还有穿着长袖衬衫的人与汗流浃背的运动员的气味”(24),七种气味的铺陈传递了南方印象。沃尔夫选择了南方食物、南方体育等最能代表南方地域性的物质文化书写,再现了韦伯南方生活的各个层面,它们成为南方地域身份的物化表达。
和很多美国作家一样,沃尔夫对于南方小镇的情感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家乡独特的味道赋予他空间存在感以及南方地域身份;另一方面,他通过气味相关的物质文化书写讽刺了城镇的落后和闭塞,揭示了小镇的各种阴暗面。
2 都市嗅觉景观与现代主体身份追寻
和福克纳、奥康纳等很少离开南方的作家相比,沃尔夫在1920年至1938去世之前,除了四次游历欧洲及短期返乡外,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度过。一方面,南方是他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印迹,另一方面,纽约生活使他熟谙都市文化。这种乡村与都市的二重性体现在小说以都市为背景的情节以及与都市味道相关的物质文化书写中。
对于美国文学中的都市书写,伯顿·派克(Pike,1981:10)认为文学中呈现都市的视角有三个范畴:一是从“上面”看,如《巴比特》中泽尼斯城体现了辛克莱·刘易斯站在城乡文化对比的高度批判城市的视角;二是从“街道水平”看,比如19世纪末的亨利·詹姆士因其上层阶级背景以从水平层面描绘都市上流社会;三是从 “下面”看,指作家在客观看待城市本质的同时保持适当距离,以一些南方作家对都市的书写最为典型,他们虽然身处城市,但常以外来者眼光打量城市。沃尔夫长居纽约,他对笔下的纽约常有一种从“街道水平”看的认同感;但作为南方人,他又时常流露出处于“下面”的疏离感;此外,作为作家,他的第三人称叙事不乏“从上面”俯瞰城市的批判性。这些复杂交织的视角成为沃尔夫现代都市书写的独特之处,也是理解《网与石》第二部分与纽约都市相关的嗅觉景观书写的一个重要线索。
和很多南方文艺复兴作家一样,沃尔夫通过描写南方人生活在北方城市的体验,开启寻找现代都市身份之旅。初到纽约的韦伯住在曼哈顿地下室,时常有种南方人在北方大都市的孤独感:“疾劲的秋风呼呼地吹着,令人心生悲凉的树叶摇曳着,空气中弥漫着寒霜和丰收的味道。”(219)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让他感到纽约生活几乎就是“地铁里的生活”,自己过着“污浊空气的生活,是充满灼热钢铁气味的生活”,处处笼罩着“疲倦和难闻气息”(216)。地下室的空间意象强化了他从“下面”看现代都市的疏离感。沃尔夫聚焦韦伯纽约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气味,一方面是“粗玉米粉、炸牛排、褐色的饼干、冒着热气的浓咖啡、融化的黄油气味”等典型南方美食,另一方面是北方都市地下室“刺鼻”的食物气味(225)。充满张力的嗅觉景观书写形象地刻画了韦伯初来纽约,因不适应而倍加思念南方的心理过渡状态。
逐渐适应都市生活后,韦伯开始独自租房投入创作。创作灵感受阻常常让他陷入很深的孤独,而青年特有的躁动更加剧了这种孤独感。恋情让韦伯的孤独感得以短暂缓解,恋人的味道令他着迷。他一方面受荷尔蒙刺激和引诱,“嗅着她身上刺鼻、令人愉快、在激情中湿润的气味”;另一方面,“向上看”的潜意识让他感到卑微,闻到的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散发出的气味”(272),抽的烟也是“那种芳香四溢、烤制的、无过滤嘴的‘好彩牌’香烟”(271)。他对异性的渴望在压抑的嗅觉中得到短暂释放,但他难以排解受“向上看”心理影响的内心孤独。和艾略特笔下的普鲁弗洛克一样,韦伯一直处于两种文明的断裂处,在现代都市中无法实现身份认同。
在从欧洲返回的船上韦伯遇到真爱,埃斯特夫人。首次相遇时他就被她身上独特的气息吸引,认为她是欲望最美丽和最崇高的体现。沃尔夫通过嗅觉景观书写了韦伯与埃斯特夫人共同生活时被爱情包围的愉悦感,“陈旧、用坏了的木板在阳光下发出的气味,春天温暖的街头传来的刺鼻柏油味,人行道上五彩绚烂、翻卷跃动的色彩和光点,市场的气味,水果的、鲜花的、蔬菜和肥沃土地的气味”(411)。小说在这一部分的嗅觉书写中没有强调上流社会女性和高档香烟的味道,相反,多次凸显了埃斯特烹饪食物的气味。韦伯“会时不时地走到厨房的门口……他站在那里把令人发狂的香气吸入肺中”;对于食物香气的描述表明韦伯在这段关系中找到了归属感,并从中得到满足。当看着爱人为自己准备饭菜,“再加上美味食物的浓烈香味,他的内心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柔情和欲望”(412)。与埃斯特的交往缓解了韦伯独处都市的孤独感,让他似乎“找到了城市的活力之源”(416)。
如果说在曼哈顿地下室韦伯是从地理景观上“向上看”这个城市,而他和埃斯特的交往则是从人际交往“向上看”纽约社会,注定了蜜月期后这段情感的失败。埃斯特交往的都是纽约上层社会的名流,虽然韦伯偶尔因为和埃斯特的关系感觉到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分子,但他时常感到“一个凄冷的阴影始终萦绕在心头”(434)。韦伯尤其认识到,他作为外地人的背景与这座大城市的宏伟和肮脏形成了鲜明对比,他难以融入上流社会,纽约的味道让他反感:“街上处处都是色彩艳丽、肮脏、令人不寒而栗的混合物,夹杂着那些令人舒适的材料散发出的浓重、清晰可辨的气味”(506),不但外面的河水气息“腐臭”(515),“房间里的一切都散发出污浊、模糊、发霉的气味”(523)。最终韦伯离开埃斯特远赴欧洲。来自南方的韦伯从灵魂深处难以认同这个城市,在他看来,这是一座基线“垂直”的北方之城(440),既美丽又野蛮。在韦伯眼里,抑或是沃尔夫本人的眼里,城市“是如此可爱、如此美妙地悸动着,充满了温情、激情和爱,同时也充满了恨”(440)。
3 欧洲嗅觉景观与南方主体身份重塑
20世纪20年代,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等现代主义作家旅居欧洲,成为20世纪上半期美国文化史上重要事件,被学界称为 “现代主义侨居”(Pizer, 1997: 138)。和这些移居巴黎的作家不同,沃尔夫四次往返欧洲和美国。因此,沃尔夫把自己的欧洲旅行与前者相区别,认为前者是“懒惰的逃避主义者,想要寻找一种可以逃避写作这一辛苦劳动的良方”(Brinkmeyer, 2009: 147)。他甚至把前者贬低为“低劣的伪文学,就像是裹着一层夸张印花T恤图案一样恶心”(Wolfe, 1968: 273)。可见,沃尔夫希望把其跨国旅行和海明威等人的迷惘、漂泊划清界限,标榜他的跨国旅行更具积极意义。不过在评论界看来,和“迷惘的一代”相比,沃尔夫的跨国移动也有着相似的逃避元素。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这一时期的作家都在跨国流动中释放出更多创作潜能,最终共同铸就现代主义文学辉煌,推动了美国文学的第二次复兴。
对沃尔夫而言,跨国旅行赋予他创作的国际视野,他笔下多位人物也拥有和他一样的跨国经历。旅欧不但让沃尔夫对自己的美国身份有着更清醒的认识,也让他换一种角度审视自己的南方地域身份。在《网与石》的第三部分,韦伯远赴欧洲,并在跨国旅行中得到心灵慰藉。无论是这一部分的欧洲嗅觉景观书写还是韦伯在欧洲不同城市的嗅觉感知,都构成了整部小说中主人公自我身份追寻的一个新阶段。
沃尔夫以韦伯先后到达的城市为线索,通过伦敦、巴黎、慕尼黑等城市的嗅觉景观书写呈现了每个“气味”独特的“伟大城市”的物质文化。与埃斯特情感将破裂时,韦伯出走欧洲,第一站是“由多种气味混杂而成”的伦敦。在沃尔夫笔下,伦敦嗅觉景观中最主要的是“四处弥漫的烟雾味”,同时混杂着“一丝麻木而刺鼻的烟煤味”;这些气味中还“掺杂着啤酒散发出的麦芽味”“淡淡的思乡茶香”以及“微甜的英国香烟味”。所有这些气味“和早晨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和烤香肠、烤鱼、烤肉的刺鼻烟味儿融合在一起,透过被浓雾遮住、却未完全挡住的金黄色太阳——这就是伦敦的气味”(606)。沃尔夫寥寥数笔对烟雾味道的特写,把伦敦“雾都”的面貌和特性进行前景化展示,也借助嗅觉景观书写勾勒出伦敦人的日常生活。第二站是“许多气味融合”的巴黎。与伦敦的烟味相比,巴黎的味道是“许多气味混合而成的怀旧气息,是腐败和精妙的融合”。就嗅觉体验而言,巴黎“最重要的气味是发霉、有些稍湿的锯木味”,而且“这是巴黎最确定的气味,是巴黎特有而其他城市没有的气味”。具体而言,“是一种从地铁通道出口散发出、穿过人行道护栏的气味……是一种凝滞的空气、耗尽且被污染了的氧气发出的气味。这是一种百万疲倦且没有洗澡的人们发出的气味”(606)。最令韦伯感到厌恶的是巴黎的香水味,“邪恶、极具诱惑的”的巴黎“弥漫着流动不畅、陈腐的香水味”,韦伯内心“涌起某种邪恶、不知满足的欲望”(600)。和沃尔夫一样,韦伯也对德国情有独钟。和其他城市相比,慕尼黑的“气味是最清新、最精妙、最令人难以忘怀、最令人激动,也是最难以定义的气味。它是一个几乎没有气味的气味,始终洋溢着阿尔卑斯山欢快、轻盈的活力”(607)。
远离美国赋予了韦伯国际化视野,让他更为理性、客观地反观母国及南方存在的问题。就嗅觉景观而言,欧洲也有着和美国一样令人难以忍受的味道,比如威尼斯运河充满“恶臭”的死水味道,法国马赛“充满危险而致病的气息,堆满了人类的垃圾和粪便,散发出南方特有的臭味、地中海古老港口的气味和鱼腥味”(607)。母国的味道对身处欧洲的韦伯而言,虽不乏“霉味”但变得不再令人厌倦,相反却勾起他对母国的回忆。他回想起波士顿街道上充斥着和伦敦一样的“咖啡的醇香和烟雾混杂的气味”;当西风吹来时,芝加哥充满了“诱人的烤肉味”;纽约则有种“发电机的气味,具有电的气味,具有酒窖里飘出的香味,具有古老砖砌建筑的气味,显得封闭、陈腐而湿冷,带着海港微妙、清新却有些发霉的气味”(607)。
在欧洲不同城市的嗅觉转换中,韦伯内心创伤得到疗愈。他因与埃斯特争吵而负气远赴欧洲,跨国旅行既是一种情感逃避也是经历情感创伤后的自我修复。在法国小镇经历的纯朴自然的嗅觉景观让韦伯心灵得到慰藉:“夜晚甜蜜的空气,夏日里大地醇美的气息,夹杂着树叶和花朵的芬芳,港湾海水的气息,大地和小镇那古老而熟悉的味道——街道的、房屋的、人行道的,还有店铺的味道,一并向他袭来,他陶醉在这种友好而通人性的气味之中。”(587)德国慕尼黑的嗅觉景观让他放松,无论是“烈性啤酒的气味”还是“友谊和温情的气味”都已经“融入了他们的大脑和心灵”(622)。最让韦伯在跨国流动中获得“主动的、积极的阈限性”(刘英, 2018: 103)的是德国阿尔卑斯山的味道:“他看不见它们,但从空气中已经嗅到了它们的气息。他嗅着那些山峰的气味,感受着阿尔卑斯山的力量所蕴藏的洁净、傲然的灵气。”(607)最终,韦伯在可以闻到“不新鲜的碘酒味”的一家德国医院里实现了对自己的真正接纳。“十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平静”的他“准备回家……和自己和平相处”。在与母国拉开距离后,韦伯得以敞开胸怀拥抱南方故乡的味道:“午间传来回家者的声音,大地勃发、青草吐翠,鼻孔里透出鲸油的清香”(644);“清晨敞开通风的房子,翻过来的床垫和破旧的地毯,旱金莲发出的温暖、常见的气味,对客厅的怀念和强烈、陈腐的味儿,街车过后留下的那份突然和沉默,那种希望中午再来的感受透出一丝的忧伤”(644)。欧洲游历使韦伯获得跨国身份和流动视角,对家乡嗅觉景观的认同暗示他找到自我,并在这种自我认同中回归了家乡的精神家园。
4 结语
沃尔夫在《网与石》里的嗅觉景观书写不但赋予叙事空间质感,也调动起读者的体验性感知,激发对虚化空间的想象和对文本主旨的深入解读。他在作品中塑造了多位追寻主体身份的现代南方人形象,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以生命本体意识追寻为主线,同时也植入了对南方地域身份、现代都市身份、美国民族身份等多重身份的追寻。
沃尔夫的南方地域身份是植根于他灵魂深处的创作源泉。他在小说中借助不同空间的嗅觉景观书写追踪了人物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情感认知。沃尔夫以人物成长轨迹为主线,呈现人物在从乡村到都市,再到国外的地理流动轨迹,进而探索人物对于南方身份、现代都市身份、美国民族身份的困惑与认同,丰富了现代主义文学中表现“个体现代意识”的审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