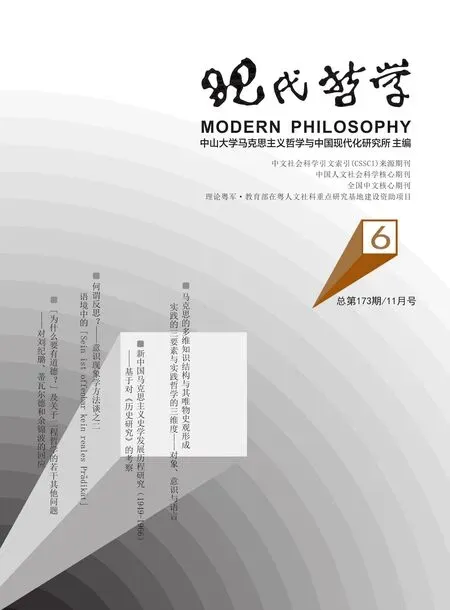语境中的“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
刘凤娟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在哲学史和研究史上都产生了重大效应。其核心立场表现在“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1)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8, S. 673(A598/B626).国内译本有邓晓芒的“‘是’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李秋零的“‘是’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王玖兴的“存在显然不是一个实在宾词”等。笔者将其译为“存在显然不是实在谓词”,同时行文中仍给出德语原文。第一批判的其他引文出自[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以下相关引文随文标明A、B版及该译本页码(如A571/B599, 349),原文强调部分改为黑体,不再一一详述。命题上(2)实际上,这也是国外学界的争论焦点。See Jill Vance Buroker,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9.,这是他“用以撬动整个思辨理性神学的支点”(3)李科政:《拨开“存在”谓词的迷雾——康德存在论题的第三种诠释》,《哲学动态》2020年第9期,第79页。。学界对该命题有多种诠释路径,笔者较关注的是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将其中的实在谓词理解为具有知觉内容的事物的规定性概念,以杨云飞、李科政等为代表(4)参见杨云飞:《康德对上帝存有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及其体系意义》,《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李科政:《康德的实存问题与本体论批判——反驳当代几种典型的质疑》,《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Stephen R. Palmquist, Kant’s Critical Religion: Volume Two of Kant’s System of Perspective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0, p.67.;第二种是将其中的“Sein”看作隶属于模态概念和“主观综合命题”的现实谓词,目前国内只有胡好持该论点,已引起学界普遍关注(5)胡好:《康德哲学中实在谓词难题的解决》,《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第68页。国外学界中,阿利森也涉及这种思路,指出“把‘存在’当作一个实在谓词,就是犯了一个范畴上的错误,把一个质的范畴(实在性)与一种模态范畴(存在或现实性)混为一谈”。(See 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16.);第三种是将这里的实在谓词理解为“上帝所包含的实在性”,以舒远招、彭志君为代表(6)舒远招:《实在谓词一定是综合命题的谓词吗?——就Sein论题中实在谓词的理解与胡好商榷》,《现代哲学》2020年第4期,第82页。另参见舒远招:《论康德Sein论题中的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从二项解读模式到三项解读模式》,《哲学动态》2020年第9期;彭志君:《被遮蔽的逻辑谓词——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现代哲学》2020年第5期;韦政希、苏德超:《康德论上帝证明与因果性问题》,《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赵林:《康德前批判时期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思想纠结》,《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陈艳波:《康德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的“存在”论题》,《现代哲学》2009年第4期,等等。。笔者认为,出现众说纷纭的原因在于,学者们对该命题的语境的理解并不统一。本文无意于重构康德的整个批判思路,而是专注于该命题,首先澄清它所处的语境,其次阐明具体语境中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的适用对象,最后揭示该命题在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该命题的两种语境的澄清
在笔者看来,“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的解读需要澄清两种语境:第一种在“先验的理想”一节中得到描述,即上帝被思考为其他一切事物的通盘规定性原理,而这种通盘规定意味着上帝对诸物的可能的谓词的规定;第二种是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在逻辑上的严格区分,即前者适用于分析命题,后者适用于综合命题(7)参见[德]康德:《逻辑学》,《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先验的理想”一节主要考察了上帝与具体存在物之间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在康德看来,如果人们要将一个谓词归于某物,不仅需要遵循一条基于矛盾律的原理,还要遵循一条通盘规定性的原理。前者是一种单纯逻辑原则,即“在每两个相互矛盾地对立着的谓词中只有一个可以归之于这概念”(A571/B599, 349)。这条原理不考虑知识的内容。但通盘规定性原理必须涉及知识内容。按照这一原理,某个谓词不仅应当与其对立的谓词相比较,而且应当在“诸物的一切可能的谓词”(A572/B600, 349)这个范围内,与其对立的谓词作比较。因此,通盘规定的原理就是“一切实存者都是被通盘规定了的”(A573/B601, 350)。为了诸物或诸实存者都能够得到通盘规定,理性就需要一个超越一切有条件者的存在者的概念,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的先验的理想。它具有一种实在性的大全(A577/B605, 352),而具有最整全实在性的原始存在者就是上帝。上帝作为一种先验的理想,就成为对一切有条件的存在者进行先验地通盘规定的理性理念。
上帝作为这种大全的和通盘规定的基底,隐含至大无外的系统整体性。上帝不像一个主体意义上的无条件者,也不像一个序列上的无条件者,后两者不提供一种系统整体概念,而上帝是“一个系统中选言综合的无条件者”(A323/B379, 211)。同时,诸物的一切可能性都只是“派生的”,“而唯一只有那个把一切实在性包含在自身之中的物之可能性才被看作是本源的”(A578/B606, 353)。这意味着上帝概念中的实在性是作为逻辑在先的先验根据来奠定派生者的实在性的基础的。
然而,上帝与有条件者之间的这种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虽涉及内容,却是“先验地,也就是按照在它们身上可以被先天思考的它们的内容来考虑的”(A574/B602, 350)。无论是上帝身上的那种整全的实在性,还是有条件者身上的派生的实在性,在这种语境中都只是先验观念中的实在性,而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实在性。在这里,派生的存在者的一切可能性都不是从经验中获得的,而是“从这个原始存在者中推导出来”(A579/B607, 353)的。并且,理性为了“只是设想对物的那种必然的通盘规定,并不会去预设这样一个符合这一理想的存在者的实存,而只会预设它的理念”(A578/B606, 352)。这就将上帝与有条件者之间的关系仅仅限定在纯粹理性内部。因此,“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一个现实的对象与其他事物的客观的关系,而是意味着理念对诸概念的关系”(A579/B607, 353)。这里的诸概念主要是指表达诸物的具体规定性或属性的谓词概念。诸物及其规定性作为杂多是被上帝先验地和通盘地规定了的,也是从其整全的实在性中推导出来的。
康德指出,“一切物的杂多不是基于对原始存在者本身的限制,而是基于对原始存在者的完备的后果的限制”(A579/B607, 353)。作为原始存在者的上帝是无限制的,而作为其完备后果的东西是“一切实在性的总和的表象”(A577/B605, 352)。有条件者的实在的规定性不是从原始存在者(上帝)直接派生的,而是从作为其后果的一切实在性的总和的表象中派生的。而对这种表象的限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否定,因为“这个实在性的某些部分被赋予了该物,但其他部分却被排除了”(A577/B605, 352)。即使这个实在性的总和中派生出去一部分,也不减损上帝的至大无外的整全性。这里的“限制”不是指上帝的整全的实在性本身被限制,而毋宁是有条件者被限制。同一个限制活动,对于上帝及其实在性来说是派生诸有条件者,而其自身并不损失任何东西,对于有条件者则意味着有限的规定性。所以,上帝通过一种关于实在性的大全的理念对一切有条件者进行通盘规定,它自身则是不被规定和限制的。这一点将在“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论题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论题的第二种语境是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区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这两种谓词的区分并未给予清晰界定。这种清晰界定出现在《逻辑学》中,康德指出:“综合命题在质料上增加知识,分析命题仅仅在形式上增加知识。前者包含着规定(determinationes),后者仅仅包含逻辑谓词。”(8)[德]康德:《逻辑学》,《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第109页。分析命题是那种谓词的概念包含在主词概念中的判断,所以逻辑谓词在一个分析命题中是能够包含在主词中或者能够从主词中分析出来的。在这样的判断中,并没有新的知识内容产生出来。虽然表面上和形式上逻辑谓词与主词是不同的概念,看起来增加了知识,但由于这种谓词的含义并未超出主词范畴,所以实质上是没有增加新知识的。这一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的第四节“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中有详细说明。
但“规定”意味着“从通盘规定的一个无条件的总体性中推导出那有条件的规定、即对受限制的东西的规定”(A578/B606, 352)。在笔者看来,综合命题所包含的规定就是受限制的东西的有限实在性,即通过对实在性的总和进行限制而得到的、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实在性。实在性的总和中的其他部分则被否定了,“一切真实的否定就只不过是限制”(A576/B604,351)。这种有限的实在性是通过上帝对有限存在者的规定得到的。这种规定表现在先天的内容上就是一种作为部分的实在性,表现在逻辑上就是有限存在者的实在谓词。
但《逻辑学》对两种谓词的区分只是一般而言的区分,仅仅在这种一般而言的区分语境中解释“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论题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和康德在“先验的理想”中所描述的那种通盘规定的语境相联系,才能对该论题有实质性的解决。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在上帝存在问题上的进一步细分,这种细分需要与上帝通盘规定原理的语境相对接。
二、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适用对象
这部分要讨论的是“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论题中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的适用对象,而不是一般而言这两种谓词的适用性。这个命题是专门就上帝存在问题而言的,并且必须在通盘规定原理和两种谓词相区分的双重语境下被理解。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逻辑谓词、实在谓词、系词的关系。康德在上帝存在命题中要强调的当然是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区别,但也涉及系词。系词“是”既可以出现在分析命题中,也可以出现在综合命题中;它既可以是对某物本身的肯定,也可以是对某物的规定性的肯定。笔者认为,关于上帝的一切判断都是分析命题;在这种分析命题中,对上帝或者其一切属性加以肯定的系词与描述上帝的一切属性的逻辑谓词是重合的。而在综合命题中,对某个有限存在者或者其属性加以肯定的系词与描述其属性的实在谓词是重合的,并都可以充实知觉内容。逻辑谓词仅仅在思维内部,而实在谓词除了在思维内部,还可以具有知觉内容。系词则是在分析命题或综合命题中对主谓词起联结作用的小词。它们的关系如下图:

因为关于上帝的一切命题都是分析命题,所以,“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东西用作逻辑的谓词。”(A598/B626, 362)。康德在《逻辑学》中指出,分析判断中主词与谓词的同一性,要么是一种表述性的同义反复,要么就是使包含在主词中的未展开的谓词得以展开。在上帝这样一种不受限制的存在者这里,从其主词概念中分析出来的任何谓词都同样地不受限制;它们之间毋宁就是同义反复的关系。人们可以用“全能的”述谓上帝这一主词,也可以用“全知的”“全善的”等概念来述谓它,甚至可以用存在(sein)或者它自身来述谓它。Gott ist命题中的“ist”不具有任何确切的实在性内容,它不是添加在上帝概念上的一个可增加其内容的东西;因为上帝本来已经是至大无外的,无需再添加什么。如果可以在上帝概念上添加新东西,就必须还有一个比当前这个至大无外的上帝更整全的上帝来使前者得到规定。这样,人们就不再能将这个至大无外的上帝看作是一切有限存在者的通盘规定的先验根据。存在(ist)作为系词,其逻辑功能仅仅是将上帝及其至大无外的实在性设定为我的概念。或者说,通过“上帝存在”这一命题,人们决不能断定思维之外一个客观实存的上帝,而只能断定思维内部一个作为先验理想的上帝概念。对于本来就具有上帝概念的理性存在者来说,“上帝存在”这一命题只是重复地使人确信了这一概念。甚至人们将存在(ist)看作是上帝的一种属性也未尝不可,因为意指其属性的一切概念都不具有确切内容。
因此,当人们说“上帝是全能的”这样的命题时,全能并不意味着一个与具体物体的重量、颜色等属性同级别的谓词概念。人们可以用重量等来描述物体,但不可以用“可思维的”来描述物体。物体的诸属性是在上帝的大全的实在性中被通盘规定的,通过这种规定,“可思维的”就被从物体的一切可能的属性或谓词中排除了。但“上帝是全能的”并不意味着“全能”之外的其他属性或谓词被排除了。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存在着的、全善的、全知的等可设想到的无穷尽的谓词赋予上帝,但绝不可能在所有这些谓词中找到一种确切的规定或限制。限制、规定、否定只能用在有限的存在者身上,不能用在上帝身上。
需要强调的是,一般而言,逻辑谓词并不仅仅适用于上帝。但笔者在这里要澄清的是“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论题中的逻辑谓词,而不是一般而言的逻辑谓词。该论题的逻辑谓词Sein适用于上帝,上帝也只能用逻辑谓词来描述。那么,该论题中的实在谓词的适用对象是什么呢?实在谓词意指一物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添加在物的概念上,而不是包含在其中。无论这种添加只是在纯粹思维中被先验地设想,还是在经验中被知觉到,都意味着有限存在者与其规定性之间的综合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康德的哲学框架内,人们可以设想两种先天综合判断,一种是先天概念与后天经验的综合,一种是在思维中的两种互不包含的概念的综合。例如,知性原理“每个变化都必须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人们在尚未获得经验内容的时候,也可以在单纯思维内部、在知性内部设想这样一个知性原理。经验内容可以先天地被知性所思考,也可以先天地在理性中被设想,即“先验地,也就是按照在它们身上可以被先天思考的它们的内容来考虑”(A574/B602, 350)。这实际上就是康德的先验逻辑的认识论的独特之处。人们可以先天地对经验对象有所认识,甚至可以先天地对经验对象进行通盘把握。在“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论题中的实在谓词,首先需要从这种被先天思考的内容角度来理解,而不是直接地将其理解为在经验中已经具有知觉内容的实在概念。
康德在“先验的理想”一节指出,“每一个概念对于在它本身中不包含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A571/B599, 349)。为了使某种不包含在其中的东西确定地添加在该概念上,人们除了遵循基于矛盾律的可确定性原理外,还需要遵循通盘规定原理。这里的“每一个概念”特指有限的存在者的概念,而不是上帝概念。上帝概念是规定有限存在者的一切谓词的根据,是原理本身,而不是原理规定下的具体对象。在“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论题中的实在谓词,适用于受上帝限制或规定的一切有限存在者。只有这种存在者,其规定性才是确定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上帝将其全部实在性中的一部分赋予某个有限存在者,该存在者的概念才被添加到作为实在谓词的规定性概念。有限存在者的实在谓词的确定性与上帝的逻辑谓词的随心所欲的特性,是该论题要揭示的最重要的一种对立关系。因此,该命题的真正含义是:在“Gott ist”中的Sein是适用于上帝的逻辑谓词,而不是适用于有限存在者的实在谓词;这两种谓词本来具有天壤之别,却被坚持本体论证明的哲学家们所混淆。
三、康德通过该命题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
康德通过“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比通过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对该证明的批判更加彻底。在笔者看来,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是指某物不仅被思考为实存着的,更在经验中被实际地知觉到(9)真正说来,一物的规定有三个层次:(1)在先验领域中并基于矛盾律的可确定性原理视角下被规定,(2)在可确定性原理基础上再通过通盘规定原理被规定,(3)在经验领域通过感性直观对该物及其属性进行精确规定。前两种规定在“先验的理想”一节有详细论述,它们都是对该物的先验的规定。但经过这两种规定并不能够形成命题或者判断,因为该物的属性究竟是什么,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还是不确定的,唯一确定的只是可能的规定性被归于该物的方式。所以,按照前两种原理,人们不能说某物是什么性质、什么样,只能说某物无论是什么样的,其可能的属性都是符合可确定性原理和通盘规定原理的。因此,例如“这朵花是红色的”这样的判断本身承载着三重规定:可确定性原理、通盘规定原理、经验中的精确规定。。在上帝存在的论题上,康德指出:“如果我想到了一个作为最高的(没有缺陷的)实在性的存在者,那么总是还留下‘它是否实存着’这个问题。”(A600/B628, 364)由于上帝仅仅是在思维中的一个存在者,不管通过什么谓词、多少谓词来思考它,都不可能使之超出思维而在客观世界中实存。所以,康德本来可以直接地说,上帝根本没有在经验中被知觉到,也就不能被看作是实存的。即便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特别是经验主义者)只要善于运用理性的批判,都有可能提出这种质疑:我从来没有经验过一个具有最高实在性的存在者,也就没有理由断言其实存。对于上帝实存与否的问题,哲学家采取更加思辨和复杂的理解方式。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的策略,不仅在于揭示“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中所要求的知觉内容,更在于区分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及其不同的适用对象。
不管人们在思维中设想的是“上帝存在”还是“上帝是全能的”,这些谓词都不能表明任何确切的实在内容,也就不是实在谓词。实在谓词首先是在上帝的通盘规定原理之下的某种有限存在者的属性的概念,其次才是需要在经验中充实知觉内容的概念。上帝与有限的存在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不能被知觉到、后者能够被知觉到,更在于述谓两者的谓词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种谓词甚至无需考虑经验内容,仅仅在先验的思考中就能够被区别开来。这符合于“先验的理想”一节在一种先验视域中所描述的,上帝与有限存在者的规定与被规定关系。实在谓词就是出于上帝对有限存在者的规定而成立的一种谓词概念。
康德对这两种谓词及其适用对象的区分,是对传统宗教哲学中相关思想的深化。哲学史上很多哲学家将上帝与其被创造者看作是有本质区别和规定关系的。例如,在阿奎那那里,“世界上一切个别的存在物都是偶然的和可能的,它就必须以某种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为其终极的根据”(10)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在笛卡尔那里,“绝对实体就是上帝”,“相对实体有两个,即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它们是“依靠上帝”(11)同上,第147页。而存在的事物。康德同样继承了这一点,并有所深化。这体现在,他将上帝的整全的实在性看作是其他事物的实在性的通盘规定的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有限存在者的规定性和上帝的整全的实在性,以及适用于两者的不同谓词。
适用于上帝的逻辑谓词与适用于有限存在者的实在谓词之间的区分,在其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工作中的意义就在于:“上帝存在”与诸如“苏格拉底存在”仅仅在先验的理解中就有本质区别。苏格拉底的存在是具体的,是有确切内容的,是上帝在其全部实在性中限制出一部分而赋予苏格拉底的。但上帝的存在不是具体的,也不具有确切内容,更不是在上帝的全部实在性中占据某一部分的那种概念。即便人们用相同的一个概念being(sein)来述谓上帝和具体存在物,所得到的判断或命题也有本质区别。这种区别甚至不需要考虑上帝或苏格拉底是否在经验中被知觉到就能成立。
康德通过区分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而批判本体论证明的举措,可以被看作是他在传统宗教思想视域中展开的彻底驳斥。阿奎那等神学家从上帝与有限存在者的等级性关系中证明上帝的客观实存,康德则在同样的基础上否证上帝的客观实存,推翻了“有条件者存在,其条件就必定存在”这样的独断教条。这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更是一种釜底抽薪的颠覆。他要指出的是:有条件者客观实存,其条件不一定客观实存,而可能仅仅是思维中一种纯粹理念。康德的先验逻辑思维方式使其将上帝(无条件者)与有条件者之间的规定和被规定关系纳入思维内部来考察。笔者认为,正是在这一点,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才具有深远意义。
与此相应,康德在这种批判中也表现了另一种深刻的思想变革。阿奎那、笛卡尔等人的本体论证明实际上有一个隐秘的前提,即内部思维与外部存在的统一性甚至同一性原则。这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经常被很多哲学家隐秘地预设为思想前提,并不加批判地加以运用。例如,在笛卡尔看来,“单从我存在和我心里有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也就是说上帝)的观念这个事实,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12)[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页。。这是因为凡是人们能够清楚明白地领会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上帝的观念在他看来就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笛卡尔将上帝的观念作为一种结果,而将思维之外客观实存着的上帝当作是一种原因。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统一性暗含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在笛卡尔这里,像上帝这样的清楚明白的观念“不是纯粹由我的精神产生出来”(13)同上,第56页。,而是必须有思维之外的客观根据。但在康德看来,上帝就是一个理性理念,人类理性自身就可以产生这样的理念。相对于笛卡尔在思维和外部存在之间寻求统一性的理解,康德“在思维内部重新建立了思维对存在的直接性”(14)刘凤娟:《笛卡尔循环与康德的解决——以逻各斯精神为研究视角》,《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100页。。
康德打破了古希腊以来思维和存在的外在统一性原则,将这种统一性内化到主体之中。这种思想变革在当前论题中的意义在于,上帝可以仅仅作为一种纯粹观念上的规定根据。而人们在思维内部对一个纯粹观念的任何述谓,都不可能推出它在思维之外的客观实存。上帝只是被悬拟地、调节性地设想为一切有限存在者的根据,与那种不仅存在于思维中也能在经验中被知觉到的具体存在物有本质区别。在后者那里,人们用以描述诸物的谓词是实在谓词。实在谓词的“实在”,一方面指由上帝的整全的实在性所通盘规定了的具体的和部分的实在性,另一方面意味着在经验中具有实在的知觉内容。上帝与具体事物的这种规定和被规定的关系,以及适用于它们的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区分,在单纯思维领域就是清楚明白的。康德将上帝仅仅纳入思维之中,也就取消了其思维之外客观实存的确证的可能性。本体论证明的根本错误在于,将述谓上帝的概念(如存在)看作是与述谓有限存在者的概念同类的、同级别的。这种混淆实际上是取消了上帝与有限存在者的本质区别,将上帝看作是像后者那样既作为思维中的观念又在客观世界实存。
四、总 结
本文最终的结论是,“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ädikat”这一命题必须在上帝与具体事物的规定和被规定关系的语境,以及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相区分的语境中被考察。基于这两种语境的结合,该命题意指:“上帝存在”中的“存在”只是逻辑谓词,不是实在谓词;只有被上帝规定的具体的和有条件的存在者才具有实在谓词。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上帝只是思维中的一个概念,述谓这一概念的任何谓词都不表达具体的实在性,而是表达上帝概念中的最高的、整全的实在性;但这样的谓词恰恰是与上帝概念同义反复的逻辑谓词。与此相反,被上帝所规定的有条件者可以既在思维中被思考又在经验中被真实地知觉到,用以述谓这种事物的谓词表达的是其具体的和确切的实在性,因而是实在谓词。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上帝与有条件者的规定和被规定关系可以在思维中先验地被设想,即有条件者的实在性是上帝的整全的实在性的一部分,并可以在其中得到通盘规定。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