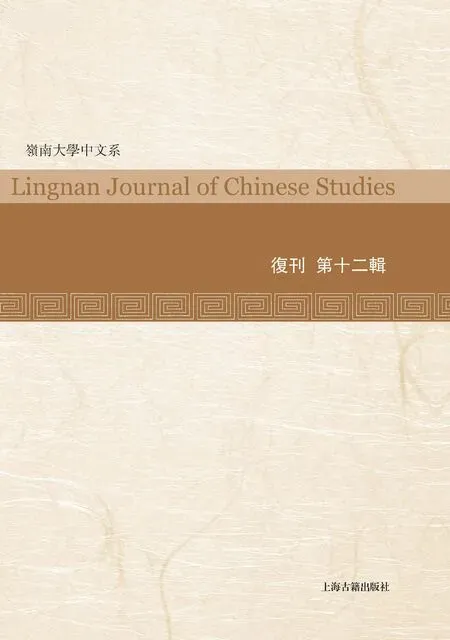李兆洛對駢文的重構*
吕雙偉
駢文是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文章體類,它追求句式駢偶,但長期以來有實無名。正如民初王文濡所指出:“駢文乃相比相並之文也,其名雖定於後,其義已見於前。”①王承志:《駢體文作法》,載於余祖坤《歷代文話續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頁。先秦經子著述中,駢語已經較多。秦漢時,文章更趨於排偶,藻飾色彩更濃。東漢、魏晉,駢體初步形成。齊梁時,對偶趨於工整且喜用隔對,隸事豐富,講究聲律和辭藻,駢文趨於鼎盛。駱鴻凱先生以《文選》中所選李斯、鄒陽、王褒、曹植、陸機、顔延之、王融、沈約的作品為例,從裁對、隸事、色采、聲律等的演變出發,説明駢文文體形成的過程性:“駢文之成,先之以調整句度,是曰裁對。繼之以鋪張典故,是曰隸事。進之以煊染色澤,是曰敷藻。終之以協諧音律,是曰調聲。持此四者,可以考跡斯體演進之序,右舉《文選》諸篇,乃絶佳之佐證矣。”①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209頁。這四個特徵確實是齊、梁、陳、隋時代駢文的主要特徵,也是唐、宋、元、明“四六”的主要特徵,因而成為駢文體裁獨立的標誌性屬性,也成為民初以來學人研究駢文的重要參考。然而,從體裁的角度來説,作為文集的“駢文”、“駢體文”直到清代纔出現。清代駢文復興,超宋邁唐,民初王文濡甚至説:“要之清之文學,突過前朝,而駢文之集其大成,自可陋六朝而卑唐宋,非所謂一變至道者耶?”②王承志《駢體文作法》,載於余祖坤:《歷代文話續編》,第1179—1180頁。清初陳維崧、吴兆騫、吴綺、章藻功、陸圻等江南文人的駢文,屬於駢文成熟後的齊梁、初唐風格。他們的駢文形式工整,四六隔對特徵明顯,有意追求裁對、隸事、敷藻和聲律等。但在嘉道以來駢散不分的文章思潮影響下,清人通過理論與創作對前代“四六”及清初“儷體文”概念進行了重構。在這一過程中,常州駢文群體,如邵齊燾、洪亮吉、孫星衍、李兆洛對駢文重構所起的作用最大。曹虹先生對李兆洛的《駢體文鈔》及其融通駢散有深入研究③曹虹:《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96—115頁;曹虹、陳曙雯、倪惠穎:《清代常州駢文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303頁。,這裏擬從李兆洛對駢文的建構與解構加以探究。
一、李兆洛對“齊梁體”駢文的排斥
面對前代豐富的文學遺產,清人多以摹擬為創新,在詩、詞、駢文、古文等傳統文體上都強調學習前代,在批評中也多以前代風貌為依據。對於“駢體文”、“駢文”,他們也作了全面深入思考,遠超唐、宋、元、明“四六”批評。康雍乾時的李紱(1675—1750)就從聲律、對偶、句式等方面,較早將前代駢文分為“六朝體”、“唐人體”、“宋人體”三類:“四六駢體,其派别有三種:平仄不必盡合,屬對不必盡工,貌拙而氣古者,六朝體也;音韻無不合,對仗無不工,句不過七字,偶不過二句者,唐人體也;參以虚字,衍以長句,蕭散而流轉者,宋人體也。”①李紱:《秋山論文》,載於王水照:《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2—4003頁。清初的詩文作者,大部分屬於明代遺民。易代之悲、興亡之感鬱結於心,加上晚明四六興盛培育了一批駢體作家等,康熙年間駢文復興。陳維崧、吴綺、章藻功、陸圻等江南文人模仿徐庾、初唐四傑而創作了大量駢文,這些駢文情感豐富真摯,句式整齊,特别是四六隔對使用頻繁,風格哀感頑豔,屬於成熟的齊梁、初唐體駢文②吕雙偉:《陳維崧駢文經典地位的形成與消解》,載於《文學遺產》(2018年第1期),第156—168頁。。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李紱没有對“六朝體”加以細分,其實前期魏晉與後期齊梁風格迥異,前期符合其所講的平仄、屬對特徵,後期則不一致。但這種駢文三分思想,反映了清初至乾隆時期的駢壇主流觀念。直到嘉道以後重視漢魏體駢文,這一觀念纔有所改變。
相對於清人多籠統地將六朝駢文視為一體,推崇齊梁文風,李兆洛較早認識到先秦兩漢、魏晉、齊梁文風的不同,明確推崇漢魏,排斥齊梁,以實現駢文的尊體。其《答湯子垕》曰:
曩與彦文(方履籛)論駢體,以為齊梁綺麗,都非正聲,末學競趨,由纖入俗,縱或類鳧,終遠大雅,施之製作,益乖其方,文章之家,遂相詬病。竊謂導源《國語》及先秦諸子,而歸之張(衡)、蔡(邕)、二陸(機、雲),輔之以子建(曹植)、蔚宗(范曄),庶幾風骨高嚴,文質相附。要之,此事雅有實詣,非可貌襲。學不博則不足以綜蕃變之理,詞不備則不足以達藴結之情,思不極則不足以振風雲之氣。閣下近作,涉興無淺,言情必遥,已足祧六朝,追魏晉矣。深之以學,則士衡、子建,何必遠人?③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八,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27頁。
他認為齊梁駢文綺靡華麗,藻飾過度,不是“正聲”。不善學者,爭相模仿,導致為文纖細俚俗,即使類似齊梁,也終究遠離大雅,因而遭到文章家的指責或嘲駡。為了使駢文由俗入雅,由纖入正,李兆洛強調駢文創作應該以《國語》及先秦諸子為淵源,以張衡、蔡邕、陸機、陸雲為指歸,以曹植、范曄為輔助,即以這種駢散不分、駢散合一的“漢魏體”駢文為“正聲”,纔有可能達到“風骨高嚴,文質相附”的境界。同時,駢文創作不能貌襲,浮在表面,應該要落到實處。這種實處,主要包含博學以綜理、遣詞以達情和深思以振氣,這樣纔能擺脱纖俗品格。他還以方履籛駢文為例,指出其善於興寄,言情遥深,成就可以承繼六朝,追攀魏晉。在這裏,“魏晉”駢體地位明顯高於“六朝”。在《跋方彦聞隸書》中,李兆洛也借方履籛駢文宗尚的轉變表達了對“齊梁體”、“初唐體”的不滿,有曰:“其為駢體也,初愛北江洪先生,效齊梁之體,綺雋相逮矣。已而曰:‘此不足以盡筆勢。’則改為初唐人,規格雄肆,亦復逮之。自以為未成也。”①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七,載於《續修四庫全書全書》第1495册,第111頁。“自以為未成”雖是方履籛的看法,但其實也代表了李兆洛的態度,上文《答湯子垕》就是對此最好的注腳。
在代好友莊綬甲為自己編的《駢體文鈔》作序時,李兆洛既批評了當時古文家排斥駢文,孤行一意,空所依傍,不求工,不使事,不隸詞的文章視為古文,非是則謂之“駢”,將古文與駢文截然對立,是好丹非素的現象;又對駢文家推崇齊梁體表示不滿:
然則今之所為文,毋乃開蔑古而便枵腹矣乎!業此者既畏“駢”之名而避之,或又甘乎“駢”之名而遂以齊梁為宗。夫文果有二宗乎?②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八附《代作駢體文鈔序》,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95册,第119頁。
李兆洛主張取消駢體與散體/古文之分,強調駢文本來出於古文,兩者本來同源,秦漢古文也離不開駢體,從而使為文回到秦漢駢散不分、駢散合一的狀態去。然而,李兆洛雖主觀上没有認為秦漢散句單行,雜有駢偶和排比的文章就是“駢體”,自己只是因流溯源,凸顯“駢體”不應該被輕視,纔將《古文辭類纂》所選録的大量秦漢古文選入,但客觀上造成了時人以及後人將這些駢散不分但有較多駢句的文章視為駢體文。此外,好友吴育為《駢體文鈔》作序時,較好地把握了李兆洛的推尊漢魏,貶抑齊梁體駢文的思想,有曰:
至枚乘、司馬長卿出而其體大備,有《書》之昭明,《詩》之諷諫,《禮》之博物,《左》之華腴。故其文典,其音和,盛世之文也。後生祖述,際齊、梁而益工,玄黃錯采,丹青昭爛,可謂美矣,然不能有古人之意。其蕩者為之,或跌宕靡麗,浮而無實,放而不收,至蕭氏父子而其流斯極。然其間如任昉、沈約、邱遲、徐陵、庾信之徒為之,莫不淵淵乎文有其質焉。惜也囿於俗,而不能進厥體,故君子有自鄶無譏焉。①吴育:《駢體文鈔序》,載於李兆洛:《駢體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
在吴育看來,漢代枚乘、司馬相如的駢文文典音和,是盛世之音;齊梁體雖然美麗,但缺乏古人之意;有的甚至跌宕靡麗,華而不實,放而不收,至蕭衍、蕭繹、蕭綱而達到極點。任、沈、徐、庾等雖文質兼有可采,但也囿於時俗,没有提升駢文的文體品格。隨著《駢體文鈔》的廣泛流傳,這種推尊漢魏,貶抑齊梁體駢文的思想深刻影響了晚清的駢文批評和駢文創作。
光緒元年(1875),張之洞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駢體文家”條目認為清朝:“諸家流别不一,有漢魏體、有晉宋體、有齊梁至初唐體。然亦間有出入,不復分列。至中晚唐體、北宋體,各有獨至之處,特諸家無宗尚之者。彭元瑞《恩餘堂經進稿》用宋法,今人《示樸齋駢文》用唐法。”②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頁。同年,其《輶軒語》叙述“古文駢體文”時指出:“國朝講駢文者,名家如林。雖無標目宗派,大要最高者,多學晉宋體。此派較齊梁派、唐派、宋派為勝,為其樸雅遒逸耳。”③張之洞撰,程方平編校:《勸學篇》附《輶軒語》,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頁。對李紱的駢文三體之分進一步細化,其中明確指出“晉宋體”,當包含“漢魏體”,風格樸雅遒逸,為清代駢文體格最高者。張之洞本身就是清末駢文名家,其説較為可信。晚清朱一新在廣州學海堂講學時,針對學生提問:“駢文導源漢魏,固不規規於聲律對偶。百三家時有工拙,惟徐、庾能華而不靡,質而不腐。取法貴上,似當以風骨為主。”回答曰:“駢文萌芽於周秦,具體於漢魏。”所謂“具體”,即體裁形成於漢魏。他還進一步指出不同時代駢文特徵的不同:
周秦諸子之書,駢散互用,間多協韻,六經亦然。西京揚、馬諸作,多用駢偶,皆已開其先聲。顧時代遞降,體制亦復略殊。同一駢偶也,魏晉與齊梁異,齊梁與初唐異。同一初唐、齊梁也,徐、庾與任、沈異,四傑與燕、許異。①朱一新著,吕鴻儒、張長法點校:《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89—90頁。
駢文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漸形成的。成體之後,隨著文體自身演變和時代風尚的變化,不同時代、不同名家的“體制”也有不同。光緒間,胡念修進一步將“耦文”分為四種:“蓋國朝文學大昌,無體不具。學奇之文,其名有四,曰周秦,曰兩漢,曰唐,曰宋;學耦之文,其名亦四,曰漢魏,曰齊梁,曰唐,曰宋。”②胡念修:《國朝駢體文家小傳叙》,載於王水照:《歷代文話》,第6249頁。更是明確將清代駢文分為四類,“漢魏”與“齊梁”並駕齊驅。可見,在晚清駢文批評中,“漢魏體”駢文備受重視,地位顯赫。在創作中,晚清駢文,特别是以王闓運、閻鎮珩、皮錫瑞為首的湖湘駢文,主要體現了駢散不分、駢散交融的漢魏文章風貌。民初郭象升《文學研究法》説到:“駢文衰於齊梁,由於玄言不振也。魏晉作者,根極道理,其言表裏瑩澈,視散文家或反過之,何得謂駢文無與於性道哉?”③余祖坤:《歷代文話續編》,第1957頁。這些都與李兆洛對“齊梁體”的排斥和對漢魏體的推崇,導致駢文宗尚在晚清發生轉向有關。
二、李兆洛《駢體文鈔》對“駢體文”指向的擴容
李兆洛不僅在理論上排斥齊梁駢體,而且在選本中凸顯漢魏甚至先秦“駢體”之文,擴大駢文涵攝文類的範圍。道光元年(1821),他編選的《駢體文鈔》刊行。該書改變駢文選本選文始於魏晉的慣例,輯録先秦、兩漢文章多篇,如李斯、司馬遷等人的;又打破宋、元、明四六選本不收頌贊、箴銘、哀祭等韻文的常規,對之加以選録;還通過相關序跋、書信指出學習兩漢文章非自駢體入手不可,推崇實際上是駢散不分的漢魏“駢體文”。這一方面擴大了駢文指向,解構了舊有的以齊梁、初唐駢體為“正聲”的傾向,建構了一種新的駢文概念;另一方面,又弱化了駢文的文體特徵,強化了駢文的類别屬性,客觀上導致嘉道以來駢文内涵更加寬泛,文體屬性更加模糊,從而削弱了駢文文體的獨立性與自足性。
《駢體文鈔》所選文章,有些並不是時人所認可的駢文。如卷一“銘刻類”中,收録李斯刻石類文章7篇。這些文章句式主要是四言單句連用,上下兩句辭、意皆不對偶,意義不是並列或互補,而是前後遞進,上下連貫,一氣流轉,更不必説使用四六隔對了。且這些銘文多是三句一韻,以三句為一個語意單位,與齊梁以後的駢文多兩兩相對完全不同。如《泰山刻石》全文曰: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跡,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①李兆洛:《駢體文鈔》,第2頁。
全文歌頌秦始皇的功德,基本為四言句式,都是三句一韻,每韻圍繞一事叙述,具有排比文意的特徵,但和後世具有裁對、隸事、敷藻和聲律等特徵的駢文差距較大。前人明確視為“散文”的一些表文,李兆洛也選入。明代沈懋孝論述“表”文時曰:“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也,有進表;吴陸士衡之謝平原内史也,有謝表;晉羊叔子之讓開府也,有辭表;劉越石之勸進中宗以系人望也,有賀表。乃若諸葛孔明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又出四體之外,直抒己志,精忠孝感,垂之到今矣。然皆散文也。駢體興於宋、齊、梁,而唐初則駱義烏以四六擅場。”②沈懋孝:《論四六駢體》,《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明文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686—687頁。沈懋孝站在駢體興起於宋、齊、梁的立場,自然將諸《出師表》、《陳情表》等視為“散文”。但這裏提到的六篇表文,除了馬援的外,其他都入選《駢體文鈔》。此外,李斯的《諫逐客令》、司馬遷《報任安書》等傳統散體文,雖使用了較多排比和對偶,但很少使用四六隔對,對偶不工,隸事較少,且多用古文虚詞和句法,也被選入。這自然引起名不副實的感覺,好友莊綬甲因而建議改名。對此,李兆洛專門寫信加以解釋:
吾弟謂《駢體文鈔》當改名,吾弟未閲兆洛前序耶?未閲所代作之序耶?自亦未之深思耶?若以為《報任安》等書不當入,則豈惟此二篇?自晉以前,皆不宜入也。如此,則《四六法海》等選本足矣,何事洛之為此嘵嘵乎?洛之意頗不滿於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兩漢。所謂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輕淺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詠,口牙小慧,譾陋庸詞,稍可上口,已足標異。於是家家有集,人人著書,其於古則未敢知,而於文則已難言之矣。竊以為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今日之所謂駢體者,以為不美之名也。而不知秦漢子書,無不駢體也。竊不欲人避駢體之名,故因流以溯其源,豈第屈司馬、諸葛以為駢而已,將推而至《老子》、《管子》、《韓非子》等,皆駢之也。今試指《老子》、《管子》為駢,人必不能辭也。而乃欲為司馬、諸葛避駢之名哉?《報任安書》,謝朓、江淹諸書之藍本也;《出師表》,晉宋諸奏疏之藍本也,皆從流溯源之所不能不及焉者也。其餘所收秦漢諸文,大率皆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者也。①李兆洛:《答莊卿珊》,《養一齋文集》卷八,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95册,第119頁。
莊綬甲循名責實,以文體定選文,認為既然是“駢體文鈔”,就應該收録駢文,不能收録傳統散體文。即從駢文、散文對舉的角度,指出李兆洛選文的不當。其實,李兆洛深知駢文内涵,曾指出時人將駢文分為六朝、唐和宋三體:“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為駢儷。而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為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為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為萬有不同可也。”②李兆洛:《駢體文鈔序》,《養一齋文集》卷五,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495册,第77頁。但他編選駢文選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駢文、古文割裂對舉的常規思維,也要打破駢文分為三體的通常觀念,主張駢散同源,駢散不分,駢文是古文的自然發展。所以,他指出諸葛亮、司馬遷的文章和《老子》、《管子》、《韓非子》等子書中都有駢體現象的存在。這種駢體現象正是齊梁成熟駢文的重要淵源,從流溯源,自然可以將某些秦漢文章選入。他借此説明駢文存在的合理性,想推尊駢體,方法卻是將駢體消泯於古文中。可見,李兆洛不是不知駢文的内涵及發展歷史,而是故意打破駢散對立,宣導駢散不分,回歸到漢魏文章駢散交融的自然狀態。這種做法,無疑是對歷代“駢體”概念的解構,也是對當時駢文概念的建構。
《駢體文鈔》不僅將駢文溯源秦漢,甚至先秦諸子,延伸了駢文發展的時間長度,還在空間範圍上,拓展了宋代四六别集和四六話主要由制誥、表啟、上樑文、樂語組成,明代四六選本主要由表啟組成的局面,將數量衆多的文類收入其中。如漢代以來的頌贊、箴銘、哀祭,都屬於韻文,晚明至清初的駢文選本一般不予録入,《駢體文鈔》卻將之收入,從而名正言順地擴大了駢文範圍。《駢體文鈔》包括上、中、下三編共三十一卷。上編包括銘刻、頌、雜揚頌、箴、謚誄哀策、詔書、策命、告祭、教令、策對、奏事、駁議、勸進、賀慶、薦達、陳謝、檄移、彈劾共十八卷;中編包括書、論、序、雜頌贊箴銘、碑記、墓碑、志狀、誄祭共八卷;下編包括設辭、七、連珠、箋牘、雜文共五卷。雖然分類有些蕪雜,没有像姚鼐將“古文辭”分為十三類那樣清晰明瞭,但實際上除了辭賦、贈序和傳没有收録外,該書包含的文類與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幾乎相同。這也充分説明,“駢體文”像“古文辭”一樣涵容廣泛,功能齊備。古文家所謂駢體多無用,散體多有用之説,就不攻自破。
《駢體文鈔》能夠在駢文内涵及包含文類上實現擴容,當與李兆洛對當時古文家輕視駢體的思想有關。“李氏之為《駢體文鈔》,欲以合姚氏《類纂》,使世人明其同出一源之義而作為此書。嘉慶末,合河康紹鏞氏在粤東取吴山子所藏《類纂》本校閲付梓,李氏時為康客,因而謂唐以下始有古文之稱,而别對偶之文曰駢體,乃更選先秦、兩漢下及於隋為是《鈔》,以便學者沿流而溯源,故蔣氏《年譜》特著之,今人鮮有知其為姚書而作者。其主暨陽書院,示諸生必以《史》、《漢》、董、管、荀、吕、商、韓、賈諸文為宗,蓋猶前志,此駢散合一一派明統之法也。”①王葆心:《古文詞通義》卷六,載於王水照《歷代文話》第8册,第7293—7294頁。正如曹虹先生指出:“他在對姚鼐的‘懋學淳詣’深懷敬意的同時,卻並不妨礙他在文學觀念上的創造與突破。事實上,《駢體文鈔》一書的選編,就隱然有與姚鼐《古文辭類纂》對壘的意圖。”②曹虹:《陽湖文派研究》,第97頁。《駢體文鈔》在道光元年(1821)刊刻後,影響極大。湧現了道光間誦芬閣本、同治六年婁江徐氏精刻本、光緒七年四川存古書局重刻本、光緒七年四川尊經書局刻本、光緒八年上海合河康氏重刻本、光緒三十四年蘇州振興書社刻本等近十種;還有陳澧、翁同書、李慈銘、譚獻、平步青、楊佩瑗等人的評點本①鍾濤、彭蕾:《李兆洛〈駢體文鈔〉成書和版本考述》,載於《勵耘學刊》(2015年第1期),第250—253頁。。此外,還有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等。無疑,《駢體文鈔》是中國古代刊刻次數最多,影響最大的駢文選本。通過所選作品時間和文類的“越界”,他的駢散不分、推崇漢魏文章的觀念廣泛流傳,從而實現了對駢文的擴容和對駢文史的重構。
三、李兆洛的“漢魏體”駢文創作
李兆洛排斥齊梁,推崇漢魏駢體,不僅體現在理論批評上,還表現在創作中。受到歷代序跋駢儷色彩濃郁的影響,在清代駢文文類中,序跋最為常見,數量最多,駢儷化程度也最高。李兆洛本人並没有以“駢體”、“駢文”命名自己文集,但其中多有駢儷色彩較重的文章。
光緒七年(1881),張壽榮編選的《後八家四六文鈔》八卷刊行。“後八家”指張惠言、樂鈞、王曇、王衍梅、劉開、董祐誠、李兆洛和金應麟,都為嘉道年間駢文家。張壽榮是浙江鎮海人,所選八家來自江、浙、皖、贛四地。該書所選駢文家地域、作品數量和排序如下:

地域 秀水 臨川 陽湖 會稽 陽湖 仁和 桐城 武進作家 王曇 樂鈞 董祐誠 王衍梅 李兆洛 金應麟 劉開 張惠言篇數 20 18 16 16 12 12 10 9排序 1 2 3 3 5 5 7 8
“後八家”中,無疑以李兆洛在駢文史上的影響最大,但入選篇數排在第五,可見在張看來,李兆洛的駢文創作地位並不算太高。12篇入選文章為《皇朝文典序》、《南漢記序》、《姚石甫文集序》、《愛石圖題辭續編序》、《跋汪桐生漢印偶存》、《陶雲汀中丞蜀輶日記書後》、《重修元妙觀碑記》、《趙收庵先生誄辭》、《蕭母吴太宜人誄》、《江蘇學史辛筠谷先生誄》、《答陶巡撫書》、《連珠十五首》,其中序跋、連珠的駢儷色彩較濃,其他誄、記、書則是駢散結合,以散為主。光緒十四年(1888),張鳴珂編選的《國朝駢體正宗續編》刊行。張鳴珂是浙江嘉興人,他以嘉道至光緒初年的駢文家為對象,除了江南地區外,廣東、湖南的駢文家譚瑩、易順鼎等入選,從而比《後八家四六文鈔》更有代表性。該書選録56位作家文149篇,其中4篇以上的14位,李兆洛入選3篇,排在第15位,地位並不高。這3篇駢文都是從《後八家四六文鈔》所選12篇四六中挑選出來的,分别是《皇朝文典序》、《愛石圖題辭續編序》、《陶雲汀中丞蜀輶日記書後》。
可以説,在李兆洛《養一齋文集》中,這3篇最能代表李兆洛文章的駢儷化程度,從中可以看出他駢散不分、駢散相容的創作風貌。3篇都不是長篇大論,篇幅較短;句式較少駢四儷六與隔句為對,多用叙述性而不是鋪陳性的四言;隸事雅潔且不多,文詞自然,文氣流暢,不像齊梁至初唐那種精緻綺靡的四六駢體。其《皇朝文典序》全文曰:
大圜不言,星雲爛然。實代之言,大方無紀。河嶽迤邐,以為之紀。其在於人,精者曰文。下挾河嶽,上昭星雲。所以經緯宇宙,炳朗絲綸者也。其儒墨之訓,彫瑑之詞,畸人術流之馳説,春女秋士之抽思,皆一花一葉,一翾一蚑,各有可觀,而非其至者矣。拘學之士,閉門距躍,高指月窟,卑詮蟲天,囿於所習,得少自足。或服習卿雲,揚㩁燕許,只襲優冠,競陳芻狗。於朝家寶書鴻典,曾未或窺。是猶不睹建章宫之千門萬户,而妄意蓬室為璿臺;不聞鈞天廣樂之洞心駭目,而拊掌巴渝以軒舞也。曩廁庶常,竊抱此愧。間搜司存,冀有採獲。旋出宰邑,斯業廢然。罷官多暇,憶之耿耿。比游維揚,聞此土前輩先有纂集,亟求而觀,巨帙充几,登縣圃而案玉,入鮫淵而數珠矣。就其輯録,小有乖紊。遂加釐次,以類相從,都若干篇,為七十四卷。羅列務盡,非有取捨。其所未備,俟諸博求。卷之大小不齊,蓋留編續之地焉。其於掌故,以當中郎獨斷;資之遣翰,或同伯厚指南。豈戴圜履方之倫,誇於創見;庶大雅宏達之彦,遂其乃心云爾。①張鳴珂:《國朝駢體正宗續編》卷一,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668册,第225頁。
全文意在為時人提供典範性的文章選本,文詞簡潔,駢中有散,堪稱風骨高嚴,文質兼備。句式整齊中見駢儷,但以散化的四言句式為主,較少使用四六隔對,毫無繁縟綺靡之弊,是典型的“漢魏體”駢文風貌。屠寄評李兆洛的駢文為“翰藻之美,張蔡是憲”①屠寄:《國朝常州駢體文録》卷三一《叙録》,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693册,頁712頁。,確為當行評價。《愛石圖題辭續編序》是李兆洛應王國棟之邀,為其父親王學愚的《愛石圖》相關題辭所作序。該文首先感慨人生短暫,一閃即逝,雖然留有圖畫默寫嗜好,有題詞叙述功德,但終究令人悲傷;接著叙述王學愚的高尚品行與閑居生活,感慨世事滄桑,人事無常:“嗟乎!逝景遥遥,百年短短。壑舟一運,石火猶遲。雖復追嗜好於平生,寄音容於模寫,抽毫述德,越世論交,其為周旋,抑已悕矣。學愚王君,珞珞自異,硜硜守中,居閑懷礪齒之風,敷衽盡他山之益。爰以高塵之賞,圖其置壑之歡。當其高齋客來,勝友輩集,銜杯晏笑,解帶舒懷。或矜冰雪之思,或動龍蛇之筆。傳玩既習,篇章日增。宛然在焉,思之如昨。乃日月代謝,存亡奄乖。一時同游,相繼淪喪。”②張鳴珂:《國朝駢體正宗續編》卷一,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1668册,第226頁。最後從王國棟虔誠守護《愛石圖》,編選《題辭續編》之仁,諸位友人題辭之誼等來讚揚王學愚的貞白之雅,磊落之襟足以流傳後世。全文同樣以四言為主,叙述清晰,文風雅潔,文氣流暢。文字看似簡潔,但堪稱句句有來歷,特别是緊扣“石”之典故,將之與叙述物件融合起來,渾然一體。如“逝景”來自王僧達《答顔延年》“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説明光陰飛逝。“壑舟”來自《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比喻事物在不知不覺中變化。“石火”形容短暫,潘岳《河陽縣作二首》有“熲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飈”。“越世”指超越世俗,來自《世説新語·賞譽下》。“周旋”出自《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鞭,以與君周旋”。“珞珞”來自《老子》“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硜硜”來自《論語·憲問》:“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礪齒”,刷牙去垢,表示清高。劉義慶《世説新語·排調》:“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敷衽”,解開襟衽,表示坦誠。《楚辭·離騷》:“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他山”來自《詩經·小雅·鶴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高塵”,崇高的風範。沈約《與何胤敕》:“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這些典故雅潔精煉而不繁縟生硬,化用無痕,體現了作者深厚的學識與過人的才華。文章整體風格也是運散於駢,句式整齊而不工致,是駢文初成時的形態。
此外,陶澍典試四川時撰寫了《蜀輶日記》,記叙沿途所經地區的山川地理、建制沿革和歷史古跡等。道光七年(1837),李兆洛寫下了《陶雲汀中丞蜀輶日記書後》。該文風格與上兩篇相似,從中還可以看出李兆洛有意追求通脱的思想:“夫耳目所構,皆關性靈;語言所抒,惟資神理。而研詞者騁詭麗,侈博者矜遠奥,考據者逐細碎,誇論者耽新奇,騖於一途,通之則窒。固才力之偏至,實神明之寡要耳。”①張鳴珂:《國朝駢體正宗續編》卷一,載於《續修四庫全書》1668册,第226頁。對於偏執一端,相輕所短,李兆洛不以為然,提出應該“通之”,但一般人才力偏至,難以做到。陶澍的《蜀輶日記》:“苞廣谷大川之氣勢,宣政治弛張之所當,究古今成敗之所原。又探本禹跡,疏通桑酈。經生之所聚訟,形家之所揣摩,片言洞微,萬結立解。詞表纖旨,經百思而愈深;言中鴻律,俟千載而不惑,此豈與夫鬻聲釣世者同日語哉!”雖有誇飾,但該書確實體現了陶澍經緯彝憲、陶甄群生、因俗成化和開物成務的主要措施,因而本文較有現實針對性,堪稱李兆洛駢文中的代表作。
清代常州是駢文最為發達的地域,湧現了大批駢文名家。“乾嘉間,陽湖工偶體文者,以洪稚存、孫淵如、趙味辛、劉芙初為最。彦聞與董子詵、董方立兄弟聯鑣繼起,以稱雄於世。”②王樹楠:《萬善花室文稿叙録》,《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李兆洛在理論批評上聲名顯赫,但根據晚清的主要駢文選本和對李兆洛文本的分析,可知他的駢文創作成就和地位都不高。民初郭象升在《文學研究法》中説到:“申耆選《駢體文鈔》,修詞者奉為指南;而平生如此,似非專家。抑且不名一體,就其善者,雅近崔、蔡。碑板之文,所擅長也。”③余祖坤:《歷代文話續編》,第2020頁。“似非專家”及“不名一體”,正説出了李兆洛對工致駢文的疏離。光緒十六年(1890),武進人屠寄(1856—1921)選編的《國朝常州駢體文録》刊行。該書收録43家569篇駢文,李兆洛入選達65篇,僅次於洪亮吉的79篇,遠超清初駢文大家陳維崧的21篇及乾嘉道的其他常州駢文名家如趙懷玉、劉嗣綰、楊芳燦、董基誠、董祐誠等。其實,這是屠寄對鄉賢李兆洛的偏愛。該書所選李兆洛文章,大部分為駢散相間之文。正如曹虹先生所言,李兆洛:“不拘於文體,或駢或散,稱心而言,而歸於氣骨深厚。屠寄《常州駢體文録》録李兆洛文六十五首,比陽湖派其他人士為多,其中如《姚石甫文集序》等文,雖被張壽榮選入《後八家四六文鈔》,但與其説是四六文,不如説是駢散相間之文更合適。”①曹虹:《陽湖文派研究》,第212頁。然而,這種駢散兼行之文在晚清被視為“駢文”中最受歡迎的一體,本身就與李兆洛對駢散不分的漢魏文章的推崇密切相關。嘉道以來,文章界流行駢散合一、駢散不分的思想。到清末民初,這種思想更加流行,從而導致了魏晉文在當時備受推崇。
結 語
李兆洛以其駢文批評與創作,給清代駢文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晚清重要的駢文選本和駢文批評,多離不開李兆洛的影響。可見,他對晚清駢文的演變具有重要的作用。他通過理論闡釋與選本批評等,主觀上想融通駢散,消弭駢散之爭,突出六朝駢文為秦漢駢散不分之文的自然發展,因而選擇秦漢文録入駢體,但這客觀上建構了駢文成體的時間,擴大了駢文的文體範圍,因而重構了駢文史。這一建構同時也解構了宋、元、明至清初駢文文體的“四六”指向,使得駢散不分的“漢魏體”駢文,嚴格來説是“駢散文”在晚清非常流行。通過這種建構與解構,李兆洛客觀上消解了自晚唐李商隱至晚明的“四六”文體含義,泛化了駢體内涵,弱化了駢文的自足性。建構是李兆洛为了推尊駢體而主動為之,有意改變當時文壇古文家輕視駢體的痼疾;解構則是他以古文為準的,推尊駢體而無心導致的客觀效果。無論建構還是解構,都顯示了李兆洛對晚清文壇帶來的重大影響,對駢文學的建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