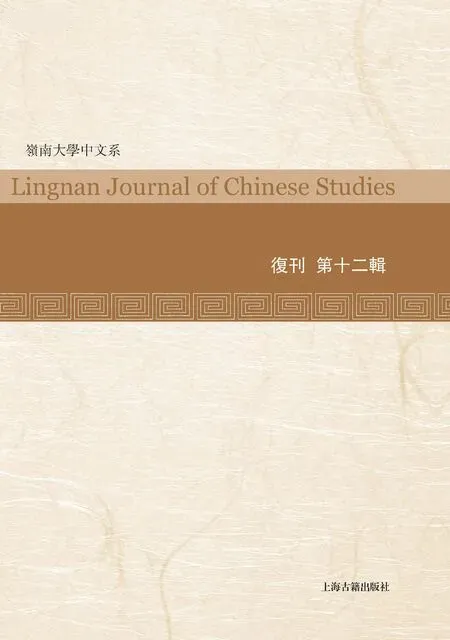“詩言志”之本義謭論
——讀朱自清先生《詩言志辨》札記
張峰屹
朱自清先生《詩言志辨》①朱自清:《詩言志辨》,載於《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355頁。以下引用該書均據此本,為免繁瑣,不再一一出注。,從“獻詩陳志”、“賦詩言志”、“教詩明志”、“作詩言志”四個維度,細緻解析了“詩言志”之内涵。朱先生此著,乃是以“詩言志”、“詩教”、“比興”和“正變”四者,勾勒上古詩學思想的根本綱領及方法論。並且他以為,此四者乃“以‘詩言志’一個意念為中心”,而四者之思想歸趣“自然都在政教”。然則所謂“詩言志”,便是“詩表達(言説)思想意志用以教化”的意思,理論重心在於詩之政教功用。朱先生的論斷,實際上是在疏釋、整理漢代的詩學思想,而不以追本溯源以及現代學術立場的分析理解為務。然而,《詩言志辨》學術影響甚大,許多現代學者都接受了朱先生的觀點,單純强調“詩言志”之表達思想意志和追求政治教化的性徵。於是,便不乏將陸機“詩緣情”之説與傳統的“詩言志”對立起來的看法,以為這是性質相對的兩種詩學思想①裴斐《詩緣情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對此一問題有精湛辯説,本文不贅。。
本文以為,朱先生將“詩言志”譽為中國文學批評“開山的綱領”,立論甚是精確。然而,他對“詩言志”之内涵和旨趣的論斷,只是對漢代詩學思想的整理和提煉,“詩言志”之本始内涵及其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發展之意義和影響,尚可再加多維審視。限於篇幅,本文僅致力於追尋“詩言志”之説的本義,從先秦“詩言志”之實踐和闡説、詩人自道“詩言志”之内涵、“詩言志”文字訓詁三個方面展開。
一、先秦“詩言志”之實踐和闡説
朱先生臚列“獻詩”、“賦詩”、“教詩”、“作詩”四個層面作論,分析細密;而其實際的焦點,實在“賦詩”和“作詩”二者。這裏先來看“賦詩”。
就傳世文獻看,“詩言志”作為一個概念或理論表述正式提出,最早似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①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34頁。
晉大夫趙武(趙孟,即下文之“文子”)在宋國參加完十四國會盟回國,途經鄭國,遂有此事。趙武請鄭國七臣賦《詩》,欲“以觀七子之志”;而會後又有“(賦)《詩》以言志”之明説。這段文字展現的,便是後來《漢書·藝文志》概述的情形:“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别賢不肖,而觀盛衰焉。”②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55—1756頁。為便於真切理解,姑簡析其“賦《詩》言志”、“聞賦觀志”的具體情形。
子展賦《草蟲》。杜預注曰:“以趙孟為君子。”③本文引證杜預注文,均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四部叢刊》影印宋刊巾箱本。案:詩見《召南》,其首章有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關於此詩之旨意,古有兩類代表性解説:(1)《毛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④本文引證《毛序》及《鄭箋》,均據孔穎達《毛詩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朱熹《詩集傳》云:“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⑤朱熹:《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9頁。毛、朱説雖不同,但均關乎男女情感問題;(2)劉向《説苑·君道》引述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⑥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説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頁。以為《草蟲》所述乃好尚善道之義。子展賦此詩,旨意近於《説苑》所載孔子之説,而融入了自己憂國而慕趙之新意,以頌美趙武為君子,並表達了憂國憂民及信重晉國之義。故趙武稱讚子展“善哉,民之主也”,並自謙“不足以當之”。子展賦此詩,與詩作之本義並不完全符合。
伯有賦《鶉之賁賁(今本作奔奔)》。杜預注曰:“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案:詩見《鄘風》:“鶉之奔奔,鵲之强强①鄭《箋》云:“奔奔、强强,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韓詩》云:“奔奔、强强,乘匹之貌。”。人之無良,我以為兄②鄭《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君謂惠公。”。鵲之强强,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關於此詩之旨意,《毛序》云:“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鄭《箋》云:“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如禽鳥。”伯有賦此詩之意,與《毛詩》義異,雖仍藉以譏刺淫亂,但所刺對象是君(鄭伯),而非女寵。故趙武會後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杜預注曰:“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伯有賦此詩乃是借題發揮,亦未遵守詩之本義。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杜預注:“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案:詩見《小雅》。周宣王分封其母舅於申(史稱申伯),命召虎(史稱召伯)帶領官兵,裝載貨物,經營申地,建築謝城以為其國都。這首詩是隨從召伯建設申國者完成任務後在歸途中所唱的歌,用以歌頌召伯對國家的貢獻。子西賦此詩,意在比趙武於召伯,故趙武自謙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杜預注:“推善於其君。”)子西賦此詩,乃是遵守了詩作之原義(儘管召伯和趙武所為之具體事務不同),而借喻以稱頌趙武。
子産賦《隰桑》。杜預注:“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案:詩見《小雅》:“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關於此詩旨意,《毛序》曰:“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毛傳》釋義較為隱曲,而“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義,於詩中則可以顯見。故朱熹《詩集傳》徑謂:“此喜見君子之詩。”子産賦此詩,表達樂見君子之義,與原詩之旨意相合。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杜預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案:詩見《鄭風》:“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關於此詩旨意,《毛序》云:“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子大叔賦此詩,藉以轉諭其對趙武的渴慕、喜見之情,故趙武感謝道:“吾子之惠也。”可見子大叔賦此詩,乃為斷章取義之屬。
印段賦《蟋蟀》。杜預注:“言瞿瞿然顧禮儀。”案:詩見《唐風》,三章詩義重疊,其首章云:“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關於此詩旨意,《毛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三家《詩》皆云此詩乃刺儉(禮儀不周備)之義(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①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印段賦此詩,遵守詩之原義,表達守禮勿荒的意願。故趙武稱讚他道:“善哉,保家之主也!”(杜預注:“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杜預注:“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案:詩見《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關於此詩之旨意,《毛序》云:“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也。”鄭《箋》云:“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果如此,則此詩乃是反義正出、以美為刺的諷諫之作。而公孫段賦此詩,當是正義正出,表達敦行禮儀之志願。故趙武曰:“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
由上述七子賦《詩》的具體情形可見,春秋時期的“賦《詩》言志”,大抵有基本符合詩之本義和不合本義兩種情形。基本符合者,如子西賦《黍苗》、子産賦《隰桑》、印段賦《蟋蟀》;餘皆不完全符合詩之原義。
《左傳》、《國語》中,此類賦《詩》言志、斷章取義例子很多,不勝枚舉。而無論其賦《詩》是否符合原義,就賦《詩》者之用意而言,都有一個基本傾向,那就是:斷章取義,借《詩》章言己意。此種情形,在先秦是很理性的行為,《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就記録了齊人盧蒲癸之説:“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
如果説《左傳》、《國語》諸書中記録的“賦《詩》言志”乃是用《詩》之實踐,那麽《尚書》記載的“詩言志”,便是理論闡述了:
帝(舜)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尚書·堯典》)
這一段耳熟能詳的史料,儘管難以相信它果真産生於堯舜時代,但必然是先秦時期的思想觀念則無可懷疑。這段史料的重要價值,一是如上述,它是“詩言志”思想的理論形態的表述;二是與《左傳》記録的“用《詩》”不同,它是從詩歌創作的角度(“作詩”)來闡述“詩言志”的。就其思想而言,這段文字的主旨明顯是指向政教,故其“詩言志”之“志”,主要應指思想意志。
《左傳》、《尚書》等典籍之外,先秦諸子的著述中也屢見“詩言志”之説,如《莊子·天下》云:“詩以道志。”《荀子·儒效》云:“詩言是其志也。”《荀子·樂論》云:“君子以鐘鼓道志。”然則,至晚到戰國之時,“詩言志”已經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成説了。
綜上可知,先秦“詩言志”説實際藴含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内涵:一種是《尚書·堯典》中提及的“詩言志”,從創作的角度立論,詩一般不是指《詩經》等既有的詩歌,而是作為一種文體類型的詩歌。另一種是“賦《詩》言志”,詩是《詩經》中的詩歌(或有逸詩),而所謂“賦《詩》”者,不是自己創作,而是引用既成之詩章以抒發一己之志意。而無論“賦《詩》言志”,還是“作詩言志”,其所言之“志”,都是偏於清明理性的思想意志。這似乎佐證了朱自清先生關於“詩言志”内涵之論斷的準確;然而,若想弄清“詩言志”的本真涵義,尚須考察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詩人自道“詩言志”之情形。
二、《詩經》中詩人自述之“詩言志”
朱先生《詩言志辨》舉出了《詩經》作者自道作詩情由的詩句十二條①《詩經》作者自道“詩言志”,不止十二處。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之《先秦兩漢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即例舉了十七條,其實還有遺漏。,顯然注意到了《詩經》中詩人自述之“詩言志”,惜乎他在做論斷時,並没有給予這些詩人自道足夠的重視,抑或是太過相信漢人解《詩》的説法,所以他還是把“詩言志”之内涵單純歸結為表達思想意志以服務於“政教”。本文以為,上述“賦《詩》言志”、“作詩言志”的史實、史料固然重要,而詩人自道之“詩言志”,從學理上説,對於準確理解“詩言志”之本義而言,更是根本性的佐證,應予特别重視。下面舉出一些含義明顯的例證,以觀詩人自道“詩言志”之本真内涵:
1.《魏風·葛屨》:“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毛序》曰:“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朱熹《集傳》云:“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今人多從之,認為是縫衣女諷刺貴族婦女的詩。
2.《陳風·墓門》:“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序》曰:“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鄭《箋》云:“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按:事見《左傳·桓公五年》。陳佗為陳文公之子、桓公之弟,殺太子陳免而自立,陳國於是大亂。朱熹《集傳》云:“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
此詩之本事尚有他説,劉向《列女傳》卷八《陳辯女》云①劉向編撰,顧愷之圖畫:《新刊古列女傳》,清道光五年(1825)揚州阮福摹刊南宋建安余仁仲刻本。:“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猶言疇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無論其本事如何,此詩之作意乃為諷刺,當無可疑。
3.《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毛序》曰:“家父刺幽王也。”鄭《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此詩乃是周大夫諷諫周王,詩義自明。
4.《小雅·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毛傳》:“倫,道。脊,理也。”)。”
《毛序》曰:“大夫刺幽王也。”此詩也是周大夫諷諫周王之作。
5.《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知此詩為蘇公譏刺暴公並示絶交之作。
6.《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序》曰:“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知此詩為閹人孟子傷讒、斥責摇唇鼓舌小人之作。
7.《小雅·車舝》:“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毛序》曰:“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鄭《箋》云:“諸大夫覬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燕飲,肴雖不美猶食之人,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知此詩亦諷諫之作。
8.《大雅·卷阿》:“矢(陳)詩不多,維以遂歌。”
《毛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起士也。”《毛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知此詩為勸誡成王求賢納士之作。
9.《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毛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鄭《箋》云:“時賦斂重數,徭役繁多,人民勞苦,輕為奸宄,强陵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又,此二句鄭《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知此為召穆公諷諫周厲王之作。
10.《大雅·板》:“猶(《毛傳》:“猶,圖也。”鄭《箋》:“猶,謀也。”)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序》曰:“凡伯刺厲王也。”鄭《箋》云:“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知此為凡伯諷諫周厲王之作。
11.《大雅·桑柔》:“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毛序》曰:“芮伯刺厲王也。”鄭《箋》云:“芮伯,畿内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王符《潛夫論·遏利》云:“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①王符撰,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7頁。此二句,鄭《箋》云:“女雖觝距己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孔穎達《疏》云:“汝雖言曰‘此惡政非我所為’,我知汝實為之,已作汝所為之歌,歌汝之過,汝當受而改之。”知此為芮良夫諷諫周厲王之作。
以上例證,詩人自道其作詩乃為諷刺、勸諫。此種情形之“言志”,含義為表達思想意志。
12.《召南·江有汜》:“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序》曰:“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蓋為歌頌媵妾遭受嫡妻嫉妒而不怨望,亦美嫡妻能夠自悔。此詩當為媵妾所歌,所謂“不我過,其嘯也歌”,意謂嫡妻不與我過往,我心憂傷,故嘯歌抒懷。
13.《魏風·園有桃》:“心之憂矣,我歌且謡。”
《毛序》曰:“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歌謡之作,乃為紓解心憂,詩義自明。
14.《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毛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鄭《箋》云:“告哀,言勞病而訴之。”朱熹:“此亦遭亂自傷之詩。”此謂作歌以抒發心中悲哀,詩義自明。
15.《小雅·四牡》:“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念。”
《毛序》曰:“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説矣。”鄭《箋》云:“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此蓋為文王慰勞使臣之詩。又,《儀禮·鄉飲酒》鄭玄注云:“《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勤苦王事,念及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此詩五章,前四相繼歌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末章以“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念”結穴。其作詩以抒發歸思及思念父母之意,十分顯明。
16.《小雅·白華》:“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序》曰:“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案:“碩人”有指褒姒、申后、幽王三説,以指申后説為勝。詩人(周人)為幽王黜申后改立褒姒而傷懷,作歌以懷念申后。
以上例證,詩人自道其作詩乃為發抒内心之某種情感。儘管或有政治本事,但詩人自言者均為抒情之義。此種情形之“言志”,其含義顯然是抒發情感。
17.《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毛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朱熹《集傳》云:“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18.《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朱熹《詩集傳》云:“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漢書·杜欽傳》載杜欽説王鳳有云:“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王),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①班固:《漢書》,第2677頁。顔師古注引鄧展説:“詩言仲山甫銜命往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為封於齊,此誤耳。”按:漢人多有仲山甫封齊之説,王符《潛夫論·三式》言及以上二詩,即云:“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言申伯、(仲)山甫文德致升平,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②王符撰,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第198頁。
上引二例,除去作詩以頌美之明顯作意外,還可注意其特别的意義——對詩歌本身風貌的描述③《毛傳》云:“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鄭《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毛、鄭仍是曲解為政教意義,明顯不合詩義。。所謂“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説歌辭很美、曲調極好;而“穆如清風”,則是象喻詩作之淳美舒和。
綜觀上述《詩經》中詩人自道之例證,容易看出他們作詩的緣由及其目的:一為諷刺、勸諫或頌美(即漢人所謂“美”“刺”),二為抒發内心之情感。前者為表述思想意志,後者則是抒發情感。合此二者,方為詩人自道“詩言志”之完整内涵。漢儒出於經世致用之需要,單純强調《詩經》的政教意義,如清人程廷祚説:“漢儒言《詩》,不過美、刺兩端。”④程廷祚:《青溪集》,卷二《詩論十三》,《金陵叢書》本。如聞一多説:“漢人功利觀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課本。”⑤《聞一多全集》第1册《神話與詩·匡齋尺牘》之六《閒話》,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356頁。這本無可厚非,因為漢人眼中之“詩”既非同今人(詳下),他們對《詩經》性質的看法也與今人不同。漢人解《詩》全説其“美”“刺”意義,完全合理;但是,今天既然恢復了《詩經》詩歌總集的本初性質,就不應再固守漢人的《詩》解,而應做出合乎其詩集身份的理解。朱自清先生解説“詩言志”,可能就是太過膠著於漢人《詩》解了。
三、從文字訓詁角度看“詩言志”之本義
以上從先秦時期之用《詩》實踐和理論闡述、《詩經》作者自道兩個維度,明確了“詩言志”之内涵,事實上包括表達思想意志和抒發情感兩個方面含義。下面再從文字及訓詁釋義的角度,來看“詩言志”的本義究竟如何。這個考察角度之關鍵,是要弄清兩個字的本義:什麽是“詩”?“志”的内涵究竟是什麽?
何謂“詩”?似乎不是個問題。但在上古時期,詩的本義究竟如何?若以今例古,則難以得到確解。先看漢代字書、辭書的解釋:
詩,志也。(《説文解字》)
詩,之也,志之所之也。(《釋名·釋典藝》)
《説文》的釋義簡潔明快,它説“詩”就是“志”。而《釋名》則把“詩”釋為動詞,是抒發出來的“志”(這是採用《毛詩大序》的説法,詳下)。無論如何,許慎、劉熙都把“詩”解釋為“志”。再看工具書之外漢人的説法: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大序》)
《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劉歆《七略》,見《初學記》卷二一、《太平御覽》卷六〇九引)
詩者,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尚書·堯典》“詩言志”鄭玄注)
詩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志。故詩之為言志也。(《春秋説題辭》)
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户也。刻之玉板,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統玄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故詩者,持也。(《詩含神霧》)
以上材料,可分三類觀之:(1)《毛詩序》和鄭玄之説,謂心中之“志”發表出來就是“詩”,故“詩”就是“志”。這是漢人經典的説法。(2)劉歆雖謂“詩以言情”,但他明確説“情”是“信”的表徵;故劉歆所謂“情”,並非情感之義,而是“實”、“誠”,他的説法是“詩言實誠”。而實誠乃在心中,故劉歆所謂“詩以言情”者,實質即是“詩言志”也。(3)緯書的兩段文字玄奥惚恍,其實義乃在“詩之為言志也”、“詩者持也”;所謂“持”即“持守”,强調的是詩之教化功能,其思想基礎仍在“志”。總之,漢人關於“詩”的這些解釋,核心内涵都是“詩言志”,並且“詩”與“志”的含義是可以直通的。
然則,要想明白何謂“詩”,首先就需弄清楚“志”的含義。先看“志”字的寫法(以下截圖見《漢語大字典》,四川、湖北辭書出版社1986—1990年版):

這個截圖,清晰呈示了“志”字書體的演變:第一、第二行的六個字,是先秦到漢代的篆書;第三行的三個字是漢代隸化以後的寫法。由此可知,“志”字的早期寫法,乃是上止下心(止字、心字均為象形;止字是一隻脚站在地上),是個會意字,意為“停止於心”。也就是説,凡“停止於心”的(内心的)東西都是“志”。隸化之後,“志”上部的“止”字被簡化為“土”,便失去了造字之本初寓意。
再看《説文》釋“志”字:“志者,意也。”(按《説文》又云:“意,志也。察言而知意也。”“志”“意”互訓。)志(意)便是心意、心思,是心中的所思、所感、所欲者。《説文》又云“詩者,志也”,則詩也是心意、心思,是心中之所思、所感、所欲。只不過,“志”是“止於心”的心思、心意,“詩”是“發於言”的心思、心意(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至此,一個至為關鍵的問題必須要明確了:“停止於心”者,都包含什麽東西?常人皆知,心思、心意非常複雜,它可以是理念、意志、清明的思想,也可以是情感、願望、莫名的情緒。凡心中之所思、所感、所欲,均為“停止於心”的東西,便都是“志”;若發表於言辭,也便都是“詩”。因此,“詩言志”之“志”,從字源上説,實際就是詩人心中之所知、所思、所感、所願,既包括知識、思想,也當然包括情感、欲願①參見《聞一多全集》第1册《神話與詩·歌與詩》,第184—189頁。。上揭《詩經》作者們説到作詩緣由和目的的那些詩句,便包含了這兩個方面的意涵。
當然,“詩”還須有語言形式上的要求。《大雅·崧高》“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毛傳》:“肆,長也。”可以“永歌”“長言”的語句,纔是詩句。《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之説,清晰顯示了志、詩、歌三者之關係:藏於心為志,發於言為詩,永(長)其聲為歌。故古人之詩,未有不可歌者,《墨子·公孟》云“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一言以蔽之,把内心的思想或情感用有節奏韻律的可歌的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因此,上古所謂“詩”,與今天所理解的純文學的詩,在内涵上是有所不同的。與之相聯繫,對詩的特質、作用的認識也就不同——這是題外話了。
以上所述,是“詩”之本義。在上古,“詩”還有一個引伸義——“誌”。上古無“誌”字,稱呼文獻典籍都用“志”字。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杜預注:“志,古書也。”又如《國語·楚語上》“教之故志,使知廢興”韋昭注:“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既然“詩”就是“志”,而“志”又可以訓為“誌”,那麽“詩”也可以是“誌”。所以《管子·山權數》篇説:“詩,所以記物也。”賈誼《新書·道德説》云:“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戒也。”可見,“詩”又可以用來記事、論理,有“史”之義,故“詩”也可以是“史”②明乎此,則古籍中一些費解的話,就容易明白了。如《論語·雍也》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儀禮·聘禮記》云:“辭多則史。”《韓非子·難言》云:“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這裏的“史”,就都與“詩”意義相通,指虚構、文采等。錢鍾書《談藝録》云:“史必徵實,詩可鑿空。古代史與詩混,良因先民史識猶淺,不知存疑傳信,顯真别幻。號曰實録,事多虚構;想當然耳,莫須有也。述古而强以就今,傳人而借以寓己。史云乎哉,直詩而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8頁),由此也産生了“以詩為史”的觀念。漢初四家解《詩》,把《詩經》裏的許多詩,都解釋為某些歷史人物的行事或歷史事件,或以為美或以為刺,這就與他們以詩為史的觀念直接相關。
從以上簡要梳理“詩”與“志”之本義可見,上古時期“詩言志”的觀念,與今天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其一,上古時期,並没有把“詩”看作純粹是抒發個人情感的東西(詩當然可以抒情),而是與經、史等一樣,同時也被當作經世致用的東西。所以,詩既可以抒情,也可以諷諫,還可以紀事論理。在這個意義上,孔穎達《毛詩正義》“一名三訓”之説差為得之:“名為詩者,《内則》説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説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故一名而三訓也。”
其二,上古時期,也没有把“志”的涵義拘限在純粹理性的“思想意志”之狹窄義域中,它同時也包括情感、欲願在内。
總之,“詩言志”的本義,比今天任何一種理解都要寛泛:“詩”既不僅僅是抒情的(它還可以表達理性的思想意志,甚至可用以紀事、論理),“志”也不僅僅是理性的思想、意志(它還包括純粹情感,甚至知識、記憶)。也正由於此,“詩言志”纔能擔當得起中國文學“開山綱領”之資格。
結 語
今天討論中國文學的抒情與叙事傳統,作為中國文學之“開山的綱領”——“詩言志”,是繞不開的基礎話題。長期以來,以朱自清先生為代表的相當多的學者,傾向於認定“詩言志”的内涵就是“言説思想意志以求教化”,這其實是漢人的詩學思想。“詩言志”的本然内涵,需要追本溯源,重新予以釐清。本文以為,單純强調“詩言志”的政教旨趣,甚至把它與晉人陸機之“詩緣情”説對立起來的認知,既不符合文學史之事實,也不是“詩言志”的完足涵義。
上古“詩言志”觀念的思想内涵,乃是抒發情感、表述思想意志、叙事論理並包的,這在《詩經》三百五篇的實際創作中已有清晰呈現。這一内涵,正説明在上古時期,中國文學便已形成了抒情與叙事並舉共進的成熟文學傳統,滋養著後世文學的發展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