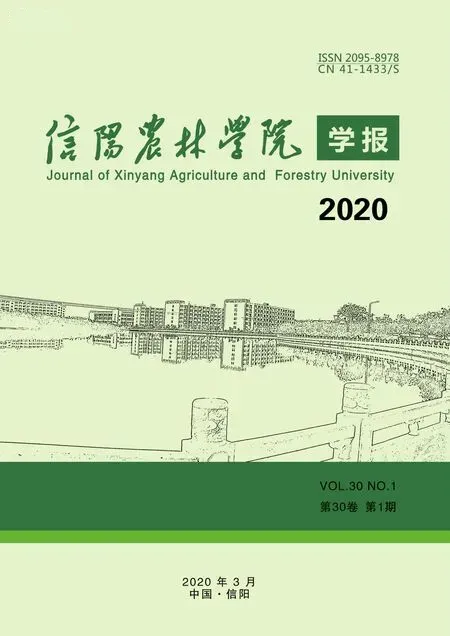论《诗经》爱情诗的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特征
李梦莹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诗经》中描写男女的爱情诗,展现了渴望拥有爱情并勇于追求爱情的男女形象,保留了人们天然质朴、自由勇敢的性格特点,有“太史初判”的放纵恣肆,有“天地元声”的朴丽清新,而较少封建道统的桎梏艰涩,亦绝无绣帐罗帏的柔糜秾艳[1]。这些爱情诗不仅是当时民风自由淳朴的写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审美形态特征,并对后代诗歌的审美形态起到了导向作用。本文将从主体意识、时间意识及物我关系三个方面对《诗经》中的爱情诗内涵进行探究,进而揭示其中国传统审美形态特征。
1 主体意识的模糊性
在《诗经》的爱情诗中,体现出了主人公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精神,但是这种相对大胆自由的创作,仍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对象性存在物[2],在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说中,人是否具有主体意识成为其关键因素。
1.1 人:主体还是附庸
在中国古代,“人”的发展具有依附性,在身体上,他们摆脱不了小农经济本身的弊端——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国家正是建立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离不开身体的自由发展,古代社会发展的根基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具有身体自由的可能性;在精神层面上,政治与文化上的加强使得社会出现了等级制度,而这种等级制度进一步影响到了人们对自我以及他人的认知。
《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了以“礼”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礼”与“乐”成为规范政治制度、礼仪、道德的重要手段,它的产生带有上层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因此占多数的下层普通群众则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诗经》的产生恰恰受到了这种制度的影响,例如,《国风·卫风·伯兮》中写道:“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从诗中可以看出造成这种相思之苦是由于丈夫因国家需要而远行出征,而这种建立在个人情感之上的家国之情才是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个人意志要服从于国家意志。另一方面,统治者通过礼乐制度来构建国家以及个人的精神文化世界,其中,宗法制的设立将男女的社会地位进行严格区分,从而影响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在《礼记·郊特牲》中写道:“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经始也”,“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等,都表明女性地位处于男性地位之下。《诗经》中的爱情诗建立在“礼”之上,这就为追求纯粹的爱情增添了束缚,就像美国批评家佩里所说的:“戴着镣铐跳舞”,对于男权社会的依附使得女性在追求爱情时受到了束缚,进而影响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实现,成了“礼”约束下的附庸。
1.2 “我思”主体的缺席
主体意识之所以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离不开“我思”主体的存在。“我思”主体地位的确立使其成了一切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反映在西方是从权威伦理转向个人伦理,在中国则意味着从亲情伦理转向个人主义伦理,而中国传统社会却呈现出亲情伦理大于个人主义伦理的特点。
《诗经》中的爱情诗便是传统思想的典型写照,从诗歌反映的内容来看,陷入爱情的青年男女难以逃脱社会伦理以及家族伦理的束缚,他们往往受外界干扰而被迫分离,其主观意愿因遭到阻挠而受挫,在《国风·郑风·将仲子》中:“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女子陷入了两难,一面是心爱的情郎,一面是至亲的父母,爱情与亲情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人伦理与亲情伦理的对抗,个人主义往往要服从于这种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亲情伦理,因此作为个体的主人公难以摆脱亲情伦理所带来的思想上的束缚。《诗经》的爱情诗显示出浓厚的亲情伦理色彩,而“我思”主体意识则处于边缘状态,并且始终难以突破这种约束,这也成为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突出特点之一。
2 时间意识的悲观性
时间内在化是人们感知时间的一种特有方式,此时时间不再是物理性质的,而是带上了个体的情感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时间内在化成为文人表达情感、抒发心绪的重要手法。以《诗经》中的爱情诗为例,诗歌借写时间的流逝来表达悲观的人生体验。
2.1 时间内在化——侵蚀感体验
《诗经》对时间的描述是借用一种物象来说明的,他们在感叹时间流逝时往往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并为其诗句注入一种悲观化色调。例如《国风·卫风·氓》中,“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借桑树的变化来写自己婚后生活的不幸和感慨。《小雅·鹿鸣之什·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采薇采薇,薇亦刚止。”借薇的生长变化来写时间的流动,从而写出了离家多年的征夫归来时的百感交集。
由于个体生命的差异,从而对时间会有不同的感知,在中国古代体现为将时间与自身的生命之感相联系,他们“受着无情力量的驱使,时常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存在”[3],由于自身主体意识的缺乏,使他们对命运产生了未知的恐惧,因而在感慨生命变化无常时,往往会对时间持一种具有侵蚀感的悲观态度,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感时惜物”的文学类型,像此后出现的“咏怀诗”“咏史诗”等便反映出中国古代借时间来表达悲观的命运之感。“时间之流中生命的脆弱性、短暂性、断裂和寂灭感被敏锐地感受到了。”[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时间意识的感知呈现出一种敏锐的伤感色调,正如孔子所感叹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后文人创作大都继承了这种感慨生命之变的时间意识。
2.2 时间的循环性展开——从过去到现在
《诗经》中所描写的对未来生活的畅想,并没有体现出对未知生活的探索与向往,而是企图回到原有的状态,体现了一种缺乏未来维度的循环时间观。从《易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就已经在建立初步的宇宙观和时间观,以八卦衍生出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同时带有“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的哲学思想,然而这种变化又处在不变之中,这种对时间循环往复的认识,一直绵延到后来的中国文化中。在《国风·邶风·击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诗中写出了在外打仗的战士与心爱之人曾立下誓言要执手到老,并渴望恢复以前的生活,但没有将思维投向一种未知的生活。
《诗经》中对未来的展望不是一种新的、从未有过的生命形式,他们试图从记忆中搜寻从前生活的种种美好并将希望寄托于过去,显示出缺乏一种大胆、无畏、不受任何限制的探索意识,并且这种愿望的满足受制于外界因素,而个人由于缺乏无所畏惧的探索精神,所以始终不能摆脱这种束缚。相反,在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文学作品却呈现出另一种风貌,英国作家笛福笔下的鲁滨逊不想受制于家庭而立志遨游世界,他摆脱了世俗中的子承父业、循规蹈矩的循环宿命,无惧外面的未知世界,敢于建立一种全新的、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这体现出现代主义话语下人对于未来的重新认知,即着眼于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并敢于为此付出实践,而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歌体现的则是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的循环时间观,从而缺乏未来时间维度。
3 物我之间的同一性
物我关系是指在审美观照中,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审美主体的情感性观照,自然物便带上了人的意识和情感。但需要思考的是,在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歌中,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下,审美客体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
3.1 移情——物我同一的审美体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有“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他认为人与物之间是互通互感的,彼此之间有一种情感的交流,物不再是简单的、生物层面的物,而是拥有了人赋予它的情感,而物本身所蕴含的情感又影响了人,这时候便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境界。
这种审美思想可以追溯到《诗经》时期,《诗经》是我国诗歌的发源地,在《诗经》的爱情诗中,这种“物我同一”的审美内涵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国风·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中把正在盛开的桃花比作刚刚嫁过来的新娘,用“灼”字既写出了桃花富有无限生机的样子,又借桃花之态来形容新娘,此时新娘与桃花之间就形成了相互映照的关系。在《小雅·鹿鸣之什·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战士刚刚出征打仗时路边杨柳依依,仿佛有无尽的不舍;而今归来时,却见雪花飘飘,仿佛映照了战士归家时悲痛的心情,“这些诗句都出现了人或自然事物,但与人的情感或要求直接明了地联系在一起,抒发诗人对它们的感受”[5],此时,人与景就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人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的交流。朱光潜曾对这种情景交融作过分析:“在聚精会神的观照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有时物的情趣随我的情趣而定,有时我的情趣也随物的姿态而定。物我交感,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互相回环震荡,全赖移情作用。”[6]这种情趣在物与我同一的关系中往复回流,其移情既是“我”对“物”的情感投注,又是“物”对“我”的审美观照。
3.2 比、兴——移情对象的具象化
“比”、“兴”是《诗经》中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法,郑众曾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比、兴的运用能让诗词产生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审美内涵,以比兴手法来寄托主人公的心理情感内容,能够实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诗经》开创了“比”、“兴”的艺术创作手法,形成了带有中国传统诗歌特点的艺术风格。
在《诗经》比兴手法的运用中,承载着主人公情感的物并非抽象的、现实中不存在的物,而是具体可见的、富有生命活力和生活气息的物。在《小雅·甫田之什·鸳鸯》中,“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诗歌运用“兴”的手法,将鸳鸯与新婚的夫妇联结起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鸳鸯成为美好爱情的象征。在《国风·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先以“桑”进行起兴,然后将“桑”的前后变化比作女子嫁人之后婚姻生活由幸福到痛苦的转变。
在《诗经》中展现的是被灌注了情感的具象的物,这种具象思维的审美形式呈现出与现代受抽象冲动影响的艺术作品完全不同的特点。沃林格指出:“移情冲动是以人与外在世界的那种圆满的具有泛神色彩的密切关联为条件的,而抽象冲动则是人由外在世界引起的巨大内心不安的产物。”[7]在中国古代诗人那里,在人与外在世界的情感交流中,往往能够从中寻找出困扰人生的解药,使其精神世界得到慰籍。
4 结语
从《诗经》中我们看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从“关关雎鸠”到“氓之蚩蚩”,写出了古代人对爱情从萌芽到破灭的认知与感悟。《诗经》在描写爱情时,也显示出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特征:主体意识的模糊性、时间意识的悲观性以及在审美观照中物与我的同一性。《诗经》作为先秦人民智慧的结晶,其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爱情诗不仅见证了先秦人民丰富的情感世界,更是传统审美思维特征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