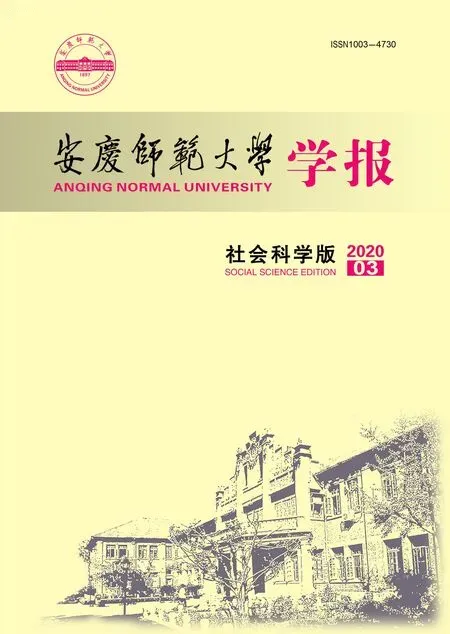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的史学价值
范宇焜
(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太原030024)
《汉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很高地位,班固在继承纪传体史书撰写方法的基础上,开创了皇朝史撰述的格局,历代“诸儒共所钻仰”[1]。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不断有学者对《汉书》进行注音和释义,约三十余家。隋唐之际,以刘臻、萧该、包恺为代表的学者以治《汉书》而闻名于世,继而有颜师古继承家学,钻研《汉书》,并吸收前人研究《汉书》的成果,撰成《汉书注》,成为“汉书学”的一代宗师。《汉书》开创了中国古代正史的撰述格局,其“汉绍尧运”的内在精神符合中国古代皇朝统治的需求,辅以其“言皆精练,事甚该密”[2]20-21的历史叙事方法,使得古代正史撰述“自尔迄今,无改斯道。”[2]20-21《汉书》在思想与技术层面的特点,使其在两宋时期成为学人研究的一个重点,产生一些“汉书学”研究专书,南宋学者王应麟的《汉艺文志考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笔者从宋代“汉书学”发展的视野,就《汉艺文志考证》的“汉书学”价值展开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复古与汉书学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庆元府(今浙江宁波)人,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宋史·儒林列传》记载王应麟少通六经,著有《深宁集》一百卷、《困学纪闻》二十卷、《诗考》五卷、《汉艺文艺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汉制考》四卷、《小学绀珠》十卷、《玉海》二百卷等,共计二十二部。王应麟非常重视对汉代制度、名物的考证,在《汉制考》中,他引用许多经书、经注。《汉书·艺文志》在《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开创中国古代正史《艺文志》的先河,著录了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众多典籍,是历史上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的这一特点为王应麟所重视,他撰写《汉艺文志考证》十卷,明确地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汉书·艺文志》中的相关内容展开考据。这使王应麟成为宋元“汉书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汉艺文志考证》在考证对象及研究方法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对其后的文献考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文化复古的倾向弥漫于整个社会,这使得王应麟本人对汉代制度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进而依托《汉书》文本展开研究,这使他有撰写《汉艺文志考证》的基础。宋代统治集团对三代制度十分向往,这反映在社会文化方面是宋代成为历史上仿制三代礼器的高峰期。两宋时期官府与民间仿制的三代青铜器据统计数量达六百余件[3],宋代仿古青铜器的制造与这一时期金石学的兴起相互促进,在学术上形成考三代典章,复三代礼制的风气[4]。宋人对三代制度的追慕,又是以考察汉代制度为主要依托的,这种倾向从王应麟所作《汉制考自序》中可窥一二。王应麟在《汉制考自序》中讲到三代礼法的发展,显现出他对三代礼法的推崇,他认为礼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三代损益,至周大备。夫子从周与从先进之言,所谓百世可知者,其法著于《春秋》”。至周平王东迁之初,由于“守古之士犹多”,还可以保证“则封建之制犹可寻也”,而到春秋时期,齐国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破坏了以往的兵制,晋国施行爰田制破坏了故有的经济制度,晋文公设执秩官主管爵秩改变了旧的官制,郑国铸造刑书而使法律制度产生变革。这些行为在王应麟看来导致了“礼几亡矣”,他虽然怀念三代礼法,但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历史变化的法则,他说:“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复乎。”[5]1-2在他看来,宋代距三代太过久远了,很多当时的情况无从知晓,而通过汉代典章制度了解三代制度就成为一条非常好的途径,他说:
汉诏令人主自亲其文,犹近于书之典诰也;郎卫执戟之用儒生,犹近于王宫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会殿以决大事,犹近于外朝之询众也;牧守有子孙,郡国有辟举,庶几建侯之旧;丞相进见,御坐为起,在舆为下,庶几敬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员,乡遂之流风遗韵亦间见焉。是之取尔,君子尚论古之人,以为汉去古未远,诸儒占毕训故之学,虽未尽识三代旧典,而以汉制证遗经,犹幸有传注在也。冕服、车旗、彝器之类,多以叔孙通礼器制度为据,其所臆度无以名之,则谓若今某物。及唐儒为疏义,又谓去汉久远,虽汉法亦不可考。盖自西晋板荡之后,见闻放失,习俗流败,汉世之名物称谓知者鲜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意义乎!此汉制之仅存于传注者不可忽、不之考也[5]3-4。
王应麟列举汉代皇帝亲自撰写诏书等事例,与古制相比较,认为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汉代诸儒“虽未尽识三代旧典”,但通过这一时期的传注,仍然可以“以汉制证遗经”。王应麟指出这条通晓三代礼法的途径后,又提到自西晋灭亡后,通晓汉代名物称谓的人十分罕见,鉴于“汉制载于史者,先儒考之详矣,其见他书者,未之考也”的情况,他撰写了《汉制考》一书。王应麟充分论述了汉代制度与三代礼法的关系,为实现追慕古风的目的,就必须考察汉代制度,而考察汉代制度自离不开研读《汉书》诸志书,在此过程中,为了尽可能还原汉代制度的样貌,就不得不对相关文献作梳理及考察。如此看来,在《汉制考》和《汉艺文志考证》成书时间尚不确切的情况下,《汉艺文志考证》有可能是王应麟汉代制度研究的“副产品”,但无论如何,《汉艺文志考证》是王应麟“汉书学”研究兴趣下的产物。
二、考证类型与方法
这里,先论《汉艺文志考证》的考证类型与方法。
《汉艺文志考证》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汉书·艺文志》展开的专门系统研究。具体来说,《汉艺文志考证》的考证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汉书·艺文志》著录典籍的考证,其二是对《汉书·艺文志》各序记载历史情况的考察。
从《汉艺文志考证》对典籍的考证来说,《汉书·艺文志》共计一万五千余字,所著录典籍近六百种。据笔者统计,《汉艺文志考证》对其中二百九十余种进行考证,典籍数量上不及《汉志》一半,但篇幅上约是《汉志》的四倍。王应麟严格按照《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典籍的顺序,将他认为需要考证的条目摘取出来,进行解释说明。对于不同类型的典籍,王应麟基本上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历代学人对《六艺略》下著录的儒家经典发论较多,为王应麟所重视。而对于《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诸略下著录的典籍,王应麟也进行了仔细的考订,这显现出他在文献考据方面的深厚素养。王应麟对《汉书·艺文志》的考证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是订正《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典籍的讹误。如《汉书·艺文志》记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6]1709在南宋嘉定十七年白鹭洲本《汉书》中,此条下已有刘敞注曰:“当作十七,计其篇数则然。”[7]但没有关于这一说法的进一步解释。王应麟从刘敞说,并展开考证,他援引《汉书·儒林列传》的记载:“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按今《仪礼》,《士礼》有《冠》、《昏》、《相见》、《丧》、《夕》、《虞》、《特牲馈食》七篇,他皆天子、诸侯、卿大夫礼。”又引南宋《仪礼》学者张淳的论断:“汉初未有《仪礼》之名,疑后汉学者见十七篇中有仪有礼,遂合而名之也。”[8]156通过王应麟的考据,订正了《汉书》中“《经》七十篇”的说法,今中华书局本《汉书》虽未录刘敞注文,但已经吸收了十七篇的观点。
其二是对著录典籍相关历史情况的考证。《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于《六艺略·春秋》下,该条目下称《史记》“十篇有录无书”。王应麟用不少笔墨考证了这一问题,《汉艺文志考证》记载:
东莱吕氏曰:“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其一曰《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其二曰《武纪》十篇,唯此篇亡。卫宏《汉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卫宏与班固同时,是时两纪俱亡,今《景纪》所以复出者,武帝特能毁其副在京师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纪》终不见者,岂非指切尤甚,虽民间亦畏祸,而不敢藏乎?其三曰《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其书具在,但前阙叙。其四曰《礼书》其叙具在,自‘礼由人起’以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乐书》,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书》,其叙具在,自书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书虽亡,然叙传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则其所载不过奏请及策书。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赞乃真太史公语也。其八曰《傅靳蒯成列传》,此其篇具在,而无刓缺者也。张晏乃谓褚先生所补,褚先生论著附见《史记》者甚多,试取一二条与此传并观之,则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传》,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书。其十曰《龟策列传》,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补尔。方班固时,东观、兰台所藏十篇,虽有录无书,正如古文尚书,两汉诸儒皆未尝见,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为伪书也。”[8]176-177
《汉书·艺文志》记载《史记》另有十篇“有录无书”,张晏在《汉书·司马迁传》注中说:“迁没之后,《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储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9]颜师古作注时除指出张晏“《兵书》”亡佚有误外,其余皆从张说,认为其中四篇是褚少孙伪作,《史记索隐》、《史记集解》也都从此说,《史记》缺佚十篇的结论似已确凿。至唐代,刘知幾认为:“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2]313宋代以前,关于《史记》“有录无书”的问题,至少存在十篇缺佚或十篇未成两种说法,但王应麟都不认同,他引用吕祖谦的说法阐明自己的观点,对张晏提及的十篇逐一考证,其结论是:一是依据卫宏《汉旧仪注》,十篇中仅有《五帝本纪》缺佚;《三王世家》虽也已不存,但其中记载的仅是奏策罢了,其赞为司马迁所作。二是《景纪》、《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傅靳蒯成列传》都是司马迁自己的手笔。三是认为《礼书》、《乐书》、《律书》中的一部分为司马迁所作,其余则“草具而未成”。四是指出《日者列传》、《龟策列传》除去“褚先生曰”的部分都是司马迁所作。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依据首先是《汉旧仪注》。其次是以“褚先生曰”的部分与司马迁的记载相比较,从褚少孙与司马迁文辞特点差距的角度进行推测。再次是以古文《尚书》的流传情况相类比,推断《史记》十篇没有亡佚的可能性。王应麟在“《太史公》”条下的考证内容皆引吕祖谦《东莱别集》中的内容[10],自己并未发论。面对前人的种种结论,吕祖谦没有实际的证据佐证其观点。但王应麟独引吕说,无疑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从《汉艺文志考证》引吕祖谦考《史记》语以后,关于《史记》十篇缺佚状况的讨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直至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都受吕祖谦和王应麟观点的影响,认为《史记》十篇是部分亡佚。近人余嘉锡专作《太史公书亡篇考》[11],对此问题有细致的分析。《汉艺文志考证》对典籍的考证内容于王应麟的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经研究者统计,在他所编类书《玉海》中,关于典籍的考证内容与《汉艺文志考证》相同或相似的达一百八十余条[12]。
其三是对《汉书·艺文志》各篇序文所记载历史情况的考察。在此过程中,王应麟注意考镜其源流。如对《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6]1707这一说法,王应麟引用《东观汉记》、《汉书》颜师古注、《汉书决疑》、《史通》等多种文献材料,列举古文《尚书》为孔子后人孔鲋所藏或孔惠所藏两种观点,对史料中记载的具体情况进行对照[8]143。王应麟对古文《尚书》的真伪并无任何怀疑,而是将注意力放在发现古文《尚书》的过程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王应麟所引《汉书决疑》的观点,源于《隋书·经籍志》中的记载,《隋书·经籍志》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 年),而颜师古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已经去世,以此可以推定,王应麟这里所引用的《决疑》非颜游秦所作,而是指南宋时王逨所撰《西汉决疑》,今《西汉决疑》已佚,《汉艺文志考证》尚录有两条《西汉决疑》的观点,也显现出《汉艺文志考证》的文献价值。
在考证《汉志》各序所记载的历史情况时,王应麟注重这些历史情况在宋代的影响,如他对《汉书·艺文志》道家小序中“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6]1736的说法展开考证:
范氏曰:“申、韩本于老子,李斯出于荀卿,学者失其渊源,其末流将无所不至。”朱文公曰:“申、韩之学浅于杨、墨。”东莱吕氏曰:“《六经》孔孟子之教,与人之公心合,故治世宗之。申、商、韩非之説与人之私情合,故末世宗之。”兼山黄氏曰:“九家之学,今存者独刑名家而止耳,佛老氏而止耳。髙者喜谈佛老,而下者或习刑名,故两家之説独存于世。秦、梁至于败亡。”苏氏曰:“自汉以来,学者虽鄙申、韩不取,然世主心悦其言,而阴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习其说,或诵言称举之,故其学至于今犹行也。”[6]233
按照王应麟所引顺序,分别引用了范祖禹、朱熹、吕祖谦、黄裳、苏轼关于法家学说的言论,这些观点无一例外都是宋代学人所作,总体来看都是承认法家学说在宋代社会中的位置,并分析法家学说能够流传并为时人接受的原因。这一历史情况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今有学者从专业研究的角度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3]。王应麟的考订使人对法家“盖出于理官”的记载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能够了解法家学说在宋代的发展状况。这显现出王应麟考证与宋代社会状况密切结合的时代感。
由以上三种考证类型来看,王应麟的考证方法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方面是王应麟大量援引他人学说,自己很少发论。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汉艺文志考证》说王应麟“所采掇亦甚博雅”[14]。王应麟所选取的材料大多出处明确,观点鲜明,这使《汉艺文志考证》的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大量对他人观点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汉艺文志考证》仅是一部学说的汇编,如《史记》亡佚十篇的问题在宋代以前就至少有两种说法,古文《尚书》的真伪宋人亦有质疑,王应麟在不同说法的基础上考证,遴选出他认为可信的观点进行辑录;又如《汉艺文志考证》和《玉海》中都有关于《子夏易传》的考证,在以材料广博著称的类书《玉海》中,关于《子夏易传》的解释收录有《唐会要》《中兴馆阁书目》《周易正义》《旧唐书·经籍志》《国史志》《孔子家語》《郡斋读书志》以及程迥、朱震等多种观点,《汉艺文志考证》中则对以上几家观点不予采纳,这无疑反映出王应麟对这一问题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是王应麟援引众家说法时,特别重视宋代学人的观点。王应麟所引广博,无论是出自史学家、文学家或是理学家,只要是他所见到的,对考证问题有意义的说法都被收录进来,所引宋代人观点出自欧阳修、司马光、邵雍、郑樵、沈括、“三苏”、陆游、程颐、程大昌、杨时、晁说之、吕祖谦、朱熹、洪迈、朱震、孙坦、叶梦得、周必大等等,共计五十余家。可以说,《汉艺文志考证》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宋代学人观点基础上的考证,所考内容不限于文献,王应麟对许多学术问题的精当考证在宋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研究范畴及其影响
在对《汉书·艺文志》进行细致梳理、考订的基础上,王应麟进而辑补,这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考证”的范畴。
王应麟将“其传记有此书而《汉志》不载者亦以类附入……凡二十六部(实二十七部)。各疏其所注于下而以‘不著录’字别之其间。”[15]在补录《汉书·艺文志》时,王应麟的态度严谨而慎重,如“《子夏易传》”条即是突出一例:
《子夏易传》不著录
《隋志》:《周易》二卷,《子夏传》残缺,梁六卷。《释文序录》:《子夏易传》三卷,卜商。《七略》云:“汉兴韩婴传。”《中经簿录》云:“丁宽作。”张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记。”《唐志》二志,今本十卷。案陆徳明《音义》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今本作“地藏水而泽,水得地而安”,但小异尔。“束帛戋戋”作“残残”。又云“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阴阳”,今本无此文,盖后人附益者多。景迂晁氏曰:“唐张弧伪作。”孙氏曰:“汉杜子夏之学。”唐司马氏曰:“《七略》有子夏传。”《十録》六卷或云韩婴,或云丁宽。《中经簿》四卷[8]132-133。
关于《子夏易传》的真伪问题,学术界至今尚存争论,学者们或认为《子夏易传》为真本,或认定是唐代张弧伪作,或认为是除张弧外的其他人伪作[16]。王应麟在补录“《子夏易传》”条时已经注意到关于其作者、卷数的多种说法,他引用唐人陆德明和北宋学者景迂晁氏(晁说之)的观点,认为《子夏易传》或存在后人附会的内容,或为唐张弧伪作。王应麟无法判断各家说法是否正确,但他补录此条,认定《子夏易传》应是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经传。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亦著录《子夏易传》,他与王应麟有着同样的疑惑:“隋、唐时止二卷,已残缺,今安得有十卷?”[17]4陈振孙同援引晁说之的说法,但他亦无法作出最终判断,“姑存之以备一家”[17]4。王应麟补录“《子夏易传》”条时,对于此书流传至宋代的真伪,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关于《子夏易传》的本来面貌,仍将是学术界继续探讨的问题。王应麟对《汉书·艺文志》典籍的补录是建立在“有”或“无”判断基础上的,他对于相关典籍真伪等问题,在广求异说的基础上并未作进一步论断。
王应麟在补录《汉书·艺文志》条目的基础上对一些典籍作辑佚。经部著作是王应麟辑佚的重点。如《汉书·艺文志》中《六艺·易》下不著录“《连山》、《归藏》”,王应麟补录此条,引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汉世盖有二易矣。”[8]130-131并指出有隋人刘炫伪作的十卷《连山》,《归藏》至当时仅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对这两部已经亡佚的易书,王应麟予以辑佚,通过《水经注》和《帝王世纪》所引内容辑出《连山》佚文两条,又通过《尔雅疏》、传注、《周易·明夷》中的记载辑出《归藏》佚文十九条。王应麟对《连山》、《归藏》的辑佚对后世学人产生直接的影响,清代学者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对这两部易书的辑佚就将王应麟的辑佚成果尽数吸收。除经书以外,王应麟补录《汉令》《神农》《石氏星经》《星传》时也对这些著作有辑佚,如他在补录“《汉令》”条后,依据《晋书·刑法志》记载解释《汉令》说:“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8]232-233进而参考《汉书》《宣帝本纪》《哀帝本纪注》《平帝本纪注》《萧望之传》《江充传注》《百官表注》等材料,辑《汉令》条令名称和具体内容共计二十九条。王应麟在辑佚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典籍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对文献的态度令人钦佩。
四、结 语
由以上论述可见,《汉艺文志考证》在研究范畴上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就《汉书·艺文志》的相关记载进行考证,二是就《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原则进行文献辑补。
王应麟有关《汉书·艺文志》的专门研究开创了目录学与考据学结合的先例,其著作中关于《汉书》的诸多考证成果为学人的汉代历史研究以及汉代史学研究提供了参考。《汉艺文志考证》作为历史上第一部以专题研究的形式系统考证、辑补史志目录的研究专书,在考据学和目录学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献考证的角度看,王应麟之后的学人对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展开考证,其考证方法为后代学人所普遍接受。明人焦竑撰《隋书经籍志纠谬》,以《隋书·经籍志》研究对象展开专门考证,这种考证方法在清代考据学家中间更加盛行。仅以《汉书·艺文志》为对象的考证,就有王仁俊《汉书艺文志考证校补》、沈钦韩《汉书艺文志疏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刘光蕡《前汉书艺文志注》等。其中,王仁俊所撰《汉书艺文志考证校补》,是直接在《汉艺文志考证》架构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考证,其标目设置,考证内容、方法都与《汉艺文志考证》有不少相同、相似之处。
从目录学发展的角度看,王应麟之后的学人对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进行补作。对于前代正史未作《艺文志》《经籍志》的情况,清代考据学家们在王应麟补录《汉书·艺文志》条目原则的基础上,对历代史志目录进行了补作,如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王仁俊《补宋书艺文志》《补梁书艺文志》《西夏艺文志》,厉鹗《补辽史经籍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等等。这都显示出《汉艺文志考证》在文献考证和目录学方面的深远影响。
王应麟作为南宋“汉书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汉书学”成就在中国古代“汉书学”发展史上有显著的地位。王应麟首次将《汉书·艺文志》作为研究对象撰成专书,是“汉书学”发展至南宋时期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