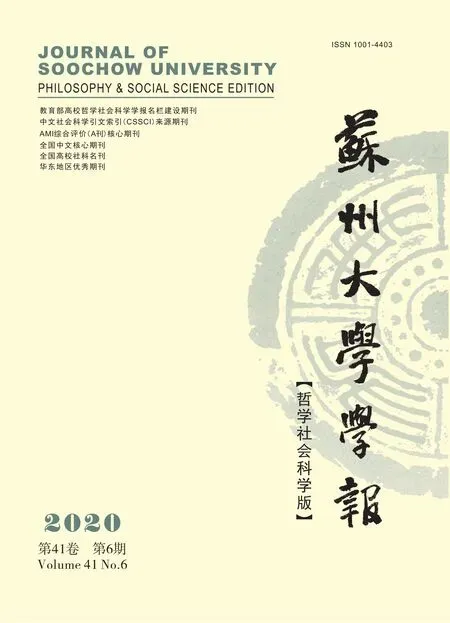“文化中国”的规范塑造
——以清代民间法中的“家法”“乡约”和“行规”为例
谢 晖
(广州大学 人权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民间法及其对“文化中国”的贡献
民间法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法学界所持续讨论的话题之一,并且从文化视角观察民间法,可以发现它并非官方法的拾遗补缺,而是承载和型塑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规范基础。之于“文化中国”的维系和发展,其作用也是一样。但究竟何谓民间法?民间法有哪些判准?民间法对“文化中国”理念之维系究竟能起到何种作用?这些仍是有待探讨的话题。
(一)什么是民间法?
虽然中国法律学术界对民间法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对于何谓民间法,学术界至今仍有并不一样的看法。如下我将分别引述梁治平和于语和的观点,以对相关研究情况略作说明,并引出我有关民间法及其判别标准的基本看法。
梁治平认为:
民间法具有极其多样的形态,它们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形诸文字,也可能口耳相传;它们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相沿成习;或者有明确的规则,或者更多表现为富有弹性的规范;其实施可能由特定的一些人负责,也可能依靠公共舆论和某种微妙的心理机制……依其形态、功用、产生途径及效力范围等综合因素,大体可以分为民族法、宗族法、宗教法、行会法、帮会法和习惯法几类。[1]36
于语和则指出:
民间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通过对成员进行各种训练、传授、教育和影响等方式,是社会文化延续和传递的过程,是一个世代之间不断继承、创造、再继承、再创造的延绵不断的超越和隔离。通过传承,保持了民间法的地域性、民族性,实现和保持了民间法的相对稳定。[2]40
上述两种对民间法的界定,各有千秋。前者侧重于从外延视角界定民间法,因此,它让读者能概括地了解民间法的形成机制、表现形式、作用方式,从中发现民间法主要作为自生自发秩序的存在类型。后者也没有明确地给民间法以内涵界定,只是更为详尽地展示了民间法形成和传承的一般原理。这种论述,大体反映了当代中国民间法研究的现状:人们对这一概念的描述性研究居多,但对其定性化的概念性研究尚不足。那么,究竟什么是民间法?
民间法是与官方法相对的规范事实,它是一定社群或区域的人们在交往行为中自发产生或者自觉制定,在官方法之外,通过人们自觉的规范意识或特定社会主体之强制,用以调整人们交往关系的规范事实。透过这一概念,可以发现其如下要点:
第一,非正式规范事实——民间法的本质。民间法与官方法相对,是官方法之外的规范(制度)事实。无论是民间法还是官方法,都是制度事实。制度事实是与物质(经济)事实、精神事实相对的社会事实。它是指经由一定的普遍规范所约定或调整的社会事实。与物质事实和精神事实相比较,制度事实总是逻辑在后的,而前两者总是逻辑在先的。制度事实总是建立在一定物质事实和精神事实基础上的,在这一层面,它是物质事实和精神事实的规范桥架和沟通机制。因此,制度事实就是物质事实和精神事实的规范提升。因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区别,制度事实也可依样二分。其中民间法及其秩序大致属于非正式制度事实,国家法则大致属于正式制度事实。
第二,自发自觉相间的生成机制——民间法的产生。民间法的生成,一方面是人们在交往行为中,通过长期的交涉、磨合、总结、提升而自发地产生的。被称为习惯法的民间法,就基本是人们交往行为中自发的结果。
一般认为,习惯法者,系社会惯行而无背于公序良俗并为一般公众心理所承认,且经国家公权力认许的不成文法。[3]54
另一方面,随着一定区域或族群的人们对规则自觉意识的提升,民间法也会像官方法那样,经由“社会权力”(1)“社会权力”这一概念,尽管在西方学者如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及众多的人类学家那里都曾论述过,但在中国,系统论述这一概念的是郭道晖先生。其论证的基本根据是现代社会的“权力多元化”导致“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与之并存的还有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有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由各国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的超国家权力,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社会权力”(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尽管我仍愿意将这种力量归于“社会组织权利”的范畴,但毫无疑问,它之于国家权力而言是权利,之于参与其中的公民而言,又是权力,因此,在性质上,其明显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性。主体的制定,形成成文的民间法规范。这在现代民间社会中尤为常见,如乡规民约、教法教规、社区公约、行会规程、协会章程等。这说明,民间法不但不同于完全经由国家权力主体制定的官方成文法,也不同于完全藉由人们在交往行为中自发形成的习惯法。民间法包括但又不唯习惯法。
第三,自觉与强制相间——民间法的运行动力。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日常生活与法律规范的须臾不可分,因此,传统理论对官方法运行之权力强制的强调,已然有所松动。国家强制力观念在法律运行的事实上呈现出明显“弱化”的情形。(2)参见刘星:《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变革》,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3期,第11页。相应地,公民自觉自愿的法律意识在官方法的实现中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作用。就此而言,似乎上述民间法的运行动力和如今官方法的运行保障之间差别不大。但细究之下,官方法如果一旦离开权力后盾和强制惩罚,则成为没有栅栏的田园,任由人们出入。特别对一个大国而言,陌生人间固有的自律缺陷,必须预备权力强制,并且把其作为法律主要的保障机制,否则,法律就是被拔掉牙齿的老虎。民间法则不同,尽管它也需要社会团体的强制力作保障,但由于其作用范围主要是小型社会和熟人交往,因此,相较而言,人们自觉自愿的规范意识对保障其实施更加现实。可以这样说:官方法实施的保障,以权力强制为主,人们自觉自愿的法律意识为辅;相反,民间法的实施,却以人们自觉自愿的规范意识为主,社会团体的强制力为辅。
第四,调整一定社区内人们的交往行为——民间法的功能。官方法和民间法都要用来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但两者对人们交往行为的规范范围却不同。官方法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其某一地区统一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而民间法却与之不同,它只作用于特定的社区。这些社区的形成,或因族群,或因地域,或因行业,或因团体,甚至或因家族。但无论如何,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较,其更多关乎的是熟人社会,调整的是熟人关系,是国家法律难以进入之地。因此,它虽然和国家法律一样,调整人们交往的社会关系,但就其内容而言,民间法调整的更多是一定社区的内部关系和熟人关系,而国家法所调整的,却每每是跨社群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换言之,民间法所调整的领域,国家法一定会涉及;但国家法调整的领域,民间法却未必能够涉及。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法和官方法共同规范着人类交往秩序:“故人间秩序者,国家法与民间法相须而成也。”[4]2
当然,强调民间法与官方法的如上区别,不是说它和官方法没有联系。反之,一方面,民间法每每是官方法得以制定的规范基础,国家法中经常会记载着民间法的内容。(3)例如,在我看来,古代中国的法律事实上表现为四种类型,在这四种类型的法律中,皆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记载和表达着中国古老、悠久的习惯。具体说来,这四种类型的法律分别是:(1)宪,是规定皇权国家之天人关系,各国家机构之间、央地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以及个国家机构内部关系的法律,如《尧典》《舜典》《洪范》等。在宪中所存有的惯例,如“祖宗之制”“嫡长子继承”等,都具有明显的藉由民间法生成的特征。(2)行,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具体用来规范各国家机构职权、职责及其社会管理权限的法律,如《唐六典》、历朝《会要》等。由于“政”所涉及的是国家日常事务的规范管理,因此,其中所牵涉并规范的日常习惯更不难想见。(3)礼,是规定人民根据一定的身份而展开其日常交往的规范。古人云:治之经,礼与刑。史传“周公制礼”,至今还传有“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这里的礼,特别是其中的“礼俗”,已经含有大量的习惯法或民间法的内容。搁在今天,则完全可以说礼就是从古至今所流传的中国传统的民事习惯和民间与民间、民间与官方,以及官方与官方所交往的民间习惯(只是后两者通常被纳入“政”的范畴)。(4)刑,乃是对违背上述法律规定,却无法在上述法律规定内部予以制裁时,所规定的专门的、统一的处罚前提和处罚标准。众所周知,古代中国刑法十分发达,流传至今的法律,大多为刑法,以至于有学者说:“除了刑法史的法制史,便觉空洞无物。”(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序》,中国法制出版2005年版,第4页)但即便由国家严格制定的刑法,也是“出礼入刑”观念的产物,也不排斥民间法的进入,反而有大量民间法被纳入其中。这种记载,即经由官方法的认可而把民间法纳入其中。另一方面,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律,在失去了其作为大传统的条件后,部分内容也会沉淀为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法——例如后文将要略微提及的彩礼。厘清了民间法概念的如上要点及其与官方法的具体区别与联系,下文我将进一步分析判别民间法的基本标准问题。
(二)民间法的基本判准
实践中,民间法经常以多元形式存在,有族群的,有社团的,有行业的,有宗教的,有家族的,还有特定地方的。即使在同一族群、同类社团中,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具体社团内,仍会有并不相同的民间法。这为民间法在一个统一国家内适用的区别造成了困难。固然,民间法不需经由国家的识别,照例在事实上发挥着其在一定族群、社区、团体、宗教、家族和地区内应有的规范作用。但这样的规范作用,在我看来更适宜人类学和社会学去研究。法学研究者之关注民间法,主要目的在于寻求民间法在正式制度,特别在司法中应有的作用。这样一来,在多元的民间法中,站在国家法立场上如何判别民间法,就是值得关注的话题。我认为,如下四个方面,是判别民间法的基本标准。
(1)获得特定时空内主体的普遍承认。官方法之外的社会规范,无论是自发地形成的,还是自觉地制定的,其要获得实际的社会效力,必须被特定时空的主体所普遍认可或承认。这既是民间法在该时空范围内普遍有效的“道德合法性”基础,也是其发挥实际效力的前提——即“可接受性”(4)“可接受性”是一个美学概念(参见谭学纯等:《接受修辞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法学上,可接受性既指作为“言说”的规范或立法被其“受众”——运用者的接受活动;也指人们运用这种规范后,社会主体对此所持的普遍承认的态度。前提。具备这一前提,则一种社会规范就具有成为民间法的可能;不具有这一前提,则民间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此意义上,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被其主体所普遍承认或普遍接受,乃是一种规范成为民间法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意味着,并不是官方法之外的所有社会规范都是民间法。特别是那些只对具体个人或极少量的人有效的规范,或者对一定团体内部少数人所遵从的规范,不能被判定为民间法。
(2)对特定时空中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官方法也罢,民间法也罢,其规范功能的技术根据,是在规范体系中能给人们分配权利和义务。或以为,权利和义务概念乃是现代法学的产物。在前现代的法律中,并无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分配。或者即便有之,也是所谓义务本位的法律。(5)如张文显就认为前资本主义法是“义务本位法”(参见张文显:《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我并不认同该说法,事实上,人们只要有交往,并且在规范地交往,该规范中就必然含有权利和义务分配的内容。哪怕是不少初民社会人们习以为常的规则,都是如此。(6)参见[美]霍贝尔:《原始人的法——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严存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3-233页。在中国以民谚形式表达的民间规范中,诸如“人情一匹马,买卖争分毫”“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银货两讫,童叟无欺”等等,就明显有权利和义务分配的特征,是人们交往行为中权利和义务分配的规范凭据。遍布中国各地的古代契约(7)中国古代的契约十分发达。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万民约”和“邦国约”的事实(参见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共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另外,杜正贞就以《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与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为书名,深入研究镶嵌在古代契约中的权利问题。,就典型地表现着古代中国在事实上对权利和义务的格外重视。能够给交往行为中的人们分配权利和义务,乃是一种社会规范能够作为民间法的技术基础。没有这一技术基础,一种规范就只能被称为宣告,而不能称为法——无论是官方法,还是民间法。
(3)在一定的时空内具有现实活动性。民间规范,既有历史上曾经遗留下来的,也有现实中根据人们的交往行为的实际要求而新生的。历史上曾经流行的规范,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发思古之幽情的谈资,那么,它就不具有现实活动性,就不能作为民间法来运用。进而言之,就不能作为人们交往行为的民间法凭据。可见,哪怕一种规范来自久远的历史传统,只要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仍在运用之,它就可能成为民间法。例如春节传统及其习惯,之于中国人民而言,尽管相当悠久,但至今其习惯规范仍活跃在人们的交往行为中,以至于国家不得不把其作为法定假日。再如彩礼,曾经是古代中国婚姻缔结的法定内容。但时移世易,如今已沉淀为中国民间活跃的小传统。这尤其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更为明显。
(4)纠纷解决中的根据或参照。一种稳定、普遍的规范,既可以是人们交往的行动指南,也可以是人们在交往中避免走入歧途的预防机制,还可以是人们交往行为的基本预期,当然,更可以是一旦产生纠纷,人们依据之解决的规范准则。如果人们之间产生了纠纷,不能据之或参照之解决,就不是民间法。因此,一种规范要能成为民间法,必须对人们纠纷之解决有所帮助。即它既要能够直接作为特定时空中民间解决纠纷的根据——这在当今中国,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村社,无论是汉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中,都普遍存在。甚至在相关的纠纷处理中,官方法反倒是退居其次的。尽管不少民间纠纷的处理,其所根据的规则未必完全符合官方法(8)例如在贵州苗侗地区较为普遍地存在的对违背村寨传统习惯的行为,如盗窃、失火等,采取罚“三个100”或“三个罚120”的纠纷解决机制(参见徐晓光:《从苗族“罚3个100”等看习惯法在村寨社会的功能》,载《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9-15页;《罚3个120的适用地域及适应性变化——作为对黔东南苗族地区罚3个100的补充调查》,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67-71页)。再如在藏族地区人们普遍认可的“赔命价”习惯法(参见淡乐蓉:《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甚至完全违背官方法(9)例如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出嫁女继承权纠纷问题,特别是农村出嫁女土地纠纷的解决问题,实际上延续着中国千古年以来执行的“出嫁从夫”原则,按照“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这样的理念来处理,完全违背现行法律有关“男女平等”的宣告(参见何燕侠:《女性财产继承权的历史考察——法原理与法习惯方面的纠葛》,载《大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37-40页;张冠男:《出嫁女儿的继承权利与赡养义务》,载《西部学刊》2018年第1期,第17-20页)。,但依其处理在实践中却比官方法更为有效。当然,民间法之于纠纷处理,不仅涉及民间纠纷处理,而且也能作用于官方的司法处理。在这方面,现代不少国家在立法上,特别是在民事立法上已经授权司法者运用、参照习惯以处理纠纷。(10)如《瑞士民法典》在其第1条、我国“台湾民法典”在其第1、2条、《越南民法典》在其第3条皆有“无法律,从习惯”的类似规定。日本虽未在其《民法典》上对此有明确规定,但在其《商法典》上有专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0条明令:“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如上四个判准,对民间法的确定而言是相互关照、缺一不可的要素。缺少任何一个方面,意味着相关规范尽管在实践中存在,但不能构成民间法。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具有现实的规范作用,但它不能作为民间法。特别是在处理人们因为交往行为中涉及权利与义务的纠纷时,其既不能作为民间纠纷解决的根据,也不能作为官方纠纷解决(司法)之参照。
(三)民间法与“文化中国”的内关联性
诚如前文所述,文化尽管有其与政治、经济等相对的意涵,但就其广义而言,人类有意识构建的所有事物,无论它是自发倾向的,还是自觉倾向的,都是文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的文化建构,乃是物质文化、精神-道德文化和制度文化共同拱卫而成的。其中制度文化——无论其表现为非正式制度,还是正式制度,都是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般性、可通约性问题的规范化提升,并藉此规范化,教化和规训人们的行为以此模式而展开。可见,制度文化是真正动态的文化——只要一种制度曾经、当下或者未来是活着的。
因此,我们谈希腊文化,所谈的不止是其戏曲、诗歌、哲学,也是其独特的城邦制度;而谈罗马文化,其诗歌、哲学可以忽略不计,但不能不谈及彪炳史册的罗马法。谈英美国家,可以津津乐道于他们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学,但如果不谈及英美法系,不谈及通过司法智慧把其小传统、习惯、日常做法和大传统勾连汇通的方式,自然会逊色不少。同样,谈欧陆国家,除了诗歌、音乐、小说以及伟大的哲学之外,更会谈及何以保障这些得以发达的制度缘由,以及这种制度是如何由贸易习惯、商人法、城邦法、宗教法、社团法逐渐发扬光大,而蔚为大观,并在如今影响了大半个地球的“大陆法系”的。可见,“文化中国”的理念和命题固然与民间或官方的制度息息相关,但“文化欧洲”“文化英美”……如果有这样的理念和事实的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过中国究竟是中国。在这里,“文化中国”被赋予了根本意义和统领全局的意义。正如在欧洲,制度具有这种根本或统领全局的意义一样。即便连法治国这样的问题,在一位欧美人看来天经地义应是制度或制度文化层面的话题,但在中国,却很容易被装置在文化的容器中加以解释。所以在中国,任何一种事物,无论它是物质的还是制度的,只有符合文化的要求才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即道德合法性。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5]“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6]3等不但为人们所理解,甚至天经地义。制度不是用来结构和型塑文化的,而是记载、发扬和光大文化的。无论是民间法还是官方法,根据其推进的治理只是执行文化的使命而已。我把这种情形,称为“文化治国”(11)参见谢晖:《论文化治国与制度(法律)治国》,载《领导者(香港)》2016年第4期。。这种情形,不仅是官方法的使命,而且也是民间法的使命。
自宋代以来,在中国有广泛影响的蓝田“吕氏乡约”,被公认为是民间法成文化的典范,但其内容则典型地表达着执行“文化中国”之使命的角色。它的基本目的,是实现人们按照文化的要求,心心相印,在行为上做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成、患难相恤”这样一种明显具有文化意义的目的。这也正是自从该成文“乡约”产生以来,在南宋、元、明、清等历朝被朱熹、方孝孺、王阳明、吕坤、章璜、刘宗周、陆世仪、陆陇其、于成龙、汤斌、张伯行等学富五车的官员们特别重视,并或者在成文方面不断完善、重新订定新“乡约”,或者把既有“乡约”努力推向其治下地方之缘由。如此一来,既能够实现一方秩序的井然有序、长治久安,也可以通达士大夫心目中那份抹不去的文化情怀,立功立德,相得益彰,地方与国家互为支持,制度文化,表里如一。“文化中国”之使命,因之而彰显,“文化中国”之践行,因之而展开。所以,我赞同一位学者在论述乡规民约时的如下观点:
传统乡规民约……立约目的在于正风厚俗、以禁非为、以全良善、和息止讼、以儆愚顽、亲爱和睦、消除怨恨、守望相助、相劝相规、相交相恤、互为扶持、以讲律法、不违法律,呈现出中华德礼法制文化的独特精神气质。传统乡规民约以‘公共’为立约原则,具有乡村社会契约性质。无论经由何种方式产生的乡规民约,均始终坚持‘共议’‘公议’‘商定’‘公定’的‘公共’性原则……传统乡规民约接通国家‘德礼法制’与民间社会规约,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做到‘有规而循’。所谓‘朝廷有法律,乡党有禁条’,‘法律维持天下,禁约严束一方’,‘国有律法,民有乡规’等,正是对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之关系以及乡规民约的性质及其自治功能的高度概括。[7]
如上种种,虽然把范围限定在“乡规民约”,但其不正一般性地表达了民间法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吗?不正一般性地说明了中国古代民间法和“文化中国”的内在关联性吗?也不正一般性地廓清了民间法以规范形式在基层社会夯筑坚实文化地基的事实吗?
通过如上对民间法之含义、特征、判准及其与“文化中国”关系的描述,下文我将有选择性地通过对清代一些民间法——“家法”“乡约”和“行规”的描述与探讨,继续论列清代民间法对“文化中国”的表达和担当。
二、清代民间法之“文化中国”表达和担当
我们知道,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朝代。在中国“正统”的历史观看来,它是由汉族之外的“异族”所建立的一个朝代,但站在“文化中国”的立场,它又相当模范地循守并在一定程度上光大着“文化中国”的传统内容。因此,至今学界,包括法学界对清代问题的研究便格外重视。兼之“五四”以后中国固有传统的日渐失落,清代又去当代时程未远,文献档案更为齐备,因此,对它的学术研究就格外活跃。其中有关清代法律的研究,在中外法学和历史学界多有深入的成果(12)例如[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S.斯普林克尔:《清代法制导论——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张守东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黄宗智:《清代的法制、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高道蕴、高鸿钧:《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忠民:《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有关清代习惯法的研究也深受人们的关注(13)仅中国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笔者所掌握就要有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孙丽娟:《清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眭鸿明:《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张渝:《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规则与秩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谈萧:《中国商会治理规则变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与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等等。。但是,清代民间法如所有时代的民间法一样,是一个相当多元化的存在:它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有官方认可的,也有官方不认可的;有家族、宗族、宗教、族群的,也有社团、财团、行会、地方的;有完全在历史长河中自发地形成的,也有通过一定的组织自觉地制定的……凡此种种,皆为清代民间法的类型化处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人们只能一般性地选取一个标准,即民间法适用的主体之标准,对清代民间法做类型化处理。我不就全清代民间法而是有选择地就清代的三类民间法——“家法”“乡约”“行规”予以介绍,并进而探究其对“文化中国”的作用。
(一)家国二分背景下的“家法(族规)”及其对“文化中国”的表达和担当
在古代中国的治理结构体系中,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家国同构”是人们探究古代中国家、国关系时的基本结论。孟子强调:“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4)《孟子·离娄上》。因此,在这里,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是“修、齐、治、平”。其中“修身”,可谓个体自治;“齐家”,可谓家族自治;“治国”“平天下”,可谓把“修身”“齐家”的志业推向国家和天下(15)这种观点,大半被归结为“家族国家论”。有些学者并不赞同这种对古代中国国家性质的解说,强调“通过‘家’论述国家的方法以及能以‘家’来阐明‘国家’的立场,都是本书所不取的。毋宁说,从‘家’和国家各个独立、特殊的职能和作用出发,努力区别和划定两者的范畴,这才是本书的着眼点。”(尾形勇:《古代中国的“家”和国家·序言》,张鹤泉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页)。——从而实现所谓“家国天下”。
中国的国家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只能放在‘家国天下’的谱系中来理解,而且它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华民族’又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不是只有一种,中原王朝与边疆王朝所建构的国家形态,一个侧重普世天下文明,另一个侧重多民族、多宗教的王权大一统……[8]
且不论人们对古代中国的家与国家持有何种立场和解释,在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家族治理从来都是其中重要内容。这是由于家族本身的相对自治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在《唐律疏议》中,就明令“刑罚不可驰于国,笞捶不得废于家”[6]1。这决定了在古代中国,有明确的皇权和族权(父权)的两分。因此,治家犹如治天下,一家不治,何以天下为?正是这种相对自治的“家”观念和事实,导致家法族规在古代中国的长盛不衰。
即便在“异族”统治的清代,被称为宗(家)族法的家法族规仍然很盛行,成为其实施“双重治理体制”(16)这种治理是指:“‘征服型’王朝”创制了“一种不同于纯中原式的国家建构模式。它不仅能在作为帝国经济基础的汉地社会和统治者的‘祖宗根本之地’之间保持着平衡,而且为进一步将其他各种非汉人群的活动地域纳入有效治理,提供了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样化、可能性因而也更能持久的一种制度框架。”(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载葛剑雄、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的重要治理规范。要对清代的家族法予以系统论述,在有限的篇幅里显然是力所不逮的。因此,我将在下文主要借助范玉伟在《清代安徽家族法研究》(17)对此作专门研究的还有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所提供的一些例证,仅就家法族规所涉及的宗法伦常方面的规定(此外,在家法族规中,通常还会规定诸如家族日常经济事务的管理、伦常纲纪的维系、礼尚往来的规范以及违反家法族规的处置等)予以简要说明。
清代的家法族规,多载于“族谱”中,如安徽的《歙托山程氏族谱》就达5卷,《合肥李氏宗谱》更多达22卷。在族谱中,除了一祖脉传(这本身具有“师法祖宗”“承接血缘”、防范错乱、团结友爱的规范意义(18)如“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之有祖,犹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歙托山程氏族谱》))的前后记载之外,更常见的,则是对这一祖族人群如何维系忠义(19)如“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婺源《王氏族谱》)。、孝悌(20)如“为子者必孝顺以奉其亲,为父者必慈祥以教其子。为兄弟者必友爱以笃其手足之情,为夫妇者必恭敬以尽宾对之礼,毋徇私乖义,毋枉法犯宪,毋信妇言以间和气,毋学博弈以废光阴,毋耽酒色以乱德性,凡此数端务宜深紧。”(《婺源长溪余氏宗谱·祖训》)。、婚姻(21)如“婚者,人道之始风化之源,上以乘宗祧,下以接宗支,论年次之,断不可以财色取。”(《金紫方氏族谱·家规》)与此同时,在族谱中大都规定同姓、良贱不婚等婚姻禁忌内容、婚姻成立条件和夫妇在家庭中应各守其位等内容。详见范玉伟:《清代安徽家族法研究》,湘潭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继承⑦(22)⑦如“嫡长之重,所以别支庶也。庶为子兄,嫡子为弟,而必先列嫡长于前而后以次递列者,庶不先嫡,正宗祧也”(《歙县桂溪项氏族谱》)。的规定。通过这些规定,人们不难理解家法族规在维系一个家庭或家族中的基本意义。如果说“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家国两分”则是实现其“家国同构”的前提。因此,家有家(族)长,国有国君;家有“家父权”,国有君权。不仅如此,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典)”。因此,在一些文献中,人们把“家规”和“国典”相并提。其中有一份族谱比较经典地写道:
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典也,国有典则赏罚以饬臣民,家有规寓劝惩以训子弟,其事殊,其理一也。⑧(23)⑧《仙源东溪项氏族谱·卷一·祠规引》。
正是家法族规在最基层社会筑牢了中国的文化根基,因此,“文化中国”历百代而不衰,在王朝更迭过程中,不论是中原王朝登基,还是边疆王朝上位,人们(不仅是士人)更关注的是“文化中国”的根基是否存留,而不是哪个民族掌握权柄,或者建立了什么样的社稷江山,甚至也不大在乎开疆拓土的百世之功。一个朝代,只要能够坚守“文化中国”的“命根”,哪怕它是“异族”统治(如清代),不论社稷如何轮转(无论汉唐),也无计疆土广袤偏狭(如南宋),人们最终都能接受并支持之。但一旦“文化中国”的“命根”失守,从“士人”到普通民众,就失去了基本的文化缅怀、生活和坚守。国家因之而失魂,因之而丧失合法性。此种情形,在当下中国各阶层人士中依然如故,并且对“文化中国”之重建也得到了当下中国官方重视、鼓励和支持。⑨(24)⑨中国当下在全国范围内所展开的弘扬“家风”“家训”“家教”的行动,虽然具有当局擅长社会动员的一以贯之的特点,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文化中国”的古老传统及重建之的社会需求,因之,更因人们喜闻乐见而被接受。可见“家法”在基层社会对“文化中国”的强大型塑功能。
(二)城乡两分背景下的“乡约”及其对“文化中国”的表达和担当
乡约,在当下中国统称为“乡规民约”。和家法相较,古代中国的乡约产生要晚一些。在《中国古代民间规约》⑩(25)⑩该书共分四册,杨一凡、刘笃才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出版。一书中,作者遍览群籍,所搜集编入的最早的乡约是唐代的《敦煌社邑立社条件》。这也大体能说明即便之前中国有乡约,但其成文的流传尚不足考。可以初步认为,古代中国的乡约发端于唐,成熟于宋(26)宋代最著名的乡约为《吕氏蓝田乡约》,由“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于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所订定并推行的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这份乡约,不但对古代中国各地的乡约具有示范意义,而且对周边彼时的朝贡国家,今天的韩国、越南等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当下韩国和越南的乡村地区,对其秩序维系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参见徐元宇:《朝鲜乡约的福利行政功能及其意义》,张小平译,载《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Dao rift Uc:《越南古代和现代乡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纪建文译.载《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发扬光大于明。在清朝,乡约则日渐被官方化。就内容与功能而言,乡约不同于家法。可以说,家法族规是血缘(姻缘)本位的,因此,调整的肯定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可简称为“亲本位”的民间法。而乡约则是地(业)缘本位的,可简称为“业本位”的民间法。
有些学者把乡约区分为广、狭两义:
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村民间规约构成了古代民间规约的主体,所以人们习惯上将其称为乡规民约。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在外延上比乡规民约为宽。因为在古代中国……除了乡村的民间规约外,还存在大量文人会社的规约、城镇的工商行规和其他民间规约。[9]135-147
由于本文的容量所限,对清代民间法中的因相对的社会自治所致的帮会法、相对的行业自治所致的行会法、相对的宗教自治所致的宗教法以及相对的族群自治所致的民族法等不能一一涉及,因此,这里借取广义的乡约概念,并以清代乡约为例来论证本文想表达的主题。
有清一代,一方面,由于王朝统治者系外来“异族”,因此,要实现其“双重治理体制”的统治,就不仅要熟悉历史上中原王朝统治国家的大传统,而且要熟悉中原以汉族为主的民众进行自治或基层治理的小传统。如此一来,乡约这种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方式就被纳入其治理天下的总体体系中。另一方面,乡约实践已通行数百、成千年之久,业已成为相当成熟的统治经验,因此,急于寻求有效统治方法和经验的“异族”统治者,顺理成章地把其纳入统治规范体系中,并使乡约成为清代正式制度的重要内容。但即使如此,也存在着与乡约相对的“乡规”。对此,有学者的研究指出:
到了清代,乡约已不再是民间组织,而彻底变成了官方法律体制下的一种正式制度。根据官方的规定,每个乡村都普遍设有乡约所,开展讲乡约的活动,内容则是宣读讲解圣谕广训及钦定律条。随着乡村自治组织演变为基层政权,乡约还用以称呼农村基层政权首领,不过这时他们已经沦落为负责替官府收取钱粮、任凭官吏驱使的职役。这时具有民间规约性质的是以碑刻形式出现的乡规。
人们往往把乡约、乡规混为一谈。其实至少在清代,乡约和乡规有很大不同……清代的乡约是国家正式制度……而乡规是村落居民集体讨论制定的民间规约。(27)刘笃才:《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引论》,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乡约的这种官办化、国家化,在实践中呈现为保甲化(参见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240页;段自成:《清代前期的乡约》,载《南都学刊》1996年第5期;段自成:《论清代北方乡约和保甲的关系》,载《兰州学刊》2006年第3期;段自成:《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载《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以及段自成:《清代北方官办乡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尽管在清代乡约与乡规是二分的事物,但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仍以乡约指称这两者。以下我分别引述官方化的一份“乡约”之部分内容和民间性的一份“社约”之部分内容,以进一步申论无论是官方化的“乡约”,还是民间性的“社约”,之于“文化中国”之维系而言,殊途同归,相得益彰。
第一份是张伯行制定的《申饬乡约保甲示》。其开宗明义强调:
为申饬乡约保甲之常规,以正风俗以靖地方事,照得自古治道,必使风俗醇和,地方宁谧,无不以乡约保甲为急务者。一主于劝善,以化导为先;一主于惩恶,以禁诘为重。名虽分,而实则同也。约束一乡以有物,有则保护各甲以无灾无害。总欲尔民迁善违罪,趋吉避凶,岂二道哉。有子谓:为人孝弟,则无犯上作乱。孟子谓:逸居无教,近于禽兽。又囊括于周礼比闾族党之意,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此可见乡约保甲之教民,原互相为益,所以重人道,而不坠于禽兽也。孝弟忠信节义廉耻,人道之纲维,忤逆斗狠奸盗诈伪禽兽之举动。人谁肯限于禽兽,而不为人乎……讲乡约,可以跻仁寿而咏太平矣。乃认真勤讲者,能有几人。或仍视乡约为具文,未尝识官民之共赖。抑且视保甲为故套,未尝揆经纬之相兼。逢朔望,一讲乡约,宣三两条,而即回衙矣。见上司一严保甲,紧两三次,而似结案矣。如此而欲反薄归厚弭盗息民,又安可得乎。(28)[清]张伯行:《申饬乡约保甲示》。张伯行(1651—1725),系清代康熙年间大臣,理学家。除了制定前述乡约外,他还制定了《社仓条约十六条》,皆得保留;他对学规也也颇用心,著有《学规类编》一书。
第二份是孙衣言制定的《诒善祠塾规约》,其第6—12条分别规定:
6.在塾子弟以恂恂有礼为贵,每日上学向先生一揖,幼者各向长者一揖。晚间下学亦然。先生有友来塾,亦各作一揖致敬。7.在塾子弟不许吸烟饮酒,不许聚处谈笑,不许互相谐谑,不许跛倚箕踞,不许私自出塾,不许涂画屋壁,不许折损花木。违者均于祠堂罚跪一枝香时,以示惩儆。其傲慢不遵教训者,罚跪三次,不听教,召其父兄来塾领归,俟知 悔改,再令上学。8.在塾生徒诵读书籍,各自携带。本塾所藏止应检查之用,用时可向管书人借阅,不得私行携出塾外,以致污损残缺。违者罚于祠堂跪一枝香时,并赔书籍。9.本塾以每年正月初十前后开馆,十二月二十日前后散学。端午、中秋各节给假一日,平时生徒非家有大事,不得任意告假。10.在塾生徒每逢节到,每人给馆童奖钱一百文,乡居赴考者赏给馆童每节二百文。11.塾中冬月裱糊窗户,夏月支搭凉棚,由祠产公款中支用。12.塾中每年用度于产款中酌量支应,由祠产值年者司其事,年终应将收支清册呈报房长。(29)[清]孙衣言:《诒善祠塾规约》(公元1875年12月订)。孙衣言(1815—1894),既是清朝道光、光绪年间的官员,也是一位相当有成就的藏书家和管理家。尤其他对规范管理格外重视,纵在今天中国,也颇值得借鉴。其在管理中除亲自制定前述规约外,还订有《藏书规约》《诒善试馆规约》《诒善祠公产规约》等,皆流传至今。
从如上两则引证资料均见,无论是官方化的“乡约”,还是民间性的“社约”,都明显地以承载和维系中国文化传统为使命,或者自觉地遵循“文化中国”的使命。
先看前引官方化的“乡约”对“文化中国”作用。“自古治道,必使风俗醇和,地方宁谧”,以官家手段,自觉贯彻古代中国官民共守的文化理念。其所开列的16条具体规范(30)参见牛铭实:《中国历代乡规民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186页。特别是其中第七条,至今看来,仍意义非凡:“禁鱼肉富翁。富是一方元气……此外富民,无论大小,原皆经营劳苦之所致……有司不许因事苛索,地方不许生端陷害。若彼果自犯法,则有应得之告,应得之罪,夫复何辞。然乡约长、保甲长诸人,还要为彼调停,责其不是而止其告者,毋使入于罪苦。这才是保全富翁……”(前引书第178-179页)古今两相对照,仔细读来,真令人唏嘘慨叹,不能抑止!,其内容皆为仔细贯彻前述乡约宗旨,进而也是在基层通过“乡约长”等半官半民的人物,以践行“文化中国”的职志。这一职志,还进一步体现在其有关抚恤贫弱,建仓济民的“乡约”——《社仓条约十六条》中。该“乡约”明令在诸乡合设一仓时,总统事务者必须是在各乡“社正、社副中,举德性优异,公正明廉者”。[10]186如果按照陆世仪“治乡三约”的说法,“乡约”及其“约正的职责,就是掌管治乡的三个约。一个是教约,用来教化乡民。一个是恤约,用来给乡民实际好处。一个是保约,用来保护乡民。”[10]159这三个方面,线条虽粗,但结合具体的乡约实施起来,却使所有治乡的举措都既获得了道德价值上的肯定,也具体入微地在制度层面彰显“文化中国”的精神内核和行为取向。
再看后引民间性的“社约”对“文化中国”的作用。有清一代,虽然国家越来越走向专制,制度越来越显得机械,但就民间结社的情形而言,无论是经常游离于官方法之外的、具有反政府色彩的一些宗教社团,还是官方法或认可保护,或放任自流的文化社团,都可谓发达。特别是士大夫和商人们,并不满足于锦衣玉食的生活,更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因此有关文化方面的“约书”,特别是诸如因藏书制定的“书约”(31)参见梁健:《明清民间法律规则考析》,载《现代法学》2017年第5期。,因教育制定的“教约”,因经商制定的“行规”等尤为发达。前文所引,属于教约范畴。其字里行间,既在宏观上典型地表达着中国“礼法传统”的内在精神,如“在塾子弟以恂恂有礼为贵”,更在微观上具体入微地落实“礼法精神”。使得“礼法传统”这一精神文化不仅是悬置墙壁的响亮口号,而且成为私塾里人们喜闻乐见的交往实践。中国固有的道德精神价值,就是通过这种具体而微的“礼法”规范,从精神层面,转化为行为层面的;同时,作为一种载体和工具,它们又在人们生动的交往行为中保存并发扬了“文化中国”固有的精髓。俞荣根曾言:
在古代中国,‘礼法’是秉承天道人情的根本大法。它既是最高法、正义法,统率各种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和家族规范,也是具体法、有效法、实施中的法……是主要的行为规范。‘礼法’意识就是法律意识、规矩意识。[11]296
这一论述提醒我们,有清一代,无论其“乡约”“社约”“教约”,都不背离“文化中国”道德精神的规范要求——“礼法传统”;反之,它是古老的“礼法传统”在清朝基层社会的延续,是“文化中国”在基层社会中动的践行和静的沉淀。不得不说,“文化中国”的流动、脉延、广播和开枝散叶,与它通过“家法”“乡约”一类的基层制度而日复一日地实行密不可分。这也是当代中国关注基层治理,并在诸如“乡贤文化”中寻求治理灵感、回味“文化中国”,并进一步藉此发扬光大,甚至重建“文化中国”的缘由吧。
(三)行业自治背景下的“行规”及其对“文化中国”的表达和担当
古代中国到清代时,仍主要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虽然从秦汉一直到明清,商业贸易源远流长,不绝如缕,特别是在唐代,还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宋明时代,又产生了同样意义非凡的海上“陶瓷之路”,乃至事实上呈现着农商并重的格局。但当局农本商末的统治理念,一直延宕在整个帝国两千多年的行程中。从秦朝开始的“奖励耕战,重农抑商”,到清代仍然坚守的“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使得以分工生产为前提的(32)《大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商业活动受到严重抑制,从而行业与“行规”的发展、健全自然也受牵连,对内抑制了经济的活力,对外,则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严重影响了“文化中国”的拓展(33)这种举措所导致的中国明清时期之海上力量衰落,参见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221页。,反而使中国日渐受制于另一种文化——所谓蓝色文明和海洋文化的强大影响。
不过尽管如此,在一个幅员如此广袤、人民这般众多、地区千差万别、需求纷呈各异的国度,寻求人们之间能够互补余缺、交流共济,乃是天经地义的,也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无法全然扼断的。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专门辟有“货殖列传”,为大商巨贾树碑立传。有清一代,行迹遍布中国乃至蒙古(彼时属于中国领土)、俄罗斯,以经营毛皮、茶叶、银票、钱庄而叱咤风云、左右全国商业经济,并在四处开设“山陕会馆”,号称“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晋商(广义上包括陕西,甚至甘肃商人)”(34)参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垄断大半个中国之盐业、茶叶、粮食、木材贸易而彪炳史册的“徽商(广义上包括彼时安徽、江西、浙江商人)”(35)参见叶坦:《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吴光:《儒学在衰落时期的变革——论清代实学》,载《浙江学刊》1991年第5期;吴传友:《清代实学美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等,俨然使中国展现出一幅“重商”的画卷。不但如此,从南宋叶适奠其基的“实学”学派,在儒学衰落期的清代有了更进的发展,在理论上支持者“重商”行为。(36)参见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这些商帮,本身就秉有特定的文化理念而经商,并把这种理念展开为人们经商的规则。有人在比较“晋商”和“徽商”的区别时指出: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熹……朱熹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12]2
由此可见,彼时中国的商人及其信念和规则,与“文化中国”的神脉关联何其紧密!具体而言,以商事领域及其衍生的慈善领域的“行规”“善书”等为代表的各类规范明晰、预期准确,操作方便的“行规”,被不断地制定刊行——不仅在商业发达的东南及江南是如此,即使在商业活动相对落后的西北(如甘肃、新疆)、西南(如贵州、云南、西藏)等偏僻之所,也是如此。(37)特别是著名的南、北“茶马古道”,更有代表性。参见邓启耀:《灵性高原——茶马古道寻访》,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北茶马古道研究会:《中国北茶马古道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甘肃南部的康县,出土了迄今仅见的茶马古道石碑——“察院明文”。虽然其可辨认的字迹有限,但它作为规范性碑文,庶几可判。仅杨一凡、刘笃才在《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全4册)》中所收录的两湖一带的商业行规,就达260余种。所涉及的行业种类五花八门,包括特许、盐业、茶叶、矿业、粮食、竹木、文具、鞋业、造纸、汇票、钱行、药业、鱼虾、山货等,真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大量的“行规”,就是制定于清代而存留至今的。这足以表明官方压制商业的措施,虽然在宏观层面抑制了中国商业发展的大格局,但并未从根基上消除商业在中国的发展。不但如此,商业发展及其带动衍生的其他社会各业的发展所孕育的“行规”,与前述“家法”“乡约”一样,在规范、进而在人们行为层面构织、圆润和促进“文化中国”之发展。下面我借用一例完整的清代重庆的“靓行行规”,以作说明。
嘉庆六年靓行行规
一议,一客之货,或一舡之货,分起三两行者,无论字号各别,务□□□酌验货作价。如一人作价,一人过秤,其货完善,通知兑银,违者公罚。
一议,凡九河来靛,务须留神查看边底,分别真伪,诚恐有昧良之辈伪造来渝鲁混。一经看出,必须经众,以杜弊端。若知弊隐匿,违者公罚。
一议。作价务须公平,过秤亦当公正,如价之涨跌,应听时市之变换。至于过秤当念天良,切不可损人利己,如买者猜疑不信,彼即三面复秤,以免后患。原买者贩往下游楚吴,上至蜀北,路隔数千里之遥,远近不一,难免无盗窃之弊,若以回信始言少秤,不足为凭。倘若彼即复出秤斤,果有一行少秤作弊,则阖行公逐,永不许入帮生理,各宜守勿违。
一议,凡收各买客银两,仍照旧规,以九一色足兑,勿得每封现扣一二钱者,私行滥收。若徇情滥收,违者公罚。
一议,凡兑卖客银两,务须斟酌,尽以收回之银兑给。勿得贪图小利,以高换低,掺入酌兑,若违公罚。
一议,凡兑卖客之秤,仍旧校准常制砝码给兑,出入一体,以免争论。勿得添扣,以紊旧规,违者公罚。
一议,凡来行买靛之客,不拘多寡,其秤与价仍然一体方为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倘有从中作弊,或暗地分肥,加倍重罚。[13]237-238
在如上共7条“靓行行规”中,仔细阅读,每条之中,不仅涉及货物度量、银两兑换的技术标准,而且此种技术标准本身含有极强的道德价值示范。如其中反对作弊、谨守天良,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奉公绝私、斟酌裁量,等等,都借着技术规程得以展现。因此,素来人说“无商不奸”,这种情况在一朝一代的个别时期,特别在商贸及其他社会自治行业初起之时自难避免,但一当其渐行发展而被体制化,通过彰显传统道德精神的规范体系和人们的交往行为体系,就必然意味着相关活动不是游离于传统文化之外的“异端”,反而一方面,它必然是被传统文化所结构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其具体的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规范,在社会底层——人们日常的商贸及其他社会交往中,夯实了传统文化通行的路基,以至商贸活动百业竞争,社会交往千姿百态,也不违“文化中国”之大道,反而在上述“规范事实”中,人们看到的是“文化中国”在商贸活动和人们日常社会交往中被坚定奉行,严谨落实。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规则既是商人们日常交往的准则,也是其公平交易的良心准据——把规则放在心上,也就践行了经商、举事的基本良心,这就是所谓“儆戒无虞,罔失法度”(38)《尚书·大禹谟》。。
三、结语:用规范塑造“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的重建,在注重科学、历史、文学、艺术、学术、道德等的同时,更应自觉地、坚定地把这些内容搭架在制度(规范)之平台上。这涉及对“文化中国”与“法治(规范)中国”关系的理解问题。一直以来,人们即便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也是站在两分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如果说“文化中国”乃主要指向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世界,以及和此相关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思想、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的话,那么这一切,都必须被置于“法治(规范)文化”的框架中,才既是长久的、可预期的,从而也是有效的。在此意义上,“文化中国”和“法治(规范)中国”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构成互为表里的关系。“文化中国”是里,“法治(规范)中国”是表。并且两者之间也相互依存,没有“文化中国”,法治中国就缺乏基础、底色暗淡;而没有“法治(规范)中国”,“文化中国”就不成形状、难以日常。可见,“法治(规范)中国”需要“文化中国”厚实基础、铺垫底色;而“文化中国”也需要“法治(规范)中国”构划蓝图、推行实践。
进一步说,“法治(规范)中国”,绝非对“文化中国”的亦步亦趋,而且是型构“文化中国”的能动因素。这是由于一方面,法治(规范)本身是一种升华了的文化,即建立在其他文化内容基础上的规范文化,是其他文化的规范浓缩和提升;另一方面,法治(规范)的稳定性、规范性、可预期性和实践性,在持续不断地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的同时,必然会影响、改造甚至型塑文化,哪怕一种文化再持久坚固,规范的运行也会渐渐风化之,并使规范融入既有的文化体系中。所以,“文化中国”的重建,自然离不开规范塑造。
说以规范塑造文化,帮助“文化中国”的重建,自然离不开官方法,甚至在国家主导的时代,官方法的风化还是主要因素。但也离不开民间法,至少民间法能够配合官方法更好地通过规范塑造文化,助益于“文化中国”的重建事业——如果说当代中国官方法主要是外域文化在中国的规范表达的话,那么,民间法,无论是作为习惯的传统民间法,还是在当代中国迅速变革的实践中新生的民间法,更可谓是本土文化的规范表达。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更能表现当代中国多元文化互动的使命,有力地襄助“文化中国”的重建。
在“文化中国”重建中民间法对文化的型塑,既须关注当代中国实践中“自然长成”的民间法,亦须关注古代中国,特别是清代中国留存至今且现实有效的民间法。这是因为:其一,这些民间法不但是现实存留的,而且对人们日常交往行为有现实的规范作用。特别是在孝道、抚养、继承、婚丧嫁娶等最日常的交往行为领域,更是如此。其二,曾经的殖民、半殖民统治,对“法治国家”和“文化中国”的建设而言,紊乱了其社会基础。强调传统且有效的民间法,可以重新理顺这种被紊乱了的社会基础,并藉由民间法和官方法的合作实现多元文化互动,进而支持“文化中国”的重建。其三,当代中国的官方法或正式制度,基本上是移植的、外来的,它在中国的开花结果,需要嫁接在硕健的砧木之上。在一定意义上,本土的民间法就是移植的官方法得以嫁接的硕健砧木。因此,两者的相互作用,一定会型塑“文化中国”的高次提升,防止“文化中国”重建中的顾此失彼。其四,在一个大国,无论古今,文化-社会交往都具有多样性,只有这样,人民对规则才有一定的选择性,并最终引致人们对规范的接受。因此,规范刚性和规范包容必须兼顾。官方法对古、今民间法的认可或“放任”,既是官方法规范包容性的体现,又有助于人们在接受的同时,也巩固官方法的规范刚性,还有益于在民间法和官方法的相互合作中,实现规范诱导的多元文化互动,以升华了的规范文化的力量,襄助“文化中国”之重建。
可见,包括民间法在内的“法治不仅是多元文化化育之结果,同时也是塑造、培育多元文化,增进宪政团结力量,促进多元文化互动实现的一般制度基础”[14],是“文化中国”重建中的型塑力量,而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