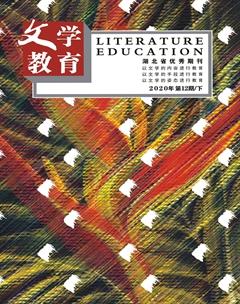自媒体与民间歌谣的复兴
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伴随着现代媒介的冲击,民间歌谣以及一般民间文学的生存遇到了重大挑战,普遍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部分甚至濒临灭绝。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分析。实际上,民间文艺与现代媒介的关系并非这么简单。细究起来,我们恰恰发现: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提供了传统背景下不可想象的有利条件,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歌谣的传承和传播。比如,花儿这种西北民歌第一次为外人所知,就是源于1949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歌手朱仲禄进行直播。正是广播、唱片以及后起的电视、磁带、DVD等这些不断发展的传播技术,使得花儿从西北一隅向全国流传,也促进了它在原生地的繁荣。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这种新媒介在民间文学传承与发展中的意义更为突出。这篇小文的目的,就是对网络媒介(尤其是自媒体)在民间歌谣传承传播中意义及局限等问题做一初步的分析。
一
我们要确认的基本看法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极大地推动了民间歌谣的传承与传播,甚至带来了一种复兴。之所以称为复兴,是因为:一方面,相对于口耳相传时代歌谣传播所受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网络时代民歌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更为活跃;另一方面,相对于单向传播媒介时代民间文化所受的强势文化与主流文化的限制,网络这一双向传播媒介极大地激活了民间歌谣的“民间”性。
网络对于民间歌谣传承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储存了海量的资源,这是过去任何时代不可想象的。海量一方面自然是指数量的巨大。比如我们以关键词“信天游”在“百度”中搜索视频,并限定时长到10分钟以内,可以获得一万一千多条数据。搜索“花儿”,可以获得三十多万条。①具体到“青海花儿”,也有近十五万条。搜索“云南山歌”,有七万多条;搜索“贵州山歌”,有一万多条;搜索“客家山歌”,也有一万多条,等等。这自然不是全网的总数或确切数据,但相对于以百首、千首为计的传统书面媒介,是个几何级的飞跃,因为31卷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也只收录了4万首作品。
其次,门类的齐全是网络资源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在前网络时代,即使是专家,一生可能也見识不了太多歌谣的类别。但在网络中,我们能够发现各个地域、类别的歌谣。比如在百度视频中搜索“号子”,能获得各种门类的劳动号子约六千多条;搜“小调”,有一万六千多条。网络资源还有另一个优势,即便捷。网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我们不必亲临演出现场,即能感受歌谣本身的魅力。而且,网络存储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民主性,它不像档案馆和博物馆,对资料查阅者设置了各种人为的限制。
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移动上网背景下的微信公众平台等使得歌谣的传播更为便捷。微信公众号成为民间歌谣传播的重要方式。当然,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要全面统计民间歌谣类的微信公众号,也是个不可能的任务。这里只以一些粗略的考察,显示一下自媒体时代民间歌谣的“火热”情形。
从2016年以来,歌谣类公众号在微信中大量涌现。一方面,这些公众号覆盖了众多的民间歌谣类型。比如,涉及西北歌谣的“花儿民歌”、“青海花儿大全”、涉及西南民歌的“云贵山歌”,涉及北方歌谣的“陕北民歌”、“山歌酸曲”、“二人台”,以及涉及少数民族歌谣的“土家山歌”、“傈僳音乐”等。另一方面,一些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歌谣类型,公众号也非常多。比如,我们以“花儿”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青海花儿MV”、“青海花儿大全”、“河湟花儿”等20个公众号。当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花儿民歌”与“青海花儿大全”,前者2016年3月10号上线,后者2016年7月29号上线,其余大多数是2017年上半年创刊。而最令我们惊叹的,还是歌谣公众号的编者与读者们的热情。“云南山歌”2016年2月13日创刊,长期每天推送七八首歌谣,阅读量普遍在一两万以上。“二人台”主要推送二人台小戏及周边流行的山曲等,阅读量要更多,其中刊发的一些时事类短视频,竟能达到10万以上的阅读量,可见关注者之众。
不过,无论视频网站还是微信公众号,还是一种单向的、静态的呈现。直播平台的出现,使得歌谣的实时表演或者交流成为可能。以花儿为例,当下许多著名的民间歌手都在“快手”开通了直播,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比如年轻歌手童守蓉,每逢周三、六晚上定时直播,也偶尔直播乡下演出等活动,粉丝人数达13.5万。另一位歌手马全也有9.5万的粉丝。此外,微信这类社交类APP,则为民众进行民歌交流、甚至对歌提供了可能。笔者加入过一个广西平果地区的民歌交流群,其成员有两百多人,成员的物理位置可能相隔千里,但网络使他们的隔空对唱成为了可能。
而且,网络尤其是自媒体,对于民间歌谣而言不仅是一个存储空间和传播手段,也满足了歌谣发展的内在要求,激发了歌谣在传统条件下无从实现的潜能。比如:第一,呈现了歌谣的表演性。作为一种多媒体,网络传播超越了书面媒介只能传达文字的局限,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歌谣的表演性和立体性。第二,实现了表演的交流性。当代民间文学理论特别强调口头艺术的交流性质,网络直播、微信对歌等实现了歌谣的这种社会功能。第三,满足了歌唱的生活性。以微信对歌为典型代表,自媒体时代的歌谣形态,告别了单向传播时代的单纯聆听,使歌唱又回归了日常生活,回归了(网络)社群中的交流。第四,提升了歌谣的艺术性。丰富的作品的呈现,自然会促进歌谣艺术的提升。而且,不同时代、地域、门类的歌谣形式的共识呈现,使得新的歌谣形态的出现正在成为可能。
三
我们之所以称网络自媒体带来了民间歌谣的“复兴”,是因为这种双向传播媒介极大地促进了民间歌谣的“民间性”的发展。因此,民间歌谣的复兴,实质上是一种民间精神的复兴,民间话语的生成。如古人所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谣是民众的心声,是对自己生活的评判与诉求。但在前网络时代,民众心声的传达,有赖于采诗官或者文艺工作者的间接发掘。网络时代的进步之一,就是民众的自我表达和传达成为可能。我们这里以网络中的最具民间性的(新)“打工歌谣”为例做一说明。中国今天有近三亿农民工,但他们的生活境况尤其心境、感受究竟如何,在主流媒体中是难得一见的,而网络媒介为他们提供了表达心声的可能。笔者以“打工”为关键词,在视频网站优酷中进行搜索,获得了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歌谣(以下称打工歌谣)。根据歌谣研究的传统,我们可以从所用曲调的角度,把这些歌谣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可以叫作传统调,即利用传统民歌曲调填词的新歌谣。利用传统音乐曲调和传统作词模式(如“十二月”调、“四季调”)创作是打工歌谣的常用手法,但歌词反映的基本上都是新的生活内容,这类作品大约有五十余首。有一首贵州山歌《十二月打工》(作词:吴显志),实际上就是传统歌谣《长年歌》,只是把地主换成了老板等新式称谓,优酷播放次数达31万,这其实是个个例。绝大多数打工歌谣内容所反映的都是当下的生活,比如贵州黔东南山歌《唱支歌送打工人》(作词者不详,播放次数40多万)、花儿《打工累》(作词、演唱:尕麻乃,播放次数40余万)等。而且各个地域的类别都有,比如有云南山歌(18首),贵州山歌(8首),花儿及青海小调(12首),内蒙古山曲(2首),安徽小调(2首),孟姜女调(1首),山西秧歌小调(1首),布依族山歌(3首),水族山歌(1首),贵州孝歌(1首),以及莲花落(2首,其中一首《打工难》播放次数有55万之多)等。
第二类可称为流行调,即利用流行歌曲的曲调重新填词的打工歌谣,大约有50首。其中被选用最多的曲调是歌手陈星演唱的《新打工谣》和牛朝阳演唱的《打工十二月》这两首反映打工生活的流行歌曲,以及迟志强演唱的《狱中十二月》(原本也是北方民间小调)、《愁啊愁》等反映监狱生活的歌曲。此外还有“天使的翅膀”调(3首)、“驿动的心”调(1首)、“爱拼才会赢”(1首)调等共十二种。
属于(陈星)“新打工谣”调的有12首,而且大多数是用状语、苗语、侗语以及广西钟山、重庆涪陵和海南儋州等地方言填词、演唱的。其中一首状语版播放次数15万。属于(牛朝阳)“打工十二月”调的有10首,也包括彝语、东乡语版本,广西贺州、广东肇庆、甘肃临夏等地方言版及普通话版。其中雷州方言《打工十二月》(作词、演唱:周阿惠)播放次数13万。(迟志强)“愁啊愁”调有3首,其中一首《打工的日子好辛苦》(演唱:丑女)播放次数近11万。用流行歌《下定决心忘记你》重新填词的《下定决心回家种地》在腾讯视频中的播放次数达886.3万,“天使的翅膀”调的《打工心声》(作词:许华升)播放次数近126万;“让泪化作相思雨”调的《打工创业血泪史》(作词:许华升)播放次数130万;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调的《离别的心语》(作词:草民、邱文献)播放次数15万多。
第三类是自度曲调,即自己作曲、填词的打工歌谣,大约有14首,但播放次数普遍更高。一首名为《广东打工》的“心酸壮语歌曲”在优酷的播放次数是60多万,《打工的辛酸》(作词:林林)播放次数30万,《打工在外》18万,《我就是个打工的》(作词、演唱:Mc基仔)8万,等等。
从内容上来看,打工歌谣主要反应了农村务工人员的日常劳动生活,他们工作与找工作的艰辛,讨薪的困难,爱情的挫折,抛家弃子的辛酸,对家乡、父母的思念,对自我处境的悔恨,以及对于出路的探索,等等。比如这首广受欢迎的《打工难》所唱的:
上班苦,上班累,上班就想打瞌睡。上班烦,上班难,上班就想出去玩。远看XX(按,打工地)像天堂,近看XX像银行。都说这里工资高,害我没钱买牙膏。都说这里伙食好,青菜里面加青草。都说这里环境好,雾霾撵得四处跑。都说这里靓妹多,混了几年没拍拖。工作辛苦工资低,有事请假很难批。
四
正是网络媒介,使得这些反映打工经验和民间情感的新歌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而且,借助歌谣的魅力,民众对世道人心表态的途径也大大扩展。因为,民间歌手可以利用自己的公众号,发出社会底层的声音,其影响力不容忽视。比如,杨晓琼是山东菏泽一位年轻的莲花落艺人,他通过公众号“杨晓琼说事”,推送自编自演的作品。其中有一首是针对甘肃农妇因取消低保全家服毒的新闻事件创作的《乞丐说唱农村低保,太解恨了》,被四川、恩施、咸阳等各地生活类公众号转载,在全网广泛流传,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公共媒介并不是公共性的媒介。这一空间为民间话语提供了表达的可能,但也是相当微小的可能。比如,民间歌谣很难在公共视频网站占取头条的位置,即使上百万的观看次数,在上亿的点击量(如电视剧《欢乐颂》)面前也是异常弱势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成为属于民众自我的空间,但在这一自在空间获得的同时,也意味着放弃与主流话语的抗争,或重新被主流屏蔽。
因为网络媒介是有倾向性的,它不是一个中立的空间。不同的平台已经造成了网民的分化。在快手、抖音、B站背后,是社会背景和文化趣味相当不同的群体。而大数据技术带来的精准推送,又有使得这些群体更加陷入固有身份的可能。流量逻辑的背后,是不同社会阶层及其文化趣味支配力的直观呈现。套用一句老话,在物质生产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阶层,也支配着媒介的生产。某种意义上,今天的网络空间,更多反映的是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和诉求。现实中的民间文化或者被遮蔽,或者被以特定的有色眼镜扭曲。典型的例子是的某10万加的网文《底层残酷无语》对直播平台快手的污名化评判。恰恰是在这个直播平台,就有西北花儿歌手的直播,有《马五哥与尕豆妹》这类经典爱情叙事长诗的演唱,但这些显然进入不了博士们浮光掠影的观察心态,改变不了他们的刻板成见。
总之,在这个网络媒介时代,民间歌谣的命运看起来也是喜忧参半。一方面,与传统时代相比,网络的发展与普及使得歌谣在复兴,而且正酝酿着不可预料的新生,对这一点我们充满信心。另一方面,民间歌谣这样的民间话语要传之久远,仍然受到文化趣味或意识形态的重重阻隔。网络并不是自然就属于民众的空间,而是需要抗争才能获得的空间。而如何让民间歌谣发挥应有的、更大的效力,实现民间话语的根本诉求,也是需要研究者持续探索的课题。
注 释
①本文中所有的网络数据和资料来在两次网络“田野调查”,第一次是在2017年5月,由笔者本人完成;第二次是2018年11月,由硕士刘莉对相关重要数据进行了复查,文章呈现的也是当时的状况。时隔两年之后这些数据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而且随着短视频类APP的流行,民间歌谣的传播形态又有新的拓展,但笔者有理由断定,其发展逻辑基本未變,所以文章仍当时的调查结果来进行论述。笔者在此也向刘莉同学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
胥志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