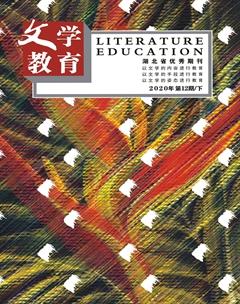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的世界文学理念
内容摘要:在《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中,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主张,语言文学的研究要独立于政治经济。他抛弃政治经济的前见,聚焦于人类文化中真正普遍现象的语言艺术生产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此外,比克罗夫特最具特色的一个观点是“民族模式”的共时性。在他看来,不仅民族语模式与民族模式要共时研究,在民族语模式内部的结构关系上,世界主义文学语言与其它语言也要置于共时段进行研究。本文从比克罗夫特独特的关于建构世界文学体系的理念出发,具体探究比克罗夫特“民族模式”的共时性特征并论其得失。
关键词: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 世界文学体系 民族语模式 民族模式 共时性
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在《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针对莫雷蒂、卡萨诺瓦固定的世界文学体系理论忽略部分历史事实,他提出面对不同的环境,文学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会发生变化。于是比克罗夫特提出六种文学体系模式:城邦模式、泛城邦模式、世界主义模式、民族语模式、民族模式和全球模式。比克罗夫特认为,这六种模式不是分别对不同时段文学体系模式的总结,他提出此六种模式主要是为了强调:要考虑到复杂的历史现实,就要将其中的几种模式共时研究。《在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中,比克罗夫特特别提出“民族模式”共时性的观点。他将“民族模式”划分为民族模式和民族语模式。在以上六种文学体系模式中,比克罗夫特特别强调民族模式与民族语模式的共时性,认为首先基于语言文学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考虑,就不能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治标准来确定民族文学,若依照此种标准,必然会出现民族语言与民族国家互相不符合的情况。其次以语言艺术为主体研究,既要考虑到本土民族语言与世界主义语言的复杂关系,又要考虑本土民族语言同其他竞争语言的关系。并且就现有的历史现实而言,一些本土民族的语言并不是由世界主义的语言发展而来,相反,正是本土民族的语言发展了世界主义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二者也相互影响。因此,比克罗夫特强调既要看到民族模式的适用性,也要注意民族语模式的复杂性。本文正是基于比克罗夫特为“纠正”莫雷蒂、卡萨诺瓦的单一模式而提出共时研究的观点,具体深入研究比克罗夫特“民族模式”共时性特征并论其得失。
一.比克罗夫特的世界文学体系
(一)独立的世界文学空间
比克罗夫特主张民族模式和民族语言文学模式的共时性研究,其实就抛弃了以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作为基点的文学体系,抛弃已持的政治和经济的前见。他不再单独从民族文学出发找寻民族国家立足于世界的方式,而是试图建构一种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体系。他认为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体系是同华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①呈映射关系,其中的连字符都不具有限定修饰的性质。许多作家援引华勒斯坦时基本都认同这一假定。比克罗夫特认为,引用华勒斯坦体系所建构的世界文学不是全世界文学生产的总和,而侧重讨论文学在其中得以生产和流通的世界—体系。他说,“我所寻求的世界文学模式应被建构为这样一种模式,它将成为文学对应对它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而采用的策略之多元性予以把握和强调的一种手段。就其本身而言,它既不会简单地宣称文学与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无关,也避免对这一秩序—以及文学与这一秩序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做出预先的假设。”②由此可见,比克罗夫特不再追求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对应,同时又并不否定其中存在着映射关系。他看到其中的复杂性,从独立的文学语言艺术的生产出发,聚焦于人类文化中真正普遍现象的语言艺术生产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共时的“民族模式”③
1.共时的民族语模式和民族模式
在比克罗夫特看来,“民族语”的与“民族”的,并非一个接一个的替换过程,而是各种体系的共时性整体。他将民族语文学与民族文学都置于世界文学空间中,并将两者作为两个维度进行研究。在《沒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中,比克罗夫特主要论述了被卡萨诺瓦忽视的民族语文学。“民族语的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倾向于在多个系统内工作,对一种或多种世界主义语言以及该民族语的一系列竞争语言加以改造吸收。世界主义语言在许多民族语语境中持续存在,这导致民族语的文学更为复杂。”④
从比克罗夫特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共时性研究可以看出,他不再单纯从民族国家界定的民族文学出发来研究世界文学的空间结构,而是将民族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学统一起来,研究民族语言文学使用的语言、世界主义语言、以及各种竞争语言之间的关系。他侧重于横向研究民族语言文学整体系统中各个方面的关系。比克罗夫特反对卡萨诺瓦民族文学模式的历时研究,他认为如果按此模式发展,则会发现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模式不具有普适性。而将比克罗夫特的共时性的文学研究方法运用于他自己所列举的希腊城邦的历史现实中去,将会产生一些有趣的问题。
作为单一城邦的民族所产生的文学,可以界定为民族文学,但同时这种文学又是利用城邦共同语写成,也可以作为民族语文学。民族语文学与民族文学存在重叠的部分,并不是比克罗夫特的共时研究方式出现错误。他强调民族语模式和民族模式的共时性,恰好是看到并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正如比克罗夫特所说:“民族语的文学与民族文学间的界限模糊而难于界定”⑤,两者作为两个独立完整的系统,却存在着或完全分离,或部分重合的关系(其中有协商和对抗)。如格里高利·纳吉指出那样:“古希腊抒情诗实际上往往处在城邦文学和我所谓的泛城邦文学的张力之中。”⑥古希腊抒情诗是用泛城邦语言写成,一方面它要遵从民族内部的语言规范和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也要同泛城邦共同语的语言惯例以及规范抗争。
2.民族语模式内部的结构关系
比克罗夫特的“民族模式”的共时性,表现在民族语模式与民族模式的共时性、民族语模式内部的共时性。其中比克罗夫特重点强调民族语言模式内部的共时性,将民族语文学使用的语言同世界主义语言放在同一时间维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克罗夫特首先将世界主义语言同民族文学使用的语言出现先后问题搁置,他强调的共时性研究不是指两者出现时间大致相同,而是将两者放在同一时间维度于空间结构中来探究两者关系。对于两者的关系说明,比克罗夫特也持谨慎态度,不再以固定的关系标准来评判。他认为世界主义语言与民族语言文学使用的语言之间关系复杂。
比克罗夫特认为世界主义语言不是作为政治经济地位的表征来使用的,它存在于完整的语言艺术生产空间。世界主义语言也许会同政治经济呈映射关系,但这只是基于历史现实讨论而不是出发点。但世界主义语言不具备侵占性,它的传播是一个自由自愿的行为。以梵语为例,梵语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传播并不是军事征服和大范围的殖民地化的结果,在这里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间出现不一致关系。此外,“阿卡德语和希腊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威望影响力在地中海地区远比萨尔贡征服和亚历山大征服长久以至于政治霸权虽削弱但语言的威望却持续长存。”⑦中国文学在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一直保持的地位也不能单从殖民化或贸易来解释说明。在世界主义语言同各民族文学使用的本土语言的关系上,比克罗夫特更重视世界主义语言不同语言使用者的影响,世界主义语言建立一个跨文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众多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共同尊奉同一种文学惯例。正如他自己所说,“民族语的文学所使用的语言倾向于在多个系统内工作,对一种或多种世界主义语言以及该民族语的一系列竞争语言加以改造吸收。”这里还涉及到民族语文学语言同其它竞争语言之间的关系,比特罗夫特谨慎地解释为改造吸收。在世界主义语言同民族语言文学语言的关系上,比克罗夫特认为两者之间也部分存在着类似于“中心—边缘”的关系模式,如在汉语体系中,日本汉诗和朝鲜汉诗绝不会在中国流通。比克罗夫认为,在他所建构的这一模式中,也可以蕴含着多种中心性的体系。这些都表明了比克罗夫特在认识世界主义语言同民族语言文学语言关系上的复杂性。
二.反思比克罗夫特的“世界文学”体系
比克罗夫特将民族语模式与民族模式置于共时谈论,避免了对所有可能出现情况的方程式罗列。但现实事实证明,比克罗夫特的宣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对民族语模式和民族模式的研究还不够精细化,以南印度少数民族语言和梵语为例,梵语作为世界主义语言,自身具备一套语言规范并且影响了大片民族区域,要研究南印度民族语言在梵语世界中发展,可以从研究南印度本民族语言文学使用的语言与梵语、其它语言的关系出发,描述民族语模式中的“竞争”关系。而梵语同南印度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既要在单一的民族语模式中考虑南印度语与梵语的关系,又要考虑到南印度民族语言对成为世界主义语言之前的梵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它民族文学使用的语言与作为世界主义语言的梵语的关系时,就不得不考虑南印度民族语言的影响因素。
相较于莫雷蒂忽视以往的历史现实,比克罗夫特对结构关系的表述更加严谨。然而比克罗夫特对世界主义语言在文学语言空间中功能结构的研究还不够具体深入。比克罗夫特重点关注空间结构中世界主义语言同民族语言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而对两者的区别表述得不够详细。他说,区别于地方本地语言用来记录世界,大多数世界主义语言是解释世界的。解释世界不是简单地依照现实历史化现实的样貌,而是依照现实进行美学建构。世界主义文学语言的“自我表述”功能涉及到对文学语言本质的理解。其中对政治秩序的自我表述涉及到语言文学与政治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同时,“自我表述”涉及到更重要的一个方向,是文学使用者所代表立场方面的自我建构。比克罗夫特没有将这些方向明晰化,这意味着一旦从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如从“自我表述”功能出发对文学语言与政治经济秩序之间的表述关系进行探索,或许会打破比克罗夫特开始想要确立的独立的语言艺术生产空间。
三.总结
总之,比克罗夫特在卡萨诺瓦和莫雷蒂关于世界文学理论基础上的“修补”考虑到了世界文学体系的复杂性,并且抛弃前两位以世界文学作为与政治经济呈映射关系的空间的论点。他从语言文学空间的独立完整性出发,在此基础上又考虑到部分历史现实中存在着语言文学同政治呈映射关系,考慮到了部分现实也存在着文学语言“中心—边缘”的关系。此外,比克罗夫特理论较卡萨诺瓦、莫雷蒂更进一步的是,他注意到不同环境下文学的结构和功能存在差异。这就考虑到了部分历史现实,比克罗夫特将历史现实纳入他所建构的模式,使其模式多了历史的确证。针对世界文学体系空间结构关系的表述,比克罗夫特较卡萨诺瓦、莫雷蒂之辈更进一步的是,他大胆地提出“去中心化”,破除民族的界限,摒弃民族模式,建立新的文学模式—全球模式。
而比克罗夫特改变卡萨诺瓦和莫雷蒂的方式主张从文学语言研究出发,实际又为研究增加了困难。如莫雷蒂所说,他之所以选择形式的分析进而达到对权力分析的目的,是因为将叙述者的声音作为重点,需要语言方面的能力。这不仅需要对几种世界主义文学语言本身有足够了解,还要了解各种民族文学语言本身。比克罗夫特建构文学模式,侧重建构本土民族语言同世界主义语言的关系模式,他强调的是一种方法、一种模式,而至于本土民族语言与世界主义语言、其它竞争的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克罗夫特没有深入具体说明。所以对于语言之间的关系研究,比克罗夫特既没有避免这一问题,也没有直面这一难题。
参考文献
[1]Gregory Naji,Pindars Homer:The Lyric Passession of an Epic Past,Baltimore 1990.
[2]Andre Gunder Frank,The World System: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London,1993.
[3]Franco Moretti,Modern Epic: The World-System from Goetheto García Márquez,1996.
[4]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1998.
[5]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义读本·文学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路爱国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美]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8]李艳林:《世界体系理论的渊源及影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9]赖国栋:《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与华勒斯坦的“世界经济”》,《古代文明》2010年第3期。
[10]万书辉:《地理学与真理时刻的现代悲剧——莫莱蒂“现代悲剧地理”论析》,《四川戏剧》2006年第4期。
[11]刘洪涛、张珂:《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热点问题评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注 释
①[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路爱国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②[美]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通向一种文学体系的类型学》,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义读本·文学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③“民族模式”:此处的“民族模式”包括民族语模式与民族模式。指代与民族语言或民族国家相关的用以研究世界文学及文学所处环境的一种模式。民族语模式指以民族语言为单位确定民族语文学的模式。民族模式指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确定民族文学的模式。
④[美]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通向一种文学体系的类型学》,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义读本·文学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⑤[美]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通向一种文学体系的类型学》,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义读本·文学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⑥Gregory·Naji,Pindars Homer:The Lyric Passession of an Epic Past,Baltimore 1990,66.
⑦[美]亞历山大·比克罗夫特:《没有连字符的世界文学——通向一种文学体系的类型学》,张永清、马元龙主编:《后马克思义读本·文学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作者介绍:刘诗环,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