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何以“敦伟大友谊”
周梦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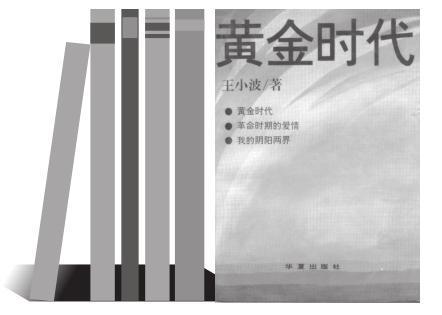
在当代文学中,王小波可能是最快进入经典化进程中的一个。这不仅在于他的作品与文学市场的强大亲和力,也在于他的死亡迅速被卷入了始于20世纪90年代、绵延至今的知识界左右之争。纪念王小波的文集里会聚了各路名家学者,后来的研究者们也非泛泛之辈。待台风势力愈减,学者们重新捡起王小波的小说,翻开《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红拂夜奔》,于是性的问题立刻成了头等大事,不过大多数皆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性,即要么以性为透镜借以体察复杂的权力格局,要么将性当作颠覆上下等级的强力戏仿与反讽。问题在于,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否具有某种肯定性、建构性,或者说自身就有某种意义的自足性?这个问题是被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回避了的。
要考察这一问题,不得不回到“王小波文学迷宫的入口”——《黄金时代》中看看。《黄金时代》是王小波最宠最爱的孩子,写性最坦荡无忌最精彩。我敢夸口,任何一个读过《黄金时代》的人,印象最深的必然是王二和陈清扬的“伟大友谊”:“老兄,咱们敦敦伟大友谊如何?人家夫妇敦伦,我们无伦可言,只好敦友谊。她说好。怎么敦?正着敦反着敦?我说反着敦。”(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P36)并继而产生“领导”般的疑问:
我把这些事写进了交待材料,领导上让我交待:1.谁是“敦伦”;2.什么叫“敦敦”伟大友谊;3.什么叫正着敦,什么叫反着敦。
“敦伦”据说源于周公之礼,“敦”有督促、勉励的意思,“伦”则指“夫妻伦常”;以“敦伦”指夫妻房事,意在将性纳入儒家伦理规则之中,使性成为一种需要“敦促”而完成的伦理义务。陈清扬乃“破鞋”村医,王二则是无赖知青,二人自然“无伦可敦”,却又都有想“敦点什么”的急迫感。那什么又是“伟大友谊”呢?在《黄金时代》中“伟大友谊”一词出现了28次,其中有5次作者尝试对“伟大友谊”进行定义——多亏了王小波的逻辑学与英美经验主义背景,我们好像接近了《黄金时代》的奥秘。但是,五次定义各不相同:伟大友谊是江湖好汉的义气,是信则真疑则伪的主观信条,是人活在世上必须要做的几件事之一,是海豚之间的“娱乐性搞法”,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诺言,甚至是王二喂猪“糠比平时多三倍”的跨物种善意。
用常识也能知道什么是“伟大友谊”:在“革命时期”,似乎只有伟大的主体才有伟大的友谊。退一步来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友谊似乎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合法的感情,且这种友谊只因靠在“伟大”名下才合法。这就是战友之情,同志之情。在《红岩》中,期待与丈夫相遇的江姐半途惊见丈夫被杀,头颅挂在城头,一下惊呆了:“老彭?那活生生的亲人!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1962年第3次印刷,P71)这里老彭先是战友、同志,然后才是丈夫;对江姐这位女中豪杰而言,她与丈夫之间的“伟大友谊”要远超夫妻之情。
领导最爱看“伟大友谊”的故事——除了那最后一次。按王二的复述,这次陈清扬在交待材料里写道:
(在被王二用力打了两下屁股之后)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陈清扬爱上了王二,她说这是她“真實的罪孽”,“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这份材料终于让见多识广的领导面红耳赤、手足无措,不得已只好把他俩放了。
以“爱”结尾,在这个通篇“敦伟大友谊”的故事里显得十分蹊跷,有些人据此认为“爱情”是《黄金时代》的主题。然而简单统计就可以知道,“伟大友谊”这个四字长词在小说中出现了28次,而单字词“爱”,如果只算亲密感情之意的话,只出现了5次。头一次是在开头:“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最后一次是如上所述的结尾处:“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中间三次则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爱:“她根本就不爱我,也说不上喜欢。”“好危险,差一点爱上你。”“她不想爱别人,任何人都不爱。”这个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耐人寻味。在革命年代,普通人之间的爱何足轻重,只有对伟大事物的爱才讲得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爱是“不能忘记的”,承载着百废待兴的人性希望;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在日常生活的复杂琐碎淹没了理想主义光芒之后,在经历了种种经济、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颠覆性的文学事件之后,谈“爱”,或者“爱情”,又成了十分可笑的。但也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爱情之爱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崛起而复兴,似乎成了关于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唯一合法的、垄断性的表述,成了诸如伟大、自由这类宏大叙事的最后堡垒。在《黄金时代》中,“爱”同样在伟大真挚与荒谬可笑之间摇摆不定;为何陈清扬以“爱”为罪,为何“领导”因爱而手足无措,这很难简单归因。以“爱”结尾,正是王小波的一个文学魔术,意在创造一个两极之间游移逡巡、绵绵无尽的意义阐释空间。而“伟大友谊”本身是“反爱”的,它起源于对爱的渴望,形成于与爱的对抗,终结于爱的生成。《黄金时代》是一个关于“伟大友谊”的故事,而非关于爱。
如此一来,“敦伟大友谊”这个动词短语就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它贯穿了封建年代、革命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在,这片后现代的废墟上伫立着唯一一个问题:“伟大友谊”何以“伟大”?除了指向他者的反讽以外,这种“友谊”是否有可能自身就是“伟大”的?这也就是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否自身就有某种正向价值?于是,我们必须在另一层面上探寻“伟大友谊”的复杂性。
王小波的师承问题一直为人乐道。他的汉语风格,按他本人的说法,承袭自查良铮、王道乾等翻译名家;他的小说素材来自唐传奇;他的经验主义与逻辑性,来自常常提及的罗素,也受作为逻辑学家的哥哥的熏染;他的黑色幽默来自马克·吐温或萧伯纳,而那种怪诞的趣味与精炼的结构则深受卡尔维诺、格拉斯、昆德拉、杜拉斯等欧陆小说家影响。相比起来,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等精神分析学家只是偶尔才被提及,看起来无足轻重。
只有在要向上世纪90年代的读者解释“虐恋”时,王小波才会援引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说,受虐狂是这样形成的: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就会爱上这种痛苦,把它看成幸福。”(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P284)他着魔地写下一个又一个虐恋故事,乐此不疲,《黄金时代》中王二的捆绑与拍打只是个开始。李银河说:“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P256)健康、干净、自然、单纯,这是评论家谈及王小波文中的性时常会用到的词,其中“健康”是重中之重,而对健康与否的判断则来自一种科学主义价值观,它与风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性论”性观念藕断丝连:在这种科学主义视野下,单纯地享受性快乐是“健康”“自然”的,正如上世纪80年代作家写性总要说这是符合“人性”的。
与其说王二的“伟大友谊”“健康、自然、干净”,不如说在它恬淡表层之下,汹涌着昂扬进取的快乐主义。这与同一个文化市场上的所有其他作家都不同。那时的作家写性,要么如贾平凹《废都》、莫言《酒国》或王安忆《米尼》,写性卷入物欲洪流、堕入无尽深渊的罪孽,要么如林白或陈染,将性写成单人独卧里孤寂的自慰与幻想。王二陈清扬二位“狗男女”,他们与审查材料的领导之间不只低等人对高等人的降格与反讽,还有自由人对不自由人的蔑视和不屑。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同步进入了后冷战与后现代的年代。正在这时代交替之时,王二的“伟大友谊”借着《黃金时代》应运而生;王二的一只脚正离开泥淖的过去,另一只脚则伸向不可知的未来。21世纪的第二个乃至第三个十年,我们生存其中的当下年代,就肇始于王小波以笔为马的90年代;在当下,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网络与交通使多元个体间的碰撞更频繁而激烈,线上沟通对当面交流的取代又使身体失去了在场的机会;996的风行重新将人抽象化为纯劳力,私人时间与私人空间的缩减,极大压抑了身体感性与对性的渴求,使中国开始出现类似于日本、美国的“低欲望社会”的状况。人越来越无趣和孤独,且因此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这是王小波绝对不愿看到的。
在当下阅读《黄金时代》,阅读这个“敦伟大友谊”的故事,那么历史与未来就全都会被揉进读者对当下的体验与思考当中;此时“敦”这个字所意味着的伦理责任感与政治紧迫性,就与“友谊”所蕴含的主动性相互引爆,向读者发出这样的强制律令:去找回你的身体,去创造新的关系,去追求快乐与自由。这是20多年前的王小波发往未来的邀请函,也是一切当下读者的命运,而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接受它,带着它去行动和创造:去“敦伟大友谊”。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