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穆斯林的葬礼》
丛子钰
爱情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殉情和死亡也是耐人思考的文学主题,此说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检点一下我自己读过的作品,留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往往是那种用情至深的故事。《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呼啸山庄》《简爱》《霍乱时期的爱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纯真博物馆》《绿化树》《黑骏马》等,自然还有“宝钗黛”,还有“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还有“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甚至还有《爱与同情》——它们都给我带来过极大的震动。
于是,我对以下这组文章充满了期待:这些年轻人会涉及怎样的爱情故事呢?年轻学者的思考与分析均可圈可点,也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而我在兴奋之余还想提醒他们的是,琢磨文学作品中的爱与殉情观,其实还可以放在古典爱情、现代爱情和后現代爱情的问题框架之下。梁祝化蝶或安娜自杀,这是古典之爱;而当王二、陈清扬这对“狗男女”无“伦”可“敦”,只好敦一敦“伟大友谊”时,这大概就是后现代之爱了。马克思曾说:“爱者在十分冲动时写给被爱者的信不是范文,然而正是这种表达的含混不清,极其明白、极其显著、极其动人地表达出爱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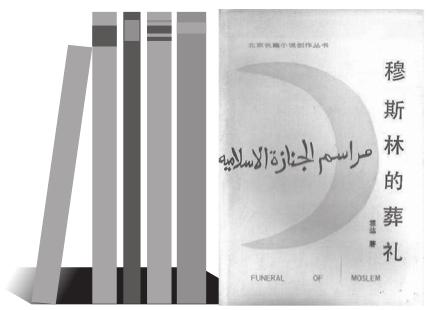
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人头攒动。那天下午,从旧公共租界的里弄,到清真寺的邦克楼,新中国的每个角落都在响着一个主要由附点音符构成的旋律,旋律之前是一片有意为之的静谧,先从G大调上的B开始,在下属音D上结束,和中心位置的主音构成了大三和弦,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移到了下一个下属音A。这就是从19岁的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俞丽拿指尖奏出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主旋律。
1961年秋天,当韩新月和楚雁潮第一次谈到这首管弦乐作品时,它仍然是流行音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爆款。而这首作品之所以成为爆款,并不仅仅因为它的题材触及一个古典时代的殉情故事,而是因为中国对民族音乐的改造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人恐怕不愿意承认,《梁祝》之所以被看作是唯美的仙乐,恰恰因为它足够通俗。
当我们注意到这个矛盾时,也就要注意到接下来的另一个不太容易接受的事实:韩新月与楚雁潮的布尔乔亚身世。试想想,在一个师资贫乏的时代,一名未受过系统音乐教育的年轻人,怎么能够演奏得出梁祝协奏曲呢?考虑到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认真的读者一定能发现,似乎正应了门当户对的法则。但真正美中不足导致了爱情悲剧的并不是韩新月致死的疾病,而似乎是因为楚雁潮是名“卡斐尔”(异教徒),触犯了禁忌。阻碍他们的,是血。
爱来自血液,所以是热的,是盲目的,是迅速的,是粘滞的。禁忌则来自对爱之死的恐惧,从源头上而言,极有可能跟爱情是非常相近的。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反而是禁忌与爱之间的对抗,比理智与爱的对抗要来得更猛烈,它引发了某种原始的内在冲突。正如在天星与容桂芳的恋爱中,伤害了天星的不是容桂芳,而是他的母亲梁君璧。出于对失去对母亲之爱的恐惧,韩天星崩溃了,他在雨中暴走。
《穆斯林的葬礼》在核心的爱情主题上反复处理禁忌,道德禁忌(韩子奇-梁冰玉)、宗教禁忌(韩新月-楚雁潮),它的悲剧性也就寓于这些禁忌之中,使打破禁忌的人获得惩罚。从故事原型来讲,霍达明显部分借鉴了《哈姆莱特》和《俄狄浦斯王》,甚至把前者嵌入到小说中,让楚雁潮和韩新月成为了一部校园话剧的男女主角,通过莪菲利亚的自我谴责和哈姆莱特的延宕,使楚雁潮和韩新月的爱情悲剧有了双倍的净化力量。
再度回到《梁祝》,楚雁潮曾经在医院里播放了这首曲子,而医院里是绝不允许有人播放音乐的,这一任性的举动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她匆匆走过去。她看到在旁边的病房中,一个患急性心肌炎的老太太在仰卧静听,颤抖的手攥着床沿;她看到一个肺动脉栓塞、右心衰竭、脾气又暴烈得想死的汉子,此刻安安静静地伏在枕头上倾听;她看到病情较轻的几个病人,被前来探视的妻子或是丈夫搀扶着在走廊里散步,也不禁驻足倾听……她走过那一排病房,终于找到了琴声的源头,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放慢了,放轻了。她看到新月那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面庞,看到楚雁潮那疲惫的身姿,就什么话都不说了。缠绵的琴声向她诉说着一切,真挚的情怀感染着这位并非无情的科学工作者,科学在艺术和情感面前退让了,她站在门外驻足良久,又悄悄地退去,没有打扰他们。
我反复地想,在这样的场景下,配合着《梁祝》的旋律,究竟是什么在打动着读者?然后我渐渐发现,还是得先回到这首曲子,在了解《穆斯林的葬礼》对心灵产生什么影响前,看看《梁祝》对耳朵产生了什么影响。当然,主要是为了解释这样一部分现象:为什么在听主旋律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强烈地体会到殉情的冲动。
何占豪和俞丽拿1958年参与组建的“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成立之初即面临着巨大挑战:写不出大曲子。同时,农民们不喜欢听小提琴的声音,除非他们演奏越剧、沪剧。早期民族化音乐进程中,很多教师认为问题出在西方化的作曲技巧与民族乐器风格的对接上,但在具体情况上,可能只是演奏手法不同。这意味着,他们将一方面不得不放弃小提琴的把位、弓法,另一方面,又仍然要接受正统的弦乐演奏教育,而这群青年学生心中很清楚,后者才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何占豪和陈钢最后选择了民族化的方法,当然,他们也必然要面对来自音乐界的批评,比如说《梁祝》的曲式不是奏鸣曲而是回旋曲,从头到尾用徵调式太过古板乏味,配器粗糙等。
《梁祝》诞生的年份也实在特殊,如果不是有“民族化”这张大旗,恐怕该曲无论如何没法在1959年上演。《梁祝》的引子与“送别”段算得上妙笔,不然单单“化蝶”就会显得过于悱恻,而轻松愉悦的节奏正是使该作从民间音乐进入雅乐的证明,而不是它宏伟的管弦乐队编制。针对小说的情节也是如此,让《穆斯林的葬礼》从爱情悲剧升华为民族史诗的并非是其炽烈的情感和华丽的表达方式,而是文中不断穿插的关于玉器的知识和那些北大英文系的日常生活。倘若只有韩新月的故事,读者生发的就是对个体命运的感叹。但人们不会忘记,她的出生是在1943年7月,西西里战役刚刚结束,盟军的胜利就要开始。她的父亲,“玉器梁”的徒弟、奇珍斋的老板、北平“玉王”韩子奇,默默犯下重婚罪,使她成为了私生女。于是,我们似乎能验证一点:让爱情变得迷人的,是爱情之外的事情。正如死亡让生命显得可贵,异端验证了信仰的价值。同时,仅仅写一场楚雁潮与韩新月的爱情是肯定不够的,故事中必然地要有陈淑彦与韩天星、韩天星与容桂芳、谢秋思与楚雁潮、韩子奇与梁冰玉、梁冰玉与奥利弗、鬼魂与灯塔上的守护人之间的爱情做对比。

爱情的另一面是恐怖。“化蝶”其实默默暗示了某种可怕的谋杀方式:活埋。在常见的上虞版本故事中,梁山伯去世后,祝英台在被迫出嫁马文才途中,在梁山伯墓前祭拜,哀痛之下,风雨大作,墓穴裂开,祝英台跳入墓中,随后墓穴合拢,风消雨霁,梁祝二人化为蝴蝶飞舞。
实话说,第一次听到这个结尾时,幼年的我是感到瑟瑟发抖的。但恐怖达到一定极限,就能突转成为绝美的爱情想象。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有很相似的情景:新月的葬礼上,由亲人为她试坑,楚雁潮被特许拥有此项权利。当他躺在墓穴中,恐怕也感到了那种隐忧,但当这种被活埋的恐惧同他对新月死别的爱情相连时,就成了痛失所爱的绵延,也让这一过程成为小说最震撼人心的部分:
他跪在坑底,膝行着进入“拉赫”。他从未到过这种地方,却又觉得似曾相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他深处颤抖的手,抚摩着穹顶,抚摩着三面墙壁,抚摩着地面,冰冷的,冻土是冰冷的。新月将躺在这个冰冷的世界!
他用手掌抹平穹顶和三面墙壁,把那些坑坑洼洼都抹平;他仔细地抚摩着地面,把土块和石子都捡走,把碎土铺平,按实,不能有任何一点儿坎坷影响新月的安息!
泪水洒在黄图上,他不能自持,倒了下来,躺在新月将场面的地方,没有力气再起来了,不愿意离开这里了!
……?……
穆斯林们用手捧起黄土,要把新月掩埋了。
楚雁潮僵立在墓穴当中,默默的,痴痴的,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他的灵魂和肉体都留在新月的身边了!人们啊,把黄土倾泻下来吧,把我们一起掩埋吧!……
楚雁潮昏迷的恰如其时,既是出于悲痛,也掩盖了对死亡隐喻的恐怖感。实际上,当爱人死去时,我们想到的不仅是对方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因为如果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已经存在于我们的脑中,倒好像是我们离开了爱人,继续留在现存的世界里,放弃了对往生世界的探索。面对挚爱之死时,生的禁忌与死的禁忌同时在起作用,不然就不会诞生“化蝶”这个复活节。殉情是对爱情的信与望,所以在“梁祝”的神话中得到报偿,化为蝴蝶复活。祝英台绝不可能提前知道这种考验,她只是在墓穴中看到了梁山伯的鬼魂。天气营造了恐怖气氛,而迎亲队伍是小说的最佳讲述者,恐惧使他们的语言变得不再可靠。
但《穆斯林的葬礼》却不是由旁观者讲述的,这让它多少显得不像小说,缺少危机感带来的愉悦,从题目就能看出来,主题过于厚重,到处是对正面史实的解释。而矛盾之处又在于,这部小说又主动地把历史的密码藏到柜子里。从人物塑造上来看,韩新月出生在世界大战期间,死时正处三年自然灾害,从她的生活轨迹(包括她的家庭,除了韩子奇是隐瞒了自己的资本家身份,假装早已破产)中不大看得出这些历史状况。因而《穆斯林的葬礼》是反“伤痕”的,有些地方明明应归罪于历史的,作者却归罪于命运。不僅如此,它还刻意地避开身体关系。楚雁潮与韩新月的柏拉图式恋爱,暗示了他们即使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身体条件,也不可能走到最后的结局。但又恰恰是这种不可能性,在历史缺席的情况下,让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精神恋爱与韩新月的死亡产生了审美的效果。不然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从有问题的人韩子奇,到没问题的人韩新月,作者通过“玉”和“月”不断交替的章节设定实现了跳跃,这个电影化的策略无疑是高超的,因为它与作品整体共谋,擦除了历史的粗暴,而实现了作者的粗暴。与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不同,这种平行蒙太奇在小说中的使用目的正好是相反的。前者把分散的历史片段加速展示出来以制造紧张的心理状态,是为了在结局中既能得到释放,也能将全部的历史归于同一个意识形态主题。而《穆斯林的葬礼》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把统一的、连续的历史拆开成平行的片段,最终实现的是把属于个人的东西从历史中取了出来,把个体还给个体。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9级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