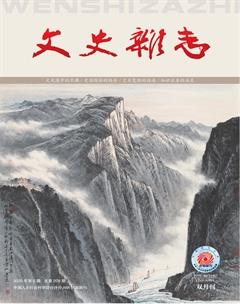重读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旧题由经入史新思索
黄加南
摘 要:由经入史的学术背景,使得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具有开拓性的突破之处。同时,由于力求界定自己的史家身份,蒙文通所叙述的史学史以“接着讲”为主,而非主流的“照着讲”范式。但是,经学传统与史学传统间的根本立场仍有差异,使得蒙文通难免受到许多来自经学的消极影响。尽管种种迹象显示蒙文通的最终目的仍是引入史学观念来更好地捍卫经学,但蒙文通并非一个彻底的经学本位主义者。事实上,其只是迫于经学日益边缘化的命运而不得不刻意抬高经学,以维持学科格局的平衡性。从这一视角来说,由经入史的意因并非仅仅在于促使学者被动将历史思维纳入研究议程,构成史学现代化路途中的独特一面,而更应是在跨学科的外景下,激发学者对知识体系和学科格局的主动思考与持续反省。
关键词:由经入史;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史学现代化
一、导言:遗义尚有未回音
尽管在英文学界受到的关注寥寥,但隨着学术史的风行,中文学界已经就蒙文通做出了许多研究;然而其中仍不免两处共有的遗憾。首先,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固然是探寻由经入史的一个极佳标本,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蒙文通对廖平学术思想是有选择地继承,尤其是对于其二变以后的学术闭口不谈以求同存异。(《文集》3:104—145)[1]过往的研究主要从蒙文通对廖平的评论来认识廖平,这并不是理解探讨二人间学术差异的最好选择。
其次,我们知道,用以估定一本著作学术意义的有效策略一般有两种:将原书放置在学术史脉络中进行剖析,或者正面检视书中论点甚或加以挑战。而之前的研究在两方面几乎都有欠缺,有把蒙文通作为普通生命个体来立传的趋向,淡化了将蒙文通的学术论述放置在学科背景中以评价其贡献的努力,更不用说评论其中的过失了。并且,蒙文通常会刻意书写自身学术进展的历程,带有强烈的个人意识。如果放弃直面其学术论点,转而从书信、跋文来切入,那么我们的研究便难免会被蒙文通流畅的文言文牵着鼻子走。
缘随对蒙文通所做史学史研究的个案考察,本文的基本意旨依旧在于对由经入史这一既定理念的进一步质疑与诠释。由经入史一语源自《书目答问》中“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2]一句,其初衷在于提供一种学术思路,却也同时影响了日后学界对晚清迄民国学术的整体把握。然而,尽管已经有许多论述借用这一思路进行个案研究,但对于由经入史的理念反省,则至今仍是相关学术史绵长图谱中的研究空白。过往的关注点局限于由经入史是如何促使学者将经学方法注入史学研究,构成阐释范式上的突破;而本文则在于强调:由经入史不仅是推动史学现代化与经学消解的动力,更是促使学者反省知识体系与学科格局的警示。
二、由经入史的遗产
特定的著作风格无法轻易地翩然显诸历史学家的笔端。蒙文通在研究中的深刻洞彻力,有赖于经学与史学观念的共同交织与影响。而在此过程中,廖平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这首先体现在蒙文通对史源叠累问题的关注上。廖平在尊经书院的授课议题,[3]直接启发了蒙文通对上古帝王世系中叠累成分的研究。(《文集》5:15—32;3:84—88,《全集》1:223—226)蒙文通将这种思维进一步拓展到史学史研究中,注意到宋代史学中的口语体初稿与文言体定稿间的差异(《文集》3:474—484),也对宋代党争背景下党政派系变换中的史书改写、尤其是朱墨史问题格外注意。(《文集》5:465—473)
此外,这也体现在蒙文通对地方史料与民族史料书写的关注上。蒙文通对古代民族与地理的研究除去产生了《古族甄微》与《古地甄微》两部成果外,也从这两方面切入,就史学史相关问题作出了探索。(《文集》2:497—505;4:81—105)这也意味着移动与静止的民族史与地方史虽然似乎截然相反,但在蒙文通的学术思维中却常被连结在一起。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二者恰恰对应被廖平誉为“史学之颛(专)门,志乘之巨例”的“辨疆里”与“考氏族”。[4]因而蒙文通对地方史料与民族史料的思考,事实上也是对廖平学术思维中史学焦点的重估,蕴含着由经入史的学术意义。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影响呈现负面的消极作用。不过当蒙文通将之应用于史学史的研究时,却也带来了崭新的思路。廖平将今、古文经学的分歧这一老命题,解释为孔门学在齐鲁(孔门晚年弟子传播)与燕赵(孔门早年弟子传播)间的地域差异。[5]这一观念启迪了蒙文通对先秦文化三系的思考(《文集》3:23;5:1),但也使得蒙文通在日后的学术道路中,对于地域因素过度敏感。意大利学者里卡多·弗拉卡索的质疑便认为,蒙文通将《山海经》理解为巴蜀文化产品的做法过于依赖地理因素而不具说服力。[6]不过在史学史研究中,我们仍充分感受到蒙文通对这一敏感性的正面利用:学界向来根据地域线索认为皇甫谧、司马彪代表北学,谯周代表南学。蒙文通则通过追寻当时经学中郑玄、王肃南北之争的大脉络,而对三人的史学渊源给出新解释,指出谯周宗郑玄而为北学,司马、皇甫主王肃而为南学。(《文集》3:296—297、429;5:3)他通过追溯学术的内部脉络而改造了史学史研究囿于人物活动地域的被动困境。[7]如果没有经学理念的熏染,这一改造多半无法顺利完成。
另一个最初呈现负面影响,但最终在史学史研究中得到正面运用的例子,是对学派模式的关注。身处保守风格与地方色彩浓厚的四川盆地,廖平是一位对派系划分极端强调的学者。他常将某些对今、古文经学并无绝对立场的古代学者归入两方阵营中的一方。这种思考方式在蒙文通身上也得到了过多的贯彻,加之受到川剧中派系区分的影响,更使得其坚信有三数人共治一学,互相影响……三数年后,则学派成矣”的理想化判断。[8]这导致某些学者的批评,认为蒙文通对于并无“组织之分流、义理之辩论”的重玄学说“强调太过,导致后人以为重玄真成一派”[9]。尽管这种源自经学而对学派的粗放界定或许有伤严密,但当其被置于由经入史的语境中时,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中国史学史》目录下仅有题名而无内容的《刘知幾与张太素》一节,虽然其内容不得而知,但联系张太素、刘知幾对官方修史的排斥行为,其立意初衷想是论述唐中前期学者对官方撰史机制的不满,以为书中第三章揭扬南宋史学作铺垫,也正应前文“子玄正所谓汝南晨鸡登坛先唤者也”(《文集》3:299)的评语。因此,从两三人的孤立式思想切入,在消极的面向上看或许是将之抬高至学派层次而夸大了其影响;但从积极的面向观察,也是从细微的波动着眼以见两宋史学复兴的大趋向。这种从孤立的点式思想中把握结构性力量萌芽的观察力,正是经学留给史学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三、史家身份自我识别意识的抬头
由经入史不仅对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有着主动的、露诸表面的影响,也使得蒙文通在潜意识中调整著作的深层结构,提出新的中国史学史书写范式。这是一个颇难表述的命题,让我们从逆向来证明它。
众所周知,“人物—代表著”的叙述范式,在中国的学术史书写传统中可以远溯至儒学宗系及佛门传灯的叙述。近代之后,这一范式在蒙文通撰写《中国史学史》之前是哲学史叙述中的主流,之后则又是史学史叙述的主要模式。然而,蒙文通甚至在提笔撰写《中国史学史》之前便有志于调整甚至否定这一范式,并在给柳诒徵的信件中自述:
偶焉特出之才,不能据以言一代之学。子长、子玄、永叔、君实、渔仲,誉者或嫌少过,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业而观其先后消息之故,不乐为一二人作脚注也。(《文集》3:417)[10]
联系蒙文通晚年回忆,該段话可理解为其在与陈寅恪交谈后因彼此对宋代史学中南北宋的偏重不同而发。[11]但就史学史撰作而言,最后“不乐为一二人作脚注”句才真正道出蒙著的风格。因此,蒙文通拒绝对个别史家加以生平陈述与著作罗列,而是用史学思潮来作为《中国史学史》中各章节的展开依据。
蒙文通与史学史书写主流范式之间的观念分歧,可以在其他学科史的叙述实践中找到明显痕迹。冯友兰在论说哲学史的书写时便特意提到“接着讲”与“照着讲”的两种方式。[12]而在文学史中,郑振铎《文学大纲》以史实为主照着讲,木心以郑著为主干展开的文学史则颇似接着讲,并直言“我讲世界文学史,其实我的文学的回忆”[13]。蒙文通、冯友兰与木心都选择了从思想而非史学的视角着眼,来“接着讲”。这些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不仅分别是史学史、哲学史、文学史领域的专家,更是分布在史学、哲学、文学中有着见解并给出贡献的学者。
因此,就《中国史学史》而言,蒙文通是以史学家、而非史学史家的身份去观察史学发展的脉络。正如其在《儒学五论》中将春秋学与礼学做为准绳来评判清季今文学的得失(《文集》1:19—20、193—194;3:215)那样,在《中国史学史》中也将义理与制度引入,用作衡量中国史学发展的标尺。(《文集》3:240—241、285—286、306—307、311—312)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史学史》其实即是蒙文通对自己史学理论的一份宣言书。
倘若我们借用政治思想家的理念,那么蒙文通之所以如此构思史学史叙述,应当归功于其自身所经历由经入史的学术道路。鉴于构建历史的动机在于身份认同或自我识别(self—identification),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就思想史起的源给出过一套解释:起初,人们用行为而非思想来识别自我,因而由之产生的历史,是一束行为(而非思想)的谱系。比如瓦萨里(Vasari)在《画家传》(Lives of the Painters)中记述意大利艺术家的生平与成就,而非他们极富创造性的传奇故事;比德(Bede)所撰《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记载的也是传道者生平,未包含宗教体验或神学思考。而思想史的产生,要迟到自我识别的重点出现在思想而不再是行为上。[14]从这一思考方向来说,蒙文通之所以没有选择将叙述重点放置在史家生平与成就上,而是着重于史学思想的解读,是因为他撰写《中国史学史》的动机,乃是对于其史学家身份的自我识别。这种自我识别在由经入史的学术背景下显得格外迫切与重要。
中国史学史由于在学科成立初期同时肩负着史学导论与史料学的使命,故而自始至终便与“接着讲”的范式捆绑在一起。蒙文通可能是迄今为止敢于在中国史学史的“照着讲”路途上走得最远的学者,而这一贡献是与其由经入史的背景难舍难分的。
四、经与史的宿怨
尽管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得知,由经入史为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更促成新的范式,但是在由经入史过程中留下的深刻经学印迹也有消极的影响。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对史学史中关键脉络的把握。与此前平铺直叙的陈述式学科史不同,蒙文通没有持理解而温存的眼光对各朝代的史学报予同等关注。相反,他仅仅聚焦于中国史学史历程中的三个关键期,认为:
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爰依此旨,谨述三时,汉唐元明,备之而已。(《文集》3:222)
而在这三个历史时段中,蒙文通又格外强调南宋,认为“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文集》3:470)。蒙文通的这一判断与学界存在极大偏离,也无疑遭到许多质疑。金毓黼可能是其中最早发声的一位:
晚周诸子,不见有自撰之史。六朝时撰史之风极盛,而亡佚其十九……蒙君于两宋则以金华、永嘉诸派之学说采摭最备。然诸派中惟东莱能撰史,诸人不过论说之而已……愚谓能自撰一史者,乃能谓之通史学,否则高语撰合,鄙视记注,则成家之作必少。[15]
争论最激烈的焦点被放置在了南宋时期,我们不妨即以此为切入点检视蒙文通在撰写史学史的过程中对历史脉络的把握。
蒙文通之所以没有选择聚焦于有“成家之作”的北宋纪传编年体史学,而是转向聚焦于南宋史论,这与其自己的历史观有关。蒙文通指出北宋在史学上“重春秋而忽制度”(《文集》3:320),政治上也相应的“重人制而忽法制”(《文集》5:461),这是有宋一朝兴亡的关键所在(《文集》5:397—398),而南宋史论是纠正这一倾向的正确选择。蒙文通强调,只有具含“义与制不相遗”(《文集》1:239)的史学精神才能对历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无所谓金毓黼所言的是否“能自撰一史”而“通史学”。但是,促成蒙文通这一观念的深层动因又何在呢?
要解答这一问题,尚需提及经学思维在方法论上的遗留。从现存的《治学杂语》与相当数量的自序、跋文中来看,蒙文通经常是事先根据印象形成论点,之后再往史料中寻找证据,可以说是潜移默化式地被经学中曲为之说的立论方式所影响。张崟对《古史甄微》的委婉质疑也显示,蒙文通常用先入为主的思维剔除了一部分可做反证的史料。[16]从这方面来说,自小接受传统教育的蒙文通在史料取舍方面,反而不如接受西式教育的学者客观严谨。而这一性质将导向一个事实:蒙文通的史学研究是在牺牲部分客观性的前提下为其既有的观点服务,而这个观点往往会是经学观点。
因此,蒙文通之所以用近乎绝对式的判断认为“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借用南宋史学的观念,以支撑主张史学应当经世的外王经学。如此一来,由经入史的归宿是否就是引入史学观念来更好地捍卫经学呢?
五、经本位抑或史本位?——旧题由经入史的新思索
《儒学五论》重刊(2007年)后,《道:比较哲学杂志》上曾有书评,第一段话就讨论了是否界定蒙文通为史学家的问题。[17]的确,尽管蒙文通在世时,无论其任职受聘、教学授课都与经学少有牵涉,但就其逝世后刊布的文稿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其对经学论述最为珍视也用力最深。而在蒙文通首部史学专著《古史甄微》毕稿后所写《自序》中的论述,更将经尊于史的论调表述无疑:
《经学抉原》所据者制也,《古史甄微》所论者事也,此皆学问之粗迹。制与事既明,则将进而究于义,以阐道术之精微。(《文集》5:15)
根据这段论述,史(制、事)是“学问之粗迹”,儒家义理才是“道术之精微”所在。长久以来的诸多研究,都显示经学与史学间有如存在永远的宿怨:亲历由经入史的道路而转型后的学者,往往无法忘却对经学的回护与经学至上的观念;而蒙文通正是一个最佳例子。那么,是否可认为蒙文通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在于为经学服务,其由经入史的现代化路途尚未通达?
必须注意的是蒙文通所撰序跋中的不可信一面。与廖平一样作为思想型的学者,蒙文通在行文中常带有刻意书写历史的意味。此类文字并不能真切地反映其学术生涯。同样的,在前引跋文中,尽管蒙文通贬低史学为“学问之粗迹”,但笔者并不认为这反映其对史学的轻视。
蒙文通对经学功用的实际认可度并非如此夸张,只是迫于经学日益式微的景况而不得不暂时作此宣称。对于和蒙文通一样提倡“通”的章学诚,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就其提倡六经皆史的动因有过一个洞见深刻的论断:“章学诚的目的并无意于亵渎儒家经典,而是将史学经典化。”[18]因而史家关注的治学重心,可能并非其终身奉行的学术范式,而只是为了弥补学界对某学科的一时疏远。蒙文通的动机,想亦是为维持学科格局平衡,而不得不贬低经史中的得势一方。只是后人往往关注史家论说中挑战与突破的一面,却忽视了其中的回护与无奈。
因此,在由经入史的时代背景下,蒙文通所扮演的并非仅是一名被动改变学术方向的研究者,而更是力图对现代知识体系与学科格局给出主动思考的教育者。起初,学界亟需从陈旧经学中打开视界,蒙文通便将历史思维纳入学术研究,反对理学家一味尊经废史的主张(《文集》3:223),并采用白话撰写论文。(《文集》3:6—46)之后经学日趋式微,蒙文通便刻意抬高经学的方式来为之回护,在“文革”期间也仍欲讲授宋明理学以续不传之业,[19]并回归到文言写作中。总的来说,蒙文通并不希望传统学术中的任何一方被世界遗漏,所以不断地改变学术中心来调适时代风气所造成的偏激与漏洞。换句话说,调汇经史、调节学科格局失衡的愿景方是蒙文通思维中最醇正的指导性气质。
六、结论
传统中国史学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中,少有其他因素比经学信仰更加剧烈地抵制学术变革;但也少有其他文化中的传统学术,如中国经学那样深刻影响了近代化路途中的史学。[20]近来的研究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形态分为新史学与新汉学两种;前者逐渐成为“现代史学的最高价值”,后者所代表的“化经为史”则日益式微。[21]然而,缘随上文的讨论,笔者仍坚信后者亦有其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为由经入史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促使学者被动接受新的思维方式,构成史学现代化路途中的独特一面;而更应体现于在跨学科的外景下激发学者的教育自觉,促使其对知识体系和学科格局的主动思考与持续反省。
回顾过往对蒙文通的学术评论,来自学术思想史界的文章往往因为《中国史学史》篇幅短小、成书较早却刊布较晚而对之熟视无睹;来自中国史学史界的文章则又因为蒙文通并非专门的史学史专家也对该书加以忽视。本文的研究显示,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在由经入史的背景下显示出独到的学科反省意义。并且,因为蒙文通是以史学家而非史学史家的视角去观察中国史学史,故而在叙述范式与侧重点上都与既有的中国史学史叙述截然不同。
无论是对于史学史、文学史抑或哲学史等其他方向,学科史书写在今日都不断陷入困境;然而蒙文通在20世纪便已尝试对造成这些困境的关键问题给出思考:在目录学化、甚至有如点鬼簿的叙述外,是否有可能建构一个属于史学自身的完整脉络?蒙文通尽管成功地改造了完全依赖人物为线索的碎片化范式,但也未能寻找出属于史学自身的脉络,只能承认“史学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文集》3:417),“故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文集》3:222)。这种将史学发展一味归功于经(哲)学的论调也是导致金毓黼等学者产生质疑的主因。因此,《中国史学史》意图挑战既有叙述范式的初衷,无疑已经成功达成;但如何构建新的诠释方式,则仍有待后来者用实践去不断探索。
注释:
[1]以下引用《蒙文通文集》,巴蜀书社(成都),1987—2001年版,简作《文集》卷数:页码;《蒙文通全集》,巴蜀书社(成都)2015年版,简作《全集》册数:页码。《全集》年前刊布,《文集》失收稿均据兹引用。
[2]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3]比如“辑两戴《记》《尚书》传说”“三世表”“汇集二帝三王二伯旧说”,见廖平:《尊经书院日课题目》,载《廖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册,第818、819、826页。
[4]廖平:《廖序》,見叶桂年等修、吴嘉谟及龚煦春纂《光绪井研县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四十册,第204页。
[5]廖平:《今古学考》,见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44页。
[6]Riccardo Fracasso: “Holy Mothers of Ancient China: A New Approach to the Hsi—wang—mu Problem,”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 74, Livr. 1/3 (1988),pp. 18—9,n. 44.
[7]蒙文通关于南北学的论述还可能受汤用彤影响,见蒙文通:《致汤锡予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北京)2005年版,第25页。
[8]蒙文通:《治学杂语》,载蒙默编《蒙文通学记:蒙文通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3页。
[9]葛兆光:《且借纸遁:读书日记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14年版,第166—167页。
[10]此信在《文集》中末尾仅标日月,《全集》(2:480)标为1935年;柳诒徵覆信经整理后刊布,信尾用括号标注为甲戌(1934)年(此信整理件字迹辨识似不甚佳,第一行即误唐说斋为袁悦斋),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1]详可参阅粟品孝:《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1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载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十,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2000年版,第621页。
[13]木心:《文学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4]Michael Oakeshott: “The Emergence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idem.: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Exeter: Imprint Academic,2004,pp. 345—351.
[15]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40.9.30日记),辽沈书社(沈阳),1993年版,第4591页。
[16]张崟:《〈古史甄微〉质疑》,《史学杂志》第3—4期(1930年)。
[17]Xiangrong Zhang: “Review of Five Essays on Confucianism by Meng,Wentong”,In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9(2): 245—247(2010).
[18]P. Demiéville: “Chang Hsüeh—ch'e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in W.G.Beasley and E.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 178.
[19]《蒙文通教授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纪念册》,四川联合大学(成都),1994年版,第67页。
[20]Q. Edward Wang: “Cross—Cultural Development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Examples from East Asia,the Middle East,and India,” The Many Faces of Clio: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to Historiography,eds. Q. Edward Wang and Franz L. Fillafer,New York &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7,pp. 187—209.
[21]王學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作者单位: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科学技术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