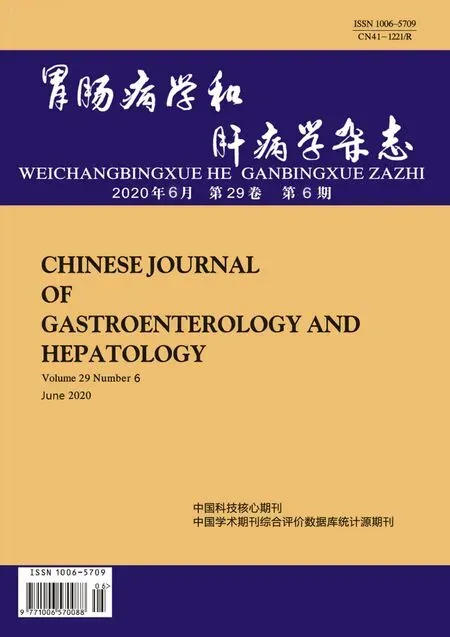上皮间质转化在炎症性肠病相关肠纤维化中的作用
贾文秀, 王 冬, 罗雨欣, 张晓岚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河北 石家庄 050035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尚不十分清楚的非特异性肠道疾病,具有慢性及反复发作的特点。IBD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疾病,其在欧洲和北美的患病率为0.3%,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病率呈逐年递增趋势[1]。纤维化在UC和CD中存在差异定位,且与炎症的定位密切相关,在UC中,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的沉积局限于黏膜及黏膜下层,而CD相关肠纤维化可涉及胃肠道的全层肠壁。肠纤维化是IBD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程,被认为是肠道组织对于慢性炎症和过度损伤的、不可逆的伤口愈合反应,其主要病理改变是以胶原为主的ECM在肠组织的过度合成和异常沉积,肠纤维化可导致严重的并发症[2],从狭窄形成到肠梗阻、穿孔和瘘管的发生,最终将转化为需要手术治疗[3]。有数据表明,30%的CD患者及5%的UC患者需要手术治疗肠梗阻,CD患者术后复发率高达50%[4]。同时,UC患者的纤维化可导致肠壁硬度增加,引起如结肠动力异常、肛门直肠功能障碍、直肠急迫和尿失禁等临床表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5]。可见,防治甚至逆转肠纤维化已成为临床IBD治疗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6-7]。
肠道间质细胞是参与肠纤维化发生的关键细胞,是产生ECM的主要细胞,包括肠成纤维细胞(intestinal fibroblasts,IFBs)、肠肌成纤维细胞(intestinal myofibroblasts,IMFs)和平滑肌细胞等[8],活化的肠成纤维细胞主要来源于组织中的间质细胞、上皮或内皮转化的间质细胞、骨髓干细胞分化的存在于外周血循环的纤维细胞[9]。近年研究表明,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是肠成纤维细胞来源的一条重要途径[10]。
EMT是指在某些病理、生理及环境等因素作用下,上皮细胞失去细胞极性及细胞间连接,且上皮细胞标志物如E细胞钙黏蛋白(E-cadherin)、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逐渐消失,而间质细胞标志物如成纤维细胞特异蛋白1(fibroblast-specific protein 1,FSP1)、平滑肌激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N细胞钙黏蛋白(N-cadherin)、纤维黏连蛋白(fibronectin,FN)等逐渐增多的过程。
1 EMT的分型与分子标志物
1.1 EMT的分型EMT根据其病理生理作用分为3型:Ⅰ型EMT参与胚胎及器官形成;Ⅱ型EMT参与炎症环境中组织纤维化形成;Ⅲ型EMT主要涉及上皮肿瘤细胞转化成转移瘤细胞的过程,参与肿瘤细胞的侵袭与转移。EMT并非简单地上皮细胞向成纤维细胞的广泛转化,而是上皮细胞可逆地获得间质细胞的特性并增强机制联系的一种级联反应[11]。随着研究的日趋深入,Ⅱ型EMT在器官纤维化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在炎症持续作用下,上皮细胞脱离黏膜层,穿过受损的基底膜,迁移至间质组织,最终完全失去上皮细胞表型,获得间质细胞表型,并产生ECM,导致肠纤维化。
1.2 EMT的分子标志物
1.2.1 细胞表面标志物:E-cadherin是参与细胞间黏附连接的主要分子,发挥着维持细胞极性与组织结构完整性的功能,其表达丢失可使细胞失去极性并与周围细胞分离。在各型EMT过程中,E-cadherin表达均显著下调,因而被认为是EMT最主要的上皮细胞标志物。同时,在EMT的发生过程中,E-cadherin表达的丢失往往伴随N-cadherin表达的增加,这也就是“cadherin-switch”学说。与E-cadherin表达部位不同,N-cadherin是一种非上皮性钙黏蛋白,主要表达于纤维母细胞、神经组织和肌肉组织中,能够促进上皮细胞与间质细胞之间的相互黏附,参与EMT过程中的调控。
整合素主要介导细胞与ECM之间的相互黏附。在正常情况下,整合素ανβ6不表达,但在EMT发生过程中,其表达上调,并与TGF-β定位相同。ανβ6可激活TGF-β前体,应用ανβ6抑制剂能显著降低组织前胶原蛋白α1、α-SMA、TGF-β1、TGF-β2水平[12]。因整合素广泛表达于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中,故常以其具体形式如整合素ανβ6作为EMT发生的标志。
1.2.2 细胞骨架标志物:成纤维细胞特异蛋白1(也称S100A4)是经典的成纤维细胞标志物,是多种器官组织重构过程中成纤维细胞的标志之一,常用来鉴定来自EMT的成纤维细胞。Flier等[13]应用免疫荧光双标证实,经TGF-β刺激后,IEC-6细胞中同时表达E-cadherin及FSP1,且E-cadherin表达量逐渐降低,FSP1表达量逐渐升高,证实了EMT这一过程。
波形蛋白是细胞骨架中间丝蛋白的一种。主要附着于细胞核、内质网及线粒体的旁边或末端,对支撑及锚固原生质内的细胞器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能维持细胞形状,保持细胞质的完整性及稳定细胞骨架的作用。然而波形蛋白在成年人体内分布广泛,不仅表达于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还表达于上皮细胞,故其是否可作EMT的标志物仍有待商榷。
此外,α-SMA是表达于血管平滑肌细胞和肌上皮细胞的肌动蛋白,器官纤维化相关的Ⅱ型EMT与表达α-SMA的肌成纤维细胞有关,而与肿瘤相关的Ⅲ型EMT中亦伴随α-SMA表达量升高。
1.2.3 转录因子:目前,参与EMT的主要转录因子包括Snail、Twist和锌指E(zinc finger E-box binding homeobox,ZEB)等。它们在EMT早期即被激活,并在发育、纤维化和癌症发生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由于这些转录因子具有不同的表达谱,因而对EMT的贡献取决于启动EMT的信号传导途径及参与的细胞或组织类型。它们通常彼此相互作用,共同协调上皮基因的抑制和间质基因的诱导,完成上皮细胞向间质细胞的转变。
锌指转录因子Snail是研究较多的转录因子,其家族成员包括 Snail1、Snail2(Slug)和Snail3 (Smuc),可以被多种信号途径激活,促进EMT过程。其中,Snail和Slug在正常黏膜的神经纤维、神经节细胞和红细胞中均有表达,但上皮、成纤维细胞、间皮细胞或平滑肌细胞并不表达。它是E-cadherin转录的强效抑制剂,E-cadherin启动子的EPal元件通过E-box序列与Snail的C2H2锌指蛋白羧基端相互作用,与Smad3结合激活转录,继而抑制E-cadherin表达,即促进EMT过程。
同Snail,ZEBs可通过自身C2H2锌指蛋白区域结合E-盒,从而抑制某些上皮连接和极性基因,如E-cadherin,同时激活调控间质标志物表达的基因,完成EMT中上皮细胞表型向间质细胞表型的转变。有研究[14]表明,miR-200b的抗纤维化作用则是通过抑制EMT相关转录因子ZEB1和ZEB2表达进而抑制EMT过程的。
此外,属于碱性螺旋-环-螺旋蛋白家族的Twist,亦被证实参与了中胚叶形成、组织纤维化发生、肿瘤形成与转移。
2 EMT在肠纤维化发生中的作用机制
EMT的发生与多种细胞因子、蛋白分子、微环境及微小RNA(microRNA)[15]等有关,涉及到庞大的细胞信号传导途径和复杂的基因调控过程。其中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是最为重要的致纤维化因子,同时也是诱导EMT过程中的重要分子[16-19]。
2.1 TGF-β与EMTTGF-β信号网络主要包括两种信号传导通路:Smad依赖通路和非Smad依赖通路。其中Smads是TGF-β信号通路的中心介质,也是EMT中最为关键的调控因子。除此之外,TGF-β也能通过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Ras同系物基因家族成员A(ras homolog gene family member A,RhoA)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PI3K)等非Smad依赖通路参与EMT的过程。
2.1.1 Smad依赖通路:Smad蛋白是将TGF-β1信号从细胞膜上的受体转入到细胞核内过程中最重要的转导分子,其和TGF-β1共同组成的信号通路称为TGF-β1/Smad信号通路。TGF-β1与其受体结合使受体相关Smad蛋白(R-Smad)磷酸化,磷酸化的R-Smads与Smad4形成复合物,进入细胞核内调节相关靶基因转录,促进EMT相关分子表达。TGF-β1/Smad通路可通过Snail、ZEB和碱性螺旋-环-螺旋(basic helix-loop-helix,bHLH)等转录因子家族,抑制上皮细胞标志,如E-cadherin的表达,同时上调间质细胞标志物的表达。在细胞水平上,Xu等[8]应用TGF-β诱导IEC-6发生EMT,可见刺激组较对照组E-cadherin表达含量逐渐降低,α-SMA表达含量逐渐升高;同样在动物水平,应用TNBS诱导的肠纤维化小鼠模型中,可见姜黄素治疗组结肠标本Masson染色胶原含量减少,纤维化程度低。进一步检测治疗组p-Smad、Smad2/3蛋白水平,可见其低于对照组,说明TGF-β1可通过Smad途径诱导EMT,抑制TGF-β1,其下游信号分子Smad随之减少。
2.1.2 非Smad依赖通路:TGF-β能通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如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p38和c-Jun氨基端激酶(c-Jun-N-terminal kinase,JNK)等传递信号并激活某些转录因子诱导靶基因的表达,此过程并不依赖Smad信号通路。体外培养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系IEC-6,应用放射线诱导EMT,可检测到TGF-β及Snail的蛋白表达量升高,同时ERK及p38 MAPK蛋白含量升高,由此证明TGF-β可通过MAPK途径诱导肠纤维化中EMT发生。在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odium sulfate,DSS)诱导的小鼠慢性结肠炎相关的肠纤维化模型中,应用选择性ROCK抑制剂AMA0825可降低TGF-β1诱导的心肌素相关转录因子和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的激活,进而起到选择性抗纤维化作用[20]。TGF-β也可通过TAK1和MKK4激活JNK MAPK通路调节EMT的发生发展。TGF-β除依赖MAPK传递分子信号外,还可依赖RhoA,Ozdamar等[21]研究表明,TβRⅡ激酶使TβR Ⅰ的ser345残基磷酸化,直接与Par6相互作用。而Par6能间接定位于RhoA,不激活Smad通路,直接促使TGF-β依赖的细胞间连接的溶解作用而介导EMT。
2.2 其他信号通路与EMTEMT的诱导作用还可依赖于Wnt和Notch等信号通路,如糖元合成酶激酶3β(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β,GSK-3β)介导Wnt信号通路通过磷酸化依赖蛋白降解作用调节产生丰富的β-catenin,并与细胞核内TCF/LEF1发生作用,从而介导EMT发生。也可经Notch通路激活Jagged1,并依次激活bHLH相关转录因子,最终这些转录因子结合在EMT基因上的适当位点,调节EMT相关基因的表达。
3 肠纤维化中EMT的相关实验研究
EMT在多种脏器的纤维化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小鼠肾纤维化模型中,约35%成纤维细胞源自肾上皮细胞的EMT转化;在小鼠肝纤维化模型中,约45%成纤维细胞来源于上皮细胞[13]。目前研究已证实,EMT也是肠纤维化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由上皮细胞经EMT转化而来的肌成纤维细胞是肠纤维化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效应细胞,可产生大量富含胶原蛋白的ECM,促进纤维化形成。
在三硝基苯磺酸(tri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TNBS)诱导的小鼠肠纤维化模型中,Flier等[13]应用双转基因技术对小鼠肠上皮细胞谱系示踪,使小鼠上皮细胞表达LacZ基因,其基因产物为β-gal,结果证实TNBS组小鼠结肠经Masson染色后较溶剂组胶原纤维沉积更为明显,β-gal+细胞并非局限于肠上皮区域,同时出现在ECM沉积区,进一步统计得出β-gal+FSP1+的细胞至少约占FSP1+总细胞数的1/3,由此证实,约33%的肠成纤维细胞源自肠上皮细胞。同样,在右旋DSS诱导的小鼠肠纤维化模型中,检测到TGF-β、Smad3、IL-13 mRNA水平较对照组升高,E-cadherin水平下调,EMT相关转录因子Snail、ZEB1蛋白水平较对照组升高[9]。在大鼠小肠异位移植产生的大鼠肠纤维化模型中也发现了EMT的证据。在移植后第21天,可检测到Ⅰ型胶原和Ⅲ型胶原的增加,并且可见α-SMA和波形蛋白的表达。同时在肠移植物中可检测到TGF-β、IL-13及相关转录分子Snail的表达[22]。
有研究证实氧化应激可诱导EMT发生,体外培养大鼠小肠隐窝上皮细胞IEC-6细胞系,应用晚期氧化蛋白产物(advanced oxidation protein products,AOPP)刺激,4 d后可见细胞形态由不规则多角形变为细长的纺锤形,同时免疫荧光染色显示AOPP刺激组上皮标志物E-cadherin表达下降,间质标志物Vimentin、FSP1及I型胶原表达升高,证实了EMT这一过程[10]。应用TGF-β及IL-17A刺激大鼠小肠隐窝上皮IEC-6细胞系,同样可观察到EMT过程[8, 14, 23]。对于人类小肠上皮细胞HT-29细胞系,WNT2b通过FZD4激活在HT-29细胞中诱导EMT[24]。
肠上皮类器官(intestinal epithelial organoids,IEOs)最近已被用于制作体外模型,可以重现肠纤维化的体内环境。目前开发了一种基于IEO的肠道纤维化模型,该模型来自人类多能干细胞,TGF-β干预多能干细胞衍生的IEO可诱导肌成纤维细胞群产生及增殖,并且可检测到相关纤维化基因表达增加。TGF-β对小肠和结肠来源的IEO的干预诱导了类器官的破坏和细胞集落的形成,并且可见α-SMA和波形蛋白阳性的纺锤形间质样细胞产生[25]。基于此类器官的上皮-间充质转换模型可用于筛选抗纤维化药物并指导纤维化的治疗。
4 肠纤维化中EMT的相关临床研究
在临床研究中,为进一步验证EMT是否存在于IBD相关肠纤维化患者中,Flier等[13]将IBD患者术后肠组织标本冰冻切片行免疫荧光染色,可见E-cadherin及α-SMA双标细胞。此外,有学者收集了18例CD患者及10例非IBD患者结肠组织标本进行研究,发现CD患者肠组织标本较对照组肠组织标本炎症程度及纤维化程度更重,并且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染色,可见CD患者的肠组织标本中有丰富的TGF-β1、α-SMA、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FAP)、Slug表达,且其表达量与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同时发现CD患者肠组织标本中E-cadherin不仅见于上皮层细胞,在黏膜下层及纤维化区细胞中也可见表达[26]。纤维化区E-cadherin及α-SMA的同时表达,验证了EMT参与了CD相关肠纤维化的发生。而对于UC患者,其结肠组织也可见明显的α-SMA、纤连蛋白表达及Ⅰ型胶原和Ⅲ型胶原沉积;但对于初发/两年内行结肠切除术的难治性UC患者与病程超过10年的UC患者比较而言,纤维化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7]。已经证明在UC患者中可观察到EMT相关基因的表观遗传修饰。在UC患者的结肠黏膜中发现了CDH1(编码E-cadherin)启动子的高甲基化。此外,Karatzas等[28]在UC患者的直肠炎症黏膜标本中检测到其他EMT相关基因的DNA甲基化状态的修饰,同时分析发现,与对照组非炎性黏膜相比,EMT相关的5种基因的启动子(CDH1、CDH13、NEUROG1、CDX1和miR-1247)在炎性直肠黏膜中高度甲基化。
综上所述,EMT在分子、细胞、器官水平均参与了肠纤维化的形成。
5 阻断EMT过程可干预肠纤维化进程
EMT是一种可逆过程,并且由于上皮细胞可以获得间质特征,类似的间质细胞可以通过所谓的间质-上皮转换(mesenchymal-to-epithelial transition,MET)过程转化为上皮衍生物。EMT-MET转化是胚胎发生和器官发育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步骤,其中某些上皮细胞的内在可塑性允许它们在上皮和间质状态之间切换。虽然目前尚无专门的药物治疗纤维化性肠狭窄,但多种抗纤维化分子或药物已在动物实验中显现效果,这可为未来IBD相关肠纤维化的治疗提供新途径。
黄蜀葵花总黄酮可抑制TGF-β1诱导的IEC-6形态学变化及迁移和侵袭,并上调上皮标志物的表达,降低间质标志物的表达,同时阻断Smad和MAPK信号通路。此外,研究还发现si-Smad和MAPK抑制剂可有效减弱IEC-6细胞中TGF-β1诱导的EMT。且黄蜀葵花总黄酮和si-Smad或MAPK抑制剂共同干预TGF-β1诱导IEC-6细胞EMT的过程,比其中任何一种抑制具有更强的作用[29]。Xu等[8]在TGF-β诱导IEC-6发生EMT过程中同时加入姜黄素治疗,可见治疗组较对照组E-cadherin蛋白表达含量高,α-SMA蛋白表达含量低;同样在TNBS诱导的肠纤维化大鼠动物模型中,可见姜黄素治疗组较对照组结肠Masson染色胶原含量减少,纤维化程度低,说明了姜黄素通过PPAR-γ介导的TGF-β/Smad信号通路来预防肠纤维化中EMT的过程。此外,中和甲状旁腺激素受体1(parathyroid hormone receptor 1,PTH1R)或拮抗甲状旁腺素类激素(parathyroid hormone-like hormone,PTHLH)生物活性阻止了TGF-β1诱导的EMT。PTH1R可以增强蛋白激酶A(protein kinase A,PKA)信号并激活下游核转录因子,包括与Runt相关的转录因子2(Runx2),结果表明PTHLH通过PKA-Runx2途径触发肠上皮细胞中的EMT,其可以作为CD中肠纤维化的治疗靶标[30]。同样,Flier等[13]应用BMP-7特异性抑制TGF-β1,发现通过TNBS诱导的慢性结肠炎相关肠纤维化小鼠模型结肠纤维化程度减轻,间质标志物表达减少,说明BMP-7通过抑制TGF-β1可有效阻止肠纤维化进程。同时,Paul等[31]发现,AIP4通过介导HIC5的泛素化来抑制IL-17引起的肠纤维化。有研究报道,在放射性肠炎相关肠纤维化小鼠模型中,应用转基因技术使上皮细胞来源的细胞永久性表达强绿色荧光蛋白(enhanced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EGFP),应用可溶性膳食纤维干预后,可见黏膜下层及上皮下层的胶原沉积减轻,EGFP+/Vimentin+和EGFP+/α-SMA+共表达细胞在造模2周时可见,在模型制造4周及12周时逐渐减少,EMT程度逐渐减轻[32]。同样,通过使用骨髓间质干细胞衍生的微泡(microvesicle,MV)的有效递送miR-200b可抑制TNBS诱导的结肠炎相关肠纤维化模型中EMT过程并改善纤维化[14]。
6 结语
肠纤维化的发生涉及到多种生物学机制,抑制炎症并不能阻止肠纤维化的发展[33],EMT的发生是肠纤维化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抑制EMT发生发展,甚至逆转EMT为肠纤维化的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2, 31, 34],但肠纤维化中EMT的具体调节机制尚未完全明了,其发生和发展受到多种信号通路的共同调控,深入探究EMT在肠纤维化中的作用机制,对纤维化治疗药物的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