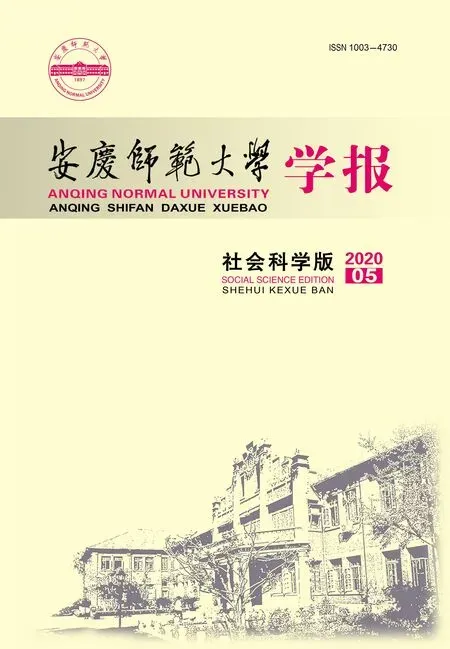从“出走”到“回归”
——吴汝纶旅日信札解读及其“中体西用”论辨析
卢 坡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孟子有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在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中,“布政施教”两位一体,为王化之始。发展到晚清,在西人政教及军事压力下,中国传统士大夫开始寻求解决困局的良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在坚辞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吴汝纶在李光炯、方磐君等人的陪同下,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吴汝纶在日时间约为三个月,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参观考察,走访众多学界人士和官员,并将他在考察走访期间的见闻和思考分类整理成《东游丛录》一书。尤可注意的是,吴汝纶旅日期间,与众多教育家和汉学家等交流研讨,存留不少信札,这些信札颇能反映出当时先进的中国士大夫面对后起之秀日本颇为复杂的心态,以及晚清之际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一、引论:“周孔遗业,几成绝响”
早在东游日本之前,吴汝纶因襄赞李鸿章及办学需要就与外国人士多有接触。从信札交往对象看,最早与吴汝纶通信的外国人士为日本中岛生,就信札所论内容而言,主要是回复中岛生关于《易》学的请教。吴汝纶在称赞中岛生的汉学研究后,有所感慨:“吾国周孔遗业,几成绝响,一二腐朽书生,龂龂抱残守缺,于身世何所裨益!方自笑托业之迂谬,不谓吾子乃复垂意兹事也。”[1]153从吴汝纶的这段感慨可以看出,一是中国的“周孔遗业”很少有人在研究,几乎成了绝响;二是即使现在有少数人尚从事传统国故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于事无补,于国无用;三是对于日本中岛生等关注和研究中国学问表示惊讶和赞赏,并愿意与其交流。从吴汝纶对于“周孔遗业,几成绝响”的感慨、于身世无所裨益的无奈以及对外国人士求学问道的惊异中可以看出,吴汝纶作为传统士大夫在晚清这一特殊时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将会断绝表现出的隐隐忧虑。
吴汝纶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这正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忧虑。如梁启超指出“中国之学,其沦陷澌灭一缕绝续者,不自今日。虽无西学以乘之,而名存实亡,盖已久矣”[2]85。故而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一文中首言“吾不忍言西学”,接言“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2]85。在他们看来,西学尚未兴盛,中学则已处殆绝之地。中学的不兴,与中学的“无用论”又有着直接的关联,特别是经历甲午海战之后,中学“无实”“无用”之论四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严复发表《救亡决论》,对中学批判道:“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3]44正是中国的战败,强化了民众对于中学无用的认识。
19世纪末,拳民与外来传教士矛盾不断激化,以致水火不容,拳民烧毁教堂、打杀教士时有发生,这为列强侵华提供了借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组织联军侵入中国,是年八月攻入北京,京城失守,两宫西逃。吴汝纶也被迫参与拳民与教士的争斗之中。从其《与天主教杜教士》的信中可以看出,教民自寻衅端,私行横恣,致使村庄被烧等事时有发生,吴汝纶认为“以上各村,均无拳匪,而教民任意索诈,良民不能安枕,无以为生”,希望“严禁东闾教民,不得再行讹索”[1]319。可以说吴汝纶所言所行,皆以护民为宗旨,但正是因为吴汝纶与西人颇有交往,舆论汹汹,甚至一度不能自保。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力之不强、国民之不启。这也愈加激发吴汝纶兴学以启民智、以栋梁救国的改良教育的决心。
吴汝纶虽无意仕途,但其用世之心一直未泯。随着国事一再糜烂,天下兴亡,众皆有责,吴汝纶认为国之不兴,由人才不起之故,所以要以造就人才为第一要务。众所周知,桐城派文人多有从教经历,吴汝纶更是主持莲池书院十余年,于教育深有心得。但吴汝纶看到,传统的教育只能培养忠孝文章之士,不能造就实业救国之才。于是,吴汝纶倡导邀请西士,创办东文学堂,学其语言,窥其技术,仿其制度,以兴中国。从吴汝纶《与野口多内》的书信可以看出,吴汝纶曾借助李鸿章之力兴办东文学堂。东文学堂实际存在时间不长,学堂教员野口多内也转为日本使署员。吴汝纶在《与日本使署员野口多内》书信中以败国之民陈其情愿:“窃谓两宫蒙尘,京师失守,若剪以赐寇仇或剖分而食,皆唯命是听。若尚存大惠,申桓文之高义,辅垂尽之微国,使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则不惟敝国宗社之灵获蒙威福,即中土黄炎以来神明胄胤,亦荷绵延不绝之嘉赐,此固欧美大国优为,尤贵国恤邻救患,爱同洲、悯同种之本愿。”[1]301吴汝纶还希望野口多内能将各国意旨之所在告知,然后由其向李鸿章报告,使得“闾阎早获安堵,遗黎得早定喘息”。从吴汝纶与外国人士的信札可以看出,中国早就不是泱泱之大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4]1296的盛世早就一去不复返,只剩下老大弱国,成为任列强剖分而食的对象。这种乱世弱国之感给吴汝纶等晚清传统士大夫的冲击是巨大的,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二、出走:“仰求师法,取长补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在各种压力胁迫下下诏开办新学,以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在晚清士林,吴汝纶作为“方今中国儒林中最有开化之思想者”[5]1167,平素以为“欲救世变,必先讲求西学,造成英伟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变,淬厉发扬,以备缓急一旦之用”[5]1128,又因“学行高、兼综中西,可以师多士”[5]1152,被张百熙奏荐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坚辞不得,以日本变法已久,后来居上,请赴日本考察学制。
吴汝纶在日考察学制,辛勤备至,可谓不负众望,这从吴汝纶汇编的十余万字的《东游丛录》即可知晓。关于吴汝纶具体考察学校、访问学制的情形,吴闿生《先府君哀状》有所记载:“以六十垂白之年,行万里绝海之域,溽暑炎蒸之际,劳瘁百端。初至,查视学校,每日辄十数区,自讲堂教室,以至一椽一桷之微;自图籍仪器,以至一名一物之细,凡构造之精,陈列之备,无不详加察览,曲与研究。炎天赤日之下,步行数十里,各校讲师更番应客,而府君曾无休时。从者皆意怠神疲,不能自振,府君亦惫甚,左右或言先生惫甚矣,府君奋然曰:‘吾为国家至此,殚精考核,正在此时,不可不自敦率!’乃益振励将事。”[5]1155从吴闿生的记载看,吴汝纶在日期间,真是焚膏以继晷,不顾暮年,抓住一切机会向日本同行请教和实地考察。吴闿生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一件突发事件,即吴汝纶为了访问日本宫中顾问田中不二麿(1845—1909),以人力车前往其住所,中途路滑,车子倾翻,吴汝纶鼻子受伤,流血如注,昏迷不省人事,被人扶至医院用冷水疗洗救治。待血止住,吴汝纶即驰车至田中宅与之谈辨甚详。在东京,吴氏日夕应客常数十人,皆一一亲与笔谈,日尽数百纸,无一语不及教育事。吴汝纶所晤多为教育名家,与其反复诘难,曲尽其蕴。待客退,吴氏辄撮记精要,手录成册,每至过午不食,夜分不寝,习以为常。此真可谓为国事奋不顾身,这一系列的举动提高了中国使者的外交形象,这也是吴汝纶在日本受到普遍尊敬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吴汝纶赴日期间存留的四十余封与日本人士的尺牍而言,主要可分两类:一是向日本教育家请教日本的学制,一是与日本汉学家商谈中国的学问。吴汝纶与日本学者信札所论的首要问题是有关日本学制的论题。正如吴汝纶在《答日野恒次郎》所言:“某尝以为欧洲新学,滥觞已久,近百余年,益造精微;贵国维新,仅卅年前,乃能尽取他人之长,输之于本国,甚且超越欧美,青胜于蓝,此中精神所注,直有贯金石感虹霓之气概,震骇无极。要其推行之始,先后之序,迟速之故,艰苦曲折之状态,必有书策所不能载,外人所不及知者,思欲观光贵国,一求要领之日久矣。”[1]405正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国力大增,甚至有超越欧美之势,这正是中国要学习和取法的。吴汝纶通过到日本学校实地考察、走访日本的教育名家,收获颇多,这在《东游从录》中有所记载。如在“教育大意”部分,关于“小学校”,吴汝纶记之如下:“小学养成德性,扩充知识,使后有国民选举之权。又须体育,后可充兵,尽国民之义务。人人应入小学,即町村不可不立小学。如经费不足,府县可补助之。小学不取学俸,如町村贫穷,可以少取,必得文部许可,然后取之。……教科书先时均由文部省编定颁发,近来则由民间编辑,文部鉴定。其教法应因地制宜,文部鉴定之书不一种,何地应用何书,必由地方官与学校教员议定,然后取裁于文部。小学教员、训导、保姆(幼稚园),师范学校所养成。师范学校之卒业生能任教员与否,应由官长检定。检定之法,或由考试,或由教员及地方官荐举。”[1]661这则记载概括地说出了小学教育之宗旨、经费、教科书及老师的选用等,显然有供中国参照学习之意。此后又分列出“中学校”“高等女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医学”“外国语学校”“美术学校”“音乐学校”“高等女师范学校”“高等学校”“实业学校”“实业补习学校”“大学校”的“教育大意”。《东游丛录》卷二日记部分,通过日记的形式记载其在日所见所感,如第一篇到医学堂,其中“过此讲堂后,至解剖标本室,所列百体,自胎儿至一肢一节,皆若生成者”,“入病理解剖室,室中藏有多瓶,皆自病人体中取出各病处结形者。导者又入病虫室,瓶中所列人体中诸虫,有无病者之虫,用显微镜视其虫,粗如小指”等等[1]703—704。这些实地考察得出的第一手资料,无疑对中国此后的学制教育产生良好的影响。在对日本的教育名家走访及对学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吴汝纶对日本经过改良后的学制,已经有所了解。但随着了解的增进,吴汝纶在如何将西方的学制与中国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式人才上,仍然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吴汝纶与日本汉学家商谈中国学问亦为吴氏旅日期间尺牍交往的重要内容。吴汝纶取进士,出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主持莲池书院,日以经艺文章研讨,为当世宿儒、文章大家。日本素有研究中国学问的传统,国内汉学家为数不少,此次吴汝纶亲赴日本,日本国内习汉学者,自然不会错过此次讨论的机会。吴汝纶集中答信夫粲、根本通明之信,多是为此而发,我们先看吴汝纶《答根本通明》一书:
史公但云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如其说则《易传》止四篇也。班氏乃云《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非史公所见旧本。史公时《易传》已失正,至班氏时又失史公所见之旧,鄙意《易传》之不可尽信者以此。执事乃为解释《汉志》“篇”为传,经传合十二篇,谓仆不细读《汉志》,真乃所对非所问矣。引《履卦》《彖卦》谓经《传》相发,仆但不敢信传为圣人手定,岂谓《传》不能释经哉[1]417!根本通明(1822—1906),曾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长,为日本汉学家,著有《论语讲义》《老子讲义》《孟子讲义》《周易讲义》等著作,曾为明治天皇讲习《易》等。吴汝纶集存与根本通明书信六封,皆是研讨汉学所作。从书信的内容上看,吴汝纶对于根本通明的研究之作不以为然,对于根本通明提出的问题多有辩驳,从上列书信就可见一斑。吴氏甚至于在第六封复信中言“凡辨论文史,以虚心商榷为宜,若挟忿失欢,不如不辨”,“贵国汉学殆绝,执事耄年嗜学,有似卫武,仆慕之敬之,非敢有争心”,“故不如各行其是之为愈也”[1]419-420。此后吴汝纶不与根本通明辩解,根本通明则于报纸上刊登其言论及与吴汝纶论辩之文,这在吴汝纶《信夫恕轩席上论辨难周易》有所反映。在这次宴席上,吴汝纶叙述了与根本通明几次辩论的情况,多次提到“根本辨拙”“根本无词相难”“逞臆为说”,至于针对根本通明报纸上的言论,吴汝纶指出“其意知仆不肯附和其说,以此见嫉,欲藉报纸以逞其忿,不足较也”[1]453。通过这些言辞可以知晓,与日本汉学家讨论后,吴汝纶对于自家学问颇为自信。
吴汝纶除与著名汉学家谈论学问,对于一般的日本民众所欲了解中国诗文也做出回答:“吾国近来文家推张廉卿,其诗亦高。所选本朝三家,五言律则施愚山;七律则姚姬传;七古则郑子尹。”[1]450吴汝纶的这封《答客论诗》书,除了以诗文大家的身份对中国之名家诗人稍做评骘以为问客指明学诗路径外,还特别提到了姚鼐七律的成就。而吴汝纶在日期间,还将姚评《汉书》等赠送他人,这无疑扩大了桐城派在日本的影响,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从吴汝纶与日本汉学家根本通明、信夫粲的信札中能总结出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即使是在中国战败、日本获胜的情况下,中国之学在日本也没有绝迹,尚有一些学者在关注和研究中国之学;第二,在西学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欧美之学也没有完全一统天下,中国之国故仍然为一些人所接受,正如吴汝纶所言“诸君精通西学而不废汉文”,甚至有“利用厚生取之西国,而正德尚取自敝邦(中国)”的言论在日本流行[1]445;第三,从日本汉学界当时的研究情况而言,即使如根本通明、信夫粲这样的汉学家也不能真正达到中国研究者的水平,很多问题没有理清,真正研究和阐发中国的国故,还需要中国自己人来完成。
三、冲突:“新旧二学,恐难两存”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长期存在着两股暗潮相互颉颃,即对西方物质的模仿的现实诉求和在精神上寻求自主、独立、区别于西方模式的民族认同。”[6]这两股相互颉颃的暗流,会因时地不同而呈现此起彼伏的状态。吴汝纶远游日本,这是一次脱离母体文化的文化之旅。吴汝纶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甚至得到明治天皇的接见。按照常理,以战败国之臣民,衰年之际,向战胜国日本取经,日本方待之以礼即可。吴汝纶受此殊荣,实在是因为个人学行高深,而支撑吴汝纶学行之高深或曰支撑这场盛大的欢迎仪式的则是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这是文化大国、礼仪之邦的专使造访。这场欢迎及以后吴汝纶在日本受到的礼遇,给吴汝纶很大的冲击,也进一步影响着吴汝纶关于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深入思考。
(1)开发教学资源:①通过引进、内化德国机电类行业培训标准、教育资源、对接德国职业标准和典型岗位工作过程、开发模块化职业技能和新技术培训课程、开发系列培训教材等一系列方式培养“师傅型”师资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理念、教材把控能力、实践教学能力等关键教育教学能力;②依托跨企业培训中心企业化的现场实践教学环境及现场管理,将典型合作企业现场管理体系融入实践教学中,强调学徒5S管理和良好职业素养的培养。
吴汝纶除与日本教育家、汉学家信札往来不断,亦与贺涛、林纾等互通书信。其在《答贺松坡》一书中对于在日期间的所得和困惑有集中反映:
新旧二学,恐难两存。执事与启儿书,意极深挚,而事亦未易办到。……但计东、西洋公学年数已如此,若再增吾国旧学,至省亦须十余年。近人多求速成,安有入学堂卅余年不变改者乎!西学但重讲说,不须记诵,吾学则必应倍诵温习,此不可并在一堂。合四五十生徒而同受业,则不能与西学混同分科;若西学毕课再授吾学,则学徒脑力势不能胜。此鄙议所谓不能两存者也。此邦有识者或劝暂依西人公学,数年之后再复古学;或谓若废本国之学,必至国种两绝;或谓宜以渐改,不可骤革,急则必败。此数说者,下走竟不能折衷一是,思之至困[1]406-407!
就吴汝纶描述的日本参照西方的学制而言,要系统地学习西方的学问,需花上一二十年,如此再加上中国的旧学,不惟学生脑力承受不来,教学方法也不相兼容,所以吴汝纶认为“新旧二学,恐难两存”。针对吴汝纶的疑惑,日本教育者给出的建议有:暂时学习西人之公学,数年之后,有所成就,再复习中国之旧学,这是应急之策;逐渐推行西方之公学,使得中学西学兼而得习,这是兼顾之法。说到底,吴汝纶既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救国图强,又放不下中国几千年的旧学,延国延种,这正是困扰吴汝纶的问题所在。
或许正是因为与日本学者的接触,使得吴汝纶在跳出母体文化圈子后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之学问并非所谓的陈旧腐朽之物。作为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承袭者,吴汝纶对中国青年弃中学改习西学充满忧虑,因为文化的灭绝最终会带来依附于文化的种的灭绝。有了这些认识和顾虑后,在日考察学制的短短三个月间,吴汝纶致书林纾,请其代为整理曾国藩的《四象古文》:
欲请我公代校《四象古文》,亦但令敝门人常济生转恳,而无一函奉闻,此是我曹疏简常态,亦料此事乃我公所乐为,虽至忙迫,必不辞也。又冒鹤亭亦必愿校此书,弟今亦无函,以待我公之法待鹤亭,不得谓薄也。此书止敝处钞有底本,人间别无副钞,殆古今最精之选本,虽已刻之《经史杂钞》不能及也。方在振兴西学之时,而下走区区传播此书,可谓背戾时趋。然古文绝续之交,正不宜弁髦视之。此诚区区守旧之愚,不审严几道亦许此举为不谬否[1]422-423?
从《与林琴南》的这封信札看,吴汝纶在传播古文之时不是没有犹豫,即如信中所言,在振兴西学之时,而传播此书,可谓背戾时趋,是一种逆流,而这恰恰反映出两股力量颉颃时,中学所代表的一方有所加强,而产生这种变化恰恰是在东游日本考察学制之时。为什么选择林纾来为此事?这本身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林纾虽然在翻译外国名家小说方面成就颇大,对当时传播西方文化有功甚大,但是林纾与真正的革新派及其后的“五四”派相比还是相对保守,其在政治和文化上仍趋守旧,这从他坚持使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即可见一斑。吴汝纶深知林纾,故而此信中言:“亦料此事乃我公所乐为,虽至忙迫,必不辞也。”至于在信札结尾处道“不审严几道亦许此举为不谬否”,尤耐人寻味。查严复集,严复与吴汝纶信三封,其中有言:“文正公《古文四象》已为里耳之大声,集资印之,自为寡和之曲。然子云虽明知之覆瓿,尚终为之。先生勉为其难,未必无同志也。”[3]523据王栻考证,此信作于光绪二十五年除夕前一日[3]523。可见,吴汝纶久有谋刻曾国藩《四象古文》之意,但严复以为曲高和寡,并不合时宜,故而称吴汝纶此举是“勉为其难”。吴汝纶在旅日期间决意请林纾代校《四象古文》,这或许正是脱离母体文化后的一种反哺心理使然。
甲午海战后,严复在致吴汝纶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且今日之变,固与前者五胡、五代,后之元与国朝大异,何则?此之文物逊我,而今彼之治学胜我故耳。”[3]521很显然,在严复看来,此前五胡乱华、五代相争以及蒙元、大清对于中国的统治,虽然军事、甚至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他们落后的文化很快就被中国先进的文化所征服,正如马克思所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7]。但这次有所不同,入侵者所随同带来的西方文化从某种程度而言比固有的中国文化更精深,中国则有亡国及因文化消亡而亡种的危险。就在出使日本的前一年(1901年),吴汝纶在《答方伦叔》的书信中道:“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1]381严复与吴汝纶的这些言论都显示出对于西学盛行中学将绝的忧虑和痛恨。旅日期间,吴汝纶一方面感慨“新旧二学,恐难两存”,另一方面欲留旧学火种,显示出思想上的某些变化。
四、调和:“本源之教,尚在己邦”
从根本上言,吴汝纶等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代中国人,自然不愿意舍弃传统文化这条根。随着对西学了解的深入,特别是在日本脱离中国母体文化之际,吴汝纶逐渐形成并强化了一套认识,即欧美之学为富强之具,中国圣哲精神为本源之教。这在《复斋藤木》一书中有明显吐露:“特今世富强之具,不可不取之欧美耳。得欧美富强之具,而以吾圣哲之精神驱使之,此为最上之治法。吾今不能富强,故不能自用其最上之学。欧美以富强自雄,而遂诟病吾国文学,以为无用,则亦未窥最上之等级。而治术所由未臻于美粹者,此也。”[1]416吴汝纶认为,相比欧美等后起之国,中国实在可以称得上以“文”胜,文与道是一体的,得其道,并其文亦得。而后世失治,正是因为肉食者不得文,不能知晓圣哲精神之所寄,这并不代表中国圣哲之精神不足以治理好国家。在当时看来,富强之国为欧美,欧美富强的那套办法可以且应该学习,但若能将欧美富强之具与中国圣哲之精神相结合,则堪称最上之法则。中国未富强,不能用中国圣哲之精神驱使之,欧美虽富强,但不用中国圣哲之精神驱使之,所以都未能到达最上之等级。吴汝纶有此看法,或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这在《三岛中洲等欢迎会答辞》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线索:
细田君谓贵国与敝国有辅车之势,又谓利用厚生取之西国,而正德尚取自敝邦。佐仓君征引西国历史,属望敝国甚殷,而以兄弟阋墙,复能协和御侮为喜。皆与鄙怀暗合[1]445。
如上所言,吴汝纶此次东游,日本人接待极优,所至大会宾客,与为宴飨,谓之欢迎会,动辄数十百人参加。这与日本国家兴学开化风声所树有关,也与吴汝纶道德文章影响有关。在三岛中洲此次的欢迎会上,有细田君畅言,谓日本的利用厚生取自西国,而正德本源之教,尚依赖中国。这一说法,与吴汝纶心有戚戚焉。一直悬而未决的心底之惑,一直因国力上的衰败所引起的文化上的不自信,在游历日本期间,特别是在与日本学界有所接触后,终于暂获解答。“暗合”一词尤为值得关注,这是一种已有未发的状态,之所以未发或是因为其本身思路并不完整清晰,或是因为缺少天时地利人和等外在因素的诱发,于吴汝纶而言,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日本学者在欢迎吴汝纶的宴会上,肯定中国文化的“正德”之功,这不能仅理解为面谀之词,毕竟日本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影响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吴汝纶也正是从历史出发,认为中国之学不可尽废,毕竟曾创造过辉煌的文治武功。
为了解决东西文化对峙、古今文化割裂等问题,吴汝纶提出“取新未必全盘革旧”的渐进改良和部分改革的调和方案,并在这种改良和调和的方案中赋予儒学以独特的价值,并把这种价值上升到精神主权和延续种族的高度。这在吴汝纶游历日本的后期文字中时有吐露:
敝国以文字立教,近今经史高文,无能深晓,治化不进,职此之由;异国长技,但可相资益,本源之教,尚在己邦[1]428。
若但讲吾国旧学,甚多缺点,但因此遂弁髦吾圣经贤传、诸史百家,此必不能。西人好讲哲学,彼哲学大明,亦必研求吾国文学,以吾国文学实宇内哲学之大宗也。凡吾学之益于世者,其高在能平治天下,其次则言能达意,足状难显之情,此诚政治家必要之事,不得以空疏见诮[1]450-451。
或许是出使交流工作的需要,使者一般都要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虽然中国成为老大弱国,虽然中国是战败之国,吴汝纶在日本学者、官员面前固然表明“下走东来,仰求师法,实欲取长补短”的态度,但实际上吴汝纶内心始终尚存着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表现在,吴汝纶认为中国“文字立教”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后世不能深晓,才导致“治化不进”。那么,儒家文化究竟有没有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或“现代化”?就实际看,儒家文化中固然有消极的一面,如“安贫乐道”“安步当车”之类,但亦有积极的因素,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等。很显然,后世人如何择取、如何对待这份遗产则成为关键所在。
张朋园曾以“启蒙—疏离—革命”三阶段说来划分近代知识分子,并以为“从魏源(1794—1856)到黄遵宪(1848—1905)”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代,他们提出了器物和制度的改革观念;“梁启超和孙中山(1866—1925)”为第二代,他们有了疏离感,即将走向革命;胡适(1891—1962)无疑是第三代[9]。这种三阶段的划分为学界提供了一些参考,但真实情况则比这种抽象概括要复杂得多。比如以孙中山为第二代,显示出对传统文化的疏离,实际情况则是孙中山已经走向革命,并付诸实施。如果魏源、孙中山等可以算作近代知识分子,那么张之洞,甚至之前的李鸿章和曾国藩又如何排列?研究吴汝纶的思想,或许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启示。“中体西用”是伴随中国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各个阶段、每一个体对其理解则不尽相同。显然,李鸿章(1823—1901)以新式枪炮武装淮军,这已经是借西之“用”,张之洞(1837—1909)则明确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主张“新旧兼学”“艺政兼学”[10]。吴汝纶(1840—1903)虽不及张之洞较早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但显然属于近代第一代开眼看世界者。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中体西用”“实际上包括学术文化和政治文化两个层面”[11],即学术文化层面的“中学为体”和政治文化层面的“中教为体”。吴汝纶赴日考察学制,即是想在“学”上下功夫,引进西学,不尽废中学,而不尽废中学则又为延续中教(儒家大义)做准备。从吴汝纶晚年主张废除科举、兴办西学、培养新民的举措看,其应当超出张之洞等人“体用”思想的局限,显示出带有向近代过渡性质的特点。
“文化交流是一个文化相互渗透的过程,但首先又是一个相互选择、适应和匹配的过程……即便是一种先进文化,也不可能马上为落后文化全盘接受,更不可能完全取而代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盘西化’既无必要,也无可能。”[12]与当代学者的反思相比,吴汝纶所面对的是汹涌而来的中西文化冲突,置身其中与时过境迁毕竟不同。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学制主要就是寻求解惑的,而在日本期间形成“异国长技,但可相资益,本源之教,尚在己邦”等思想则是走出困惑后的某种自我肯定和回归。“西学东渐,为日尚浅,不可能迅即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旧思想旧意识毕竟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人们实际上不可能与之一刀两断[13],这也是造成一大批先驱思想、行为矛盾龃龉的根源。张灏曾言“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14],这是看到了晚清士大夫对于“五四”的先导作用,吴汝纶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