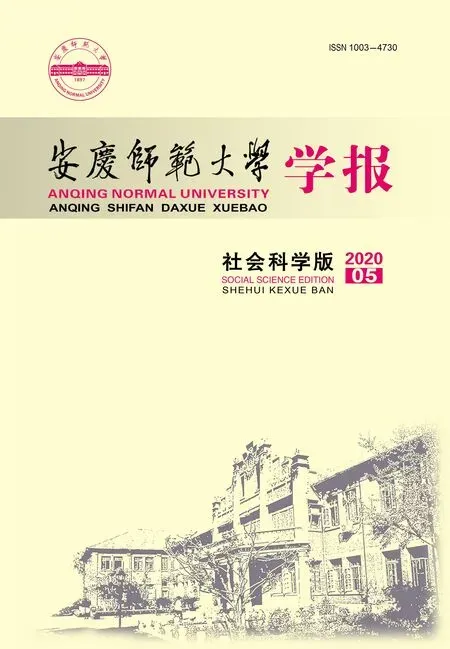桐城派文史研究的结合
叶当前
虽然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但桐城派研究界不同专业学者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文史互证的研究越来越丰富。文学研究学者在桐城派政治思想史、家族史、中外交流史、学术发展史、文学编年史等领域的耕耘更加精细,历史研究学者在桐城派史料、史学思想、桐城派与近代社会等领域的阐释更加清晰。持续推进文史研究的沟通与碰撞,在桐城文章中发掘史料、提炼史识、总结史法,在历史语境中对话桐城文章、思考桐城义法,当是桐城派跨学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桐城派文人重视经典史籍《左传》《史记》《汉书》等的笔法,其评点阐释的理论成果既是文学研究对象,也是史学参考材料;桐城派古文家或参与或主持正史及方志的修撰,在官方修史的工作中践行了桐城派创作理论;方苞、姚鼐、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等桐城派名家为时人写作了大量的传状、碑志、墓表等文章,是列传、文苑传、儒林传的重要参考资料;桐城派作家留存有丰富的笔记、日记,既是作者生平经历的原始记录,又是一个时代私人视角的剪影。故桐城派的史学研究不仅要从纷繁的文献中厘清史实,还要熟谙桐城派义理与经世相结合的思维,以文史互证的方法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同样,桐城派文人自觉的历史意识也为桐城派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线索与论据。如梳理桐城派发生发展史的问题,必然要以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吴闿生《〈吴门弟子集〉序》等桐城派文人的自述为主要依据,姚氏推歙县程晋芳、历城周永年为桐城文章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借势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经典化,遂举桐城派大旗,确立传承谱系;曾氏则明确以江西诗派与桐城派相比类,关注姚门弟子的开枝散叶,遍举桐城、新城、宜兴、广西、湘乡等地桐城派传人,从地域空间上坐实了“天下文章”,明确了地域与流派的关系问题;方宗诚则从唐、宋发掘桐城籍作家的诗文成就,诠释桐城派与唐宋八大家及归有光的关系,通过文章范本证实了桐城派“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创作理念;吴闿生身处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乃能在家学传承下求通求变,突出晚期桐城派的文教事业重视“中外大势、东西国政法有用之学”的价值意义,彰显“莲池群彦亦各乘时有所建树,或仕宦有声绩,或客游各省佐行新政,或用新学开导乡里,或游学外国归而提倡风气,或以鸿儒硕彦为后生所依归”的吴门业绩。回到桐城派自身建构的流派史,再参以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李详《论桐城派》、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论述,在历史线索中梳理桐城派文学史,大抵是不会错的。至于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为什么不设师事及私淑曾国藩的门人为一卷,亦值得文史研究者深入探索。桐城派文人的历史意识还表现在其诗文中存有大量标明的时间节点、地理空间、史实背景与事件经过,为理解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相结合的文章创作提供了实证。
本期刊出卢坡的《从“出走”到“回归”——吴汝纶旅日信札解读及其“中体西用”论辨析》与郑素燕的《薛福成史学思想初探》两篇论文,都是文史结合的研究成果。前者以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期间写给日本教育家、汉学家及国内同仁的书信为研究对象,剖析吴氏在空间转换背景下中西文化观的嬗变,从史料开掘思想,总结规律,虽是个案研究,却有推广价值。鸦片战争以后,桐城派文人不得不开眼看世界,曾门弟子中一批驻外使节投身外交事业,思考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留存的外交档案、往来信札、日记丛谈等自然是桐城派思想史的一手资料。后者以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庸庵笔记》为研究对象,阐释薛氏因势而变、学习西方的史学思想,同时也呈现了置身域外的桐城派文人保守与开新的思想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桐城派域外文献的汇辑集成与研究工作也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