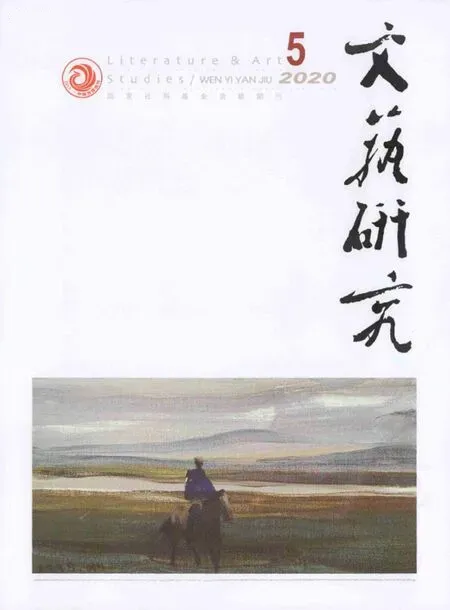周初文献搜求、整理活动考论
王 浩
周初曾进行过一场文献搜求、整理活动,但对其进行直接记述的史料比较少,遂使这一重要史实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然仔细分析西周文献所折射和反映出来的信息,不仅能够确认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亦可简要勾勒出其基本面貌与特征。此一问题的揭示,对于认识早期文献、历史的流传以及西周政治、思想、文化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今就周初文献搜求、整理活动发生的背景、文献来源及内容、方式等予以讨论,以求正于方家。
一、周初文献搜求、整理的背景与文献来源
周初的文献搜求、整理活动是在鉴古思潮和制礼作乐活动的刺激与推动下发生的。小邦周战胜大国殷以及殷代夏的史实,使周公、召公等人认识到天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转移的,从而提出了“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的天命观,进而发展出“天不可信”(《尚书·君奭》)的观点①。天命是否转移,关键看执政者能否敬德保民。周人虽然取得天下,但并未沉湎于成为天下共主的喜悦中,而是产生了深沉的忧患和戒惧意识。“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尚书·君奭》)“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尚书·召诰》)②在直面现实忧患与反思历史的双重促动下,周人认识到唯有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方能长久保有天命、坐拥天下。
这种新的天命观建立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强调对历史、人事和民心的重视。《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③《逸周书·芮良夫》:“古人求多闻以监戎(戒——引者校);不闻,是惟弗知。”④基于这种认识,周人涵养出“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国语·周语上》)、“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国语·周语下》)的重史传统和观览、咨问前代书面与口传文献以资借鉴的风气⑤。周人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夏、商两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对成功的统治经验加以提炼以供学习、效法,对罪过、错误和失败的教训予以归纳以供戒备和警惕。王晖指出:“历史意识的升华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批判总结,使周人逐步摆脱了殷人那种完全用神权来维护政权的思想观念。周初以武王、周公为首的姬周统治集团及其有识之士能够以历史理性来认识政治、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否定天命并提出‘敬德保民’等思想主张,推动了一场思想维新运动。”⑥文献是历史的重要载体,对前代文献的搜求、整理实质上就是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是以史为鉴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换言之,以史为鉴必然要求重视前代文献的搜求、整理,而文献搜求、整理活动本身也是以史为鉴的具体表现和应有内涵。周初的文献搜求、整理活动,不仅为思想维新运动的展开提供了丰富、可信的资料,而且为西周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历史和文献依据。
周初开始的制礼作乐活动也吁求对前代文献进行搜求、整理。随着东征的胜利和分封制的推行,周王朝的统治疆域进一步拓展,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被纳入到新的共同体之中。如何以周人的文化为核心吸纳、融合不同族群的文化,从而建构新的政治、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成为姬周统治集团面临的新课题。制礼作乐就是在继承、借鉴夏、殷文化的基础上,于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一场革新,开创了有周一代新的文化制度。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⑦这彬彬之盛的“文”不仅指礼仪制度,也包括文献典籍。记录、承载前代思想、文化的各类文献典籍,周公定然会收集、整理,以求为新的文化制度的创建提供借鉴。而丰富、广泛的文献来源为文献搜求、整理活动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初文献搜求、整理活动的文献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周人历代累积的文献,二是殷商储藏的文献,三是从各诸侯国搜集的文献。
周人历来就有重视文献的传统。自后稷、不窋时代起就拥有训典之类的文献,至迟在太王时期设立史官⑧,文王时代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文献典藏制度,设有专门管理档案文书、文献典籍的机构,从而累存了相当数量的文献。《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纂修其绪,修其训典。”《国语·周语下》又载:“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⑨商王朝从汤至纣约三十一王十七世,与周世系相当,则周弃应是夏末人。徐旭生说:“按周先公的世次,周弃生年当在夏朝的末叶。他到商代才被祀为稷神,也可以证成此说。”⑩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商人先公的二示——夏代末期,商人的典册此时已有简单的记事⑪。祭公谋父所说的不窋修后稷之训典,与中国成文历史开始的时间相吻合,当有所据。周族自古公亶父至周初立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史官也必会书之简册,藏于府库。《左传·僖公五年》载:“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⑫由周初至鲁僖公时代约四百年,其册命、载书仍藏于盟府,为春秋时人所称引,则周人对文献的重视及其典藏制度的完善可窥一斑。
同时,周人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接收了商王朝所藏文献。首先,克商前,殷商贵族、史官、乐官奔周携带来的文献。《吕氏春秋·先识览》载:“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⑬文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周本纪》)。武王时,“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史记·殷本纪》)⑭。这些贵族、史官、乐官来归,都携带着图法、典册等,至周后又多担任旧职,定然也会追记、补记一些重要文献。其次,克殷后所得商王朝所藏文献。《逸周书·世俘》说文王“修商人典”⑮。《尚书·多士》载周公告诫殷遗民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⑯说明商代确有典册文献流传。《墨子·贵义》云:“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⑰说周公朝读书百篇,当是夸张之辞,但从周初诸诰来看,周公对夏、商历史非常熟悉,缕举商代史事如数家珍,说明他确实掌握了不少夏、商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周公之子伯禽分封至鲁国,得到王朝赏赐的典册,陈梦家指出,“鲁国于周初分封时得典策彝器,其中或有商与周初的典策”⑱,则武王克商后将殷商典藏的部分典册带回宗周。再次,迁播殷遗至宗周所得文献。武王克商后曾将庶殷成族迁入宗周,一则强干弱枝,预防殷遗反叛;二则借重殷文化孕育人才,为新王朝服务。移居宗周的殷遗,其中不乏担任祝、宗、卜、史等职务者⑲。这些专门的技术人才分别掌有前代传下来的文献典籍及其职业文献,随着他们的迁徙,亦被携带、传播至宗周。
此外,在各分封国“敷求”“别求”前代书面文献和口传文献⑳。《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诸侯: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㉑
伯禽封鲁,得到祝、宗、卜、史、备物、典册等赏赐。《尚书·酒诰》记载周公告诫康叔要善待殷商的遗臣太史友和内史友㉒。“这两类史职人员,应即为卫国初封时与鲁国一样所得到的来自王朝的赏赐。”㉓《乍册孛由鼎》载:“康侯在柯师,锡作册孛由贝,用作宝彝。”㉔也可证明周初卫国设有史官。以此推之,唐叔理应也得到了王朝赏赐的史官。史官的重要职责之一是负责档案管理和文献典藏,给各诸侯国设立和赏赐史官,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文献的搜求、整理。因而《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慨叹“周礼尽在鲁矣”㉕,表明春秋晚期鲁国的文献典藏仍很丰富、完备。卫国的史官在春秋政治、文化舞台上表现十分活跃,著名的有华龙滑、礼孔、柳庄、史朝、史苟、史、祝史挥等人㉖。从《左传》所载春秋时代称引《书》类文献的情况看,“由周所封的姬姓国为引《书》的主要区域”,“传播最为广泛的区域为晋、鲁、卫三国”㉗。这与三国初封时就得到王朝赏赐的祝、宗、卜、史和典册有密切关系。卫为殷商旧地,便于开展对殷商文献的进一步搜求。唐为虞、夏旧墟,当更措意于虞、夏文献的搜求。《左传》所载晋籍人物称引《虞夏书》的频次明显高于其他各国,故陈梦家推断《夏书》可能为晋人所追拟㉘。可见,宗周以及卫、鲁、唐等诸侯国对上古、夏、商的文献均有搜求、整理。
二、周初文献搜求、整理的内容与文献类型
王国维曾指出:“《虞夏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商书》中如《汤誓》,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㉙这一论断隐含有周初曾对前代文献进行搜求、整理的意见。在此活动中,武王、周公起了主导性作用。史料所见,武王、周公比较重视下列几类文献的搜求与整理。
(一)文王言论、事迹的汇集、整理。周初在祖宗中特别尊崇文王。德行上,文王具备各种美德,是纯德的典范;政治上,文王伐密、伐崇、戡黎,“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㉚,奠定了周王朝的基业;宗教上,文王生时受天命,死后“在帝左右”(《诗·大雅·文王》)㉛,成为上帝的代理人。徐复观指出:
周公们所以能把文王与上帝结合在一起,乃由文王能明德、慎罚,保民、爱民,因为“文王之德之纯”。正因为文王在个人与政治上树立了最高标准的行为,上帝才看中了他,把“命”降落在他身上。他们(周公们)对国家兴亡之故,表面上说是决定于上帝,而实际则是决定于统治者的行为,由此而规定出政治的大方向,并由此而实际以“行为史观”代替了“神权史观”,这是殷周之际的历史发展的巨大关键。㉜
天命不易把握,但可以通过文王的具体德行得到启示。职是之故,周人对文王的言论、事迹进行汇集、整理,作为政治宣传的口号、治国理政的典则、反思历史的依据和教育后世的教材。《诗·周颂·我将》云:“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㉝《尚书·酒诰》云,“聪听祖考之彝训”,“尚克用文王教”㉞。这些“典”“训”“教”正是有关文王言论、事迹的文献类编。今《逸周书》载录文王的训、诰、命类文献多篇,其中《程典》《酆保》《文儆》《文传》,“保存了西周原有史料”㉟。清华简《保训》记载文王向武王讲述“中道”的遗言㊱;《程寤》讲述文王受命的来龙去脉,有些语句与《尚书·吕刑》《逸周书·小开》相类,成篇不会太晚㊲。
此外,周公等在诰命中征引文王的言论和故事,扩大了这些文献的流传。周公告诫卫康叔时称引文王发布过的戒酒辞来增强言说的权威性: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㊳
《大盂鼎》记载周王册命盂的命辞,也反映出对文王所颁戒酒诰命的熟悉㊴。《尚书·无逸》中周公诫勉成王要体恤百姓、不能贪图安逸,也强调要以文王为榜样,“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于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㊵。《逸周书·大聚》载周公对武王之问,劈头就说“闻之文考”,并称引文王“令县鄙商旅曰: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的命辞;《本典》记周公答成王之问亦以“臣闻之文考”云云为对㊶。这些正是周人“仪式刑文王之典”和“克用文王教”的具体表现。
(二)殷先哲王和古先哲王治国保民的德言。《尚书·康诰》云:“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㊷王引之《经义述闻》云:“言遍求殷先哲王之道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郑笺以‘敷求’为‘广索’,是其义也。”㊸周公告诫康叔,应当继续遵循文王学习殷人先进文化的传统,广泛寻求殷家古先圣王的治国之道。另外,还要广泛搜求古代圣王安定和治理人民的遗闻旧说。宗周典藏有周人历代累积的文献和商王朝部分文献,此处“别求”与“敷求”对举,属互文见义,主要是指在周族之外的他族广泛搜求前代文献。“敷求”“遍求”“广索”表明搜求的规模大、地域范围广。《逸周书·商誓》载武王告诫殷商旧官人说:“百姓,我闻古商先哲王成汤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怀,用辟厥辟。今纣弃成汤之典。”④从“我闻……”的引证方式看,武王所讲之语有其来源和依据,“成汤之典”表明殷末周初流传有记载殷先哲王诰命的典册和其治国理民的遗文旧说。
《尚书·康诰》将“殷先哲王”与“古先哲王”并举,则“古先哲王”当指夏代及上古的贤王。周初确实流传有不少夏代和上古的文献、传说与神话。清华简《厚父》记述周武王与夏遗民厚父关于夏朝兴衰的问答㊺,简文云:“□□□□王监嘉绩,问前文人之恭明德。王若曰:‘厚父!遹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少命皋繇下为之卿事,兹咸有神,能格于上,知天之威哉,问民之若否,惟天乃永保夏邑。在夏之哲王,乃严禑寅畏皇天上帝之命,朝夕肆祀,不盘于康,以庶民惟政之恭,天则弗,永保夏邦。’”㊻武王认为,夏朝的崛起和兴盛,关键在禹、启等哲王能够勤政爱民、重用贤臣、敬畏天命、恭敬祭祀。武王对夏代历史的追溯以“遹闻”打头,说明其所述有文献依据。《尚书·吕刑》引“若古有训”论证修刑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其中涉及蚩尤、重黎、伯夷、禹、后稷等人物的事迹㊼。《逸周书·尝麦》也是记载周穆王时期正刑书的文献㊽,其所引“古遗训”述及黄帝、赤帝(炎帝)、蚩尤、少昊、大禹等上古人物的故事㊾。称之为“古训”“古遗训”,说明是从西周以前流传下来的文献。此类文献和传说,卫康叔定然会留意搜求、整理,以资借鉴。
(三)商代贤臣的嘉言善语。周公认为贤臣在辅佐君王治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告诫康叔要重视对贤人言论的搜求、整理。《尚书·康诰》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㊿要求在“敷求”古先哲王、殷先哲王“德言”的同时,搜求商邑中老成人的言论,用心体会他们的训教。《尚书·君奭》云:“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曾运乾解释说:“陈,久也,此云‘有陈’,犹《庄子·寓言篇》之‘陈人’,所谓老成人也。”即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贤、甘盘等贤臣。商代一些贤臣的事迹、言说经搜求、整理后流传后世,影响深远,并产生了一些托名文献。比如伊尹,《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伊尹》51篇,小说家《伊尹说》27篇。今传世文献中存有《伊训》《咸有一德》《太甲》的佚文。清华简关于伊尹的文献有《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和《汤在啻门》等5篇,其中《尹至》《尹诰》是伊尹见汤时的对话,属于《书》类文献;《汤处于汤丘》与《汤在啻门》以阐述伊尹思想为主,道家色彩明显,当为战国时的依托之作;《赤鹄之集汤之屋》则是比较典型的“其语浅薄”的小说家言。又如傅说,《国语·楚语上》载白公子张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贾逵、唐固云:“《书》,《说命》也。”⑤《说命》佚文见于《国语·楚语上》《礼记·文王世子》《学记》《缁衣》《孟子·滕文公上》等。郭店简《成之闻之》称引的“允师济德”也是其佚文。清华简《说命》为傅说作书以命高宗,内容与《国语·楚语上》所记载的傅说事迹相近。后世也流传有《仲虺之告》《史佚之志》等专门记载殷、周贤臣嘉言善语的文献。这些均可说明,商代一些贤臣的言论、事迹经周初搜求、整理后广为流传。
(四)夏、商刑法文献。周人治国,“明德”与“慎罚”并重。文王能够做到明德慎罚,所以肇基了周邦王业。武王秉持明德慎罚之道,最终获得天下。“明德慎罚”思想是周人奠定基业、获得天命、攻取天下的致胜法宝。取得政权后,周公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对其内涵作了进一步的提炼、升华,使其成为周王朝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尚书·康诰》云:“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又云:“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孔颖达解释说:“既卫居殷墟,又周承于殷后,刑书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谓当时刑书或无正条,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无条,求故事之比也。”强调决狱时要参考借鉴殷商的经验和做法,亦即整理、学习、吸收殷刑中的合理内容。《荀子·正名》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殷代刑法的系统、完备与严苛。周公命康叔师法殷罚,不止因其国俗,也是因为殷商刑罚比较完备、允当的缘故。
刑法文献是重要的《书》类文献。《墨子·非命上》说:“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大方论数,而五(三——引者校)者是也。”墨子将先王之书分为宪、刑、誓三类,这与伏生本《尚书》的内容比较接近。《尚书·康诰》明确提出“明德慎罚”思想;《吕刑》专门谈法,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献之一;其他如《尧典》《皋陶谟》《洪范》《酒诰》《梓材》《多士》《立政》《君陈》《费誓》等篇章也有与法律相关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法学价值。
夏、商刑法文献在春秋、战国时期仍有流传。《左传·昭公六年》载:“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刑》至战国时仍有流传,《墨子·非乐上》云:“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⑥《吕氏春秋·孝行览》:“《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高诱注:“商汤所制法也。”二者所引皆为《汤刑》中的内容。《左传·昭公六年》又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杨伯峻注:“《尚书·吕刑·序》云:‘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曾运乾《尚书正读》:‘命,告也。训夏《赎刑》者,申训夏时《赎刑》之法耳。’是相传夏有《赎刑》,亦曰《禹刑》,未必为禹所作耳。”则夏《赎刑》在穆王时代还能看到,直至春秋晚期仍为叔向所熟知。这些文献在后世的流传,恰可印证周初对夏、商刑法文献曾进行过专门的搜求、整理。
(五)前代口传文献。夏、殷文献,除典册文献之外,还有许多是口述文献。周人分封前代圣王之后的举措,避免了一些文献在殷周易代之际湮灭。《吕氏春秋·慎大览》云:“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巳(杞——引者校),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将武王分封圣王之后定在“入殷,未下舆”和“下舆”之时,恐为缘饰之辞。但武王克殷后,确有分封圣王之后的举措。《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礼记·礼运》记孔子之言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巳(杞——引者校),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时》,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杞为夏后,自然保存有夏代流传下来的文献。现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其经文部分当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国语·晋语四》载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关尧、舜、禹、启等上古时代的口述文献,经这一举措得以部分保存。杨希牧指出:“纵然所传《夏书》和《虞书》非必当时人的记载,但未必非商、周之世的学者根据民间传说编辑而成,正如汉以后各代正史皆系后代学者所编一样。尤可注意的,即五帝之后裔均曾为周武王所分,迄于春秋之世,其后裔仍存在,如陈为舜后、莒为夏后之类。《夏书》《虞书》或者即是据五帝后裔所记忆的祖先事迹续或传说而辑成的。”分封先王名姓之后使上古口传文献得以保存、流传,部分文献被书写记录下来,作为后世治国的参考和教学的材料。
(六)前代诗乐文献。周代礼乐文化繁盛,王公贵族有撰作诗歌的雅好。清华简《耆夜》记载武王八年伐黎大胜之后,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典礼。武王作《乐乐旨酒》《辆酋乘》诗二首,周公作《赑赑》《明明上帝》《蟋蟀》诗三首。《周公之琴舞》记述“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卒”,“成王作儆毖,琴舞九卒”。此可与传世文献记载的武王、周公、成王作诗的说法相印证。出于礼乐文化建设的需要,周人对前代礼乐文献非常重视。克商前,商王朝乐师携乐器归周,部分诗乐文献亦随之入周。《史墙盘》记述,武王克商后微史烈祖来见武王,武王命周公在周地给他住所,“俾处甬”。“俾处甬”同窑30号器作“以五十颂处”。“颂”“甬”古音极近,是指一件事情,即掌管五十种威仪。《国语·鲁语下》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说明周人掌握了比较多的商代颂诗。今本《诗经》所保存的五篇《商颂》即为殷商旧歌,只不过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加工润色。前代乐舞如《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等在周代也得到传习,展演于各种典礼仪式之上。此外,周初可能也有采诗活动,收集各诸侯国的歌谣,用于体察民情和政治取鉴。
周初文献搜求、整理活动所涉文献,时间上跨越上古、夏、商,尤重殷商和周人自己的文献;文献形态既有书面文献,又有口传文献,亦旁及图像文献;既有对前代文献的搜求传承,又有整理创造,催生出新的文献;夏书、商书、殷书、夏训、商人典、成汤之典、典刑、占书、商周虞夏之记以及典、册、训、教、刑、志、言、记、箴、铭、颂等称名,反映出当时已有文献分类的意识。类分文献,不仅便于保存、查阅,也凸显出文献的不同性质、形态和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体学意义。
三、周初文献搜求、整理的方式与特点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种剧变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的跃迁。从甲骨文来看,“殷人的精神生活,还未脱离原始状态;他们的宗教,还是原始性地宗教”,“周人的贡献,便是在传统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自觉的精神;把文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升而为观念方面的展开,以启发中国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周人虽然信奉天命,但周人的天命观与德相联系,促使政治重心从鬼神转向人事,呈现出重视道德人文价值和历史理性的特点,从而使历史意识获得了解放。
这种对前代历史祛魅化的要求,势必规范着此次文献搜求、整理活动的导向与趋势。以史为鉴的需求对文献搜求、整理活动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文献的选择。在新思想、新观念的指导下,那些符合周人期待的文献被选择、整理,而不符合新思想的文献则被有意识地遗弃和淘汰。二是文献思想、观念的改造。晁福林指出,周初的“以史为鉴”是通过改铸历史的办法来实现的。周公多处所讲的夏鉴和殷鉴,都是有针对性的,这些历史教训完全服务于周初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这种历史教训里的“历史”,只能是改铸后的历史。接受历史教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改铸历史的过程。不经改铸,历史鉴戒就无法进入人们的历史认识领域。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流传下来的早期文献在思想观念方面与周代思想观念高度吻合的重要原因。
文献搜求、整理活动促进了新文献的产生。相比之前的文献,新产生的文献在性质、形态与功能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口传文献向书面文献转化。周初许多文献依赖口耳相传,文献搜求、整理活动促使部分口传文献转化为书面形态。周初非常重视对前代哲王、贤臣言论的搜求、整理。《礼记·文王世子》云:“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沈文倬解释说:“养老与乞言、合语联系在一起。乞言者,向年老的贤者探求善言。合语者,在欢宴时‘得言说先王之法’。”《礼记·内则》云:“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皆有惇史。”乞言、合语之礼上老者所告教、晓谕之言由史官进行记录,转变为书面文献。
《尚书·洪范》就是武王咨政于箕子时,由箕子陈述而被史官记录下来的一篇文献。《洪范》开首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村南西周甲组宫殿遗址西厢二号房内窖穴H31出土的一片甲骨刻辞记载:“唯衣鸡子来降,其执眔厥吏。”“鸡子”即“箕子”,颇可佐证《洪范》的记载。据箕子所言,《洪范》传自夏代。文章采用“以数为纪”的结构,通篇大体押韵,符合口诵特点,表明该篇最初确为口传文献。清华简《保训》云:“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堪终。汝以书受之。”“书”指用简册记录文王的遗训。
从文献载体来看,这些文献既可载录于简册,也可记载在玉石或金版上。《尚书·顾命》云:“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蔡沈《书集传》云:“大训,三皇五帝之书。训诰亦在焉。文、武之训亦曰大训。”曾运乾认为:“‘谓礼法,先王德教,虞书典谟’是也。”王国维《陈宝说》则谓:“大训盖镌刻古之谟训于玉。”其实,三说并不矛盾。蔡氏、曾氏强调“大训”的内容,王氏强调“大训”的载体。将古人或文、武之谟、训书刻于玉石或金版,以为宝器,欲使传之久远。《逸周书·大聚》载武王“乃召昆吾治而铭之金版,藏府而朔之”。孔晁注:“朔,月旦朔省之也。”陈逢衡云:“国有大训则书于版,重其事也。”又《逸周书·武儆》:“丙辰,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孙诒让云:“‘金枝’,当作‘金版’,‘版’俗作‘板’,与‘枝’形近而误。”
第二,档案文书向《书》类文献转化。李零指出,古代“书”的概念包含三方面的内涵:文字、档案文书和典籍古书。早期古书脱胎于文书档案,但不是文书档案的照搬,而是经过了删选、改编。有些可能是原始记录,有些可能是后人拟作,有些是收集故老传闻改编的故事。选取标准也多是谈话、议论中有一定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篇章。经整理的文献,在性质、形态和功能上对原始档案都是一种超越。形式上,史官在编纂档案时进行选择、增删和改动,如增添时间、地点、人物、情景、原因、结果等背景性文字;有的还会处理成对话形式;或者将部分词语替换成当时的通行语;或将产生于不同时间的与同一事件有关的文书类编在一起,等等。如《尚书·禹贡》开首即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公》亦云“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禹敷土”三字全同,所叙内容与《禹贡》也相吻合,可能《禹贡》中的九州部分在西周前期已有传本流传,故二者相似。今本《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等文献,从性质上讲,都已不是原始的档案文书,而是经过改编的《书》类文献。这些文献,既保留着文献产生时代的印记,又有明显地经过后世整编的痕迹。档案属于小众文献,主要用于查阅,“书”则属于大众文献,主要用于思想传承和教育,“书”是对档案的提炼与升华。
第三,征引促动文献的传播与经典化。征引是《尚书》《逸周书》中西周文献的一个显著现象。从征引方式来看,主要有“古人有言曰”“我(余)闻在昔”“我(余、朕)闻曰”“我闻惟曰”“我闻亦惟曰”“若古有训”等作为标志性开头,也有直接引述具体篇名的,有的则没有明显的称引标志。引证是当下与传统的对接,是增强话语权威的手段。周初大量的征引现象显示出对前代格言、历史故事和传闻的重视,也反映出周初文献的丰富内容和多样形态,可视为周初搜求、整理前代文献史实的旁证。征引现象不仅显示出对文献文本意义和价值的重视,同时扩大了文献的传播,促动了经典文献的形成。
从文献生成角度来看,征引往往并非是对原来文献的照搬。为了适应新思想、新观念表达的需要,征引时经常会有删节和改动。一些宗教、礼仪文献,通过征引,脱离了仪式语境,文本本身的意义得到凸显和增殖,故而又成为新的文献。比如《无逸》: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太宗,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太宗之享国三十有三年。其在〕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以“我闻曰”打头,说明其所言是征引文献。这段文字重点讲述殷太宗、中宗、高宗各自的经历、德政。值得注意的是,周公对他们的享国年数也言之凿凿,他可能是以殷商时代流传下来的世系类文献作为蓝本和依据的。《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⑨饶宗颐指出:“殷时有正式负责世系专门官吏之小史,所以记录非常审谛,可证周官所言的小史,是可信据的。所谓奠系世意思是审谛地去厘定世系,这有如后代禅宗灯谱之慎重处理。古代有这样的专职,应该说是谱牒学的萌芽。”世系类文献本由史官和瞽矇共同掌管,用于世系厘定和仪式讽诵,是典型的宗教、仪式文献。甲骨刻辞中的祀谱刻辞和家谱刻辞也可资佐证。但周公所引,明显是对殷商世系文献的删节、改造,也脱离了具体的仪式语境,凸显的是文本本身的意义和教育功能。虽然是称引,但性质上属于新的文献。《国语·楚语上》申叔时所说的“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指的正是此类性质的世系文献。
综上所述,周初的文献搜求、整理活动,是今可考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文献搜求、整理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使大量前代的书面文献和口述文献得以保存、流传,为《尚书》等典籍的整编成书提供了丰富材料。对前代文献的保存、转化、改造和征引,推动了早期文献的书面化和经典化进程,促进了中华民族重视保存与整理文献传统的形成,并发展出比较完备的文献制度,文献自觉意识也逐渐形成。这是中华历史、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能够持续传承、发展的重要基因。
⑥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⑦㉚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页,第108页。
⑧ 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页。
⑩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⑪ 参见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
⑱㉘ 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页,第108页。
⑲ 参见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6—143页。
㉓㉖ 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332页,第332—340页。
㉔㊴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第183页。
㉗ 马士远:《周秦〈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7页。
㉙ 王国维:《古史新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㉛㉝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46页,第945页。
㉜ 徐复观:《有关周初若干史实的问题》,《两汉思想史》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㉟ 刘起釪:《〈逸周书〉与〈周志〉》,《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5页。
㊱ 参见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
㊲ 参见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㊸ 王引之:《经义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00页。
㊺ 《厚父》中的“王”究竟指谁,尚有争论。李学勤、杜勇、刘国忠等认为是周武王,论证可信,故采其说。参见李学勤:《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深圳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杜勇:《清华简〈厚父〉与早期民本思想》,《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刘国忠:《也谈清华简〈厚父〉的撰作时代和性质》,《扬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㊻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10页。
㊽ 参见李学勤:《〈尝麦〉篇研究》,《古文献丛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