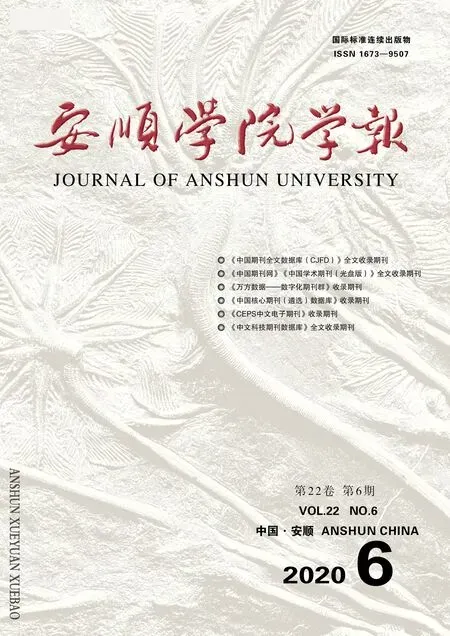《贵州山民图》的艺术源流
黄 斌
(安顺学院艺术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庞熏琹(1906—1985年)是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先驱者和中国现代设计艺术教育的开创者。他于1930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后,与一批艺术同仁发起组织了“决澜社”,决意掀起中国新艺术的狂澜。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美术社团之一的主要组织者,“决澜社”时期,庞熏琹吸收了西方流行的现代画派,其作品呈现明显的西式趣味、装饰趣味。在巴黎画派和法国装饰艺术运动鼎盛时期,庞薰琹于1925年到达法国留学。作为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传统教育而又充满艺术幻想的年轻人,庞薰琹如同海绵一样吸收着巴黎无处不在的艺术养分。这种随处可见的绚丽多彩的世界使他意识到“原来美术不只是画几幅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1]。从这个时期他就对装饰艺术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对于装饰艺术的毕生追求埋下了注脚,他所思考的,所追求的是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这也是庞熏琴一生的艺术探索。
一、《贵州山民图》研究现状
对于庞熏琹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傅雷和倪贻德分别撰写了《熏琹的梦》(傅雷)、《决澜社的一群》(倪贻德等)。①延续至今,对于庞熏琹的艺术创作思想与教育思想、工艺设计、回忆文章、大事年表等方面,许多学者进行了专题论述。庞熏琹在留学期间、回国伊始、决澜社时期、抗战时期、建国初期的艺术创作有几次较为显著的转变,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转折标志之一就是《贵州山民图》的创作。
对于《贵州山民图》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贵州山民图》的绘画内容与艺术特色的介绍阐述,此类文章主要有顾朴光、顾雪涛的《庞熏琹与“贵州山民图”》[2]、裴临风的《从留学西洋到回归东方——庞薰琹〈贵州山民图〉创作成因与艺术特色探析》[3],上述文章对《贵州山民图》的图像内容与创作手法进行了分析论述,都关注到了庞熏琹对于民族艺术的浓厚兴趣,意识到庞熏琹中西融合的探索意图。二是论述《贵州山民图》对于现代绘画创作的影响:将视角关注于其历史脉络的主要有杨肖的《“职贡图”的现代回响——论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创作》,将谢遂的《职贡图》与《贵州山民图》进行对比,认为在画面的“内容、媒材、技法和形制”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而差异主要存在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贵州山民图》的视野与《职贡图》不同,《职贡图》是帝国视野,《贵州山民图》则是民族国家视野,具有现代民族学视野;其次,《贵州山民图》的功能定位与《职贡图》完全不同,《职贡图》是官修绘画,反映帝王意志,而《贵州山民图》系列则是个人创作,呈现出高度风格化的倾向,融合了不同来源的观念图式,是庞薰某在跨文化、跨媒介意识下重构本土文化传统的现代艺术实验[4]。袁峰的《庞熏琹〈贵州山民图〉系列作品的价值及对当代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启示》[5]将视角转向《贵州山民图》对当代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影响,论述艺术创作与情感的联系,强调庞熏琹艺术创作的思想境界与对山民的深厚情谊对于其创作的积极作用。
上述研究分别站在作者关注的角度展开了关于《贵州山民图》的研究,丰富了《贵州山民图》研究的层次,本文试从其创作的源流、同时期苗族题材绘画的分野,以及《贵州山民图》的图像分析、风格特征等角度对这一系列作品展开阐述论证。
二、庞薰琹早期艺术思想
在庞薰琹晚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的回忆中,对巴黎的观舞、漫游经历津津有味的描绘可以清楚地呈现其悠游的留学时光,与现在名声显赫的常玉的交集,使得他对西方现代艺术与东方韵味结合的迷恋显得自然而然。博物馆、画廊和展览会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艺术的多样化和多重探索导致了他的短暂迷惘。而常玉那散发现代气息与东方意趣的绘画无疑吸引了同时代人的关注,对庞薰琹的启发和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庞薰琹也学习常玉用毛笔画速写,对于线条和用笔的练习使其作品的画面呈现出中国传统绘画的韵致,线条的流畅与雅致成为庞薰琹绘画的艺术特征。巴黎期间几千幅线描作品锤炼了其画面表现能力,这与西方现代艺术以线造型,注重装饰性和平面性相吻合。西方现代艺术介绍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写实绘画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私立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学报《美术》,连续对西方最新的艺术流派进行了介绍。莫奈、塞尚、马蒂斯是日本青年画家的梦想,也随着留学日本的学生“梦”到了中国。
20世纪初,在经历了19世纪晚期对西方文明功利实用性的引进学习之后,中国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由器物性转而关注精神性的思考,中国美术进入现代化演进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关于中、西美术的大论战拉开帷幕,其余绪可以说延续至今。其时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藏画目》之序言为开端,康有为的言论在当时有多大影响不好下定论,但是确实是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的主流意愿,他们用实业、工业、技术等一切实用文化来取代书斋里的传统文化,写实的、实用的艺术被一部分文化界人士所赞美,写实主义得到倡导。而黄宾虹的“化古为新”,吕澂与陈独秀关于美术革命的讨论,吸引了众多希望博采众长、融合东西的实践者的认同。留洋归来的艺术家,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归来,有着“求真”“求美”的纯朴艺术追求,尊崇东方传统绘画和西方现代艺术,直观认知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创作心理和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意象创作相契合,在此误读的基础上认为二者内在创作思想是一致的。他们试图将西方的文化艺术与传统的东方文明相融合,用现代文化改良传统文化,在艺术界,就是将许多艺术流派与中国趣味嫁接,创造文化趋同的新的艺术形式,是对陈独秀“美术革命”论的反正,“决澜社”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
归国之初的庞熏琹仍在继续进行形式探索,创作了《自画像》《屋顶》《绿樽》等作品。这个时期的作品面貌与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虽面目多样,但庞薰琹这个时期的作品还是可以依稀辨认出立体主义、野兽派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现代运动,正如当时许多画家手握两只画笔的实践一样,尝试西方现代艺术创新思潮与中国国粹的艺术精神碰撞,试图开辟出一条新的形式之路,重估中国艺术价值。“决澜社”时期庞熏琹的《地之子》《无题》《如此上海》《如此巴黎》《藤椅》《裸女》《路》等作品的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尝试,就是这种艺术思想的实践,是源于探索中西融合的艺术思想。1932年的《熏琹随笔》道出了其艺术思想:“我国古今好的作品我们应该研究,世界各国好的作品我们也应该研究,但是不一定呆板板地模仿”“我想,我们不妨尽量接受外来的影响,凭它们在我们的神经上起一种融合作用,再滤过我们的个性来著作、来创作。”[6]他不预设界线,融合中西,用传统的媒材,寻求一种现代的绘画之路。庞熏琴这个时期思想代表了同时期许多留洋归来的画家们的真实的想法,这些走出国门的画家大多有着深厚的国画功底,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虽在国门之外见识了万花筒一般使人眼花缭乱的艺术流派,但内在的东方文化修养决定了他们艺术探索的方向。作为具有现代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难于在那个时代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而只关照个体精神世界,因此庞熏琴一贯认为艺术家不应脱离时代而应该将自己的艺术探索与追求与时代结合,将中西文化结合,去体验观察生活,让作品反映艺术家的思考。
三、《贵州山民图》的时代背景
1939年庞熏琹参与了民族语言学家芮逸夫主持的苗族地区调查工作,进入西南的贵州地区。这次苗区的民族学田野考察工作,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纹样的基础上,增添了其对苗族丰富的民间工艺美术的深刻印象,是为记录,也是个人的兴趣所在。他在深入实地考察之后,对苗民们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这份感情既有对底层困苦人民的同情,又有对少数民族风情的好奇,二者合为一体,促使他发出了强烈的创作热情,于1940至1944年间创作了在现代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以苗族题材为主题的绘画作品《贵州山民图》系列共计20幅作品。
芮逸夫与凌纯声、勇士衡于1933年起就前往湘西苗族地区调查,他们所做的调查详实深入,涵盖苗族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式出版的著作共有十二章节,并另有附录和图片),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技术设备——摄像机,可见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已意识到图像之于考察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的爆发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一个转折点,科研院所和大量学者向大后方迁移,进入西南边疆地区,客观上提供了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研究的便利。正是在这个时期,庞薰琹对于装饰艺术的喜好愈加浓烈,这与滕固、俞剑华等人将考古学方法引进美术史研究领域不无关系。庞薰琹痴迷于传统装饰纹样,专注于收集整理,用传统的白描手法绘制传统的纹样,他的《中国图案集》使他得到偏隅西南的知识分子精英推崇,亦使得庞薰琹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与芮逸夫的苗族调查。此次调查主要是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苗民的生活习俗、服饰文化也是考察的目的之一,虽有当时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记录,但记录服饰纹样还需要庞熏琹这样的画家来细致刻画。庞熏琹与芮逸夫先后在贵阳、花溪、龙里、安顺等地八十多个苗族、布依族和仲尼族村寨展开调查。调查过程中,在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情感后,丰富多彩的苗族装饰图案在民间生活中的高度创造性运用,激荡起庞熏琹创作苗族题材绘画的冲动。
西南调查之后,庞熏琹创作的《贵州山民图》系列,一改前期作品有点硬性、机械的分割方式,使用中国传统的毛笔和绢用水彩颜料作画,耐心细致地刻画苗族女子的服饰纹样,这既是当时的考察需要,也是庞熏琹艺术探索的回归,回归到更为浓郁的东方趣味和含蓄的文人情感。《贵州山民图》的创作说明庞薰琹走出了对西方艺术的简单模仿阶段,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较之同时期董希文的《苗女赶场》可以清楚地看到民国时期苗族题材绘画的分野,一方面是庞熏琹几乎是拷贝一样,将苗女的服饰纹样一丝不苟地记录在画面上,用更为中国化的技法结合西化的形式语言,在忠实于苗族生活原型基础上,表现苗民生活与艺术情感;另一方面是董希文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用率性而奔放的笔触,用纯粹的西化媒材——油画结合少数民族题材,在模糊苗族生活原型的同时,自由抒情地展开艺术诉求。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对现当代苗族题材绘画影响至深,时至今日,苗族题材绘画还是在这两条艺术之路上发展前行。
《贵州山民图》是庞熏琹艺术探索的另一个阶段,西方的现代艺术手法隐没在中式的题材和内容中,与传统的文人画、人物画、山水画都不太一样,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庞熏琹对形式主义美学探索的另一层意义,即在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此种“新中国画”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这里所谓的“民族形式”,绝不是所谓的“国粹形式”,纯然“国粹”与纯然“西洋的”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文化立场正是现代社会文化趋同现象的一种表现,弥散在现当代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之中,《贵州山民图》系列体现了这种文化立场在中国美术现代化演变中的姿态。
四、《贵州山民图》的艺术源流及风格
明清时期,在国家重视边疆治理背景下,少数民族民俗民情载记、绘画作品的撰写、创作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视。文字作品如《黔记》《黔书》等,绘画作品如《百苗图》之类,都是其产物。源于《职贡图》描绘民族图像,用于记录边疆民族形貌,识其土俗的绘画早已有之。其中描绘苗族形象的图书多种,名目多样。计有《黔苗图说》《黔苗诗》《苗蛮图册》《蛮僚图说》《黔省各种苗图》《贵州全省诸苗图说》《苗蛮图》《苗图百幅》《百苗图泳》等贵州民族图集数十种。
庞薰琹是否见过明清苗族图册,虽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是据记载“民国时,国立北平图书馆有《苗民图》8卷,彩色绘本;《贵州全省诸苗图说》2卷,l册,旧钞(抄)本,《贵州苗民图》1册,清绘本(色绘》(按:后2种今藏北京图书馆)。北平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有《黔苗诗说》1册,旧钞(抄)本。未注明收藏处的有《长黔苗图说》抄本,《贵州百苗图》民国2年石印本。”[7]以及芮逸夫明确说过在北平见过此类图册而不得,可以推断庞薰琹应该也是见过这种绘本的。
照相技术没有出现的时代,画工手绘边疆民族的人物和生产、生活场景,同时配以文字,用以说明民族历史演化、来源、迁徙、性格特点和民族关系。清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西南少数民族种类繁杂,不易辨别,因此,清代绘制《苗蛮图》蔚然成风。《苗蛮图》类文献在西南少数民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描绘细致的视觉图像,为贵州民族提供了形象资料。这类图册不尽相同,但多运用白描或工笔重彩,注重人物形象、发式、头饰、项饰、服饰、器物、建筑、娱乐场景、祭祀活动等细节描绘为共同特征,此类绘本基于实时实地的记录,忠实记录是其首要,具有较强的可信性,为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传统苗民图的典型是描绘几个苗族人物的活动或生活劳作的场景,一般没有背景。这些不同版本的苗民图册因画家的文化教养、审美趣味、社会阶层不同,表现出来的艺术形式、风格又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地以风俗画、文人画来划分。早期的苗民图具有明确的文献工具性,艺术性不强。

图1 《采摘》(庞薰琹)
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是在走进苗区,深入实际体验的基础上所创作的,是对《苗蛮图》《皇清职贡图》的一些不实和歪曲的反正。庞薰琹对一些《苗蛮图》绘本的歪曲和猎奇描述十分反感,在对苗族的人物形象、性格特点和生产、生活习惯进行深入了解基础之上,在纸本和绢上用水彩和中国传统毛笔绘制了他所强调的民间的、源于生活的、真实的民族形式。他借用了《苗蛮图》的题材,如回娘家的苗女、芦笙舞、射箭、捕鱼、收获等场景,延续了注重人物形象、发式、头饰、项饰、服饰、器物、建筑、娱乐场景、祭祀活动等细节描绘的艺术特征,注入其中西融合、装饰意味浓厚、唯美化的艺术理想。《黄果树瀑布》《车水》《丧事》《射牌》《洗衣》《苗人畅饮图》《跳场》《芦笙舞》《背柴》《名族少女》《赶集归来》《背篓》等就是他对《苗蛮图》艺术特征的延续,体现了比较忠实于苗民生活记录的艺术追求。

图2 《赶集归来》(庞薰琹)
《采摘》和《赶集归来》以写实的手法描绘苗族女子的形象,画面借用了西方肖像画的构图,人物形象饱满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背景是纵深的远山丛林。庞薰琹不厌其烦地细致刻画了女子头巾和服饰上的彩色织锦纹样,以线描为主,较为准确地呈现了黔中苗族女服的基本款式。女装多为交领对襟衣、中长褶裙,且上衣多附有披带、背牌、多层衣脚等配件。颇富特色的多层衣脚、披带、背牌等配件的工艺手法多样,以挑花最为普遍,间用蜡染、平绣、锁丝、色布镶补、织花等,图案多为几何纹,也有鸟蝶花卉等纹样。妇女头饰各地有别,或以布缠头,或戴帽,或包帕。银饰有耳环,项圈、手镯、头簪等。当时的苗族被分为杂苗、花苗、青苗、白苗、红苗等,庞薰琹对调查过程中所见的民族服饰作了详尽的记录。如花苗的挑花装饰,黑布上的白色挑花和红线陪衬。正方形的背牌为花衣的主要装饰,有挑花的附加装饰为背带、围腰。而花溪的青苗衣服较为简朴,没有挑花,仅在对襟和衣袖处有两道镶边;龙里的白苗的阔边帽,背挂蜡染布条。这些他都在自己的回忆录和作品中,用文字和图像作了忠实的记录。庞薰琹的这批绘画中的人物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高更所描绘的塔希提女子,面部表情平静而安详,色彩几乎是平涂,虽着苗族服装,人物形象其实不太接近真实的苗民,人物肌肤粉嫩紧致而有淡淡忧伤之感,晕染五官,立体感强烈,服饰下人体体积感的表现完全是油画手法,背景植物的刻画使用了西方古典油画背景的处理方法,人物神态的东方韵味与绘制手法的西化浑然一体。他已经从偏重于形式的分解构成逐渐进入了对绘画本体语言的完善和个人感受相结合的境地,作品的技法轻松自如,具有明显的抒情意味。描绘农家女子却有深闺小姐之忧郁气质,流露出他的个人气质。作为一名有教养的艺术家,在深入穷乡僻壤,看到最底层人民的真实困苦的生活后,庞熏琴所能做的只能将一切感受表达在画面中,但是理想和浪漫的情怀使得他表现底层人民也是委婉而含蓄。
庞薰琹抗日战争时期对中西融合的探索,较之其早期作品,已有所不同。他更多地注意了造型的准确性,力求依循形体结构用笔用色。在设色上,肌肤晕染表现肌骨起伏转折关系,强化人物的立体感。其作品力图将西方的造型元素与国画的情趣结合,与同时期的林风眠、徐悲鸿等人的想法接近,但在画面的呈现上却又不失个人的美术艺意蕴。如果说庞薰琹早期及“决澜社”时期的绘画还是注重西方绘画的形式因素,与林风眠的探索接近的话,那么《贵州山民图》系列人物造型、结构、光色的严谨写实,已经更为倾向于徐悲鸿了。庞熏琴的这一批苗族题材绘画,在忠实记录苗女服饰纹样的基础上,融入了他个人的艺术思想,从中西融合的探索出发,探寻中国绘画的现代之路。
注 释:
①《熏琹的梦》系1932年傅雷为庞熏琹个展开幕所作,原载于《艺术旬刊》第一卷第三期(1932年第3期第12页);《决澜社的一群》系1936年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倪贻德《艺苑交游记》中的一个重要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