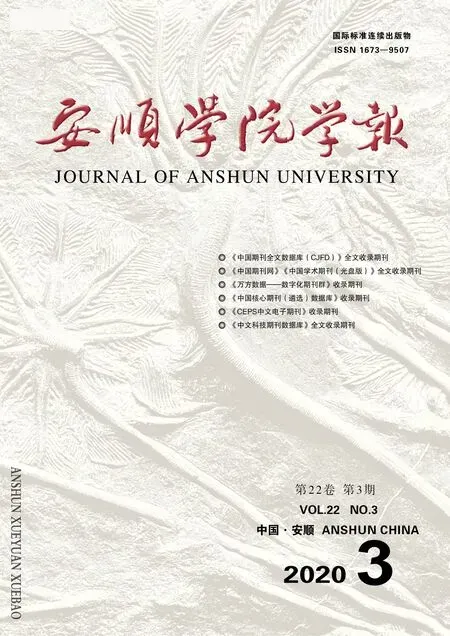论大花苗服饰的文化记忆及象征表达
(1.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安顺学院政法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2.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在符号学领域,继索绪尔提出“能指”和“所指”二元结构模式之后,皮尔士开创了三元指号(sign)的结构分类图式,其影响深远。皮尔士把指号分为三组,即征象(sign)、对象(object)、释义(interpretant),每一组下面又分三类,即“征象”分为质感符(Qualisign)、实在符(Sinsign)、常规符(Legisign),“对象”分为象似符(Icon)、标指符(Index)、象征符(Symbol),“释义”分为特征符(Rheme)、命题符(Dicentsign)、思辨符(Argument)[1]。纳日碧力戈教授采用九宫图的方式进行列举,这正好切合皮尔士将单一分类符所进行的组合,形成有区别意义的指号系统 。其中,将指号对象分为象似、标指和象征三类对物体符号意义的分析极为有用:(1)象似:指号与对象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照片与本人、地图与地理区位之间的关系;(2)标指:指号与对象间彼此相关联,有某种逻辑关系,如风帆与风、烟与火、子弹孔与子弹等之间的关系;(3)象征:与前两种指号类别不同,象征指号与对象间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如语言符号指代某事物等。经后来的阐发,皮尔士的指号理论超越了语言符号范围并广泛使用于非语言领域。基于其有效性,艾克在评价皮尔士指号理论时指出:“肖似记号(象似符,引者注)概念包含着大量建立在准确惯约法则和运作上的生产运作,其分类法和分析研究是未来一门发达的记号理论的任务”[2]。
一、 大花苗及其服饰
古时对苗族的分类通常按服饰或头饰特点,如《百苗图》中分为红苗、黑苗、花苗等,这样的分类依据沿用至今。今人何宴文根据服饰特点还可将苗族服饰分为“湘西型”“黔东型”“川黔滇型”“黔中南型”“海南型”等类型[3]。大花苗属于川黔滇型、西部方言区,研究大花苗的学者习惯称其为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以区别于其他苗族支系。大花苗主要分布于滇东北、黔西北及川西南、川南等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小部分散居于南方各地,按照苗族学者苗青的观点,大花苗迁徙至川黔滇交界地并以之为“托天之顶”而生存下来,其原因一是受到水西彝族的庇护,二是源于黔西北地处高寒,环境恶劣,易于逃避外界的侵犯。苗青认为,大花苗迁徙到今威宁一带有两条主要的迁徙路线,第一条路线,由北而南而西——而西北而西南的大迁徙。第二条路线,由北而中而西——而西北而西南的大迁徙[4]。两条迁徙路线都起始于北方大平原,最终汇聚到黔西北威宁、赫章一带,在人迹罕至、环境恶劣的高海拔崇山峻岭中安顿下来,形成今天大花苗支系的族群基础。
王文宪认为“大花苗是当年在中原涿鹿战争中跟随蚩尤奋力杀敌的先锋部队,因为这支部队勇猛,历来受汉族、彝族等民族的排挤和杀害,才使大花苗在各种苗族支系中最悲惨。”①此观点在大花苗传唱的古歌中得到印证,如西部苗族古歌中叙述了大量的迁徙路线、战争场面、英雄人物等,其演唱时常常催人泪下。大花苗至今在婚丧嫁娶等场合中有迁徙舞的表演,而其与古歌演唱相契合惯使场面一度伤感。古歌、舞蹈与服饰互为表里的立体性表述,故使大花苗服饰在苗族迁徙文化的符号象征上可谓独树一帜。
大花苗族今天的居住环境,多为海拔较高的高山箐林,具有气候寒冷、温差较大、土地贫瘠、干燥少雨等特点。耕种与畜牧为他们的主要生计方式,基于山间环境适宜种植麻的特点,因此麻和羊毛成为大花苗服饰制作的主要材料。大花苗服饰形制简单、色彩单一、图案粗犷。首先,大花苗服饰主要由披肩、背牌、百褶裙三部分组成。其中背牌下方饰有垂蕤,垂蕤古时以布结作饰,如今改为串珠,垂蕤底端系有铜铃,走路时可晃啷作响。据说大花苗服饰古时还有绑腿,后来弃而不用。男女服饰具有相同的披肩和背牌,唯一区别在于男服没有百褶裙,因此有了男披肩內褂比女披肩內褂长而至脚踝。其次,大花苗服饰色彩单一,以红白二色为主,外加少许青色。再次,大花苗服饰图案几乎为几何纹样,如菱形、锯齿形、曲线等,图案形大且简单,大花苗因此得名。披肩及背牌的纹案采用挑花的制作方式,百褶裙则使用蜡染印制。披肩和背牌由麻线和羊毛线镶嵌编织,而披肩下的白褂则全由麻线结构。其服饰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披肩的服饰,苗语称“卓鲁”,汉意译为“换衣”。也有人把“卓鲁”释为“花衣”。一般在婚娶、节庆等场合穿戴;另一种是没有披肩,完全由白褂构成的服饰,苗语称“卓撮”,汉意译为“笑衣”(一作“孝衣”解),主要在丧葬仪式中穿戴。大花苗服饰图案的历史迁徙象征意味,在服饰制作过程中极为严苛和稳固,加之服饰暗含有一定的祖先崇拜信念于其中,因而其形制规则不易变化,这对于一个无文字民族的文化记忆与传承起到莫大作用,并被学界称为“背在背上的历史书”。
二、 大花苗服饰象征的表层结构
大花苗服饰是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通过这套象征符号实现一定的文化标指,从而建构民族的精神内涵。与其他苗族支系服饰不同,大花苗服饰采用刻板的几何纹样,图形简单,经上千年历史洗礼其形制较少变化。大花苗服饰具有鲜明的象征与记忆等特征,其图形虽少了几分灵动,然则却多了几许厚重。大花苗服饰象征的表层结构如下:
披肩纹饰表征“天地”“山川”“田园”。在大花苗族服饰的披肩上,以红黑二色交错、白色为底色,采用对称的几何纹饰,即边上绣有锯齿纹、波浪纹、螺丝纹,中间饰以菱形纹,菱形纹内又织斜方格纹等,其间留有大量空白。含义为每方图案的上方代表“天”,下方代表“地”,左右代表“山川”,中间代表“田园”。
背牌纹饰表征“城池”。大花苗服饰中有一块起装饰作用的背牌,苗语称为“劳搓”,形状呈横长方形,其图案工艺以刺绣为主,兼用蜡染、挑花、编织,纹饰有菱形纹、锯齿纹、凸字纹、云雷纹等。其具有“城池”的象征意义,是苗族祖先迁徙中被迫离弃的中原故地,背牌图案线条的繁复刻画了曾经的城池繁华。另说背牌还象征战争中的旗帜,在背牌下方坠有垂蕤,垂蕤跟旗须类同,而垂蕤底端的铜铃,走动时发出“咣啷”声,象征战场上金戈铁马的厮杀声响。
百褶裙纹饰表征“江河”。象征“江河”的图形纹绣在百褶裙上,从裙边及腰有数条约2厘米宽的蜡染几何纹,在几何纹饰间有大面积的白地,白地上下有2组回环绳辫纹和4组红黑二色布条的平行线段,线段分为两段的和三段的两种类型。中部三段红黑相间,叠压平行的布条从上至下依次象征黄河(浑水河,苗语称为“涤望涤垛”)、平原、长江(清水河,苗语称为“笃纳伊莫”)。白地象征着宁静的天空。诚如苗族古歌所唱:
我们走一步望一步/望着江普这宽广的地方/平整整的土地一丘连一丘/多可惜的地方啊/一定要留下个纪念/照田地的样子做条裙子穿/把江普的瓦房绣在衣裳上/我可爱的家乡江普呀/绣上花衣裙永远叫子孙怀念[5]
大花苗服饰图案自上而下的空间布局象征着苗族先祖迁徙路线的时空逻辑,即由中原一带繁华的“城池”经高山、平原,跨过黄河、长江等河流,进入荒无人烟的高山箐林,最后落脚云贵高原的广大地区。可见,与其说大花苗服饰是些形制简单的象征图案,不如说是一副崇高的故园迁徙图。它通过历史叙述的方式记忆富庶的祖籍故地,暗含苗族人回望故土的文化心理。
三、 大花苗服饰象征的深层结构
(一)大花苗服饰是一种历史书写
“历史在两个面之间摇摆。一方面,它是一种实践,是一种现实;而另一方面,它则是一个封闭的叙述,一种由精神模式所组织并完结的文本。”[6]大花苗族的服饰超越了服饰的基本功能,俨然成为记录苗族历史的符号文本,与塞尔托所述相符,它既叙述历史也观照现实。从现实的面向看,作为苗族文化的母题无论“迁徙”或是“东方故里”,在苗族整个文化结构中演化而世代相传,苗族人对传说故土的眷念并非真的有朝一日要卷土故里,实际上是通过这些虚化的文化事实在历代苗族人苦难的现实遭遇中树立生存的信念,形如宗教想象着追溯天国的美好以增强对现实种种(大花苗等苗族支系的生存环境一般都比较恶劣)的忍耐,乃至在此基础上实现诸如伦理、审美、超脱的生命意志和终极追求。
历史是人对过去的追问和记忆,然而,常常受身体结构的局限,即面对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人的记忆显得无能为力。苗族学者杨昌国认为,苗族历史记忆有许多母题,然而各苗族支系对共同的母题有不同的阐释方式,有古歌、舞蹈、服饰标记等[7]。大花苗对历史的记忆依托于服饰图案的书写,把迁徙史形式化地绘制在服饰上,形成一种独特的记忆场。作为符号,图案不同于古歌或舞蹈,其已凝固并较为稳定而不易变化。一般来说,族群历史的记忆或仪式操演主要由某一族群中的文化精英掌管,如很多民族中的祭师或巫师作为文化掌管者,抛开其他文化职责,他们肩负着记录和传承历史的文化使命。而大花苗族服饰的历史记忆方式已经突破这种惯制,把祖先的历史以几何纹样的方式记录在服饰上,形成统一格式,人人都是历史记忆的记录者和传播者,并千古流传,生生不息。在大花苗族中,制作服饰成为苗族女人必备的能力,年轻女子总是跟年老妇女继承服饰制作技艺,其中包括几何纹样的绘制规则、尺寸、颜色搭配等,从而把历史记忆与文化惯习有机统合起来。
(二)大花苗服饰隐喻祖先崇拜
大花苗服饰的文化记忆暗含了祖先崇拜的文化心理。“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8]不错,“研究记忆的社会构成,就是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授行为。”[9]也即是说,集体记忆具有建构并维系某社会成为可能的作用,大花苗族的服饰作为族群的符号象征,在服饰的制作及其穿戴中没有举行一定的仪式,但对服饰纹样的膜拜和祖先的记忆,已然超越了个体记忆的特点而成为集体记忆的共同表征。大花苗是一支因频繁迁徙而徒增悲剧性的苗族支系,生活环境恶劣,历史上曾受到其他民族的欺凌,并坚毅地延续至今,其中服饰起到了聊慰内心和精神寄托的作用。其一,服饰记载了大花苗祖先曾居住富饶之地,虽辗转各处仍不忘回到祖先失却的那片丰饶家园,即使死后也要把坟墓朝向东方。其二,大花苗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蚩尤涿鹿战场的主力军,能征善战,其服饰中的披肩作为战袍的变体,基本能影射曾经浴血战场的将帅概貌,并引以为傲,他们正是通过服饰等文化形态形塑了民族文化心理。
苗族一般自认为是蚩尤的后裔,进而把蚩尤加以神化并崇拜,形成祖先与神相交融的信仰特点。大花苗族没有严格的关于蚩尤信仰的仪式,他们自古把服饰的符号象征作为信仰载体,予以慰藉,从大花苗语对其服饰的称呼可见一斑。大花苗将其民族服饰称为“撮鲁”,即“换衣”之意。相传蚩尤当年涿鹿败走后受敌方追杀,为了让带伤的蚩尤逃避被追杀的危险,其中一个跟随蚩尤左右的大花苗族祖先主动与蚩尤调换衣服,才使蚩尤顺利逃过一劫。此后大花苗族一直按照当时蚩尤的战袍规格制作衣服而传承,并取名为“换衣”。“换衣”的传承一是对蚩尤的纪念,二是以祖先战场杀敌的忠勇告慰悲苦的现实生活。②
作为祖先记忆的符号,大花苗服饰由最初的迁徙历史的回忆,逐渐演化成一种族群边界的分划符号,即它既在族群内部催生出成员间的团结,又在族群外部区隔与其他群体间的关系。这种区隔表现在,一则通过服饰模塑大花苗族历来规避与其他族群之间如婚姻往来的文化标识,二则以服饰符号建构的边界心理不断加固大花苗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三)大花苗服饰实现文化认同
扬·阿斯曼认为:“群体与空间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构建了一个有机共同体,即使此群体脱离了它原有的空间,也会通过对其神圣地点在象征意义上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10]也即说,记忆的象征意义在于重建族群“共同体”,然而实现这个共同体必须借助于一个“神圣地点”。对于大花苗族而言,他们唯一表达“神圣地点”的符号载体就是服饰,他们借助于服饰上的符号象征体系去实现民族文化的认知乃至认同,进而建构这个“共同体”。源于服饰图形的特殊性,按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标准制作民族服饰成为大花苗女孩婚前的必备技能,她们首先必须深知每一个图形的涵义,才能固守缝制技艺不得任意改变服饰特征。大花苗服饰与其他民族或苗族的其他支系有着显著区别,他们对服饰符号象征意义的重视旨在通过服饰加深对族系内部的文化认知,进而实现族群认同的目的。大花苗服饰的传承是在不断增强族群自我意识的过程,当族群意识得以加强后反过来又增加族群边界的认同感,这是一个辩证协进的过程。大花苗服饰把其记忆功能与族群身份认同有机结合起来,既能以服饰符号形式促进大花苗特有的文化特质的世代传递,也可在服饰生成的认同关系中实现文化对族成员的控制,促进族群内部的团结与和谐。
结 语
作为一种符号表征,大花苗的服饰图案结构符合皮尔士的指号释义。皮尔士认为指号三分法只是一种分析方法,目的在于理解符号体系的特性,现实中这些分析类别并不单独存在,而是重叠和融合的整体,分析便是为了更好认知。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借助该理论以解释大花苗服饰的象征涵义,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一种文化物象,进而深刻地认识大花苗。大花苗服饰几何纹案记载,诸如图案中的菱形代表田园、矩形代表城池等,其最初采用的便是皮尔士提出的“象似”指号的标记法,通过描摹形似的方法把祖先在中原一带失去的家园及其迁徙路线记录在服饰上。这套象似符码历经上千年而传承,其指号与对象间(曾经的家园)渐渐超出它原有的形似对应,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或族群的标识。这样的变化可由指号的释义得以说明,即皮尔士所说的“特征符”(又称直接解释项)演化为“命题符”(又称动态解释项),再到“思辨符”(又称最终解释项)的过程。其中 “特征符”分析特征表明必须把征象对象放入到对象产生的文化场域中,诚如大花苗服饰的符号意义只有在大花苗文化语境中才能呈现一样。“命题符”表明征象通过自身以限制对象来指示释义,可理解为服饰图案对大花苗来说是一种族群边际的文化标识。而“思辨符”表明征象直接规定释义,从而达到其合理性,此处尚可理解为大花苗民对本族服饰符号的自我认同与归属感。事实上,“释义”的三个类别之间表达了皮尔士指号征象与对象间的辩证推演过程,这正暗合大花苗服饰从表层符号到深层记忆内涵的演进。另则,诚如符号具有约定俗成特性一样,大花苗服饰图案所展示出来的象征符号也有一定的“社会规约性”,如皮尔士所说:“所谓象征符号就是被符号的解释者如此理解或解释的符号。当然,这种理解或解释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解释者所处的社会或共同体的规范的制约的。”[11]。
注 释:
①引自2017年访王文宪录音资料。
②根据王文宪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