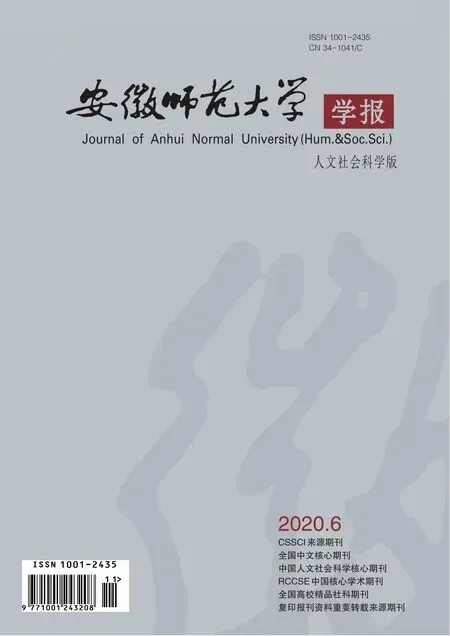菲利普·罗斯的“恋地情结”:《再见,哥伦布》的空间叙事*
姚 石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2018)作品的叙事空间经历了三次转向。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的是美国,特别是自己的家乡新泽西州纽瓦克。中期(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作品主要表现的是欧洲和以色列。晚期(从90 年代下半叶开始)作品的故事空间又转向了美国,其中大部分作品表现主人公在纽瓦克的童年生活。纵观他的整个创作历程,可以发现罗斯的艺术世界起于纽瓦克,也终于纽瓦克,即使他中期的作品也有很多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纽瓦克,正如作者在一次访谈中谈及作家“强迫性主题”(obsessional theme)时指出,“小说家对于强迫性主题表现出可怕的无知。因为他最不了解这个主题,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围攻它——他清楚地感知到他对此知之甚少”。[1]10故乡纽瓦克的童年经历就是他的强迫性主题之一,他表现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恋地情结”。
罗斯的“恋地情结”通常表现为既逃离又留念的复杂情感,致使多数研究者过于强调罗斯笔下主人公逃离纽瓦克融入主流社会的同化主题,而忽略了这些主人公即便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之后仍然心系纽瓦克的故乡情结。鲍斯诺克(Ross Posnock)指出,“罗斯并不限于纽瓦克,而是居住在‘文化共和国’之中,这是一个以阅读界定的空间,不是以地理上或者传记上的出生地界定的空间”。[2]ⅷ她认为罗斯的作品空间在不断扩大,从纽瓦克走向美国主流社会再到欧洲。帕里西(Timothy Parrish)也指出,“从《再见,哥伦布》《波特诺伊的抱怨》到《鬼作家》表现了犹太青年融入美国社会的挣扎”。[3]127可见,纽瓦克对于罗斯的特殊含义被国外学界严重忽视。杨金才和朱云在分析国内的罗斯研究时指出,“我国研究者对罗斯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偏向,对罗斯早期作品鲜有问津……但作为对一个作家的整体研究,早期作品不应忽视”。[4]因此,贯穿罗斯创作生涯始终的纽瓦克“恋地情结”成了国内学界的盲点。
纽瓦克作为欧洲犹太移民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定居点,他保留了犹太人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犹太会堂和学校,这几乎是对欧洲隔都的复制,纽瓦克是连接美国犹太生活与欧洲历史的纽带。美国的资本主义文明很快将作为犹太人身份标记的传统生活方式从有形的第一空间中抹去,但是,那种生活方式深深地烙在了他们的心灵深处。本文以罗斯第一部小说集《再见,哥伦布》(Goodbye,Columbus)中的同名中篇小说为例,运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理论和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分析罗斯在纽瓦克犹太社区解体之后在“第三空间”中再造纽瓦克的“恋地情结”。
一、“第二空间”的抽象观念生产
《再见,哥伦布》以纽瓦克和肖特山两个不同空间为对照展开情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再见,哥伦布》属于典型的空间叙事,因为经典叙事学家都强调时间,而将空间贬低到为背景,韦斯莱·科特(Wesley A. Kort)在《现代小说中的地方与空间》一书中援引夏珑·斯宾塞(Sharon Spencer)的观点时指出,“她将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视为叙事形式上的分水岭,自此,对空间的强调取代了对时间的强调”。[5]14传统小说情节表现为人物在时间中的展开,而现代小说情节倾向于表现人物与空间的互动。《再见,哥伦布》这部小说既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也没有具有强大魅力的圆形人物,它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对空间的细腻展现。
主人公尼尔·克勒门是刚从纽瓦克鲁特格斯大学毕业的犹太青年,他在图书馆上班。暑期他在俱乐部的游泳池邂逅了布兰达·帕丁金,俩人关系发展迅速,布兰达很快就将尼尔带到她所居住的肖特山。肖特山是纽约郊区有名的富人区,当尼尔告诉格拉迪斯舅妈他的朋友家住肖特山时,格拉迪斯舅妈难以置信地问道,“犹太人打哪时起住在肖特山的?我想他们不是犹太人”。[6]52尼尔第一次驾车来到肖特山时就觉得这是一次驶向天堂的朝圣之旅,“郊区的地面虽比纽瓦克只高了八十码,却使人感到好像更接近天堂,太阳似乎更大、更低、更圆”。[6]6布兰达就像是引领他进入天堂的天使,在他们第一次拥抱时,尼尔发现,“在她的肩胛骨上,我触摸到两块湿泽,再往下,我明显地感觉到一阵轻微的颤动,……这颤动犹如鸟儿振翅欲飞,然而那翅膀很小,……但我并不嫌弃那对翅膀的短小——因为我无需老鹰把我驮升到一百八十码高的肖特山,那里的夏夜比纽瓦克凉爽宜人得多”。[6]11肖特山就是在美国现实社会中建立的人间伊甸园,是美国人所追求的美国梦的化身,纽瓦克犹太人的梦想就是离开那里的犹太社区进驻肖特山。
尼尔对帕丁金家的第一印象是丰富的食品以及他们惊人的食量。尼尔在纽瓦克家中吃饭时,格拉迪斯舅妈精打细算,一点都舍不得浪费,舅母经常让他吃那些冰箱里的垃圾食品,“对格拉迪斯舅母来说,生活似乎就是处理东西。她的最大的乐趣是清理垃圾,清理储藏室”。[6]4尼尔第一次在布兰达家吃饭时,帕丁金先生戏谑道,“他吃饭像只鸟”。[6]20“有时应邀去她家赴宴,为使帕丁金先生垂青,我不得不咽下两倍于自己食量的饭菜。但事实是,从他首次对我的胃口下过评语后,帕丁金先生再也没有心思继续作观察。即使我吞下正常食量的十倍,并因暴食而死,他还是不把我当成人,而只是只麻雀罢了”。[6]50有一天,尼尔独自一人来到帕丁金家的地下室,里面除了储藏了各种精美的餐具和名酒之外,最让尼尔难忘的就是一台庞大的冰箱。他不由地感叹道,“啊,帕丁金!水果在他们的冰箱里长出来,运动器材从他们的树上掉下来”。[6]38这里的大冰箱让尼尔想起了昔日在纽瓦克四户人家合用的大冰箱,而冰箱里堆放的并不是搬上餐桌的食物,而是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新鲜瓜果,似乎水果是从他们的冰箱里长出来的。尼尔对冰箱内部的描绘暗示了伊甸园的意象,这里各种瓜果应有尽有,色彩斑斓,永不凋谢,一伸手就可以抓过来吃,尼尔随手抓了一把樱桃和油桃,没有洗就直接食用了。置身其间的尼尔再也不会想起舅母所担心的陈腐食物造成的浪费,远离生活的烦恼。
然而,肖特山的天堂是一个物质化的天堂,繁华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尼尔第一次开车来到这里时经过一排排房子,“门前平台上空无一人,却亮着灯,窗户紧闭,仿佛屋里的人谁也不愿意与外面的人共同体验世间的甘苦,他们把湿度不多不少地调节到他们皮肤所能适应的程度”。[6]6肖特山的居民不仅养尊处优地安享物质财富,不关心下层民众的疾苦,而且他们互不往来,每个人都封闭在自己的家中。尼尔父母离开纽瓦克让他与舅舅和舅母住在一起,舅舅和舅母把尼尔当作自己的孩子,虽然生活艰难,但是大家相互帮助,有着很强的凝聚力。但是帕丁金先生与弟弟利奥之间却形同陌路,在布兰达的哥哥罗恩的婚礼上,尼尔遇到了利奥,他是个穷困潦倒的推销员,在婚礼上帕丁金先生一家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他只顾一个人喝酒,利奥直到最后才带着妻子和孩子与尼尔一起离开酒店的,“看他们的背影,那浑圆的肩膀上背着沉甸甸的孩子,宛如从沦陷的城市中逃出来的难民”。[6]109尼尔觉得利奥就是被上帝忽略的人,而利奥与纽瓦克的犹太人基本处于同一社会阶层,在富有而薄情的哥哥家中凸显了他的贫穷与凄凉。
肖特山属于索亚(Edward Soja)理论中“第二空间”的典型,其间,物理空间成了抽象观念的表达,标准化的商品生产模式决定了这个天堂是扼杀个性的。索亚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生活空间”重新界定为“第三空间”。列斐伏尔在“感知空间”(perceived space)和“观念空间”(conceived space)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空间”(lived space),走出了二元化的思维模式。索亚将这三类空间分别命名为: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7]66-76第一空间是物理空间,第二空间是意识形态空间,第三空间是主客体交融的生活空间。第三空间包含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化物理空间为人的生活空间,化抽象的观念空间为具体的经验空间。列斐伏尔还用“作品”“自然”和“产品”区分三者,“感知空间”属于“自然”,“观念空间”是人工生产的“产品”,而“生活空间”中创造的是“作品”。《再见,哥伦布》中的“人间天堂”就是“第二空间”生产的产品。
肖特山的天然风貌被改造成体现生活档次的体育场,健身场和公园,肖特山的居民也成了抽象的“理想人生”的化身,失去了具体的现实生活世界。尼尔在山上的公园里看到了几个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她们就是天堂里“不朽的女神,她们的头发始终保持着她们理想中的颜色,衣服也保持她们所喜爱的料子和色彩”。[6]88-89她们的里里外外都是商品社会包装出来的,批量生产抹去了她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她们的外貌和生活方式都惊人地相似,因为她们都是机器化大生产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尼尔感叹道,“她们是女神,假如我是帕里斯,我无法在她们中进行选择,她们彼此的区别太细微了。命运把她们揉压成一个模样,只有布兰达闪着光,金钱和舒适不能磨灭她的棱角——或者说它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吗?”[6]89正是布兰达身上所表现的叛逆深深地吸引了尼尔,正是她的叛逆打破了纽瓦克与肖特山不同空间之间的隔绝,把尼尔带入了她的家中。面对帕丁金太太的蔑视和帕丁金先生的冷漠,布兰达还是说服父母让尼尔在他们家住两个星期。
然而,布兰达也和肖特山上的女神一样在刻意消除自己的个性,斩断与打上个性印记的过去的联系。帕丁金一家是从纽瓦克迁往肖特山的,尽管他们家发家致富的商店仍然在纽瓦克,他们却极力摆脱与纽瓦克的一切联系,他们将从纽瓦克搬来的所有东西都锁在了一间废旧的储藏室中,在这里开始他们全新的生活。布兰达对她母亲身上遗留的节俭陋习深为不满,她向尼尔抱怨道,“金钱对她来说是废物。她连怎么享用金钱也不知道,以为我们还住在纽瓦克”。[6]23为了完全抛开纽瓦克的一切踪迹,布兰达做了鼻子整形手术,她的哥哥“准备今年秋天也去整形”。[6]11
布兰达的叛逆只是表面的,她其实也是肖特山“第二空间”中没有灵魂的产品,就连她的叛逆本身也是“第二空间”的产物,她的叛逆行为并不是基于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和思考,而是玛丽·麦卡锡小说的复制品,麦卡锡以大胆的性描写而被诺曼·梅勒称为“引领之光”[8]283,就连布兰达与尼尔在一起偷欢也是模仿“麦卡锡小说中波西米亚性格的姑娘”[9]206。她就读于哈佛大学这样的人生路线也是“第二空间”的产品。其实,这种人生路线图已经刻写在这里的街道上了,“这里的马路皆以东部大学的校名命名,好像这个镇多年前给马路命名时就已经为这里的子孙后代做好了安排”。[6]6-7可见,布兰达进入名校哈佛大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迎合主流社会的观念,她到哈佛大学求学并不是出于对知识的追求,而是看重名校的光环给她带来的符号价值。
肖特山和纽瓦克都是被“第二空间”生产出来的两种观念的代表,它们分别代表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前现代的隔都。为了实现“第二空间”生产的主流观念,这两个空间被人为地对立起来,正如王卫华所述,“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实现了两个重要的翻转:一是从‘信仰支配世界’到‘欲望支配世界’的翻转,二是从非经济性到经济性的翻转”。[10]纽瓦克作为前现代社会的化身,其间的信仰世界和非经济关系需要被翻转,以实现现代化。纽瓦克的隔都传统成为“第二空间”拯救的对象,同时也为“第三空间”的救赎提供原型。现代性社会中的欲望化和经济性表现为平面化的去时间性,使人成为空间中的流浪者,失去家园感,“第三空间”的“地方感”为流浪在“第二空间”中的现代人提供精神家园。由“第二空间”的抽象空间到“第三空间”的具体地方的转化的关键在于“恋地情结”。段义孚(Tuan Yi-Fu)以“恋地情结”表示空间中时间的累积带来的“人类与其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11]93在人类对环境的体验中,“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12]136这种情感纽带使得没有差别的空间变成地方,时间依附于地方,时间的流逝会在地方留下记忆,形成“地方感”。
二、“第三空间”的救赎
图书馆在这部小说中成了一个部分独立于“第二空间”之外的“第三空间”,是主人公尼尔抵制“观念空间”侵袭的“生活空间”。索亚在列举现代都市的“第三空间”时指出,“例如博物馆和图书馆,在这里‘时间从未停止累积’从而建立一个‘普通的档案’,一个‘包含所有时间的空间,这个空间处于时间之外,从而免遭时间的侵袭”。[7]160可见,图书馆是典型的“第三空间”,时间在这里无限累积,这里由于包含所有时间而不受现时的意识形态操纵。“第二空间”就是现时权力运行的场所,后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方式主要表现为时间空间化,帕丁金一家从纽瓦克到肖特山原本是一个时间历程,而这一历程却表现为空间的转换。帕丁金一家从纽瓦克迁往肖特山之后就极力斩断与纽瓦克的联系,因为“第二空间”并不接受时间的累积,只迫使人们不断地进入“现时”,从而将过去无休止地驱逐出自身,让空间成为观念的符号。
作为社会机构的组成部分,图书馆也无法完全摆脱社会权力的操纵。图书馆的物理空间属于“第一空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生活在“第二空间”,而图书馆中的读者和图书作者建构了“第三空间”。尼尔选择图书馆的工作不是因为这份工作在社会权利层级中的位置,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热爱读书的文化人,他要在这份工作中帮助困惑的人们在书本中寻找答案。尼尔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哲学,当帕丁金太太因为尼尔不去犹太会堂而怀疑他是异教徒时,尼尔为了证明自己的信仰就搬出了马丁·布伯的著作,马丁·布伯属于19 世纪由拉比犹太教的解体引发的世俗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批欧洲犹太知识分子之一。在拉比犹太教解体之后,犹太知识分子逐渐取代拉比为世俗世界带来救赎,而图书馆则取代犹太教会堂成为守卫精神家园的神圣空间。
除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之外,尼尔发现图书馆工作本身也是权力运行的场所。资料室的玛莎·维尼摔坏了髋骨,馆长斯格培罗先生决定把尼尔提升到维尼的位置上,并说他自己十二年前也是这样升迁的,而在这次升迁中尼尔看到的却是权力在机械地运转。他无奈地自嘲道,“这样看起来,要是我能维持现状,有朝一日就会成为另一个斯格培罗先生”。[6]62权力的运行就像庞大机器的运转,个人作为权利运行的载体就像机器的一个部件,完全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因此,尼尔觉得这种工作正在吞噬他的灵魂,“过一段时间,我就耐心地等待着有一天,我可以在一楼的男厕所抽着烟,对着镜子,喷云吐雾,端详着自己,我将发现早晨某一时刻,我的脸色变得苍白,好像在我的皮下,就如在麦基、斯格培罗和维尼小姐的皮下,有薄薄的一层空气,隔开了血和肉”。[6]29尼尔在这里表现了他对“第二空间”中权力的抽象化运行的抗拒。
尼尔对“第二空间”的抵制除了体现在他对同事的反感之外,还突出表现在对一个黑人小男孩的保护上。这个经常来图书馆的黑人小男孩缺乏教养,理应被清除出图书馆的文化空间,而尼尔却努力帮助他在第三书库阅览他喜欢的画册,甚至不惜找借口拒绝将这本书外借给一个看上去很严肃的白人读者。小男孩进入图书馆首先引起保安的警惕,然后是图书管理员的监视,如果没有尼尔的保护他很难享用这里的文化空间。尼尔非常友好地接近小男孩,发现他被高更绘画中的塔希提岛原始风光和土著妇女深深吸引。塔希提岛是高更寻找的西方现代文明之外的伊甸园,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到:“一股稳定祥和的力量已逐渐侵入我的身体,欧洲的紧张生活早已远去,明天、后天乃至永永远远,这儿都会永恒不变的存在吧!”[13]6高更有大量作品表现这里原始而神秘的土著人生活,展现没有遭到资本主义“第二空间”侵袭的“第三空间”。高更为了逃离西方文明来到塔希提岛生活,但他很快发现这里其实早已遭受西方文明的侵蚀,而他作品中的塔希提是他创造出来的艺术空间,具有救赎功能,如韦伯所言,“无论怎样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14]342高更的作品为黑人小男孩带来了救赎,他指着其中的一幅画对尼尔说,“老兄,这就是他妈的生活”。[6]33艺术对日常生活的救赎正是列斐伏尔的目标,他宣称,“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让每一种技术方式都被用来改变日常生活!”[15]203艺术作品以具体的生活经验表达抽象的观念,抵制日益膨胀的“第二空间”对日常生活的抽象化进程,构筑“第三空间”。
由于美国社会解除了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歧视与迫害,犹太人可以很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这部小说中图书馆代表了美国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挪用”方式。与“同化”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身份以获得美国身份不同,“挪用”表明犹太人在保留犹太身份的同时积极吸收主流文化,从文化上融入主流社会。波斯诺克指出,“‘挪用’所需要的就是一座好的图书馆,因为图书馆内安置着杜波伊斯所谓的‘文化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的美国无法标示出清晰的黑白界限”。[2]3尼尔与布兰达之间矛盾的一个焦点就是“挪用”与“同化”两种立场之间的冲突,他们最终分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尼尔不愿意放弃图书馆的工作。在他们分手的那天晚上,尼尔并没有立刻乘车离开,而是漫步于哈佛大学校园,来到莱蒙图书馆前,他从图书馆的玻璃窗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他想,“我就是这样一块料,这就是在我面前的四肢和脸庞。看着,看着,然而我的外部形态表达不出我的内心世界。我多想用比光线和声音还快的速度跑到窗户的反面,去捕捉影像后面的以及从自己眼里所看到的一切”。[6]127尼尔从玻璃窗上看到了自己的镜像,这也是别人眼中的他,而这个外在的自我并不能代表他内心真实的自我,尼尔在外表上完全是一个美国人形象,而他的内心却不仅仅是个美国人,还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美国犹太身份需要在图书馆这样的“第三空间”中重建。
三、精神隔都的重建
“恋地情结”使得没有差别的空间成为具体的“地方”,罗斯的“恋地情结”是他在小说的第三空间中再造作为地方的纽瓦克的动因。罗斯作品中的纽瓦克犹太社区因为“第二空间”的侵袭而解体,当隔都从“第一空间”中逝去时,他笔下的犹太主人公在“第三空间”中重建精神隔都,精神隔都中的纽瓦克因为时间累积的记忆而成为具体的地方,对抗着“第二空间”的抽象化观念生产。同时,隔都中拉比的权威和父亲的威严,让社会规范打上了父亲之名的人格烙印,抵制非人格的抽象规范。罗斯后期作品以强大的父亲改写了《再见,哥伦布》中父亲的缺席,升华了记忆中的纽瓦克,个体的记忆与人格化的权威让纽瓦克成为独特的地方,承载着美国犹太人特殊文化记忆。美国犹太人对纽瓦克的“恋地情结”在“第一空间”中无所依托,又被“第二空间”所不容,罗斯在文学作品的第三空间中重建精神隔都,让纽瓦克成为他们永恒的故乡。
尽管纽瓦克在“第二空间”中已经成为贫穷落后的符号,但是尼尔对其仍有着深挚的情感,他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恋地情结”。尼尔上班的图书馆旁边有一座公园,一天早晨尼尔漫步其中时很自然地就回想起了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他感叹道,“我坐在公园里,感到自己对纽瓦克了如指掌,我对它的依恋如此之深,以致这种感情不能不发展成为热爱”。[6]27由于纽瓦克承载了尼尔太多的记忆,他的身份认同已经深深植根于这块地理空间。尼尔对于纽瓦克的挚爱并没有因为这里犹太社区的解体而消失,当尼尔来到位于纽瓦克黑人区中心的“帕丁金厨卫洗涤槽”商店时,他脑海中浮现的是“许多年前,在大移民时代,这儿曾是犹太人区,人们还可以看到小鱼铺、犹太熟食店,土耳其式澡堂,在本世纪初我的祖父母曾在这儿购物和洗澡”。[6]83尽管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纽瓦克已经逐渐变成黑人区,但是早期犹太人在这里建立的犹太人传统生活方式是值得犹太人永远守护的文化之根。
与“第二空间”生产的非人格化的抽象观念不同,纽瓦克犹太社区代表了人格化的权威。在拉比犹太教时期,拉比是隔都中的权威,父亲是家庭中的权威。欧文·豪在考察隔都生活时指出,“一个男人的声誉,权威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识。博学之士坐在犹太会所的东墙,靠近约柜。妇女通常外出挣钱养家糊口,让她们的丈夫专心钻研学问”。[16]8在隔都中,拉比和博学之士的权威维持着社会秩序,父亲的威严维持着家庭秩序,但是在美国社会中,非人格化的抽象观念取代了人格化的父亲,“第二空间”生产的抽象观念瓦解了纽瓦克的隔都。
在罗斯晚期的自传体小说《遗产》中,主人公罗斯在父亲的最后岁月中似乎又回到了他儿时的纽瓦克犹太社区,在陪伴父亲的过程中,罗斯跟着父亲又在老年公寓和俱乐部中与当年在纽瓦克的邻居们聚到了一起,遇到了父亲当年的同事,他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犹太人的隔都之中,这是一个掺杂着记忆与想象的精神隔都。在罗斯后期以真诚的态度正面刻画父亲形象的作品中,精神隔都把主人公与主流社会隔开,在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中为主人公提供庇护。罗斯后来在《反美阴谋》和《罪有应得》两部作品中将这种精神隔都的构建分别延伸到主人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四、结 语
罗斯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书写纽瓦克的生活,他有着难以割舍的“恋地情结”。纽瓦克是犹太人从欧洲来到美国后所建立的第一个犹太社区,是连接欧洲与美国的纽带。罗斯笔下以自己为原型的美国犹太青年就是从纽瓦克走进美国主流社会的,他们在另一个空间中继续着欧洲犹太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离开隔都融入主流社会的历程,这是一个以知识精英取代拉比的世俗化进程。他在作品中主要通过父子关系表现纽瓦克的危机,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纽瓦克往往是犹太儿子由于不堪忍受父亲的管束而急于逃离的场所,在他的后期作品中,纽瓦克则是犹太儿子在父母呵护下免遭外部侵袭的美好家园。这种贯穿始终的“恋地情结”使得纽瓦克置身于“第二空间”的抽象化进程之外,成为“第三空间”中的精神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