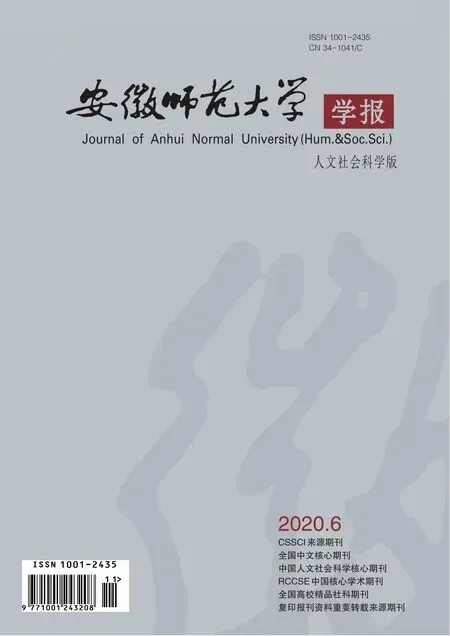论“姑苏版”中的“观”与“象”*
庄 唯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肥230026;2.南京财经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南京210023)
清代苏州地区的古版画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极为浓重的一笔,日本学者黑田源次冠之以“姑苏版”之名①黑田源次在1932年出版的《支那古版画图录》([日]美术研究所编,大塚巧艺社发行)撰写序言部分,名曰《支那版画史概观》,其中提到:“本图录所集中国版画,以余所谓:‘姑苏版’或‘苏州版’为主。”,为苏州古版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姑苏版”生动描刻了苏州地区的人文风貌、城市景观以及市民的生活情状,用古朴素雅的笔墨勾画了古苏州的摩登风情。一方面,“姑苏版”脱胎于吴门画派文人画的审美体系,吸收了西方绘画的审美特征,构建成为独有的、且代表了市民生活的审美范式,其艺术理念也成为市民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中西会通的艺术特色在中国艺术史上也极为罕见。另一方面,清中期的“姑苏版”明显带有文人画的表现技法与审美情趣。突出体现在母子图、美人图等内容中,她们常读书、赏花、抚琴、作诗,自娱自乐,风雅且有情趣。这种安闲自得、洒脱自在的生活方式,成为了姑苏市民的向往和追求。对于文人画中的题跋、书法以及装裱的借鉴,也促使“姑苏版”将文人情趣与世俗风尚完美地融合起来。
事实上,“姑苏版”不仅在形式上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对于传统观念的转变,催生了特有的艺术思维。这种艺术思维体现在“观”与“象”两个层面,前者不仅需要多维度的观察,更需要有思考、有创新,才可能与时尚前卫的社会风尚相互匹配,而“象”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被创造出来。因此,相较于传统年画,“姑苏版”更能够贴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更加深刻。然而,由于艺术偏见,时人并不视民间艺术为正统,用郑振铎的话来说:“其未必能充分地融化在中国画里……且只是‘昙花一现’而已。”[1]209我们认为,若要理解“姑苏版”独有的艺术理念和创作范式,唯有厘清其中“观”与“象”的内涵与关系才能够阐发对其本体的诠释。然而学界对此问题关注不多,研究成果很少,故而本文拟就“姑苏版”中的“观”与“象”及其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姑苏版”中“观”与“象”之释义
“观”,有“见”“显”“游”“景象”“认知”“建筑”等多重意思……内涵丰富,不胜枚举。从词源学上看,“观”主要表示主体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也指主体在外界事物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认知。“观”作为中国绘画艺术的语言,以其构建而成的词汇分为两类,一类表示信息的直接接收:“观看”、“观察”、“观赏”、“游观”等;另一类则是主体对于信息的再认识:“观点”、“观想”、“观感”等。此两类“观”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结构。仅观看无观点,落笔则无气韵无层次;仅有观想不实际观看,形与神则无法合一。二者相互转化的关系正符合《周易》当中“变易”的思想。《周易》当中的观卦主卦为坤,客卦为巽,临卦之爻位正与其相反。众生在上以为“临”,众生在下以为“观”,二者互为综卦,正所谓:“临观之义,或与或求”[2]271,也正体现出“观”在不同境遇下相互转化的本体内涵。那么,“观”在“姑苏版”中是如何体现的?能否揭示其艺术风貌的本体之源?这是本文得以继续深耕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观”是理解“姑苏版”艺术结构的重要关口,是阐发其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
“姑苏版”中的“观”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从观察的层面来看,“姑苏版”侧重于将宏大的城市景观图融于传统的年画范畴之中,同时将中西艺术不同的技术与视角进行融合。例如,《西湖胜景图》(日本王舍城美术宝物馆藏)、《西湖十景图》(日本收藏)、《金陵胜景图》(日本收藏)等均以写景为主。细读此类画,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之所以围绕姑苏景致展开描绘,与古苏州地区经济文化的繁盛不无关联。台湾学者刘石吉说:“18世纪苏州米市及商品经济之繁盛,可推知彼时正是苏州发展至最高峰的时代,而其临近各市镇,亦多受苏州商业机能的影响而肇兴。”[3]157物质的风华带动“观”从传统的年画视角转向更为宏大的景观描绘,经济的支撑亦使其能够批量化的生产。这种转向并非尝试,而是逐步形成了一种母题范式,成为“姑苏版”独有的文化标识。从观念的层面来看,“姑苏版”既乐于表现传统年画祈福迎祥的主旨内涵,亦注重表达新思想的萌发。“姑苏版”中有相当数量的母子图,这部分画作与以往单纯表现母亲教子之责与孩童敬孝之道的年画有所区别,它多以体现女性内心育子之苦累,思君之心切为主旨,如《妻儿待郎图》(日本海杜美术馆藏)中的母亲袒胸露乳,怀抱婴儿,看似正在哺育孩童,一旁题词却云:“人懒无眠,独坐在床沿,……自别良人后,相思有万千,满腹愁肠与那个言,……”[4]99画中美人以不羁之形象与内心之实感,构成了有血有肉、厚重真实的母子之“观”,根据王树村所言:“画面上印刻的唱词,不是含有孝悌忠义等传统道德教育之意义,而是……破坏封建礼法的说唱。”“也表明了封建思想的婚姻问题在人们头脑中已起变化,人们的要求不只是丰衣足食,还要再精神方面得到满足。”[5]124事实上,对于“观”进行观察与观念两个维度的阐发,随即产生了“观”的观点,而“姑苏版”的形式与内涵不断发展,“观”的意义也会随之变化。此外,上述两个维度是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对“姑苏版”的认识和理解,而从微观的层面来说,“姑苏版”还包括社会不同阶层生活情境的谐谑图,反映战争场面的战斗图,诉说戏曲故事的连环画等。综上可知,“姑苏版”中“观”的形态较为丰富多变,从个人之观、群体之观到城市之观,从传统的年画之观到反映姑苏百态的“新版画”之观,逐步形成了由点到面的同心圆,每一个圆都在传统的形式上有所发展,但无论如何变化圆心始终是儒家所倡导的礼乐精神。
无论是观察的层面还是观念的层面,“姑苏版”较传统中国画都有较大的改变,这一变化离不开其对于“象”的理解。“象”最初出自于《系辞上传》:“圣人立象以尽意。”[6]132针对立象的缘由,唐孔颖达有云:“圣人之意难见也,所以难见者书,所以记言,言有烦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虽欲书录,不可尽竭于其言。”[7]23由此可见,由于当时语言文字传播不畅,故以象表达心中见解,此为“意象”诞生的最初缘由。而后,来知德(1525—1604)在《周易集注》中云:“立象则大而天地,小而万物。精及无形,粗及有象,悉包括于其中矣。”[8]649此时,“象”有了大、小、精、粗之别,随即产生了“形象”之意。“意象”与“形象”自然不同,前者注重观者心中所想,由此生成的“象”带有了主体的意志,而后者更加偏向于自然物的客观呈现。
在“姑苏版”中,“象”兼有“意象”与“形象”之意,这两层含义从传统中国画由形如意,形意相融的境界观中剥离开来,分布在不同类别的画作中。例如,《桐下美人图》(日本王舍城美术宝物馆藏)以“月光版”的形式进行构图,承袭了明代的团扇画。画面中的假山、墨竹、桐树纷纷隐于左侧,美人持扇凭栏远眺,而身后则大面积的留白。表现出美人内心的寂寥空虚、相思情切,此与清代改琦笔下的仕女风范如出一辙,意象所指较为明晰。而以写景为主的诸多画作却不似文人画那般经过精心的布局设计,大多偏向于客观形象的准确表达,此尤以“洋风姑苏版”为甚。如《江南水景图》(私人藏)以西洋透视法与明暗法相融合,极为真实的描绘出江南水乡周遭的生活景致。整幅画构图较满,水道两旁的房屋鳞次栉比,百姓生活之貌尽收眼底,此与传统风俗画虚实相融的画面结构亦有区别。再如《临潼斗宝图》(私人藏)描绘了春秋伍子胥于临潼之地单手举鼎、技惊四座的历史故事。由于刻画细致,立体感强,此图丝毫未有千年积蓄的历史沧桑感,反倒是引领观者身临其境,以传说之事描刻出真实之感。
通过“姑苏版”对于“象”的描绘,可以反推其在观察与观念层面的构成:一是传统中国画之观,二是外来西洋画之观,这两者融合会通,使得传统绘画观念发生了变革。前者主要体现在特定人物以及局部空间的表达上,后者主要体现在宏大景观的描绘上。那么,二者之“观”是否存在交集?答案是肯定的,它们在一些作品中有所体现:第一,在表达女性与娃娃形象的时候,会有阴影排线置于衣饰之上,但涉及到画面主体人物的面容肌肤则不会出现,如:《麒麟送子图》(海杜美术馆藏)、《三元及第图》(海杜美术馆藏)、《采莲母子图》(私人藏)等。第二,部分景观的绘制沿用了界画与院体画之法,局部细节依然会留有阴影排线的痕迹,如:《苏州景新造万年桥》(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藏)、《姑苏虎丘胜景》(私人藏)等。可见,“观”在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逐步解构、融合以至重构的过程。综上所述,“姑苏版”之“观”在观念与观察两个层面打通了中西艺术之间的文化壁垒,弥合了二者无法共存的硬性间隙。对于“象”的呈现既有沿袭融合,亦有突破创新,丰富了中国绘画的内涵与空间表现。
二、“姑苏版”中“观”与“象”之关联
中国古代绘画是古人认识、理解与改造世界最为直观的艺术形式,笔墨空间的营造即是“观”赋予“象”的动态转换过程,而“观”的形成亦离不开“象”的外在构建。就“姑苏版”而言,其注重凸显市民生活的安闲与舒适、文人意趣的洒脱与自在以及中西艺术的融合与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观”与“象”的互相匹配,强调从整体上观察姑苏百态,以得到城市之“象”;重视在观念的冲突与和谐中观察姑苏市民的生活情状,以得到美人之“象”,乐于将事物置于美好的寓意之中进行观察,以得到祈福之“象”;崇尚中西文化会通融合并进行创造性的观察,以得到景观之“象”;倾向于在实践活动中进行历时性的观察,以得到戏曲故事之“象”。正如成中英所云:“客体和主体共同决定能够从事物中看到什么或者事物如何表达自己。这既不是使知识成为可能的主观唯心主义,也不是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客观唯物主义,而是一种‘预定和谐’。”[9]228在“姑苏版”中,最终呈现的和谐图景包含了复杂的融合过程,这是“观”与“象”内在矛盾的消解过程,也是“姑苏版”自我否定,不断超越向前的原动力。
在“姑苏版”中,“观”与“象”之间存在着四重矛盾,分别是传统封建礼教与姑苏“新气象”之间的矛盾,中西融合与传统中国画体系之间的矛盾,意象与形象之间的矛盾,以及文人阶层与普通大众及海外市场之间的矛盾。“姑苏版”最终陨落之肇因在于这四重矛盾并未真正的消解与弥合,厘清这四重矛盾是构建“观”与“象”二者关系之根本前提。
(一)矛盾与根源
中国年画历来重视表现祈福迎祥、驱灾辟邪的主题内涵,这是支撑民族信仰文化的精神寄托。这在“姑苏版”中体现得也较为明显,无论是婴戏图、母子图还是花鸟图、关公图等,无一不透露出明确的祈福意象。矛盾之处在于,部分母子图在表现教子育子、多子多福的传统意象之外,还融合了女子寂寞难耐,思君心切的儿女私情。与母子图相关的美人图对于女子内心情愫的表达更加直接,如《男女相爱图》(私人藏)印有题诗:“……相亲相爱还相避,情长情短为情深。……”这些诗句较之母子图的思念之语更为直白露骨。王树村云:“上述唱词一般都被视为‘淫词秽说’,属于诏谕‘限文到三日销毁’的范围。”[5]123是故这些唱词不仅在历代年画之中未曾出现,即便在与“姑苏版”同时期的其他木版年画中也鲜有提及。若从图像的视角对这些美人图加以品读,可感受到其中极为丰富的内涵。如《美人裁缝图》(日本收藏)中的女子背对着桌案,侧脸观瞧一旁的花篮,腰间系着耀眼的红丝带与手中正在缝制的秀鞋相互交织,俨然一副取悦观者的姿态。女子微妙的眼神、拈花的手指与衬衣之下凝脂的肌肤无不展现出姑苏女性的妩媚与风情,由此而生的观感并非寻常的秘戏图所能比拟,欲望之下的女性依旧身着素雅长衫,气质丝毫不逊于文人画笔下的一众仕女。而这正是“新观念”在传统与潮流、守旧与开放的碰撞中绽放出来的意象之美。事实上,无论是母子图、美人图还是文人笔下的仕女图,都蕴含着“互观”的结构理念,美人在画中观观者,观者在画外观美人,这是一对互为转化的关系。传统的教子育子图中,女性观的是孩童,观的是责任,观的是母爱传达的和谐之美与观者之间的共鸣与呼应。而观者所观是礼教精神框架内“母”和“子”稳定的二元结构,是男性审美标准之下家庭和睦、妻儿幸福的主观臆想。至于“姑苏版”中,美人在画中诉说着自己的烦恼与苦闷,以寂寞空虚的欲望表达撩拨着观者的心弦,相比之下,男性已不再是礼教驱动之下的审美主导者,转而变为了姑苏女性眼中的倾诉对象与观赏对象。似可认为,在这些美人画面前传统礼教的桎梏已经瓦解崩塌。究其根本,“观”的转换是不同时代人们思想认识的直接表达,清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妇学的发展与西教精神的传播过程中,各种“新思想”的迸发借“姑苏版”之载体,将新旧观念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女性新旧思想之变化。
依照前文所述,“姑苏版”中的“观”在形式上的分野主要聚焦于物象体积感的空间描述,由此引发出意象、形象之争。此间矛盾主要通过本、体两个向度体现出来。成中英对于本、体诠释为:“本,乃根源,是一种动态的力量,并在动态的过程得出结果:体。体,是一种目的。本,在成为包含目的的“体”的发生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10]在“姑苏版”中,本、体分别对应“观”与“象”两个层面。本之于体,既是前提也是核心,无本即无体,中国传统绘画的表达注重阴阳两和、虚实相济的“易简”思维,这既是千年传承的绘画语言,也是古人理解世界之根本。观者对于物象的描绘着意于空间位置的经营,宗白华云:“中国画法六法上所说的‘经营位置’,不是依据透视原理,而是‘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全幅画面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是大自然的全面节奏与和谐。”[11]117对于绘画元素的合理安排,归根结底源自于《易经》卦象之中的阴阳两爻,二者交错排列即可营造出多重的意象。“姑苏版”之本自然源自于此,但在西洋绘画的浸染下,却将阴阳之变汇聚于立体的宇宙空间中,形成了二维空间与三维空间交互叠加的宇宙观,这是导致“姑苏版”之体不同于文人画、风俗画、界画,也不同于西洋画之根本所在。这里以《西湖十景图》(海杜美术馆藏)为例,十里长堤、亭台楼阁、圆月拱桥均置于真实立体的空间中,而人物与马匹却以平面的形态生存于此,虽符合近大远小之理,但面容、肢体却无丝毫光影的描刻。西画之中多以近实远虚来模拟真人视野的逐步衰减,但此画之中,远山异常清晰可辨,山峦的层次之别、树木的疏密之别尽收眼底,完全不符合西画之中对景写生的节奏规律。如此情状不止于斯,《西湖胜景》(私人藏)、《滕王阁胜景》(海杜美术馆藏)、《姑苏虎丘胜景》(私人藏)等尽皆如此。如此说来,张烨所云之“洋风姑苏版”非“洋风”一词所能囊括,乃是以中西融合之思想描刻姑苏城市之新观感。
“姑苏版”中“观”的转变使得“象”的呈现亦有变化:除了有一些以传统手法表达意象精神的作品之外,还存在大量以写形为主的作品。中国绘画史上的形、神之辩由来已久,到明清,基本已成定论。石涛云:“山川万物荐灵于人,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苟非其然,焉能使笔墨之下有胎有骨,有开有合,有体有用……”[12]6如此论说便将中国画之“神”韵推向了顶峰。正如成复旺所云:“以前所未有的豪迈气概,更加彻底地解脱了‘形’的束缚,而且把‘神’的解放引向了人的解放。”[13]37而在“姑苏版”中,很大一部分胜景图选择了对景写生,这便与主流绘画理论背道而驰,此举缘于何处?又有何意义?形、神之辩其根本在于意象与形象之别,象之别其根本在于观之别。而观之别其根本在于“姑苏版”本体空间的变化。形成如此变化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
一是“姑苏版”本体的内在需求。清顾禄形容“姑苏版”曰:“鬻者多外来游客与公馆行台,以及酒肆茶坊,盖价廉工省,买即悬之,乐其便也。”[14]379作为以市场为导向,以精准受众为目标的“姑苏版”,在制作与发展的过程中所秉持的原则就是“求新求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清初期的苏州无论是开放度还是生活的奢侈度,以及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都是美术界西风东渐最佳的落脚地。”[15]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其既要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又要注入新鲜的艺术元素,这是“姑苏版”不仅存有一定的国内受众,还能持续远销海外的重要原因。
二是受宫廷绘画的影响。自康熙朝起,宫廷对于西洋艺术较为热衷的态度是“姑苏版”得以发展的通行证。“据高士奇《蓬山密记》,是年四月十八日,康熙帝对高士奇言:‘西洋人写像,得顾虎头神妙。因云有二贵嫔像,写得逼真。’”[16]康熙皇帝对于“神妙”与“逼真”的理解,深得西洋绘画之理。到得乾隆时期,西洋绘画已经成为宫廷绘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宫画师们不同程度地运用了透视,尤其获得了乾隆帝的称赞。”[17]192此外,“姑苏版”绘画空间的拓展也缘于“清廷与姑苏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供职于内廷的苏州画家徐扬所画的《盛世滋生图》、《乾隆南巡盛典图》可窥其一斑),这种新的绘画技艺在江南重镇苏州生根发芽”。[18]
上述原因促使“姑苏版”与清代艺术理论家们极度推崇的写“神”风韵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在二者话语权极不相称的情况下,“姑苏版”依然能够坚持发展了数百年,其意义不仅在于祈福迎祥、避祸消灾,更重要的是极为真实地再现了古苏州地区的人文风貌。若将“姑苏版”置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其艺术成就在文人眼里远不及其他品类的中国画富有意趣与神韵,但市井阶层的追捧与海外市场的热销足以证明其内在丰富的艺术内涵与人文精神。
(二)辨证视域下的“中和”
面对诸多矛盾,“姑苏版”选择将立体与平面的宇宙空间、中国与西洋的绘画语言、传统与前卫的思想观念视为对偶与互动过程中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在此之中,既包含了合适的运思方式,也呈现出和谐的图像内涵。二者在本体与思维的会通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和”之意,这也成为理解、评价姑苏文化与市民生活的“观”。
在“姑苏版”的艺术结构中,“中和”并非图像元素的简单拼接,而是在不同的视角之中适度再现了“观”的多样与统一。有将不同的社会现象进行中和。如《姑苏治平寺俗语》(海杜美术馆藏)中描绘了治平古刹中各僧侣的生活情状。有改邪归正的逃僧,有卖百家货的滑生、有勾肩搭背看热闹的厌僧与梦僧,更有口吐“假慈悲”却用烟管向一旁美人借火的小僧。不同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拼贴出一幅诙谐、讽刺的图景。再如《富贵贫贱财源图》(海杜美术馆藏)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于财富的追求与向往尽皆表现在画面上,有财有势的朝臣、见财起意的书生、念着谋财害命的官吏,还有梦见上方山求财神的妇人。这些揭露人性的谐谑图正是构成社会百态中的一部分,给观者带来愉悦的同时能够引发共鸣,且不会引发读者的反感。正如《诗经》所云:“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有将艺术形式进行中和的情况,如乾隆十二年制的《岁朝图》(海杜美术馆藏)以界画的形式表现长廊与庭院,借助西洋的明暗排线法构成画面的体积感,同时运用红、绿、黄三色敷彩,整体画面既保持了文人画的雅致,亦有年画的喜庆,更兼具西洋画的体积感,正可谓集众家特色于一身。又如乾隆八年(1743)制的《百子图》(海杜美术馆藏)表现的是元宵佳节之盛景,此图共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为题诗,中段为宅院中孩童们嬉戏玩闹的场面,下段则为府邸内孩童与美人共度佳节的情境,全图的绘制突出表现了西式焦点透视法以及明暗排线法,又结合中国传统节日的欢闹情状,此图即便置于今日也颇具时尚感。此外,亦有将不同观念进行中和的情况。如《双美爱竹图》(海杜美术馆藏)中左边的美人依靠着竹竿,用手整理着鞋袜,另一人手握兰花与之观赏,整幅画看上去和睦友爱。然而一旁娇嫩的竹笋却隐喻着美人的玉足,引起观者无限的遐想。如《双美舟游图》(海杜美术馆藏)描绘了两个年轻貌美的女性在池塘里采莲的情景,女子手握荷花象征着清白、高洁。而所穿长裙却是薄透的质料,隐隐的露出双腿,大有取悦男性之意。不难看出,这些图像突出表达了姑苏女性对于时尚的追求,但其艺术风格却依然秉持着文人仕女画的结构特征,如此便能凸显“姑苏版”运思之精巧。
这种“中和”更体现在对于“姑苏版”的理论总结中。例如,阿尔瓦雷斯·德·塞明多(Alvarez de Semedo)云:“就绘画而论,中国人喜好新奇,而不去追求完美地表现对象,……但是由于我们的启发,最近已经有一些中国的画家开始学习表现远近和阴影的方法,画出一些比较好的画出来。”[19]98又如:“郎世宁及其他的技术影响逐渐由宫廷画家向外与向下普及,最后终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专业画家与画商的画室、工厂中推广,在那里一种低水平的中西合璧的形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20]313虽然洋人以傲慢的语气品读19 世纪中国的绘画艺术,无可否认的是“中和”的思想确付诸于实践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莫小也云:“晚于此图(《清明上河图》——引者注)六个世纪的民间版画《姑苏万年桥》或许在场面范围与技巧方面还显得有点逊色,然而它所采用的写实主义手法,确实已经非同往昔。”[21]215此处的“非同往昔”既是对于“姑苏版”变革发展的客观阐述,实则也肯定了其求新求异的创新精神与艺术内蕴。
三、“姑苏版”中“观”与“象”的追求
《周易》作为易的系统化最高的成就显示了三个机体相关的系统与层次:一是宇宙自然取象系统,二是人事文明取象系统,三是心理行为取象系统。这三个系统的存在见之于易卦意义的确定与卦爻辞之形成。[22]16简而言之,“象”的生成源自于卦爻,而爻位之变化则始于“观”。《周易》以卦爻为中介连接了“观”与“象”,“象”既促使了“观”的形成,亦是其外在表达。对于“姑苏版”而言,“象”所具有的二重性使得“观”的阐发有了落脚点。若以自然取象为起点进行观察,这便是第一重“象”与第一重“观”。此后,在易学家的眼中,物象以阴阳二爻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姑苏工匠则将其刻画成美女娃娃、亭台楼阁的形式呈现在画纸之上。无论是意象还是形象,这些都属于第二重“象”,正是在这一层级里,成中英所言之人事文明取象系统以及心理行为取象系统才得以生成。这是第二重“象”的核心所在,亦是“观”进入到第二层级,形成繁复多变之观点的根本。大而言之,“观”的终极形态,也即成氏所言之“无观之观”,源自观者对于第二重“象”的理解,无“象”即无“观”。
“象”从大局来看,重视时间或空间的构成并以和谐稳定的图像结构为核心。此概念关系着“观”的理解与认知,又影响到观者对于第一重“象”(即原始物象)的再现与重塑。于此,可以说取“象”成为了“观”的原点,亦是其勾画理想与追求之本体。人们对于“象”的审美准则愈发严苛,这才导致“姑苏版”的艺术表达在当时处于诸多矛盾之中。实际上,对于“姑苏版”的质疑与漠视也正是清代艺术家们为了保证中国画之“观”内在的纯粹性而采取的保守态度。这看似是关于艺术风格的争辩,实则是对中国艺术本体的拷问,是艺术话语权的争夺。在第二层级当中,“观”是“象”的提炼与总结,是在“象”所引发的联想之中,以变化融合之势展开,从对本体的理解发展到自本体的诠释。这当中既有将印象与图像进行共时性的匹配,也有将个人情感置于时间与空间的变换当中,阐释历时性的动态变化关系,这不仅显示出“观”在不同视角、不同维度,或艺术作品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凝练过程,也充分展示了“象”在不同层次、不同理路之中的生成样态。
“姑苏版”中不同观点的形成并逐步演化为独具风格的“观”,离不开“象”内在的变化与融合,如若论其“观”,必以是否得“象”为要。如《大庆丰年图》(海杜美术馆藏)运用西法构建了准确的建筑空间与明暗关系,图中所绘大宅院布局精巧,层次分明,第一重“象”与第二重“象”相互映衬,由于绘制极为准确、精细,两重“象”几乎达到了无缝衔接的地步。观者遨游其中,如临现场,这正是取真实自然之“象”,通过画面中人物故事的铺设,凝练出五谷丰登、吉祥喜庆之“观”。若“象”引发了观者的联想,并形成与身体的共鸣,从某种程度而言,“观”便会处于理性范畴之外。如《春宵闺怨图》(个人藏)中的女子独坐床沿,宽衣解带,肤如凝脂,露出胸前粉色的内衣,下身着醒目的红色长裤。图中诸多敏感且强烈的暗示足以引发清代男子无限的遐想,观者对于第一重“象”的认知缺失使得图中所绘第二重“象”逐步与前者进行置换。处于第二层级的“观”在封建礼教之中应与此“象”产生巨大的冲突,欲望与意志之间的抗争便会影响“观”的路向。清政府严厉打击,而百姓则争相购买私藏,“观”因“象”而摇摆不定。如果两重“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观”也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如《白赖游放生池》(个人藏)描绘了名叫白赖的人去放生池游玩的场景,原本是为了百姓积累功德,放养动物的放生池,白赖所见却让人啼笑皆非。画面左侧的老僧将一条咸鱼进行放生,上方的倪道士买了一只鸽子放生,下方的商人将羊卵割下放生,右边的道士将死鸡拿去放生等。这些“象”原本可能是历时性的偶然事件,此图却将其拼接组合,形成共时性的存在,这就加大了两重“象”之间的距离,夸张的造型与滑稽的动作使得图中各人对于“放生”不同的理解与作者讽刺批判的观点融化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转化为高于生活的意象表达。
关于如何在“观”之中取“象”,古代圣贤早有定论,多以“易简”思维将物象化繁为简,取之精要。如《易传》所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3]343“姑苏版”中既含有繁复之象,简易之象,亦有传统之象,新潮之象,这也体现出《周易》当中简易、不易、变易、交易与和易的思想。以繁复之象而论,“姑苏版”以描绘姑苏城的宏大景观、年节庆典以及经典故事为主。因为这类主题的版画需要以丰富的细节吸引观者,而细节的生成离不开繁复结构的层峦堆叠,空间的分割与融合便能够带给观者最为直接的临场体验。而简易之象多以描绘人物、花鸟为主,这类主题的版画与文人画联系颇多,受其影响较大,即便融入了西法的明暗表现,但对于空间格局、层次排列而言并无较大突破。传统之象与新潮之象均是指观念的表达,对于传统意象的刻画正体现出其内在文化精神之源头,无论在形式上有多大更迭,传统文化的不变正是“姑苏版”能够多元发展之前提。新潮之象则与姑苏女性的群体形象以及吴地的社会风尚密切相关,这一方面是对于闺阁之中的女子而言,她们久居屋内却“含情不敢言心事”。儿女相伴,却始终想着“才郎何日锦衣还”,虽是人之常情,但通过画中诗词直白的表露出来却并不常见。另一方面,年轻女子纷纷结伴出游,或泛舟湖面,或信步林间。如张瀚所云:“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24]137此与传统妇女所遵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之纲常伦理相去甚远。此番景象既与清代思想解放之思潮密切相关,亦与吴地经济的富庶以及宽松的社会环境不无关联,新潮之象虽与传统封建伦理形成了冲突,但无疑影响了晚清乃至民国妇女解放思潮的萌发。综上所述,“姑苏版”通过“观”的表达,试图赋予“象”形态与情状的变化,进而追寻其内在的审美张力以及超越笔墨空间的心灵拷问。
四、结 语
从“姑苏版”中引发出来的“观”,成为清代中西艺术相互统合之基本关捩,而且可以看到“观”的不断发展使得“象”的呈现形式愈发丰富多彩。成中英云:“作为‘象’的发现和发明的‘观’,就是所有重要文化活动和文明活动的意义、灵感、动机的无穷源泉。”[9]229“姑苏版”各类图像均是在“观”的基本框架之中构建而成,而将“观”置于中国艺术的语境之中,亦使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了栖落与依托。正因如此,“观”的深化与发展不仅能够用以诠释“姑苏版”的美学特质,也成为催生意象的媒介所在。如刘继潮所云:“‘观’超越视觉生理,更多心智活动,是本体经验的综合直觉,内含记忆、想象的心理成分、情感成分,表现为思维的智慧。”[25]53
一如前文所言,“观”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姑苏工匠对于社会与自然的普遍观察,使得“象”的发现成为可能,而在进行思考并融合了创造性的观察之后,物象最终转化为“姑苏版”中的各类意象。在“观”被建立之后,本应有更加普遍和创造性的“观”得到阐发,我们却发现“姑苏版”意象内涵的发展逐步停滞。无论是薄老所云之“清军与太平军交战中阊门及山塘被战火摧毁最为严重,山塘画铺从此一蹶不振。”[26]还是张烨所云之“乾隆皇帝愈加保守的儒家道统观念以及政府愈加严厉的禁教政策”。[18]257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中断了“姑苏版”意象不断发展的生命历程。清末以后,桃花坞所制年画大量销往农村,“观”的结构理念与乾隆年间的“姑苏版”大相径庭。后世之人甚至不再记得“姑苏版”曾经辉煌的历史,转而将它与此类农村年画混为一谈。于此,便很难寻觅其中的诗画情境与古雅意趣。
虽然清末以后“姑苏版”的形式与风格发生了转变,然其以丰富的“观”构建而成的图画在今天依然洋溢着无可替代的美学气质,中西艺术的融合与发展也彰显出姑苏意象所具有的丰沛生命力。冯骥才在给2018 年“中国苏州首届国际木版年画展”的贺词中云:“姑苏年画曾是世界认识苏州的迷人窗口,未来将是苏州走向世界的靓丽名片。它曾经是古丝路上联系文化的纽带,未来将是各国之间文化的桥梁。”今天对“姑苏版”进行总结与挖掘,有助于当代苏州版画内在的“观”的丰富与发展,亦可促进“象”的多元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