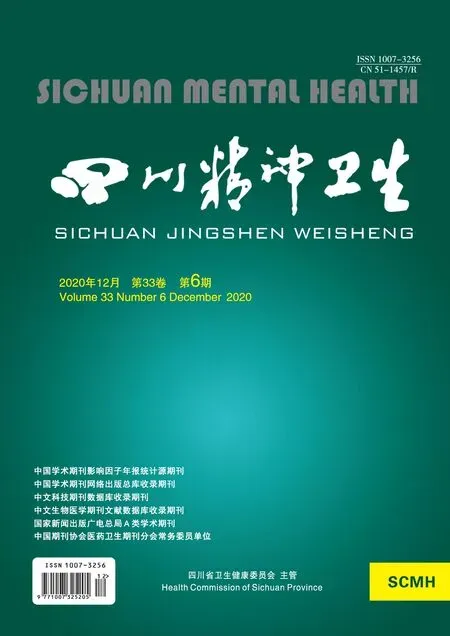双相障碍的功能损害及相关因素
张 勇,张 健,邹韶红
(1.天津市安定医院,天津 300222;2.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新乡 453100;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1*通信作者:张 勇,E-mail:zhyzhangyong003@163.com)
双相障碍是以心境高涨与低落为特征,易复发、呈慢性化发展的一组疾病。据报道,全球高于1%的人群罹患双相障碍,其中双相障碍I型终身患病率为0.6%,双相障碍II型为0.4%,2.4%的人群为边缘性双相谱系障碍[1]。黄悦勤等[2]报告双相障碍的一年患病率和终身加权患病率分别为0.5%和0.6%,男性和女性患病率相似(0.5%vs.0.4%),35~49岁的人群患病率高于其他年龄段。双相障碍因存在严重的自杀行为和躁狂发作而反复住院,复发率高,功能严重受损。
1 双相障碍患者社会功能损害
我国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规范指出,社会功能是指社会生活中个体参与社会交流沟通并适应社会的能力[3],社会功能基本上涉及工作或学习、社交和家庭功能三个层面,包括工作能力、学习能力、独立生活能力、休闲娱乐活动和社交活动等多个维度[4]。
双相障碍患者社会功能损害的程度虽然不如精神分裂症,但躁狂抑郁严重程度、风险因素和残留症状等可能加重社会功能损害。双相障碍患者即使在稳定期仍表现出与精神分裂症类似的社会功能损害,如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职业功能损害[5-6]。相比人际关系和自我照料能力,双相障碍患者的职业功能受损明显[7],比单相抑郁患者失业率更高,13%~34%的双相障碍患者面临频繁的工作挫折[8]。大多数双相障碍患者症状稳定后,仍难以达到病前的社会功能状态。一项为期2年的随访结果显示,尽管64%的双相障碍患者达到临床痊愈,但66%的患者仍不能达到功能恢复[9]。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58.6%的稳定期双相障碍患者存在社会功能损害[10]。
社会功能受损的原因较复杂,涉及生物学和社会心理因素等。社会认知研究发现,躁狂相及缓解期双相障碍患者对恐惧和厌恶表情识别较差,而抑郁相患者则对惊讶和快乐等面部情绪识别较差[11-12]。功能磁共振成像提示,患者在接受情绪识别任务过程中右腹侧前额叶皮质区、右前扣带回前膝部、杏仁核、边缘皮质异常活跃[13]。错误信念和情绪认知差与心理社会功能下降存在关联,表明社会认知缺陷可能是双相障碍患者社会功能减退的关联因素。此外,双相障碍患者敌对的归因模式是导致社会交往减退的社会心理因素[14-15],推测社会认知可能通过神经认知的介导影响社会功能,但其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
双相障碍社会功能损害还可能和性别、发病年龄、发作形式、不同亚型等相关联。有研究显示,男性、发病期年龄大可能是社会功能差的危险因素,年龄大的双相障碍患者可能更倾向于感知自己日常生活和功能受损状态[16-17]。双相障碍发作形式也与社会功能损害存在关联,阈下情感症状,如不严重的轻躁狂和轻度抑郁可能与职业功能差有关[18]。但轻度至中度抑郁发作对职业功能的影响比躁狂发作严重,推测抑郁发作可能减少了人际交往、削弱工作效能,进而导致职业功能下降[19]。持续的阈下抑郁症状可能与社会功能恢复差相关,反之,功能缺陷更有可能使情绪症状不稳定[20]。荟萃分析显示,残留的抑郁症状是社会功能损害最显著的影响变量[10]。
双相障碍不同亚型之间社会功能损害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有研究表明,双相障碍I型和II型患者可能面临同样程度的社会功能损害,亚型间差异并不显著[21]。但也有研究显示,双相障碍II患者功能损害程度较轻[22]。社会功能损害的差异性可能与评估工具、病程和患者病前认知和心理功能有关。
临床实践发现,双相障碍社会功能存在从浅至深的损害特征,首先是个人生活技能缺陷,如不能自我照料、个人事物处理困难、购物就医需要帮助等。其次是日常社交能力不足,如和亲友及邻居的基本交往能力差或技巧匮乏,延伸至和陌生人交往被动等。严重者表现为工作和学习能力损害,甚至个人价值的实现受到挫折,社会认同受阻,再严重者社会退缩和隔绝。在对双相障碍患者社会功能认识的评估过程中,应把社会功能分层细化,选择有针对性的评估量表,如社会交往技巧评估,工作效率评估和工作能力评估等,对社会功能损害严重程度的分层评估越明晰,临床干预措施才越有效。
2 双相障碍患者认知功能损害
认知功能包括信息处理速度、注意与警觉性、词语学习、视觉记忆、工作记忆、执行功能和社会认知等方面。认知功能障碍应该包括主观认知下降和客观认知下降两个层面。主观认知下降(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SCD)是指自我感受的认知过程如注意、记忆和工作能力的下降。客观认知下降(o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OCD)是通过相对量化的工具评估的认知功能损害,涉及记忆、语言、执行功能、视觉-空间知觉、定向和注意力等。目前对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主要是指客观认知损害,如轻度认知损害(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23]。研究显示,SCD可以预测4~10年后痴呆和MCI的发生,它可以早期预测客观认知下降甚至认知损害[24]。
双相障碍认知损害涉及较广,包括执行功能、注意、词语-非词语记忆等。近70%的稳定期双相障碍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损害[25],Cullen 等[26]报道了稳定期成人双相障碍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程度,其中执行功能损害最高达57.7%,注意和工作记忆损害程度为9.6%~51.9%,词语记忆和视觉记忆损害分别高达44.2%和32.9%,病程长和使用抗精神病药物与认知功能损害关联显著。由于认知功能损害评定方法不同,双相障碍认知功能损害的发生率为4.1%~67%(中位数15%),如限定至少有两个认知维度的平均Z值≥1个标准误差(SD)时,才认定为有临床意义的认知损害(clinically significant cognitive impairment,CSCI)[27]。因此,双相障碍认知功能的客观评估方法仍需进一步探索。
认知功能损害存在显著的生物学机制。双相障碍执行功能和词语记忆的遗传因素突出[28],双相障碍患者的未患病一级亲属认知功能完整占45.6%,有选择性的认知功能损害占31.0%,认知功能完全损害的占23.4%,且其词语流畅性和工作记忆受损比健康对照者严重,但在控制了阈下抑郁和躁狂症状、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IQ)值之后,一级亲属和健康对照者之间其他认知维度的损害差异并不显著[29]。双相障碍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的脑影像学Meta分析显示,双相障碍患者左侧扣带回后部的白质纤维链接显著减少可能导致认知功能损害,而脱髓鞘病变可能是白质纤维链接减少的原因之一[30]。一项研究比较了青少年和成年双相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差异的脑影像结果,两者情绪识别和加工存在不同的脑结构和功能差异,青少年双相障碍患者的杏仁核活性高于成年双相障碍患者;而针对非情感类的认知缺陷,青少年双相障碍患者扣带回前部功能下降比成年人更明显[31]。双相障碍认知损害可能存在谷氨酸(Glu)和γ-氨基丁酸(GABA)神经递质功能失调,荟萃分析尽管发现双相障碍患者海马的Glu能水平增高,但未发现与记忆存在相关性,但提示前扣带回GABA低功能与认知功能受损存在关联[32]。
影响双相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因素较多,如受教育程度、病程或住院次数、不同亚型、共病以及抗精神病药物使用等。受教育程度低和共病躯体疾病不仅是普通人群轻度认知损害和痴呆的危险因素,也是双相障碍患者记忆和执行功能损害的相关因素。患者受教育程度高、病前IQ水平较好是双相障碍认知功能的保护性因素。躯体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和炎性疾病对认知功能损害影响最突出[33]。双相障碍反复发作,病程长以及多次住院都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认知损害。Bora[34]研究显示,有精神病史,不论哪种亚型,都会加重认知功能损害,尤其是词语记忆、信息处理、执行功能(问题解决和计划性)、工作记忆和社会认知等,这可能与伴有精神病性症状以及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有关。
双相障碍II型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维度与I型相似,只是严重程度较轻。与双相障碍I型患者相比,双相障碍II型患者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尤其是词语记忆损害较轻,双相障碍II型患者在注意、计划性、工作记忆和抑制性等方面与双相障碍I型患者差异不显著[35]。
目前对双相障碍认知障碍的认识和评估并不完善,一方面,国内外仍缺乏针对双相障碍的敏感性高、特异性强的评估工具,即使有一些认知评估工具也是源于对精神分裂症认知损害的评估,是否适用于双相障碍有待验证和商榷,开发适合于双相障碍患者的本土化认知评估系统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由于对双相障碍阈下抑郁或者(轻)躁狂的界定不清,识别困难,伴发的认知损害评估欠缺。因此,对双相障碍认知功能的客观和量化评估应建立在严格而明确的诊断基础上,阈下双相障碍症状是否归类在严格意义的双相障碍诊断之内还存在争议,如果扩大诊断,会削弱对认知功能损害的认识。
3 双相障碍认知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关联
双相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紧密相关。Stern等[36]提出“认知储备”的概念,反映神经网络及大脑功能的灵活性和效率,包括病前智商水平、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成就三个层面。认知储备作为临床症状的保护性调节因子,对临床症状和治疗结局具有重要作用。Anaya等[37]进一步研究发现,稳定期双相障碍患者认知储备不仅与词语记忆、信息处理、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相关,而且可以预测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认知储备好的双相障碍患者可能更有能力处理个人日常生活,保持更好的人际关系,获取更多的自我满足感。回归分析显示,对60岁以上双相障碍患者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抑郁严重程度以后,词语学习和记忆、执行功能仍是社会功能的预测变量[38]。
虽然认知功能损害可能是社会功能受损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但还无法确定哪一种认知维度对社会功能造成影响。词语记忆、信息处理速度、词语流畅性和工作记忆可能和功能残疾关联性证据较多,而且在双相障碍全病程始终存在。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联性也受其他因素影响,对共病精神活性物质使用障碍的双相障碍患者,其认知功能损害水平显著高于不伴有精神活性物质使用障碍的双相障碍患者,而且发病后的社会功能更差,恢复的时间可能更长[39]。同样,双相障碍患者共病精神病性症状,其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损害更显著。这些研究提示共病不仅影响基线认知水平,也可能加速社会功能的损害。
虽然较多研究显示,认知功能对社会功能有预测和影响作用,但二者的关系并不简单,认知功能对社会功能的影响,强调了认知功能的生物学属性,如脑功能连接和神经电生理异常等机制,即使如此,认知功能如何影响社会功能的机制还不是很清晰,认知功能是否通过调控情绪加工和识别从而影响社会功能还在探索当中。同时,社会功能的心理社会属性并不完全受生物学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知觉同时也受归因方式和负性思维模式的影响,而社会知觉偏差可能会导致社会功能尤其是人际关系的缺陷。因此,评价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必须考虑二者之间可能的中介机制。
4 不足及展望
国内外研究和指南均提出,双相障碍功能改善作为治疗目标,强调了双相障碍功能损害对疾病转归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对双相障碍患者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的研究仍存在不足:首先,缺乏对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评估的有效工具,尽管一些研究显示双相障碍社会功能的评估工具如功能评估简版(Functioning Assessment Short Test,FAST)、席汉残疾量表(Sheehan Disability Scale,SDS)信效度较好,可以比较全面地评估患者的社会功能[40],但针对双相障碍患者社会功能的评估工具仍缺乏;对认知功能也缺乏一致性的评估手段,甚至对认知功能的主观感受和客观评估存在差异,提示在认知评估中应重视客观评估和主观感受的一致性评价,可能更准确地反映认知功能。其次,对双相障碍患者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的病理心理机制探索不深入,如双相障碍患者的情绪识别和加工障碍与社会功能损害的病因不明。而认知功能损害的动态脑网络研究虽有初步发现,但不足以揭示认知损害的脑网络机制[41]。最后,国内精神障碍康复服务规范提出了促进精神障碍患者的功能康复训练目标,提示双相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和社会功能康复还需要结合国际前沿,发展本土化的干预康复范式。
综上所述,双相障碍患者的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评估工具需要进一步开发,尤其是操作简便、评估有效的工具。此外,影响双相障碍患者功能损害的多维度因素,如脑功能、免疫炎性等生物标志物、生活方式和临床症状的综合研究还需深入,将促进对双相障碍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的认识,对进一步干预提供临床依据[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