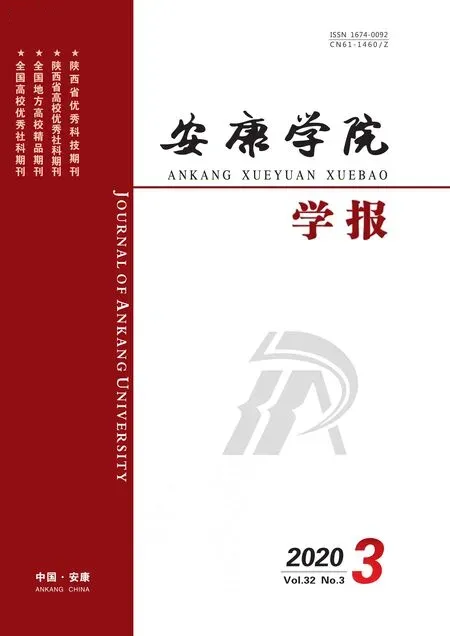《史记》中的少年郎
韦秀娟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它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形象丰满的历史人物,少年郎便是其中的一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说的少年时期是指一个人从出生到身体发育达到成熟的这段时间,包括幼年、童年、少年时期,属于成年前的时期即二十岁之前。《史记》中塑造的少年形象,是比较多的,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高祖本纪》中的刘邦、《孔子世家》中的孔子、《陈涉世家》中的陈涉、《留侯世家》中的张良、《陈丞相世家》中的陈平、《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吴起、《商君列传》中的商鞅、《樗里子甘茂列传》中的甘罗、《孟尝君列传》中的孟尝君、《屈原贾生列传》中的贾谊、《李斯列传》中的李斯、《张耳陈余列传》中的张耳和陈余、《黥布列传》中的黥布、《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扁鹊、《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的卫青和霍去病、《万石张叔列传》中的石奋、《酷吏列传》中的张汤等。司马迁对这些少年故事的记述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在篇首直接交代姓名、籍贯、身世等,这类篇目比较多,比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 《张耳陈余列传》 《淮阴侯列传》 《卫将军骠骑列传》等。有的则是借助他人之口,转述少年时期的故事,如《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吴起,是借助鲁人之口向读者介绍了少年吴起“猜忍”的形象。虽然记述方式不一,但呈现出来的少年郎形象都活灵活现,令人印象深刻。
一、少年类型
《史记》中塑造的少年形象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少年不凡型和少年平庸型。首先,少年不凡型又可根据描写方式的不同,具体划分为以下四种:
(一)胸怀大志型
李长之曾说:“至于司马迁在所爱的才之中,最爱的是哪一种?一般地说,是聪明智慧,是才能,是不平庸,或不安于平庸,或意识到自己不平庸的。但尤其为他所深深地礼赞的,则是一种冲破规律,傲睨万物,而又遭遇不幸,产生悲壮的戏剧性的结果的人物。”[2]这类人物的突出代表是《项羽本纪》中的项羽、《陈涉世家》中的陈涉。《项羽本纪》中的项羽在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时,发出的“彼可取而代也”[3]80的豪言壮志,向我们展现了项羽自命不凡、立志高远的非凡形象。《陈涉世家》中陈涉的一句“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3]2365历来为人称道,成为不甘平庸的励志名言。这些少年郎虽然人生经历各不相同,甚至身份差距悬殊,但都因胸怀大志而异于常人。
(二)少有异才或异举
一般而言,少年时期是传主功业未就、还未发迹的时期,但不乏特殊情况。因为才华出众、能力非凡而得到重用,其出场便是成功的少年郎形象,比如《樗里子甘茂列传》中的甘罗、《屈原贾生列传》中的贾谊、《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的霍去病等。具体而言,《樗里子甘茂列传》中的甘罗一出场便意气风发,年仅十二岁,出使赵国,略施计谋便让秦国轻松得到十几座城池,被拜为秦上卿。此外,贾谊一出场也向我们展示出年轻有为、才华出众的成功者形象。据《屈原贾生列传》记载,贾谊十八岁时便因能诵读诗书会写文章而闻名当地,后经吴廷尉的推荐二十多岁便被征召为博士。《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的霍去病也是如此,年纪轻轻便因抗击匈奴有功,被封为冠军侯,食邑达一千六百户。
少有异举是指《史记》中所塑造的少年郎在少年时期表现出超越本年龄阶段的行为,往往以其惊人之举,令人惊叹不已。以《孔子世家》中的孔子、《酷吏列传》中的张汤为典型代表。如《孔子世家》记述孔子一出场就“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3]2311少年时期的孔子便表现出好礼的举动,异与同龄人。纵观《史记》所载的孔子一生行迹,“礼”字贯穿始终。《酷吏列传》中的张汤“少年审鼠”表现出来的老练残酷的举止,给读者留下了少年老成的深刻印象。其举止超越了该年龄段应有的行为,连他的父亲都大吃一惊。
(三)借他人之口突出其不凡
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在塑造《史记》中的少年郎不凡形象时,一般不会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直接交代,而是采用多种方式,巧妙地表现出来,比如经常会引入第三人,借用他人之口,强调人物未来命运的不凡。这在《黥布列传》 《卫将军骠骑列传》 《商君列传》篇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如《黥布列传》记载:“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3]3151相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司马迁在此借用客人的言语预示黥布未来的大好前程。类似的故事情节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书写少年时期的卫青时,同样出现了。再如《商君列传》中少年商鞅的奇才也是通过公孙座向魏惠王引荐来展现的。可见,司马迁在塑造人物形象、记述人物事迹时,有固定的叙事模式。
(四)少有传奇经历
由于司马迁自身有“爱奇”思想,故其在史料的取舍上往往会倾向于奇闻轶事,追求故事的曲折离奇。正因如此,《史记》的文学色彩十分浓郁。如司马迁在塑造少年刘邦形象时,为追求文章的新奇,采用了民间传说,使得故事叙述充满了神秘和传奇的色彩。再如《扁鹊仓公列传》中,司马迁在塑造名医扁鹊时,就在传记的开头记述了扁鹊因得到长桑君的禁方而使眼睛具有“透视”功能,从此医术出神入化的故事。整个故事的叙述同样充满荒诞传奇的色彩。司马迁在叙述扁鹊医术的过程中,也塑造了他礼、恭、谦的形象特征。再如《留侯世家》中的张良,少遇黄石老人得兵书的经历也充满浪漫色彩,亦是司马迁爱奇思想的体现。曾国藩曾对此评论道:“太史公好奇,如扁鹊、仓公、日者、龟策、货殖等事,无所不载,初无一定之例也。”[4]663
此外,是少年平庸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平庸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才识平庸、碌碌无为,而是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指经历平凡,没有传奇之处,出场方式比较常规;第二,指社会地位一般,不显赫。如《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陈丞相世家》中的陈平、《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吴起、《孟尝君列传》中的孟尝君、《张耳陈余列传》中的张耳和陈余、《李斯列传》中的李斯、《万石张叔列传》中的石奋等。这些少年郎并不一定兼有这两点,符合一点即可,但不乏两者兼有的。如《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他的出场方式就很常规,其少年故事并没有太大的波澜起伏,不会给人特别新奇、眼前一亮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万石张叔列传》中的少年石奋,虽没有任何才能却能凭借“恭敬”的性格,得到了汉高祖刘邦的重用,从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司马迁在这里对统治者作了不露声色的讽刺。
以上是对《史记》中的少年郎进行整体的把握。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少年郎多是《史记》中的出场人物,即人物的首次亮相。人物的出场方式对于展示人物形象具有重要作用。精彩的出场不仅能夺人眼球,引起阅读兴趣,还能让读者瞬间捕捉到人物的本质特征。
二、塑造艺术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编撰体例,其写人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塑造了千姿百态、活灵活现的历史人物,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少年郎时,同样调动了多样化的艺术手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先声夺人
先声夺人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常用的叙事技巧,即在人物出场之前,先由一个“第三人”对他们进行引荐、评价,突出其卓越非凡、与众不同,达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艺术效果。比如《屈原贾生列传》中,汉文帝知道贾谊,是因为吴廷尉的引荐。值得注意的是,贾谊的出场运用了多次“先声夺人”法,首先吴廷尉因“闻其秀才”而赏识贾谊,汉文帝知道吴廷尉是听说他“治平为天下第一”[3]3020,汉文帝知道贾谊是因为吴廷尉的引荐,三个层次环环相扣,对所要表现的贾谊形象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再如《商君列传》中的商鞅,人物还没出场,先借助“第三人”公孙座之口,由公孙座病危举荐,才将商鞅的奇才引出来。
(二)以小见大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曾说过:“(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3]2487张良平时与刘邦谈论天下的事情很多,凡是与天下大事无关的,就不记载了。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是有自己的书写原则的,抓住最能表现人物风采的典型事件。但《史记》中仍然穿插了许多轶事,这些故事看似闲笔,漫不经心,实则富有深意。如司马迁在塑造这些传主少年形象时,总是会选择一些典型的小事,避实就虚,见微知著,通过这些小的事件来展示主人公的性格志向或者品德才能。具体体现在司马迁在《李斯列传》 《酷吏列传》 《淮阴侯列传》篇对李斯、张汤、韩信形象的书写。如《淮阴侯列传》中连续记载了韩信少年时期的三件小事,以突出其爱憎分明、知恩图报、忍辱负重的性格,而这些性格始终贯彻韩信的一生。《李斯列传》中,开头便记述了李斯见仓中鼠和厕中鼠的故事。当李斯看到仓中鼠和厕中鼠见到人犬时的不同表现,不禁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3]3083由老鼠想到了人,表现出了李斯内心深处对名利的追逐,这便为后来李斯被赵高用名利策反埋下伏笔。如同白寿彝所说的“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5]。钟惺对此也有经典的评价:“李斯古今第一热中富贵人也,其学问功业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贵之资;而其种种罪过,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之道。究竟斯之富贵仅足以致族灭,盖其起念结想,尽于仓鼠一叹。”[4]627最为典型的是《酷吏列传》中对张汤少年事迹的记述,如下: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3]3809
不同于对其他酷吏的书写手法,司马迁在书写少年张汤时,别出心裁地选取了“少年审鼠”的生活琐事。通过这件琐事,突出了少年张汤睚眦必报的性情以及在审案方面的杰出才能,为其日后治狱毒苛埋下伏笔。纵观张汤的一生,皆以此为线。故事虽小,却能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以达到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的效果。此外,还能借助这些小事来折射当时的社会风貌。如《留侯世家》中的张良、《项羽本纪》中的项羽。借助张良狙击秦始皇、项羽扬言要取代秦始皇来暗寓世人对秦始皇统治的不满。
(三)反复渲染
反复渲染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叙事技巧。具体是指司马迁为突出人物性格或奇异之处,习惯用多个事件来反复强调。比如在写刘邦少年时期的事迹时,为了突出“天命神授”之不诬,连续写了几件“异人异兆”。先是用母亲刘媪有孕的奇异故事突出不凡,再用“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3]437的体貌特征以示不同于常人,再借助酒店主人的视角等表现天人异象。司马迁在此虚实结合,多角度、多层面地去书写少年刘邦的非凡之处,不仅使整个故事充满神秘色彩,而且丰富、充实了人物形象。同时,也体现出司马迁自身的“爱奇”思想和创作倾向。这种笔法在《史记》塑造少年郎时比较常见。再如《孙子吴起列传》篇,司马迁为了表现法家人物吴起“刻暴少恩”的特征,借助鲁人之口,连述了其“杀妻求将”“诛杀乡党”“母死不归”的三件事情,层层渲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对比烘托
对比就是将事物相对比,具体表现在人与人之间或者事与事之间。比较的方法是司马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经常使用的艺术技巧。通过对比,造成巨大的反差,有助于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鲜活。比如《陈涉世家》中的陈涉: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3]2365
司马迁为了突出少年陈涉的不凡,将其与同类庸者进行对比,突出了陈涉出言不凡、志向远大的光辉形象,同时也为下文陈涉起义反秦,自立为王埋下了伏笔,提供了性格依据。
三、叙事功能
由于《史记》时间跨度比较长,内容丰富,司马迁在作《史记》人物传记时,往往着眼于最能代表人物成就、最能表现人物本质的事件。《史记》中塑造的少年郎大多是《史记》中人物的首次亮相,因此司马迁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对故事做到了精挑细选。这些故事看似笔调轻松,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旨在探究这些少年故事的用意和作用即叙事功能。应注意到,司马迁在叙述这些少年故事时,有一定的“套式”即叙事模式,使读者在阅读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一)预设作用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史记》在塑造这些少年郎时,其叙事有一定的“套式”,经常设置悬念,具有预设作用。其预设往往有两种方式:第一,以神秘现象预设,充满神奇色彩。比如《高祖本纪》为了突出少年刘邦的天命不凡,连用几件奇异事件。第二,借助预言来达到草蛇灰线、埋伏千里的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暗示人物未来与命运,司马迁塑造人物,经常会借用一些预言来做伏笔。比如《黥布列传》中记载了英布相面的故事,相客预测其将“当刑而王”[3]3151,成年后的黥布果然因为违法被处了黥刑。后被徙骊山,组织刑徒逃亡,在秦末大起义中逐渐发迹,先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被刘邦封为淮南王,一生轨迹皆如相士所言。《卫将军骠骑列传》书写少年时期的卫青,同样是借助预言的方式。借助钳徒相面,预示卫青将来会官至封侯的人生走向。
其次,预测事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商君列传》篇。《商君列传》记载了公叔座向魏惠王举荐商鞅,魏惠王不重用商鞅最终导致魏国国势衰微的故事。司马迁在这里借助谋臣策士公叔座的预言,对未来作了预测,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最后,预设人物性格,为后文情节的发展提供性格依据。司马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会在文章的开头设有“文眼”,即文章之骨,通常以一两个关键词便能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无论后文情节如何波澜起伏,人物故事皆以此为主线,万变不离其宗。《项羽本纪》是个典型的例子。项羽出场时,司马迁通过记述他学书、学剑到学兵法的事迹,刻画了其性急而又有豪气,志气远大而又浮躁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在他少年时初露端倪,并伴随其一生。同时,这些故事也为后文情节的发展,即项羽失败的悲剧结局提供了性格依据。这类篇目还有很多,比如《淮阴侯列传》开篇记述的少年韩信的三件小事,展现了其爱憎分明、知恩图报、忍辱负重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也贯穿韩信的一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司马迁在塑造这些少年郎时经常设置悬念,使得故事跌宕起伏,增强了《史记》的文学色彩。
(二)结构完整
司马迁描写的少年故事除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外,还尽可能地兼顾了结构的完整性。“传记文学是人物一生行事的实录,由于人物出场往往出现在一作品的开头,而作者总是在出场中点明传主一生行事的主导倾向的总轨迹,因而它兼有概括全文,点明线索的作用。”[6]正因为如此,使得《史记》的叙事结构比较完整。
司马迁往往会在人物出场时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人物身上的某些特质,以此作为全文总线,而在全文故事发展中屡次穿插,多方呼应,以达到前挂后连的效果。如《孔子世家》记述孔子一生的行迹时,处处写了他学礼、问礼、好礼、司礼、讲礼,孔子一出场就表现出学礼的举止。“礼”贯穿孔子的一生。《商君列传》与此同例,“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学,则鞅所以说君而君说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变法’,曰‘卒定变法之令’,曰‘于是太子犯法’,曰‘将法太子’,而终之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血脉何等贯穿!”“法”字是《商君列传》一以贯之的主线。[4]577正如余嘉锡所评论的:“司马迁之文,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未尝枝枝节节而为之。相其气势不至终篇,必不辍笔。”[4]221
此外,其结构完整还体现在司马迁在塑造这些少年形象时,表现的人生轨迹是完整的。虽然,司马迁笔下人物的出场和退场年龄不一,有的出场便是一位年老者,如《项羽本纪》中的范增、《齐太公世家》中的吕尚、《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及《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老子等。有的少年时期便匆匆退场,如《樗里子甘茂列传》中的甘罗。但《史记》中不乏有人生轨迹完整的,这在《史记》单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司马迁对这些传主的书写都是“从传主的姓名、籍贯、家族、青少年轶事写起,再到登上历史舞台后的重大事件,最后写其人生结局”[7]。纵观《史记》中的少年郎,司马迁对他们人生轨迹的书写相对比较完整,有始有终。结构的完整性对丰富传主人物形象、把握传主人生轨迹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法,向我们展示了众多风神各异的少年郎,勾勒出一幅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因《史记》中的少年郎多为首次出场的人物,司马迁在对他们进行书写时,对故事材料的抉择可谓精挑细选,富有深意,但同时又特别注意谋篇布局,兼顾结构的完整性和情节的关联性。同时,司马迁在书写这些少年故事时,有相似的叙事模式。纵观这些独具匠心的叙事手法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浓郁的文学色彩,可以说《史记》无愧于中国叙事文学之伟大里程碑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