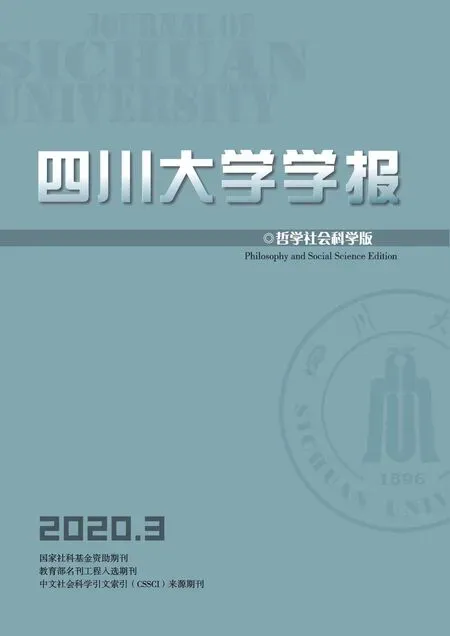论主权国家边疆的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
罗中枢
边疆的发生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同时空条件和文明体系中的边疆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现代国际国家体系的开始。此后,主权国家逐渐成为国际国家体系的主体和划分世界空间的基本单元,主权国家及其主权、领土、边界和时空表现成为框定其边疆内涵、形态和特征的根本依据。尽管不同国家的边疆各不相同,但边疆有其共性。“在某种程度上,世界上的边疆地区是相似的”。(1)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袁剑译,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6页。那么,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边疆区别于非边疆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一般边疆概念的核心意蕴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同理,主权国家边疆及其本质特征的考察也可以成为一把钥匙,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上的种种边疆形态。本文拟在考察中外学者关于边疆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主权国家的边疆区别于非边疆的本质特征,考察一般边疆概念的本质,并进而认识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的对象和性质。
一、边疆的特征是中外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主权国家的边疆作为一种特殊的时空统一体,其存在和变化涉及多方面的复杂关系,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发现其不同的特征。19世纪以来,边疆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边界、边境、跨境流动等成为多种学科研究的对象,中外许多学者对边疆的特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深化了对边疆的认识。
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从地理政治学角度探讨了国家及其边界、边疆、疆域的空间关系和毗邻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集中考察了国家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和毗邻国家之间的“边界-边缘”关系,阐述了边疆的政治性、临界性、边缘性、有机性、关系性和复杂性等特征。(3)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第122-136页。
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从历史学角度把欧洲通常使用的边疆概念即靠近边界的“政治边疆”,转变为源自美国本土的边疆概念即拓殖和西部开发进程中的“拓居边疆”,并借此阐述了美国的西进运动及其作用,以及独具特色的美国历史、文化、制度、民族和时代精神。特纳所描述的“移动的边疆”犹如冰川作用过程中碎屑堆积而成的冰碛,(4)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指出:“开初,边疆是大西洋沿岸。真正说起来,它是欧洲的边疆。向西移动,这个边疆才越来越成为美国的边疆。正像一层一层的堆石是由冰河不断地流过而积成的一样,每一次的边界都在它的后面留下了痕迹,而一旦形成定居地以后,这块地方仍然保有边界的特点。”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黄巨兴译,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页。总是处于生成、混杂、沉积、叠加、变化、延伸的过程之中,表现出生成性、动态性、扩张性、弥散性、社会性、模糊性等特征。
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从英殖民帝国的利益出发,从地缘政治博弈、战略防御与扩张的角度探讨了边界和边疆问题,他把边疆视为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作出的一种战略设计,明确提出了“科学疆界”和“战略边疆”概念。在寇松看来,边界和边疆都具有利益性、传承性、建构性、缓冲性、权宜性、战略性等特征。(5)乔治·纳撒尼尔·寇松:《论疆界》,张凯峰译,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第153-191页。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把边疆与古今文明、社会结构、民族文化和地缘政治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上的边疆可分为“在两个同质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和“在两个相异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边疆”,(6)欧文·拉铁摩尔:《历史的疆域》,牛昢昢译,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第353页。前者以动态性、内聚性、融合性、延续性等为特征,后者以静态性、排斥性、抗衡性、变异性等为特征,两类边疆的发展、表现和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拉铁摩尔重点考察了中国边疆的特征、变化及其原因,(7)欧文·拉铁摩尔向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社会及边疆社会中,什么特征是主要的?什么特征是次要的?近代新的力量因素进入后,哪些特征被摧毁?哪些特征仍然存在?这些仍然存在的东西又必然经受什么样的改革与修正?还有,我们所谓的近代文明中,有什么特征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什么是次要或不必要的?”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页。阐述了边疆的形成、类型、一般规律以及中国在北部和南部创建“两类边疆”的具体过程,强调了边疆的政治性、社会性、建构性、动态性、相互性、矛盾性等特征。
国外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边疆的特征。比如,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在《上西里西亚的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政治边界与文化边界的紧密联系,以及边境与边界的区域性、动态性、交互性、文化性、功能性等特征。(8)理查德·哈特向:《上西里西亚的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张凯峰译,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第221-251页。琼斯(Stephen Barr Jones)把包括边疆在内的政治区视为一个运动的“场”,对其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进行了考察,展现出政治区的场域性、建构性、动态性以及有形与无形相结合等特征。在琼斯看来,“政治区”包括任何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区域,“所有政治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有公认的界线,虽然界线不一定是条线,也不一定就是永远不变的”。(9)转引自王恩涌等:《政治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拉普拉德尔(P.Geouffre de Lapradelle)从国际法角度对边界和边境进行了研究,强调了边界的条约性、利益性、人为性和边境的边缘性、关系性、政治性和过渡性等特征。(10)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二卷“边疆民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8-252页。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在研究国家、社会与民族相互关系的过程中讨论了边疆和边界问题,强调了边疆的区位性、边远性、边缘性、时空性等特征。(11)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59-62页。
在国内学界,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就边疆和中国边疆的特征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何明在《边疆特征论》一文中联系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阐述了边疆的建构性、交错性和矛盾性,指出边疆是国家形塑及多重力量互动的产物,并随着国家治理模式、战略选择、实力消长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变化而不断被解构与重构;边疆是国家疆域伸缩和边界重新划分与民族分布空间的非同步性所形成的领土边界与民族分布的交错区域;边疆既是为了国家安全而对境外武装力量、跨国流动的人和物以及意识形态、文化、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阻隔,同时也是跨国配置资源以获取利益的一种桥梁。(12)何明:《边疆特征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30-136页。
周平指出,中国陆地边疆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边”“远”“杂”“贫”“特”——边疆处于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并与边界和他国相邻,深受他国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边疆处于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能量和信息传导的末梢;边疆的族际关系复杂;边疆地区大多自然条件较差,环境脆弱,资源有限,贫困现象较为严重;边疆的社会机制、发育程度、文化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等都有其特殊性。(13)周平:《国家治理视阈中的边疆治理》,《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4期,第51-54页。
王铭铭在《说“边疆”》一文中,从政治、历史、社会角度分析了从古至今由“边缘”到“边疆”再到“边界”的演化历程,探讨了中外边疆概念的同异和“边缘/边界”(boundaries)、“边疆/前沿”(frontiers)、“国界/边境”(borders)的同异,认为边疆(frontiers)与边界(borders)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产物,代表两种国界边缘(border margins)形态,“frontiers广泛存在于不同的传统国家中,但borders 则是民族国家出现之后的特定产物。前者多与帝国相关,具有常变形、扩张性、非主权性,后者则只存在于民族国家时代,具有稳定性、内敛性、主权性”。(14)王铭铭:《说“边疆”》,《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85页。
李大龙针对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的意见分歧,对“中国边疆”概念的词义来源、历史沿革,官方界定、学界研究和分歧观点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认为“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主要体现在:“政治属性是‘边疆’得以形成的第一要件,或称之为决定性因素;‘主权国家’理论较‘民族国家’理论更适合阐述多民族中国尤其是‘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边疆’是动态的,会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弱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陆疆’和‘海疆’是构成今天‘中国边疆’的两大基本要素;‘边疆’具有地缘优势,既是军事防御的前沿,也是连接两个乃至多个国家的纽带;‘边疆’不能脱离‘疆域’而存在,将其泛化也不利于对‘中国边疆’的研究。”(15)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第12页。
姚大力通过考察“中国”“华夏”“边裔”“边疆”等概念以及中国边疆的形成、边疆地区主要民族的历史,指出中国语境中的“边疆”概念既不同于作为线的边界,也不同于指称濒临边界线的幅员有限的边境,辨别边疆之所以不同于非边疆的特殊性在于民族性和内亚性诸特征,“中国边疆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民族性。基于中国边疆的极大一部分属于内陆亚洲的地理范围这一事实,中国边疆的民族属性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内亚性诸特征”。(16)姚大力:《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第176页。
中外学者所认识的边疆、主权国家的边疆、中国边疆的特征是多种多样的,政治性、区域性、场域性、建构性、动态性、复杂性、矛盾性、民族性、文化性等都是近代以来边疆在不同方面的表现。但是,这些特征都不足以辨别边疆之所以不同于非边疆的特殊性,即不能将主权国家的边疆与其他政治、社会、文化等区域区别开来。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任何自然区域包括内地的自然区域都具有区域性、动态性和矛盾性,任何政治区域包括政治中心区域都具有政治性、场域性和建构性,任何文化区域包括所有少数民族聚集区域都具有民族性、文化性和复杂性。所谓特征,即“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1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35页。事物的本质特征是事物质的规定性,应当是反映事物的根本特点并能够使此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通过认识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人们能够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具的特殊差异或内在规定性。认识这种特征既要分析也要综合,分析是由感性的具体进展到理性的抽象,重在对边疆纷繁复杂的表现进行甄别、比较、筛选,撇开那些外在的、偶然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抽象出内在的、必然的、至关重要的规定;综合则是由理性的抽象进展到思维中的具体,重在理解各种本质特征的丰富内涵和相互关联,从总体上把握具有本质属性和鲜明特征的主权国家边疆概念。
二、临界性:靠近边界并随边界的变化而变化
近代以来,国内外认同度很高的一个“边疆”界定是:“靠近国界的领土”。(1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4页。《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关于“frontier”的第一种解释是:“the land near the line that separates two countries(分离两个国家的界线附近的地带),国界,边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04年,第705-706页。这一界定言简意赅,高度概括了主权国家边疆的依据、实质和表现形态。但是,对于边疆的认识不应满足于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而应关注与边疆直接联系的必要条件和本质方面。诚如恩格斯所言:“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9)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页。
理解主权国家的边疆就得追问何为“国家”“领土”“国界”“靠近国界” 等问题。国家的性质、形态和功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化的。古希腊最早的国家是作为地域概念和相关成员特殊共同体的“城邦”,中国古代的国家是家国同构的王朝国家,近代以来的国家则成为由主权、领土、边界、公民和政府等要素构成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国家是由很多人民组成的社会;永久占有一块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统治;有一个为人民在习惯上所服从的政府”。(20)迦纳:《政府科学与政府》,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0页。主权国家的边疆与当今多种含义上的“国家”具有内在的联系,它是领土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占有和控制的政治地理空间的边缘部分,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nation)主权辖治的一种特殊区域,是政权意义上的国家(state)在多重力量互动过程中建构的产物,“综观近代西方‘边疆’概念的分疏走向,我们将更为清晰地发现‘边疆’概念与所在国家内在结构的某种内在适应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服务于国家整体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21)袁剑:《近代西方“边疆”概念及其阐释路径:以拉策尔、寇松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39页。
领土是主权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行使主权的空间范围,也是在全世界框定主权国家政治地图的空间结构。“领土既是一个‘社会空间’(以民族共同体的形式),也是一个地理划分;或者换句话说,领土用以界定国家在隐喻和字面意义上的历史和记忆、地方和位置”。(22)David Jacobson, “New Frontiers:Territory, Social Spaces, and the State, Sociological Forum,” Mathematics in Thinking about Sociology, Special Issue, Vol.12, No.1, 1997, p.127.领土边疆作为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特殊部分,与所有领土一样归属于一个主权国家,由主权国家所享有、管辖、控制和支配,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等领土的属性,不可侵犯,不可蚕食,不可分割。主权国家的领土是立体的和多维的,边疆也应是立体的和多维的。有学者基于以往的“领土安全”概念已无法概括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某些准主权领域或非主权领域,明确提出将“‘领土’或‘国土’概念修订为‘国域’概念,使其既包括传统主权范围内的国家生存发展空间,也包括非传统主权范围内甚至是非主权范围内的国家生存发展空间,形成覆盖陆域、水域、空域、底域、天域、磁域、网域等七个领域的‘国域观’”。(23)刘跃进、宋希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行政论坛》2018年第4期,第15页。按这种观点理解,当代的边疆既应包括传统主权范围内的领土边疆,如陆疆、海疆和空疆,也应包括非传统主权范围内甚至是非主权范围内的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
国界是划分主权国家领土的边界,也是确定国家统治或管辖的界限。领土边界是国际国家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国家的利益通过边界清晰地界定,世界空间的有限性与国家利益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也通过边界而得以调整。用吉登斯的话来说,主权国家“是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是现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器”。(2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45页。主权国家的边疆与边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边界是划分领土的界线,边疆则是一个国家内靠近边界的领土,“不相交、固定和相互排斥”这种特殊的领土形式是国际政治中现代性最明显的特征。(25)John Ruggie, “Territoriality and Beyond: Problematizing Modern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1, 1993, p.168.其次,边界由毗邻国家共同约定和共同管理,边界的划分、勘界、定界、管理等有大体公认的国际规则和程序,其争端和变化会影响到国与国的战争与和平,边疆则是一个国家根据自身安全、发展和治理战略需要而建构的,其建设、发展和治理属于一国的内政。第三,边界通常被理解为线性的,“边界是在地球表面精确、固定、可以用地图加以标识的无限细的线条”,(26)Kerry Goettlich, “From Frontiers to Borders: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Linear Borde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London, 2019, p.3.边疆通常被理解为区域性的,指的是主权国家靠近边界的区域。
边疆与边界的关系十分复杂,理解主权国家的边疆还应进一步加深对边界的理解。第一,边界与领土不可分。边界是包围国家领土的界限,“边界线只能由此获得,即:国家所掌控的那块区域,在此边缘划出界线。边界的推进以获得国土为前提,边界的后退以国土丧失为前提”。(27)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第135页。第二,边界是建构的。“任何疆域边界本质上都不是‘天定’之物而是人之主体性创造”。(28)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二卷“边疆民族”,第673-674页。哪怕是河流、湖泊、山脉等自然的边界,也都是毗邻国家根据自身的安全、利益、实力和战略需要,经相互约定而使之成为边界的,边界的确认具有条约性质并被国际法认可。第三,边界是动态的。当今边界的内涵、形态和功能正在发生变化,“在社会秩序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不是边界线本身,而是边界的过程”。(29)David Newman, “On Borders and Powe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Borderland Studies, Vol.18, No.1, 2003, p.15.第四,边界的功能是综合的。边界既可成为发挥隔离、阻止和排除功能的屏障,也可成为发挥接触、交流、合作功能的桥梁,还可成为发挥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的显示器、调节器、过滤器。边界如同工具,其如何使用取决于主体的意图和行为。第五,边界是“线”与“面”的统一。边界是“线”还是“面”,理论上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拉策尔巧妙地指出:“这一概念的本质不是线而是位置。”(30)转引自斯蒂芬·巴尔·琼斯:《时空背景下的边界概念》,冯永明译,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第321页。即或把边界视为“想象的界线”,(31)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2分册,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60页。也不意味着边界是一种虚构,因为正是线性边界成为分隔开具有排他性领土的不可或缺的依据和确定国家根本利益为法律上权利的基本法律实存。第六,边界蕴含着诸多矛盾。边界内含着线与面、静与动、隐与显、分离与接触、阻隔与联通、地理与文化、有形与无形等种种对立面的统一。第七,边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边界不仅仅是可以作为自然实体凝固在地图和地图册上的物理的、经验的线条或区域,而且必须被视为多维的社会结构。(32)Anssi Paasi, “Europe as a Social Process and Discourse,”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Vol.8, No.1, 2001, p.22.第八,边界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形态领土边界的划分和表现形式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学者把边界归纳为三类:一是“领土边界”(territorial borders),它划分开不同国家的领土;二是“功能边界”(functional borders),它将政治、社会、法律、科学、经济等不同的功能系统分开;三是“象征性边界”(symbolic borders),它是基于“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区别的集体身份的表达。(33)Bastian Sendhardt, “Borders and Border Regions in Europe: Changes, Challenges and Chances,” Transcript Verlag, 2013,pp.28-29.第九,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模糊性。由于边界的建构性、动态性、矛盾性、多样性,即使是明确界定的领土边界也有模糊的边缘。尤其是,领土边界与功能边界和象征性边界的关系错综复杂,“由于上述三种边界类型的相互作用,边界具有相当‘模糊’的特征,而不是分隔不同(国家)领土的清晰切割线”。(34)Thomas Christiansen, Fabio Petito, and Ben Tonra, “Fuzzy Politics Around Fuzzy Borders: The European Union's ‘Near Abroad’,”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5, No.4, 2000, pp.389-415.
边疆“靠近国界”,主要是指地理空间上濒临边界,但是边疆的“临界性”在更深层的含义上意味着边疆始终随边界的性质、位置、形态和功能等变化而变化。比如,边界的空间方位决定边疆的空间位置;边界的长短决定边疆区域范围的大小;边界的长度与边疆的面积具有可比性;边界的弯曲形状影响边疆的防御强度等;靠近领陆边界的是陆疆,靠近领海边界的是海疆,靠近领空边界的是空疆;发挥屏障功能的边界对应于防御型的边疆,发挥桥梁功能的边界对应于交往型边疆,等等。琼斯谈到:“我关注边界(boundaries)而非边疆(frontiers),但探究这主题的任何人均知道,将这两个术语完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35)斯蒂芬·巴尔·琼斯:《时空背景下的边界概念》,第321页。克罗宁(William Cronon)、迈尔斯(George Miles)和吉特林(Jay Gitlin)等也都强调过程和地点、边界和区域之间的联系,认为边界和区域实际上是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的,并且各自在对方中最好地理解自己。(36)David M. Wrobel, “Beyond the Frontier-Region Dichotom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65, No.3, 1996, p.408.边界既确认了主权国家的领土和权力,也限制了国家在空间上的延伸边际,边疆则成为靠近边界并向本国领土纵深延展的区域,成为在边界内侧面向毗邻国家的区域,成为以边界为中介并随边界的变化而变化的区域,成为国家具有主权的根据自身安全、发展和治理战略需要而建构的区域。虽然靠近边界的区域并非都是边疆,但是边疆必定靠近边界,边疆与边界形影相随;未靠近边界的区域,哪怕是相对于国家政治中心来说非常遥远的异质性区域,也不成其为边疆。所以,临界性是主权国家边疆最典型的、本质的、普遍的特征,认识边疆既要以边界为支点、以领土为归依,更要以临界性为关键,因为它既使边疆在主权国家和世界版图中的位置具有独特性,也使边疆区别于边界,区别于其他区域的领土,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自然区域、政治区域、社会区域和文化区域。
由于不同形态的领土边界差异很大,边疆的临界性特征也表现各异。陆疆与领陆边界在空间上难以严格划分开。“在陆地上虽然竖有碣石界碑,而实际上它仍然像是领海中‘隔开’两个水域的一条基线。它能区分出不同的区域和国界,但却挡不住海风的劲吹,海啸的侵袭,洋流的移动,鱼群的漫游以及一切海洋资源的跨界滋生。因此陆地上的国界也只是意味着表面上的分隔。……国界仅是地球表面上人为制造的一个可见的‘篱笆’,它能够挡住和分隔的只是极为有限的事物”。(37)张之沧:《空间多维:国家疆域的当代拓展》,《江海学刊》2016年第4期,第9页。海疆、空疆、底土边疆范围的确定更是与人类认识的深化、科技进步、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秩序的变化等密切相关。尽管国际上早就形成了关于领海的界定,但是由于领海边界的特殊性和边界划分的重叠性,许多国家对于领海范围的确认一直存在争端。“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相邻或相向的沿海国之间出现了400多条潜在的海洋边界,目前得以划定的仅约160条,海洋划界争端问题不断凸显”。(38)孔令杰:“译者序”, 维克多·普莱斯考特(Victor Prescott.)、吉莉安.D.崔格斯(Gillian Triggs):《国际边疆与边界:法律、政治与地理》,孔令杰、张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2页。关于国家领空的外部界限,国际上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有的主张以主权国家有效控制高度为界限,有的主张以空间的物理属性如空气压力或密度的不同考量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外层空间飞行器不依靠大气可以运行的最低限度来确定,还有的主张选择地球表面上空的某个高度来划分。由于领海边界和领空边界的复杂性,确定一个国家海疆和空疆的具体范围不仅涉及国家主权和领陆,而且涉及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科技进步,牵涉海洋毗邻区、经济专属区、大陆架、航空识别区、外太空等方面的博弈。
更重要的是,边界是动态的社会空间,具有关系性、功能性、规划性、生产性等特征,因而靠近边界的边疆,其意蕴十分复杂。长期以来,对边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物理特征为主的静态的边界上。但是,边界从划分到管理到维护,涉及很多方面的“交叉”。边界的形成是自然、政治、历史、民族、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边界的划定和维护涉及毗邻国家、国际法、地缘政治和多种多样的关系。“国家的政治边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自然地理或诸如族群、语言、宗教、生计方式等其他人文地理性质的边界都犬牙相错而不保持一致”。(39)姚大力:《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第182页。任何一条边界,都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边界如山脉、河流、湖泊、沙漠、沼泽、森林、界桩、铁丝网、哨所、隔离墙等物理特性的边界,无形的边界包括政治、思想、民族、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界线,有形的边界蕴藏着无形的边界,无形的边界通过有形的边界表现出来。在有形的边界确立之后,地面上似乎有了静态的固定的界线,但是作为特殊社会空间的边界和边疆无时无刻不是在变化之中,观念渗透、跨界贸易、民族交流以及边疆人群的生活生产和社会关系等都不会是静止的。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从仅仅把边界视为地理划界,转向了强调边界的变化意义、不同类型的不同功能的边界以及边界的社会结构”。(40)Sendhardt,“Borders and Border Regions in Europe: Changes, Challenges and Chances,” p.25.
从动态的观点来看,边疆的临界性表现为一种“临界”的性质和状态。边界既有地域性和相对稳定性的一面,又有非地域性和流动变化的一面。“由于边界不再被简单视为国家事务,而且处于一种动态过程之中,所以边界不仅存在于领土边缘,而且随着流动人口的移动、边界管理制度的安排而表现为一种弥散形态”。(41)赵萱:《全球流动视野下的民族国家转型——基于海外边界人类学政治路径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117页。冷战后政治格局的变化给各国的领土主权带来了挑战,世界金融市场和资本的流动、全球经济机构和跨国公司的涌现、多国生产和管理网络的形成、跨境交易的自由化和便捷化、跨国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的发展、非传统安全事件的大量增加、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问题的凸显、难民潮在全球的扩散、欧盟国家内部边界的开放等等,都冲击着以主权国家为唯一架构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电信、互联网和网络空间的技术进步也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传统边界的封闭性、阻隔性和界分性,改变着不同类型边界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边疆的临界性出现了“内卷”和“外溢”,越来越明显地从临界的空间位置转向临界的性质和状态。一方面,边疆相关问题从靠近地理边界的领土内卷到国内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任何地方。事实上,在欧洲最经常显示边界的地方,似乎不再是申根区国家内部或外部的地理边界,而是在边界警察的笔记本电脑里,在欧洲相关使馆的签证记录中,在相关机场的安检处,在难民登记中心,在申根信息系统 (SIS) 的网上入口处。(42)Vassilis Tsianos and SerhatKarakayali,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uropean Border Regime: An Ethnographic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13, No.3,2010, pp.373-387.另一方面,边疆相关问题也以各种方式从国内外溢到国际。例如按“移民自主权”的观点,曾经的单一边界装置被重新概念化为竞争和谈判的空间,“由于移民运动的力量和智慧,边界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不断遭遇、紧张、冲突和争论的场所。……移徙是一种共同构成边界的力量,通过每天的过境行动挑战和重塑边界”。(43)Sabine Hess,“Resistance:Subjects, Representations, Contexts,” Transcript Verlag, 2017,pp.89-90.在当代,国家的、民族的、区域的、世界的多重势力的影响相互交织,要求我们以相应的方式来适应不同类型边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转换。哈特向说得好:“对一条国际边界线,恰当的研究主要应该是关注‘联系’(associations),各种各样的联系、边境地区不同部分与他们所接壤国家的联系。……特征相同是一种联系,特征不同但存在共同利益的又是一种。”(44)理查德·哈特向:《上西里西亚的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张凯峰译,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第226-227页。全球化固然并不意味着进入一个“无国界的世界”,但是仅仅关注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和靠近地理边界的边疆是不够的,边疆研究必须以地理空间意义上的领土边界和边疆为重点,但是又应当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关注边界和边疆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趋势。
三、边缘性:不断解构与再造的多维度重叠的边沿或前沿
从氏族部落到城邦国家再到王朝国家,边疆都是远离中央政权统治中心的边缘区域。“只要一个国家足够大,其中就会形成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这种对立会通过与中心的距离以及与毗邻区域的政治、经济、种族边界构成的相互影响而在理想化边界线的两端形成。……一个民族对其边疆如何划分,一开始就有其情况的特殊性,据此使划分更容易进行,并在此后有助于边疆的维系和巩固”。(45)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第135-136页。主权国家的边疆由过去相对于“中心”而言的边缘区域转变为靠近边界的边缘领土,既延续了“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又新增了“边界-边缘”的结构关系,而且后者上升为边疆观中最根本的关系。对任何主权国家来说,边界都是其领土范围的极限,尽管边缘之处未必都是边疆,但是靠近国界的区域必定是边缘性领土,从边疆的临界性可以必然地导出边疆的边缘性。
边疆的边缘性首先表现为边疆是主权国家领土的边缘。边疆是本国领土的边缘,同时也就是面向毗邻国家领土、受到毗邻国家影响的边缘,其治理不同于本国的中心和腹地,在自然、历史、族群、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有其特殊性,表现出自在性、质朴性、脆弱性、敏感性等特征。从与本国的关系来看,边疆与本国的主权、利益、权力核心、内部组织的关系,犹如人的神经末梢与中枢神经和整个身体的关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国家领土的增减、某段边界的伸缩、边疆的发展和治理等,都不只是边疆所在地的事情,而是决定于国家的意志、战略和实力。边疆与国家内部组织、上层集团和核心部门的关系既折射出一个国家内部的种种重要关系,也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和实力盛衰的测度计。从与邻国的关系来看,陆地边界两侧的区域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国家,毗邻国家各自的规模、实力、国体、政体、发展战略、治理方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不仅影响本国边疆,而且影响毗邻国家边疆的功能定位。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复杂的国家同美国、英国等周边主要为海洋所包围的国家相比,其边疆的边缘性特征更为突出和复杂。而且,这些国家边疆特征的强弱与内部力量影响的强弱成反比、与国家外部力量影响的强弱成正比——国家对边疆越重视,内部的影响越强,边疆与国内其他区域的均质化越明显,边疆的特征就越淡化;国家对边疆越不重视,外部力量的影响越大,边疆与国内其他区域的异质化越明显,边疆的特征就越突出。
边疆的边缘性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不只是指地理空间上的边缘。“边缘”概念包含“沿边的部分”“靠近界限的”“同两方面或多方面有关系的”等多种含义。(4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4页。首先,边疆的边缘性往往表现为层叠状态,展现于不同的圈层。在古代,由于距离政治中心的远近、政治控制力的强弱、民族分布和文化认同的差异等多方面的原因,边疆往往表现为多圈层的结构。“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对于关照中国边疆问题有什么助益呢?最起码可以启发我们反思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单层边疆观是不是历来如此。拉铁摩尔的‘双边疆’范式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灵活性,即边疆的‘内’和‘外’具有相对性。一条线就分两个边疆(twofrontiers),边疆的相对性决定边疆往往是成双配对出现的,也就意味着边疆可能不是一层两层,而完全可能是多层”。(47)宋培军:《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内涵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27页。近代以来,边疆从边界向领土纵深延展的范围有近有远,因而边疆既包括小边疆,也包括大边疆,既包括主边疆带,也包括次边疆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边疆的边缘性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观看、被描述、被书写、被塑造的。“边疆不仅因其自然资源、地理空间、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边缘地位而成为边疆,且被来自核心的人们观看、描述,而强化其边缘、边疆性”。(48)王明珂:《建“民族”易,造“国民”难——如何观看与了解边疆》,《文化纵横》2014年第3期,第20页。其次,边疆的边缘性是多维度的。“从清代实行的王朝体制看,古代中国‘边’的文化性至少体现于下列方面:其一,以文野不同而态度有别;其二,规制与实施因地制宜;其三,具体处置因人而异”。(49)桑兵:《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91页。当今的边疆表现在多个维度,从政治看是国家的影响与周边的影响重叠的边缘区域;从经济看是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边缘区域;从社会看是社会发展欠发达的边缘区域;从文化看是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交互作用的边缘区域;从对外开放看是与国外交流合作比较频繁的边缘区域。第三,现代的边缘性意味着被挤压、排斥、抛弃。“现代性制造着差异、排外与边缘化”。(5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边缘性既是与中心相对、也是与重心相对的一个概念,如果不加强边疆地区的发展和治理,边疆地区与中心和重心长期脱节、差距拉大,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现代意义的边缘性。第四,边疆居民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边疆的边缘性。由于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边疆地区的渗透融合,在边疆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活动于斯的特殊群体,即边疆居民。边疆居民与主权国家内部和外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既从边缘看中心,也从里面看外面。边界双方的居民彼此来往,经济利益可能强化政治倾向,也可能弱化政治认同。所以,边疆的边缘性隐藏着边疆居民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摇摆性。历史经验反复表明,边疆地区常常处于“向心”与“离心”的矛盾运动之中,容易成为统一或分裂抑或地缘政治博弈的特殊场域,边缘与中心的关系、族群的凝聚力与国家向心力的关系以及边疆居民的人心背向,历来都是与边疆的巩固和国家的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边疆的边缘性与前沿性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边疆地区一般都是人烟稀少、贫困、偏僻和国家治理相对薄弱的地区,容易成为国家发展和治理的“短板”。中心地区的强度固然非常必要,边疆地区的“短板”效应亦不可忽视。在各国交流日趋频繁的世界格局下,边疆地区往往成为国际经贸和文化交流的要冲之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边缘效能,可以为跨界交流与合作奠定基础,因而一些重要的历史机缘往往存在于靠近边界的边缘。临界之处亦是跨界和超越的前沿,“疆界问题在于超出边界线以外,在于领土外部现象与领土内部出现的过程之间存在的关联。边疆是与外部联系的地方,边疆线是这种接触的地点”。(51)Jean Gottman, La Politique des Etats et leur Geographie, Paris: Librairie Amand Colin, 1952, pp.121-145.转引自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二卷“边疆民族”,第332页。陆地边疆是国家所有区域中离外部世界更近、交往更频繁、联系更密切的区域,既是国家领土的“前端”,也是国家向外辐射的“前沿”;既是国家对外阻隔和防御的前沿,也是国家对外开放和合作的前沿;既是国家统一和民族整合的前沿,也是国家反分裂斗争的前沿。只看到边疆的边缘性而看不到边疆的前沿性是片面的。
边疆的边缘性价值和效能既取决于边疆所归属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能量的积聚以及边疆与内部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边疆对邻国的空间位置和所属国家与周边的关系。哈特向在考察上西里西亚这一边境地区时发现:“对于每个相关国家而言,它在政治上都属于边缘区位,但是由于其位于大陆腹地的矿产资源,又有一定的工业发展、相当数量的人口以及经济、战略价值,这又可以很好地与一个政治中心区位发生联系。”(52)理查德·哈特向:《上西里西亚的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第240页。今天中国的边疆地区,从东北到新疆、西藏,从香港、台湾到南海,无不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前沿阵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的边疆地区已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中外交流合作的桥梁。新疆正成为我国走向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前沿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西藏正成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中的战略桥头堡;云南正从全国交通末梢一跃成为中国走向东南亚、南亚的交通枢纽,和中国与东盟、南亚市场的结合处,也成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重要陆路通道和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前沿。国外一些学者为在理论上适应边界的动态性和模糊性,提出了“去边界/再边界”概念。“去边界”意味着领土边界的越界、可渗透性增加、国家对各种跨境活动的封闭能力下降以及功能性系统边界和领土边界的脱钩,“再边界”意味着边界的重构和再造,如收紧新的边界、加强边境管制、重新实现空间领土化等等,去边界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再边界的过程。(53)Sendhardt,“Borders and Border Regions in Europe : Changes, Challenges and Chances,”pp.29-30.可见,边疆的边缘性研究固然主要应从主权国家的“边界-边缘”结构来考察,从国家靠近边界的边缘性领土来切入,但又应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宽的视野,尽可能把“区域性”“政治性”“民族性”“文化性”和“战略性”结合起来,把边界、边疆等问题与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边疆的边缘性不是静态的、固化的、僵硬不变的,边缘与中心、边缘与重心的关系是辩证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特纳称边疆为“野蛮和文明的交汇处”,(54)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第5页。这种边疆已暗喻着超越有形的地理边疆而衍生出无形的社会边疆的意义。事实上,美国的“边疆”一次又一次地伴随着“文明”的升级而不断解构和再造,始终是在多种对立统一关系中转化的前沿,其边缘性并无绝对的限制。美国沿海一带本是美国大陆的边缘,后来逐渐摆脱大陆性,其人口、工业、服务以及政治力量大幅度增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由边缘转化为中心和重心,形成了一个围绕和支配大陆腹地的环海圈边疆,并使美国新的边界和边疆延伸到了近海区域。美国一直遵循“战略前沿随战略利益而动”的原则,从大陆的边缘走向近海,再从近海迈向深海、公海和太空,其边疆早已超越了领土边界的限制和固定的地域性。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30多位科学家、经济学家、空间工程师和军事战略家合作研究撰写出《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报告,积极为美国拓展太空领域这一战略高地出谋划策,率先提出了以“高边疆”战略为代表的新战略理论。近年来,美国一批智库又提出了“有限太空战”“主动防御”“太空再平衡”等诸多颇具创新性的太空安全战略与理念。美国的边疆研究固然直接服务于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霸权政治,但是其研究的原创性、战略性和对实践活动的指导性,是值得我国的边疆研究批判性借鉴的。
四、交集性:诸多要素、关系和势力在其中相遇、融合、共生
主权国家边疆的临界位置、性质和状态以及边疆多维度重叠的边沿和前沿,使边疆成为国家之间影响互动和实力较量的场域。边疆还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内含着国家与民族、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内部与外部、传统与现代、隔离与交往、流动与稳定、靠界与跨界、向心与离心、有形与无形、同质与异构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具有明显区别于国家其他区域的杂多性、混合性、自我组织性和自我调节性,等等。边缘效应是生态学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两个和多个不同生物地理群落的交界处往往结构复杂,出现不同生态环境的种类共生,种群密度变化较大,某些物种特别活跃,生产力相应较高的状况。(55)Pingyu Zha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Shenyang City,” Chines Geographical Science, Vol.13, No.3, 2003, pp.216-223.这种边缘效应在人类社会也普遍存在。边疆犹如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复杂政治、民族、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挑战的一种缩影,不同要素、关系和势力在其中相遇、抗衡、融汇、共生和共存,呈现出相互交织、渗透、互构、蚁合、嵌套等交集性特征。拉铁摩尔在关于中国边疆的分析中,常常就以辩证的方式阐述边疆的交集性。他在谈到亚洲内陆边疆社会历史的动荡性时,深刻阐述了进化与退化、动荡与稳定、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多元自然环境与持久混合社会、畜牧经济与农耕经济、集中原则与分散原则、个人与集体、兴盛与衰退、统治部落与从属部落、血缘关系与自由选择等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汇聚在边疆这一场域之中。(56)欧文·拉铁摩尔:《亚洲内陆边疆:防御帝国与征服帝国》,牛昢昢译,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第388-389页。
边疆的交集性使其凸显为人类社会少有的矛盾汇聚的场域。边疆两侧跨越边界的相互影响就像大海总会冲击岸边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相互渗透尤为突出,一些热点问题也常常在边疆被放大。边疆是周边多方面影响叠加的区域,与周边环境、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紧密关联,涉及区域性乃至国际性的复杂问题,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毗邻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都会使边疆的意义、价值和功能相应发生变化。拉策尔精彩描述了富于交集性特征的“边疆风格”:“边疆与其所环绕空间中的任一点都有着关联,而且它们一般越近越强烈,在那里它们导致了一种特殊的边疆风格,并向远方递减。但是,就像环状的边缘从其每个点出发与同样距离之外的中心有着一种密切的发生学的、机械性的关系那样,它也被归为政治中心,尽管这些地点与边缘利益相距甚远,就像其他任何不直接位于边疆的地点一样。人们可以说:只有在边疆才存在这样的地点,它对于整个政治中心有着同样的意义。”(57)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第134页。边疆居民为适应边疆环境而创造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和精神追求,在历史过程中逐渐沉淀为特定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又将处于其中的人们凝聚成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因而边疆地区在国家认同、政治认知、政治信任、政治感情、政治参与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度等政治文化方面,与国家的中心和腹地存在显明的差异。如果从毗邻国家接壤的区域而不是仅从一个国家单边来看,通过跨越边界的人群、货物与观念的流动,可以加速经济生产模式的重构、社会结构的转变和文化的传播与融合,边界两侧的区域可以成为毗邻国家合作、发展、共治的特殊区域。所以,对边疆的研究既要关注理性主义的领土国家理论,把边疆与所归属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毗邻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对边疆的治理方略联系起来理解,又要关注建构主义的边界、边疆和领土理论,尽可能把边界及其两侧的区域联系起来考察。
边疆的交集性呈现为一种过渡性状态。所谓“过渡”,也就是既是这、也是那,既不是这、也不是那的状态。A与B“交集”,即A与B混杂黏合、渗透融合,其结果是既非A也非B、既包含A的要素也包含B的要素的C。拉铁摩尔在阐述中国的边疆过渡地带时就指出,其过渡性表现为地理环境的过渡、不同族群居住地的交错、族群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多元文化交互融合等,也表现为“接触与退缩、征服与反征服、坚持与妥协的过渡地带”。“混合文化是草原与中国之间的桥梁,两方由此相互影响。但是这两个世界的联系,似乎只是在桥的中间,而在两个桥头上,它们依然还是两个不同的世界”。(58)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50、376页。借用复杂性科学术语,边疆呈现为一种个体简单而整体复杂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整体性、动态演化性、网络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等特点的复杂系统。随着国际社会互动的日益频繁和复杂,主权国家边疆的过渡性更重要地表现在政治、利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过渡,跨越边界的流动深刻地塑造着边疆的空间形态与内外关系,出现了超越国家领土的区域合作和区域治理趋势,“使经济、文化和国家安全的边界延伸到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之外,与领土边疆形成张力与交错的格局,促使边疆概念从有形到无形、从清晰到模糊、从排他性到交错性,从线型结构向网状结构的转化”。(59)何明:《探索多元化时代的多元边疆理论与实践》,方铁:《边疆民族史新探》,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5页。
边疆的交集性、过渡性也表现为一种缓冲性。边疆地区是毗邻国家由边界向两侧延展的缓冲带,依照毗邻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边界为中介的两侧区域既可以成为军事对抗和地缘政治博弈的角斗场,也可能成为彼此交流和相互合作共治空间。寇松曾通过对古今边界、边疆的同异、演变和作用的考察,包括从“防御屏障”到“经济关卡”、从“中间地带”到“边区”、从“缓冲带”到“保留地”、从“中立地带”到“缓冲国”再到“势力范围”的考察,论证了边界和边疆最重要的作用是利益的协调、强权的缓冲和冲突的阻隔。他认为,近代以来边疆演变为边界,但是边界及相关防御与扩张方略仍然延续了古代边疆的核心价值和作用:“古代的、中世纪的中间带或者说隔离带,正是现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设立的中立区、中立国或者中立地带的鼻祖。它们的目的相同,即,将两个发生接触时可能引发冲突的强权隔开,只是具体做法有异。”(60)乔治·纳撒尼尔·寇松:《论疆界》,第171-172页。
边疆的交集性使其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有机性。边疆既表现为内部各要素和各方面的关联与互动以及两个或多个领土单元之间相互影响和嵌套的区域,又表现出在国家整体空间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陆地边疆是一个内含着复杂关系和诸多矛盾而又能够有序运行的一个系统,在行政区划和运行上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其区情特征是:市场边缘、交通末梢、开放末端、人才洼地、社会发育度低、文化异质多元、地缘环境敏感复杂、自然生态脆弱易损等。现代国家治理中,边疆发挥着拱卫国家安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构筑生态屏障、滋养中华文化、发展周边公共外交等重要作用”。(61)方盛举、陈然:《现代国家治理视角下的边疆:内涵、特征与地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22页。这一切,对边疆地区尤其是靠近边界的边境县(市、区、旗)级政权机构及其领导干部的政治立场、政策水平和治理能力,包括边境政策法规知识、政治鉴别能力、边境维稳能力、跨境管理能力、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依法行政能力、民间外交能力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五、认识边疆本质特征的意义
“特征”是一个反映人们的认识活动已达到相当深度的概念。“从‘特征’的内容看,它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对特定事物所特有的那些现象的简化、抽象和界说;所以,特征与现象和本质有密切联系,又区别于现象和本质,是一个在认识发展过程中必然地出现的有‘自己的’领域和意义的概念,是一个在人们的认识之网上占有独特地位的‘网上纽结’”。(62)茅生荣:《论“特征”》,《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60页。事物的本质特征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或内在规定性,这种特征较之于其他特征更为深刻、稳定和典型,能够较为准确地理解事物的一般概念。
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与主权国家的边疆具有必然联系,每一特征都反映出边疆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又都包含着许多具体的特征。它们交织在一起,凸显出边疆区别于非边疆的显著标志,对于揭示边疆的本质起着决定性作用。“边疆之所以称其为边疆,恰恰就在其具有独特的魅力。这种特征、这种魅力、这种风情,正如拉策尔所言是往往被学者们所疏于敏锐捕捉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边疆学的构筑才显得理直气壮”。(63)张世明:“导言”,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经典文献》,第171-175页。在边疆研究中,从认识具体边疆的特征到认识一般边疆的特征和本质特征再到揭示一般边疆概念的本质的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生动直观到抽象思维的过程,也是从感性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再到“思维中的具体”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在经验事实、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的基础上按照一定逻辑结构规则来建构系统化知识的过程,也是用边疆学理论来解说经验事实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
认识边疆的本质,一方面需要撇开其外在的、偶然的、无关紧要的要素和关系,把边疆的本质特征从纷繁复杂的具体表现和关系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需要综合把握这些本质特征的内在联系,从总体上理解边疆的本质。通过边疆本质特征的辨析我们认识到,主权国家的边疆在较严格的意义上指靠近边界的边缘性领土;在较宽泛的意义上指复杂矛盾关系所形成的国家主权、利益、能力所及的边缘性场域。无论是“边缘性领土”还是“边缘性场域”,边疆都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有形的物理空间。从哲学视角看,边疆观念源于“我”与“他者”的区别意识。只有“我”自觉了,才可能有“我”与“他者”的区别意识以及亲与疏、近与远、中与边、内与外的关系意识,也才会有边疆意识。国家从不成熟到成熟,犹如从童蒙未开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其鲜明特点就是出现了“我”与“他者”相互区别的意识。边疆意味着一种双向关系,仅仅从单方面看,地理上的“边”、民族上的“夷”、文化上的“生”、政权控制上的“弱”都不成其为边疆,只是在“我”与“他者”的交汇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汇处、主流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汇处、有效控制与失效控制的交汇处,才构成了边疆。比如中国古代的边疆,“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渗透着农业和草原势力的世界,一个两种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64)唐晓峰:《长城内外是故乡》,《读书》1998年第4期,第126页。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边疆是“我”与“他者”既相互区别、冲突、对抗又相互影响、互动、互构的一种场域、关系或过程,犹如“城乡结合部”,犹如两条不同颜色的河流交汇而形成的第三种颜色的水域,对立面在这里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我”与“他者”交汇的过程,既包括政治、军事上的遭遇、对抗和影响过程,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也包括民族、文化、社会、国际关系互动和互构的过程。抓住了“交汇处”这一特殊规定性,也就抓住了一般边疆概念的核心意蕴。“古今中外,边疆所内含的各种矛盾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正是其生命和活力之所在。如果没有对立统一以及复杂矛盾之间的相互制约、影响、依赖和作用,边疆的活力也就消失了,边疆的生命也就终止了”。(65)罗中枢:《论边疆的特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49页。考察各种边疆形态和拉策尔、特纳、拉铁摩尔等众多著名边疆研究专家所理解的边疆概念不难发现,贯穿其中并使各种边疆形态和边疆概念勾连融通的,正是“我”与“他者”的面向、遭遇及其引申而来的“对立面的统一”。赵敏求在拉铁摩尔《中国的边疆》中译本引言中所界说的“边疆”,就是包含了这一核心意蕴的边疆:“所谓‘边疆’,是两个不相等形式的文化,互相接触,因而产生相互的影响,造成许多行动及反动,形成特殊的势力,并从其中发展出新的观点来。”(66)赖德茂(Owen Lattimore):《中国的边疆》,赵敏求译,南京:正中书局,1941年,“引言”第1页。曹聚仁在20世纪70年代所认同的“现代的边疆观念”,(67)曹聚仁:《曹聚仁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530页。也是这样一种以辩证的方式所表达的边疆观念。
主权国家的边疆是政治、社会、地缘、文化等要素和关系交汇互动的一个特殊场域,也是由陆疆、海疆、空疆、底土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交织而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它一方面具有客观实在性和相对于主体而言的独立性,其地理状况、自然条件、空间方位、规模结构、资源构成等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又打上了人的精神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烙印,尤其是受到国家的性质和形态、国体和政体以及制度安排、资源配置、政策导向、外部关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作为“交汇处”的边疆,从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看是个体、局部关系不可预测而整体演变规则可以把握的一个复杂系统。杰克·D·福布斯(Jack D. Forbes)说得好:“在其最狭窄和最不含糊的用法中,边疆指的是边界线或边境地区——两个团体互相对抗的地方。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边疆’一词已被修正和扩展到不仅指物理的边境,而且指与未知事物的相当模糊的斗争(如‘知识的边疆’):但即使在这里,人们通常也可以用‘边境’一词来代替(如‘知识的边境’)。从根本上讲,‘边疆’这个概念是指两股力量相互对抗的交汇点,无论它们是人类群体,还是文明与荒野或知识与潜在知识等模糊的事物。应该强调的是,如果没有至少两个实体的交汇或相互抗衡(简而言之,一种接触状态),就不可能有任何边疆。”(68)Jack D. Forbes, “Frontier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Role of the Frontier Historian,”Ethnohistory, Vol.15, No.2, 1968, p.206.
认识边疆的本质特征有助于促进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建构。世界各国由于自然地理、文明体系、政治制度传统、工业化程度等不同,其边界、边疆、疆域的发展演变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和特殊性。所以,边疆研究应当将哲学思辨与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结合起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在借鉴国内外边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识边疆的共性、本质属性及其特征,进而明晰边疆学的对象、性质、范围、功能、特点和在学科领域中所占的逻辑地位,提炼出边疆学的范畴和原理,建构起边疆学的理论体系。根据复杂性科学的研究,社会性昆虫(蜜蜂、蚂蚁、白蚁等)在个体的层次上以高度的概率性行为为特征,其活动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在整个群体的规模上却可以建立起作为特定社会特征的相关模式。(69)G.尼科里斯(G.Nicolis)、I.普利高津(I.Prigogine):《探索复杂性》,罗久里、陈奎宁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60页。同样,边疆由个体、局部和具体关系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立体的网状的场域,尽管其个体活动不可预测,但是其基本特征是可以概括的,其一般原理是可以发现的,其共通现象是可以解释的,其演变趋势是可以预测的。
所有的科学都只是整体的一部分,边疆学与其他科学的研究领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政治学、政治地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军事学等科学都涉及边疆研究,但都只是研究边疆的某些侧面。历史学关注疆域的演变,地理学关注边疆的地理变迁,民族学关注边疆民族的活动,政治学关注边界争端的管控和边疆的治理,社会学关注边疆地区的社会现象,法学关注边疆安全、发展和治理的立法和执法,经济学关注边境贸易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军事学关注边境防卫、管理和边防建设,等等。多侧面的边疆研究固然十分重要和必要,但是缺乏对一般边疆的整体、本质及其特征的研究,难以建构起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的边疆学是关于边疆的认识活动过程和认识活动成果的统一,它把边疆作为完整的对象,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综合研究,横切过诸多科学而成为关于边疆研究的交叉科学和综合科学。为避免边疆学“涂上了其他科学的色彩而没有发展它自己的独立特征”,(70)借用哈特向以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Ritter. Carl)的观点来阐述地理学的性质的话语(原文见Allgemeine Erdkunde, Berlin, 1862.),转引自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黎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8页。就需要在深入探讨边疆的本质属性及其特征和边疆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方面狠下功夫,高度关注边疆形成和发展中的各种要素及其互动、互构关系,高度关注边疆所内含的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高度关注边疆的本质和特征在不同情景中的变化,高度关注边疆在时空压缩、时空重组和时空延展中的变化,高度关注不同形态边疆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高度关注边疆地区的人群及其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要高度关注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而变化的国家活动方式、国家安全边界和国家利益重心。只有这样,边疆研究才会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充满生机和活力。
认识边疆的本质特征有助于更加有效地推进边疆安全、发展和治理。近年来,中国边疆安全、发展与治理的形势严峻,边界冲突与纠纷时有发生,“疆独”“藏独”等分裂破坏活动威胁边疆稳定,“台独”和“港独”势力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边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日益迫切,周边局势和国际敌对势力对边疆的影响无时不在,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已经凸显,走私、贩毒、洗钱、跨境赌博、人口非法流动、极端民族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边疆地区远比在其他地区更为严重。此外,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还存在海域和岛屿争议,在大陆架、海洋权益、深海、极地、外太空、网络空间等方面的竞争和博弈也日益加剧。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动力、出发点和归宿点,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为实践服务。另一方面,理论对实践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指导作用和促进作用。主权国家边疆本质特征的研究及其在此基础上关于边疆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探讨,对于边疆安全、发展和治理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比如,边疆的临界性告诉我们,边界的性质、形态和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因而靠近边界的边疆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情形,尤其是海疆、空疆、底土边疆范围的确定与人类认识的深化、科技进步和国际秩序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边疆研究不仅要关注传统边疆问题和主权、领土等问题,而且要关注边疆与边界及周边的关系、陆地边界争端管控、边境安全、边界两侧的区域比较、跨境经济合作问题,关注边界与近海、远洋和极地的问题,包括国家领海战略和政策、边海防方略、海域争端管控和解决、海洋权益的保障和拓展以及极地权益、极地政策和人类共同遗产等国际法原则对领土和边界的影响,等等。这一切,都迫切需要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积极推进多学科、跨学科的集成研究,努力把对边疆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以更加有效地推进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和边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