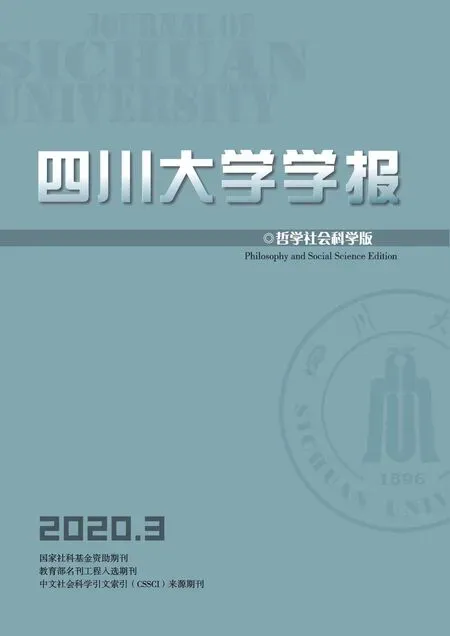“黑人权力”运动之社区济贫:黑豹党“生存计划”探析
巩大松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黑人青年休伊·牛顿(Huey P. Newton)、鲍比·希尔(Bobby Seale)和埃尔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等人所领导的黑豹党,(1)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 Party),1966年10月成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最初自称为“黑豹自卫党”(Black Panther Party for Self-Defense),1968年底改称黑豹党。牛顿任黑豹党武装部长,实为头号领袖;希尔任黑豹党主席,是为名义领袖;克里弗曾任黑豹党宣传部长。通过积极倡导黑人激进民族主义并寻求主流媒体的关注,迅速崛起为“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2)关于“黑人权力”运动国内已有部分研究,参见谢国荣:《19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第40-52页;梅祖蓉:《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公民权运动中的极端主义》,《世界民族》2014年第3期,第71-82页;巩大松、谢国荣:《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黑豹党的武装自卫及其影响》,《求是学刊》2018年第5期,第142-154页。国外相关研究参见Jeffrey O. G. Obar, Black Power: Radical Politics and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eniel E. Joseph, Waiting 'Til the Midnight Hou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2006; Richard Wright, Black Power: Three Books from Exile: Black Power, The Color Curtain, and White Man, Liste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0.的主力军。黑豹党在黑人社区携枪巡逻以遏制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是其成立初期常态化的“黑人权力”斗争手段。黑豹党人统一身着黑色皮衣、黑色贝雷帽、黑色眼镜,高举枪支与美国警察对峙的画面,也构成了媒体和大众对黑豹党的基本印象。(3)Obar, Black Power, p.118.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黑豹党开始在黑人社区推行名为“生存计划”(Survival Programs)的系列济贫项目,包括向黑人学童提供免费早餐、向黑人贫民免费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等。社区济贫日益取代武装自卫成为黑豹党开展“黑人权力”运动的主要形式。那么,以激进言行闻名的黑豹党为何会转向社区济贫?黑豹党又是如何将社区济贫与“黑人权力”有机结合起来,动员黑人大众参与的?济贫斗争对黑豹党本身及其领导的“黑人权力”运动意味着什么,对美国黑人社区和主流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目前美国学界关于黑豹党所倡导的“黑人权力”运动研究多聚焦于黑豹党的武装自卫策略,(4)Joe Street,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44, No.2, 2010, pp.351-375.关于其济贫斗争的研究还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5)关于黑豹党济贫斗争的整体研究,参见Daniel Crowe, Prophets of Rage: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in San Francisco, 1945-1969,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Paul Alkebulan, Survival Pending R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7. 关于黑豹党济贫斗争中某一具体项目的研究,参见Susan Levine, School Lunch Politics: The Surprising History of America's Favorite Welfare Progra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Nik Heynen, “Bending the Bars of Empire from Every Ghetto for Survival: The Black Panther Party's Radical Antihunger Polit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Scal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99, No.2, 2009, pp.406-422; Alondra Nelson, Body and Soul: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and the Fight against Medical Discrimi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一些黑豹党成员的回忆录成为学界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但他们往往夸大黑豹党社区济贫的具体成效;(6)David Hilliard, e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Service to the People Program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08.一些美国学者对黑豹党由武装自卫转向济贫斗争的起源分析往往过于强调现实压力的驱动,忽视黑豹党意识形态变迁的影响,(7)Crowe, Prophets of Rage, p.222.更未能有力阐释社区济贫与“黑人权力”精神内涵和运动属性演变之间的关系。(8)一些学者仍将黑豹党的济贫斗争视为其激进政治诉求的沿袭或微调,参见Curtis J. 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Violence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2006, pp.262-266; Obar, Black Power, pp.90-91. 另一些学者则在是否将之界定为革命或改革运动的问题上游移不定,参见Alkebulan, Survival Pending Revolution, pp.127-132.国内学界对黑豹党社区济贫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仅个别学者有所探讨。(9)于展:《美国民权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全球史评论》第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4-168页;黄逸云:《试析黑人力量运动的源泉:黑豹党及其社区基层组织行动》,《台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52-55页。笔者以为,黑豹党的济贫斗争在与黑人社区的互动中革新、拓展了“黑人权力”的精神内涵和表现形式,赋予“黑人权力”运动明显的社会改革运动属性,对黑豹党、美国黑人社区和主流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依据黑豹党档案材料,(10)本文所用的黑豹党档案文献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录、1967—1980年间黑豹党所发行的报纸文献——《黑豹》(Black Panther)。Black Panther又被称为The Black Panther Newspaper、The Black Panther Community News Service,最初发行于1967年春,大致每两周一期,是黑豹党向黑人社区提供新闻、开展政治教育以及对外宣传的刊物。并参考相关研究,揭示黑豹党开展社区济贫的社会背景、自身考量、宣传实践以及社会影响,进一步探讨美国“黑人权力”运动的本质和影响。
一、美国都市黑人贫民的生存困境和联邦济贫的不足
20世纪50-60年代,由于产业调整升级、人口再分布和白人种族主义等因素,美国西部和北部都市黑人贫困现象加剧,下层黑人的生存状况更趋恶化。当时,美国西部、北部都市正进行急剧的产业转移或调整。以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为例,二战期间美国西海岸的工业化吸引了大量的南部黑人移民奥克兰,战后其黑人人口比例已经接近白人,但该市一度繁荣的军火产业随着战争结束走向衰退。“去工业化”和白人的种族歧视给蜂拥而至的黑人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就业、住房、教育问题。当地一半的黑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形成了新的贫民窟。(11)Donna Jean Murch, Living for the City: Migration,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in Oakland, Califor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10, pp.3-10.美国传统都市如芝加哥、纽约则更多因产业升级(特别是自动化生产)造成黑人类似的生存困境。与此相伴生的是都市白人加速向郊区迁移,白人的郊区化带走了内城(inner city)的经济资源和税收收入,使传统慈善组织和市政当局无力开展相应的济贫事业以应对黑人生存困境。(12)Andrew Wiese, Places of Their Own: African American Suburba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183-209.此外,地方政府在济贫对策上也存在偏差,没有直面黑人贫困问题本身。如旧金山市当局认为黑人青少年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参与违法犯罪,因此将济贫重点放在建立青少年矫正机构上。(13)Murch, Living for the City, pp.13-17.
在这种情况下,1964年林登·约翰逊政府出台的“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的联邦政策似乎给都市下层黑人带来了新的生存希望。但一方面,美国逐渐深度卷入越战,极大消耗了联邦本应用来解决国内贫困问题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向贫困宣战”的运行机制也存在脱离黑人民众的问题。联邦政府曾试图采取社区本位的济贫原则,即根据社区贫民切实需要创设联邦济贫议程、分配联邦济贫资源的“社区行动计划”(Community Action Programs)。但约翰逊政府顾忌黑人民权组织趁机掌控基层民众,极力避免将联邦济贫与民权运动结合起来,“社区行动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向市政机构和传统济贫力量妥协,使后者实际掌控济贫对策的主导权和济贫资源的分配权,因而未能真正满足黑人贫民需要。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等民权组织在此背景下开展的济贫斗争,就没有得到约翰逊政府的信任和支援,在都市下层黑人青年动员上也缺乏影响力。(14)Crowe, Prophets of Rage, pp.159-168.
而无论是传统市政济贫、社会济贫,还是联邦济贫,对黑人受众普遍存在种族歧视问题,并漠视黑人抗争。譬如,1964年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当局出台的救济政策以只资助农业领域劳工为名完全绕开了黑人失业者,并压制当地黑人民权组织的抗争。再如,1965年,美国农业部与社会慈善团体共同发起的“学校午餐项目”以及1966年联邦《儿童营养法》(ChildrenNutritionAct)支持的“学校早餐项目”曾使数十万贫困学童享受到免费早(午)餐,但受益者基本为白人儿童。一些黑人民权组织屡次抗议却没有效果。(15)Crowe, Prophets of Rage, p.226.“新左派”运动典型代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组织也曾响应“向贫困宣战”,支援北方都市黑人贫民应对失业、教育等难题,却见证了联邦和地方体制抵制济贫的顽固性。(16)吕庆广:《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反叛与修复机制——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57-58页。因此,无论是以废除南部种族隔离和保障黑人政治权利为核心的联邦民权改革还是“向贫困宣战”,都没有给西部、北部都市黑人的困境带来即时和实质性的改善。在黑人贫民看来,他们成了社会的“弃儿”,部分人被迫从事卖淫、赌博、吸毒、街头暴力等非法活动和“地下经济”,许多黑人陷入迷茫甚至绝望状态。
这些黑人极易在激进思潮影响和敏感事件(特别是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刺激下发生集体性的骚乱,造成巨大社会破坏。当时,国际上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步入高潮。在美国国内,以马尔科姆·X为代表的黑人激进民族主义(17)关于马尔科姆激进思想对当时美国黑人社会的影响,参见Obar, Black Power, pp.45-55.和国际左翼革命思潮在黑人大众中迅速传播,引发黑人对“黑人革命”(Black Revolution)的讨论和想象。(18)Joshua Bloom and Waldo E. Martin, Black against Empire: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p.2-3.国内外激进思想的泛滥,使深陷生存困境的城市黑人往往通过骚乱发泄不满情绪。根据约翰逊总统设立的调查骚乱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的报告,仅1967年前9个月,美国各大中城市就发生了164起骚乱。该委员会认为,种族主义氛围下的黑人贫困问题、白人警察暴力执法以及媒体的偏颇报道是引发黑人骚乱的主要原因。(19)United States Riot Commission, 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8, pp.9-11,362-367.
社会济贫和联邦济贫的不足,特别是其中暴露的种族歧视问题,迫使各派黑人民权团体探索新的济贫斗争方式来解决黑人生存困境,进而遏制黑人骚乱的爆发。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温和派民权组织率先做出回应。1967年8月,在全美发生新一轮都市骚乱后,金做了题为《美国的都市危机》的报告。他提出,与其让贫困、暴力等问题引起黑人无组织、无目标更无意义的大骚乱,不如以“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形式将黑人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建设性博弈手段来应对城市中的“饥饿政治”。金后来又批评约翰逊的越战政策将导致“向贫困宣战”的彻底失败,他号召“全国各地的千百万穷人涌上华盛顿街头,让联邦政府看到民众贫困的真相”。这种主张最终演变为1968年春季的“穷人大进军”(The Poor People's Campaign),数千名支持者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建起帐篷营地坚持抗争,试图迫使国会通过新的系统性经济民权法案。(20)Gordon Keith Mantler, Power to the Poor: Black-Brown Coalition and the Fight for Economic Justice, 1960-197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Books, 2013, pp.92, 4-5.然而这次大规模示威却招致保守政客和媒体的强烈批判,未能达成相应的立法目标。(21)Gerald McKnight, The Last Crusade: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FBI, and the Poor People's Campaig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pp.13-20.温和派民权组织依托体制内的立法和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解决黑人贫困问题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
与此同时,激进派民权力量开始借用新兴的“黑人权力”话语,重新思考黑人贫困问题的对策,并尝试践行社区本位的济贫道路。1966年夏,时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22)该组织曾是温和派民权斗争的重要推动者,但在南部种族主义刺激下日益激进,卡迈克尔担任领导人后进而提出“黑人权力”。参见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主席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正式提出了“黑人权力”概念。他认为,美国存在着顽固的“体制性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 racism),从根本上阻碍了黑人获取实质性社会权力与资源,而这并非民权改革和民权立法所能解决;他主张黑人应放弃与白人自由派以及联邦政府的合作,团结起来依靠自身力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进行权力斗争,掌控黑人社区。(23)Stokely Carmichael and Charles V. Hamilton, Black Power: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pp.4-10,37-43.“黑人权力”所蕴含的黑人自主斗争、事务自决精神,昭示黑人民权组织不再完全寄希望于政府或社会济贫,而是尝试自主开展济贫事业来解决下层黑人生存问题。一些曾参与联邦济贫项目的激进黑人青年,如牛顿和希尔,也从“社区行动计划”中获得了济贫斗争的经验和教训,(24)Crowe, Prophets of Rage, p.223.将“黑人权力”诉求与社区本位的济贫原则结合起来,帮助黑人应对贫困。
二、黑豹党“生存计划”的提出
“黑人权力”运动兴起后,应运而生的黑豹党以“武装自卫、社区自治”的激进言行成为这场运动“弄潮儿”。黑豹党创始人牛顿和希尔均成长于奥克兰及其所属的加州海湾地区,对于都市黑人贫民遭遇的“体制性种族主义”深有体会,因此积极响应卡迈克尔所倡导的“黑人权力”斗争。(25)黑豹党的名称和标识完全沿袭了卡迈克尔在阿拉巴马州帮助创设的黑人武装自卫组织。参见Huey P. Newton, Revolutionary Suicide, New York: Harcout, 1973, pp.112-113. 黑豹党还一度将卡迈克尔奉为精神导师和荣誉总理(Primer)。参见The Black Panther, June 20, 1967, p.7.两人提出的以武装自卫为基本手段、以黑人社区自治为目标的具有党纲性质的“十点纲领”(Ten-point Platform),(26)黑豹党党纲包括:实现黑人社区自决、充分就业、体面住房、平等教育、公正司法待遇、反对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反对白人剥削黑人社区以及释放一切黑人犯人等。参见The Black Panther, July 3, 1967, p.3.将“黑人权力”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现象。当时,白人警察频频在黑人社区暴力执法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司法惩处,经常成为骚乱的直接导火索。但黑豹党的武装自卫不单指涉携枪自卫以应对警察暴力执法,更是糅合了其激进的政治理想与都市黑人贫民的现实需要,构成其“黑人权力”斗争的突出标识。
一方面,黑豹党在宣传中借鉴国内外激进思潮对种族暴力和种族压迫体制的批判话语,以武装自卫理论建构“黑人权力”的精神内涵。当时知名的反殖民主义理论家弗朗茨·法农认为,殖民者对暴力的垄断和压迫性统治,会使受压迫者人格异化,政治和文化意识萎缩,他进而提出“暴力革命”才能“净化”这种社会“病态”。(27)Frantz Fanon,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p.4-18.马尔科姆批判种族暴力是种族主义体制的化身,提出“以暴制暴”和“黑人自治”的解决方案,并将黑人暴力自卫作为恢复黑人受损的尊严,特别是男子气概,激发黑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关键所在。(28)参见于展:《马尔科姆·X的早期思想轨迹》,《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第68-72页;王恩铭:《马尔科姆·爱克斯与“黑人力量”》,《世界民族》2011年第5期,第81-91页。民权运动激进派先驱罗伯特·威廉姆斯流亡古巴等地后,宣扬黑人携枪斗争的“革命气质”最有利于黑人摆脱深重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29)参见于展:《美国民权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全球史评论》第7辑,第146-161页。这些激进思潮构成黑豹党以“革命之名”动员黑人携枪自卫进行“黑人权力”斗争的丰富语境资源。黑豹党借此将黑人携枪斗争与健全黑人人格、提升黑人种族自豪感、建构黑人新形象密切联系起来。譬如,在报纸宣传中,黑豹党借用流行的反殖话语将都市贫民窟称为美国的“国内殖民地”,不受监督的警察是国内的“种族主义殖民军”,(30)The Black Panther, July 3, 1967, pp.3, 7; July 20, 1967, p.11.将黑人携枪应对警察种族暴力视为“种族解放”的正义斗争。而黑豹党在公开活动中的准军事形象——统一身着黑色皮衣、黑色贝雷帽、黑色眼镜,高举枪支列队行进,则直接回应了激进黑人对强力反抗种族暴力的“黑人男子气概”和“革命气质”的想象。
另一方面,黑豹党在实践中将武装自卫演绎为美国都市黑人贫民的独特政治博弈手段,赋予其在“黑人权力”斗争中为都市黑人争取实质性社会权利和资源的政治功能。起初,黑豹党利用加州等地法律允许公民和组织携带枪支公开活动的规定,对进入黑人社区的白人警察展开常态化武装巡逻(“Police the police”),以遏制警察暴力执法。(31)Bloom and Martin, Black against Empire, pp.45-47.接着,当一些州议会试图通过控枪法案限制本地黑豹党等激进组织的公开携枪活动时,黑豹党组织若干成员在州议会大厦前携枪示威,制造轰动性的媒体事件,(32)例如,1967年5月2日,加州议会准备审议通过一项禁止加州公民在公共场所携带上膛枪支的法案,大约30名黑豹党人(其中一些人带着枪支)出现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议会大厦门前抗议,后遭逮捕。借机控诉警察暴力执法问题。黑豹党还利用其成员因携枪等激进言行遭到非法逮捕、监禁或人身侵害,批判美国司法体制中的种族歧视现象,要求确保黑人言论和集会自由、设立黑人陪审团、增加黑人法官和黑人警察比例、释放被捕黑人“政治犯”等。(33)Bloom and Martin, Black against Empire, pp.104-110.这种激进但合法的“黑人权力”斗争方式,在保障黑人人权、维护黑人社区安定、争取司法公正等焦点民权事务中开辟了不依赖白人自由派和联邦政府的合作,谋求黑人自主斗争、事务自决的新途径。在密集的媒体曝光下,武装自卫等激进言行满足了贫民窟黑人对抗种族暴力及种族主义压迫的客观民权诉求和激进“革命”想象,提升了黑人的尊严和种族认同,促使黑豹党迅速兴起。(34)1968年底,黑豹党已拥有数千成员,在美国各大中城市建立了数十个支部,《黑豹》的发行量也达到每期25万份。参见Molefi K. Asante and Ama Mazama, eds., Encyclopedia of Black Studies, Thousand Oaks, C.A.: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5, pp.135-137.
黑豹党的武装自卫也招致主流媒体的污名化和当局的压制,对自身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严重障碍。主流媒体将黑豹党塑造为“犯罪分子”,(35)Jane Rhodes, Framing the Black Panthers: The Spectacular Rise of a Black Power Ic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p.77.使大部分美国民众对黑豹党产生疑惧感。与此同时,以联邦调查局为代表的美国各政府机构也开始对黑豹党进行重点压制。(36)Kenneth O'Reilly, Racial Matters: The FBI's Secret File on Black America, 1960-1972,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pp.287-320.随着一些州议会和联邦国会出台了限制公民公开携枪和限制青少年携枪条款在内的控枪法案,(37)参见巩大松、谢国荣:《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黑豹党的武装自卫及其影响》,《求是学刊》2018年第5期,第150-152页。黑豹党的有组织武装自卫也逐渐丧失了合法性。黑豹党的主要领导人纷纷卷入各种刑事案件,被迫入狱或流亡国外;(38)1967年底牛顿卷入奥克兰警官谋杀案,被判杀人罪而入狱;1968年底,克里弗卷入袭警案,流亡古巴、阿尔及利亚;1970年,希尔也被控谋杀了一位所谓被联邦调查局收买的黑豹党纽黑文支部成员而短暂入狱。而参与携枪行动的普通黑豹党员也经常被警方以各种罪名逮捕,仅保释金开支就令黑豹党捉襟见肘。(39)黑豹党当时经常在《黑豹》上刊登成员被捕的消息,以向社会募集保释金。参见The Black Panther, May 15, 1967, p.7; July 20, 1967, p.7.黑豹党认为美国当局正采取特工渗透、直接谋杀、煽动黑人激进组织间冲突等各种“法西斯”手段,竭力摧毁黑豹党,(40)Huey P. Newton, War against the Panthers: A Study of Repression in America, New York: 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 1996, pp.43-51.他们认识到,“虽然部分黑人社区声援黑豹党,呼喊着‘黑人权力’,但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冒险与当局发生暴力冲突”。(41)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 p.106.显然,单纯以武装自卫应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激进做法并不能动员大部分黑人参与“黑人权力”运动。日益严酷的现实压力迫使黑豹党必须降低激进姿态,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但黑豹党“黑人权力”斗争的济贫转向并不只是向现实妥协的结果,它更反映了黑豹党内意识形态和“黑人权力”观的转变。黑豹党最初的意识形态底色更接近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其后逐渐加入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色彩。牛顿和希尔早年就习读了国际左翼运动思想著作,尤为钦佩毛泽东、切·格瓦拉等第三世界革命运动领导人。(42)Obar, Black Power, p.84.当时流行的《毛泽东语录》(“Little Red Book”)成为黑豹党人几乎人手一本、每日集中研读的“革命教育”读本。(43)Alkebulan, Survival Pending Revolution, pp.38-39.1963、1968年毛泽东两次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主义激进斗争的公开声明,(44)于展:《美国民权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全球史评论》2016年第7辑,第147-149页。更启迪黑豹党以阶级斗争思维重新思考美国的种族问题。黑豹党认为,黑人与白人贫民大众、反战人士、“新左派”知识分子、各少数族裔都是美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的受害者,其中黑人受到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最为深重。(45)The Black Panther, May 18, 1968, pp.11, 25.黑豹党将贫民窟黑人称作“失业的无产者”(lumpen proletariat),(46)Kai T. Erikson, In Search of Common Ground: Conversation with Erik H. Erikson & Huey P. Newt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3, p.45.视其为未来革命的主力军。(47)Bobby Seale, Seize the Time: The Story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and Huey P. Newt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p.4.黑豹党的日常言行呈现左翼化倾向。
黑豹党意识形态的左翼化促使黑豹党的“黑人权力”观发生重要转变,开始将社区济贫作为开展“黑人权力”斗争的新战场。黑豹党积极研习国际左翼运动思想以促进自身组织建设,尤其注重加强与黑人民众联系,从而为“黑人权力”运动争取更广泛的社会基础。黑豹党在兴起过程中吸收了包括大量黑人失业青年、街头帮派人员、黑人大中学生等在内的各色新成员,他们当众酗酒、滥用武力、思想混乱,再加上联邦特工渗透等问题,日益引起黑豹党高层警觉。(48)The Black Panther, January 4, 1969, p.14.对此,黑豹党领导人通过效仿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开展政治和纪律教育来提升黑豹党组织形象和凝聚力。(49)“三大纪律”(3 main rules of discipline)、“八项注意”(8 points of attention)等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纪律条令也被完整纳入黑豹党新设立的党纪规章中。参见The Black Panther, January 4, 1969, p.20.黑豹党尤为赞赏中国共产党服务人民大众的宗旨(50)1968年起,《黑豹》宣传中经常出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Serve the People Body and Soul)、“所有权力属于人民”(All Power to the People)之类口号。参见The Black Panther, September 14, 1968, p.3;April 10, 1971, p.11.和根据群众迫切需要灵活开展工作的斗争策略,并自诩为美国黑人的“革命先锋”(The Vanguard Party)。但牛顿等人逐渐认识到,“武装自卫并不适用于每一种场合,而黑人的生存困境却无处不在”,应根据“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调整斗争策略,满足大众的真正利益需求”。牛顿认为,“美国的种族主义体制和当局的法西斯主义行径造成黑人的种种生存困境,制造着‘种族大屠杀’(Genocide),……黑人大众甚至看不到明天或革命到来,我们想要改变这一切;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生存下去”。(51)Toni Morrison, ed., To Die for the People: The Writings of Huey P. Newt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p.44-53, 20-22.因此,黑豹党试图以“生存计划”发动一场迫在眉睫的“生存革命”(Survival Pending Revolution),争取黑人大众对“黑人权力”运动的支持。
在这种语境下,黑豹党领导层纷纷强调开展社区济贫对于维护黑人社区生存,进而推动“黑人权力”斗争的意义。希尔声称,“黑豹党生存的核心原则在于相信人民,并取得人民信赖”,“当黑人社区无法生存,黑豹党定然无法生存”。(52)The Black Panther, April 6, 1969, p.14.他将开展社区济贫、加强与黑人社区的联系视为黑豹党立身之本,势在必行。希尔还认为,“社区济贫行动能够培养黑人勤勉工作的精神品德,促进黑人自立自强,使黑人感受到‘黑人权力’魅力进而加入组织”。(53)Seale, Seize the Time, pp.35-44.克里弗也曾表示,“当黑豹党人为黑人学童提供食物而频频出现在黑人大众眼前时,后者将感受到黑豹党人的勇气和能力”。(54)Quoted from 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 p.260.他强调将“黑人权力”用于社区济贫能够提升黑豹党人的社区形象和大众号召力。
黑豹党主要理论家牛顿则提出了“社区交联”(Intercommunalism)思想,进一步发掘社区济贫的政治价值,为“生存计划”的具体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牛顿认为,当代(第三)世界因帝国主义压迫和渗透,实质上并不存在享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而是由一个个低于民族国家政治阶位的社区(Community)组成的,如北越和美国黑人贫民窟。他预言,未来的“世界革命”将是在各社区内部完成整合并互相援助的基础上,推翻人类史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压迫,汇聚众社区而实现共产主义(Communalism)的过程。牛顿提出,诸社区间整合程度取决于其社区机构对基层民众的(权力斗争)意识启蒙与动员能力。而美国黑人贫民窟不仅面临种族主义体制压迫,还受到国内产业升级浪潮的冲击。因此,黑人只有建立服务于自身的社区机构,实现黑人各项事务自决才能应对各种挑战。(55)Morrison, ed., To Die for the People, pp.28-43.这种由自治的社区而不是独立的民族国家导向“世界革命”的理论,虽颇为自负,但其社区本位倾向使黑豹党人觉得在美国黑人贫民窟开展自由斗争,具有不亚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战争的“革命”意义。这将为他们专注于服务、建设黑人社区提供新的信念和动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开始强调健全黑人社区机构、提高黑人社区整合能力是美国黑人有效参与种族政治博弈的关键,突出了社区济贫在“黑人权力”斗争中的非凡意义。牛顿认为,以往贫民窟黑人的民权斗争无法动摇种族主义体制的根源在于贫民窟各类社区机构的缺失,特别是缺乏“社区政治工具”来培养一种“社区精神”(community spirit)对抗这种压迫。(56)Morrison, ed., To Die for the People, pp.66-67.这表明黑豹党的社区济贫并非简单的慈善之举,而是希望借此有效动员黑人大众建立健全社区机构,实现黑人事务自决。为此,牛顿重新阐释了黑豹党的“自卫”理念,认为它不仅指涉黑人应携枪捍卫人身安全,更蕴含以社区济贫满足黑人大众的生存需要、捍卫黑人社区生存之意,声称这种“自卫”才能启蒙并动员黑人大众。牛顿还辩称,黑豹党一直以来的宗旨即是“为黑人大众提供生存服务,使之免受压迫”,这可以得到黑豹党“一以贯之”的党纲佐证。(57)The Black Panther, April 17, 1971, p.1.显然,宽泛关注都市黑人面临的一系列民权问题的黑豹党党纲不能等同于更具体、更有执行力的“生存计划”。但以牛顿为代表的主流黑豹党人将“黑人权力”斗争重点从黑人政治与安全领域转向经济和社会事务,将社区济贫而不是武装自卫视为有效整合黑人社区、推动“黑人权力”运动的主要手段,是毋庸置疑的。
三、黑豹党“生存计划”的宣传与实践
下面笔者将以“生存计划”中的“儿童免费早餐”(The Free Breakfast for Children Program)、“免费健康诊所”(Free Health Clinics)、“自由学校”(Liberation Schools)三大主要济贫项目的运营概况为例,阐释黑豹党社区济贫的宣传与实践机制以及“社区交联”理论在其中的具体运用。
(一)儿童免费早餐项目
美国黑人贫困家庭的学童经常饿着肚子上学,黑豹党声称,尽管无法做到使“每个黑人家庭都有只鸡吃”,但至少可以“给每个饥饿的黑人学童送上一份早餐”,随后推出儿童免费早餐项目。(58)The Black Panther, December 21, 1968, p.15.黑豹党希望该项目能够使儿童和黑人大众意识到,免于饥饿是基本人权,当联邦政府或社会不能保障时,黑人应依靠社区组织实现自救(self-help)。黑豹党希望把儿童免费早餐项目打造成将“黑人权力”与社区济贫结合起来的范例。早在1968年9月,黑豹党便在奥克兰地区首先试行了该项目;1969年起,逐渐将该项目推广至全国数十个支部。(59)Heynen, “Bending the Bars of Empire from Every Ghetto for Survival,” pp.411, 406-408.黑豹党人通常在清晨小学生上学前,在社区教堂等地向当地黑人儿童免费发放加热的牛奶、鸡蛋、面包、香肠等食品。每个发放场所除了厨师、餐桌服务人员外,还安排了交通引导员护送儿童安全往返街道,甚至还有专员帮助学童检查作业、纠正穿衣。(60)Hilliard, e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p.30-32.
为动员黑人社区各阶层积极参与该项目,黑豹党在宣传中竭力渲染黑人学童饥饿问题的危害,号召黑人社区各尽其责共同应对。黑豹党批判黑人的饥饿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剥削造成的,是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体现,而政府却毫无作为。(61)The Black Panther, March 3, 1969, p.11.他们认为饥饿不仅影响黑人学童的学习能力,也关系到其未来的成长,可能使贫困黑人孩子输在起点上,最终无法摆脱贫困。(62)Quoted from 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 p.260.黑豹党通过《黑豹》向黑人大众呼吁:“在充满压迫而没有关怀的当下,我们怎么能对孩子们饿着肚子听课熟视无睹?”希望有能力的家庭能够提供食物,并号召黑人妇女充当志愿服务人员。(63)The Black Panther, January 4, 1969, p.16.实际上,黑人商户的捐献是早餐食物的主要来源,为争取他们的支持,黑豹党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宣传手法。黑豹党称赞黑人实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黑人社区自治能力,鼓励黑人商户建立独立的商业社团对抗白人资本家的经济盘剥和种族歧视行为。(64)Morrison, ed., To Die for the People, pp.109-111.黑豹党还声称要为那些积极捐献、富有社区责任感的黑人商户免费在《黑豹》上投放广告,并曝光那些不愿捐献、只顾私利的商户,使之受到整个黑人社区的抵制。(65)The Black Panther, May 11, 1969, p.8.为争取当地教会提供活动场地并代为宣传,黑豹党在公开演讲中声明要搁置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肯定教会在缓解黑人受压迫之苦、凝聚社区人心方面的贡献,表示愿与教会合作,共同对抗饥饿这种“社区之恶”。(66)Morrison, ed., To Die for the People, pp.60-62.黑豹党还宣称,儿童免费早餐项目能使志愿者和捐献者切实感受到“社区精神”,并使孩子感受到超越家庭的“社区之爱”,(67)Hilliard, e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34.进一步以社区共同体话语感召黑人大众。
(二)免费健康诊所项目
美国贫民窟的底层黑人非常容易罹患疾病,特别是传染病,而私立医疗机构价格过于昂贵,公立医院又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黑豹党认为健康生活是黑人贫民也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批判美国医疗健康体系“只是增强阶级统治的工具”,要求“医疗应基于民众福祉而非利益”。(68)Alkebulan, Survival Pending Revolution, p.36.黑豹党认为,“免费诊所展现了黑人事务自决的力量,也使医生因医疗费用问题疏离黑人下层民众的局面不再出现”。(69)The Black Panther, October 18, 1969, p.3.因此,黑豹党推出免费健康诊所项目。免费诊所通常开设于具有不少于一层闲置空间的居民大楼内,以分置候诊室、治疗室、实验室、器械室等必要的医疗功能单元。诊疗团队通常由三名以上职业医生、若干名医学实习护理和技术人员组成。所有团队人员均属志愿、无偿服务,每周抽出时间轮流工作,所有医疗设施和器械也来自社会捐赠。这些诊所向黑人提供了常见病筛查、初步诊疗服务并向社区发布医疗健康信息,以满足黑人最基本的医疗需要。(70)Hilliard, e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p.21-23.
黑豹党在开展该项目时尤其重视对镰状细胞性贫血(Sickle-Cell Anemia)的防治。当时,该病是黑人贫民中最严重的遗传疾病之一。黑豹党反复向黑人群众科普该病的防治措施,并批判当局对该病防治的漠视是“坐视黑人贫民病亡,变相制造‘种族大屠杀’”。(71)The Black Panther, April 10, 1971, p.10; April 1, 1972, p.6.为应对这一疾病的威胁,黑豹党设立了镰状细胞性贫血研究基金会,以支持对该病的学术研究,并在全国各免费诊所对前来就诊的黑人贫民进行免费筛查和诊治。(72)Hilliard, e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p.24-26.
(三)自由学校项目
美国黑人受教育水平远低于白人等族群,且贫困学童辍学现象普遍。(73)Crowe, Prophets of Rage, pp.175-179, 152.不仅如此,黑豹党认为黑人儿童所接受的有限的公立学校教育也存在严重问题,导致黑人不能适应产业升级的时代要求而逐渐陷入生存困境。1969年起,黑豹党决心开展自主教育事业,向黑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而有效的教育。1971年设立的奥克兰社区学校(Oakland Community School)是该项目的典型代表。该学校向2岁半至11岁的学生提供系统的初级教育,既开设了数学、语言、科学等应用性课程,以培养黑人迫切需要的“生存”技能;还开设了美国黑人历史文化课程,教授黑人自由斗争的历史,以培养黑人对自身社区的认同。(74)Hilliard, e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p.5-7.该学校的另一个特色是按照学童的实际认知能力而非生理年龄划分班级,如11岁的学童可能上着二年级的英语和五年级的科学课。学校对所谓体制内“不堪教育”的学童也予以收纳,耐心教导。入学的孩子们有免费校车接送,还可以享受免费餐饮和定期体检。(75)Elaine Brown, A Taste of Power: A Black Woman's Sto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2, pp.391-393.
值得注意的是,黑豹党的社区济贫并不只是针对黑人。儿童免费早餐项目也不排斥邻近社区的白人贫困儿童,特别是墨西哥裔儿童。(76)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 p.260.黑豹党还声称,“黑豹党人会平等对待每一位患者,不论其种族或出身”,一些白人贫民因此享受到了“免费诊所”服务。奥克兰社区学校也招收毗邻的墨西哥裔学童,并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进行双语教学。同时黑豹党开设的诊所还根据实际需要,招募白人志愿者。比如,鉴于黑人医护人员的严重短缺,黑豹党向当地医院白人医生群体求助。黑豹党赞扬这些医生富有同情心,是履行救死扶伤、服务民众天职的“革命”医生。(77)The Black Panther, February 7, 1976, p.4; September 29, 1975, p.4; August 2, 1969, p.4; p.3.一些白人医护人员不仅积极响应,还对作为助手的女性黑豹党人进行了基本医疗服务培训。(78)David Hilliard and Lewis Cole, This Side of Glory: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Hilliard and the Story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Boston: Little Brown, 1993, p.259.黑豹党还与当地墨西哥裔劳工组织联合抵制歧视少数族裔劳工和黑人贫民的白人企业,迫使后者做出改善。(79)Lauren Araiza, “In Common Struggle against a Common Oppression: The United Farm Workers an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1968-1973,” 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Vol.94, No.2, 2009, pp.200-223.黑豹党试图通过这种跨种族、跨社区交往拓展济贫资源,同时扩大黑豹党的影响力。
综上可见,黑豹党的社区济贫宣传与实践充斥着对美国种族主义体制和当局的尖刻批判,通过渲染黑人社区的“生存危机”,试图提高黑人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支持社区济贫。黑豹党通过这种社区共同体话语的宣传与实践,使“黑人权力”呈现了明显的社区化特征。这意味着黑豹党的“黑人权力”斗争视阈从社区之上(州、联邦、第三世界等)回归到社区,从热衷于以激进言行制造媒体事件转到关注黑人具体民生问题。这种社区化倾向既受到了黑豹党以社区为本位的“社区交联”理论的影响,更是在与黑人社区的互动实践中形成的。一方面,黑豹党的“社区交联”理论本身就契合了美国都市黑人和其他族群的社区化存在特征。它虽然声称要以社区为基本单位推进新的“世界革命”,但实际更像是一种为动员激进黑人投身社区改革的“革命化”宣传。不可否认,随着其意识形态的左翼化,黑豹党继续在国内外制造了一些激进事件,如参与反越战运动、(80)The Black Panther, September 14, 1968, p.10.派人出访北越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非洲多国等,(81)Bloom and Martin, Black against Empire, pp.309-322.但新兴非洲国家依然受到帝国主义干涉与渗透的现实使牛顿清醒认识到即使黑人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也无法享有独立主权和经济、文化自主。加之中美关系走向缓和、(82)1971年9月,牛顿在尼克松访华之前访问了中国大陆,但未如愿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参见Newton, Revolutionary Suicide, pp.349-351.美军逐步撤出越南等国际因素都促使牛顿实质上彻底放弃发动“革命”,转而专注于黑人社区建设,不过宣传上仍然保持着借用体制外激进话语的惯性。
另一方面,“黑人权力”的社区化,也继承并发扬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基层化或草根(grassroot)斗争传统,是黑人社区民众积极参与、塑造的结果。新近的美国民权运动研究发现,除了知名民权领袖及主流民权组织领导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国会游说等,更多的民权斗争是由地方草根组织或基层民权人士发起的,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创设民权议程。(83)于展:《美国民权运动研究述评》,《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122-132页。从黑豹党社区济贫的动员策略和议程设置来看,它沿袭了这一传统,但将服务对象转移至以往民权斗争所忽视的都市贫民窟黑人,并加入更为激进的动员话语。事实上,黑豹党不仅实施了上述服务项目,还根据黑人社区群众的其他要求,不断拓展“生存计划”的具体内容。譬如,根据大批入狱黑人家属来信反映没有经济能力探监的情况,黑豹党开办了免费探监巴士项目。(84)The Black Panther, September 5, 1970, p.9.针对黑人贫民反映衣物短缺的情况,黑豹党在社区开设了鞋厂、制衣厂,免费向黑人贫民发放鞋子和衣服。(85)Hilliard, e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pp.61-68.黑豹党的一些南方支部还应邀开展了反对毒品的斗争,以遏制毒品在黑人社区的扩散。(86)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 pp.252-255.这些新设立的济贫项目显然超出了黑豹党高层最初的规划,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基层黑人贫民对社区济贫的参与,最终形成多达60项内容的“生存计划”。(87)“Black Panther Party Community Programs (1966-1982),” https:∥web.stanford.edu/group/blackpanthers/programs.shtml, May 22, 2019.
四、“生存计划”的社会影响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黑豹党以社区济贫形式开展的“黑人权力”斗争,丰富了“黑人权力”的精神内涵,黑豹党与黑人社区以及整个美国社会的关系也因之出现了诸多微妙而重要的转变。
第一,黑豹党的济贫斗争顺应了当时民权斗争重心转向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趋势。虽然黑豹党的党纲涵盖了都市黑人就业、教育等经济和社会权利问题,但在早期实践中,黑豹党偏执于应对直接引发黑人骚乱的种族暴力,而未能直面其根源——经济、社会权利和资源缺失下的黑人贫困。黑豹党以武装自卫等激进活动对抗美国司法体制中的种族不公和政治压迫,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黑人权力”的精神内涵和动员对象。而社区济贫这种相对缓和的斗争形式,不仅弱化了“黑人权力”的激进性和大男子主义色彩,更适应了都市黑人对经济、社会权利和资源的渴求,以及在主流女权运动刺激下黑人女性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客观需要。大量黑人妇女得以投身“黑人权力”斗争,积极创设新的济贫项目,日益成为黑豹党社区济贫的主力。(88)Robyn C. Spencer, The Revolution Has Come: Black Power, Gender, an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in Oaklan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90-98.社区济贫使“黑人权力”与黑人的女权诉求、生存诉求形成某种共振,从而极大拓展了“黑人权力”的精神内涵。“黑人权力”不再呈现为专属于黑人男性青年的武装自卫,而演变为黑人社区各群体皆可参与、皆能受惠的社区赋权运动。
2)在课上,学生利用平台开展课程的自主学习,并且完成平台上相关的学习测验。在课程测验结束后系统会根据教师的设置布置有关本次课堂的探究任务,指引学生在课堂开展探究型学习,包含学法指导、学习评价等内容,立足学生的角度,以帮助学生解决问题、突破面向对象的概念、类与对象等重难点为重心,促进知识的内化。学生围绕教师设计的教学活动,在课上展示课前作品、进行成果汇报、针对课前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与教师和同学面对面地讨论、探究,在这过程中开展多元化的学习评价。[5]
第二,黑豹党的济贫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黑人贫民大众的生存困境,促进了黑人社区认同,也赢得了自身发展的社区环境。就社区济贫的直接效果而言,“儿童免费早餐”项目收效最为显著。1969年,仅在黑豹党旧金山支部某一处场地每天即有两百多名儿童就餐;(89)Crowe, Prophets of Rage, pp.175-179, 224.而遍布全美的数百处项目场地,每天供应上万名儿童的早餐。(90)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 p.262;Levine, School Lunch Politics, p.139.另一说为“每天免费供应两万名儿童早餐”,参见Bloom and Martin, Black against Empire, p.184.黑豹党的“免费诊所”项目也使黑人大众受益匪浅。据称,1969年黑豹党在芝加哥“免费诊所”项目推行头两个月内就接诊了超过2万民众,黑豹党对镰状细胞性贫血的普查人数更是超过百万。(91)Alkebulan, Survival Pending Revolution, p.36.黑豹党的“自由学校”项目整体效果难以评价,但奥克兰社区学校深受学生家长欢迎,该校招生规模从最初十多名学生逐渐扩大到一百五十多名。(92)The Black Panther, September 29, 1975, p.4.其教学质量更受到加州教育部门的称赞,被誉为奥克兰内城初级教育的示范学校。(93)Alkebulan, Survival Pending Revolution, p.35.社区济贫对黑人社区整合的间接效果亦不容忽视。在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忽视黑人贫民生存困境的情况下,黑豹党主张黑人同白人一样拥有免于饥饿、维持健康、接受教育等基本人权的吁求,获得黑人社区的广泛共鸣。黑人教会提供济贫场所并为之募捐,黑人中产阶级贡献了实物和捐款,黑人青年承担基层动员与具体服务职能,共同形成社区自主济贫机制进而造就了上述济贫成效。诸多社区互助行动及其体现的“社区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黑人社区中贫民与中产阶级、激进派与温和派、下层病人与当地医生、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修复着持续骚乱对黑人社区的撕裂与破坏,重塑了黑人的社区认同。在黑人贫民眼中,这些济贫事业不仅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物资援助,还提升了他们的种族团结、尊严和权力意识。(94)The Black Panther, September 13, 1969, p.19.许多黑人青年认为黑豹党这种“黑人权力”斗争真正给黑人社区带来了福音,因而加入黑豹党。(95)Crowe, Prophets of Rage, pp.175-179, 224-225.
第三,社区济贫不仅提供了修复黑人社区内部裂痕的契机,也局部修正了主流社会对于“黑人权力”的片面和负面认知。当时,卡迈克尔所领导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将白人成员开除,伊斯兰民族协会(Nation of Islam)宣扬黑人种族神话和“黑人穆斯林”思想,美利坚黑人合众国组织(US Organization)强调美国黑人应在语言风俗与审美文化上全面“非洲化”。(96)伊斯兰民族协会是当时比较活跃的黑人宗教民族主义组织,主张基督教为种族压迫工具,黑人应信仰伊斯兰教。参见Obar, Black Power, pp.11-35. 美利坚黑人合众国是当时典型的黑人文化民族主义组织,致力于建构美国黑人的非洲文化认同。参见Scott Brown, Fighting for US: Maulana Karenga, the US Organization, and Black Cultural Nation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2003.这些典型黑人激进组织的自我隔离做法和“黑人权力”所具有的黑人自治激进诉求,使主流媒体宣称“黑人权力”等同于“黑人种族主义”。“黑人权力”激进派对非暴力民权斗争的批判,特别是黑豹党的武装自卫言行,更使“黑人权力”被媒体渲染为具有宣扬“暴力”倾向。(97)Peniel E. Joseph,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A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96, No.3, 2009, pp.751-756.而黑豹党在济贫斗争中展现的跨种族、跨社区友善交往和互助姿态,特别是其维护贫民生存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冲击了主流媒体对“黑人权力”的污名化,争取了黑人社区以外的支持力量。一些白人文化名流和慈善组织还对黑豹党施以道义和资金援助。(98)例如,1970年美国著名钢琴大师莱昂纳多·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在其纽约家中邀聚一批社会名流为黑豹党募捐,引发媒体热议。参见Tom Wolfe, Radical Chic & Mau-Mauing the Flak Catch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0.
第四,黑豹党在济贫宣传中对美国政府忽视黑人生存人权的猛烈批判,以及黑豹党可观的济贫实践成效,更迫使联邦政府对黑人的一些经济和福利诉求做出回应。黑豹党组织部长大卫·希利亚德(David Hilliard)声称,约翰逊政府所实施的“学校早(午)餐项目”正是受到黑豹党儿童免费早餐项目的启迪。(99)Hilliard and Cole, This Side of Glory, p.14.如前文所述,这显然有悖于事实,但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国会在1975年通过决议将《儿童营养法》和“学校早餐项目”长期化并覆盖黑人社区之举,是受到黑豹党“儿童免费早餐项目”的成功推行所带来压力的结果。(100)Heynen, “Bending the Bars of Empire from Every Ghetto for Survival,” p.411.希利亚德还声称黑豹党对镰状细胞性贫血严重危害黑人健康的成功宣传使尼克松两度在国会演说中提及该疾病的防治问题,镰状细胞性贫血研究基金会也受到了社会大量资助。(101)Hilliard and Cole, This Side of Glory, p.339.一些美国学者也持此论。(102)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 p.265; Alkebulan, Survival Pending Revolution, p.36.笔者以为,已有研究结论多直接转述黑豹党当事人回忆录,并存在不小的个体描述偏差,不宜高估黑豹党在上述事件中的直接影响。美国福利体制做出的某些种族平等化调整,同样离不开温和派民权组织发起的“穷人大进军”,以及同期全美福利权利组织(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等(103)该组织存在于1966—1975年,成员曾达两万多人,并以黑人女性为主,为妇女和儿童争取福利权益是其斗争重点。参见Guida West, The National Welfare Rights Movement: The Social Protest of Poor Women, New York: Praeger, 1981, pp.3-11.发起的为弱势群体争取福利斗争的影响。美国民权学者威廉姆·范·德博格提出,“黑人权力”组织的激进斗争会创造一种“体制危机”,迫使当局更青睐温和派民权组织所提供之方案。(104)William Von Deburg, New Day in Babylon: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and American Culture, 1965-197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306.或许黑豹党社区济贫在其中的真正影响亦在于此,它使得在尼克松上台后民权改革退潮的保守政治情势下,黑人大众的饥饿和健康问题仍然能够得到当局的某些立法和行政举措回应。黑豹党的人权批判话语和济贫斗争最终转化为美国体制内对黑人部分经济和福利权利的赋予与保障。
总之,相对于携枪斗争方式,黑豹党的社区济贫显然在黑人社区内外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影响力。在美国国内,黑豹党在济贫斗争中开辟的依靠种族团结自主开展民权斗争、实现事务自决的种族政治博弈方式,对其他少数族裔投身类似的改革运动也具有重要启迪意义。(105)Joseph, Waiting 'Til the Midnight Hour, p.xiv.在国际上,有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也注意到仅仅赋予黑人公民政治权利在满足后者生存和发展需要上的局限性,也开始模仿黑豹党的“生存计划”开展济贫事业。(106)The Black Panther, April 1, 1972, pp.1, 2.因此,在主流媒体对黑豹党的济贫事业关注度不高(相对于携枪斗争)的情况下,黑豹党依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继续发展壮大。
但黑豹党的济贫斗争也面临难以克服的众多内外问题,最终走向了终结。首先,黑豹党的社区济贫转向加剧了黑豹党的内部冲突,甚至引发了黑豹党大分裂。以克里弗为代表的黑豹党内极端左翼,轻视社区济贫而推崇武装自卫,并试图将之引申为直接的革命手段,以“城市游击战”形式发动革命。(107)Bloom and Martin, Black against Empire, pp.318-321; 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 pp.115-116.在牛顿入狱后,克里弗等极端派更是失去掣肘,沉迷于挑衅当局的激进言行。(108)克里弗将携枪行动发展为暴力袭警等犯罪活动,还应邀在北越河内发表了煽动美国士兵叛乱的演说。参见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 pp.102-104.1970年牛顿出狱后,批判这类激进言行使黑豹党“背离”了黑人社区实际需要,实是一种“反革命”。牛顿强调,“真正的革命先锋必须提高民众权力意识,使他们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并通过合适的方式改造社会”。(109)Morrison, ed., To Die for the People, pp.44-53, 101-103.而克里弗一派也批评牛顿的济贫斗争背弃了“革命”,转变为修正主义和改革主义,使黑豹党变成了一般性社区济贫组织。(110)Austin, Up against the Wall, pp.298-304.两派冲突不断加剧,导致1971年的公开决裂,这给黑豹党带来重创。1972年起,牛顿为确保对黑豹党的控制力,要求黑豹党人放弃各支部汇聚于奥克兰总部,黑豹党逐渐沦为地方组织,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迅速下降,走向衰落。
其次,黑豹党的济贫斗争转向也未能完全改变美国主流媒体对其污名化的倾向,亦未彻底缓和其与当局的矛盾。除了少数“革命派”黑豹党人一贯奉行的体制外激进言行外,主流“改革派”黑豹党人也习惯借用左翼激进话语实施济贫动员,并继续与当局发生暴力冲突,这为黑豹党的社区济贫带来巨大的体制阻力。(111)Ryan J. Kirkb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Community Activism an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1966-1971,”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Vol.41, No.1, 2011, pp.25-62.主流媒体依然聚焦于黑豹党与警察的冲突等激进事件,在关于黑豹党济贫项目的有限报道中,也往往将之渲染为“社会主义”宣传,视之为黑豹党蛊惑下层民众进行“革命暴动”的手段。(112)Rhodes, Framing the Black Panthers, pp.252-257.美国当局对黑豹党的敌视和压制政策也没有减轻。联邦调查局认为,黑豹党在借济贫活动攻击美国政府和体制的不足,在发放救济的同时进行煽动宣传。(113)Bloom and Martin, Black against Empire, p.186.联邦特工和各地警方对黑豹党的救济项目频频进行骚扰、破坏。比如,联邦特工和洛杉矶警察以搜查嫌犯为名,闯入黑豹党免费早餐发放处,捣毁食物,殴打工作人员。伯克利当局则试图分化当地教会与黑豹党间的关系,使之拒绝提供济贫场地。黑豹党的镰状细胞性贫血筛查工作也受到类似的干扰与破坏。(114)The Black Panther, January 19, 1974, p.8; September 13, 1969, pp.6, 19.
五、结 语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黑豹党针对美国政府和社会救济体制的不足,特别是对黑人贫民的忽视,开展了涵盖黑人社区各民生领域的济贫事业。黑豹党从强调武装自卫到开展济贫斗争,最初是借鉴国际左翼政党经验加强社会基础以抗衡当局的压制,推进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黑人权力”运动。而“社区交联”理论的提出和运用,表明牛顿并不是要盲从国内外激进思潮发动“黑人革命”。黑豹党以社区利益为本的济贫宣传与实践,促使“黑人权力”出现社区化倾向;黑人社区各阶层力量的加入也使“黑人权力”斗争更加关注黑人社区层面的议题,并确立了这一趋势。在与黑人社区的互动中,黑豹党进一步摆脱了激进意识形态的束缚,其“黑人权力”斗争在实践中发生“去革命”的变迁,不再热衷于以激进言行制造媒体事件,而是切实解决黑人日常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加之黑豹党在济贫斗争中表现出的跨种族、跨社区友善交往和互助姿态,淡化了“黑人权力”的激进性和理想化色彩,使之更易为社会认可。在此过程中,黑人社区开始形成社区互助的自主济贫机制,其内部认同与凝聚力也得到增强,黑豹党的“黑人权力”运动也由此具备了明显的社会改革运动属性。
但黑豹党因长期坚持武装自卫等激进言行招致当局的持续压制和主流媒体的污名化,当其意识到社区服务和建设对于黑人民权事业的重要意义时,已丧失了可以继续“生存”的社会环境。黑豹党的社区济贫始终伴随混乱的激进意识形态宣传、与当局的暴力冲突等杂音,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内外障碍,因而未能继续开展下去。然而正如牛顿所称,“生存计划”并不是解决黑人贫困问题的长久之计,也不是终极方案。它的真正目的在于批判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对黑人贫民关注的不足,使后者“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职责,并尽可能地修正自身”。(119)Morrison, ed., To Die for the People, p.68.在骚乱持续发生而黑人失业及贫困问题成为民权斗争新阶段核心命题的情况下,争取黑人经济、社会权利成为温和派与激进派民权领袖的共识。马丁·路德·金致力于通过体制内的立法和行政改革直接为黑人社区谋求联邦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援助,而牛顿则诉诸黑人自主济贫,并以黑人社区自治的激进姿态间接迫使联邦政府和主流社会关注黑人的生存困境。两种解决方案其实“殊途同归”:各以其擅长的种族政治博弈方式谋求改变美国权力体制中种族主义和非民主的一面,改善黑人族群的政治生态。因此,民权运动与“黑人权力”运动既有区别更有联系,它们共同揭示了,解决黑人的贫困问题既需要黑人自立自强,也需要主流社会的必要援助以及政府的积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