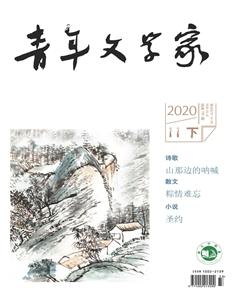村上春树对现代性的反抗
摘 要:以理性为主体的现代性对人的真实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致使人们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村上春树通过小说创作对现代性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反抗,同时在如何拯救世人的问题上作出了尝试。但在现代社会中,村上春树提出的拯救只是具有私人性质的想象,人们既没有找到精神家园,社会也依旧按照其逻辑在运行。
关键词:现代性;村上春树;反抗;拯救
作者简介:王勇,男,汉族,四川省合江县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3--02
村上春树的前期小说创作中,主要描写的都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现代都市环境中的青年男女。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迷茫、孤独、反叛等特性,恰是对现代人的真实反映,是对积极现代性和现代繁华社会的冷静关照。
一、现代性存在的问题
现代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它给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也带来了各种问题,尤其是给“人的现实”带来了不确定性。卢梭以“自然”、“自由”对启蒙运动进行了批判,认为启蒙的进步推翻了蒙昧的统治,却又建立起它自身新的奴役。主体理性带来的是自然人性的遮蔽,是理性社会中人的异化。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现代与传统产生了决裂,现代的进步成了一个谎言。它消蚀了统一的价值和真理标准,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虚无主义的危机。马克思围绕“异化劳动”从人的本质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异化劳动最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人不仅与他人相对立,还与自己的本质相对立。这使得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存在遭受到了巨大的灾难。韦伯从理性范式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在文化的理性化中,现代社会文化和精神层面上出现了危机,使得“意义丧失”。没有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和取向,价值的多元化变成了意义领域中杂乱无章的喧嚣。尤其是在人的精神的自治性上,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带来的不是个人主体自治;理性成为整个公共领域的运行原则,其生产出来的是一种与自由相对、使自由丧失的强大的统治力量。传统确定性在这种力量面前没有任何作用,决定人生存在世的本质性的价值观念从根基上崩塌了。
二、村上春树对现代性的反抗与结局
村上春树前期小说的一个主要的背景是整个日本社会发生的从经济上到人精神上的巨大改变。工业文明的演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主义的盛行,却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此环境下,村上春树创造出各种形象和故事,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进行了反思和突破。
(一)寻找本真
在对现代性的斗争中,有一种最深刻的方式便是对自然、本真的回归。在《1937年的弹子球》中,“我”为配电盘举行葬礼,“我”执着于寻找弹子球机器。配电器是新的科技仪器到来之前的传统社会生活中具有的安定、静谧的象征。弹子球身上承载着“我”和“鼠”那一代人在经历了理想的破灭后沉浸于欢乐时光的美好记忆。这些看起来十分可笑的事物和寻找过程,其实代表的都是对过往美好事物的寻觅。村上春树在《五月的海岸线》中还写到了故乡和故乡的大海。这些对童年、故乡的寻找,便是对现代性“高墙”的反抗,是对生存困境的解救道路的探寻。村上春树在努力地寻求稳定真实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希望能够在迷失了归家之路中通过返璞归真的努力,把握自身存在的意义,进行自我确证和完善,从而真正回到美好的精神家园中。
但从主人公的寻找的最终结局来看,这种努力是白费的。大海已经消失在往昔,“我”无可奈何地说“忘掉好了”。童年的美好、过往事物承载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被现代社会抹除殆尽。村上春树善意地说,寻找的结果是无用的,但寻找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寻找本身。林少华对这种寻找的认识是:“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1]这样一种执着便有了一种类似于西西弗斯的形而上的悲剧意义。
(二)对性的求取
性,也成为了村上春树的不可缺少的创作元素。作品中充满了作者对身体、对情欲、对性的描写。这种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能够让人得到一种源于大自然赋予生物本能的安定。它成为排解生活焦虑、获得心灵稳定的重要途径。在对性的追求中,村上春树笔下的青年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和安全感;通过爱与被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了对自我的肯定,并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快乐,同现实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像常人一样努力生活。
但是主人公感受到的只是短暂的欢愉,之后便是彻底的厌倦和空虚。他们觉得自己的欲望污浊不堪、一文不值,从而陷入了更为痛苦的深渊中。每个人身上具有的沉重的痛苦印记把生活中的真正价值给消解掉了,现实的力量让他们无可奈何,在寻求性爱过后还是终究走向了个体的孤独。就像《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我”说的那样,“那时我懂得了: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底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孤独的金属块儿。……下一瞬就重新陷入绝对的孤独中。总有一天会化为灰烬。”[2]
(三)对死亡的书写
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受到严重精神折磨的人无处不在,通过自杀或其它方式告别人世的人比比皆是,如木月、直子、直子的姐姐、初美、鼠、五反田等等。在《斯普特尼克恋人》中,堇一开始积极地投入到現代社会中,然后却突然出走消失不见。“我”认为堇去了另一侧,这个“另一侧”,与其它作品中写到的生命世界的“这一侧”和“那一侧”相呼应。在《挪威的森林》中,这就是“生的世界”和“死的世界”。“另一侧”就像《挪威的森林》里边的“阿美寮”疗养院一样,可以看作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作为最后的精神避难所的理想世界,也可以看作是留存于现实世界即生的世界中的一丝残余与死亡世界的复合体。堇也可以看作是同时在生的世界里,也在死的世界里。
对于任何人来说,死亡都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但死亡在村上春树的笔下却显得极为平淡和自然。小说中没有对死亡的前因后果进行详细的交代,没有以强烈的口吻对生命与死亡进行叙述,没有流露出浓烈的感情。这种冷静客观的叙事恰反映了村上春树的无力感。死亡成为了作品中青年男女在面对现代社会无可奈何的绝望之举,以至于绝望到死亡成为一种常态。这种行为在实际上以及形而上学层面上只是一种纯粹虚幻的救赎。
(四)把玩孤独
林少华称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新的人生态度——“把玩孤独”、“把玩无奈”。这种对孤独的把玩,其实就是一种保持适当的距离,一种对人生的拯救。村上春树“很少与文坛打交道,不属于任何作协组织,不喜欢出头露面——不上电视,不大让人拍照,不出席报告会,接受采访也极有限。”[3]村上春树沉溺于自己的创作中,运用作品来对抗着现代社会的禁锢。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对任何人和事情都保持距离,对生活从不刻意去追问意义,而是在“无所谓”的态度中生活。于是,孤独在这里得到了安置。这种孤独“实质上这也是一种自我认同或曰对同一性的确认,一种自我保全、自我经营、自我完善。”[4]这样,村上春树把玩味孤独作为了一种新的人生方式,成为了一种诗意的、智性的人生活法,一种潇洒、积极的人生态度。
然而,村上春树所作的一切努力只属于他个人的实践,他自己获得的拯救也只是他个人的精神想象。他所希望的通过文学作品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拯救的尝试,在面对现实社会中强大的现代性铁笼时,最终是失败的。村上春树一直宣扬的玩味和拯救,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对现代性的反讽。他苦涩的幽默、压抑的调侃、刻意的潇洒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他心中难以消去的块垒。村上春树说要玩味孤独,但他又说:“然而包围着我们的这个现实社会,却非常强大,而且是难以清理地混杂,好像在把我们想要完全自由自在地活下去的意志,一一加以打击粉碎。”[5]这种孤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虚无之中,“空”成了现代社会的实质。
三、结语
村上春树的作品那么容易引起青年人强烈共鸣的原因,就在于现代都市中的青年人自身的生存境遇与作品中所描绘的世界是如此的相似。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不断泛滥的时代中,人生命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不断被削平,尊严和价值不断被摧毁。在这种异化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中,人经受的是难以除却的痛苦和折磨。不管学者们对村上春树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的评价是好是坏,不管村上春樹自己是否有实现他的拯救的目的,他在作品中毕竟把如此贴合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危机反映了出来,可以说也让广大青年人暂时找到了一片栖息之地。但是人们不管出于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不管是出于对横流物欲的积极追求和享受,还是出于对偶然反思中所产生的羞愧意识和罪恶感而作出的自我掩饰和欺骗,亦或是出于对现代社会中种种异化的反叛,现代人包括作家的这种将飞逝的时刻保持住甚至永久化的企图和努力都是不堪一击的。神圣既没有作为一个整体为人们所拥有,也没有散化为带有意义和价值的光点驻足于现代物象之中。
注释:
[1]林少华:《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2页。
[2][日]村上春树:《斯普特尼克恋人》,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122页。
[3]林少华:《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见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序言,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2页。
[4]林少华:《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见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序言,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3页。
[5][日]村上春树:《给台湾读者的一封信》,见《1973年的弹珠玩具》序言,赖明珠译,台湾:台湾时报文化公司,2001年第1版。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等译.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美]马泰·卡林内斯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林少华.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5]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