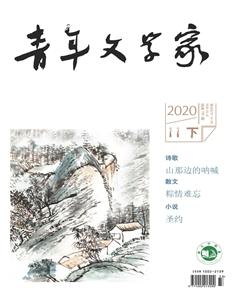论晚明女性黄媛介
摘 要:黄媛介是明清之际女性诗坛中颇有才华的文人。黄媛介忠于爱情,忠于家庭,相夫教子,完成其在家庭中良家女性的角色;战乱、生计的压迫下为养家糊口而卖书画、做闺塾师,同时与名卿大夫、闺媛名妓交往酬唱,用诗词赋抒写时事,完成其家外的职业女性角色。她的女性身份为其他女性拓宽了一条良家女子与职业生涯、妇德与交游结合的新路径。
关键词:明末清初;黄媛介;闺塾师;双重身份
作者简介:王晶晶(1995-),女,河南人,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3-0-02
黄媛介(约1614-1668),字皆令,秀水人(今浙江嘉兴),女词人,出身儒门之家,杨士功之妻。黄媛介对诗词有着极高的兴趣,在《离隐歌有序》中提到“予产自清门,归于素士。兄姊雅好文墨,自少慕之”。她所创作的诗歌较多,“这些作品大多佚失,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湖上草》、《黄皆令诗》以及零星的诗文”。[1]据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可知,仅能见到七十余首诗歌。她作为传统女性,遵循洁身自好的品格,也打破了传统儒家所宣扬的“三从四德”观念,开始从家内空间拓展到家外空间,具备着男性的才华与洒脱精神。
一、未出衡门:忠于家庭之坚贞
方孝孺《逊志斋集》写到:“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2]女性作为男性控制下的附属品,需要顺从,担负着相夫教子的责任,是丈夫的贤内助,是儿女的教育者。黄媛介选择贫寒的落魄士子杨士功,坚守对婚姻的忠贞不渝。婚后黄媛介勤于家务,即便生活窘迫却依旧怡然自得。黄媛介与杨士功是青梅竹马,由双方父母定下婚约。可惜生不逢时,明末政治上的变动引起社会动荡,杨世功家境一落千丈,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迟迟没有娶黄媛介。黄媛介虽有婚约在身,却才华横溢,爱慕者依然不少,“太仓张西铭闻其名,往求之,皆令时已许字杨氏,久客不归”。[3]她“不可”。黄媛介对待感情始终如一,面对追求者仍选择杨氏,坚持“一女不事二夫”。吴伟业(1609-1672)提到黄媛介“诗名日高,有以千金聘为名人妾者”[4]黄媛介淡薄名利,秉持传统女性的忠贞,等待杨氏。婚后,黄媛介与杨氏生活简朴,但好在两人举案齐眉,相互扶持。好景不长,清军攻陷南京,两人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家被蹂躪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橘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羁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滞云阳。”[5]生活陷入困境,黄媛介只能选择出外谋生。当时漂泊在西子湖一带,黄媛介便开始卖文鬻画,做官绅人家的闺塾师维持生活。名卿士人钱歉益(1582-1664)、吴伟业都对她的诗书“皆称异之”,名声俱增。黄媛介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儿女幼年之时,负责孩子的启蒙教育,不幸的是,黄媛介一家在“舟抵天津,一子德麟溺死,明年女本善又夭,介遂无子,懑甚。过江宁……半年卒。”[6]黄媛介因伤心过度而离世。
黄媛介一生如她所说“虽衣食资于翰墨,但声影未出于衡门”,选一人白头偕老,忠于婚姻,不做有违闺秀女子名声的事情,并在社会中努力获得名望接济家庭。依照儒家传统的“三从四德”的标准,黄媛介算不上良家女性,她的社会空间比传统女性更广。
二、资于翰墨:家外之洒脱
明清之际,流离失所的生活对黄媛介产生极大影响。其收入来源方式有卖书画、做闺塾师。黄媛介与各类友人交往,其中包括名卿士子吴伟业、王士禛(1634-1711)、钱谦益,闺秀诗人商景兰(1605-1676)、王端淑(1644-1661),名妓柳如是(1618-1664)等。在黄媛介的诗歌中,不同于闺秀女性的哀怨多愁,更多的有写实情怀。
乙酉动乱,“然皆令实贫甚,时鬻诗画以自给。”后迁居到西陵,“地主汪然明时招至不系园,与闺人辈饮集,每周急焉”。[7]在跋涉吴越间作《夏日纪贫》曰:“著书不费居山事,沽酒恒消卖画钱”,以此为生。黄媛介还有一种新身份—闺塾师,闺塾师是靠自己的学问获取而来,算是明代典型的女性职业。男女之别的观念存在,一些有财力、重视女子教养的士绅纷纷向黄媛介伸出橄榄枝,由此她加入闺塾师的行列,成为部分闺阁女子的指导者。此职业要求繁多,具体指闺塾师名声被士人所认可,在江南地区活动的知识女性。授课对象是士绅家族的闺秀,授课内容大概是教授儒家经典,诗歌艺术和绘画。施闰章载“会石吏部有女知书,自京邸书币强致为女师”,[8]可见黄媛介名声远播。徐树敏《众香词》称其“吴中闺阁争延置为师。尝有公卿内子假其诗而大宫禁,名重天下”,足以见其名望。好友商景兰《送闺塾师黄媛介》诗提到她:“才华直接班姬后,风雅平期左氏余……始信当年女校书。”商景兰工诗词,把黄媛介与班昭、左芬相比较,十分认可她的文学地位。
闺塾师的身份是黄媛介跨出家内的主要动力,借此接触社会中的不同人物。同男性交游中,吴伟业赞她为“儒家女,能诗善画”,且“诗名日高,德胜于才”[9]。黄媛介赠诗曰:“石移山去草堂虚,漫理琴尊葺故居”,人去楼空,就连习琴、修屋都变得漫无心绪。王士禛提及黄媛介“近为予画一小幅,题诗‘懒登高阁望青山,愧我年来学闭关。淡墨遥传缥缈意,孤峰只在有无间,并赞其小赋‘颇有魏晋风致”[10],字词间皆见欣赏之意。钱歉益《士女黄皆令集序》谈到“余曾与河东评近日闺秀之诗……河东曰‘皆令之诗近于僧,河东之言僧者信矣”“叔祥之序,仓萃古今淑媛以媲皆令,累累数千言”。[11]以吴伟业、王士禛、钱谦益三人对其的往来知黄媛介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性情皆出色。同女性交往时则更加亲密,如出外游玩、吟诗作赋。商景兰曾写《送闺塾师黄媛介》等诗,黄媛介与之互赠,黄媛介常与商景兰等一同交游,互相切磋文诗。王端淑与黄媛介境遇类似,亦是家道中落,出外谋生,故两人更加惺惺相惜。王端淑的《寄皆令梅花楼诗》、《为垄汝黄题黄皆令画》可见两人交往甚密。黄媛介同名妓柳如是密切,柳如是曾热情邀其去絳云楼小住,两人闲谈作词,交酬唱和。陈寅恪先生认为黄媛介《眼儿媚·谢别柳河东夫人》与《前调》这两首词都是为谢别河东君所作,前者“曾陪对镜,也同待月,常伴弹筝”,后者“分手更多情。栏前花瘦,衣中香暖,就里言深。……满船归况,万种离心”[12]可推测两人关系匪浅,连分别都难舍难分。朱彝尊(1629-1709)在《明诗综》认为:“世独盛传皆令之诗画,然皆令青绫步障,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不若皆德(其姐)之冰雪聪明。”[13]由此猜测当时因与名妓交往甚密,导致部分文人对黄媛介的评论过于偏激。综上可知,黄媛介的社交范围较广,无论在男性文人还是闺秀诗人、名妓等活动圈,其品行与诗才皆受到极高的赞扬。她勇于跨出性别限制,接触男性文人墨客,于在家外中洒脱与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