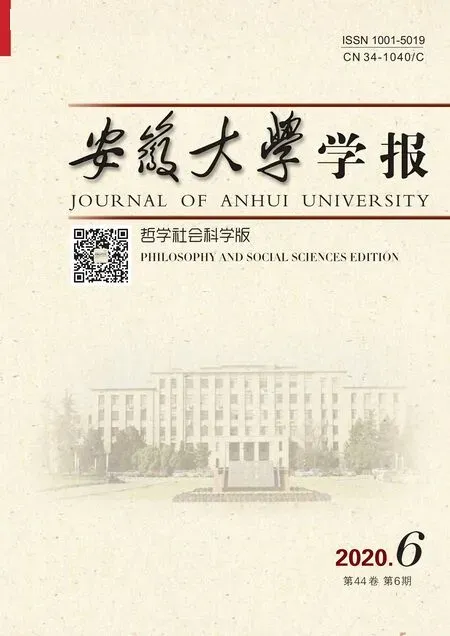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本群的媒介思想探析
吴学琴,左路平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只有报刊一类的传统媒介,现代化的媒介技术尚未发明和使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直到20世纪后才开始发展流行起来。不过,“马克思直接创办和主编、参与编辑和领导的报刊共有 12 家……他为 100 多家报刊撰稿,其中签约撰稿的报纸有3家”(1)陈力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新闻传播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6期。,可见,马克思对报刊媒介有着充分的认知,他的媒介理论也主要是基于对报刊等传统媒介的研究而形成的,这些思想集中在马克思从1842年2月初到1843年3月18日退出《莱茵报》的一年多时间里撰写的以《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为代表的文本群中(2)本文将马克思在这一段时间撰写的关于报刊媒介的文章视为一个文本群,包括《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好报刊和坏报刊》《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答“邻”报的告密》《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莱茵—摩泽尔日报》《评部颁指令的指控》《〈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莱茵—摩泽尔日报〉的修辞练习》等17篇文章。。这一年多时间,正是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以及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时期,对报刊媒介的剖析,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变,使他深刻洞察到信息传播和新闻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通过揭露和批判隐藏在媒介背后的权力和商业资本,马克思提出媒介传播应当遵循其自身逻辑,坚守客观地报道新闻真相和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职责,而不应被皇权和资本所裹挟。这一理论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媒介机构和媒介传播的意识形态属性,昭示了马克思的理论从一开始就秉持人民立场,人民立场也成为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内在动力。
一、马克思对媒介本质规定和功能的阐释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曾长期从事报刊记者的工作,正是通过这一段经历,马克思发现了报刊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本质规定性,也深刻意识到报刊媒介在表达思想自由、进行知识生产、实现精神交往中的重要作用,这为他进一步理解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媒介的本质规定是人民性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当时德国的另一份报纸《莱比锡总汇报》遭到普鲁士的查禁,理由是该报发表的文章“轻率不老实”“行为不端”,对此,马克思尖锐驳斥道,这是报刊本身的任性,发表了轻率不负责任的谣言谎言,还是因为报刊的文章报道真相,触及了普鲁士王室的利益,致使王室任性指责进而查禁报刊?“假定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根有据的,那么,试问这些指控是用来反对《莱比锡总汇报》任意行事的特性呢,还是用来反对刚刚崛起的、年轻的人民报刊必然具有的特性呢?问题所涉及的仅仅是某一种报刊的存在呢,还是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的不存在呢?”(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夹注页码。《莱比锡总汇报》创刊于1837年,是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喉舌,代表激进的自由派观点,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所以谈及普鲁士查封一事,马克思断定普鲁士政府表面上查封的是《莱比锡总汇报》,实质上查封的是代表人民呼声的年轻的人民报刊,并且以此恫吓那些准备创办此类报刊的人,所以马克思担忧经此一查,不是某一种报刊,而是所有人民报刊都不复存在,马克思从而从侧面阐明报刊应该服务于人民,其本质规定应该是人民性。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报刊呢?马克思在同一篇文章中针对英国和法国报纸间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报纸以实际生活为基础,它们的观点就是现存的老成的势力的观点。它们并不强迫人民去接受任何学说,它们自己便是人民及其党派的真正学说。”(第353页)虽然英法的报刊就其是“现存的老成的势力的观点”看,未必是真正的人民报刊,但它来源于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的生活,不强迫人民接受任何学说,从这一点看具有人民性的一面。而普鲁士官办报纸则完全相反,它们非但不替人民代言,还把自己的思想和利益捏造为人民的,再偷偷地塞给人民。因而马克思认为,“应该把对《莱比锡总汇报》的种种责难看作是针对年轻的人民报刊、因而也就是针对真正的报刊的责难,因为十分明显,报刊不经过渊源于其本质的必然发展阶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报刊。我们应当把对人民报刊的指摘看作对人民政治精神的指摘”(第353页)。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报刊按照其本质发展,一定会发展为人民报刊,所以普鲁士指责和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就是指责人民政治精神,封禁人民言论。实际上,早在《莱茵报》工作之初,马克思就曾对人民报刊的本质进行过思考,1942年3月发表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就阐发过这一观点,其基本要点如下。
第一,报刊是人民观察和认知世界的另一双眼睛。报刊的内容应源于生活,表达对生活的感悟,它所传递的思想和内容在本质上应当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是实践生活在观念世界的表达与呈现,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第179页)。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传播媒介的自由报刊,是人民透视、观察和了解世界的一双眼睛,是思想传播与精神交往的中介,源于生活又指导生活。人们借助报刊媒介传递信息,展开争辩,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认知。换言之,报刊媒介用理性帮助人民认知自我,反思自我,审视自我,进而达到自我批判、自我教育和教育他人的目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第179页)报刊媒介在辅助人民进行自我批判和现实批判的过程中成为文化生产的机器,其生产了文化,教育了人民。这样的报刊应该是自由的,是不受普鲁士王室、书报检查官等外在权力因素干涉的。
第二,报刊媒介是人民表达意见和展开思想斗争的场域。在马克思看来,报刊媒介是政治思想和人民精神的表达,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场域,报刊媒介“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第179页)。在《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一文中,马克思甚至直接认为:“正是由于报刊把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把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把需要、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智和形式的斗争,所以,报刊才成为文化和人民的精神教育的极其强大的杠杆。”(第329页)因此,承载着这种功能的报刊,需要自由批评的氛围,才能产生正向的社会舆论,推动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所希望的“自由报刊”既是人民意见的表达场域,又引领社会发展,其使类似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贫民的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使他们的贫困状况引起普遍关注和同情,并进一步为减轻这种贫困而发声,因此马克思要求“自由报刊”是“带着理智,但同样也是带着情感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第378页)。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发声,因而在报刊内部,“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第378页)。这样的报刊才是马克思所真正希望的,它是人们精神交往的纽带,是不同的思想观点表达和交锋的场域。“‘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第378页),报刊媒介是社会舆论斗争和舆论交锋的场所,在驳斥反动者对于年轻报刊的诘难时,马克思也道出了这一点:“凡是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而刚刚觉醒的人民精神公开表达出来的日常政治思想,同那种已经在政治斗争中成长壮大并充满自信的人民精神所表达的政治思想相比,就显得不够老成、不够确定、不够周密。”(第352~353页)在马克思眼中,作为媒介的年轻报刊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不成熟、不确定和不够严谨的问题,但是它预示着活力与朝气,展示和表达人民精神,同时为思想斗争提供舞台。在斗争中实现理性和智慧的升华,也完成对人民的思想教育。正是秉承这样的主导思想,马克思所供职的《莱茵报》在当时才成为人民表达心声、各种观点交锋的战场。
上述分析表明,1842年,马克思虽然囿于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藩篱,仍用自由报刊代表人民报刊,但他眼中的自由报刊是人民智慧的呈现,是人民理性的表达,也是人民道德的展现,“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第171页)。彼时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报刊媒介的本质是对人民本质的展示与呈现,是对真实性和善的追求。显然,当马克思在思考媒介本质时,已经隐约感觉精神世界源于现实生活,实践生活是思想和观念等精神内容产生的现实基础,即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生成基础,观念世界的发展又引导和作用于现实生活,这一思考成为他唯物史观萌发的起点,正是在这里,马克思触碰到了让他“苦恼的疑问”。
(二)媒介的内在属性和现实功能
在《莱茵报》任职期间,马克思看到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和书报检查官,为了皇权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完全罔顾事实真相,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通过揭示媒介自身的内在属性和现实功能,阐明了媒介作为人类精神交往手段和工具的独特价值。
第一,独立报道新闻真相,自由探寻真理是媒介自身的内在属性。1841年,针对普鲁士政府准备修改出版政策,实施书报检查的制度,马克思抗议道,报纸“将不能陈述事实了。它应当仅仅局限于一般的空话”(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72页。。这句话表达了马克思对书报检查令控制下报刊未来发展的担忧,隐含了马克思关于媒介内在属性,即报纸应当独立自由地陈述和报道事实的观点。到了1842年11月15日,当马克思从《科隆日报》上看到普鲁士“王室的内阁指令”中有支持报刊独立性的提法时,立即表示欢迎:“普鲁士报界应当对王室有关报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一前提表示欢迎,并把它看作是这种独立性的最好保证和王室意志的明确表达。”(第319页)不过王室指令中所谓报刊的独立性,事实上是要求报刊不要受到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激进思想的影响,把报刊编辑出版的独立性规约在王室指令的控制之下,以保证普鲁士王室的意志表达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并没有赋予人民表达意见诉求的权力。即便如此,马克思仍然赞同普鲁士王室对报刊独立性的承认,认为独立性是报刊实现自身逻辑的必要保障,体现了新闻的独立报道功能。这一评价,饱含了马克思对报刊媒介能够自由表达人民精神的期盼,所以,在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批判时,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媒介的自身逻辑是对真理的探索与追寻,“书报检查不得阻挠的对真理的探讨,在这里有了更具体的规定:这就是严肃和谦逊的探讨。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无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第110页)。诚然,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中也强调报刊应该探索真理,并且是严肃和谦逊地探索,但其深层含义则是要求媒介在对真理的探讨中要配合政府的管理和约束,将探讨限制在某个恰当的范围内,即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所以,马克思讽刺书报检查令中所谓对真理的“严肃和谦逊地探索”,是对自由报刊变相的控制,“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对它本身吗?真理是检验它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那么是对谬误吗?”(第110页)书报检查令的这种对真理的探索的规定,实质上变成“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不允许我用自己的风格去写,我只能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是首先必须使这种面貌具有一种指定的表情!”(第111页)显然,受普鲁士皇权制约的媒介生产是对媒介自身逻辑的悖逆,也违反了媒介运作的内在规律,是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亵渎和违背。而在马克思看来,媒介应当遵循的自身逻辑,应当是独立自由地表达人民精神,而不是受制于某些外部条件的限制,失去探索真理的精神。
第二,报刊媒介是思想传播和精神交往的载体。在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名为保障报刊独立自由,实为服务统治阶级后,马克思又阐释了报刊媒介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即作为思想的载体,报刊能够帮助人民进行思想传播和精神交往。1942年12月31日,马克思在谈到《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遭到查禁时,直接提出:“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诚然这种表达往往是充满激情的、夸大的和失当的’。”(第352页)报刊的表达虽然难免失当或夸大,但只有自由报刊,而不是什么别的报刊,才能传递人民最为真实的想法和观点,成为人民精神的传播平台和中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尖锐地、充满激情地、片面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第352页)。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媒介的报刊应该是人民思想的呈现者和感情的表达者,即使有时候由于过分的感性冲动而导致这种表达和呈现有失偏颇,但是它依然寄托着人民的希望,呈现着人民的欢乐与痛苦,依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且,这种错误、片面和激进的看法和观点,也会在报刊随后的发展中不断被纠正和改善。也就是说,媒介应该作为人民自由思想和情感表达的传播中介,这种自由的表达能警醒人民,最终会引发人们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引导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里,马克思也再次表达了媒介服务于人民的观点。
二、马克思对报刊媒介意识形态性的揭示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注意到报刊的各种政治倾向以及官方的和民营的、政党的和商业的等等性质上的差异。”(5)陈力丹:《马克思论报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新闻界》2017年第12期。从马克思对报刊媒介本质、内在属性和功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媒介作为思想生产、思想斗争和思想传播的公共领域,是思想产品的聚居地和精神的高地,而这些思想产品作为现实关系的反映,必然呈现出意识形态属性。
(一)揭示普鲁士的政治权力介入媒介传播
马克思1842年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花很大力气批判了普鲁士专制政权对报刊媒介的控制,1843年1月又写作《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进一步分析和批判政治权力介入媒介领域,以及制度性权力和政府代言人影响媒介传播的情况,从而揭露报刊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
第一,政治权力通过制定制度和法规实现媒介控制。马克思批评当时的书报检查令,认为它是“为政府所垄断的批评。……最后,当它如此缺乏批判能力,以致错误地把个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把权力的要求当作理性的要求”(第172页)。制度成为政治权力控制媒介传播的工具,而作为书报检查令的执行者——书报检查官“被委任去管理精神”(第134页),这是极其不负责任,因为书报检查官行使普鲁士专制权力,使得媒介被用来为某些特殊阶层服务而不是关注人民的利益,当媒介成为统治阶级思想控制的工具,把统治阶级的利益装扮成人民的普遍利益,把统治阶级的理智看作人民理性的表达时,媒介传播也就行使了意识形态统治的功能。因此,当“王室的内阁指令”要求一部分“不良报纸”自己更正造谣惑众的报道时,马克思认为它是对普鲁士新闻出版界的政治承诺,是对报刊独立性的支持,如果没有报刊独立自由地报道真相,即便“欺骗、撒谎和有害意图的倾向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高尚的、忠诚的、庄重而坦率的思想也更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并站住脚了”(第319页)。报刊有了独立性,才能客观报道事实真相,才能更正不实之言,这是马克思欢迎这项指令的原因。但是,这项指令所称报刊的好与坏、良与恶,与马克思的观点迥异,其并非从人民利益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而是以是否符合王室的利益为判断标准,政治权力正是通过这样的内阁指令制度实现对报刊的控制,保护王室利益。通过批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颁布的书报检查令的伪善本质,马克思揭露了书报检查立法的目的不是要保障国家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而是要维护反动势力的利益,把反动统治者的观点和要求提升为法律,以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
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对媒介传播自由进行适当约束的合理性,因为不加限制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对于书报检查制度而言,就是“应当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因此,在没有人向我们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由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本身中产生的以前,我们就一直要把受检查的报刊看作坏报刊”(第171页)。也就是说,对媒介传播自由的这种制度化限制,如果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以服务人民为目的的自由,那么它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就是统治阶级实现意识形态控制和限制思想自由的工具。这里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如果这种制度的制定和运作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保障人民的思想自由,那么无疑这种制度就是可接受的,是善的。事实上,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不受约束的纯粹自由的新闻出版容易被集团利益绑架,并将造成恶的后果,因为“卑劣的思想、人身攻击以及无耻行径在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的报刊中都可能发生”(第170页)。如果失去一定的制度制约,新闻出版自由也会为恶的言论与行为提供栖息地。
第二,政治权力通过书报检查官对报刊媒介自由言论进行监管和控制。在谈及书报检查令对媒介传播的负面作用后,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书报检查机关和检查官对媒介言论自由的控制:“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查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第108页)报刊检查机构和书报检查官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监控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直接工具。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这些人却成为统治阶级的替罪羔羊,即统治阶级推出这些个人和机构来承载公众的不满和抱怨,以此避免公众对书报检查制度本身的质疑,从而维护这一制度本身。“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对事物本身的愤恨就会变成对某些人的愤恨。……人们的注意力就从书报检查制度转移到了个别书报检查官身上”(第109页)。马克思旨在揭示统治阶级通过制度性权力的介入,实现对媒介自由的控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在必要时刻还会以牺牲其代言人的方式来维护这种控制思想的制度本身。同时,马克思还认为,政府通过“够资格的作者”和“不够资格的作者”的划分来实现媒介领域思想控制的目的。对作者的划分,“且不说这样一来新闻出版不会成为把人民联结起来的普遍纽带,而会成为分离人民的真正手段,等级的差别就会在精神上得到固定”(第194页)。这种划分实质上成为统治阶级分离人民的政治手段,会在精神上固化人民的等级思想,为维系既定的统治秩序服务。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你们从你们那一伙人中招募一帮官方作者,那是肯定实现不了新闻出版自由的。那样一来,够资格的作者都成了官方的作者”(第195页)。统治阶级就是这样通过在媒介传播领域进行精神和思想作品的生产来控制人民的精神世界,进而维系既定统治秩序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以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
由于受制于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掌控,媒介领域所传播的思想和知识不再是客观的知识和自由的思想,而是单一化、同质化的思想,其维护的是既定的统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利益。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时指出的:“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第111页)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虽然人民有机会在报刊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媒介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主要受统治阶级的控制和支配,媒介实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
(二)批判商业资本对报刊媒介内容的控制
在马克思看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刊媒体为其商业市场、资本利益与新闻垄断违背新闻自由原则”(6)王凤翔:《略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广告批评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6期。。因此,马克思在分析政治权力干预媒介的过程中,还指出了商业资本对报刊的影响。虽然在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正常,好像一个“妖魔”,这个“妖魔”“犹如一个小孩,头大如南瓜,满嘴黄胡子,一头花白发,双手长又粗,肠短胃口大”(7)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青载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46页。,但其毕竟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报刊媒介自然出现了被资本控制的情形。以马克思供职的《莱茵报》为例,这份报纸受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持,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当时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广受人民欢迎,报刊的销量倍增,使报纸的控股者获利颇丰,但由于马克思的激进态度,报纸遭到当局的查封,为此,报纸的股东专门递交了请愿书《莱茵报社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这个请愿书间接证明当时的报刊已经由资本家控制,报刊的控股者通过资本控制报刊的办刊方向,为资本服务。其他报刊也有类似情况,如《科隆日报》从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代表天主教会,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莱比锡总汇报》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喉舌。马克思当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该问题,他发现在资本控制下,媒介作品生产的目的与手段颠倒,其发行传播也受到限制。
第一,批判出版商颠倒作品生产的目的与手段。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报刊作品是具有真理性的作品,作品就是作者创作的目的。但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出版商却对媒介作品有着生杀决定权,在出版商干预下,报刊作者不是为了真理和正义写作,而是为挣钱写作,挣钱是目的,写作只是挣钱的手段,如此自然无法保证作品的真理性和客观性。所以,马克思认为:“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第192页)马克思一生都是这样践行的,他坚持创作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的作品,强调不能把私人利益作为媒介产品生产的目的,否则作品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
第二,批判商业资本干涉出版自由。马克思通过深刻地诠释新闻出版自由和贸易自由之间本质上的差异,批判商业资本对出版自由的控制,马克思认为:“宣称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行业自由,这无非是在未保护之前先行扼杀的一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新闻出版向行业说道:你的自由并不就是我的自由。你愿服从你的领域的规律,同样,我也愿意服从我的领域的规律。”(第191页)在马克思看来,新闻出版自由与行业自由或贸易自由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用行业自由的规律来规约和支配新闻出版的自由发展。就像马克思揭示的那样:“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当然,新闻出版也作为一种行业而存在,不过那已不是作者的事,而是出版商和书商的事了。”(第193页)也就是说,对于作者而言,新闻出版自由要求遵循写作自身规律来进行自由创作并自由出版,作者是为了真理和正义而写作,不能受到社会资本和商业出版的影响。但对于出版商而言,为了实现利益,则要遵循行业自由的规律,即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为利益最大化而出版。如果按照贸易自由的逻辑和规律来支配和控制新闻出版,那么新闻出版自由则丧失了自身的本质,新闻出版也成为社会资本控制下的纯粹的商业活动,变成资本实现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在1843年2月12日《莱茵报》的股东就《莱茵报》复刊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代表资本的股东与报刊编辑部之间展开争论,焦点集中在是为人民办刊还是为私人利益办刊,当时上诉法院参事奥本海姆曾提到,“我并不想否认股东们有批评管理机构的权利,但是我认为他们没有直接干预管理机构所采取的措施的权利”(第991页),这就直接暴露了两方之间的分歧。股东对编辑部管理机构的干预,体现出资本对报刊出版的介入,当然这一介入和干预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今天资本的干预不再仅仅是通过董事会决议,还直接通过资本的注资或抽离影响媒介的生存。
显而易见,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报刊媒介已经广受商业资本制约,虽然在此时,马克思并没有科学地揭示资本逻辑的演绎机制,但是他已经初步发现资本的秘密,即资本对媒介的操纵秘密。也就是说,无论是受私人利益的驱动,还是受社会资本的驱使,在商业资本操控下进行的媒介产品的创作和生产都烙上了意识形态的印记,违背了自由创作精神产品的初衷,使得媒介产品沦为资本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
(三)批判报刊媒介制造的意识形态幻象和同质化趋向
在马克思看来,在统治阶级权力控制和商业资本控制下的报刊媒介,一方面不断地为人民制造意识形态幻象,迫使人民生活在幻觉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推动思想的同质化发展,消除人民的个性以维护统治阶级思想的统治地位。
第一,统治阶级借助媒介制造意识形态幻象。1842年3月,马克思在写作《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时指出:“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因此,人民也就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信,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第183页)马克思在批判书报检查令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指出:“检查令的这种不彻底性只是一种假象,因为这种不彻底性的立足点就是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对宗教进行某些攻击也是许可的。但只要不带偏见,一眼就可看出这种假象只是一种假象而已。”(第117页)可见,检查令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法律层面的表现,它试图让人民以为,他们的权利得到了保障,他们可以自由地通过报刊媒介展开对宗教的批判,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
第二,统治阶级借助媒介驱动思想的同质化发展。马克思在批判书报检查令时指出:“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第111页)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书报检查令试图以同质化的意识形态生产取代多样化的精神产品生产,以趋同的思想控制人民思想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还进一步评价道:“我的生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性被看成是一种坏的个性,而且由于这种意见我要受到惩罚。……我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我的行为并不违法,只是由于这一点,我就迫使好心肠的、善意的法官去追究我那非常慎重、并未见诸行动的坏的思想。”(第121页)在马克思看来,新的检查令造成了一种对人个性的压抑,为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统治阶级居然通过颁布法律来对人的思想倾向进行监管,这种对媒介内容的控制已经造成对公民自由权利的损害,马克思认为这已经不是法律,而是特权,是一种维护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特权。就这样,借助媒介传播,统治阶级试图营造一种意识形态幻象,让人民生活在这种美好幻觉之中;同时,统治阶级又借助法律来引导媒介内容的同质化发展,促使人民思想趋同化,泯灭人的个性特征和自由本性。因此,普鲁士的法律制度与国家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制度,因为这个国家是和人民根本对立的。
三、马克思媒介批判的特征及其评价
马克思的媒介意识形态批判具有多重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包括人道主义批判、阶级性分析方法和媒介话语的多元化书写等,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唯物史观,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已经展现了唯物主义观点,同时,马克思的媒介意识形态批判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媒介批判思想的三重特征
马克思进行的媒介意识形态批判有着三重特征:第一,对媒介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批判。年青的马克思带着对人民的感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普鲁士的媒介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的媒介操纵对人类社会道德的背弃和在价值认知上的错误。一方面,马克思在应然与实然的对比中批判书报检查令的伪善。马克思指出:“起败坏道德作用的是受检查的报刊。最大的恶行——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恶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丑陋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样)恶行——消极性。”(第183页)按理说,报刊作为文明的产物,给社会带来的应该是一种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善的力量,应当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对报刊的检查却是一种恶行,它会使报刊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给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对这类报刊应从道德上加以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在批判媒介生产之目的和手段的颠倒中阐发报刊的价值。马克思强调,“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第192页)。在马克思看来,不能把目的变成手段,对于媒介作品的生产者来说,创作更好的作品本身就是目的,创作不应该成为作者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一旦媒介作品成为作者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作品也就失去了其内在价值。
第二,对报刊媒介意识形态运作的阶级性批判。1842年的马克思虽然没有形成成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的思想,但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而在对媒介领域的思想控制进行分析时,马克思也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媒介思想控制背后隐藏的阶级统治关系。其一,马克思对媒介权力进行了阶级分析。马克思在对媒介传播领域的权力逻辑进行批判时,不仅以现象为批判对象,还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剖析了现象背后统治阶级的权力支配关系,“或者,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而那一伙专看官方眼色行事的卑劣作者,便放心大胆地反对那些不受宠幸的人,对政府却称颂备至”(第109页)。马克思认为应当从本质上去改善这种统治阶级支配和控制下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不应仅从表象出发,把制度的缺点归咎于个人,在实质上,书报检查官只是统治阶级维系统治和进行思想控制的一个中介和工具而已,应当看清事物的本质,从改变这种制度着手,从改变制度背后的普鲁士统治阶级权力控制出发。其二,马克思对政治机构参与媒介思想控制进行了阶级分析。马克思在批判国家机关借助制度性权力进行媒介思想控制时指出:“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第121~122页)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作为统治阶级控制工具的国家机构,它们自以为站在道德和理性的制高点,用自身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包括评判媒介领域自由思想传播的合法性,运用不合理的法律来惩罚人民,控制人民的思想,而本质上它们只不过是普鲁士统治阶级思想控制的工具罢了。
第三,媒介批判话语的多元化书写。马克思在对报刊媒介本质的研究以及对新闻出版自由问题的评析中,运用了极其丰富和精彩的话语表达方式,使得其媒介意识形态批判更具现实批判力,更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其一,马克思擅长用生动形象而又极具辛辣讽刺意味的大众话语来进行媒介批评,他在批判意识形态对媒介的控制时,就运用了这样形象的话语:“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第111页)。马克思先用类别的叙事手法,阐明了大自然中生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与精神世界的发展作对比,指出媒介的出版自由应当遵循精神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不应该被“同质化”和“单一化”;随后运用比喻的手法,阐明精神世界的自由发展带来了绚烂丰富的色彩,但受制于官方的支配和控制,精神世界失去了它本应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二,马克思在对报刊媒介的论述和对官方媒介的批判中运用了大量的反讽手法,借助这种写作方式强烈地讽刺统治阶级政策的内在矛盾和欲盖弥彰。如在分析官方既鼓励报刊媒介对真理的探寻,又强调作者要保持严肃和谦逊的态度的内在矛盾中,马克思论述道:“请随意写吧,可是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必须同时是对自由的书报检查机关的阿谀奉承之词,而书报检查机关也就会让你们那既严肃又谦逊的言论顺利通过。可千万不要失去虔敬的意识啊!”(第113页)马克思通过反讽的手法,尖锐地批判了书报检查令的内在矛盾,辛辣地嘲讽了官方当局自欺欺人的做法。
(二)马克思媒介批判思想的定位及其启示
客观而言,此时马克思的媒介批判思想尚未成熟,他对媒介的认知和分析未能呈现科学的深刻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的论述一方面包含民主进步的时代内涵,如新闻自由即追求真理的自由,一方面尚未超越启蒙理性与唯心主义的认识局限。”(8)徐梦菡、李彬:《马克思早期新闻思想及其时代性——〈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再解读》,《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9期。由于此时,马克思尚未形成科学的唯物史观,因而其对媒介意识形态的分析和认知还较多地停留于人道主义层面,只是以道德良知对官方媒介意识形态控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不过,“在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认识已经显现了转变之中的特征,显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9)苑秀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0期。。他的媒介批判话语中亦透露了其唯物史观的萌芽,如对政治权力逻辑的剖析,对资本和商业利益逻辑的批判等,无不体现了其早期思想中的洞见。
虽然新时代的媒介形态及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但是马克思的媒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依然能为新时代媒介意识形态批判和建设提供一些启示。其一,新时代新闻媒介的本质规定性依然是人民性。马克思在对报刊媒介进行研究和评述时指出了媒介的本质规定性即是人民性,为人民服务是媒介的根本使命。在新时代,我国媒介的发展应当依循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不断开拓媒介发展新方向,为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其二,进行错误意识形态批判是新时代媒介的重要使命。马克思认为,拥有独立的批判性是报刊媒介的重要功能。由于媒介是思想斗争,也即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场域,因而,在新时代媒介及主流媒体应当主动对错误的社会思潮、敌对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斗争,揭示其错误性和虚伪性,进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
四、结 语
报刊媒介研究是马克思初入职场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在《莱茵报》任职期间也是马克思研究新闻出版问题最集中的一个时期,这一阶段对报刊的认知和研究,奠定了马克思媒介思想的基础。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虽然媒介形式已经变得丰富多样,但马克思揭示的媒介本质规定依然没变,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新时代媒介的根本使命,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各种网络自媒体,都应当坚持人民立场,以独立客观报道新闻真相为首要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4页。因此,在网络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注意借助媒介宣传展开错误意识形态批判,揭露其本质和危害,维护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和思想健康,把媒介的使用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使新媒体成为表达人民思想的场所,成为对社会进行价值引导和思想教育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