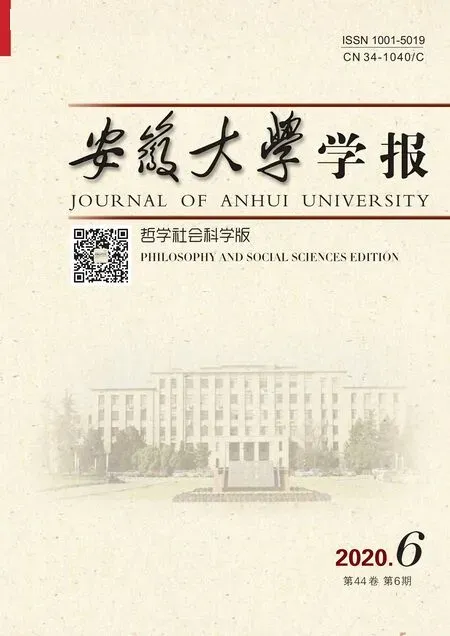批判:体系的艺术
——论批判哲学的知识批判与形而上学艺术本质的启蒙
张 广
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纯粹理性建筑术”一章中,使得“科学”得以可能的知识的综合被界定为“体系的艺术”(Kunst der Systeme)(1)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A 832/B 860. 下引该书按学界惯例随文夹注A/B版页码。。由此《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也就将“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可以说,这个提法不仅凸显了《批判》引以为傲的成就,也锐化了理解它的困难。因为,一方面,这明确了它“哥白尼思想”(Gedanken des Koperniskus)(B xvi)的鼎革之意:客观的认知被修正为了主观的建构。但是,另一方面,其也带来了问题:客观的认知怎么能和主观的建构关联起来?并且,更有甚者,“建筑术”还指出了“体系的艺术”不仅给“科学”提供了一个“整体的形式”(Form des Ganzen),也赋予了它“整体的目的”(Zweck des Ganzen)(2)学界关于“建筑术”的理解的差异也体现在这一区分上,例如Goy就系统性地介绍了前者,Höffe却引入了后者而没有过多地论及前者。Cf. Ina Goy, Architektonik oder Die Kunst der Systeme: eine Untersuchung zur Systemphilosophie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arderborn: Mentis Verlag, 2007, S. 18; Otfried Höffe, Architektonik und Geschichte der reinen Vernunft,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von Georg Mohr und Marcus Willaschek,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618-644.(A 832/B 860)。这就意味着,主观的建构并非只是简单地附加上来,它还要为客观的认知奠基并架构客观的认知。因此,《批判》实质上还会面对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客观的认知不也排斥一个主观的建构吗?
与之相应,借助一个知识元素的区分,《批判》也发展出了一个解构性的“纯粹理性的规训”(A 709/B 737)。因为,借此它首先将作为纯粹“概念”的理性与“直观”这一客观的表象关联起来,继而将其限制在了“范畴”(Kategorie)这一直观综合的功用之中,最后还指出了作为“理念”(Idee)它是导致“背反”(Antinomie)而取消“理想”(Ideal)的“谬误”(Pralogimus)(3)这一知识论的否定,以及康德在知识体系上的论述缺陷,导致直到现在都有对“建筑术”的质疑。Cf. Dieter Henrich, Systemform und Abschluβgedanke—Methode und Metaphysik als Problem in Kants Denken, in Kant 2000. Akten des Internationalen Kant-Kongresses, Hrsg. von Volker Gerhardt, Berlin: De Gruyter, 2000, Bd. I, S. 94-113;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579; Paul Guyer, Kant and the Claims of Knowle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A 407/B 434, A 574/B 602, A 341/B 399)。这样一来,它就不仅解析也解构了理性的综合。因此,再提出“纯粹理性建筑术”就与之前的解构相矛盾了。但是,客观的表象与主观的创造不也能兼而有之吗?具体的直观不是只有借助概念才能有自己的普遍的规定吗?这表面的矛盾之中不也有可能隐藏着被动与主动的结合吗?并且,不是正因为受制于直观,才有阐明自我的建构以使其不至于被直观排除的必要吗?
对理性体系的论述涉及对批判哲学的整体认知,这向来都是批判哲学研究的基础话题。在这一话题下,一方面批判哲学也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述。为此,它不仅在它的实践哲学中以自由为基础,架构了理性的体系,也以审美的培养说明了如何在自然之中发展出一个自由的体系的可能。另一方面,受观念论的批判和重构的影响,理论界也出现了对理性体系进行“再先验化”和“去先验化”的双向修正(4)Cf. Otfried Höffe,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die Grundlgung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München: C.H.Beck, 2003, §24.1.在这一节中Höffe全面总结了观念论以后各种哲学思潮对批判哲学所做的理性综合的说明的双向修正。。但是,不得不说,无论是批判哲学之后的补充,还是后来的理论对批判哲学所做的接连不断的修正,在发掘和拓展了相关议题的同时,也遮蔽了《批判》开创性的贡献。这样一来,也就有必要指出:《批判》不仅以一个知识元素的解析解构了形而上学,也以一个理性体系的建构重整了形而上学;并且,这一解构和重构,不仅为知识提供了一个体系化的认知形式,也赋予了理性的知识论批判一种道德启蒙的本质;甚至,以此它还将知识和道德结合在了一个规划了人类整个存在的理性理想之中。
一、形而上学:无能的科学
“科学”应是一个“体系”,这一观点无疑在观念论那里得到了更为专门的发挥,以至于成为后者的核心贡献。不同于此,在以解析两个知识元素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之中,作为最后总结性的“方法论”之下的一个论题,它则并不显著,因此也常常为人所忽略。不过,即便如此,在《批判》中这个论题也并非无关宏旨。实际上,《批判》不仅比观念论更早地提出这个论题,同时,因为架构了“科学”的整体,这一论题也提供了《批判》的全景:不同于先行的“元素论”只是逐个分析知识的具体成分,作为后来的知识的整体的说明,它超越了局部的解释,提供了知识的整体,因而也给出了作为一个知识论的《批判》的整体。因此,虽处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文本位置上,它却是隐藏在《批判》——作为“纯粹理性的体系(科学)的导引”(A 841/B 869)——中的一条极具价值因而必须被揭示的暗线和主线。
并且,作为形而上学的修正,《批判》也必须说明我们的知识为什么应当是一个“体系”。因为,它所接手的以三个问题的形式出现的形而上学,也就是“灵魂”“世界”和“上帝”,预设了一个“体系”(A 3341 f./B 391 f.)。首先,“灵魂”要求认识能回到事物自身之上来开展,因此不同于偶然的外在的表象,“灵魂”作为本己的规定要求达到对必然的内在的原则的认识。进而,“世界”要求认识将一切现象都纳入一个“总体”。并且,作为一个超验的理念,“世界”也一样应该是普遍的,因而也同样应该是源于原则自身的一个总体。最后,“上帝”这一理念更是要求将全部的原则,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原则都纳入一个总体,因而它更是一个总体的总体。因此,要修正形而上学,《批判》也就需要认识和架构一个“体系”。并且,这一“体系”不仅是一个现象的总体,也是一个原则自身的总体。
当然,想要在形而上学之上整理出一个体系也绝非易事, 甚至《批判》也否定了整理出一个体系的可能。因为,首先《批判》接手的形而上学并不是一个已然存在的体系,而是上述的三个理念,因而它首先得到的就不是一个“科学”,而是一个理念的“集合”(5)就此而言,不仅形而上学自身的架构是不清晰的,也可以说《批判》也没有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非常清晰的说明。C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Werke. Band 3,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S. 9.。可见,即使《批判》整合了这三个理念,架设了一个体系,但它们会怎样结合起来,依旧还留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更不要说,《批判》还指出:作为普遍的“概念”,这些理念都远远地超出了经验,因而它们连同它们指向的“体系”一起都无法被认识,也就不能被认定为是客观的存在。如此一来,与其说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个知识的“系统”,倒不如说它带来了“科学”自身的否定:没有超验的认识。利用“幻象”,通过辩证,《批判》明确地阐明了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带来任何真理,而只是不实的言辞和空洞的想象(A 293/B 349)。因此,一个“体系”,对于《批判》而言,也就不是要认识的总体,而是一个警诫:不要让认识超出经验。
更有甚者,《批判》还揭露了形而上学有内在的自我否定,因而还从形而上学自身否定了形而上学。因为,《批判》认为它所接手的形而上学还是一个“战场”(Kampfplatz):尽管有“一切科学的女王”(Königin aller Wissenschaften)这一尊号,但是在它的统治之下却没有出现诸科学的联合,而是“公民联盟”(bürgerliche Vereinigung)的瓦解(A viii ff)。对此,《批判》在“辩证论”中借助三个推理形式进一步展示了:形而上学不仅会因为将纯粹的“概念”混同为“直观”而成为“谬误”,在这一错误之上,它还会陷入足以取消自身普遍运用的“理想”的自我的“背反”。这就是说,形而上学凸显了我们的认识有脱离实际走向主观的可能。因此,它也就不免会带入我们观念上的分歧,从而引起我们的对立,以至于消解了我们达成普遍共识的可能。这样一来,《批判》也就以形而上学自身的矛盾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一个“体系”的可能。
然而,正如《批判》将“概念”从“直观”中分离出来所表明的那样,我们的知识并不只是客观的、具体的。与之相反,因为有理性的整合,它们也会是主观的、普遍的,以至于最终还会被纳入一个唯一的“体系”。如此一来,形而上学对于我们而言也就不只是一个“谬误”,它也弥补了感知的不足,架构了“世界”总体,建立了“科学”的“体系”。因此,我们也同样需要离开外在的有限的经验,进入我们自身的普遍的理性,并要在它之上建立我们认知的普遍形式和体系化的架构,以至于我们会不可避免地会犯下“谬误”,陷入取消了我们“理想”的自我的“背反”。因为,如果知识只是感性的,那么它就还缺少一个普遍的规定,而同时作为一个具有理性的主体,我们不仅要也同样能提出一个体系化的知识建构。
二、元素分析:体系的重整
事实上,不只是指出了形而上学令人绝望的错误、矛盾和空疏,借助“直观”和“概念”这两个知识元素的区分,《批判》也将我们的知识引向了使“科学”得以可能的“体系”(6)这里可以参看《批判》对知识“分枝”(Stämme)和“根基”(Wurzel)的区分(A 15/B 29, A 50/B 74, A 835/B 863)。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海德格尔的理解,“分枝”指的是“直观”和“知性”两个知识元素,“根基”指的是纯粹理性,而不是结合“直观”和“知性”于一体的想象力。因为根据两个元素的先验演绎,它们都被追究到了主体自身的综合也即理性之上。再者,想象力尽管联结着感性和知性,其自身也仍然需要一个主体的综合,因而也仍然可以追溯到理性之上。并且,《批判》在第二版的修改中也删去了首版的这种过于主观化的论述。还有就是《批判》探讨的主题是理性而不是想象力。Cf.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Hrsg. von Friedrich-Wilhelm v. Herrman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10, Gesamtausgabe 3, Abschnitt 3, B.。首先,在“感性论”中通过“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直观形式的区分和说明,我们的表象被追溯到一个自我的综合之上。接着,在“分析论”中,利用对“范畴”的发现和演绎,上述综合进一步地被追溯到一个系统之上。最后,在“辩证论”中,通过对“理念”的说明和辨析,《批判》也最终说明了理性自身是如何建立上述“体系”。由此可见,在最终指出形而上学并不具有认识对象的功能的同时,《批判》也阐明了我们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理性,也会最终将我们全部的知识都纳入一个“体系”。因此,它不是完全否定了形而上学,而是让它由一个不可能的外在的客观的体系转变为一个可能的主体自身的建构。
当然,要想发现上述线索,进而在“元素论”中认出一个“体系”,也同样是困难重重。首先,一个理性体系的说明是通过两个知识元素的区分来实现的。这样,《批判》首先也就是一个元素的解析,而不是一个体系的说明。更不要说,在不同的元素之下《批判》还做了诸多细密的区分,因而它也确实冲淡了对体系的说明。再者,“元素论”也没有系统地说明理性是如何逐步建构出知识的“体系”的。因此,与一个“科学”的“导引”相反,《批判》看起来确实更像是一个知识元素的解析,而不是一个科学体系的说明,或者带有同情地说,它也只是为这一说明做了准备(7)Otfried Höffe, Architektonik und Geschichte der reinen Vernunft, in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von Geoge Mohr und Markus Willaschek,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S. 625.。当然,虽然“方法论”也提出了一个“纯粹理性建筑术”,并且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上述缺失,但是,不得不说,“建筑术”的说明仍然是庞杂和抽象的,因此《批判》并不能完全消除上述的重重困难。
不过,即便如此,无论是在自身的意图上,还是在实际的功效上,都能看得出《批判》是一个体系的说明。首先,在意图上,它并没有只局限于说明形而上学中的理性问题和矛盾,即说明在形而上学中理性如何因为“幻象”而陷入了自我“背反”,以致取消了它自身的“理想”。与之相反,它要化解理性的矛盾,为形而上学提供“全面的满足”(A xii, A 804/B 832)。可见,尽管面临问题和否定,《批判》并没有放弃形而上学的抱负,甚至是毫无妥协地,因而也比以往任何尝试都还要激进地寻求建立一个“体系”。并且,也正是因为出现了问题和矛盾,才使得《批判》有了寻求说明体系的必要(8)这里可以参见《批判》对“安乐死”(Euthanasie)(A 407/B 434)的解释。。因为,问题会提醒人们出现了自我否定,为摆脱困境,人们需要重整我们的理性,重建形而上学。并且,如上所述,《批判》也确实能在普遍的“概念”上说明建成一个的“体系”的所在、可能与架构(9)这里可以参见《批判》对“完全的满足”(völlige Befriedigung)(A 856/ B 884)的解释。。
事实上,上述理解的困难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一方面,尽管“元素论”接连不断的元素解析大大冲淡了体系的说明,但是它还是将自身展现为逐步揭示体系的一个“科学”的“导引”。并且,如上所述,最终它也抵达了“科学”的“体系”,在“科学”的所在,也就是理性自身之上,说明了“体系”自身的建构。因此,断定《批判》只是一个元素的分析,而不是体系的说明,或者只是体系说明的准备,也的确责之过切,忽略了它开创性的贡献。另一方面,尽管“方法论”作为《批判》的统合,其表述极其抽象,因而不易理解,但是,在“方法论”中,《批判》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体系”,也在“建筑术”中进一步明确了“体系”的构成和实质,说明它的方法以及它的批判意义。显然,《批判》所提供的,与它想要提供的,都绝非只是一个元素的解析,同样也还有一个体系的说明。
无疑,《批判》不只是一个“纯粹理性的规训”,一个体系建构的否定,它也是一个“体系的艺术”,科学的说明。它不仅指出我们无法在外在的直观上建立一个理性的体系,也凭借概念内在地说明了我们的知识会被整合入一个体系。并且,这一积极的“建筑术”不只是最后出现在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方法论”中,而是在否定了纯粹理性认知功能的“元素论”中就已经出现。甚至在“元素论”中,《批判》也不是在“辩证论”最后的“纯粹理性的理想”中才提出了体系,而是在“分析论”中就利用“范畴”指出了存在着体系的建构,甚至早在“感性论”中就以直观的先验说明提出了理性的综合。可见,《批判》从一开始就在发展为一个体系的说明。这样,也就自然不能将其只看作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否定,而应该也看作是科学何以可能的说明,即使纠缠在否定和建构之间,它的确也给我们设置了认识这一转变的困难。
三、理性综合:主体的建构
在《批判》的理性的知识论批判中,值得注意的还有:通过“直观”和“概念”这两个知识元素的区分,“科学”这一体系化的表象认识也被修正为了理性的综合这一主体自身的建构。可见,《批判》探讨的就绝不只是知识的架构和界限,同样它也触及了主体自身的展开和建构。因为,在一个知识元素的解析中,将“直观”和“概念”联系起来,就让它指出了“直观”也包含有主体的综合。继而,通过判断的形式发掘“范畴”,也让它不仅区别于“直观”这一被动的表象,展示为主体自身的整合,还让它将这一综合展示为主体自身的体系化的建构。最后,通过对推理形式的解析来辨析“理念”,它甚至还直接说明了主体如何架构出了“体系”。由此可见,确实《批判》不只是一个知识元素的分析,也是一个体系的说明,并且是一个主体自身建构的说明。因此,它不能只被视作一门说明“科学”何以可能的知识论,也应该被看作是一项说明主体如何架构自身的启蒙。
之所以具有主体启蒙的意义,从根本上说也同样是因为形而上学给我们架构了一个主体的领域。因为,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理性的三个理念,也就是“灵魂”“自由”和“上帝”,共同构成了一个主体的世界。首先,“灵魂”这一理念要求我们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外在的经验的现象之上,而是也要追踪到事物自身的规定之上,因而需要是一个主体的自觉。其次,“自由”这一理念虽然也被看作是“世界”这一总体的原因,但是能够提供这一原因的也不会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主体。并且,作为一个现象的总和,它还是一个主体规定的运用和展开。最后,“上帝”作为一切原则的总体,更是主体的总体。因为,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原则都纳入一个“体系”,这就不仅意味着将不同原则之下的直观都整合在一个总体中,同时也意味着连同提供原则的主体都一起被整合了起来。可见,作为形而上学的修正,《批判》也必须提供一个主体的启蒙,并且是主体的总体,因而是人类整体的启蒙。
实际上,《批判》也意识到它的这一职责。一方面,正如它在“纯粹理性的规范”中阐述的那样,它不仅指出三个理念的理论功能微乎其微,实践意义才正当其用,进一步地,它还阐明“我能知道什么”只是它的起点,它还会探讨“我应该做什么”,甚至最终它要回答是“我可以希望什么”(A 805/B 833)。由此可见,它有一个回答“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的思考框架。另一方面,通过首先将“概念”与“直观”区别开来,继而将“范畴”从“概念”中剥离,最后用“理念”这一纯粹“概念”来阐明理性的建构,它也说明了我们并非只有经验的认知,还有自我的建构,并且是我们自身总体的建构。因为,如此一来,首先我们就不仅有被动的表象,也有了主动的综合。继而,我们的综合不仅体现为直观的综合,也体现为我们对自身的综合。这样,《批判》也就指出了作为理性的存在,我们有自我的规定和建构(10)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提醒的是,艺术哲学作为人的本质说明与建构并非只是出现在谢林的先验哲学中并进而成熟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中,也不是在《判断力批判》的目的论部分才出现,而是早就呈现在《批判》之中,尽管这一思想在《批判》中还纠缠在理性认识能力的划界这一消极的论述中,因而并不是那么明显和突出。Cf. Hegel, Phö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D. Köhler und O. Pöggeler, Berlin: Akadiemie Verlag, 1998, VII B; Schelling, 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Hrsg. von Walter E. Ehrhardt, Hambuger: Meiner, 2000, 6. Hauptabschnitt.。
当然,正如形而上学呈现给《批判》的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三个问题一样,《批判》对形而上学的解析也不直接就是一个体系化的说明,而是更多地分散在了“辩证论”对三个理念的分别说明之中。这样,它呈现的就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三个问题。因此,即使我们可以借助三个理念以及《批判》对它们的解析整理出一个主体的建构,因而超出一个知识论的框架,但是,不得不说,三个理念怎样构成了一个体系,构成了一个怎样的体系,也还是有许多环节有待阐明。且不论,从一个知识的形式论到一个道德的目的论,也恰如《批判》所言,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将客观的表象修正为主观的建构。这也就要求《批判》具备足够引导思想转变的能力。但是,与之相反,《批判》却将自己的论述集中在了“元素论”这一知识元素的解析之上,因而即使它带来了一个道德的转向,它也还是缺少充分的论述来引导人们进行上述转变。
但也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消除这种说明的不充分,呈现出一个主体自身的建构,也不能通过简单地引入道德的目的论来解决,而是要一个彻底的认识论批判才能达到。因为,正如《批判》运用“幻象”所说明的那样,由于也涉及直观,所以在理性的客观运用中人们不免会将其混淆为直观,从而因为直观的分化招致理性自身的对立,以至于会取消理性的普遍运用。对此,只有像《批判》所做的那样,明确地将“直观”和“概念”区别开来,才能既明确地说明“科学”何以是一个体系,又能有效地建立一个道德的立法。因此,上述说明的不充分不在于没有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在于一个有效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充分说明,并没有充分地呈现出来它其实已经解决了问题。更不要说,出现这一问题也不能只归咎于《批判》,也是由于形而上学本身就有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仅是概念的科学,也涉及直观的综合,集直观和概念于一身,因而不免让人挂一漏万。
四、知识批判:体系的艺术
到了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批判》让一个自我的建构既摆脱了外在的遮蔽,也解除了内在的矛盾,因而使其获得了自觉与可能。但是,无论将“直观”与“概念”联系起来,继而又在“概念”上说明直观的综合,以至于最终将“直观”追溯到一个“体系”,从而澄清“科学”,还是回到“概念”自身,将其与被动的“直观”区别开来,以至于将其与“直观”的综合区别开来,转而在主体自身的建构之上说明理性的综合,从而说明了“道德”的所在,这些都只是着力在一个体系的某个元素的解析上,因而也还是没有达到对体系整体的说明。易言之,在理性的运用之上,或是回答了“我能够知道什么”,或是回答了“我应该做什么”,因而或者着重于对直观的表象,或者着重于概念自身的发挥,但它们都没有回答“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个将“我”与“希望”联结起来,将“概念”与“直观”结合起来的体系整体的建构问题。
不同于此,事实上,在对形而上学的认识上,《批判》不仅超越了对外在运用,也就是对“直观”的解析,也超越了对内在规定,即对“概念”自身的说明,从而将这两个知识元素集中在了一个“体系”之中。如上所述,对于《批判》而言,形而上学既非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也非止步于一个道德问题,而是牵扯到“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个将科学与道德结合在一起的信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通过“尊严”(Würdigkeit)(A 813/B 841),《批判》架构起了“至善的理想”(Ideal des höchsten Guts)(A 810/B 838),即以“以德配福”的方式将知识与道德结合起来,因而它确实也将“直观”与“概念”整合在了一个体系中。当然,就整个《批判》来看,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与“我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一样,较之于第一个问题,对这第三个问题的解答也是非常单薄、抽象和初步的。但是,即便如此,它还是告诉我们:《批判》不是只有两个元素的解析,它也有体系的整合,甚至于有将知识和道德这两个体系整合为一个体系的整合。
应该说,《批判》对于形而上学的解析,不仅可以看作是对作为一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所具有的不同元素的区分和解析,也同样可以看作是将不同元素结合为一个“体系”的形而上学的整合和重构。因为,一方面,通过区分两个异质的元素,《批判》的确给出了形而上学的不同含义,因而可以排除无论是理性论的还是经验论的片面的认知,从而呈现一个全面、开放、多样的视野。另一方面,通过重整形而上学的体系,它也将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个总体中,由而重构了整个形而上学。可见,《批判》提供了一个知识元素的解析,呈现了一个理性综合的不同规定。这样,它不仅将“直观”与“概念”联系了起来,将其追认到了“科学”,同时,它也道出了“概念”之中所包含的主体的自我建构,从而以“道德”更新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以此,它还将上述二者都结合了起来,建构了结合感性与理性于一身的人类的整个存在。
就此而言,确实可以说,《批判》可谓“科学”地、本原地、批判地,因而是原教旨地回到了形而上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一方面,将作为纯粹“概念”的理性与客观的“直观”联系起来,并将其限制在直观综合之上,它使形而上学得到了客观的内容,因而使其成为科学。另一方面,将“概念”与“直观”区别开来,进而将“概念”展示为主体自身的建构,也不仅让它说明了形而上学的自我取消是因为将纯粹主观的“概念”误认为了完全客观的“直观”,因而是对理性的不当主张,同时,这也让它澄清了理性综合的所在、可能与架构,因而也本质地呈现了主体自身的规定和建构。因此,无疑《批判》引入了科学,使形而上学获得了客观的意义。同时,它也批判了理性的不当运用,解除了理性的矛盾 。此外,它的确也本原地说明了形而上学的可能。
通过区分一个体系的不同元素来重整理性,《批判》也同样可以说是一门最激进的形而上学。因为,如此一来,一方面,形而上学就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理性建筑术”,而是也成了一门“科学”,一门“直观”的综合理论。这就意味着,它不仅要从主体自身之上提出理性的建构,也要将其与客观的直观结合起来。这样,即使它否定了纯粹理性的认知功能,它也还是让我们的理性突破了自身,使其具有了原本不曾具有的客观内容。另一方面,作为一门理性的“科学”,它也没有让自己完全沉沦为一门直观的理论。因为,在将理性与直观联系起来的同时,区别于直观的综合,它也将自己追溯到纯粹的概念之上,基于主体自身的综合提出它的体系。这样,在获得了理性综合的客观内容的同时,它不仅将认识整合为体系,因而说明了科学,同时它也返回了理性,甚至以此还为我们整个人类的存在都确立了理性的规范。
五、结 论
尽管不仅与“直观”有关,并且也只有限制在直观的综合之内,形而上学才具有客观的内容,否则,它就会让我们的理性成为招致“背反”由而取消自身“理想”的“谬误”,但是,作为纯粹“概念”的科学,不超出“直观”,形而上学就既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理性会陷入自我取消,也无法说明它如何借助理性将知识建成了“体系”。故而,为了说明形而上学的这些问题与其体系化的建构就必须将其与具体的直观分离开来,转而在普遍的“概念”之上说明它的所在、问题与建构。当然,这样一来也会发现,虽然是一个知识的基础理论,但是它不只是一门说明如何将表象综合为体系的“科学”,同时也是一门呈现主体建构自身总体的“艺术”。易言之,它不只是说明如何将知识体系化的认知理论,也是道出主体是普遍的自我的理性启蒙。
利用一个认识元素的区分,《批判》不仅说明了作为纯粹“概念”的理性之所以陷入自我取消的矛盾是因为人们将其误认为了“直观”,为其主张了“独断”的运用,因而发展出了一个否定了纯粹理性认识能力的“纯粹理性规训”,同时,在“概念”自身的建构上,它也说明了知识系统性综合的所在、可能与架构。由此,它不仅本原地解释了“科学”的体系架构,也带出了形而上学的“艺术”本质。因为,将知识由“直观”摆渡到“概念”,也就将其由被动的表象修正为了自主的建构。并且,作为“纯粹理性的批判”,《批判》也不应只是一个知识的综合这个理性外在运用的说明,而应该是一个对理性自身的建构的澄清。事实上,作为一个“体系的艺术”,它不仅区分了直观的综合和概念的建构,还将二者作为元素结合在了同一个“体系”中。